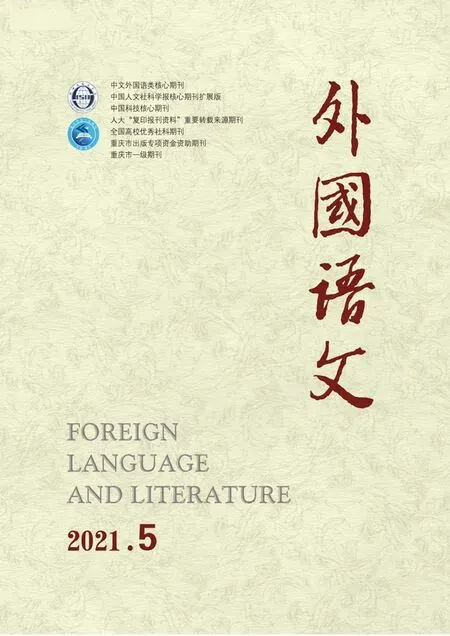论芥川龙之介对近代苏州的传统性身份建构
何荷 杨伟
(四川外国语大学 日语学院,重庆 400031)
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的特派员来到中国,回国后陆续写下了在近代日本人中国纪行中极具影响力的《中国游记》。对于临行前一直通过“诗歌典籍”“旅行指南”及谷崎润一郎、德富苏峰等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纪行来想象中国的芥川来说,1921年在中国的这次“越境”无疑是其动用了全身心的理性和感性,来追寻想象中灿烂的中华传统文明,重新审视“中国”这个巨大“他者”在近代化过程中之位相的珍贵体验;同时也是芥川发现苏州这个富于传统文化魅力之地域的良机。1921年5月10日,到访苏州的芥川龙之介在给下岛勋的明信片上写道:“别处暂且不提,但建议先生,苏州定要观赏一番。”(高慧勤 等,2005: 377)并在《新艺术家眼中的中国印象》一文中坦承:“在南方,苏州、杭州、南京、汉口等地我都去过了,最中意的还是苏州的景致。” (芥川龙之介,2007:164)而在《江南游记》之十九《寒山寺与虎丘》一节,芥川毫不吝啬对苏州的赞美:“苏州是个好地方。依我说的话,苏州是江南第一。苏州还没有像西湖那样染上美国味。”(芥川龙之介,2007:104)从中不难瞥见芥川对苏州的钟情与亲近。而从“苏州还没有像西湖那样染上美国味”的叙述中亦不难看出,芥川对苏州情有独钟是因为,其眼中的近代苏州较少受到近代浪潮的侵袭而保留着传统韵味。相较之下,对于吸引了无数近代日本人前往朝拜的上海,芥川则评价到“上海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就是西洋”(芥川龙之介,2007:31),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罪恶之都’”(芥川龙之介,2007:35)。
野村浩一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一书中指出:“《中国游记》是大正文学家芥川龙之介的文学作品。其中自有芥川的‘艺术’和韬晦。” (野村浩一,1981:97)然而,这一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究竟体现在何处,“芥川的‘艺术’和韬晦”又是什么,却鲜有人论及。本文试图从芥川龙之介《江南游记》中的苏州书写入手,通过考察芥川在书写苏州时的交通工具叙事策略,以及对同行导游岛津四十起的隐喻性形象塑造等,来分析芥川在文本苏州中,为实质上同样被裹挟于近代进程中的近代苏州所赋予的与上海之“西洋性”相区别的传统性身份。
1 驴背上的苏州
“驴刚把我驮在身上,就一溜烟地跑了起来。” (芥川龙之介,2007:88)
《江南游记》之十三《苏州城(上)》的第一段,芥川通过对“毛驴”这一交通工具的聚焦,展开了对驴背体验的介绍:
赶着驴若是行走在平坦的石板路上,也并非怎样的无法忍受。……苏州的桥之多,有“姑苏三百六十桥,吴门三百九十桥”之说……即便如此,在过桥时我也只看到了斑驳的白墙之间,有一条细细的运河水在闪闪发亮。(芥川龙之介,2007:89)
“石板路”“拱桥”“运河水”“白墙”以及“狭窄的街道”,无一不是苏州明信片上的经典符号。值得注意的是,芥川的苏州书写,并没有按照一般纪行文的惯例,在篇章开头首先交代自己的行程(尽管在第二段对行程也有所介绍,但那毋宁说更像是被从外部嵌入文中的插入性文字),而是将交通工具“毛驴”径直引入读者的视线,有意识地以“毛驴”作为苏州叙事的起点,不吝笔墨地反复描述初次骑驴的心境和体验。
其实,除了苏州的“毛驴”,热衷于交通工具书写的芥川,在《中国游记》中对其他各个城市的交通体验也均有不同程度的描写。比如,关于上海的人力车世界,他写道:“刚走出码头,几十个黄包车夫一下子就把我们围住了……中国的车夫,说其不洁本身就毫不夸张,而且放眼望去,无一不长相古怪。”(芥川龙之介,2007:5)而在杭州,他的描写是:“车把刚刚被拉起,车子就突然向狭窄的道路中冲去。”(芥川龙之介,2007:61)到了扬州,则成了:“我坐在沾满泥巴的黄包车上穿街过巷。”(芥川龙之介,2007:115)在镇江,则是:“我们在黄包车上摇晃着。”(芥川龙之介,2007:122)在南京,芥川“同往常一样坐上了黄包车”(芥川龙之介,2007:124),而到了北京,“我们坐上肮脏的黄包车来到了门前”(芥川龙之介,2007:145)。
显然,“我”的中国之行大多是在人力车上完成的。“不洁”“长相古怪”“沾满泥巴”“肮脏”等词语传递出“我”在中国并不愉快的人力车体验。然而,不同于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书写中的交通工具——“人力车”,芥川在文本苏州中为“我”安排的交通工具却是“毛驴”,以至于关于毛驴的叙述贯穿了芥川笔下作为文本空间的苏州书写。然而,在近代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人力车,是否真的没有出现在现实空间的苏州城呢?
游览江南时,芥川曾以池田桃川的《江南的名胜史迹》为指南。实际上,通过查阅这本出版于近一百年前的指南就会发现,在其介绍苏州的首页上,就有关于交通工具及价格的详细说明:“游览苏州可以利用毛驴、轿子或是游船。城外可以乘坐马车……人力车是按照里程计价,驴是按日算钱,每日一元。”(池田桃川,1928:1)可见,毛驴并不是苏州唯一的交通工具,马车、轿子、游船,以及人力车,都同样存在于近代苏州。值得一提的是,先于芥川游览苏州的谷崎润一郎貌似更钟情于游船,而其笔下在苏州的骑驴体验就不那么愉快了:“恐怕是昨天骑了一天的驴吧,臀部上擦破了皮,一刺一刺地疼。今天怎么也没精神再骑驴了。”(谷崎润一郎,2018:32)竹内逸对“骑驴”也不乏微词:“驴蹄子敲打地面的声音就好像是在敲打骑驴之人的脑门儿……我好像失去了知觉,胃啊、肠啊,都好像在体内微微地摇晃着。”(竹内逸, 1999:128-129)然而,芥川的整个苏州书写却完全没有提及其他交通方式,以至于很容易给读者一种错觉,似乎毛驴乃是苏州唯一的交通工具。这一方面或许是基于价格因素的考量(人力车比毛驴更贵),另一方面或许也是芥川在书写苏州时,对不同交通工具本身承载的不同文化想象进行考量之后的有意识选择,亦是芥川叙事策略的具体呈现。至于其在苏州的实际游览过程中是否真的只是乘坐了毛驴,而未使用其他交通工具,根据目前已知的资料来看,不啻是一个未知数。
关于近代苏州的交通工具,《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州(1895-1937)》一书做了详细考察:
伴随着苏州第一条马路的建设,马车于1897年在苏州首次亮相……人力车在苏州的诞生则是在1896年……人力车则常常被拿来与西方的“汽车文明”对比,并成为近代中国落后倒退与麻木不仁的标志;人力车夫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阶级压迫的典型代表。(柯必德,2014:74-78)
曾有学者这样论述芥川对近代中国人力车交通的态度:“中国第一瞥便遭遇了人力车夫,这使日本文化人对现实中国的认识大打折扣,在他们看来,中国车夫肮脏、无序、愚钝甚至有心智返祖化倾向。” (王升远,2013:22)可见,无论是西方舶来的马车,还是已然成为近代中国落后标志的人力车,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近代化的政治话语装置中。与之相对,“毛驴”这一交通工具,则具备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想象力。相较于马车、人力车的舶来身份及其出现在中国的短暂历史,毛驴无疑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土产。大凡熟悉中国古代诗词的读者便不难发现,毛驴作为交通工具,不但历史悠久,还颇得中国古代文人的青睐,无论是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的“细雨骑驴入剑门”,还是孟浩然踏雪寻梅时的“吾诗思在驴背上”,抑或是杜甫穷困潦倒时的“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再或是苏轼的“路长人困蹇驴嘶”,甚或是贾岛在驴背上思索“僧推月下门”与“僧敲月下门”的微妙,都与毛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驴背似乎驮起了古代诗人们的诗情和诗思,难怪钱钟书在他的《宋诗选注》中将毛驴定义为“诗人特有的坐骑”(钱钟书,1989:178)。由此可见,如毛驴这般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渊源的交通工具并不多见,以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似乎贯彻到了“驴背诗思”的体悟中,其中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想象可见一斑。而马车、人力车所引发的近代想象恰与毛驴催生的传统文化想象构成了一组鲜明的对比。众所周知,交通工具作为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并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气质。可以说,不同于引发近代文明想象的人力车交通,毛驴作为催生传统文化想象的触媒,成为彰显苏州传统性身份的隐喻性表征,让苏州的传统氛围跃然纸上,并且让近代苏州成了异于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扬州、镇江等城市的独特存在。

然而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苏州城并非仅有芥川书写的传统风物。众所周知,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苏州便被开为商埠,并由此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据《江南事情——扬子江富源》(1910年)一书有关苏州经济、贸易、交通状况的记载, 1899年到1908年的十年间,苏州的贸易总额翻了三倍;1908年沪宁铁路全线开通,强化了苏州与周边城市(上海、杭州、南京等)的经济网络;此外,苏伦纱厂、制丝会社、生生电灯会社等新式工厂拔地而起;商业银行、外汇银行等近代金融机构亦纷纷诞生。甚至有学者将彼时的苏州定义为一个现代性的城市:
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苏州城市空间的转型成为城市概念转换的一个缩影,它从一处赋有龙脉的祥瑞吉兆之意的超自然景观,转变为致力于商业和工业利润最大化的地区……苏州最终从天堂下落到一处空幻且难以捉摸之地,此地即现代性。(柯必德,2014:24-25)
毋庸置疑,与上海、杭州等其他中国城市一样,近代苏州也同样驱驰在近代化的道路上。比如,谷崎润一郎在《苏州纪行》小序中就有如下描写:“傍晚五时左右抵达阊门外的苏州火车站。坐上马车沿平坦的南北护城河大街前行一里半路程,日暮时分到达日本租界。”(谷崎润一郎,2018:29)“船的左岸有一座叫苏纶纱厂的工厂。” (谷崎润一郎,2018:35)然而,“火车站”“马车”“租界”“纱厂”等近代产物,却被芥川排除在了苏州书写之外。芥川的苏州书写有意避开了工业、商业、市场、金融等与近代化紧密关联的城市要素,选择性地对近代文明符号视而不见,故意忽略对苏州近代性的描述,并将其拒斥在苏州的形象谱系之外,仅把传统风物写进游记,促使读者形成对苏州传统性身份的单一性想象。可见,作为芥川文本的苏州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完全是与现实的苏州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基于实际游览体验所描绘的“实像”,而是一个被强化了传统意义的“虚像”,是一个被芥川赋予了“传统性”想象的文本空间。芥川深厚的汉学修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有关姑苏水乡的想象,无疑促进了这一“传统性”塑造的完成。而芥川为近代苏州赋予的这一“传统性”身份,恰与西洋上海的“现代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然,芥川对近代苏州的建构,并不仅限于驴背视角下的“黑瓦白墙”“小桥流水”等物理意义的空间堆砌,作为“文本的苏州”,其文学性逻辑,还体现在了芥川对导游岛津四十起的上海体验与苏州体验的差异化书写中。而这一对同行导游之中国体验的特别关注,恰为我们继续探讨文本苏州的传统性身份提供了另一种解码作用。
2 被作为隐喻的岛津四十起
岛津四十起原名岛津长次郎,是芥川中国之行的重要向导之一,1921年春带领芥川游览了上海、苏州、镇江、扬州等地。他1900年来到上海,1912年创办金风社,刊行杂志《上海消息》, 1913年起连续14年编写、修订《上海指南》,1926年发行俳句作品集《荒彫》,是上海内山书店文艺沙龙“文艺漫谈会”的成员,更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日本人会的知名出版人。佐藤春夫曾以岛津四十起为原型,创作了小说《老青年》。相较于芥川的初来乍到,岛津在中国生活多年,就中国经验而言,明显凌驾于芥川之上,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乃是作为“中国通”和向导带领芥川游览中国。关于岛津丰富的上海经验,芥川在《上海游记》中有颇多着墨:“我”常常踮着脚匆匆地循着四十起氏的足迹,“据四十起氏说,这一带街道以前曾经是城墙耸立的地方”(芥川龙之介,2007:14),“对于四十起氏来说,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感慨的罕见景色”(芥川龙之介,2007:15)。显然,“我”对岛津的上海经验十分认可。如果说“我”的中国认识尚处于一个从想象到现实过渡的阶段,那么岛津的中国则完成了从想象到现实的切换,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通”。然而笔者注意到,先行研究却几近无视了这样一位在上海日本人群体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存在地位的“中国通”。
芥川访华的两年前,中国爆发了以“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为口号的五四运动。在此背景之下,来到苏州的“我”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苏州强烈的排日氛围。当“我”和岛津四十起一同登上苏州天平山时,看到依山而建的亭壁上,随处写满了排日标语:“诸君,尔在快活之时,不可忘了三七二十一条”、“犬与日奴不得题壁”(芥川龙之介,2007:124)。排日标语中“犬与日奴不得题壁”一句给“我”和岛津所带来的不同冲击,值得玩味。《上海游记》之十二《西洋》一节,芥川在提到帝国主义的霸权空间—— “公共花园”时特意评论道:“外国人可以进去。中国人则一个都不让进。名之曰‘公共’,真是极尽了命名之妙。”(芥川龙之介,2007:29)前田爱在《都市空间中的日本文学》中论述道,芥川虽未直接点明,但此番评论显然是针对公共花园内“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语而发出的感慨,这句给中国人带来无尽耻辱的标语,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帝国主义罪恶的象征,铭刻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中(前田愛,1987:369)。关口安义认为:“‘犬与日奴不得题壁’的字句,是中国人对上海黄浦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抵抗……而将‘犬与日奴’这样反日情绪强烈的词句记录并发表出来,正体现了芥川作为一名人道主义者和新闻记者的情怀及才能。”(関口安義,1997:121)有趣的是,文本苏州中,紧跟着“犬与日奴不得题壁”的字句之后,芥川有意识地加括号描述了岛津四十起面对排日标语时的反应:“(话虽如此,岛津氏还是毫不在乎地题了一首层云派俳句。)”(芥川龙之介,2007:96)如果说“犬与日奴不得题壁”的字句,是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激烈抵抗,那么在芥川的苏州书写中,其为“岛津”这一角色所设置的“毫不在乎”的题壁行为,无疑彰显出该角色对于这一排日情绪的无视甚至挑衅。值得关注的是,芥川为这一题壁行为赋予的隐喻性意义并不仅限于对待“排日”态度的层面,其中折射出的还有岛津对于“日本人”这一民族身份所附带的身份特权的强烈意识。不难发现,上海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与苏州的“犬与日奴不得题壁”这两句标语,对于日本人岛津四十起来说,亦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前者将“中国人”与“狗”置于同一序列之中等而视之,并将二者同时拒绝在“极尽命名之妙”的“公共”花园之外,明显饱含着帝国主义的殖民暴力和对中国人的无尽侮辱。然而,身为日本人的岛津四十起,却可以自由出入于这一公共空间,拥有居高临下地审视与狗处于同一序列的中国人的俯视视线,彰显出远高于普通中国人的身份特权。但在苏州,充满抵抗意味的“犬与日奴不得题壁”,则剥夺了日本人“题壁”的权力,同时针锋相对地将“日本人”与“狗”置于同一话语层面。这无异于宣告,来到苏州的日本人岛津,丧失了在上海时所拥有的身份特权,而不得不置身于被拒绝、被俯视的境地之中。岛津看似“毫不在乎”,实则“非常在意”地试图用“题壁”这一不乏挑衅意味的行为,来挽回些许被称为“日奴”所失掉的自尊,捍卫身为日本人的尊严,掩饰内心遭遇身份特权丧失时的失落与无力。相较之下,“我”的民族身份则似乎被芥川有意识地模糊化,即便面对言辞激烈的排日标语,“我”也能冲破民族身份的制约,而始终用新闻记者般冷峻的视线,在一旁默默地观察岛津的表演。面对岛津的挑衅题诗,“我”虽未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在后文中芥川却花了大量笔墨细致描述了“我”处处与岛津没有缘由的针锋相对:“我一听这话,忽然大为恼火……岛津氏的无动于衷激起了我的满腔怒火。”(芥川龙之介,2007:103)在《天平与灵岩(下)》一节,芥川再次提及岛津题诗一事:“我不期然的回头一看,岛津氏竟毫不在意地摊开笔记本,记下他今天所得的俳句。” (芥川龙之介,2007:103)看到岛津试图将在天平山所题俳句记录下来,“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发酵已久的冲动,觉得“非得找碴儿吵一架” (芥川龙之介,2007:104)。有趣的是,一年后的1922年5月,芥川在寄给西村吉贞的明信片上,对岛津进行了一顿痛批:“四十起既不懂俳句,亦不解短歌。”(高慧勤 等,2005:441)这一激烈批评与芥川为“岛津”设定的天平山题壁这一情节之间的微妙关系,不得不说是耐人寻味的。
不难瞥见,芥川借“题壁”一事,为在上海和在苏州的“岛津”制造了相互对照的城市体验,彰显出日本人在上海与在苏州时的不同身份感和存在地位。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滋生出这种“对照”与“不同”的,则是近代上海与苏州的不同文化空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饱含对近代中国的侮辱与轻蔑,而这样一句令中国人倍感耻辱的标语能够在上海这一都市空间中(尽管是在租界)堂而皇之地存在,这本身就折射出了近代上海被西洋侵蚀,无意抵抗“西洋”,“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就是西洋”(芥川龙之介,2007:31)的城市面影。上海之“西洋”虽然有着“文明”“秩序”的面向,但同时也意味着侵略、殖民、暴力。当芥川将上海定义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罪恶之都’”(芥川龙之介,2007:35)时,充斥其心中的恐怕不乏对上海之“西洋”的厌恶与反感。相反,“犬与日奴不得题壁”这句满含爱国主义情怀的标语,则生成于尚且保有传统文化风貌的苏州,而与芥川眼中近代苏州之为传统地域的内在理路相吻合。可以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与“犬与日奴不得题壁”这两句标语在岛津身上发生的不同化学反应,折射出岛津在上海与苏州时相对照的城市体验,也映照出近代上海与苏州之不同的城市文化氛围。
值得关注的是,芥川对岛津之上海体验与苏州体验的对照书写并未止步于此。在苏州书写中,芥川将岛津描绘成了一个已然习得了上海话的“上海通”。岛津在游访苏州时试图用上海话与当地人沟通。不过,“岛津氏的上海话能够让对方听懂,遗憾的是对方的苏州话好像很难让岛津氏听懂。岛津氏在几个回合的问答之后,最终还是断了继续交涉的念头”(芥川龙之介,2007:103)。关于苏州和上海两地的方言,《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指出:“上海话的权威地位是民国之后才逐步确立起来的。在清代上海话的地位还远逊于苏州。” (周振鹤 等,1986: 68)可见,虽如大众所知,上海话与苏州方言同属吴语系,然而两者并非完全相同,且相较之下,苏州方言似乎更具历史地位。方言作为多元化地域文化的载体,体现并反映出不同区域的文化和习俗,而由苏州方言营造出的文化氛围想必也给芥川带来了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文化体验。
在此,笔者不由得联想到许纪霖的《城市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一书。他在该书中用方言对上海人进行了定义:
什么是上海人?在近代,所谓的上海人是有特定含义的,特指能讲上海官话……会讲上海话的才是真正的上海人……为什么上海话如此高傲,自以为高人一等?这与上海人骨子里自认为自己是文明人有关。(许纪霖 等,2011:6.)
根据许纪霖的定义,上海人之所以是上海人,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是否会说上海话。并且,会说上海话的上海人认为自己是“文明人”。由此看来,在芥川的苏州书写中,久居上海,并学会了上海话的岛津可以说已经完全融入了上海,被上海所接纳,成为具有“文明人”标签的“上海人”般的存在,甚至是可以自由进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共花园,比普通上海人更具特权的“特殊上海人”。而用上海话与当地人沟通的岛津,似乎也通过“上海话”这一内含着“文明”意味的方言,彰显出自己文明人的身份,并在置身较少受到近代浪潮侵蚀,尚且保留着传统风貌的苏州时,获得一种身为文明人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值得关注的是,通过这一有关方言的情节设定,芥川也在读者脑海中勾勒出一幅上海话/苏州话的对比构图,进而为上海和苏州构筑出了象征着近代文明与前近代之传统的言语空间。
然而,芥川笔下这位已然习得了内含着“文明”意味的上海话的文明人,在苏州的游览却显得无所适从。梳理苏州书写中芥川为岛津四十起打造的苏州体验,会发现其中充满了挫败、徒劳、疏离、迷失:虽然在上海拥有高于普通中国人的话语权(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但在苏州却被剥夺了这一话语权(犬与日奴不得题壁);不说北方官话,而用象征着“文明人”的上海话与苏州人沟通却处处受阻;骑驴“得意洋洋”最后却狼狈摔下;身为“中国通”(实为“上海通”)做苏州向导却在苏州迷路,最终遭到“我”的责备并与“我”大吵一架。“我”心中在苏州之行伊始便隐隐存在的违和感,最终酝酿并发酵成了愤怒:“彼此都给对方添麻烦,如果做向导的不熟悉当地情况的话……”(芥川龙之介,2007:104)可以说“我”的这句带有怒火的指责,一方面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岛津作为“中国通”之不通的失格,暗含着对其浅薄的中国经验的反感,另一方面也点出了一个事实:这位“上海通”并不理解苏州,他的上海经验似乎并不适用于尚且保留着传统风味的苏州。之后,二人又陷入了尴尬的对峙:“我们在寂静的桑田前,两个人都紧紧地绷着脸,一直那样站着。”(芥川龙之介,2007:104)此时的岛津俨然成了一个苏州的“他者”,尴尬地注视着苏州。周作人在《“支那通”之不通》一文中指出:“日本的‘支那通’见了一地方的情形,一个人的事件,便以为全支那都是如此,妄下论断,即使别无恶意,也已荒谬可笑,足以证明‘支那通’之多不通了。”(周作人,1998:69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芥川在文本苏州中塑造的久居上海的岛津,同样是一个未能逃脱上海经验之影响的“中国通”:即便在苏州失去了在上海时的身份特权,却仍然使用上海话与苏州人沟通,习惯性地用自己的上海经验来指导苏州游览。但上海只是上海,并不能代表中国。所以,他所深谙的摩登上海的游戏规则,也不适用于苏州这样一个传统的江南地区。
然而,事实上,现实中的岛津四十起对苏州并非一无所知。比如,在1926年出版的《第一短诗集》中,就收录了岛津四十起撰写的《小传》,从中可以管窥到他频繁造访苏州的事实:“明治33年来到上海生活,起初常在包里装上千金丹、宝丹等药品,到苏州、杭州城乡一带兜售,做点生意。大正元年开始从事出版业。”(西村陽吉,1926:58)作为旁证,在佐藤春夫以岛津四十起为原型所写的《老青年》(和田博文,2014:339)中也有类似描述,说他“常到上海附近的乡镇做药品生意,主要售卖宝丹、千金丹一类药品”(佐藤春夫,1957:556)。显然,对于岛津而言,苏州并不是陌生之地,而是长顾之所,理应相当熟稔。此外,如前所述,1913年至1927年,岛津四十起曾连续14年编写、修订了《上海指南》。14年间,《上海指南》共发行11版,而1913年发行的初版,便专设有“苏州指南”的栏目,对苏州的交通、住宿以及景点进行了介绍。到1921年3月,第九版《上海指南》发行时,不仅配有《苏州游览地图》,选取介绍的苏州景点数量大增,且景点说明也格外详细。有趣的是,岛津带领芥川游访苏州的时间点,恰恰是在第九版《上海指南》发行两个月后的1921年5月。对比芥川的苏州书写不难发现,《江南游记》中涉及的苏州景点与《上海指南》中选取介绍的苏州景点有着高度一致性。由此大致可以推断,岛津的苏州经验并不贫乏,而芥川的苏州游览也与上海游览一样,乃是岛津基于自己丰富的中国经验而精心安排的结果。然而,相较于岛津的“上海通”形象,芥川却在文本苏州中塑造了一个骑驴摔下、沟通受阻、丧失身份特权,身为导游却迷失在苏州的“岛津”形象。“上海”似乎成了一种潜在的思维方式而规定着岛津的苏州认识,即便置身苏州,也未能冲破上海的规定性,用上海的语言与苏州人沟通。然而,芥川眼中的近代苏州,尚且保有传统风韵,而与“西洋”的上海有着全然不同的城市逻辑,不能被“上海”逻辑所简单粗暴地收编。试图用上海逻辑来理解苏州的岛津,最终在苏州收获的也只能是一份“狼狈不堪”。毋宁说,芥川对岛津之上海体验与苏州体验的对照书写,恰恰折射了两座城市的性格差异。想来,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的特派员来到中国的芥川龙之介,原本将自己的中国见闻记录在游记中已然足矣,但在文本苏州中,芥川却如此这般令人意外地耗费大量笔墨,不乏文学性地、有意识地为岛津构造了与其上海体验相对照的苏州体验。这一对岛津之上海经验与苏州体验的差异化叙述,配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与“犬与日奴不得题壁”映照出的“西洋”与“传统”的不同城市文化氛围,以及上海话与苏州话构筑起的象征着文明与传统的言语空间,强化并放大了芥川笔下近代苏州与上海的不同属性,有力地凸显出近代苏州不同于魔都上海而富有的传统风韵。
3 “西洋”的上海与“传统”的苏州
芥川到访苏州的大正年间,经历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日本已基本完成了近代国家的变革。“上海”作为明治时期距离日本最近的“西洋”,曾吸引了无数日本人前来游览,而在进入大正年间,则逐渐失去了“西洋之窗”的魅力。《中国游记》中,芥川不止一次地将上海定义为“罪恶的都市”“恶俗的西洋”,而在到访苏州时,却产生了一种与西洋化的上海大相径庭的“姑苏城的优美的心境”(芥川龙之介,2007:89)。不难发现,对于芥川来说,上海的“西洋”并非吸引其前往中国的焦点,毋宁说古典中国才是其渴望的诗和远方。
毋庸置疑,近代苏州的文化身份自然应该是多元的,但芥川的苏州书写却摒弃了苏州城原本存在的近代文明产物,消解了苏州的近代性,而对苏州的传统性身份进行了隐喻性的强化甚至建构。在苏州叙事的起点,芥川用“毛驴”这一独特的交通工具语言,编码了苏州城的传统空间逻辑;接着通过“驴背”视角对“苏州的水”“拱桥”“黑瓦白墙”等苏州传统文化符号的堆砌,有意识地保留甚至扩大了其形象谱系中的传统文明特质。同时通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与“犬与日奴不得题壁”的对照叙述,以及同行者岛津四十起之上海体验与苏州体验的差异化书写等,将掩映于文本之内的苏州的传统性身份凸显出来,并让浪漫、诗意的姑苏水乡生出了与上海所彰显的西洋性、殖民性相对峙的意义。可以说,芥川笔下的“文本苏州”拥有着历史与传统性的力量。这一方面是因为苏州作为中国典型的江南水乡,其悠久的历史沿革和众多历史古迹所构成的强大传统文化逻辑,促使芥川对其传统意义进行强化叙述,另一方面,也是源于芥川对古典中国难以割舍的热情与渴望。回国后,当芥川书写苏州时,并没有拘泥于一年前真实的苏州体验,而是以是否与“想象中的苏州”相吻合作为取舍的标准。无疑,内含于“毛驴”“拱桥”“黑瓦”“白墙”中的苏州城市气质恰恰迎合了芥川的想象,从而充当了这一想象的载体。难得的是,芥川心中的传统苏州,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的轨迹中面对近代化的冲击时,相较于其他城市,有幸保存了更多的传统文明。对于厌恶资本主义的凡俗世界并崇尚“诗的精神”的芥川来说,苏州作为具有更为强大的江南传统文化性格的水乡,让其倍感倾心。《中国游记》中,芥川对苏州的偏爱跃然纸上,即便在书写扬州、南京等城市的过程中,芥川仍然常常回忆苏州之行,并不止一次为苏州书写添加注脚,续写结局。“毛驴”“拱桥”“流水”“黑瓦白墙”似乎冲破了汹涌的近代浪潮,构成了一个意蕴深厚的文本苏州。这文本中渗透着芥川对传统中国、传统东方文化的无限想象和深情挽留,并投射出芥川对东方和西方、传统和近代的迥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