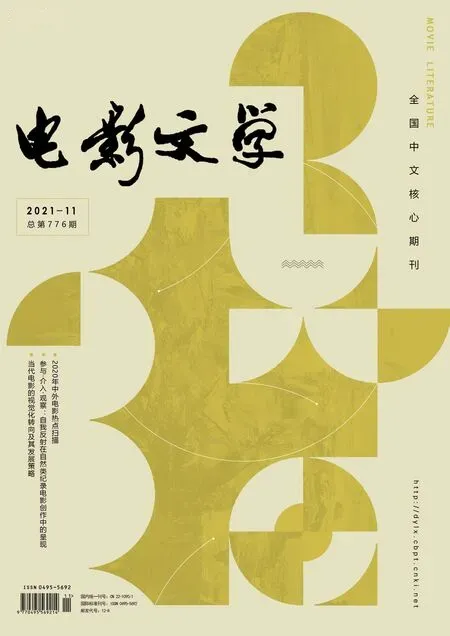唐纳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
沈艾娥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重庆 401120)
翻开早期中国电影的相关史料,唐纳在早期中国影坛是一个知名的进步人士,他积极参与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电影抗战事业:发表大量电影评论文章及欧美电影译文,打响了反击“软性电影”理论的第一枪;加入艺华、电通等影业公司,不仅担任导演助理和编剧,还主演电影,为电影创作主题曲;主编多部电影期刊,其中,由他主编的《抗战电影》率先在电影期刊界扛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加入国防电影组织等爱国电影团体,积极开展进步电影活动。
一、对“软性电影”展开批评的第一人
唐纳(1914—1988),苏州人,原名马继宗、马骥良、马季良,笔名罗平、陈陀、蒋旂、安尼等,其中,“唐纳”这一笔名最为知名。1933年,因出演左翼话剧而被追捕的唐纳到上海避乱,时任《晨报》副刊“每日电影”主编的姚苏凤,邀约唐纳撰写电影评论,于是唐纳开始发表大量电影评论文章及欧美电影译文。1933—1935年期间,他的笔名频繁地出现在《晨报·每日电影》《申报·电影专刊》《新闻报·艺海》《中华日报·银座》《大晚报·剪影》等报纸副刊上。
“在左翼影评人和进步人士中,唐纳是对‘软性电影’展开批评的第一人。”早在1933年,刘呐鸥、黄嘉谟等人率先提出“软性电影”主张,唐纳旗帜鲜明地予以反驳, 1934年6月15日至27日《晨报》副刊“每日电影”上刊载唐纳的长篇影论《清算软性电影论》,反击“软性电影”论。首先,唐纳反对“电影是软片制成的,所以它是软性的”这种论调,批评其为“硬性的武断”,也认为:“软性电影”所提倡的是“软性志趣”,批评“软性电影”是不折不扣地包上糖衣的麻醉品。他提倡电影要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认为:“艺术是客观的流动着的现实的反映,电影是艺术的一部门……在各个艺术部门中,电影是最有利于具体地反映客观的真实,同时,更因为它的社会机能的广大,而更需要正确地表现客观的真实。”他甚至将电影所表现的社会真实程度视为正确评价一部影片的基准:“对于一部电影作品的正确评价,应该是用在电影艺术的形象里所表现出来的客观现实——社会的真实程度为基准的。”在强调电影需要正确地反映客观真实的同时,唐纳也强调电影的思想性,他在另一篇文章《论电影的启发性与中国电影》中写道:“电影不独传达情感,同时还传达思想,所给予人们的不是单纯的慰藉等,而且是爱的慰藉,生的感激,肉的陶醉,对资本体制的愤怒,殖民地奴隶的悲哀,胜利的喜乐等的思想。没有了这些喜乐悲哀,电影将不成为其消遣品;假如在喜乐悲哀的背后的思想没有了,电影将不成其为精神的食粮。”
与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左翼影评人比较关注电影意识形态批评而忽略电影艺术特性有所不同,唐纳并不否认电影的艺术性。同时,唐纳发表了不少关于电影艺术特性研究的文章,他强调电影的表现方法与艺术技巧,认为“电影技巧正是跟其他的艺术作品一样,乃是决定于内容”,提出“用动作来思维与说明,开末拉的努力和Montage的构成”是电影独特的艺术表现元素,他赞赏电影《互助》中的表现形式,认为“因为这大画面的连续,由于他的特有的Montage之有机的编辑,显示出他伟大的迫力,不仅是刺激着你们的视觉,更深深地刺激着你的心窍。”他强调蒙太奇对于电影的艺术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认为影片《同命鸳鸯》的成功是“懂得电影的Montage的运用者的胜利”。除了强调蒙太奇对电影表现力的重要性外,唐纳还强调声音与画面对电影艺术表现力的作用。他赞美影片《亡命者》中的音乐运用得“是非常合理的,没有一些牵强的地方”,认为影片《红酒金刀》“音响构成与画面构图的成就是极大地帮助了剧的演出”,评价影片《莫斯哥奇情案》“在开末拉的角度上善用仰角俯角,而特写的多用也是一特色,但毫不令人厌倦”等。此外,他还意识到电影中地方色彩的重要性:“电影剧本中的地方色彩与空气之描绘,是与剧情之构造、个性之刻画、境遇之安排等一样重要的。”
总之,唐纳从强调电影思想性,将电影所表现的社会真实程度视为正确评价一部影片的基准,来反击“软性电影”论的同时,也重视电影的艺术性。
二、参与艺华、电通及明星等电影公司工作
“唐纳确是多才多艺,影评之外更从事剧本创作和影片摄制事宜。”1934年秋,唐纳进入上海艺华影业公司工作,担任编剧及宣传相关工作。事实上,艺华影业公司成立初期富有鲜明的左翼色彩,就已引发了国民党当局的惶恐,1933年11月10日上午9时许,“特务机构蓝衣社派人捣毁艺华公司以示警戒”。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压力,艺华影业公司在制片策略上进行了微妙的调整,但于1935年依然出品了《人之初》《新婚的前夜》《逃亡》等经典抗战影片。唐纳参与了影片《逃亡》的制作,担任该片导演阳翰笙的助理,并与聂耳一起为该片创作主题曲《自卫歌》及《塞外村女》,唐纳作词,聂耳作曲。在《塞外村女》歌词中,唐纳描绘了一幅幅民生苦难图:“采了蘑菇把磨推,头昏眼花身又累,有钱人家团团坐,羊羔美酒笑颜开。寒鸦飞过天色灰,老爹上城卖粉归,鹅毛雪片朝身落,破棉袄渍透穷人泪。铺面寒风阵阵吹,几行寒雁几行泪,指望今年收获好,够缴还租来免祸灾。”而在《自卫歌》歌词中,唐纳抒发了自己对民族抗战的满腔热忱:“拿起一切拿得到的枪,上前!我们没有了豆米;拿起一切拿得到的子弹,上前!我们没有了土地。誓为民族牺牲,齐向强权奋斗,我们要决心救自己……”正是在共同的创作中,唐纳与聂耳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在给聂耳的悼念文章中写道:“一种率真的挚诚的态度,一种旋律的飞腾的热情,很快在我的心头烙上了深深的印……永远不会在我记忆里遗忘你的影子,你,我最忠诚最亲切的朋友。”
然而,唐纳对待电影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随着艺华影业公司的改组而不能在该公司得以持续。1935年春,艺华影业公司的“左翼”主创田汉、阳翰笙等相继被捕,不久,唐纳也离开艺华。1935年下半年,黄嘉谟、刘呐鸥等“软性电影”论者进入艺华,掌控了该公司的创作与制片大权。从这开始,艺华影业公司拍摄的不少影片,如《花烛之夜》《小姊妹》《喜临门》《白宝图》等,引发了左翼电影人士的强烈不满,其中的《化身姑娘》更被认为是“软性电影”的代表作。1936年11月22日,唐纳与凌鹤、尘无、汤修梅等32人联名,先后在上海《民报》副刊“影谭”,《申报》《大晚报》等报刊上两次向艺华影业公司发表公开信——《敬告艺华公司》《再为艺华公司进一言》,信中指出“艺华公司以过去的努力,曾经表现过不少光辉的成绩,但他们目前所走的却是一条十分错误的路”,并警示艺华影业公司“不要悍然负起‘民族罪人’的十字架,来贻害社会,毁灭自己,明白自己责任的重大,为推进电影文化运动而努力”。
离开艺华影业公司之后的唐纳,转而进入电通影片公司,并主演了该公司于1935年上映的影片《都市风光》。该片以音乐戏剧的方式把真实的生活和大胆的夸张结合起来,展现了小市民阶层人物的狭隘和愚昧,反映出旧中国大都市畸形的社会现实。唐纳在片中主演了无聊的穷知识分子李梦华。1935年底,电通影片公司停办,“其出品号称前进,乃为影业中后起之秀,顾以国产影业之衰落,事实上支持不易,经几次之艰难险阻,迄今卒以结束闻”,唐纳也于1935年底离开电通。
1935年10月,“明星公司重建编剧科,聘欧阳予倩刘呐鸥黄天始诸先生担任编剧职务”。1936年唐纳也加入明星公司,“七月一日起成了明星公司二厂的编剧员”。刘呐鸥、黄天始等作为“软性电影”论者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曾与唐纳等为代表的左翼电影人士就“软硬电影”之争展开过激烈讨论。1934年6月15日至27日,唐纳在《晨报》副刊“每日电影”上发表长篇影论《清算软性电影论》,对黄嘉谟、刘呐鸥等人予以指名道姓地批驳——“嘉谟先生所要求的只是低级趣味而已”;“他(刘呐鸥)在‘中国电影描写的深度问题’‘与关于作者的态度’一文中在艺术的香气的烟雾下进行了对于新生电影的虐害”。电影观点的不一致显然会影响到彼此的共事。进入明星影片公司编剧部的唐纳,“并没有为明星编过剧本,但他为明星看外来的剧本,和修改外来的剧本,在这上面的功绩是不可泯灭的”。针对当时中国电影界为了商业利润而讲求快制作的现象,唐纳予以批驳,认为“‘慢’在营业方面说是‘过’,可是,纯在艺术方面,也许是‘功’”,并号召“在中国电影事业极度险厄的目前,每一片制作者应当尽可能地把自己的作品赶快完成是不错的,但是,每一个制作者还需要对于自己的作品抱一个严肃的态度,和提高技术水准的这一稿雄心,向全世界千万人群中去建立中国电影的信誉”!1936年7月,明星影片公司正进行大量的人员扩张,准备加快电影制作,显然,唐纳的电影“慢”制作主张,未能与明星影片公司的目标保持一致。“明星公司中无论任何一人对于这一次‘扩充’有较严重的认识,以后在制作工程上所万万要不得是‘片以慢高贵’主义”。1936年年底,“明星编剧科,自欧阳予倩辞去主任后,姚莘农、卢敦、唐纳等,均有共同进退之意”。不久,在明星影片公司工作仅几个月的唐纳,也随后辞职。
三、编辑多部电影期刊
参与电影公司工作的同时,唐纳还主编了多部电影刊物,其左翼电影观念也体现在了他所编辑的电影期刊之中。1935年1月1日创刊于上海的半月刊《文艺电影》,由凌鹤主编、唐纳等编辑,文艺电影社发行。该刊“为文学、电影、漫画、戏剧各艺术部门之综合刊物”,对电影界、文坛消息均较为关注,对于其中的不良现象也多加批评,典型如漫画《脸子主义的明星制度》,揭露了电影界中污秽不堪的淫乱现象及各种潜规则,具有一定的左翼倾向。
1935年5月,为配合电通影片公司的宣传和发行,唐纳、孙师毅、袁牧之、许幸之、司徒慧敏轮流编辑《电通半月画报》。唐纳在该刊第一期中呼吁电影制作者们“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解释世界,而且要变革世界”,并予以忠告——“只抓住现在,变成个庸俗的功利主义者。把握着时代的过程,世界流变的法则,才能跳出命定论的圈套而推动时代,变革世界”。唐纳的这一主张,与他一直关注社会现实,重视电影的思想性启发性是一脉相承的。
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丁君匋为主创之一。“经友人丁君匋推荐,唐纳主编上海《大公报》‘戏剧与电影’周刊。”该刊为戏剧与电影方面的综合性刊物,唐纳身为主编,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影评文章,如1937年4月24日的《〈同命鸳鸯〉的蒙太奇》,1937年3月6日的《革命情侣》,1937年6月5日的《关于〈新土〉》等。不久,以《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大公戏剧电影读者会正式成立。丁君匋任理事会理事长,唐纳任总干事,他们“在自己所主持的‘《大公报·戏剧与电影》读者会’召集各剧团作川灾筹款公演”。1937年7月25日至27日三日间在蓬莱大戏院,“大公戏剧电影读者会这团体,主办赈济各省灾区联合公演,参加者有海上各小规模剧团”。
1937年上海沦陷,马季良随《大公报》至武汉,任该报外事记者。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由张道藩任总主席,领导行礼毕,报告组织意义,大意谓,当此抗战时期,每国国民均应运行其本能,为抗敌前途努力,电影界应利用电影艺术,担负宣传工作,为欲集中力量,乃发起组织,作共同的奋斗云”。唐纳等七十一人为该会第一届理事,该协会的会刊《抗战电影》则由唐纳一人主编。
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唐纳又为进步报纸《商务日报》主编《每周影剧》,茅盾、冯亦代、瞿白音等都为之撰稿。在该刊的“每周闲话”专栏中,唐纳以散文、小品形式对影剧坛中的不良倾向提出了批评。
四、开展进步的电影活动
唐纳的进步电影观与其电影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早在1932年,时年18岁的唐纳便加入了地下共青团,在苏州多地出演左翼话剧《工厂夜景》《活路》等。1933年来到上海后,唐纳加入了左翼戏剧家联盟。进入电通电影公司后,唐纳不仅从事编剧宣传等工作,还在电影期刊上大声呼吁电影制作者们,“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解释世界,而且要变革世界”,并告诫他们不要“只抓住现在,变成庸俗的功利主义者”。
因频繁参加进步电影活动,1935年6月20日,上海市社会局呈报“抄共党在电影界活动情况”给市长吴铁城,要求“严加取缔以戢反动,而肃乱源”, 并列出一份“左倾电影从业员”名单,共计16人,其中就包括唐纳。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唐纳前进的步伐。
1936年8月9日,“国防电影的制作问题”座谈会在上海南京路冠生园酒家举行,唐纳、尘无、凌鹤、沈西苓、郑君里等二三十人参加。“这次座谈的结果,得到关于‘国防电影’具体办法,多方面的可以进行。”唐纳对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36年四年间的中国电影进行概述的基础上,提出“四年来民族危机非惟没有减灭,而且更严重到了千钧一发,每一个进步的电影制作者,都应该认识并担负起在自己领域内所应负的责任,由混乱重行趋行统一,由三反归并为一反,向着一个新的正确的中心:‘反帝’”!他还号召:“中国电影批评者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尽量提倡摄制些什么样的抗战电影,和怎样去摄制它们,以作为中国电影制作家们的一种参考,也可以说是一种鼓励。”唐纳不仅注重国防电影的主题及其思想,对国防电影的艺术技巧也同样重视,他认为:“为了要使我们的作品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的拥护,为了要使我们的作品更能燃烧起张大的群众的心头的火焰,‘为什么’的问题之外,‘如何写’的问题也该是值得每一个制作者所特别注意的呵!”
1936年,唐纳为明星影片公司创作歌曲《明星之歌》,明确表达出“要挽救人类的厄运”“和长夜的黑暗斗争,要引导千万的同胞,向光明迈进”。歌词慷慨激昂振奋人心,为明星影片公司看重,1936年7月明星公司重组后准备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招待会,“定在那天盛会开幕时各部人员手执火炬高唱《明星之歌》”。
离开明星电影公司后,唐纳开始进行剧本创作。“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从事编写历史剧《陈圆圆》的舞台剧本。”1937年上海沦陷,唐纳随《大公报》来到武汉,创作话剧《中国万岁》,轰动武汉三镇,该剧后经重庆同行修改,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排演,享誉山城,随后 “中国万岁剧团”成立。“中国万岁剧团,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的一个艺术单位,和中国电影制片厂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个团体。”此后,唐纳将大部分精力放在话剧创作及报刊事业上,逐渐淡出电影领域。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正遭逢战争浩劫,中国电影也荆棘塞途,但唐纳始终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将目光投向人类的命运、世界的改造和人性的觉醒,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喜欢‘中庸之道’,凡我所认为‘是’的,我必偏向它。我不爱‘公正’的‘打圆场’,但愿意为了‘真’而不客气地说老实话。”无论是他撰写的影评,他在电影公司所从事的工作,还是他所编辑的电影期刊,或是他开展的电影活动,他都直面深重的民族灾难,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抗战事业做出了不容小觑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