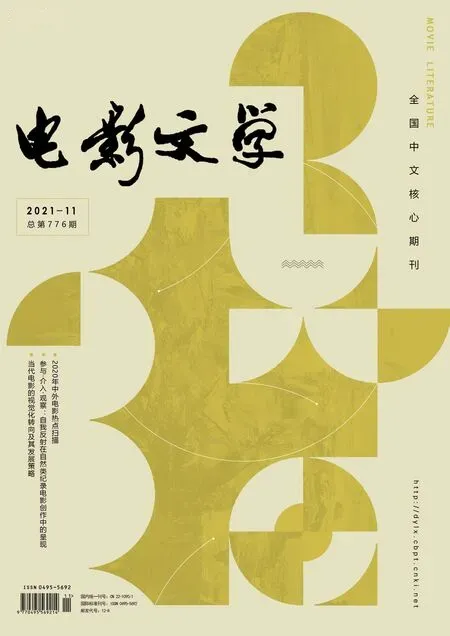底层书写与空间政治:当下国产电影中的工厂叙事
年 悦
(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天津 300387)
回顾中国电影历史,以工业题材尤其聚焦工人群体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影片可谓数目繁多。新中国成立之际,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表现工人阶级的影片《桥》(1949)。此后,以天津本土话剧剧本改编而成的影片《六号门》(1952)引起了较大反响。这部影片以天津码头工人胡二一家的遭遇揭示工人阶级的普遍命运及其成长过程。影片的主要演员由熟谙工人运动斗争艰苦的真实的天津工人扮演,在塑造坚毅与智慧并存的工人形象方面尤为突出。继影片《六号门》之后,各大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批旨在弘扬集体主义精神的工业题材影片,如《伟大的起点》(1954)、《上海姑娘》(1958)、《黄宝妹》(1958)《换了人间》(1959)、《春满人间》(1959)、《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1960)等。在“大跃进”运动中纷纷筹建的地方电影制片厂如天津电影制片厂甫一成立就计划拍摄《工人亦生产,学生亦工人》《为钢而战》《土法炼钢》《张士珍》《穆成锐》等工业题材新闻纪录片与人物传记片。
如果说“新中国”工业题材影像不断书写着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体性,那么“新时期”工业题材电影诸如《乔厂长上任记》(1980)、《血,总是热的》(1983)、《二十年后再相会》(1984)等则从改革视角呼应着变革时代新的意识形态诉求。进入新世纪以来,国产电影创作中涌现了很多以工人群体为主角、以工厂或厂区为主要叙事空间的作品,形成了颇为值得关注的创作现象,如《二十四城记》(2009)、《钢的琴》(2011)、《黑处有什么》(2016)、《八月》(2016)、《暴雪将至》(2017)、《少年巴比伦》(2017)、《六人晚餐》(2017)、《引爆者》(2017)、《暴裂无声》(2018)、《地久天长》(2019)等。这些影片与历史上的工业题材电影相比,塑造了怎样的工人形象?其所设置的工厂空间发挥着怎样的叙事功能?这些工厂叙事提供了怎样的历史想象与现实表征?在此基础上,如何界定和解读当下国产电影工厂叙事的意义是值得进一步展开的问题。
一、双重群像:国企职工与“新工人”
当下国产电影创作中所塑造的工人群体形象可以概括为两种主要类型:其一是《钢的琴》《八月》《暴雪将至》《少年巴比伦》《六人晚餐》等影片所刻画的国企改革历史进程中的职工群像;另一种则是《暴裂无声》《引爆者》等影片所描绘的当前现代化、全球化语境下的“新工人”群像。
其中,第一种群像可以概括为历史群像,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背景下,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历史中的工人群像。国企职工在社会改革进程中由于其技术工种、知识结构等诸多方面不适应全球化大生产而被甩出社会体制结构之外。这一庞大社会群体跌落后缺乏稳定的社会保障和社会地位,他们的精神面貌与现实处境成为近年来很多国产电影试图记录与刻画的对象。例如,在贾樟柯导演的影片《二十四城记》中,以个体陈述的方式塑造了420厂工人及其子女等多位性格迥异的国企工人形象,呈现了他们在历史转折中生活方式、情感经验与代际认同等方面的矛盾,420工厂空间隐藏的正是历史的一种“断裂”。在张猛执导的影片《钢的琴》中,以陈桂林、淑娴、王抗美、胖子和快手等为代表的国企职工在工厂转轨后下岗,为谋生而落入社会底层。陈桂林为争夺女儿抚养权而想打造一架钢琴,这一想法使得陈桂林及其分散在社会各个行业的工友重新回到“钢”厂,他们以新的个人化需求和生产方式来制作“钢琴”。影片在“集体”与“个人”的强烈对比下触摸底层工人的历史处境与现实命运。
相国强执导的影片《少年巴比伦》则重构了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工人群像,如小路父亲、小噘嘴、牛魔王、长脚等工人形象作为时代的缩影,镶嵌在下岗潮、三班倒、反应釜爆炸、甲醛超标环境中作业的工厂生活中。这一国企工人群体不但物质上窘迫,精神上也常常陷入困境,他们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原有的价值观崩塌,新的价值观尚未建立。影片着力描摹了国企工人在时代转折之中的无力感,以及他们苦中作乐的荒诞感。
除了塑造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中的工人群像以外,当下国产电影还塑造了第二种工人群像——“新工人”形象,即伴随国家土地政策从农村土地分离出来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形象。正如黄宗智所论:“今天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既非传统意义的产业工人,也非传统意义的农民,而是半工半农、亦工亦农的农业户籍人员。他们大多处于劳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外,被认作为临时性的‘劳务’人员,处于‘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之中。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真正的中产阶级差别悬殊,两者几乎属于两个不同世界。”
当下新生代导演十分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他们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在一种鲜明的底层书写与空间政治中塑造了“新工人”群像,并充分汲取好莱坞电影、韩国犯罪片、香港电影等类型电影经验,构成了一种痛感现实主义风格。例如,忻钰坤执导的影片《暴裂无声》中,男主人公煤矿工人张保民年轻时因打架咬伤舌头而无法发声,为了寻找失踪儿子而遭受煤矿老板昌万年的迫害。张保民的无法发声与生存绝境代表着集体失语的底层人群和沉默的大多数。再如常征导演的影片《引爆者》试图呈现当前现代化、全球化语境下“新工人”群体在商业化大潮中被迫离开土地,利益被损害的遭遇。影片中煤矿爆破工人赵旭东侥幸躲过一次矿难,却不幸被卷入煤矿主之间的阴谋。当下国产电影中塑造的“新工人”群像作为历史转型时期的复杂文化症候,凸显了对当下中国社会伦理秩序的深刻反思。
二、工厂空间想象的多重面目
在当下国产电影中,上述两种工人群像所生存的工厂空间的营造通常包含破旧厂房、高耸烟囱、杂乱昏暗的生产车间、生锈机床与工具等标志性场景,既集合了工人们单调、困顿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体验,也指称着历史与现实的变迁。不仅如此,工厂空间还与私人空间高度重合,依托工厂而存在的厂区建筑设施如筒子楼、球场、舞厅是具有集体主义时代特色的生活空间。上述工厂空间往往以多重面目出现,既是一种叙事空间,又饱含着更深层的文化意涵,是创作者审美意图的外化。
工厂空间第一重面目是充满温情的怀旧场域,工厂作为个体经验的承载空间而被笼罩着记忆的柔光。在当下国产电影工厂叙事中,导演往往将故事场景设定在工业城镇里的大工厂与工人居住的厂区大院之中,围绕工厂建立了师徒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等社会关系网络。这种较为封闭的空间形态充满着对机械工业时代温情的留恋,也经常作为影片的怀旧场域。怀旧作为一种心理现象与文化现象,是对于曾经拥有而如今失去的家园的向往。“怀旧不仅是对一段已经逝去的时间和消失的家园的思念,也是对于曾经居住在那里、现在却散居全世界的友人的思念。”影片《钢的琴》中的工厂空间作为怀旧场域而被呈现。那些因国企改革下岗散落在各个行业的原国企职工重新聚集在工厂厂房之中,在被尘封而又再度被重启的工厂中,他们操作起机器重温了分工合作的美好时光。再如影片《地久天长》中的工厂空间因为他们的欢声笑语而充满集体主义的温情,也呈现了一种对逝去的集体生活的怀念和反思。伴随反复响起的《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工厂作为一种空间记忆凝聚了工人们的情感、情绪与想象,故事得以在这种亲密的“阶级兄弟”关系基础上展开。而在张大磊导演的影片《八月》中,以张小雷较为冷静疏离的儿童视角描画了改革背景下国营电影制片厂工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个体遭际。“宏大历史就这样沉潜于自由松散的日常生活叙事中,成为少年成长经验中不可或缺又难以清晰描述的一部分。”那些个体经验散落在碎片式的工厂社区场景中,仿佛不经意地撷取的片断任由观众体味。
当下国产电影工厂空间的第二重面目是作为社会异质空间表征着充满束缚和压抑而使人意欲逃离的“异托邦”。“与其说异托邦是乌托邦的‘反面’或对立面,不如说异托邦同时既是乌托邦,又是乌托邦的他者……异托邦相对于日常处所而言,承载着某种强烈的相异性和某种对立或对照的标志。”如果说工厂空间曾经作为国产电影中一种带有乌托邦式的浪漫想象色彩,那么与此相对照的则是它的另一重面目——隔绝、压抑与封闭的“异托邦”。例如,影片《少年巴比伦》建构了关于戴城糖精厂的故事,并按照20世纪90年代工厂空间精心设置:潮湿的水泵房、昏暗的锅炉房和电工班,以及清一色蓝色工服。影片中呈现的工厂空间显示出风格化特征,工人们在工厂空间内从事简单重复的工作,建构了工人们破坏、暴力以及百无聊赖的生活状态。作为“巴比伦”的工厂空间意味着奴役和放逐,这里充满了机械化、危险性和压抑感,这与原本青春应有的激情和热血刚好形成反差,这种反差促成主人公路小路个体心灵的改变与成长。再如王一淳导演的影片《黑处有什么》,通过飞机工厂防空洞、人工湖等空间氛围的营造,凸显了20世纪90年代工厂家属区内少女青春的迷茫以及笼罩其中的种种恐怖与疑惑。
与此相呼应,由吴越导演、天津世纪百年影业公司出品的影片《暴雪将至》中,再无工厂热火朝天的钢铁碰撞,而是在冰雨浇注之下逐渐熄灭的锅炉烟火。在对角线构图中钢架交错,冷色调的工厂冰冷得如怪兽一般凝视着世人。影片中有一段长达八分钟的工厂内追逐的段落,在光影构图中呈现的是在迷宫般的工厂里,人的困顿与迷失。国有工厂的标志性建筑之坍塌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以及新时代的开启,同时也是对工人群体主体性的放逐。在工厂衰落的历史转折下,命运轨迹发生了深刻变化。影片中两次以广角镜头全景仰拍镜头展现如迷宫一般的筒子楼,具体化的空间场景成为集体记忆与时间的坐标。曾经作为国企工人赖以生存的完整而稳定的工厂空间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也是使生长在其中的工人及其后代们不断陷入精神迷茫与挣脱无力的旋涡。
另一方面,工厂空间还以历史废墟的面目呈现,是充满危险的暴力之地。近年来国产电影在工厂叙事中最为突出的美学特征是灰色空间的建构:伴随昏暗的雨夜和凛冽的寒风,作为法外之地频繁出现的废弃工厂和矿井象征着犯罪、威胁与损害时常发生的社会暗礁。在影片《暴裂无声》中,充满了乡村和城市空间的符号隐喻,突出煤矿开采地阴暗、逼仄的空间来进一步深化主题意涵。而在影片《引爆者》中,工厂不仅是“废墟”,也暗示着主人公赵旭东藏身之处和反抗之地。影片最后的场面富有象征意味,赵旭东在废弃的工厂里不断引爆炸药发起反抗。以工厂空间叙事反思工业化进程对人的异化,在这里工厂既是主人公的困境,同时也是他重新建构自己主体的场域。
三、失落的主体: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认为:“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过去’的投影。”当下国产电影的工厂叙事或反思历史,或观照现实,在历史与记忆的交织中共同呈现出对于工人这一失落的社会群体的深切关注。
当下国产电影的工厂叙事首先一个面向是反思历史,对于历史中的曾经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衰落的反思。他们在工厂中缅怀过去的集体感,同时也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因丧失主体位置而成为失语者。如果将工厂空间视为通往文化记忆的一种路径,那么,工厂空间将会打通历史和现实的通道。与此同时,国企改革作为一个标志性历史事件和历史记忆,构成了工厂叙事与情感表达的知识背景。德国著名学者、文化记忆理论奠基人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概念关注的是记忆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和文化决定的,开展文化记忆研究,不是把一个来自个体心理学领域的概念运用到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分析中,而是强调心理、意识、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当下国产电影工厂叙事正是通过文化记忆建构了一个缅怀历史的凝聚性结构,以或温情或悲情、或戏谑或庄严的多时空叙事穿梭于冷峻历史与诗意现实之间。例如影片《二十四城记》尝试用纪录片的电影手段叩访“历史真实”。与八位受访人讲述行为相切换的是叶芝、曹雪芹、欧阳江河、翟永明、万夏等的诗句,这鲜明地构成了一种历史与诗歌并置的凝重感。再如,影片《钢的琴》从总体上观照国企工人在集体主义时代作为一个“群体”瓦解之后以个人化方式进入历史的过程。而影片《地久天长》在三十余年的长时段叙事中,将刘耀军夫妇和沈英明夫妇等几个普通工人家庭的悲欢离合书写为大时代转折下的平民史诗。
除了历史反思以外,当下国产电影的第二种面向是观照现实,即较为注重对当前“新工人”群体的生存境遇与身份焦虑进行探讨。“较之20世纪的工人阶级,‘新工人’群体的人数与规模要庞大得多,但这一群体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却几乎没有自己的位置,以至于他们究竟是一个阶级还是阶层至今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事实上,“新工人”群体的产生可以视之为城乡对立和区域分化的产物。当下工厂叙事中的乡村不再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而是一片破败的荒凉景象,是代表着落后的、了无生机的封闭空间。资本市场分化导致“新工人”群体成为“新穷人”,而那些被迫离开土地来到城市的“新工人”,等待他们的是回不去的家乡也留不下的城市。在影片《暴裂无声》中,乡村与城市的交界处有一处山洞,这个山洞是隐藏着所有的阴谋和罪恶的渊薮,也吞噬了无数面如土灰的打工者,并即将吞噬他们的下一代。影片最后,庞大的矿山在一声爆破中訇然倒塌,寻子无果的张保民落下眼泪,既是一位父亲的心理溃败,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之殇。因此,处于农村或城市边缘的“新工人”群体在当下国产电影工厂叙事中往往作为漂泊者与失语者出现,他们拒绝卖掉土地可以被视为一种艰难的反抗。有意味的是,当前国产工人题材电影常常还会加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弥合历史、记忆、空间与现实的裂隙,描画“新工人”群体过去二十余年来不无悲凉的生存境遇。空间中的幻象常常被用来隐喻记忆的消退,逃离现实生活的幻想,以及人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中的驻足、徘徊与彷徨。
结 语
当下国产电影中的工厂叙事描绘了20世纪90年代国企工人和“新工人”两种工人群像,在呈现曾经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衰落的同时,也试图反思当代中国社会高歌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从土地分离出来的“新工人”群体无处寻找的身份焦虑与生存困境。当下国产电影也密切关注中国工厂的变迁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历史关联,将工厂空间作为铭刻社会转型的场域来连接历史、记忆与现实。在具象化的空间坐标中寻找和唤醒流逝的时间,使人们可以清晰地体认不同代际的工人群体所经历的集体记忆与个体伤痛。实际上,在当下围绕工人群体与工厂空间的影像表达之中,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平凡的工人群体的选择与遭遇深藏着某些影响和塑造历史的因素与结构。这些底层书写也密切联系着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与精神动向,并始终保持着独特的艺术品质与深切的人文关怀。在此意义上,当下国产电影的工厂叙事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