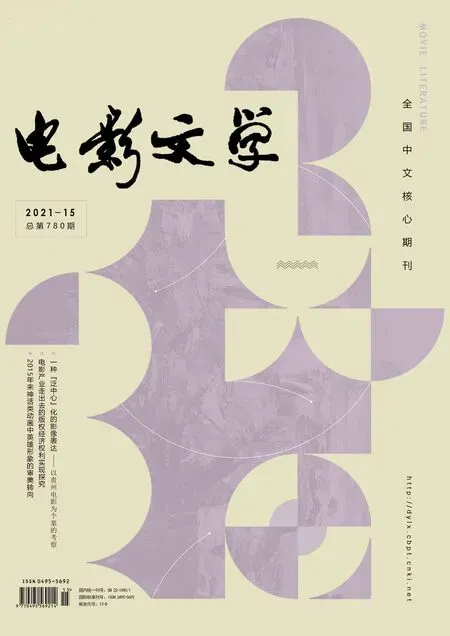《隐秘的角落》与当代现实主义症候
王 圣 (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自2017年《白夜追凶》《法医秦明》《心理罪》等十多部网剧连续上映后,开启了中国城市犯罪悬疑剧的热潮。2020年上半年《十日游》《沉默的真相》等剧再次井喷,其中尤其以《隐秘的角落》(以下简称《隐秘》)的全民追剧及热议引人注目。与其他犯罪悬疑剧相比,改编自紫金陈小说《坏小孩》的《隐秘》,就直观上而言,无论在故事背景、叙事情景、人物设定上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即它竭力将犯罪悬疑安置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从而在叙述本应具有高度假定性的刑侦故事的同时,似乎构成了一幅当下鲜活的城镇生活世界的景象。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犯罪动机、行动与日常的城镇市民生活逻辑之间形成了令人不安的激烈冲突,即后者所敷衍的现实主义的自然性,并不能成功假装“(杀人)事件”自己在发生,因为文本以震惊为目的而驱动的冷血的数学老师与阴骘的14岁少年,早已超出了我们生活中的“集体经验”。当《隐秘》启动现实主义叙事机制时,构成文本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性,即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化环境中的一种新症状。
一、现实主义的叙事欲望
一般而言,犯罪悬疑片自希区柯克那里形成了典范性的叙事策略——让观众比剧中人更早更多地知道危险与真相,即遵循狄德罗在《论戏剧艺术》中就已经构成的典型的戏剧假定性的种属。近年来港剧、美剧以及韩剧在犯罪悬疑类型上将这一戏剧假定性发挥到了极致,构成了发达的逻辑推理、精神分析,司法律政等叙事套路。无论是电影《烈日灼心》还是电视剧《白日追凶》都深受这一类型传统的影响。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人的极端处境中各个要素的设定,由此建立脱离日常生活的情感逻辑及行为动机,从而在戏剧情景中考察人物性格的转化弧线。与此相较,作为一种创新,《隐秘》的现实主义形式构成了观众极大的视觉及共情差异,消解了文本身处中国城市犯罪悬疑剧的热潮所必然带来的同质化的焦虑。
《隐秘》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的表达欲望。首先,它将叙事场景设置在当下中国极为类同的三线城镇湛江。我们知道,经典犯罪片往往依附于写字楼、咖啡馆、闹市街头交织的大都会魅影之中,而《隐秘》则将人物裸露于实景拍摄的湛江赤坎区骑楼老房、金地豪苑、七中、二十中、六峰山、华都汇等真实生活景观之内。剧集强力地将杀机四伏融合于生活常态之中,任何试图跳跃出现实的凶杀,都被小心翼翼地铺陈在对日常生活的描绘之后。即便开篇最突兀的张东升杀害岳父母,也是在惯常的毫无波澜的登山拍照中,突然一推,但又马上抑制凶杀的激荡,让人物迅速返回到生活的场域。为了缝合将人物撤回生活的惊悚空白,在十二集剧集中,连续使用了十二首阴森哀悼的音乐,以弥合犯罪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断裂地带。其次,每个人物都服从由现实给定的生活逻辑和细节。与《白夜追凶》那种人格分裂的戏剧逻辑不同,《隐秘》的两条线索都造成了生活现场的幻觉,一是在少年宫培训班代课的中年数学老师张东升,作为入赘女婿遭受亲戚的嘲讽、妻子的背叛及离婚危机,展示围困独生子女一代的中年危机现实。另一条线是14岁的初中生学霸朱朝阳及逃出孤儿院的严良和普普,在这三位少年身上,铺开了城镇离异家庭和底层市侩社会的生活常态。再次,《隐秘》将犯罪的动机置换为日常生活中细微的伦理矛盾、道德焦虑及创伤性痛苦,将犯罪悬疑类型既定的天生杀人狂模式重组为生活矛盾的受害者。张东升与朱朝阳互为镜像关系,他们都是认真遵循社会正面规则的优秀分子,却在生活阴暗覆盖的冷暴力中惨遭应激性创伤。为了将人物的动机推至触发杀戮的高点,这些创伤被密布的生活细节所勾勒。尤其是以张东升为他者的朱朝阳,被离异家庭中母亲情感的压抑、父爱的沦丧,以及校园孤立的细节暗示。以上种种都显示,《隐秘》在宣泄犯罪类型的快感之前,似乎在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上做足了功夫,以实现一种“真实信念”的叙事欲望。
现实主义叙事欲望派生于科学理性对人和世界的把握的雄心壮志——理性不仅可以认识自然,而且同样可以理解自由意志,从而创造出符合进步规律的秩序美学,鲍曼称之为“造园抱负”。我们可以说,现实主义在经典意义上即是对人的社会行为的有效理论,一种预言人的行为的切实方法。
浙大工科出身的紫金陈对数理逻辑的偏爱深刻影响了小说《坏小孩》的结构及语言风格。紫金陈的系列犯罪悬疑小说往往在故事开始就承认谁是凶手,并且用近乎简单直接的语言对凶手心理和行为进行社会学性的观察和白描,换句话说,悬疑不是来自未知的凶手,而是凶手复杂的心机和意图,这恰恰是紫金陈小说的理性魅力所在。相信理性可以把握人的心灵,将人的复杂动机和行为还原为逻辑化的、有章可循的数理推论的渴望,正是小说文本呼唤影视化过程中现实主义叙事的原始欲望。从文学到影像,文本的理性欲望被进一步推向了一种整体的真实欲望,即犯罪悬疑不是专一地聚焦凶杀奇观,而是倒置为对现实生活本身的体验和观察,再从现实导出凶案的进行时态,也即构成文本的“作者现场”感——犯罪是在生活中自己发生的“事件”,叙事者仅仅是现场的转述人。
二、真实及其剩余物
《隐秘》所展现的现实主义叙事欲望与130多年前马克思与恩格斯热情赞扬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形成了一种意味深远的重影。1888年4月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敏锐地指出了在巴尔扎克身上存在的悖论性的两面,“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这种“胜利”的内在原因,在于“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如前文所述,《隐秘》的现实主义叙事欲望同样也来自其文本之外的科学理性,这是否意味着它同样是今日现实主义的某种“胜利”呢?抑或至少是一种现实主义不可抹消的恒久魅力的体现呢?
在《隐秘》的文本之中,现实主义恰好体现了理性与消费之间的分裂,即理性不是指导认识获得真理的知识,而是更“合理”地消费的态度。人们对商品恋物癖的享乐并不表现为癫狂,而是更加理性的规划。现实主义在这里不是认识世界的科学原则,而是更好地体验惊悚的工具,是更类似于VR的仿真设备,以帮助观众获得逼真的幻觉效果。然而《隐秘》对现实主义“真实感”的倒置性的征用,由于并不是一种理性在人的历史的实现,而是将惊悚呈现于“跟生活一样的现实”的幻象之中,因此,现实主义在这里遭遇了自身的分裂。
《隐秘》创造的真实幻觉的断裂,恰恰在其剧集开始的第一幕。作为全片剧情的动力和逻辑,张东升的提前到来的中年危机正折射出独生子女一代的真实日常生活,然而这一蕴含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的生活世界,被极度压缩为张东升简单的一句对大他者隐含反抗性的质疑:“你看我还有机会吗?”随之,马克思所说人的全部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一切纠缠和矛盾被简约为山顶上的果断一推。而张东升的一推被两个凝视所捕捉。一是现场中的岳父母的视角,展示了广角下张东升的畸形的脸,二是远处朱朝阳和三个孩子用照相机录下的模糊的身影。张东升作为真实生活的矛盾高潮,被两个凝视转化为一种齐泽克称之为畸像(anamorhosis)的扭曲了的图像,即张东升的复杂背景下的行动必须被转化为一种特殊的角度才能被识别。齐泽克认为这个特殊的角度就是一种框架,而这个框架就是幻想,它提供了一种关于现实的特殊的或者主观的视角来看现实。岳父母的视角提供了观众的凝视位置,构成了一种大众对刺激的反日常的犯罪欲望,而朱朝阳三个小孩所捕获的,则是构成全剧叙事动力的镜像欲望——朱朝阳将张东升作为理想自我而毁灭,从而实现自我拯救。
我们看到,正是将张东升的行动的真实转化为畸像,才可能启动《隐秘》的叙事。然而畸像仅仅是文本的一个污点,它看似与整个文本没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只是作为一个开场白,“直视这个因素,似乎它就是毫无意义的斑痕,但从另一个确定的侧面审视,它突然展示了清楚的轮廓”。可以说,张东升的一推形成了《隐秘》的真实幻想的一个剩余。“幻想规定了一个显眼的元素,这个元素无法被整合进既定的象征结构,但它恰恰因此建构了象征结构的同一性”。而作为真实的一个剩余,恰好向我们展示了,它是如何在一开始就将真实带入幻想的。
随着真实的剩余的产生,《隐秘》试图构建的幻想体系充满了无法克服的断裂。为了将惊悚犯罪埋设于生活之中,文本必须为它们寻找生活的价值与逻辑。朱朝阳三个小孩的行动被命名为对普普的弟弟欣欣的拯救。欣欣在全剧中占据行动的中心位置,然而却如同一个缺席的在场的幽灵,一个希区柯克式的麦格芬。齐泽克对此有精彩的分析:“麦格芬就是拉康成为客体小a的最纯粹的情形:一个纯粹的空无,却发挥着欲望的客体成因的功能。”亟待30万元治病的欣欣缝合了《隐秘》所要建构的真实幻想的统一性,然而它也恰好就是这一统一性的空洞。这个幽灵随着围绕朱朝阳的镜像行动的发展,在后半段逐渐迷失在文本之中。
让麦格芬式的幽灵消失的真正原因,在于欣欣是一个虚假的价值客体,也即它不过是文本努力建构日常生活的一个想象性符号,而朱朝阳的真正的客体小a恰恰是张东升本身。《隐秘》的后半段从欣欣向张东升的欲望滑动,显示出现实主义的真正撕裂,即朱朝阳的黑化,从一个现实的矛盾(筹钱治病)转向为一种精神分析式的象征化展示。朱朝阳的镜像犯罪实际上来自著名的拉康精神分析案例“爱梅”,通过对理想自我的模仿并通过对它的毁灭而消除自我统一的焦虑。换句话说,《隐秘》的现实主义断裂,正是从现实矛盾的畸像化以及欲望符号的替换之中产生的,将现实置换为幻想,正是当下消费理性的深刻矛盾所在。
三、事件与现实主义的沉默
张东升的现实生活被压缩为《隐秘》的故事前提,而朱朝阳导致同父异母的朱晶晶坠楼才是整个故事的“激励事件”,罗伯特·麦基称之为“彻底打破主人公生活中各种力量的平衡”。朱朝阳从渴望友情到寻求新秩序的启动,来自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晶晶坠楼的偶然事件。在这里,事件(event)这个概念浮出文本的结构,在巴迪欧看来,“事件是一种被转化为必然性的偶然性(偶然的相遇或发生),也就是说,事件产生出一种普遍原则,这种原则呼唤着对于新秩序的忠诚与努力。”建立在事件之上的哲学认为历史及人由纯粹的偶然构成,根本不存在可以把握的连续性及规律性,而所谓的客观规律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任何事件的发生不是内在规律的呈现,恰恰相反,都是“认识框架和存在框架之外的某个溢出(excess),一个无法还原为既定存在和认识框架的残余物(surplus)”。可以说,事件是对现实主义最致命的解构,它撕裂了现实主义所根本依据的唯物史观。很显然,朱朝阳导致晶晶坠楼,表面上是对张东升的镜像性模仿,但是在叙事结构上承担起将现实主义的生活矛盾转化为纯粹偶然的事件,一种毫无缘由、互为因果的、刺穿象征秩序的症候。当晶晶在秩序链条的位置消失后,朱朝阳优等生家庭背后的不能被言说的实在界就被揭穿了,晶晶坠楼事件是对既有的现实主义叙事框架的毁灭,它“涉及的是我们借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架构的变化”,从晶晶空缺的位置,朱朝阳看到生活秩序重新组合的入口。但正是晶晶的缺席是一种随机装置,它本质上是对现实主义理性铁律的脱轨。
现实主义要求文本必须从现象世界开掘出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以此作为人的尺度则产生了批判的立场。但现实主义的事件化使得《隐秘》在整体上失去了评判的位置。晶晶坠楼以及随后朱朝阳父母、王立的死总是一个个脱离象征秩序的意外(剧情中不必要的凶杀),它们具有打碎秩序的先决性,也即必须有这些死亡,然后才可以看到戏剧的变化。齐泽克即认为事件的先验性在于事物的存在和统一依赖矛盾的存在,总存在一个证明规则的例外。据此,齐泽克分析了基督复活作为事件与人类堕落之间的辩证关系,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为了基督能够降临并拯救一部分人类,所有人都必须先行堕落。”而为了证明救赎的规则,则必须先行创造复活的事件。因此事件总是先验地开启一个认识的空白之处,一个有待重新叙述的意义混杂的失语领域。在现实主义叙事框架内,任何离异的家庭中的孩子总是解散的家庭成员的创伤点,朱朝阳既是父母不愿面对的他物(the thing),甚至也是晶晶的眼中钉。在这个可被描述的生活世界中,朱朝阳处于一种痛苦的平衡之中。然而晶晶坠楼带来了意义与事实的模糊。自晶晶坠楼和王立被杀开始,朱朝阳开始力图重新组织意义秩序,以至于在剧集结束时,朱朝阳的日记留下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开放结尾。在此处,现实主义的表象终于迷失在事件的含混之中。
事件总是对秩序的破坏,因而事件在本质上具有堕落的恶的属性,是创造救赎的起点。朱朝阳对张东升的凝视欲望并非来自任何现实的犯罪动机,而是突然插入的事件将其迅速带入堕落的黑化路径。从“一无所求”(没有犯罪动机)到“想要无”(如张东升所说“希望能回到从前”),朱朝阳的堕落过程同样让现实主义失去批判立场。因为堕落本身是寻求善的恶,或者说“因恶生善”,因此堕落在其实质上仅仅是重整象征秩序的行动,它无法被善恶两极的任一方所界定,毋宁说它是从恶向善的滑动过程。
为了呈现这个不可界定的滑动,我们看到《隐秘》的摄影机占据了全知的视角,这本是犯罪悬疑剧的禁忌,但在《隐秘》中它向我们展示了朱朝阳不可言说的、善恶滑动的过程。在晶晶坠楼、王立失踪、朱永平及王瑶被害后,在警察叶军的几次调查问询中,摄影沉默地注视着朱朝阳,这是一个缓慢而孱弱地重建生活意义的时刻,同时也是善恶无法介入的时空。现实主义在《隐秘》中的启动,在这里彻底地沉默了。而同样是这个全知视角恰好伪装成为现实主义的叙事视角,似乎一个完全没有被介入的生活正在展演着一幕幕凶杀。
四、个体化危机与犬儒主义
《隐秘》的现实主义欲望的失败来自其对真实的消费性幻想与惊悚的事件化叙事之间的矛盾,然而我们看到这种现实主义的症候更可能来自文本背后的文化状态。与一般犯罪悬疑剧的不同之处是,《隐秘》的悬疑和恐怖不是来自不可知的随时到来的毁灭性力量(例如经典的《死神来了》《惊声尖叫》不可知的死神和杀手),相反,在真实的欲望下,它认真地围绕着当下社会的个体危机展开剧情。尽管张东升的城镇白领的中年危机被压缩为一个最终的行动,但是他仍然折射出当今大多数大学生异地就业谋生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状态。在脱离了乡土的熟人共同体,个体一旦在职业或家庭遭受到打击,就是毁灭性的创伤。而本剧的真正主角朱朝阳,更是显现了少年儿童在媒介与消费社会中过早地介入成人世界时的精神的困惑与孤独,尤其是以婚姻取代父子为纽带的现代家庭,一旦婚姻解体对子女将产生致命伤害。而严良与普普则更是生动地体现当下小资文化所未能覆盖的流动性人口和底层生态的真相,他们不仅缺少安全感,而且更加绝望。《隐秘》尽管在现实主义的欲望面临失语,但是无意间展示了当前社会的一种深刻的个体化危机的图谱。
实际上个体化危机正是金融资本取代产业资本后的一种全球景观。正如鲍曼所准确观察的,技术与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促成后现代的高速流动,导致鲍曼所谓的“时空极化”——人类不平等的进一步加剧,穷人在空间的安全(长期雇佣与适应社会迷宫)与时间的自由两方面的丧失。剩下的是急速流变的每个瞬间小游戏,现代性的启蒙理性与毅力失效了,在规则超出人的适应之后,最终出现了个体化危机:“全球资本的流动性腐蚀和瓦解了现代社会建构的秩序基石,其后果是,所有个体脱离了传统纽带而以个人的方式来解决系统的问题,从而使所有凭自身能力追求此充分消费自由的人们失去了稳定秩序的安全保障,使传统关系的认同、爱和信任空间变得不确定、短暂和萎缩。”
简言之,个体化危机正是传统社会的家庭、社群、宗教及职业的坐标已经失效,在社会的整体失序中,导致每个人孤立地以自己的方式面临系统性的生存挑战。当张东升两次询问岳父母和妻子“我还有机会吗”时,表明作为个体的他已经没有任何方法来应对家庭的崩溃,他唯有采取极端的自毁来逃脱个体的危机。朱朝阳在晶晶死亡的空缺中洞察到了自身困境的根本所在,他向母亲痛称“你们都是为了自己”,在解体的婚姻中,孩子彻底地丧失了爱和信任,他只能永远独自面对他创造的隐秘的谎言。而在本剧中配角严良和普普最出彩之处,恰恰在于他们在城市流浪中独自应对生活危机的生存技巧。严良犹如困兽般的警惕与正义,普普远远超出其年龄的成熟与机敏,都透露出超出他们心智所能承受的系统压力。《隐秘》在展示个体危机时的一个讽刺是张东升与三个小孩之间的相爱相杀的情感。在严良与普普在台风中陷入绝境时,唯一愿意帮助他们的竟然是他们勒索的杀人犯张东升,而普普的乖巧甚至引发了张东升渴望孩子的父爱。这样一种倒错的情感,正是显示出当下个体在极度孤独和无助中,一丝悲凉的心境。正是他们共同承受着个体危机的自觉与阵痛时,他们才能真正走入对方的心灵。
然而这种个体化危机如何走出困境?《隐秘》由于其伪现实主义的立场,促使它给出了一种犬儒主义的道路。齐泽克将鲍曼的个体危机称为在后现代社会中“大他者的瓦解”——即社会建制、习俗和法则的公共网络的失效,我们只是假装大他者没有死。如此构成了个体危机时代的一种新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即在经典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一种对我们认识的扭曲,而现实主义的任务就是通过揭露商品拜物教所遮蔽的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一旦意识形态被认作意识形态,那么它就消失了。然而在个体危机的后现代,人们已经知道我们正在接受现实的扭曲版本,我们坚持这种虚假而并不拒斥它,齐泽克称之为当代的犬儒主义(cynicism),“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是他们依旧坦然为之”。朱朝阳从晶晶坠楼开始一步步陷入谎言的深渊,他的父亲无比沮丧地说:“我们教育孩子诚实,但是却希望他们撒谎。”朱朝阳的虚假意识不是被大他者所扭曲的谎言,而是他为了换取更有利的生存而主动编造的谎言。张东升最后求死时对朱朝阳说“你可以相信童话”,而普普在绝笔中所言“希望你有一天能有勇气说出来”,但是我们最终看到,他讲述了笛卡尔的“童话”版本——严良快乐地回归生活,普普与欣欣配对成功手术顺利,而这个不过是一种积极的寻求利己的犬儒主义。真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实际地活得更好。在这里,不仅现实主义的善恶的批判无法介入,甚至真实与谎言也被主体完全放弃,他们看重的是“有利可图”。现实主义试图在认识论上揭露的由上层建筑所构建的那个巨大的虚假网络消失了,或者说现实主义的根本任务在这里被终结了。
与前文相贯通之处在于现实主义叙事欲望来自科学理性,然而随着金融资本的进一步渗透,科学理性与消费欲望走向深度融合,现实主义成为真实幻想的体验方式。同样,理性与消费的融合产生出犬儒主义的态度,即求真意识在这里被扭曲为一种真正利己主义的手段,至于犯罪悬疑类型片所追踪的真相,在这里已经变成喜闻乐见的成功洗白。现实主义在《隐秘》剧中遭遇的变异,即是现实主义从经典马恩时代移位当下的话语变迁的显证,但它的失语的背后,更是值得我们深度思考的价值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