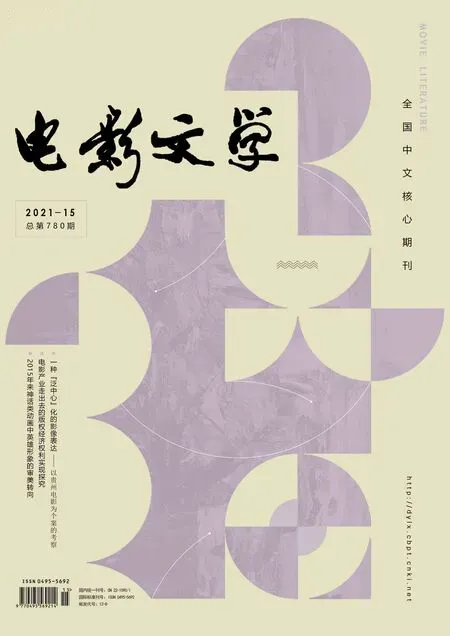一种“泛中心”化的影像表达
——以贵州电影为个案的考察
肖艳华 (贵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近年来,贵州电影成了当下视觉文化传播的热点现象,从历史的在场缺席,到当下的多维审视,贵州的实在空间与影像空间被不断地赋予了多重意象的解读。“依托贵州地理、文化、经济背景,在中小成本类型电影和艺术电影的生产中佳作不断。无疑,在高速发展、复杂多变的当下中国电影艺术、文化与工业版图和‘工业美学’建构图谱中,这一支中国电影的‘贵州新力量’,有着重要而独特的意义。”与北上广等现代性极其明显的城市空间或其他中西部省域相比,贵州电影的生产实践展现出了自我空间影像消费特征的美学意识,且极大地彰显了贵州作为主体在电影作者属性上的影像书写。
在考察贵州电影生产的历史时空中,战争特征代表的长征文化影像、少数民族身份书写的传统影像、艺术诗意逻辑运行的魔幻空间构筑,不同的影像特征并行使得贵州影像逻辑归纳以及中心影像难以确定。因此,“有必要考虑:并不存在中心,中心亦无自然的位置,它不是一种固定的点,而是一种作用,一种不定点”。借助德里达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视角,解构是一种对成规化法则否定的变革。这种变革性使得贵州电影对原有的影像结构框架有了“调节的转换”,现有的影像类型与形式规则在贵州的影像符号实践存在着明显的“延异”表征,即差异性的镜像生成:贵州电影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影像符号层面上的差异,更指涉着这些影像符号差异形成的运动过程。差异形成之后的延缓运动使在场者的显现,即贵州电影的生成,“无意识实质上并不是隐藏着的,潜在的‘自我—在场’;它使自身变化,并延迟自身,这无疑意味着差异的交织”。由此可见,任何影像符号意义都是延异中差异“踪迹”的交互运动衍生的。
德里达的延异观不仅使得传统结构的中心化意识被质疑,在否定决定性、唯一性中心化的同时,相对性、主体间性多元中心点的视角对复杂事物的辨析有了更全面的意义探究。“泛中心”化正是基于“去中心”化的意识上,认为事物唯一的、显著的中心点被多个并存的、且重要度均化的中心点所取代。正如利奥塔认为,后现代意识的集中表现在对于元叙事的怀疑,“确切地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的否定,是对于现实社会中权利、制度、生活方式行为等传统认知的反认同。在贵州的影像思考中,其繁复在肯定与否定的矛盾之下,既定的影像法则成了无解的意象,由此“泛中心”化的意识成为思考其持续行进的重要路径之一。
一、有意义的在场者:贵州电影“泛中心”化特征的生成
(一)历史维度下影像出现的反本土化与去同一性
电影作为一种舶来品,它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有着明显的本土文化结合特征显现。“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现在可以更进一步,确切指出联系原始因素与最后结果的全部环节。”电影的自觉性创作与本民族文化存在着极大的互通倾向,它以视听符号形式“记录与承载着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变迁,城市的空间展现也往往成为电影媒介中极其重要的民族文化书写与象征”。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1905)诞生于北京,其与京剧相结合的形式有着明显的北京传统意象承载。20世纪20年代中国城市电影在上海掀起高潮,这亦与上海开放性的都市化特征难以剥离。反观贵州影像的发展历程,其电影作品的首次出现以及在不同时空中特征的显现,均并非遵循这一传统的电影实践策略。贵州作为少数民族的形象主体是一种现实性的既定认知,但是在梳理贵州电影引发关注的节点时空轴时,却呈现出了与本土违逆的表征,即并非以民族影像为原初的创作。
贵州电影的开山之作是《密电码》(1936),这是一种战争类型的创作,而并非少数民族文化主体的影像书写,而后以革命解放为主的战争影像表述成为贵州电影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主旋律符号,也基本贯穿了整个贵州影史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第五代导演的美学隐喻崛起背景下,《良家妇女》(1985)借助女性主义视角透过贵州外化环境的封闭性与差异性,表达了深层次的悲剧意识。新世纪以来,贵州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良家妇女》的艺术风格与形式,还进一步注入了在贵州现代化极其不均衡体验下的后现代意识,并一再地引发聚焦化。《寻枪》(2002)“选择以整体隐喻的方式讲述人性的异化的物恋悲剧,并以感性跳切的方式展现不无荒诞的生存幻象”。王小帅的“三线三部曲”《青红》(2005)、《我11》(2012)、《闯入者》(2014),在贵州特殊的历史在场身份之上,传递出了个体命运与社会时代的互文反思。《路边野餐》(2015)的时空交错、《地球最后的夜晚》(2018)的梦境诗意,不仅在技术影像上新意迭出,且在传统美学原则上做出了“陌生化”的阐释。原初影像与关键影像的书写在以往的电影发生上,与本土传统文化的衔接是固化的习性,但在贵州空间却出现了在场的脱离,尤其是艺术影像中的诗意逻辑运用在这并不具备开放性意识的空间上,衍生了与后现代最为接近的奇幻意象。
历史时空的坐标系中,在贵州电影被不断关注的节点上,战争与艺术成了两个最主要的影像符号书写,但这并不意味着贵州影像史上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消隐。贵州少数民族电影从20世纪60年代逐渐拉开序幕,《秦娘美》(1960)与《蔓箩花》(1961)在中国电影史上都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秦娘美》与黔剧结合,演绎了传统与创新的别样民族表达:《蔓箩花》以苗族传说为母题进行了极具神话意蕴的影像书写。新世纪以后,贵州民族电影不仅在量上逐渐递增,且在表达上呈现了立足于本土空间的内外视角思考,如贵州籍女导演丑丑的民族三部曲:《阿娜依》(2006)、《云上太阳》(2010)、《侗族大歌》(2017)在自我民族意识内化的主体性表达下,勾勒出了与外在世界存在强烈差异体验感的心灵栖息地。而他者视角下宁敬武的《滚拉拉的枪》(2008)、《鸟巢》(2008)则介入了更多的外界力量,对贵州封闭的外化与心理空间做了突破界限的审视。
在贵州电影引发关注点的不同时空转换中,战争影像的首创与艺术影像的更迭幻变成了贵州影像发生的特殊轨迹,同时又兼具着民族影像的重点与密集书写。战争、民族、艺术成了贵州影像作为现实在场者的三个关键词,而这三个关键词在类型与风格的传统判定中,却又充满矛盾性与相悖性。
(二)当下贵州影像作品维度取向的复杂性
电影的生产,被默认为是一种有迹可寻的规律式判定,如电影发展中类型化的形成、不同风格化的电影流派成型。人们往往习惯于通过已成型化的规则去理解与阐释其他影像,但在贵州影像的差异实践化下,传统的中心结构变得界限模糊,甚至在意义空间上不断延伸绵延,形成了多元化的影像在场者。贵州战争电影的持续创作,在革命历史空间上延续着重大历史事件题材选取的一致性,且进一步对贵州长征文化的传播发挥了巨大的助力;囿于少数民族省域的社会形象,贵州民族电影的创作日渐密集,少数民族的身份形象也在民族影像的泛化表达中更趋明确;继而又在艺术电影的特征中,贵州空间亦蔓生出了令人迷幻的诗意之美。基于内容表达的类型化、抑或是风格与受众取向的商业与艺术泾渭分明,在成规化的电影理论与实践界域里却实难辨析与归置贵州的电影内容与形式。
事物观念的形成往往是主观研究的意识中产生,再回归到客观中获得绝对性。电影作为类型的存在就是电影理论视域中一种极为固化的观念性的存在。类型是电影作品分类的一种主要方式,是电影内外情境中不同参与者达成共识的一种默契存在,“而重复在每部电影中出现的类型公式和惯例,给予了各个类型电影共用的识别规律”。类型的区别主要在于主题与情节模式化的影像实践,但类型的观念在贵州电影考察中无法获得一致性。类型化的生产有书写历史革命事件的战争电影,也有展示少数民族文化的民族电影,这两种类型构筑了贵州影像的两个重要维度,即以内容为取向的战争类型与民族类型。但在以诗意为特征的艺术影像中,它的类型取向是缺失的,尤其是在当下,贵州诗意影像在内容上有着极度的自由表述,有纪录影像下《四个春天》(2018)的日常生活思考美学、有摄取城镇漫游者的《无名之辈》(2018)现代幻象,还有魔幻现实主义与梦境逻辑指引下的《路边野餐》与《地球最后的夜晚》中迥异的平行时空显现,这些诗意影像内容的交迭在传统的影像规则下并未形成终极意义的推出,如何能延展出有效的意义在类型框架上失去了目标地。
即使绕开类型的规则,试图在形式上仍然无法找到贵州影像统一的原则。形式往往与内容作为相对的概念所理解,但实质中,电影的形式也经常因内容的选取而发生变形。基于内容,形式指向电影的两大组成部分,叙事与风格。尤其是在风格的形成上,风格模式不仅仅是作品的单一风格,也是导演的创作风格,在法国新浪潮的“作者论”中,风格的延续性常常是判断一个导演作者色彩的标准之一,像侯孝贤的写实、贾樟柯的超现实、毕赣的魔幻现实,或集体的风格,德国表现主义、苏联蒙太奇等。贵州电影中的诗意影像在艺术的维度里找到了形式与风格的明晰特征,但在战争与民族的维度中却又脱离了形式与风格的定性。
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贵州电影是一种从类型走向形式风格的趋势,但是这一走向性却并非一元或二元的对应,尤其是在当下的时间的维度里,贵州影像类型与风格并存构筑了多重点的时空意象。如20世纪80年代的《四渡赤水》《奢香夫人》《良家妇女》三者并存的在场。即使在“毕赣现象”不断引发热议的当下,战争影像与民族影像并未消隐,反而流溢着更强化的类型影像生产,尤其是在2018年至2019年初,《迫降乌江》《无名之辈》《四个春天》《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引发的贵州电影热潮中,战争、民族、艺术诗意同时交互映现,它们风格相距甚远却交互复现。
贵州电影的本土化、同一性被各种特征离散,绝对概念、无区别的差异已然被非常规性的逻辑所阻断,形成了传统结构下无法释疑的差异性影像图景,而这种差异性正是“泛中心”化在场显现的基础符号。恰如德里达所质疑的封闭的传统翻译书写模式,“忠实于原作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作,无限地区别于原作的”。完全比拟的等同翻译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同真诠释与转化,因为文本是没有可抵达的终极意义的。贵州电影作为一种影像文本的主体书写,它的能指与所指意义性远非传统影像观念的“翻译”。因为“所指概念绝不在一个仅仅指自身的充分的在场中靠本身自行地出现。每一概念在本质上被合法地刻写在一个系列或者系统中,其中以差异的系统活动或者说游戏的方式指涉他者,指涉其他概念”。可见,所谓概念意义的形成并不是先天的,那它的指涉意义就不应该是固化,反观贵州电影,它也可以突破刻板印象的框架,形成合乎实际化的影像在场还原,或许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理解为:电影不应该是影像规则的附属品,而是影像规则的缔造者。
二、原初踪迹的寻找:贵州电影“泛中心”化生成之因
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在场构建在场者”,德里达认为事物的延异运动过程才是最终在场者的构成,而“原初踪迹”就是运动过程中起到作用的、可能消失或并未消失的某种因素。“在专门的痕迹(踪迹)领域中,差异产生了种种要素,并使这些要素构成为文本和痕迹(踪迹)系统”。贵州电影作为解构传统的在场者,它的“泛中心”化形成,正是“原初踪迹”提供了可确立的依据。
(一)贵州文化主体性的缺乏
“文化不是可观察的行为,而是共享的理想、价值和信念,人们用它们来解释经验,生成行为,而且文化也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之中。”任何艺术作品的生产离不开它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因而不同区域的电影影像生成是有着明显的自带文化特征的,如上海城市影像与它高度城市化的现代环境息息相关,香港电影里的非理性逻辑与香港后殖民身份的懵懂与迷离相依,台湾电影的长镜头美学有着对故土文化眷恋的诗意隐现。影像的传统解构是存在既定文化历史情境下的一些解构姿态,尤其是与居于凸显意识的中心文化难以抽离,因此大部分的地缘电影文化都基于一种主体性文化而进行影像阐释。但审视贵州电影的不同特征,却很难将它们统一对应到贵州文化某一特征上,在战争、民族、诗意的影像之间,少数民族文化似乎只彰显了其中一个符号特征的呈现,且这一民族符号亦存在多种少数民族文化形式的交融。这种文化主体特征的缺失与困惑,可以在溯源贵州作为主体形象生成的历史中去寻找踪迹:贵州文化由于其历史与政治场域的变化,在传统、记忆、语言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异与散点化。于此,我们不难发现,贵州影像生成的复杂之因源于贵州自身主体文化的难以确立。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贵州是缺乏先天主体性的。在今天的地理位置上,贵州是一种不边不内的位置,既不像边疆省域一样处于跟异国的接壤边界,也不如四川、湖南一样与内陆地区联系紧密。这种现实的形成,源于贵州历史上在场感的边缘性。由于山重水复的复杂环境,在各种封建皇权中,贵州均被视作野蛮荒凉之境,直至明朝1413年,贵州才作为单一省份出现,且基于云南、四川、湖南、广西等边缘地域的划分合并而成。因此,贵州的形成是本身就是一种无中心的各周边区域的拼图。在这样的一种身份形成下,该区域的政治制度也变得复杂,土流并治下各种原生的、氏族的、封建的社会类型交汇,直至进入大环境的现代社会中,贵州的仍存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各种复杂社会镜像。
其次是多民族的杂居现象。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元素尤为彰显的省份,这种彰显性不仅因为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种类众多,且成分极其复杂,光世居的少数民族就多达十几个。此外,贵州还有许多未识别的民族。贵州的少数民族,不仅支系庞杂,还存在极其明显的同源异化,各少数民族追溯至汉、百越、苗瑶、濮、氐羌等不同族系。众多的少数民族在贵州山地环境主导因素的影响下,民族居住环境的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逐渐形成。但由于“溪峒型”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信息的交流与传播存在着天然的障碍,并恍如罗盘星布于贵州地域,他们拥有着自身本质的生存方式与文化信仰,又通过与当地本土文化的交融,兼具了多样化色彩。“溪峒型”地域特色使得贵州文化四处“撒播”,且各自独立成为贵州民族文化的共生现象,但中心化的民族文化却至今都处于模糊中,难以确立。
最后是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造就的影像多元根基。贵州建省以前处于相对独立自主的边缘区域,不仅远离彼时行政中心的管束界域,且在汉文化的接受影响上存在较大的间离性,因而这一空间的各民族有着极大的自由性,不同民族的生产方式与文化传统原真度保存较高。随着不同朝代的变换,由于其地理位置偏远,贵州地域成为各朝战乱年间最佳的庇护之地,加之它本身拼凑而成的缺主体性,因此它在不同民族的融入下更趋开放化,相异民族的原始文化也在主体少数民族的缺乏下,变得更具包容与兼收,并在相互的文化交融之间各自调整与适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大走廊。在贵州少数民族中,每个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这些不同信仰与风俗在本土的泛化与相互认同,衍生出了有贵州本来印迹,但是又各不尽相同的民族文化共存意象。
(二)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不同程度参与下的影像生成
绝对中心意识的怀疑与否定,是德里达对于事物“延异”与“踪迹”的解构渗透,并通过“播散”的行为进程最终抵达泛中心化之实在境地。“踪迹是一般感性的绝对来源,踪迹是显现外观和意义的延异。”事物的差异变动是无时无刻的,但是却又未必具备实在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当下事物的呈现都不可避免地裹挟着它所经历的印记。这种感性的踪迹寻觅跟波德莱尔的现代性体验有着惊人的相似,“现代性是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的”,而这瞬息万变的元素需要去捕捉与获取才能真正确定艺术作品的意义性,“因为我们所有的创造性都来自时代加予我们情感的印记”。现代性问题虽然发端于西方世界,但在全球化的步伐之下,它已逐渐嬗变为一种世界现象。“中国的现代性我认为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性不仅有着与西方的迥异性,还夹杂着不同区域之间现代化发展程度的断裂性,贵州影像的生成与复杂性正是源于自身极具差异化的现代性体验而形成的。“所谓现实都是过去传下来的,向未来伸展,现实不可能停留在‘点’上,现实生活中没有零点。”贵州影像的差异分延,就是对现代性差别性感知下不同踪迹的捕捉。
对于身处西南腹地的贵州来说,它的现代性初体验是一种不同于艺术审美文化的残酷体验,即战争被动性的卷入。鲍曼认为战争是现代性的固有可能,是“在社会失范——不受任何社会约束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无视伤害他人的可能性而做出各种反应”。这种社会约束的目标是外部力量介入中国强加的自私意图而演变的野蛮杀戮,贵州本在远离战争中心区域之外,但偶然失衡的战争格局使得革命空间不断波及与深入贵州的内部,给予战争影像最核心的主题与叙事素材,《突破乌江》《四渡赤水》《遵义会议》等影片都集中凸显着长征红色文化的集体记忆。纵观战争影像的生产,被动性的意识不仅体现在内容的聚焦上,且从影像的生产体制上也可窥见贵州作为从属的非主体立场,历史上贵州电影制片厂从1958建成至1963年全部结束,短暂的存在并未在影片生产上发挥主导生产力,因此早期的较为有影响的贵州战争影像基本上都是由外省电影制片厂出品,如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突破乌江》与《四渡赤水》,这是一种依附于外在力量的空间生产,而贵州作为主导力量的出现在战争影像中是较晚的,直至2005年以后才逐渐有了贵州本土生产主体的战争影像生产实践参与。
民族影像里的贵州是一种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交织体验。贵州山地环境与“溪洞型”生存状况使得贵州当下的民族环境中仍然保存着前现代性的景象,原生态世外桃源里的古朴技艺展示、山地环境中的文化景观、未经商业社会浸染的民族至善都保留着前现代性的痕迹。贵州的前现代性不仅仅有着传统环境决定论的因素造就,还有着历史原因造就的民族多样性下民族文化各自的存留,在民族影像中的原始崇拜、巫傩文化的隐秘原初信仰暗喻的是前现代性表达。但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虽然贵州固有的环境劣势滞缓了经济与文化在现代化上的普适性推导,但是众多偏隅一角的原初民族生态系统,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现代性的入侵,宁敬武的《滚拉拉的枪》中猎人生存技能演化为法律禁止的行为、吴娜的《行歌坐月》里杏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却最终带着遗憾回归故里的唏嘘,这些影像书写对不同时空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进行了内外视角的思考。
后现代意识往往是在现代化的泛化之下而衍生的新的审美趋势,并将现代审美的固有界限彻底模糊化,“后现代主义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文本——其内容形式及经验范畴,皆与昔日的文化产品大相径庭”。贵州作为艺术影像的空间生产被关注,瞩目于新世纪以后的第六代导演的关注,《寻枪》用传统的空间反映了人主体的涣散与物恋的悲剧,继而王小帅的“三线”三部曲的贵州认同书写、再到毕赣的黔东南艺术宇宙呈现都是后现代意识与本土文化景观的相互作用生成的诗意影像表述。这其中,毕赣现象成为艺术影像中被反复阐释的关注点,“导演在调度空间中重构时间的能力比缭绕的诗意和精工的画面更令人惊叹,他在重复、也在延续塔科夫斯基对‘电影最珍贵潜能的思考’”。一种新的诗意美学在贵州的差异空间中不断被读取,外化自然的差异空间成了地方生活经验的内化摄取,成为均质化的城市空间中独特的美学生产空间。而诗意影像的具化逻辑运用在毕赣的演绎下是魔幻现实主义策略的运行,一种“奇异的现实”在时空交错的幻象中,正是源于贵州本土部分空间现代化急速完成与前现代性空间残存的交互感知。
三、解构意义的生产:“泛中心”化下新的西部影像美学形成
纵观不同区域的电影影像表达,贵州电影特征的复杂与意义多元化是一种已然成立的影像事实:战争、民族、艺术的多重交织构筑了贵州电影作为中国电影中具有超越意义的一种个体现象。在当下的区域影像考察中,很难再辨析出如贵州电影般三者截然不同影像的皆存空间,贵州电影呈现出的丰富层次感突破了其他区域电影的一元或二元生产,形成了新的影像审美逻辑判断的可能性。
贵州电影在传统的影像逻辑中并没有呈现出普遍性的类型与形式归纳,因而无法建立中心主体影像特征的唯一性。但这种中心化涣散的意识,并不是虚无主义与游戏主义的思维表述。“解构不是摧毁,而是揭开遮蔽,暴露可能性,关注他者和异域”。“如果一定要确定通过解构人们构建了什么,我要重复我说过的:解构不是否定的,而是肯定的。……如果一定要确定通过解构人们构建了什么……那就是世界的新面貌、人、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新面貌,以及通过解构寻求的新的规则和法则。”正如德里达所理解的那样,电影系统的开放性使得贵州影像获得新的美学意义理解。
贵州影像特征的差异性使得传统的西部电影类型瓦解,新的西部电影美学类型获得了可行性,中国区域电影的多元化进一步得以深化。在中国的地缘电影划分中,贵州电影被笼统地归在了西部电影中,1984年钟惦棐所提出的中国西部片概念指的是立足于大西北的影像摄取。“中国西部片是一种以中国大西北独特的自然景观、悠久的历史积淀和丰厚的人文意蕴为底色的中国电影类型片。”由此可见西部电影在我国的电影语境中有着双重意味:一是西部地区出品或长期定居西部的导演所拍摄的电影作品;二是以生动、逼真的影像来展示、叙述、言说“西部”地区的电影,它可以是写实、表意,也可以是奇观、戏说、神话等。这一原初的电影类型存在逻各斯的中心意识,贵州电影因其泛中心化而颠覆解构了这传统的西部类型标志。
从西部电影的概念上来看,贵州的西部意味较为牵强。首先是地理位置上的偏南,导致它的自然风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与大西北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必定无法在影像外化的属性上形成统一化的风格。其次是从精神文化上来看,贵州是不同省域边缘区域边缘文化的拼合,因此贵州本身的巫文化与四周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滇文化、越文化相互交融扩散,在不同文化“杂”交之下,彼此认同、粘连,最终形成文化的多元。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贵州不同于其他西部地区文化的一元性,如四川的汉文化、西藏宗教文化、云南与广西的少数民族单一主体文化,这构筑了它与其他西部区域文化的别样性。正因如此繁复的文化载体,贵州的影像表达才呈现出了战争电影、少数民族电影、诗意的艺术电影三者迥然不同却又各自彰显的意义,如再以传统西部电影定义去判定贵州影像的创作,显然已无法与贵州电影的外化显现与精神内涵相对应。
贵州影像的不同维度特征交融,延长了地缘电影的审美意义空间,创新了西部电影的概念。“西部电影是一开始就确定了要在追寻自身的无限性发展中来确认自身的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它的问题不在于总结和说明,而在于发展和创新,它不是对创造者的总结,而是对创作的参与与创造”。在当下的中国区域电影中,上海电影、北京电影、香港电影、台湾电影已然成为中国电影的不同中心区域,反观其他中西部地区,单一省域的地缘电影特征读取却稍显片面化。因此新的影像类型的意义赋予,为以往属于边缘影像的贵州话语存在提供了一个更为恰当的空间,一种更多元化的叙事语境。贵州的不同影像在泛中心下达成“共识”的美学意象,“‘共识’不是建立在对一个事物的客观认知的基础之上,而是主体之间遵循一定的有效性要求所达到的一致意见”。在更有效地理解贵州影像的生成与发展下,这种共识性的结果就是新西部电影空间的不同主体间性的确立。
结 语
还原到“一切都是影像书写”的意识里,以解构视域的态度介入贵州电影的思维意义界域里,其差异性、他者性以及新的被遮蔽的意义重新被赋予了在场显现的能力。“从某种它无法定性、无法命名的外部着手,以求确定那被其历史所遮蔽或禁止的东西”。贵州电影作为一种不同区域主体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国区域电影多中心播散行为的生产。以“泛中心”化的视域考察贵州电影的具体历史实践与现实书写,其影像的表达已超越普适性影像规则,衍生出了多面的影像交错。置于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层动因,可以对贵州电影泛中心化形成得出合理性的依据,这对于其他区域电影的差异性剖释给予了可借鉴的反向式思维判辩。正是基于这种多重意义场的过渡和跃潜,在区域电影的研究中,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国不同地缘电影存在的合理意图。于此,中国区域电影不同的影像实现了对位式、症候式的读取意识参与、多层次的影像摄取意义趋于完善、非均质化的影像美学个体区域获得平等化的关注,而这也正是贵州电影个案带来的超越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