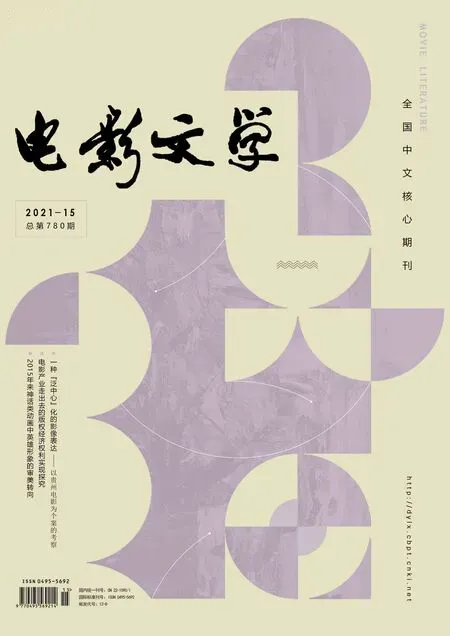影像本体论与《1917》的镜头语言
王福燕 (闽南科技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福建 泉州 362332)
安德烈·巴赞的“影像本体论”始终是研究电影真实美学的重要理论,巴赞认为镜头应当还原事物的本来面貌,剥离掉人对镜头的参与和影响,让镜头中的事物通过自身形象与主体性塑造世界。巴赞的影像本体论对于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也影响颇深,为了提高镜头叙事的艺术真实,电影镜头去技术化,长镜头往往成为诸多现实主义电影导演的共同选择,让观众在一气呵成的镜头中主动参与到叙事中去,最终完成电影真实性叙事。
萨姆·门德斯执导的最新电影《1917》为了最大限度地营造观众的在场感,让观众完全沉浸在历史的“真实时间”当中,采用了技术性的“一镜到底”,即以遮盖等技术剪辑方式将22个剪辑点连在一起,构成了时长119分钟的长镜头。听似简单的传递指令的任务,却在跟随士兵布雷克和斯科菲尔德的镜头中,逐渐显露出战争的血腥和残酷,以及生命的脆弱和意志的强大,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和角色代入感共同汇聚成巨大的心灵震撼。
一、“一镜到底”的长镜头:时间的连续,空间的统一
安德烈·巴赞认为,电影透过摄影机排除人的主观意识,还原事物的本来面貌,真实的记录和还原才是电影美学的根基。巴赞的真实美学思想影响深远,不仅对于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成型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对于电影语言的风格化起到了引导和推动的作用。作为巴赞电影理论的核心,“影像本体论”成为诸多想要塑造真实、还原历史的电影创作者的主要理论工具,避免人为剪辑、蒙太奇造成的人的主体意识的传递,而是通过纪实性的镜头记录连续的时间与统一的空间,让镜头对准的人、事、物主动“说话”,还原镜头对准的世界的本来面貌。而巴赞的影像本体论与长镜头的艺术特征不谋而合,在诸多追求真实美学的电影中广泛应用,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长镜头语言的发展。
长镜头丈量的不是镜头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当然也不是焦距或实际镜头的外观长度,而是一个时间概念,是指从开机到关机的时间间距,长镜头没有固定的统一的定义标准,而“一镜到底”既是一种技术手段也属于长镜头的一种。在现实主义创作的黄金时代,长镜头被看作是艺术片的基本构成元素,往往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或者是具有震撼力的事件的完整发生发展过程。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以及其对电影制作的浸润,拼剪辑、比技术的数字电影早已将拖慢叙事节奏的长镜头淘汰,只有极特殊的叙事情节才会采用适当时长的长镜头进行艺术表现。极少数的电影为了探索长镜头的叙事边界,探索长镜头技术的更多的表现可能,大量使用长镜头,或者极端的追求“一镜到底”的长镜头手法拍摄,其目的一方面是满足艺术真实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炫技或加强艺术张力,如《俄罗斯方舟》(2002)、《维多利亚》(2015)等影片。此外,还有一类电影是采用“伪一镜到底”,即用黑幕或遮挡衔接的方式连接多个长镜头,使其成为看似摄影机不停拍摄的一个超长镜头,如希区柯克的《夺魂索》(1948)、冈萨雷斯的《鸟人》(2014)等。
《1917》同样采用了这种“伪一镜到底”的长镜头手法,而导演萨姆·门德斯并非为了炫技,而是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延展时空,让连续的时间和动态的空间变化和谐统一地完成客观世界的还原,因为仅需客观真实地还原这段真实的历史,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两名送信士兵的所见所感,看到生命的流逝,人内心的恐惧,战争的无情,就足以震撼人心,充分表述影片的和平主题以及对牺牲精神的赞颂。
二、观众的在场:“真实时间”中的沉浸式体验
在影像本体论的视域中,对自然对象的完整的、真实的再现包括对自然光、声音、色彩等全部环境信息的再现,自然的世界被真实地记录在镜头当中,自然会与镜头画面另一端的观众进行对话。巴赞“影像本体论”倡导的真实美学倾向于一种倡导创作者真实记录、观众沉浸观看的美学,观众的主动感受是对真实美学进行审美活动的关键。因此,“一镜到底”的长镜头强调的时间与空间的连续性与延展性,给予了培养观众在场感以极大的帮助,这种形式主动地帮助观众进行了角色代入的审美活动,观众在相对真实的、连续的时间和空间内得以实现沉浸式体验,与镜头时空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1917》的题材内容并不新鲜,同类型的战争电影如《血战钢锯岭》《拯救大兵瑞恩》《敦刻尔克》等,或是塑造了救世主一样的英雄人物,或是打造了史无前例的震撼的血腥战争场景,抑或是书写了另一种逃离战争的人性之歌。导演萨姆·门德斯认为,《1917》的故事已经足够震撼人心,无须通过花哨的镜头剪辑制造紧张感或加强戏剧张力,“一镜到底”的长镜头能够给予观众与主人公并肩作战的角色代入感,与人物共同经历,在张弛有度的情节中顺理成章地产生共情心理。
于是,观众从《1917》的第一个镜头开始就与士兵布雷克和斯科菲尔德一同呼吸,肩并肩前行。影片从开满鲜花的原野上开始,镜头逐渐拉远,正在小憩的士兵布雷克和斯科菲尔德慢慢入框,观众可以通过镜头中微风拂动的花以及闭着双眼的二人感受到一丝惬意,随后第三人的入框打破了这份安静祥和,镜头中的人物不断对话、行走,周围环境逐渐从开满鲜花的草地变成堆满沙袋、布满泥坑的战壕,镜头移动过程中不断出现在画框中的自然事物主动释放着信息,迅速将观众拉入战争氛围当中。
由于影片故事与当下相去甚远,与观众有着巨大的审美距离,如果直接通过镜头的剪辑将导演的主观思想和情绪传递给观众,这始终是一个被动的审美活动,唯有更强烈的戏剧张力和视觉冲击才能让观众有更强烈的感受。因此,《1917》的“一镜到底”的长镜头在连续的时间内让观众在场,布雷克和斯科菲尔德经历的松弛片刻或者生死瞬间,观众都有完整的参与感和在场感,各种情绪也都是自然而然生发的,没有了导演主观剪切镜头的外部干扰,《1917》完全提供给观众一种沉浸式的观影体验。
虽然影片的119分钟并非是故事描述内容的真实时间,观众只是在长镜头中连续的时间内体验了相对的真实时间,但跟随主人公在不断变换的空间和推移的时间中获得的沉浸式体验是无比真实的。也正是在推、拉、摇、移的镜头运动当中,观众在镜头的视角移动中主动参与其中,对各个部分的叙事都产生了自己的理解,最终一同参与并完成了叙事。
三、审美的距离:镜头运动对其的有限消弭
《1917》的故事发生的背景与观众所处的现实世界相距甚远,即便影片在一镜到底的长镜头中还原了一个不间断的、连续的、完整的时空,但镜头中的人、事、物(即审美世界)依旧是与观众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换言之影片所塑造的战争美学对于观众的认知审美也是浸入式的,观众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审美接受并产生审美共情,然后主动参与到电影叙事当中去。因此,《1917》需要在避免传递导演主观思想情绪的前提下,通过镜头的运动来缩短观众与片中世界的审美距离。
(一)审美共鸣
无论是“一镜到底”的长镜头,还是镜头运动的克制和把控,都印证了“影像本体论”之于《1917》创作的重要性,该理论的核心——真实美学也是导演门德斯想要呈现的重要美学内容。观众在第三人称的镜头视角下获得了在场感,并在关键性场景的多次反打镜头下更深刻地代入了角色和情绪。
影片通过周围环境在镜头中的不断变化,观众不断接收到大量的信息,逐渐根据镜头中连续的时间和空间内出现的人和事物梳理内容、建立认知。片中大量的跟拍镜头始终保持与主人公士兵布雷克和斯科菲尔德水平一致,制造第三人称视角,几乎保证了观众与二人的视线高度是统一的,与二人在送信的路上共同进退。为了给予观众在场感,萨姆·门德斯在运镜方面不仅维护了第三人称视角的合理性,即镜头没有戏剧性的运动,也没有凸显镜头的主体意识,同时也做到了镜头的运动与人物状态和环境氛围协调一致。但是,镜头的情绪化并非是人为赋予的,而是通过镜头与人物之间距离的远近(人物始终是镜头焦点),以及镜头移动过程中入画的自然事物,让镜头中的事物主动传递信息、交代的。影像本体论支撑下的镜头语言,保证了观众获得的全部信息都来自镜头中出现的自然事物,而这种浸入式的观影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观众与影像世界的审美距离。
(二)审美间离
长镜头的本来用意是通过避免人为地切换镜头、剪辑造成的审美异化,剥离摄影的技术性,去掉镜头意识,规避掉导演在镜头前的主体意识,尽量做到自然地记录。但是,《1917》即便做到了对镜头运动的克制,但片中大量使用的360度旋转摄像机的方式,仍然强迫观众脱离角色代入感,产生了审美间离性,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即便这是一种近乎于上帝视角的摄影方式。此外,为了强调一些情节与场景的隐喻色彩,影片在镜头的运动上依旧采用了一种上帝视角。例如,斯科菲尔德头部受伤后从地上爬起来走到外面,摄影机沿着斯科菲尔德的视线移动到二楼,敌方士兵的尸体倚靠在窗边,窗外空中腾空而起的燃烧弹瞬间将房间照亮,也将窗外废弃的小镇蒙上了一层诡异的光影,此时镜头越过窗户一跃而下,斯科菲尔德蹒跚地入画,其前方的小镇如鬼域一般,远处燃烧的火焰和近处不断射向他的子弹加剧了此处的恐怖氛围。此处运镜与构图的隐喻性不言而喻,林立的残破废墟,熊熊燃烧的火光,不断划过头顶的照明弹和落在脚边的子弹,斯科菲尔德脚下的路正如通往地狱之路一般,死神的触手如同头顶嗞嗞燃烧的燃烧弹一般不断追逐着斯科菲尔德。在如此强烈的隐喻性和戏剧性镜头场景中,镜头再次间离了观众与影片的审美。
因此,无论影片《1917》的长镜头如何消弭片中影像世界与观众所处现实世界的距离,在运镜方面依旧存在审美间离的情况,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镜头运动导致的审美间离强化了观众的主动审美。
战争片《1917》对长镜头的技术性应用,一定程度上将战争电影的叙事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相对于其他战争片追求的蒙太奇式视觉冲击,导演萨姆·门德斯用“一镜到底”的方式为观众制造了一场角色代入一般的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在影片119分钟的相对的真实时间当中,战争的残酷、命运的无常、生命的脆弱、人性的复杂等,观众与士兵斯科菲尔德执行任务的全过程一同感受。安德烈·巴赞的影像本体论是解构该片的重要理论工具,片中完全采用自然光,最大限度地遵照影像本体论对于真实美学的要求,长镜头使时间得以连续,也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故事背景与观众之间的审美距离,让观众更深切地感受了影片诠释的真实美学。
但影片刻意强调“一镜到底”长镜头的技术也一定程度上拖沓了影片的叙事节奏,镜头中自然事物的信息传递能力有限,使影片更多地成为一部感受型电影,人物的塑造也有扁平化的倾向,主要人物布雷克和斯科菲尔德的个性欠缺,但这些都不影响该片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尤其是影片在当下数字电影时代做出的真实美学回归,观众透过这样一种具有挑战性的艺术实践,充分理解并体会了导演门德斯透过电影传递的值得敬仰的牺牲精神,影片核心的反战主题也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