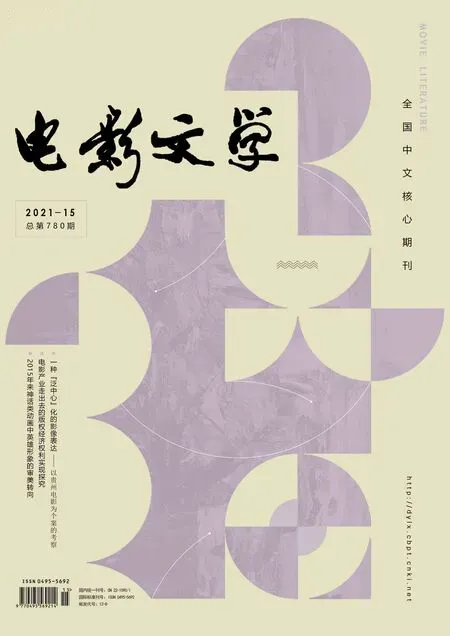新时期以来国产青春类型电影文化转向分析
王 蒙 高殿银
(1.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2.宜宾学院文学与音乐艺术学部,四川 宜宾 644000)
2002年中国电影产业改革之后,海外分账大片进入中国电影市场,中国本土电影饱受冲击,针对此现象,类型电影的研究有了更加现实、深刻的意义。类型电影分类依据的分歧、类型电影理论与电影创作关系的错位,成为一个深刻而重要的学术问题。青春电影能否被当作一种类型片?它成为类型片的独特性在哪里?从题材所指的中国青春电影类型到观念、范式建构完善的中国青春类型电影,它们在电影文本观念、青春类型元素和艺术特质上有何种变化?这些成为中国本土电影在好莱坞惯性语法系统中建构自己话语权并形成一种成熟的、特有的民族化类型电影的重要问题。
如今,“电影类型”被片面当作“一种艺术语言的规范和审美创造接受的心理架构”;而“类型电影”也只能在“电影语言”和“创作观赏的类型系统”两个方面满足观众的趣味鉴赏;试图将两个概念完全对立的研究立场,违背了类型电影是一种“带有文化性质的工业制作”的普遍认知。当电影“被允许进到理论的神圣殿堂里去”时,它只能权衡“文化”和“商业”两者比重,却不能被另一方所吞噬。所以类型电影是“电影制作者的美学表现,同时也看作是艺术家和观众在协同表达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因是之故,类型电影中“类”的划分均由题材产生,而它能够被观众普遍接受的前提必然是题材叙事的成熟。从一种题材所指的电影类型到“观念”与“范式”固定的类型电影,无疑才是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类型电影的理论范畴下,“青春电影类型”和“青春类型电影”间的关系,亦是遵从这个规律。中国青春类型电影既然可以成为一种成熟类型,无疑其在类型观念、类型元素上有独特之处。
“青年”形象以其敏锐的社会感知、思潮的前瞻性常常是影视作品中不会缺席的重要元素。从《劳工之爱情》(1921)中的郑木匠,到《马路天使》(1937)中的小红、小陈;从“十七年电影”《柳堡的故事》(1957)中“副班长”与“二妹子”,到“文革电影”《闪闪的红星》(1971)中的潘冬子;从“新时期”以来《湘女萧萧》(1986)中的萧萧,到新世纪以来《少年的你》(2019)中的陈念。“青年人”的形象、“青春残酷影像”已经在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逐步清晰起来,中国青春影像也在电影发展史的维度完成了从元素奇观的“青春电影类型”到“观念”“范式”完备的“青春类型电影”的建构。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青春类型电影”没有停留在“一种题材所指,甚至只是一个更大的概念范畴”,它与爱情片、武侠片、西部片等“类”一样,在情节、角色、布景、主题、技巧、明星以及观众消费心理等元素的处理上已经呈现共有的影视叙事文法特征。
中国青春类型电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城市与乡村”影像空间的解读;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西方文论东渐的文化背景下对社会人生、人学内涵的分析;新世纪海外影视资本涌入中国电影产业背景下对中国电影产业变革和市场重组有着极为深刻的样本研究作用。中国青春类型电影符合了艺术分类的两大基本原则——“统一性原则和稳定性原则”,从艺术形式对观众观影快感的培养上,中国青春类型电影的“青春形象”完成了从奇观到反思的突转;从艺术内在的文化意蕴构成上,中国青春类型电影的“观念”和“范式”完成了“以电影的表现方法来发挥电影艺术特性”的审美追求。
一、中国青春类型电影文本“观念”成熟:从父权的式微到女性意识的觉醒
文本“观念”稳定是中国青春类型能够归到“类”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电影史视角下的中国青春类型电影在表达父权/夫权、母性/女性、伦理/法律、尊严/自尊等主题上有独特优势,其“所承担的主题和社会意义的元素”虽然随着观众审美新鲜感的趋势变化,但最终还是回归到青春的终极宏大命题——父权的式微和女性意识自觉上。因为针对“残酷”的青春来说,对威权的反抗和“成为人”的向往是青春类型片的精神实质。
1975年,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一文中提出叙事电影“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在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之间发生分裂”,女性在电影中被男性凝视,同样,当观众的目光通过银幕投射在女性身上时,观看癖促使观众在这一观影过程中产生欲望的满足,这种“被动/主动”与“被看/看”的关系,使得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身上承载诸多不平等。尽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女性获得一系列的政治权利,在社会组织生活上也使女性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意志,但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女性独立意识的建构之路依旧曲折漫长。
男性/父权曾经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极为明显特殊含义,早期电影《劳工之爱情》(1922)在家庭伦理剧的模式和思想局限之下,“父亲”形象强势介入到家庭关系中,“父亲”的许可使“女儿”得到爱情,即便在他需要“女儿”帮忙缝补衣物时,亦是“女儿”弯腰依附在父亲的身形之下,这无意中反映了民国初年父权在社会组织中不容置疑的地位。善于“直面现实的爱与憎”的左翼影片《姊妹花》(1934),一方面在感叹“可怜是穷人,可怜的是女人”,另一方面又喊出“女人不是各个都可以给你们欺负一辈子的”。这里青年女性作为独立“人”的追求初绽,这是对父权的一次并不成功也无法成功的抗争。尤其这里的“父亲”想要偷偷带走其中一个女儿,挑选谁能在将来变得更漂亮时,导演破天荒地使用了俯拍镜头,虚伪、猥琐的“父亲”形象跃然于观众眼前,父权的社会控制力在电影艺术史层面开始瓦解。这种质疑所持续的时间有限,到“十七年”电影时期,父权与政治发生置换,在意识形态的文艺机制中,父权依托意识形态重新拥有绝对的权威性,更不用说“文革时期”所宣扬的“要破除对所谓的30年代文艺的迷信”,创作者在此时描绘的青春形象,极力模糊性别界限,以革命同志的阶级感情替代了其他所有的“人”的私有情感。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承载着父权的式微重新显现。张暖忻导演的《青春祭》(1985)里,不懂青春和美是什么样的李纯,刚开始穿着粗布蓝衫,极力掩盖身体的曲线,直到在傣家姑娘依波的刺激下,她开始意识到青春的“美”,这也是她作为一个女性对自身认知的开始。李纯这个女知青由接受挑水,到之后在迷雾中划船离开,最后她身后寨子被泥石流吞没。由水开始,由水结束,“水”的意象承载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女性的青春被封印于父权的窠臼中。
虽然这一场为女性发声的尝试在中国青春电影发展中略显羸弱,但伴随着《周末情人》(1993)、《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十七岁的单车》(2001)等电影的出现,女性似乎都成为其中男性的成长附属。但不可否认,女性导演的出现使青春影像中以女性为表现主体的部分逐渐增多,并且出现了一次次的父权反抗。
《红颜》(2005)中的小玉,面对母亲的质问,站起来反抗,用一种决绝方式来试图冲破社会加筑的伦理道德之墙。可是她力量微弱,人们对她睥睨、嘲笑、猎奇和消费的目光背后,反映出成人世界对于青年女性的强大控制欲。十年以后,小玉“成为人”再次面对同样的目光,她毫不犹豫选择反抗,这时小玉的身体,不再是曾经干瘪未完全发育的瘦弱躯体,而是玲珑有致的成年女人身体,她不再因此羞愧,青春时期的困惑伴随着成长逝去,但女性青春的叛逆灵魂依然会落入无因的窠臼中。当《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2011)成为分界线,青春电影呈现出新的形态,根据众多文学作品改编的青春电影席卷国内电影市场。女性的身体成为其中不断被消费的主体,女性形象的建构面临一次巨大的转折。《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匆匆那年》(2014)、《同桌的你》(2014)都将女性形象变为男性成长的附属,在男性成长过程中充当着辅助的作用,同时青春时期的爱情变为最重要的表现部分,将女性成长过程中的诸多环境悬置,模糊了女性形象的多样性与反抗性,仿佛爱情成为女性唯一的选择。包括冯小刚执导的《芳华》(2017),虽然将青春置于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但是仍可以看到对于女性身体的视觉消费。
随着“消费青春”的浪潮涌动,一部分女性导演站在同性别立场思考女性的成长究竟面临着什么?文晏导演的《嘉年华》(2017),将焦点集中在了挣扎在成人社会中的几个女孩身上,15岁的小米谎报年龄在海边一家宾馆打工,逃脱乡村,急于加入成年人的世界。她做出三次选择,首先在面对小文身体与心理受到双重侵犯的真相时,她选择了撒谎,之后她用最为残酷的成年人方式去解决问题,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被打之后的她“恍然明白”,原来在成长这条路上,女性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身体,所以她选择利用自己的身体,试图在残酷的成人世界获得一席之位。但小米在威权的强势裹挟下,最终选择反抗——骑车逃离。电影中她与被拔起的玛丽莲·梦露塑像一起出现往前方驶去,如同《末路狂花》(1991)结尾那一场飞车坠崖的场景,青年女性用肉体逝去的方式,发出灵魂的怒吼。这一场交织在男性目光中的身体寓言的隐喻,是国内无数青年女性形象的无声反抗。
青春影像中女性形象发生的这几次明显变化,与历史传统、政治动因和文化冲突是无法割裂的。而青春影像中的女性主体建构,毫无疑问是中国青春类型电影文本观念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中国青春类型电影观众的审美观念培养:青春形象从“被消费”到“独立观照社会”的突转
“青春形象”是中国青春类型电影中最重要的类型元素,对其赋予更多文学性价值和“现代性”的意涵,以达到引导大众审美、培养固定受众群的目的,亦是其类型化逐步成熟的标志。中国青春类型电影中的青春形象经历过一段建构——解构——重构过程。电影《顽主》(1988)里青年形象所表现的“迷茫”和“反叛”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群体形象的关键词。正如《周末情人》(1993)的旁白所说:“不是社会不理解我们,而是我们不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表现了这个时期,青年人置身于各种社会思潮激荡下的迷茫与恐惧,他们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来发声,却最终淹没在成人时代的狂潮中。《摇滚青年》(1998)里的他们在广场上尽情跳舞,但却耻于在成人世界看似成熟的围城里展现自己的身体;《顽主》里的3t公司,像是青年人建立起来的乌托邦式幻城,用于反抗“成功人士”的一切,观众们在影片结局清楚地看到青年三人组走过公司门口的长队,这无疑是对现实世界赤裸裸的嘲讽;《周末情人》终日排练的地下乐队,也正是这群青年人不安现实、独立思考“又不得”的口号,架子鼓的鼓点声是他们内心躁动不安的呼喊,又是空虚被无限放大后的失落。
第六代导演善于表现“反叛的青年形象”,“多少带有某种现代主义、间或可以称之为‘新启蒙’的文化特征,他们步入影坛的年龄与经历,决定了他们共同热衷于表现的是某种成长故事;准确地说,是以不同而相近的方式书写的‘青春残酷物语’。”大岛渚的《青春残酷物语》(1960),对日本电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青春残酷物语”一词也随之形容青年人在现实社会中的迷茫、无因的愤怒、反叛、绝望、暴虐,承载着青年人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窒息的生存状态,而其中的核心,无疑是对固化社会阶层的挑战。
王小帅执导的《十七岁的单车》成为中国第六代导演“青春残酷物语”的代名词,十七岁的青少年不懂如何与社会相处,将成长寄希望于一辆单车,付出的代价是残酷的,在这一场名为成长的战斗中,他们头破血流、伤痕累累;贾樟柯的《小武》(1998),小武时常穿着宽大的西服、抽着烟游荡在城镇的大小街道,他是那个时代青年形象的缩影。在乡村城市化进程中,小武熟稔的社会记忆逐渐消亡,最终被社会抛弃,成为弃儿。
当然,青春残酷物语并没有在这里截止,到2006年吕乐的《十三棵泡桐》,青少年的成长都伴随着原生家庭的种种问题,将时代背景悬置之后,青少年们“无因的反抗”显得更加明显。传统家庭构成的崩解,让生存其中的青年人尝试在其他社会构成元素中找寻到慰藉,最终只能用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成长对他们来说,是一条如此艰涩的道路。这种艰涩的成长处境也存在于李玉的《观音山》(2010)中,青年三人组所面临的困境依旧揭示了青年人在这个社会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高考落榜、居住地拆迁、县里的姑娘力图摆脱乡村的束缚,三个人一起租房,逃离原有的地方,找寻属于青年人的生存空间。同样,以《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2012)为分界线,一夜之间滋生了无数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中国青春类型电影,青春形象的情感开始被消费,观众好奇的目光集中在校园爱情这一主题之上。麦克·费瑟斯通在谈及消费文化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时曾说:“随着消费文化中艺术作用的扩张,以及具有独特声望解构与生活方式的孤傲艺术的解体,艺术风格开始模糊不清了,符号等级结构也因此开始消解。这需要一种多元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各种不同的品位,对待文化的消解分化过程,其瓦解了区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基础。”不难察觉出2012年—2015年的包括网络大电影在内的青春影像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青春形象逐渐类型化,模糊了单个的主体特征。《匆匆那年》(2014)、《同桌的你》(2014)、《栀子花开》(2015)、《左耳》(2016)等影片,以“怀旧”为主题,借势走上一条“消费青春”之路。
2015年以后,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遭遇困境,以青春片为内核的类型融合浪潮奔来,从爱情怀旧主题复归于对现实世界的思考:《狗十三》(2013)、《黑处有什么》(2015)、《嘉年华》(2017)、《大象席地而坐》(2018)、《谁先爱上他的》(2018)、《过春天》(2018)、《阳台上》(2019)、《少年的你》(2019)等影片,将潮头上社会目光下的青年形象解构的同时,也在重新建构青春片中的主体新形象。
《谁先爱上他的》将传统伦理道德撕开一条口子,使观众的目光转移到青年人中这个群体生存的真正状态,青春片的主体所承载的目光,有了背后的意义与价值。影片中所反映的台湾地区家庭离散更多是因为人心之变,中产阶级家庭观念的解体,让传统血缘伦理陷入了危机。为了对抗这种危机,影片的创作者虚构出一个非血缘家庭的温情图卷。这是对中国当下价值危机的一种想像式救赎,在现实压迫下的道德焦虑感明显呈现。这也说明了,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青年人期望以构建一个新的伦理道德社会,弥补情感上的缺失。胡波导演的《大象席地而坐》,体现了青年创作者对于青春成长的反叛,作为导演的胡波,也用自己逝去的生命,表达着对成长伤痕的反思与绝望。“满洲里”在电影中,就像是《等待戈多》中的戈多,它作为一个意象的存在,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而一直坐在“满洲里”的“大象”,就是不断在现实中迷茫、跌倒、愤怒的年轻人。《狗十三》中,李玩也是在成长过程中跌跌撞撞,她与小狗一样,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父权的压迫之下,李玩最终学会了成人世界的语言,忍受着翻滚而来的呕吐感,咽下一口狗肉,那是对成人世界无声却有力的控诉。青春形象发生的突转不仅标志着创作者们从迎合大众审美到引导大众审美的转变,也标志着中国青春类型片“娱乐属性”之外所承载的“为生民请命”的文化精神。
三、中国青春类型电影艺术形式成熟:空间叙事话语体系的建构
电影空间是影片的一个重要部分,空间叙事以电影空间的特征为基础。“电影空间的生产既是对现实空间的呈现,同时也是对现实社会空间的想象、生产乃至补充。”不论是作为青春影像中重要地理空间的城市、城镇和乡村,还是独特空间废墟、乌托邦,首先具有青年人“生存空间”与“想象空间”的双重表意、同时兼具“空间叙事”与“文化隐喻”的双重内涵。在观照70年来中国青春电影的发展变化这一过程中,空间叙事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中国青春类型电影艺术形式成熟的重要表现。
《顽主》的故事发生在北京——一个有着较强政治隐喻的城市,影片以三个青年在城市中的创业过程为线索,上演了一幕批判现实主义的“人间喜剧”。青年们生存在北京这座城市,以“社会刺刀”的形象将当时的社会假面撕开,反映隐藏的历史问题、社会问题,从而批判现实。这也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北京、广州、上海发展迅速,生活在城市中的青年们,却找不到一个适合的生存空间。当《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北京已经远离20年代90年代的青年人,这些人的成长记忆和马小军们一起留在了那个特殊的年代,当代青年们如今只能在城市的阴暗处残喘、反抗。电影《周末情人》镜头所及之处的城市,没有广阔的天地,只看到逼仄的角落:阴暗的地下室、昏暗的楼道、狭长的走廊,无不隐喻着这群青年人在逐渐繁华的城市化进程中狭小的生存空间。手持摄影和明暗交织的光线,搭建出不稳定的青春电影空间,强调城市中青年人徘徊与迷茫的现实境遇。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阶级革命的淡化和市场经济的兴起,中国卷入全球化经济浪潮。此时城市电影的复兴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同步,践行着近乎一致的路径:城市化进程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都市开始,继而在深圳、成都、武汉等二、三线城市普及,与此同时,城市电影的叙事空间也相应从北京、上海和广州扩展至其他城市。”可以看到,青春影像的地理空间选择也从北京、上海等城市转移到山西、四川、贵州等省份的一些小城镇上。山西、四川、重庆、贵州从地理位置来说,远离经济飞速发展的沿海地带,但这些地方都极具传统文学价值,以往文学创造的精神赋予小城镇青年“以个人生命史、心灵史、血肉情感和性格发展的逻辑”。《红颜》(2005)中小玉的青春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开始,又在小县城结束,湿漉漉的街道,笼罩了一层迷雾,就像是一直跟随小玉的青春伤痛。《小武》中,贾樟柯拍摄了自己的家乡——山西汾阳,摇滚、西服、皮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小城表征,随处可见的“拆”字,是小城必不可少的伤痛,小武终日在这座小城的街道上游走,无法适应社会的飞速发展,只能守着自己的“老手艺”,被围观的他就像是被城市化所包裹的小城,迷茫、孤独、无助。
“与城市相比,乡村是中国电影中一个稍晚出现,且甫一出现便是有着自然美学和意识形态双重意味的空间范畴。”胡炳榴的《乡音》(1983)、张暖忻的《青春祭》立足乡村,摒弃对大城市中青年生活的描摹,此时乡村空间所承载的历史与社会意义,不仅是乡村这一空间地理位置本身的特点,也彰显了其意识形态属性,并建构出一种回归现实、终极浪漫的电影创作观念。从社会性来看,乡村既代表着淳朴、自然,也无法摆脱其历史基因中落后、贫穷的片段。所以在青春影像中,有青年回归乡村,期望“乡村的疗愈”;同时也有青年逃离乡村,渴望“都市生活”的狂欢。这与青年人身上所带有的反抗特质、独立精神无法割离。
1947年,费穆执导的《小城之春》,废墟作为空间叙事的重要元素出现,断壁残垣成为影片中传统伦理道德崩解的见证。废墟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作为主体、意象、空间等形式反复出现,承载着众多的意义。显然《观音山》中地震后的废墟,这一空间元素包裹的是灾难所带来的伦理社会中无法弥合的伤痕与青年人对“大同世界”的虚妄坚守。《风中有朵雨做的云》(2018)亦是如此,城中村的废墟,标志着疯狂城市化进程下被同化与消解的乡土文明。在中国青春电影的创作中,“废墟”成为青春影像叙事的一个重要空间,不仅介入于城乡文明割裂的现实,还承载着当代青年人的迷茫、恐慌等情绪。
“乌托邦”一词,本身兼具双重悖论,即“美好”和“乌有”。乌托邦作为电影中的异质空间,在中国青春电影中是重要的叙事空间,利用这一想象中的空间,揭示出青年对于现实的逃避,渴望通过“乌托邦”找寻生命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大象席地而坐》中,“满洲里”即乌托邦,逃离城镇带来的苦痛,实则是逃离成人世界的冷漠,期望用乌托邦来解决现实问题,并由此呈现了一出存在主义悲剧。《观音山》中青年人的疗伤地点,不是更大的城市,由于城市中的空间对他们来说越来越逼仄,因此他们追求一个理想世界的乌托邦。悬崖上的观音庙、船、河、火车、铁道,看似是地理位置上的乡村,实际是乡村背后的乌托邦。中国青春影像的叙事空间表现了同时代的青年人生活以及相应的社会问题,与青少年、青年形象建构融为一体,是中国青春类型电影艺术形式逐渐成熟的重要表征。
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经历着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青春类型电影的研究,应当放置于现当代文化史、艺术史以及中国电影发展的“大历史”背景下去考量。类型电影的理论研究不能一味地“法古”,它“不应被视为一个在形态学意义上的完全封闭的系统”,实则类型电影的理论一直处于消化吸收各种思想,并不断前行的动态之中,这样才能使类型电影的理论适应层出不穷的电影创作,也是改变类型电影理论一直滞后于电影实践的不二法门。特别是当中国电影产业多种指标进入世界前三,中国电影正在成为世界电影产业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摒弃“类型电影”中的“文化”属性,“世界视野下的民族电影”这一发展目标则无从谈起。我们能够清楚地察觉到:其一,类型电影“类”间的元素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其二,类型电影的发展与“民族电影”并不冲突,电影的创作者会极力找寻它们在“商业”与“文化”的结合点。至此,中国青春类型电影里“青年形象”已由《同桌的你》中的消费“奇观”转变为《大象席地而坐》的“思考”其社会存在价值;对于青春类型电影的评论也从“泛西化”的倾向转换成“世界视野之下”“民族电影”的阐释。观众们近些年欣喜地看到一系列“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中国青春类型电影成为主流。中国青春类型电影满足了特定观众的审美需求、具备类型片特征和独特的叙事话语模式,它成为一种依托商业与资本制作,借助青年视角观照其当下生存处境的新一轮现实主义类型创作的潮头。新世纪以来的中国青春类型电影在“影像本体的艺术电影、人学内涵的现代电影和世界视野的民族电影”的映照下,为中国的类型电影发展进行着执着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