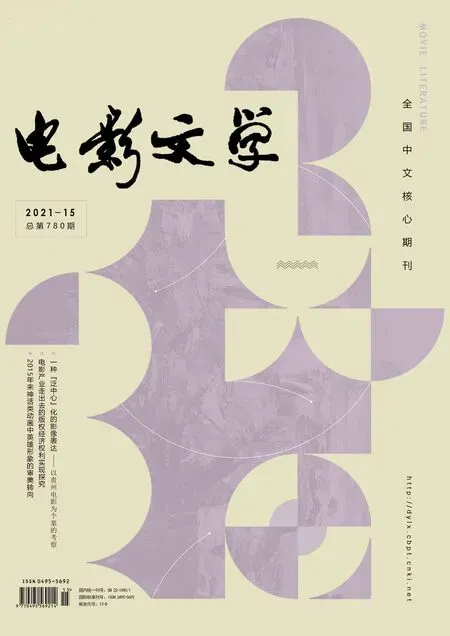媒介素养视域下的电影批评与实践
——以20世纪20年代为例
张 琳 (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一般认为,媒介素养的研究源自社会行动诉求,其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发展契机均来自电影。20世纪20年代,电影从默片时代跨入有声电影时代,声音的出现不仅给电影制片商带来了巨大的票房收益,也使电影以强大的视听表现力及低廉的售票价格吸引青少年走进电影院。据统计,1929年美国的未成年电影观众大约为4000万,其中1700万观众年龄不到十四岁。面对电影媒介的强大影响力,人们对其是否会影响青少年成长的争论愈演愈烈,为了应对电影对观众的不利影响,“佩恩研究”应运而生,被认为是媒介素养的早期实践。几乎同一时期,电影的故乡法国巴黎,为应对电影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创建了法兰西电影俱乐部,引导观众发掘电影的艺术性和文化性,形成了媒介素养教育的早期尝试。而“媒介素养”概念的首次提出,同样与电影媒介有关。1933年英国保守主义文化学者利维斯和他的学生桑普森出版了《文化和媒介:媒介批判意识的培养》,针对以电影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兴起,及其所推动的大众文化变革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担忧,为了抵制大众流行文化对传统精英文化所产生的恶劣影响,首次提出了“媒介素养”的概念。因此,从媒介素养的角度考察我国20年代电影批评与实践,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媒介素养思想萌芽,既具有现实的理据性,同时也有助于拓宽研究视域,与世界媒介素养研究产生共鸣。
伴随着媒介技术的革新以及人们对媒介认知水平的进步,媒介素养研究经历了从“保护主义”到“文化识读”到“批判主义”再到新文化背景下“参与赋权”的范式转移,媒介素养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虽然概念之间有所差异,但关于媒介素养的主要研究内容却基本取得了共识,包括:媒介信息批判认知的建构,媒介近用能力的培养以及媒介行为主体的规范。以上三方面在我国早期电影批评和电影活动中均有所体现,可视为我国媒介素养思想的萌芽。
一、伦理批评:批判认知的理念与建构
自1896年电影进入中国,既呈现出与世界电影发展大致相同的规律,又与我国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紧密相连,表现出文化与国家的差异。“影戏观”作为我国早期主要的电影观赏与创作理念,与法国电影艺术家侧重“记录真实的生活”的理念相区别,体现出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性审美心理和电影逻辑——在承接传统戏曲大众性、娱乐性的基础上,强调教化功能。中国的“文化”概念自古以来就包含了以“文”来“化成天下”的意蕴,“文以载道”成为大众文化的内在逻辑。电影,作为19世纪末出现的新兴视觉艺术,借助新颖的表现形式、奇观化的视觉影像,迅速俘获了中国大众的目光,表现出对电影“奇观”的赞叹与仰视,认为电影“开古今未有之奇”,电影被纳入大众文化的类型范畴,实现“寓教于乐”的教化功能就成为其生存发展的必然逻辑,进而促进了20世纪20年代电影道德伦理批评模式的形成。早期的电影实践者,如漱玉、李柏晋、顾肯夫等,出于艺术的自觉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对电影存在的负面影响提出警醒与担忧,体现了对媒介构建现实和传播意识形态功能的早期认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电影视觉语言原始综合的完成及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建立,美国逐渐取代法国,垄断了世界电影市场,中国也不例外,美国片几乎独占了中国的电影银幕。当时美国输出到中国的影片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制作粗劣、审美低俗的影片,另一类是具有较高制作技艺、反映一定社会意义的影片,如卓别林的滑稽短片以及格里菲斯的影片。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人一方面通过观看欧美电影,学习钻研先进的电影拍摄技巧,另一方面也对部分欧美影片内容低俗、道德失范、中国人形象猥琐等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和抵制,此时的电影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抵制影片中诲淫诲盗的低俗文化
一直以来,“批判”以及“批判意识”作为媒介素养的关键概念,包含了对媒介内容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接收和选择性理解理念,抵制低俗文化,拒斥不良内容,在我国则体现为,以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为批评标准,在文化与道德两方面对电影中有关犯罪、性、暴力的描述及其他不符合公众道德观念的题材进行评判。漱玉在《电影言论与事业》中指出“或剧情过于荒谬,或艺术不堪瞩目,……即千百有识之观众,亦无不受其愚”。李柏晋从电影的社会功能视角对媒介效果进行了辩证的思考,提出电影既能“导社会于淳朴高尚,发扬民族精神,巩固国家基础”,反之也能“陷社会于骄奢淫逸,辱国羞邦”,甚至“能使亡国灭族”。20世纪20年代,中国正在经历社会政治制度的大变革,中国电影人脱离了电影具体特性的文化批评,与利维斯对流行文化的反思与抵制不谋而合,成为促进中国媒介素养思想萌芽的原始动力。
(二)抵制他者视域下的国人形象污名化
1922年美国学者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的概念,媒介创造信息的“拟态环境”,将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世界联系起来,强调媒介对现实的建构功能。而媒介本身也是被建构的,世界信息传播资源和结构的不平衡,导致媒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媒介欠发达国家的污名化。顾肯夫在1921年《影戏杂志》的发刊词中谈道:“外国人来中国摄剧,都喜欢把中国的不良风俗摄去。”“无论长篇短篇,要是没有中国人便罢;若有中国人,不是做强盗,便是做贼。做强盗做贼,也还罢了,还做不到寻常的配角,只做他们的小喽罗。一样做一个侍者,欧美人便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侍者;一换了中国人,就有一股萎靡不振,摇尾乞怜的神气”,进而发出了中国人在欧美影片中“人格破产”的哀叹,并警醒道:“没有到中国来过的外国人,看了这种影片,便把他来代表中国全体……,哪的不生蔑视中国的心呢?”这种对欧美影片中“模式化”“类型化”国人形象的否定,既有出于民族自尊的文化使命,又包含对媒介垄断的批判,以及对媒介建构功能的认知与警觉。
二、电影教育:近用能力的培养与实践
英国媒介素养专家莱恩·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认为,对媒介素养的理解不仅包括对媒介的批判性接收,也应包括对媒介的主动创造。开展媒介教育,不仅构成媒介素养研究发展的主要内容,同时有助于提升媒介近用能力,为抵抗媒介霸权、理解媒介作用路径提供有效帮助。作为20世纪初的新兴媒介,电影教育自然也要纳入媒介教育的范畴之中。早在1926年,以欧美为代表的77个国家成立了教育电影的国际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电影教育广泛应用于军事培训,战后,以电影为主要媒介进行视听教学的方法开始逐渐普及,教育思想逐步成熟,教育学会纷纷建立。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即发端于1923年所成立的视觉教学部。20世纪60年代,美国媒介素养研究者约翰·卡钦(John Culkin)使用电影、电视等开展人文、艺术等学科的教学,同时成立理解媒介中心(Center for Understanding Media,Inc.),向教师教授如何使用和理解电影电视等媒介。通过电影的教育,以及关于电影的教育,二者共同构成了电影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一理念,同样体现在我国早期的电影教育之中,并产生了具有良好社会效果的媒介实践。
(一)通过电影的教育
1912年,蔡元培在担任教育总长之时,曾督促各省都督推行社会教育,“通令各州县实行宣讲,或兼备有益之活动画影画,以为辅佐”。其中所提到的“活动画”即是指电影。此后,蔡元培多次强调电影的教育效果,认为电影的动态性和直观性能够“补图书之所未及”,“为教育上最简便的工具”,同时也提出了电影的大众娱乐功能大于教育应用的现实,“近日各都市盛行的都以娱乐为最大目的,中国人自编的甚少,且多为迎合浅人的心理而作,输入的西洋影片亦多偏于富刺激性的。他们的好影响远不及恶影响的多。”在对电影的批评与思考中,蔡元培提出当时中国电影的两大积弊:其一是电影的过度娱乐化,缺少具有美学价值和引导意义的高尚之作,“其情节多诲淫、诲盗”,对观众产生了很多消极、负面的影响,辨别能力较弱的青少年尤甚,发出了“我少年品行,不知被破坏几许矣”的惊叹;其二是国产影片不多,且质量不高,既不能启迪民智,普及教育,也缺乏反映民族危亡、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大众传播在此时对受众的满足仅为低层次的感官满足,远不能起到引导作用。蔡元培作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教育的核心人物之一,借鉴英、法、美、苏等国利用电影开展国民教育的成功案例,肯定了中国电影教育发展的可能,推动了电影教育的积极探索。
(二)关于电影的教育
关于电影的教育包括学习电影技术,发展民族电影,推动了我国媒介信息传播能力的发展。在辱华电影刺激与中国电影人艺术自觉的双重作用下,20世纪20年代,我国电影事业迅速发展,其中关于电影艺术与技术的探讨,体现了中国电影人对电影媒介的认知已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郑正秋在《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一文中就曾对电影的拍摄流程进行简单的总结,其中“选地、配景、导演、择人、摄剧、洗片、接片”与现代电影拍摄流程非常接近。明星公司摄影主任汪煦昌1924年与人合办昌明电影函授学校,并编撰了《昌明电影函授学校讲义》作为学校授课教材,其中《影戏概论》系统地探讨了电影发展历史、基本概念、社会功能等,对电影知识的普及提供了指导;《导演学》介绍了导演的基本知识,包括导演的任务、导演分场及注意事项等,明确了导演在电影拍摄中的角色划分;《编剧学》将剧本对于对电影的重要性予以强调,并指出了电影剧本之于文学作品的不同,在于剧作者必须具有“文学上的知识”和“对影戏知识也有充分的研究”,其中“电影剧本是一种新式的文字”体现了我国早期电影人对电影语言的准确认知。这一时期对电影制作技艺的论著还包括侯曜的《影戏剧本作法》、陈趾青的《对于摄制古装影片之意见》、欧阳予倩的《导演法》等。电影摄制技术的教育与传播体现了我国电影人掌握电影媒介制作技巧、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尝试和努力。
(三)从电影教育到创作实践
电影教育既可以提高媒介接触者的批评能力,又能够赋予媒介使用者实践能力的提升。1923年,中国儿童电影之父郑正秋拍摄了我国第一部儿童故事长片《孤儿救祖记》,有别于1922年但杜宇所拍摄的电影短片《顽童》滑稽打闹的风格,《孤儿救祖记》讲述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家庭故事,通过关于遗产继承的矛盾展开叙述,刻画了“善”与“恶”的价值对照,并以“善”终于战胜“恶”的大团圆结局满足了大众的观影期待,同时通过捐助义学,使影片主题得到升华,将乐善济贫、提倡义务教育、瞩目国家未来的意义泛化到整个社会。该片一扫萌芽时期国产影片庸俗低级的“游戏”之风,实现了商业与艺术的双赢,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在艺术上较为成熟和完整的影片”。自此,中国电影创作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在学习先进电影技术的过程中,我国电影艺术家拍摄了脍炙人口的本土电影,发展了具有中国美学特征的电影实践。
三、电影法规:行为主体的规范与引导
媒介素养的核心目标是培养理想公民,而理想公民的培养既需要媒介教育的实施,同时也需要社会制度的规范。出于对电影政治、社会功能的清醒认识,蔡元培在推动电影教育的同时,致力于电影审查法规的制定,其得意门生郭有守于1930年起草并推行了中国第一部电影法令《电影检查法》。1931年在蔡元培、郭有守的推动下,国民政府组建“电影检查委员会”,在1931年6月到1932年6月间,依据《电影检查法》,以保护儿童身心健康为宗旨,“第一次大规模禁演有害儿童身心健康的进口与国产电影”,共计71部;同年,为增强海外华人儿童对祖国的认同感,第一次大规模向东南亚输出国产电影116部,其中包括郑正秋的《小情人》等。
建立法律法规是从制度层面,对电影媒介信息进行把关,而提高观众的批判性观影能力,则是从接受者的角度,建立信息传播过程的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壁垒。我国早期电影艺术家郑正秋所创办的明星影片公司在致力于影片拍摄的同时,以提高观众的观影水平为目标创办《影戏杂志》,希望由此“引起观众研究影戏的兴趣”“使得看影戏的得到极灵通的消息”“使得中国人有分辨影戏好坏的眼光”,从媒介的应用,到信息的获得,再到批判的眼光,其所强调的正是媒介素养的核心概念。其在1925年所撰写的《我所希望于观众者》一文中对电影观众提出了六条希望,其中包括抵制无益于我国的外国影片,“相约家族亲友勿观之”;支持国产影片,避免国产电影“被压迫于外货之下焉”;娱乐与教育并重,避免过度娱乐化,对陈义高尚之作品“亦须力为提倡”等,均体现了我国早期电影人建立电影媒介规范,提高观众媒介素养的思想萌芽。
结 语
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电影事业的重要发端,电影人、教育家以及社会活动家出于强国富民的民族自觉,从电影批评、电影教育、电影法规等方面,对电影的社会功能、电影与观众的关系、电影艺术的内容与形式进行探讨与研究,其中所蕴含的媒介素养思想,契合了国际媒介素养研究的发展理念,同时,也拓宽了我国媒介素养的研究视野,对视觉文化时代的电影教育与电影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