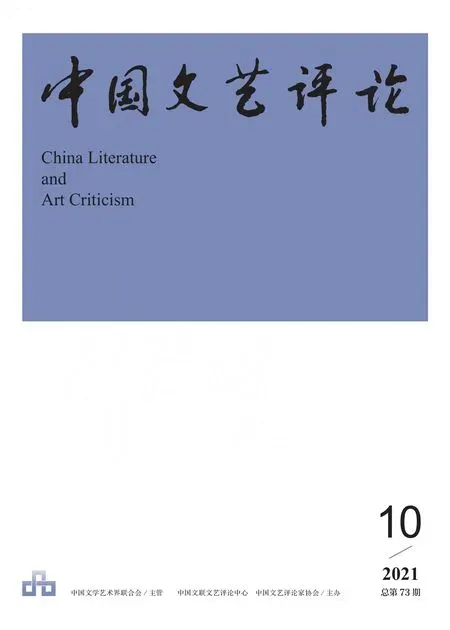传统画学中的“体道”理路与心性修养
朱 剑
“体道”作为中国传统画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深受传统哲学中心性修养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心性修养成为理解传统画学之“体道”的关键。然而,正如不同思想流派在如何修养心性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认识,画学领域中的“体道”观念也一样存在着不同理路,即道家和儒家的理路。不同理路下的“体道”又对应着不同的心性修养方式,并因此区分出“体道”的层次。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一、传统绘画品评体系逻辑与道家“体道”理路
某种程度上,唐代以后逐渐形成的绘画品评体系最集中地反映了画学中的不同“体道”理路。例如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将绘画的品级分为“自然”“神”“妙”“精”。他说:“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再如唐代朱景玄也在《唐朝名画录》中提出了“神”“妙”“能”“逸”四个品级。北宋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则将绘画分为“逸”“神”“妙”“能”四格。对此,清代范玑在《过云庐画论》中就提出:“学者由能入妙,由妙入神。唐朱景元始增逸品,乃评者定之……宋黄休复将逸品加三品之上……即三品而求古人之逸正不少,离三品而学之,有是理乎?”张彦远的表述,指出了五个品级之间具有一种序列性的逻辑关系。而不同“体道”理路,恰恰就蕴于此逻辑关系中。鉴于黄休复的四格绘画品评体系阐述完整且影响最大,我们就以其为例进行讨论。
四格中最明确涉及“体道”的绘画品级是妙格,因此先将妙格的内涵转引如下:
画之于人,各有本性。笔精墨妙,不知所然。若投刃于解牛,类运斤于斫鼻。自心付手,曲尽玄微。故目之曰妙格尔。
这里的“若投刃于解牛,类运斤于斫鼻”源于《庄子》中的两则典故,描述的正是“体道”状态。这是一种物我交融,眼前没有异己的对象的状态,画家在过去经历和习性积淀而成的某种惯性状态下进行创作,黄休复称之为“不知所然”。若用《庄子·养生主》中的话讲,就是“以神遇不以目视”。不难看出,妙格所涉及的“体道”属于道家范畴,其理路则源于先秦老子的“涤除玄鉴”“致虚极,守静笃”和庄子的“坐忘”“心斋”等心性修养思想。传统画学中的“澄怀味象”“澄怀观道”“凝神静思”等美学命题,也是这些思想影响的产物。而此种心性修养的具体方式,就是悬置现成之见,解构已有的知识系统和精神世界,从对象性的关切及意向性的活动返归虚无的精神形态,做到内心的虚静空灵。简言之,如果做到了心性的“致虚守静”,便意味着符合道家的“体道”理路。我们再看高于妙格的神格,其内涵是:
大凡画艺,应物象形。其天机迥高,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非谓开厨已走,拔壁而飞。故目之曰神格尔。
所谓“思与神合”,表示神格也达到了物我合一的“体道”状态。至于最高等级的逸格,其实也实现了“体道”。逸格的规定是:
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
此处的“出于意表”,指画面中出现的无法捉摸、难以预测的偶然性效果,这是对“得之自然”的阐释。如前所言,道家的“体道”其实是由过去的经历和习性积淀而成的某种惯性状态。而这种状态中的行为由一种类似于本能的原发知觉所驱动,并不受画家的理性控制。在此,画家正在创作的身体回到了作为原本意义的发生状态,沉浸在一种先于一切现成性的知觉实践场中。先于一切现成性,就意味着拥有无限可能性,于是便有了“出于意表”的效果。这种情形与妙格所说的“不知所然”,显然一脉相通。所以,达到逸格也需要创作者处于“体道”状态。至此可以说,道家理路的“体道”乃是妙格、神格、逸格共同的基础。
此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妙格中的“画之于人,各有本性”这句话的意思是绘画作品可以体现出不同画家的不同本性。处于妙格层级的作品,能够体现出画家在“体道”状态中流露的本性,或者说画家在“体道”状态下可以呈现自己的本性。画家的本性虽然为自然产物,却由于天赋不同而各不相同,继而会产生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人生选择,其作品达到的审美品级也自然不同。所以,尽管妙格、神格、逸格都需要“体道”,但所呈现出的画家的本性却不会相同。事实上,不同本性正是导致画家不同人生境界的关键因素,而意识到这一点并加以发挥的,则是另一条不同于道家的“体道”理路。
二、郭熙论“养”与儒家“体道”理路
综上所言,道家“体道”的落脚点其实就是心性的虚静。然而,追求虚静同时也是儒家心性修养思想的内容。如《荀子·解蔽》就曾提出“虚壹而静”的命题。当然,儒家的“虚静”与道家必有不同,且这种不同在画学中亦有所反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北宋郭熙的观点。我们来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的一段话:
世人止知吾落笔作画,却不知画非易事。庄子说画史“解衣盘礴”,此真得画家之法。人须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如所谓易直子谅,油然之心生,则人之笑啼情状,物之尖斜偃侧,自然布列于心中,不觉见之于笔下。
首先,郭熙使用了“解衣盘礡”这一源于《庄子》的命题,说明画家首先需要达到道家理路的“体道”状态。接着,郭熙又进一步指出要“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才能“油然之心生”,实现“体道”状态的“自然”与“不觉”。在此,郭熙提出了一个关键词——“养”。“养”的概念来自于孟子。孟子认为,人的“体道”就是心性对“道”的体察,“道”不在心性之外,心性亦不能离“道”而行。所以,“知心”“知性”“事天”是目标,而实现目标则需要实修的工夫,即“存心”“尽心”和“养性”。具体地说,即“存”“尽”“养”的工夫。其中,尤其是“养”观点对画学影响颇大。郭熙将“养”视为实现“体道”的心性修养工夫,显然便是受此观点的影响。郭熙还有一段论创作前的准备工作和状态的文字,既进一步规定了“养”的内涵,也指出了另一条不同于道家的关键“体道”理路:
余因暇日阅晋唐古今诗什,其中佳句有道尽人腹中之事,有装出目前之景,然不因静居燕坐,明窗净几,一炷炉香,万虑消沉,则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想不成,即画之主意亦岂易!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源。
所谓“万虑消沉”,就是指“虚”“静”的状态。而这里所描述的外部创作环境和画家创作前的状态,就是如何达到“虚”“静”的“养”,其规定有:一是没有外部的干扰(静居);二是环境优雅(明窗净几);三是画家外表行为端严(燕坐)。“燕坐”在此处有两种解释。一是带有正式意味的安坐,二是与坐禅异名,即于身心寂静中安住坐禅。如苏轼《成都大悲阁记》说:“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镜”。可见,“燕坐”是一种与坐禅功能方式相似的方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阅晋唐古今诗什”,也成为“养”的方式,这是一种学习知识的方式,而这正是区别于道家“体道”最大的不同。下面我们来详细讨论儒家的“体道”理路。
三、“体道”视域下的学习、人品与游心
传统画学中有大量强调“体道”需要以学习作为基础的论述。如宋代刘学箕《方是闲居士小稿》中说:
古之所谓画士,皆一时名胜,涵泳经史,见识高明,襟度洒落……
清代张式《画潭》中也说:
学画当先修身,身修则心气和平,能应万物;未有心不和平而能书画者。读书以养性,书画以养心,不读书而能臻绝品者,未之见也。
这两段话指出,心性修养过程就是“涵泳经史”“读书养性”。清代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中也有段文字值得重视:
夫为学之道,自外而入者,见闻之学,非己有也;自内而出者,心性之学,乃实得也。善学者重其内,以轻其外,务心性而次见闻,庶学得其本,而知其要矣。故凡有所见闻也,必因其然,而求所以然,执其端而扩充之,乃为己有。苟以见闻取捷一时,究之于心,罔然未达,诚非己有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学问之道”的影子。郑绩认为,修养心性本身就是一种学问即“心性之学”,与之相对的则是“见闻之学”。其中,“务心性”是“为学”的根本,需要将外在“见闻”找到与自身的相关之处并真正内化于“心”。可见,见闻等知识的学习必须要与心性相关联,二者结合才是完整正确的“为学之道”。
宋代以后,“为学之道”中的“心性之学”主要反映为“画品”与“人品”的关系。换言之,就是通过修养心性来完善“人品”。但这里的“人品”与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不同,不仅突出了道德意味,也强调了价值取向。概括而言,画学中的“人品”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特征的政治立场和反映道德水准的生活态度。二是正义之气。即孟子所言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也针对道德而言。与“道”观念关系最近的“人品”是第三种。我们先来看明代李日华《竹嬾论画》中的一段文字:
姜白石论书曰:“一须人品高。”文徵老自题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乃知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一物……
李日华所说的“人品”,是指无我的精神境界,即所谓“胸中廓然无一物”。但这种“胸中廓然无一物”的无我,实际上是一种包含宇宙的广阔胸襟。该观点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子思的“与天地参”以及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等对“体道”境界的描述。尤其是子思、孟子提出的从“尽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到“与天地参”的心性修养过程,其实就是通往最高“人品”的道路。因此,李日华眼中的高“人品”,一方面既要筑基于“体道”,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一个心性修养的过程。我们还可以结合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的相关论述来理解:
凡画必周气韵,方号世珍。不尔,虽竭巧思,止同众工之事,虽曰画,而非画。故杨氏不能授其师,轮扁不能传其子,系乎得自天机,出于灵府也。
此处提及的“轮扁”,也是《庄子》中的著名“体道”者,故可以推论绘画中的“气韵”与“体道”相关。然而,“不能授其师,不能传其子”,似乎否定了由学习通往“体道”的路径,但郭若虚还说:
六法精论,万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笔以下五法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
事实上,郭的观点并无矛盾,因为他说气韵不可学是指不可在笔墨技巧间学,而要在心性修养中学。也因此,郭若虚提出:
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
只有“人品既已高”的“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作品气韵才“不得不高”。而“轩冕才贤,岩穴上士”显然是重视学习以修养心性的创作群体——因为他们“依仁游艺”。在此,“游”将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切入点。除了“依仁游艺”,郭若虚还提到另一个概念:游心。他说:
凡画,气韵本乎游心。
我们知道,“游心”概念出自《庄子·人间世》中的“乘物以游心”。但郭若虚的“游心”内涵却应该源于《论语·述而》中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谓“游于艺”,意思是在学习技艺的过程中保持一种“游”的超越心态,用孔子自己的话形容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不勉而中”,不期然而然便可以和“道”相合。而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知识和技能方面的“艺”,则是“道”的具体形态。所以,“游于艺”本质上就是“游于道”。虽然“游”最终是一种主体不自知的精神自由状态,但并非随性任意无规则——它是生命的极高境界,需要筑基于“道”“德”“仁”并经长期修养心性,使“道”内化为“体道”者的生命形态,感受不到任何外在强制性规约的力量。郭若虚说“气韵本乎游心”,而“气韵”又通过高“人品”表现出来。因此,这里与“体道”相关的“人品”内涵,归于儒家思想的范畴。
四、人生境界层次与“体道”层次
我们知道,强调学习、高标人品来实现“体道”的理路源自儒家,而强调学习、高标人品的目的是什么?答案是:提升人生境界。因为人生境界的层次,决定了画家作品属于哪个品级的“体道”。我们先来看清代张庚《浦山论画·论性情》中的一段话:
大痴为人坦易而洒落,故其画平淡而冲濡,在诸家最醇。梅华道人孤高而清介,故其画危耸而英俊。倪云林则一味绝俗,故其画萧远峭逸,刊尽雕华。若王叔明未免贪荣附热,故其画近于躁。赵文敏大节不惜,故书画皆妩媚而带俗气。若徐幼文之廉洁雅尚,陆天游、方方壶之超然物外,宜其超脱绝尘不囿于畦畛也。记云:“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其是之谓乎!”
在此,张庚将画家的作品境界与画家的人生境界联系起来考察的观点值得充分重视,我们可以借用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观来理解。冯友兰先生曾根据不同的宇宙人生观,将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大致上,张庚所说的“贪荣附热”可对应功利境界,“大节不惜”对应道德境界,“平淡”“冲濡”“超然物外”则对应天地境界。张庚所列举的都是中国山水画史上的大师,我们不妨选择其中的吴镇、倪瓒、王蒙、赵孟頫及各自的代表作品《中山图》《六君子图》《具区林屋图》《秋郊饮马图》进行比较分析。先看吴镇的《中山图》(图1),采用淡墨皴擦,浓墨点苔,山形、树形都相对简约,整体风格清淳蕴藉,松秀空灵,给人一种幽深静穆感。此视觉特征和审美气息,完全能够透现创作者本性的“孤高而清介”。再看倪瓒的《六君子图》(上页图2),与吴镇的湿笔画法不同,这幅作品是用淡笔干墨草草点染,在画面的主体部分描绘了具有道德象征意义的松、柏、樟、楠、槐、榆六棵树,画面顶端则是一抹远山。整件作品干净疏朗,无一丝烟火之气,十分符合画家“一味绝俗”的本性。王蒙的《具区林屋图》(图3)的最大特点,就是密和满。这幅以实景为题材的画作,山势扭曲,笔法繁复,颇有躁动感。若对照其本性的“贪荣附热”,产生此略显“躁”感的画风便不难理解了。最后看赵宋皇室后裔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下页图4)。画面中的绿岸、丹枫、红衣相互映衬,色彩浓郁,工细严谨。较之吴镇、倪瓒、王蒙的作品,的确“妩媚而带俗气”。加之此画作于“皇庆元年(1312年)十一月”,赵孟頫时年59岁,又刚刚得到元文宗的允许还乡祭祖立碑,正值其一生中政治上最为得意的时期,因此最能反映其本性中的“大节不惜”。上述作品境界各不相同,究其原因,就是前文所说的画家本性存在着差异。虽然画家的本性皆为自然产物,但由于天赋的不同而各不相同,所以会出现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人生选择,作品也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事实上,这几件作品即使不作分析,我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张庚所言不虚。

图1 元 吴镇 《中山图》 纸本水墨 26.4×90.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 元 倪瓒 《六君子图》 纸本水墨61.9×33.3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图3 元 王蒙 《具区林屋图》 纸本设色68.7×42.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4 元 赵孟頫 《秋郊饮马图》 绢本设色 23.6×59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
儒家学者对本性问题还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论述。宋代张载提出,每个人的本性都秉承于“道”(太虚),即“天地之性”,但同时也存在着“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正是障蔽“天地之性”的主因之一,因此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朱熹也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之分,每个人的“天命之性”虽然相同,但“气质之性”却存在着禀赋的差异,所以“天命之性”常被“气质之性”遮蔽。在此,“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受之于先天,“气质之性”同样也具有先天依据,两者都是人的自然本性。如果我们把上述观点放到画学领域,就可以说即使画家实现了“气质之性”,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天地之性”也实现了。正是因为画家的“天地之性”没有充分实现,才会导致作品的审美品级高低不同。
再回到黄休复的绘画品评体系。该体系的逻辑关系恰好也说明了“体道”层次与人生境界的联动关系。如前所言,从妙格到神格,它们的相通之处皆为画家创作时能够进入“体道”状态。但逸格和神格的“体道”并不等同于妙格,原因也是画家的天赋各有不同。进而言之,妙格、神格、逸格对画家天赋的要求是逐级递增的。在神格的定义中,黄休复就直接提出了“天机迥高,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天机迥高”即指画家的先天禀赋卓越。画家卓越的天赋,则是指画家能够对既有规则有所突破,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新规则,即所谓“创意立体”。至于逸格,对画家天赋的要求就更高了,画家要创造出几乎全新的规则。事实上,逸格对画家的天赋要求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清代恽寿平在评价元代画家曹知白时说:“云西笔意静净,真逸品也。山谷论文云:‘盖世聪明,惊彩绝艳’……涪翁论文,吾以评画。”所谓“盖世聪明”,就含有非常难得之意。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仅仅凭借天赋,画家是无法创作出完全意义上的逸格作品的。因为其首先必须对既有的创作技法和创作理念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只有在此基础上实现突破,创造出新规则,才能达到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所谓“最难其俦”“莫可楷模”就是此意。
因此,传统画学中关于实现“逸”的主流意见,是由下而上的进路,即通过提升人生境界来实现作品的“逸”。对此清代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曾有论述:
是在天资敏妙者,能于规矩中寻空阔道理,又当于超逸中求实际工夫。内本乎性情,外通乎名理。奇处求法,僻处合理……
“天资敏妙”阐述的正是天赋与“逸”之间的关系,而“道理”“理”“法”“规矩”等字眼,都凸显了对既有创作技法以及理念进行整体掌握的重要性。可见,“求实际工夫”才是关键所在,具体来说就是追求人生境界的“实际工夫”。这些工夫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换言之,画家只有从功利境界一步步超越至最高的人生境界,其作品才属于最高审美品级的“体道”。
其实,这也是更为可靠的进路。一方面,天赋并不十分突出的画家肯定是大多数;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强调不在自身控制能力范围之内的天赋因素,那么对这些画家而言,逸格将失去作为现实目标的意义。而从个人修养的培养入手,逐渐生出博大的胸襟和高远的视野,并在此过程中明确创作的目标,进行艰苦的技巧训练,佐以个人先天禀赋,使本性、作品境界和人生境界在“道”中得到统一,这是每个画家都可以具体付诸实践的。由此可见,如果注重人生境界的提升,会使“逸品”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画家通过自身的努力逐级而上,最终达成自己的目标。概言之,心性修养是途径,人生境界是基础,“体道”是目标,传统画学所反复强调的,都是实现三者的统一。
五、结语
在上述两种“体道”理路中,道家理路主要是针对创作过程而言,就像庖丁解牛只是在肢解牛的过程中“体道”那样,画家在创作过程中能够自然地呈现本性。而儒家的理路则是除了要在创作过程中“体道”以外,还十分强调画家应具备很多画外的工夫,且这些工夫均应该在作品中体现出来。在此,画家进学修养心性的工夫是主体得以超越的基础,基础越深厚,主体超越后所能达到的境界就越高。换言之,心性修养的结果就是画家为了充分呈现自己的本性而要实现自我扬弃,即主体要去除心中各种束缚心灵的成见。画家虽丢弃了成见,却留下了境界。当画家能够将成见完全悬置起来时,就是彻底的虚己,天地万物与自己一体相融的本然状态便呈现出来,“道”的境界也就达到了。只有这种“体道”,才是绘画创作的最终目标,因为它是从较低的人生境界超升上来的,深厚的人文积淀可以使心性始终保持在最高的层次而不堕。
心性修养观曾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画学,而它对当下的创作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将“体道”作为创作目的,可以最有效地让艺术创作行为超越功利的追逐而关注精神的自由。在今天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文化语境下,艺术创作的纯粹性在很大程度上被集体忽视,浮躁情绪到处弥漫,导致创作者极易迷失心性。而通过读书养性、重视人品来修养心性,不仅对艺术回归本质和对创作者找回初心有直接帮助,对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发展而言,亦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