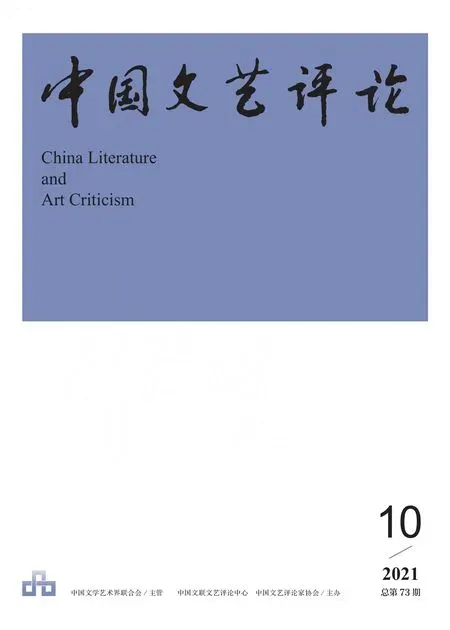现代中国的杂糅半觉式典型
——论话剧《活动变人形》中的人物形象
王一川
看完话剧《活动变人形》,我的脑海里不禁思绪起伏,围绕倪吾诚这个中心人物而逐渐凝聚成一连串观感:这里呈现了中国现代话剧舞台上从未有过而又意义重要的一组中西方跨文化典型形象。这组人物形象虽然早就在王蒙的同名小说原作(1986年)中出现,但作为由小说改编而成的舞台艺术形象,毕竟还是首次亮相,因而值得关注。
一、舞台中央与边缘的对话
这种观感与这部话剧的特定舞台处理方式和表演效果有关。该剧在舞美设计和叙述人设计上都有其独出心裁之处。舞台中央先后随处变换着主人公倪吾诚及其家族在河北孟官屯老宅院、北京胡同住宅或城市餐馆等处多重场景,灵活而自由,便于主人公及其家族成员上演自己的喜怒哀乐或悲欢离合故事。而这多重灵动场景装置的设置,恰如倪吾诚送给儿子倪藻和女儿倪萍的日本产“活动变人形”图书一般,该书全是画,头、上身、下身三部分都可以独立翻动,由此而任意排列组合成无数个不同的人形图案。这图书由其儿女多次翻看,寄托着倪吾诚对儿女的西化生活方式的想象和幻想,其实也寄托着他对自己的未完成梦想的期待。但其真正意味深长的寓意可能在于,它可以反过来寓指倪吾诚的自我形象本身:他自己不正是一个什么新鲜事物都想模仿、但结果什么都不是的半吊子人物吗?多重灵动场景装置及其与“活动变人形”图书的多元形象组合寓意间的同一性关联,为倪吾诚其人性格的典型性呈现提供了合适的舞台时空。
与上述多重灵动的舞台中央场景相应,舞台边缘处为全剧旁观者兼当事者、叙述人倪藻的双重叙述(旁白)提供了自由灵动的位置。这位叙述人飘忽不定地在舞台边缘行走、在椅子上端坐、拨打电话,时而又迈入舞台中央的空隙处,最后还与姐姐倪萍一道作总结。这样的双层舞台构造就为观众对该剧故事的观看提供了双重视角:一重视角是倪藻作为上述双重叙述人对当年发生在父辈和自己这一辈的故事进行事后的冷峻反思,另一重视角则是这个家族的所有当事人在当年的即时本真演出。因为倪藻作为当事人和旁观者也无法真正了解全部事件过程及其秘密,而只能叙述其中的大约一半;而倪藻无法叙述的另一半,就该由所有家族成员自我表演了。如此一来,真正的全知全能者(如果有的话)应该也就只能是观众了,他们可以时而旁观在外、又时而投身其中,既可以有事后旁观的冷峻姿态、也可以有当时倾情投入的狂热体验,从而对以倪吾诚为中心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跨文化旅行产生出距离感与疼痛感相交融的多味体验。
二、家族下跪仪式及其“分隔”意义
对这种跨文化冲突状况,不妨以剧中一幕场景为集中标志。当留洋归来的倪吾诚热切地要把自己倾心向往和热烈拥戴的喝牛奶、咖啡等西洋日常生活方式移植到自己家中时,没想到遭遇妻子姜静宜、岳母姜赵氏和姨姐姜静珍的联合一致的坚决反对。我们无法不面对这一家族仪式般的严峻场面:当倪吾诚眼见岳母随地吐痰而向妻子间接表达不满和批评态度时,没想到妻子向母亲和姐姐告发,导致妻子和姨姐都一致地不仅不以为错,反倒指责他不孝,还一致蛮横地要他向岳母赔礼道歉,直到强行让他下跪、赔罪才罢休。在观众目睹倪吾诚如何在静宜执意要求下和姜静珍目击下,无奈中极不情愿地向岳母下跪认错的瞬间,一个鲜明而重要的转折点仪式般地出现了,表明从此倪吾诚在自己与姜静宜的夫妻战争中就基本上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尽管后来当他生病且被解聘时静宜细心看护而导致夫妻关系一度转暖,但夫妻间精神上分道扬镳的格局终究不再发生根本改变。一名留洋归来的大学教师,在自己没错时反倒当众向岳母下跪,这一举动无疑仪式般庄重地宣告他的整个家族生活改革举措遭遇挫败,主人地位就此沦丧殆尽。
要理解这一仪式性场景的意义,可以参考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有关“过渡礼仪”的研究:“每一个体总是共时性或历时性地被置于其社会之多个群体。为从一群体过渡到另一群体以便与其他个体结合,该个体必须从生至死,始终参与各种仪式。”每个人的一生总会参与这类“过渡礼仪”,经历其人生环节“过渡”所产生的“分隔”功能。“尽管仪式形式多有差异,但其功能则相近。有时,个体独处一地,隔离于所有群体;有时,作为某群体的成员,与其他群体成员分隔开。一切社会的分隔均有两大特点,且不拘时空所限:男女之性别区分;世俗与神圣之巫术—宗教性区分。……无论对个体或群体,生命本身意味着分隔与重合、改变形式与条件、死亡以及再生。其过程是发出动作、停止行动、等待、歇息、再重新以不同方式发出行动。其间,要不断逾越新阈限:季节、年月或昼夜之交;诞生、青春期、成熟期及老年之变;死亡与再生(对有此信仰者而言)之转换。”这种“过渡礼仪”的主要功能是将该仪式的当事者与自己的过去及其他人群“分隔”或“区分”开来,以此宣告新的阶段或状态的开始。所以,“过渡礼仪”的人生功能主要在于“分隔”,通过这种“分隔”而让当事者告别过去之我而奔向新我。这样,个体在其人生中具有关键意义的过渡时刻所经历的社会仪式,会为他下一阶段的状况提供重要的“分隔”线。由此回看倪吾诚所经历的上述下跪仪式,当他被迫向岳母和妻子及姨姐三位女性臣服时,就宣告了他与自己过去的家族身份之间的庄严“分隔”的完成:他不得不与自己过去在这个家族中的主人、统治者或主动者地位“分隔”开来,转而沦落成为家族中的臣民、被统治者或被动者。
应当看到,发生在舞台中央家族住宅场景下的这场下跪仪式,对倪吾诚后来的人生轨迹有着强大的“分隔”力——其人生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当这一“过渡礼仪”的“分隔”力由舞台上演员们的投入表演而逼真地产生出来时,与阅读小说原作时读者自己在头脑里想象出的场景相比,显然要生动和强烈得多!这也反映出话剧在舞台场景鲜活再现上所具备的独特美学优势。
三、杂糅半觉式典型
透过上述标志性中央场景和边缘叙述者的设置及其寓意,还有下跪仪式的效果,可以再来看看剧中三位主要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特征的刻画。
从舞台故事呈现可知,倪吾诚是一位向往西方异文化并全力将其移植到中国但遭遇惨败的典型。他年轻时勇敢地走出还在吸食鸦片的河北老家孟官屯,留学欧洲两年,回国后满腔热诚地想把其实只是一鳞半爪、半知半觉地学到的那些杂乱无章的西方文化理念,一股脑地移植到中国来。他开口闭口“胡适之”,似乎要像胡适那样实施中国本文化的西化变革,还热衷于推行一整套吃西餐、喝咖啡牛奶、到浴池洗澡等带有西化色彩的日常生活仪式。至于家庭,他首先从改造妻子的旧生活方式做起,无论是在老家还是在新家北平,他都要求静宜学会挺胸走路,去看电影、划小船、吃饭馆,还带她听蔡元培、胡适、鲁迅、刘半农等的演讲。但意料不到的是,妻子本人对此全然不解和顽固抵抗,还联手娘家人——岳母和姨姐等予以阻击,不惜发动一场场阻击战。这类家族内部频繁战斗的激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当姨姐将一锅沸腾着的绿豆汤泼向倪吾诚时,当三位女人一齐扑向他时,醉酒中的倪吾诚的最后一个绝招就是当着她们的面脱掉裤子,这才终于成功地吓退这三位女人。这无疑也相当于一场“过渡礼仪”,标志着他与她们仨之间已然泾渭分明地“分隔”开来,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的地步。他随后改变策略,转而从教育两个孩子倪萍和倪藻做起。但也接连遭遇挫败——在娘家人联合起来的压倒多数的逆向环境下,他的任何一次西化或洋化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其标志就是这两个孩子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竭力抗拒,让他倍感失望、落寞。他失败的根源看起来主要来自他所身处于其中的家族环境的落后和愚昧,其实更多地还是来自于他自己。他内心生成了一种强烈的基于外来异文化的杂糅半知半觉式情结:一面不无道理地崇拜和师法自己东鳞西爪地生硬搬来的西方异文化,但另一面由于个人理性或分析能力欠缺,无法分清皮毛和精髓,在杂糅性的半知半觉中根本无法顾及中国国情、家情、人情、乡情等,只知盲目照搬,“食洋不化”,加之个人意志力的薄弱,必然只能接连碰壁,结果一无所成。
由此看来,倪吾诚的一生称得上是一个杂糅半觉式跨文化典型。杂糅半觉式跨文化典型,简称杂糅半觉式典型,是就倪吾诚的典型性格来说的。他虽然是现代中西方之间跨文化旅行的一名有勇气的亲历者,但在这段特殊的跨文化旅行中,又不过只是一名对中西方文化都有所了解但只知其皮毛而不知其整体、停留在半知半觉、一知半解或半道而止状态的“半人”或“废人”。杂糅半觉式跨文化旅行,表明这里的本文化与异文化在相互接触中各自都呈现出相互杂糅、半知半觉、半途而废或未完成态。这无疑表征着现代中国跨文化旅行中的一种特殊的挫败状况。
处在他的对立面的是妻子姜静宜。她是一位顽固地持守本文化、反对将外来异文化移植到家中、并同样遭遇失败的典型。她本来已经在新式学堂上学了,也对现代新事物有所了解,包括“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但奉父母之命而与倪吾诚定亲后,就退学在家专心等待夫君从国外学成归来,过上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这位一辈子都信奉从一而终、安分守己的家族礼教的中国旧式女性,面对丈夫的“西化”生活主张,竭力抗拒,坚决不从,加上来自母亲和姐姐的强力支持,在与倪吾诚一生的战斗中时时居于上风。试想,假如没有来自母亲和姐姐的鼎力帮助,她与倪吾诚的战斗结局可能会是另外一副样子。在早已丧失古典本文化生存依据而必须承认现代性进程的世界上,要想顽固地一概拒斥异文化而持守本文化,不知变易、变通或与时俱进,同样会遭遇失败。与倪吾诚相比,静宜身上也有着基于本文化的杂糅半知半觉式情结:一面不无道理地顽固信奉古代本文化中的基本的或僵化的信条,一面却对本文化中固有的变易、变通或革命精神缺乏理解或领悟,从而在外来异文化奔涌而来时不知进取,不懂移植和转化,属于与“食洋不化”相对峙的“食古不化”,同样也只能以其半吊子本文化而归于失败。诚然,她表面上在与丈夫的斗争中胜利了,但每一次胜利都只能导致丈夫的进一步身心分裂:其身体暂时归家而其精神则继续流浪在外。
这就需要特别提及姨姐姜静珍其人了。她是倪吾诚和姜静宜家庭中的“外人”,但又是其中特别重要的搅局者,尤其是静宜的重要帮手。她出嫁两年丈夫即去世,无儿无女,就回到娘家守寡,一心扮演“烈女”角色。但与此同时,她生性热情如火,刚强勇猛,外向外露,抽烟喝酒、吵嘴打架、刻薄尖酸、专横撒泼等样样精通,无所不能。她有着鲜明而强烈的个人野心和狂野个性,既熟悉古典白话小说,又熟读《家》等现代小说,似乎既是古典本文化的捍卫者,又是现代文化的热心人。古典本文化与现代异文化在她身上形成一种奇特的矛盾杂糅体。她与母亲一道搬来与妹妹一家同住,无形中壮大了妹妹在家族中的地位。当静宜与倪吾诚争吵时,她总是妹妹的强力后援。她一旦参与其中便能立时左右战局,让倪吾诚迅速溃败。然而,当妹妹选择与丈夫和解时,她反倒生活情绪消沉,似乎丧失掉日常生活存在的充足理由了。正是由于她的狂野式存在,这个家族的跨文化精神乱象才愈发鲜明和彻底。说到底,姜静珍也是一位杂糅半知半觉式典型:半情半理、半古半今、半正半邪、半刚半柔、半醒半醉、半淑女半魔鬼……一句话,也是中西方跨文化对话中的半吊子畸形儿。
这三个主要人物,从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人物画廊来看,共同构成一组少见的典型人物群像,即都以他们各自的独特方式去呈现现代中国特有的杂糅半知半觉式跨文化景观。倪吾诚这一知识分子形象,过去在《倪焕之》的主人公身上有过部分原型,但这里更加鲜明地显露出杂糅半知半觉式跨文化特点来。姜静宜的既温和贤淑但又顽固守旧的性格有着某种新颖性,但根底里也是杂糅半知半觉式跨文化的。姜静珍其人则尤其复杂多义:部分地既带有《雷雨》中繁漪的怨毒、也有《北京人》中愫方的开明和坚强,还带有《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强悍,以及带有《原野》中金子的疯狂等等,也就是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杂糅的和半吊子式的。有这样一位帮手的强力扶持,姜静宜在与倪吾诚的斗争中没有不胜的道理,尽管这种胜利只是表面上的。
四、杂糅半觉式典型在现代中国
确实,在这部话剧里,现代知识分子倪吾诚与妻子姜静宜和姨姐姜静珍等实际上共同构成杂糅半知半觉式跨文化典型主人公群像。因为,在倪吾诚与姜静宜夫妻之间,假如没有姜静宜的突出的对手作用,倪吾诚的人物形象是无法成全的。姜静宜成全了倪吾诚,倪吾诚也成全了姜静宜,他们夫妻二人共同构成相互成全的关系,也就是相互成全了对方的杂糅半知半觉式跨文化典型形象。同样,姜静宜得益于姜静珍作为帮手或中介者出现,才能一举打破夫妻二人间暂时平手的局面,而让胜利的天平从一开始就轻易地摆向妻子一方。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既有化不开的本文化,也有同样化不开的异文化,导致本文化与异文化间形成双重凝冻状态,也即本异双凝态。本异双凝态表明,处于跨文化接触中的本文化和异文化双方都同样处于冥顽不化的凝冻状态,无法通向积极的变革或更生。按照跨文化学,真正成功的跨文化进程不应该是这种本异双凝态,而应该是相反的本异双化态,也就是要求本文化在与异文化相接触时,既不是一味地固守本文化,也不是不加分析地全盘归顺于异文化,而是要通过异文化而使本文化自身发生真正的创造性转化、感化或涵濡作用,即从异文化中吸取优质成分并加以转化或改造,融合于本文化的面向未来的自我更生历程之中。
相比而言,还是倪吾诚的杂糅半觉式跨文化性格在现代中国文化进程中有着尤为鲜明的典型性意义。历时地看,他应当是继欧洲的堂吉诃德、“多余人”等典型形象,以及现代中国的孔乙己、阿Q等相关典型人物之后的另一种有着一些新内涵的典型人物:中外多种多样的现代典型人物的半吊子杂糅体。正如小说原著续集第二章借助于儿子倪藻所反思的那样:“在父亲辞世几年以后,倪藻想起父亲谈起父亲的时候仍能感到那莫名的震颤。一个堂堂的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既留过洋又去过解放区的人,怎么能是这个样子的?他感到了语言和概念的贫乏。倪藻无法判定父亲的类别归属。”倪藻确实曾经一遍遍地反复列数自己所知的种种人物的“类别归属”:“知识分子?骗子?疯子?傻子?好人?汉奸?老革命?堂吉诃德?极左派?极右派?民主派?寄生虫?被埋没者?窝囊废?老天真?孔乙己?阿Q?假洋鬼子?罗亭?奥勃洛摩夫?低智商?超高智商?可怜虫?毒蛇?落伍者?超先锋派?享乐主义者?流氓?市侩?书呆子?理想主义者?这样想下去,倪藻急得一身又一身冷汗。”在这段描述中,叙述人倪藻急切地和竭尽所能地调用自己当时所知的中外政治人物、文学典型人物、艺术流派人物和社会阶层人物等多种不同的名称去尝试反思父亲的人格构成,终不得解。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用这样诸多人物类别中的任何一种去单独规范父亲典型性格的“类别归属”,都显得过度、过分,或过于单一化或简单化。或许,倪吾诚不过就是其中任何一种典型人物的半吊子性格状态而已,也就是杂糅半觉式跨文化典型。这是现代中国文化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位半道而止的或似乎永在半路上的半知半觉式典型。
作为杂糅半觉式跨文化典型,倪吾诚的典型性格中有着这样的多层次特征:第一层为崇西贬中症,即狂热而简单地认定西方一切都好而中国一切都坏,表现为热衷于大谈胡适之、到浴池洗澡、喝牛奶咖啡等,忽略对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冷静认识;第二层为原因误认症,即误以为旧式婚姻是万恶渊薮,似乎自己一生的失败都源于包办婚姻本身,而不知从自身性格上找原因以及从倪姜两家经济实力悬殊上找原因;第三层为知行分离症,空有想象力或理想力而缺乏务实有效的行动力,即只有韦伯意义上的“意图伦理”而缺乏应有的“责任伦理”。这几层特征在倪吾诚身上是相互交融一体而难以分开的,它们共同地组合成为这位具备杂糅半觉式跨文化性格的典型人物。
导致倪吾诚这一典型性格生成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去考察。文学评论界在分析小说原著时已有多方面涉及,在刚出版不久即被解读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缩影”和“一个现代孔乙己的形象”等。而在近年则被与王蒙自传高度联系地解读为一个“标准的‘混蛋’”式形象,要“借倪藻痛苦的童年往事来写倪吾诚作为启蒙者的独特的这一个(夹生的流于皮相的新文化拥护者)的困境和失败”,其主题在于“以四十年代日据时期北平倪家的悲剧来显示现代文明要在古老的东方古国结出美善花果将会何等艰难,或者说是为了显示新文化运动自始至终的尴尬,以及古老中国实现文化转型与文化创新的任重道远”。这些解读和评论都各具其合理性,但我在这里还是主要从话剧舞台创造的人物形象来看。
这里想特别指出的一点在于,倪吾诚的杂糅半觉式性格之来由,交织着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等多种复杂元素,而其中尤其不可忽略的一点在于经济原因:他从出国留学时起直到后来很长时间,日常花销主要来自妻子及其娘家人,这座沉重的经济大山令他在回国后与妻子及其娘家人的历次战斗中理不直、气不壮,甚至在儿女面前有时也变得低声下气,尽管也有随意呵斥之时。正是在经济原因这一点上,假名章事件也有着“过渡礼仪”般的转折性作用:一次在与妻子吵架时,他故意交出已经作废了的名章,说可凭这个去他所在学校总务科领薪水,似乎表明他已经决定在经济上完全臣服于妻子,结果让满心欢喜的妻子在他学校两名秘书面前受辱。正是这一假名章引发的当众受辱事件,以“过渡礼仪”式的严肃姿态,将他与家族经济地位上的主导权“分隔”开来,标志着他的家族经济地位的完全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家政权力上的败落,甚至就连在人格上,他也在整个家族成员中遭遇挫败,蒙受“骗子”等可耻称呼的羞辱。
进一步说,倪吾诚真正深层而致命的性格生成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原始体验情结即“原忧”的作用力。我曾在《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1994)里分析过洪灵菲小说《流亡》(1928)中主人公沈之菲性格的形成原因:沈之菲之所以能在反动派面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却在父亲面前唯唯诺诺、诚惶诚恐,就是因为他身上存在着一种“原忧”——将西方文化中科学、民主、自由等现代性价值移植到中国的历史使命感,与需要加以反抗的古代家族制度和整个古典传统抱有的忠诚、孝顺、敬畏等态度之间,在他深层无意识心理层面构成相互冲突和消解的力量,尽管在意识层面上前者似乎早已战胜后者了。倪吾诚更是如此:他一面将自己杂糅而来的半知半解的西方式价值观全力移植到家族生活中来,而自身理性能力和意志力又都孱弱不堪;另一面还不得不承受妻子娘家所代表的传统家族势力的强力压制和阻碍,特别是经济力量所支撑起来的家族权力压制作用,致使懦弱无能的自己在这两股力量的夹击中变形、变态、扭曲等,最终只能落得半吊子跨文化者的悲剧性结局。他一方面有着大义凛然的进取气象,另一方面又显出懦弱无能的败落景象,从而无法不化身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道病态心理奇观。
再看姜静宜性格的典型性之根源。她并非不懂得现代新学或西学的先进性和作用力,她也曾阅读过巴金、茅盾等的作品,只不过内心深处更习惯于古代烈女、贞节、包办婚姻等旧观念以及旧生活方式而已。这就在她内心播种下一种难以调和的羡慕与怨恨相互交融的无意识情结:越了解或羡慕现代新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就反而越感到自己不过是旧社会或旧历史的可怕和可悲的残酷牺牲品,产生出强烈的羡慕与怨恨交融的扭曲心理,从而越是坚决地予以抗拒。具体地说,她自身的先裹脚又放开、包办婚姻、从新学堂退学回家待嫁等“不良出身”,恰如永远无法洗刷的原罪之根而深植于内心,每当留洋归来的丈夫起劲地宣扬新生活方式时,总会激发起她内心的原罪感而生发出深重怨恨,随即异常激烈地予以反抗或阻挠。于是,她带着对未来人生的绝望而展开了一次次疯狂的反抗。这从每当倪吾诚提出离婚时她总是予以拒绝、宁肯接着遭罪也不愿离婚和改嫁中可见一斑。当然,她也有和解和宽容的时候,那就是倪吾诚少有地在经济上负责任地支持家里之时:“如果倪吾诚月月拿回足够的联合准备银行的货币,如果倪吾诚拿回金条至少是银元,那么,即使传来倪吾诚与哪个女人胡搞、倪吾诚去了舞厅乃至去了妓院的消息,她内心里可能为之痛心疾首,但她毕竟还能约束自己遵守妇道,她没有道理闹,更没有道理‘躲了’他。”静宜的这一类怪异行为,是单纯以新旧间冲突来解释时无法自圆其说的。
虽然同样是杂糅半觉式跨文化典型,与倪吾诚有勇气走出孟官屯、师法西方文化,但因自身理性能力欠缺和意志力薄弱而终究只停留在半知半觉状态不同,静宜性格的根源主要在于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怨羡情结的东西。在我看来,怨羡情结代表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一种基调。“怨羡情结是一种怨恨与羡慕相交织的深层体验”,在其中,“怨恨往往是由羡慕激发而起的,而羡慕则回头强化怨恨;反之亦然,羡慕常常成为怨恨的另一面,愈是怨恨则愈能见出羡慕”。这“两种基本的现代性体验心态……是交织一体的,相互扭结和共生,难以分开,因而宜合起来称为怨羡情结”。静宜总是带着怨羡情结去处理与倪吾诚和他西化生活方式的关系:一方面羡慕这类外来西方文化,并且还了解它的一些内涵;但另一方面又怨恨它,因为直觉感到它会彻底毁了她的原本平静而又顺利的家庭生活。于是,她可以接受或承认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变革进程,但无法承受家族中的任何这类变革,因为后者总是让自己承受恶果。在这方面她也有着相当强烈的女性性别意识:为什么总要让女性承受现代化变革的代价和恶果?一旦直觉到要自己承受这种严重代价和恶果时,她的奋起反抗必定是毋庸置疑、迅速、不管不顾和疯狂的。她的整个婚后生活仿佛都在从事这样坚决而又无望的激烈反抗。在这方面,她与年轻守寡而一生守节的姐姐静珍颇为相似:同样羡慕新生活方式,但同样因个人原罪在身而无法去适应和享受,于是只能同样进行狂野的反抗。这一性格特点从静珍屡次在家中长时间凝视镜中自我的一幕可以瞥见:她此生有太深重的怨羡情结需要宣泄而又不得。可见姐妹俩之所以总是轻易结成同盟而一道反击倪吾诚,恰是因同样受制于内心汹涌澎拜的怨羡情结的煎熬之故。就这点而言,姐妹俩性格中的怨羡情结的典型性意义是不亚于倪吾诚性格中“原忧”的隐秘作用及其深厚意义的,两者合起来共同组成现代中国人病态心理的双棱镜像,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父母一辈以及作为他们后代的我们自己。
五、子一代反思及其意义
所幸的是,透过剧中倪藻的回顾性陈述,我们能够一瞥子一代对父辈道路的沉痛而又冷峻的反思:只有坚决而又彻底地了解本文化面临的新境遇和异文化的优劣性,才有可能实施真正的中国现代跨文化工程,并让其成功地引领本文化走向借力于异文化而实现的文化更生。从杂糅半觉式跨文化进程回归于完整的跨文化进程,这可能正是该剧透过倪藻的反思性陈述所要告诉观众的。
而在从杂糅半觉式跨文化回归于真正完整的跨文化旅行方面,现代中国艺术中早已有合适的美学典范。在本文化的现代性持守上,吴昌硕面对西洋美术冲击而复活古代金石艺术传统并挪用西洋绘画中的浓墨重彩,齐白石致力于日常生活花卉虫鱼的现代形象刻画;而在异文化的现代性移植上,曹禺运用西方式话剧样式写出《雷雨》《北京人》和《原野》等传世佳作,徐悲鸿将来自西方的写实技巧与中国固有的水墨画传统密切交融而创造出系列奔马图。它们分别作为本文化和异文化的跨文化进程中的优秀之作,其成功秘诀之一就在于,绝不满足于杂糅半觉式跨文化的半吊子工程,而是务求真正彻底的跨文化进程,目的在于现代中国文化借助于异文化中介而实现的自我更生。话剧《活动变人形》透过倪藻对杂糅半觉式跨文化旅行的理性反思而能够让观众想象跨文化旅行的新未来,其目的就已基本达到了。
不过,还需要考虑的是倪吾诚和倪藻这两代人文化身份间的差异。倪吾诚作为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半吊子跨文化旅行者,其失败者形象是否就一钱不值?对比王蒙自传所载,其父王锦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其同学中就有后来赫赫有名的现代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何其芳以及文艺评论家和文学史家李长之。而王蒙自己和姐姐的名字就分别来自于其父这两位同窗好友的赐名:“我的名字是何其芳起的,他当时喜读小仲马的《茶花女》,《茶花女》的男主人公亚芒也被译作‘阿蒙’,何先生的命名是‘王阿蒙’,父亲认为阿猫阿狗是南方人给孩子起名的习惯,去阿存蒙,乃有现名。李长之则给我姐姐命名曰‘洒’,出自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洒)》。”从文化身份看,倪吾诚的原型人物无疑也像其同学何其芳和李长之一样,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向西方求取真理的一员,只是他不像这两位同窗那样完整和成功。相比而言,何其芳早年出诗集《燕泥集》《夜歌》和《预言》等,后来去往延安找到文学与文论的主心骨,实现了从新月派诗人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转变;李长之青年时代迷恋西方美学和浪漫主义精神,本科时代就写出鲁迅研究领域第一部个人专著《鲁迅批判》,直至全民族抗战时期确立起“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文化建构和文学批评新思路;而王蒙之父则是在北大毕业后去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教育学三年,回国后最高做到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单从个人专业及职业选择来说,本来他们之间无所谓高低之分,关键还在于同时代社会环境下个人能力及其在家族境遇中的扭曲状况,例如个人的理性能力欠缺和意志力软弱等,以及家族境遇压抑下的性格变态等。简言之,倪吾诚因为自身遭遇的种种变故而沦落为一名杂糅半觉式人物。通过原型人物与其同学的对比,也可从一个侧面见出倪吾诚其人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成长历程上的阐释学价值:他可以像一面镜子一样映照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道路及其变态命运。有了这面不可或缺的镜像,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才更加丰富和完整。
再来看作为反思者的子一代倪藻其人。当他在舞台边缘以旁观者身份进行观照和反思时,观众可以看到他的高明的和超然的一面;而当他进到舞台中央时而穿行于老宅之中、时而行进在当年家人身边时,观众又可以见到他作为当事者的无力和惶恐情状。其实,在观众看来,倪藻诚然有着倪吾诚的旁观者这一超然身份和位置,但也有着难以超然的当事人角色,从而无法真正做到纯旁观的和纯中立的冷静反思,也就无力对倪吾诚展开真正完全而彻底的理性批判。倪吾诚这样的典型人物,固然曾经存在于20世纪中国文化土壤里,但想必还会以有所变异而又息息相通的方式,继续存在于21世纪之中。对此,不仅倪藻个人的家族反思想必无法完全洞察,而且观看倪藻反思的观众想必也无法完全洞察,因为,观众也同样生活于与倪吾诚或其原型人物的生活流之间无法斩断其相互联系纽带的同一条生活流之中。当然,观众或许也会像倪藻一样,带着继续反思的愿望和使命走向未来。
再说小说原作者王蒙与《活动变人形》之间的特定关联。他在该小说前所出版的中篇小说《杂色》等,以及在之后出版的《季节》系列等,主要是审核自己的,即以审己构成核心题旨;而《活动变人形》则具有新的用意:把审核目光移置到父亲身上,从审己转向审父,要透过对自身一代人物性格和父亲一辈人物性格的双重反思性体验,试图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或精神史提供不同而又相通的镜像。我曾经指出,王蒙的以审己为主的小说传达出一种独特的“骚讽”风格,即《离骚》式热烈的政治情怀与冷峻的反讽基调之间相互交融的新型美学风格。“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新的文体创造——以‘拟骚体’形式造成‘骚讽’效果,写出20世纪后期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有机悲喜剧’。”相比而言,小说《活动变人形》的美学价值则在于,运用几乎相通的“拟骚体”形式转而去反思20世纪前期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性格悲剧,试图从审父这另一面打开反思现代中国文化史奥秘的门径。
应当讲,话剧《活动变人形》在延续小说原作的上述审父意识的同时,又透过观众对舞台上倪藻灵动自由的反思状态的旁观和反思,可以同时见出倪藻对父辈反思所呈现的高明处和局限处。反思者倪藻自己也难以同被反思的父辈完全分离开来,因为他的身上既有对父辈的半吊子跨文化者性格的叛逆,也有父辈的那些注定了会继续生长的家族基因或原罪感的传承。恰如王蒙在自传中所说:“爸爸!妈妈!在你们活着的时候,我没有好好地照顾你们。在认定自己是革命者以后,我对你们更多地采取批判的态度。呜呼!污垢并非一次风暴能够荡涤干净,罪的脉络罪的根是一代代延续下来的。我现在只能为你们痛哭一场了。你们的痛苦的灵魂,在天上能够安息吗?”当这种“罪的脉络罪的根”呈现出“代代延续”的趋向时,子一代显然无法将自己完全排除在原罪感之外,而同样需要自觉地与父辈一道分担罪责。或许当看完这部话剧后,当代观众的新的反思性分责之旅才刚刚开始。他们在自己的反思性分责之旅中是否可能发掘出前所未有的新意义来,何妨拭目以待?
六、结语
总体来看,倪吾诚作为杂糅半觉式跨文化典型形象,应当是现代中国典型人物画廊里继《阿Q正传》之阿Q、《倪焕之》之倪焕之、《家》之觉新、《雷雨》之周朴园等之后涌现出来的一个无可替代而寓意深远、并可与上述前辈典型相媲美的独特艺术典型,为当代人回溯既往百余年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跨文化精神旅程提供了一个可以频频回首而兴味蕴藉的杂糅半觉式文化镜像,称得上当代北京文艺界、乃至当代中国文艺界对现代中国艺术典型的一次独特创造和重要贡献。
这部作品的现有质量已然可观,但鉴于话剧是可以通过持续演出而不断改进、更新和提高的艺术样式,着眼于其愈改愈佳直到成为经久不衰的话剧经典的目标,这里想就其可能的修改提几点不成熟建议。首先,作为故事主要发生地的河北孟官屯(其故事原型为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潞灌乡龙堂村)和旧北京胡同(如西城的西四、平安里等)的具体环境特征,还应当更鲜明和更具表现力,以便使主要人物性格生成的特殊地缘性力量及其地缘美学密码能更加完整而有力地展现出来。正如小说原作者回忆南皮时所说:“我不想回避这个根,我必须正视和抓住这个根,它既亲切又痛苦,既沉重又庄严,它是我的出发点、我的背景、我的许多选择与衡量的依据,它,我要说,也是我的原罪、我的隐痛。”其次,整部剧中演员与现场观众的共鸣及共情点可适当增加,这可以通过反复提炼和锤炼出当代观众感兴趣的重要对白语句来实现。最后,从今后作为适合于普通观众观赏的常演不衰经典剧目考虑,现有的大约160分钟演出时长可缩减到120至140分钟。
顺便说,当北京正在为建成全国文化中心城市和国际交往城市而奋力探索之际,这部话剧的出现或许还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由北京的话剧表演团队改编和演出的、由北京出生作家所讲述的自己家族的现代北京生活故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代北京人对过去生活的美学反思,并且通过这种反思来集中展现当代北京人的跨文化精神肖像。如果说,话剧《茶馆》的典型性意义在于揭示旧北京衰败的必然性,那么,话剧《活动变人形》的典型性意义在于透视出新老北京变迁的心灵史。假如这部话剧能够更加精益求精地反复打磨和提升,想必在不久的将来有望跃升成为新时代北京的一张名副其实的“文化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