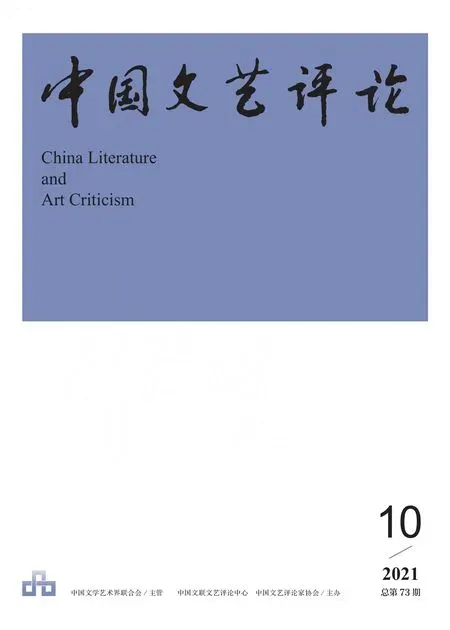增殖的美学:论文艺高峰的文本世界
李 宁
古往今来,那些傲然挺立的中外文艺高峰构筑了一个个深邃而迷人的艺术世界,不断吸引着人们深入其中探赜索隐。所谓“文艺高峰”,可以视为在艺术史中取得至高成就、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品、艺术家、艺术流派、艺术风格,等等。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文艺创作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以来,“文艺高峰”日益成为文艺领域探讨的重要议题。与“高峰”相近而更常用的概念为“经典”,不过“经典”更强调艺术作品本身在艺术传统中的典范性、权威性与导引性。二者的区别在于,“艺术髙峰必然就是艺术经典,但艺术经典未必就能成为艺术高峰”。
以往,对于“何为经典”“经典的特质有哪些”等问题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不过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文艺经典或文艺高峰本身,而常常忽略了紧紧环绕在其周围的更为纷繁多样的文本。由于文艺高峰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艺术文本不断在后世被改编、引用、戏仿、致敬、评论,等等,从而被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伴随文本所环绕,最终累积增殖为一个高度互文的复杂文本网络。如果说文艺高峰是一座山脉的群山之巅,围绕着这一主峰或最高峰的,还有形态各异的山岭与山谷,以及山体上的各种覆盖物等。简言之,文艺高峰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本文拟从客体/作品的角度,探讨文艺高峰的文本世界是由哪些类型的文本所构成的,以及不同文本在这一文本世界中的特征及地位。美国叙事学家玛丽-劳拉·瑞安(Marie-Laure Ryan)曾提出“增殖美学”(the aesthetics of proliferation)的概念,并总结出“叙事增殖”(narrative proliferation)、“本体增殖”(ontological proliferation)与“文本与媒介增殖”(textual and medial proliferation)三方面,以此考察当代文学艺术中跨媒介叙事与故事世界兴起的现象。在她看来,当代文艺创作的一大显著现象是围绕着某一核心原文本,以各种跨媒介的改编、借鉴、戏仿等不断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其他文本,最终形成复杂的文本网络。而文艺经典或文艺高峰最显著的文本特征恰恰也在于增殖,在于围绕某一核心原文本不断地衍生、扩展。因此,瑞安的“增殖美学”概念为我们思考文艺高峰的文本特征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视角和框架。本文尝试借鉴与改造这一概念,总结出文本增殖、叙事增殖、意义增殖与风格增殖四个方面,希望能借此进一步深入探究文艺高峰的文本世界。
一、文本增殖:超文本网络的生成
一座文艺高峰往往要在一个历史的长时段中才能得以崛起和巩固,在这一过程中,原初的艺术文本要经历种种旅行、裂变与衍生。以莎士比亚这座西方戏剧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为例,其作品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被不厌其烦地搬演、翻译与评论,也被跨媒介地改编为数量繁多的影视、绘画等其他门类作品,还衍生出电影《莎翁情史》等诸多与之紧密相关的文艺作品。与此同时,莎士比亚本人及其作品更是以种种或隐或显的方式出现在后世各类文本中,成为言说不尽的对象。
那么,面对一座座文艺高峰所形成的复杂的文本宇宙,又该如何去加以归类与阐释?在此,不妨借鉴法国文艺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在《隐迹稿本》中建构的与前人不同的互文性理论。在该文中,热奈特提出“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的概念,用以指代文本之间的种种显性或隐性的连接关系。他进而将跨文本性区分为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副文本性(paratextuality)、元 文本 性(metatextuality)、承文本性(hypertextuality)与广义文本性(architextuality)。由此,从原文本/蓝本(hypotext)出发,便可以概括区分出与之相关的副文本、元文本、承文本与广义文本等不同文本类型。热奈特的上述理论,为我们分析文艺高峰的文本世界提供了富有可行性的框架,据此大致可以区分出如下几种主要文本类型。
首先,是位居核心的原文本。原文本是文艺高峰形成的根基与主峰。从李白的诗歌作品到贝多芬的音乐作品,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从魏晋艺术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不同时代的原文本都散发出独一无二的光晕,展现着文艺高峰可供仰望膜拜的价值。至于这些文本究竟有哪些内在的普遍性的美学特质,以至于可以成为千古留名的经典,至今研究者们仍然聚讼纷纭。例如,艾略特(T. S. Eliot)的《什么是经典作品?》一文总结了经典作品必须具备“成熟性”“广涵性”与“普遍性”等基本特质。布鲁姆(Harold Bloom)则独推“陌生性”,他的《西方正典》分析了西方二十多位经典作家,并指出:“对于这二十六位作家,我试图直陈其伟大之处,即这些作家及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何在。答案常常在于陌生性(strangeness),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童庆炳认为经典形成的内部要素在于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开阔的阐释空间,陈雪虎则认为文艺高峰的内在规定性在于“从根本上直抵生活和人心”。对于这一问题,言人人殊、各有侧重的状况反而展现了文艺高峰理应具有的多样化特性。
其次,在文艺高峰的文本网络中,数量上更为庞大的是各类承文本。所谓承文本,指原文本的衍生文本。热奈特将通过简单改造和间接改造而从先前某部文本中诞生的派生文本定义为承文本或“二级文本”。热奈特的定义主要聚焦于文学领域,本文则将视野扩展至整个艺术领域,将以改编、复制、仿造、借鉴、戏仿、挪用、抄袭等种种方式对原文本加以改造而形成的艺术文本都称之为承文本。承文本的数量及成色,往往是衡量文艺高峰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准。如果说原文本展现的是文艺高峰的膜拜价值,承文本呈现的则是文艺高峰的展示价值。例如,金庸小说如今已经成为文艺创作中一个取之不尽的富矿,诞生出形形色色的承文本。金庸小说在我国内地的广泛传播,又与彼时盗版书籍的泛滥不无关系,同时一些创作者假金庸之名而创作出的许多伪作,从侧面也印证了金庸小说的巨大影响力。而在美术领域,许多中外艺术家、艺术作品都遭遇过赝品问题,其中的经典作品更是借助现代技术被大量复制和传播,在展示其经典价值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其经典位置。
第三种文本,是对原文本加以阐释的种种评论性、阐释性文本,可以称之为元文本。元文本既有来自于艺术场中专业人士的艺术批评话语,也有来自于普通受众的非专业性品评话语。如果说承文本增加的是原文本的广度,那么元文本拓展的便是原文本的深度。元文本的主要功能是对原文本进行美学、思想等层面的分析、解释和判断。因此,元文本话语的多寡以及元文本作者在艺术场、权力场中的地位往往是衡量原文本艺术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志。以中国艺术发展为例,其中涌现出的刘勰的《文心雕龙》、谢赫的《古画品录》、钟嵘的《诗品》、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艺术理论与批评著作,对于文艺高峰的筛选和认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再如,围绕着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我国涌现出了跨越学科与行业、至今不衰的“红学”,蔡元培、王国维、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王蒙、白先勇、刘心武等现当代诸多有影响力的研究者都参与其中。“红学”之盛,印证了《红楼梦》之高,也参与建构了后者的文艺高峰生成。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文本之外,还有在原文本周边以辅助功能出现的副文本以及言语类型、艺术体裁等更加广泛而隐秘的其他广义文本。其中,伴随各种文艺作品出现的题记、前言、题跋、插图、附录、扉页、印章、推荐语、发刊词、编者按等种种话语形式都可称之为副文本。副文本不仅为原文本营造了一个历史的现场,也在文艺高峰形成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正如有论者所言,“所有与正文本一同诞生并作为文本构成的副文本,在作品的原创阶段都已进行着某种经典化的工作”。例如,印章与绘画的结合是我国古代艺术中的一大传统。绘画作品中出现重要艺术家、收藏家的印章常常是画作价值较高的一种体现。当然,副文本与元文本有时是交织渗透的,副文本也常常发挥评论的作用。例如,我国明清时期涌现出了小说评点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小说评点主要是以眉批、旁批、总批等副文本形态跟随原文本而出现的,同时它本身也是一种元文本。以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为代表的小说评点,对文学作品价值的认定与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可见,每一座文艺高峰几乎都是一个由原文本、承文本、元文本、副文本及其各类广义文本构成的复杂文本网络,这一文本网络的基本属性在于高度互文和动态开放。围绕着原文本,每一个文本都处于其他文本的交汇处,都可以通过种种紧密的链接和互动而进入到另外一个文本世界,从而形成了一个开放的、且往往是跨媒介的超文本(hypertext)。
二、叙事增殖:多元世界的崛起
文艺高峰在文本数量与类型不断扩张的同时,其另一显著特征在于叙事的不断增殖。后来者会对原文本展开种种改造,对原文本与艺术家的创作背景、成长经历等展开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当然,叙事增殖这一特性主要针对的是叙事类文艺高峰,尤其体现在承文本的形形色色的再创造上。不同时代的人们争相参与其中,最终日益编织起超时间、跨媒介的多元故事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文艺高峰的叙事增殖可以说是受众发挥艺术生产功能的显著体现,彰显出受众在文化资本积累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文艺高峰的叙事增殖往往会采取怎样的路径呢?总体来看,大抵有两种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在原文本建构的艺术世界范围内展开叙事,这一类创作是较为忠实于原文本的改编(adaptation)行为;第二种路径则是在原文本的世界之外重新建构一个新的但又与原文本有着种种或强或弱关联的文本世界,体现出文本之间的“跨虚构性”(trans fictionality)。“跨虚构性”这一概念由法国叙事学家理查德·圣-格莱斯(Richard Saint-Gelais)提出,它指代的是“两个或更多的文本在共享人物、想象位置或虚构世界等元素时表现出的一种跨虚构的关系。跨虚构性可以被看作互文性的一个分支,但它却通常掩饰这种互文联系”。简言之,“跨虚构性”体现的是承文本对于原文本的大幅度的重构。这种重构的方式相对来说较为复杂,可以借鉴瑞安的观点,将其概括为四种操作形式:转置(transposition)、扩展(extension)、修正(modi fication)与引用(quotation)。所谓转置,指将原文本的主要设计或故事移植到新的时间或空间设置中;所谓扩展,指的是用前传、后传等方式延展原文本世界的范围;所谓修正,指的是重新设计结构与故事以建构与原文本本质上不同的版本;所谓引用,则是指抽取和应用原文本的某些局部元素。
在此,可以以《西游记》为例来进一步展现文艺高峰的叙事增殖特征。取材于《大唐西域记》、元杂剧和民间传说的古典小说《西游记》,建构了一个奇异诡谲、宏阔恣肆的神怪世界,自问世以来就不断被各个艺术领域加以开掘和改造,衍生出的艺术文本难以计数。首先,有忠实于原著的改编类作品,例如动画片《铁扇公主》《大闹天宫》,杨洁执导的电视剧《西游记》更是成为影响几代人的文化记忆。此类作品着眼于原文本在不同艺术媒介间的流徙,为原文本的大众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有以明代《西游记》三大续书(《续西游记》《西游补》《后西游记》)、电视剧《西游记后传》等为代表的扩展类作品。再次,更有大量的对原文本进行改头换面式重新演绎的修正类作品,诸如电影《大话西游》、网络小说《悟空传》、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动画片《大圣归来》,等等。此外,还有将原文本故事移植到新时空中的转置作品,如日本漫画《最游记》;以及将原文本某些元素加以征用的引用类作品,如日本漫画《七龙珠》,等等。由此,围绕着原文本《西游记》,诸多承文本合力构筑起了纷繁复杂的艺术世界。当然,由于创作主体多样、跨越时间久远等原因,这个多元世界的建构是充满随机和抵牾的,许多文本在人物命运、故事走向与价值理念的建构上有着种种冲突之处。因此,文艺高峰的叙事增殖注定不可能像如今文化工业中的许多“跨媒介叙事”案例那样,可以事先进行由上而下的整体设计,从而建构起一个严整而自足的故事世界。当然,多元世界的崛起对于文艺高峰中原文本的地位也很难形成实质性的威胁。
三、意义增殖:在建构与解构之间
与文本和叙事的扩张相伴随的,是文艺高峰文本意义的不断增殖。一方面,后续出现的许多承文本往往在沿袭原文本的某些创作基因的同时另辟蹊径,从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生发出新的意义。另一方面,来自艺术批评家、艺术理论家、艺术史家以及其他身份研究者的元文本则持续不断地从原文本中开掘出更广阔的意义。文艺高峰就在无穷的阐释中生发出一个无限衍义的意义场。
文艺高峰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实现意义的增殖,首先在于原文本自身需要有广阔的阐释空间。童庆炳在讨论文学经典时指出:“文学作品本身描写世界是否宽阔, 作品所蕴涵的意味是否深厚而多义, 对文学经典建构是十分重要的。”这一论断也适用于其他艺术门类。如果艺术作品的思想主题过于鲜明狭隘,形式元素过于僵化单一,艺术意味过于直白寡淡,是难以成为文艺高峰的。巴尔扎克小说的特异之处在于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建构起了一幅立体丰满、五光十色的世俗风情画;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流传至今在于其飘逸雄健、意蕴无穷。总而言之,原文本的蕴藉性是决定其意义增殖的根基所在。
作者意图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原文本的形态,但更重要的是,原文本在完成之后便向各种各样的阐释者敞开,成为一个开放的、可写的文本。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解读的既有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意图主义者,也有试图反抗艺术家权力意志的反意图主义者。无论如何,对于文本的任何阐释都无法绝对地回溯和重建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而是阐释者立足于自身的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化背景对原文本进行的带有一定偏差的解读。对文本的阐释总是无可避免地带有或多或少的偏见。以“耶鲁学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甚至主张“一切阅读都是误读”。
当然,强调误读的重要性并非独尊阐释者,而是要说明艺术作品意义的开掘是一个可以发挥受众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过程,这对于受众数量更为庞大的文艺高峰而言更是如此。例如,凡·高绘画在20世纪所受到的几位重量级阐释者的反复解读便是例证。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书中,海德格尔对于凡·高所画的一双农鞋展开了热情洋溢的阐释,他用诗性的话语论述了关于艺术与真理关系的思考:“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的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冥。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这器具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存。正是由于这种保存的归属关系,器具本身才得以出现而自持。”海德格尔的这番哲学沉思已经成为哲学介入艺术批评的经典案例,不过其后却遭到了美国艺术史家梅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的质疑。后者从历史考据的角度指出凡·高所画并非一双农妇的鞋,而是一双来自城市的且多半是画家本人的鞋,并由此认定海德格尔关于画作中存在之真理的发掘乃是一种“自我欺骗”,认为“在艺术品面前, 他既体验太少又体验过度”。在此之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也加入到对于农鞋的阐释中,并针对这场夏皮罗与海德格尔的争辩给出了自己基于解构主义立场的观点。除了上述三位学者之外,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20世纪90年代也曾将凡·高所画农鞋与安迪·沃霍尔的画作《钻石灰尘鞋》进行过比较,由此展开对现代主义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区隔的研究。凡·高画作上看似普通而陈旧的一双鞋子,却引得诸多重量级的哲学家、艺术史家、文艺理论家纷纷展开阐释,也有效提升了凡·高画作的意义空间与历史地位。当然,这些富有洞见的阐释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误读。
可以说,文艺高峰的确立是不断被解读甚至误读的结果。建构传统与解构传统、正读与误读是文艺高峰的一体两面。正如有论者所言,“诚如解构本身已经成为传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经典的确立和传布之中,误读也是势在必然的事情。”这里,布鲁姆(Harold Bloom)的“影响即误读”的理论或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文艺高峰意义增殖的内在机制。在布鲁姆看来,前辈作者的经典作品对于后世作者而言是笼罩于他们之上的犹如父亲和传统般的巨大阴影,使得后来者总有一种“迟到”的感觉。为摆脱前辈们所施加的这种“影响的焦虑”,强有力的后世作者必须采取一种修正式的、创造性的误读,从而实现一定程度的创新。他甚至断言,“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布鲁姆所提出的“误读”(misreading)概念不同于“误解”(misunderstanding)。如果说后者指的是一种由于知识浅薄而造成的被动错误,那么前者指的便是一种反抗式的、有意为之的主动创新。
由此来看,古往今来诸多文艺高峰之所以意义不断增殖、阐释空间不断拓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后来者以积极的误读行为来抵抗文艺高峰的巨大天幕,以开拓新的意义空间。这种误读不只体现在批评家对于原文本的重新解读,也体现在艺术家对于原文本的有意突破。中外美术史上的许多借鉴与挪用的案例就体现出后来者被经典文本所笼罩但又有意突破阴影的误读行为。例如,我国当代艺术家岳敏君创作于1995年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就从构图上直接借鉴了法国浪漫主义画派代表人物德拉克罗瓦的经典作品《自由引导人民》。不过,前者以调侃、戏谑的后现代主义手法描画了工业化与消费主义时代人们空虚而荒诞的生存状态,全然改写了后者崇高而浪漫的启蒙与革命主题。当然,创造性误读更多地体现在后来者对于原文本的改编实践中。例如,张中载曾勾勒了人们对于《哈姆雷特》中“奥菲利娅”这一人物的各种误读:“从17世纪到20世纪,不同时期的读者、导演、演员、画家、批评家在不断的误读中演绎奥菲利娅——17世纪纯真的少女,18世纪奥古斯都时期端庄稳重的淑女,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疯女人,20世纪放荡的性欲狂以及为女权奋斗的英雄人物。人们根本不去操心考虑莎翁心目中的奥菲利娅, 而是根据自己的文化环境和意向来阐释她。”由此可见,文艺高峰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误读和解构。而许多误读和解构往往又反过来成为一种正向的、积极的建构,协助原文本持续稳固其历史地位。
当然,也需要警惕的是,误读并不代表阐释的无政府主义或虚无主义。对于包括文艺高峰在内的任何文本的阐释都需要有一定之规,需要建立在对艺术家和文本的有理有据的考察基础之上。否则阐释就变成了没有尽头的符号游戏,意义的增殖也就沦为了意义的贬值。
四、风格增殖:以原作气质为中心
由于文艺高峰的文本网络在不断扩张,各类后继艺术文本所持的艺术观念往往各自不同,甚至会形成迥异的艺术风格,最终使得文艺高峰呈现出色彩斑斓的风格光谱。实际上,每一次对于文艺高峰的重新诠释,每一次对于经典的重新言说,都是一次新的艺术话语实践。
文艺高峰的风格增殖显著体现在大量风格断裂现象的产生上。如前所述,面对原文本带来的“影响的焦虑”,总是有后来者以创造性的误读迎难而上,从而开辟出新的话语空间与艺术风格。上文提及的电影《大话西游》、小说《悟空传》便是以后现代主义手法形成了与《西游记》原作截然不同的文化旨趣。达·芬奇的经典画作《蒙娜丽莎的微笑》在艺术史上所遭遇的风格断裂现象更具代表性。1919年,法国艺术家杜尚在一幅购买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印刷品上添加了几撇小胡子,由此形成了一幅全新的、荒诞不经的作品《L.H.O.O.Q》。杜尚藐视经典和传统的大胆举动使之成为恶搞《蒙娜丽莎的微笑》的始作俑者,也开启了后者被不断调侃与戏仿的先河。从美国画家达利和美国摄影家菲利普·哈尔斯曼合作的《蒙娜丽莎·达利》,到哥伦比亚画家费尔南多·博特罗绘制的肥胖版的“蒙娜丽莎”,到西班牙艺术家苏比拉克的雕塑《蒙娜丽莎》,到日本艺术家森村泰昌以自己为模特创作的摄影作品《怀孕的蒙娜丽莎》,再到法籍华人艺术家严培明的油画《蒙娜丽莎的葬礼》,艺术史上形成了各类版本、各种媒介材料的“蒙娜丽莎”。其中,既有以杜尚、达利等人为代表的戏谑风格,也有严培明以死亡为主题的阴冷风格,当然也有苏比拉克的致敬式的温情风格。种种风格的出现,使得《蒙娜丽莎的微笑》呈现出了更加多元丰富的面目。
当然,文艺高峰的风格增殖并不意味着风格的杂乱无序,而是始终以原作气质为主导的。所谓原作气质,并不仅仅是原文本所表露出的气质或风格。对于文艺高峰而言,原作气质是原作者、受众、后续创作者等合力建构的一种文本属性,它是在开放中不断建构起来的一种审美趣味。当然,原作气质也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他性。是否符合原作气质,往往是一部承文本能否得到受众认可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而文艺高峰往往就是在原作气质与多元风格的交织激荡中,生发出丰富而别样的美学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