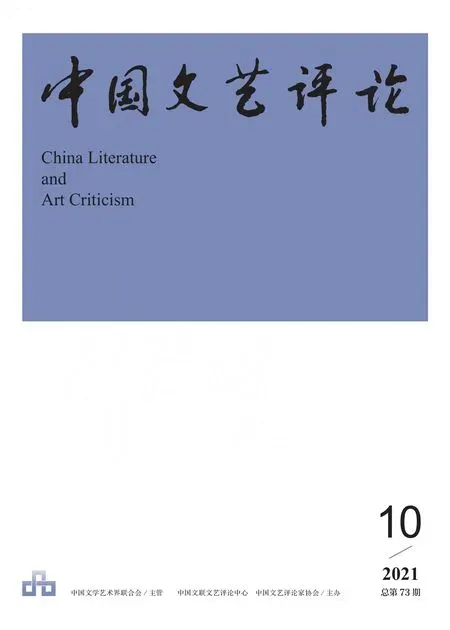宗白华“象”本体论美学思想及其艺术精神
彭 智
“意象”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十分重要的审美范畴,备受当代文艺理论学界关注,并引来诸多学者热议。而对意象的阐发,还须基于对其中“象”的体认与界定。“象”作为中国哲学美学的核心范畴,滥觞于《易传》,居于中国传统哲学核心地位,对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重要的意象说的产生与形成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然而,历代对“象”的界说芜杂纷繁,玄妙莫测,如碎玉散珠,枝蔓不成体系。鉴于“象”内涵的丰富性与言说的复杂性,故而尚有不少阐释的空间。对此,现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以其广阔的中西方哲学视野和丰富的审美体验,以中西哲学比较的方式,在《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等论著中首次系统地阐释了“象”的性质和结构,并创造性地将“象”提高到与西方形而上学并峙的本体论地位,完成了象哲学的现代转化这一难题,并较早地运用于艺术意境的创造论之中。
不过,宗白华对艺术之“象”的形上建构,是在中西互鉴的语境中展开的,并未独立撰述,且篇幅简赅,诸多重要而富有启发的观点大义而微言,且学界鲜有从哲学角度解读“象”在宗白华哲学体系中的形而上地位和艺术美学中的具体内涵。因此,本文从本体、价值以及方法论角度对艺“象”中形上本体的合法性、艺“象”本体的性质及结构、艺“象”之体用关系等问题再作探究。如此,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发掘与阐释,对现代中国美学思想体系、特别是中国意象美学思想的建构或有启发。
一、艺“象”中有形而上学之道
艺术之“象”,或曰艺“象”,在宗白华看来,不仅仅是形而下的艺术表现,也是形而上之道。象在道器之际,表里一体而非绝对区隔。重要的是,宗白华论艺“象”,首先为其奠立了哲学基础,也即为艺“象”赋予了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就此,宗白华提出,“‘象’即形而上学之道也”。这意味着,与此前仅将“象”视为具体艺术形式的研究不同,“象”在此被纳入了中国形而上学的研究视域。
宗白华这样规定作为形而上学之道的“象”:“象=是自足的,完形,无待的,超关系的。象征,代表着一个完备的全体!”“象为情绪中之先验的”。宗白华明确指出“象”具有自足、完形、无待、超关系的先验特性。形上学之为形上学,就在于其自足自洽的先验特性,绝对无待的超越性,它解决的是最广泛的、最深邃的、最原初的问题,因而在地位上具有首要性、根基性。在宗白华看来,“象”具有这些特性,因而说“中国形而上之道,即象,非理”。又曰:“象即道”,“中和序秩理数”。作为形而上学之道的“象”,其先验超越的“中和序秩理数”特性,从作为世界基本结构的最高尺度来看,无疑具有宇宙本体论意义。
宗白华认为,形而上学以其“最高容量”“最高尺度”和“最高平衡”三个维度而具有最高范型的意义。《周易》中的卦象,因包含宇宙人生的结构和价值而具有这三个维度,从而也就是最高的范型。为论证“象”作为中国形上学的依据所在,也就是证明“象”作为中国哲学本体的合法性,宗白华指出,作为形上学的“象”,具备“天则”“条理”“正”等几个最高规定性而成为“法象”,从而在本体上具有对宇宙生命和人生进行范导的意义。他认为,形式可见的天地万物是“象”,其内在条理亦为“象”。古人“制器尚象”,制作器物崇尚取最能象征天地、体现万物运行规律的“象”,这样取出的“象”就是“法象”。“法象之所取,即此‘正’‘条理’‘天则’是也。”“天则”“条理”“正”等最高规定性,就是作为宇宙世界最高尺度的“量”和“规矩”,这样的“法象”就具有最高范型的意义。故宗白华称“象”“能为万物生成中永恒之超绝‘范型’”。宗白华称之为“法象”的“象”,就此具有了形而上学意义。“‘象’如日,创化万物,明朗万物!”宗白华谈“象”,与尼采论日神精神相似,亦重于其形塑性、规定性。宗白华论“象”,与中国哲学另一个核心范畴“道”,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宗白华认为,中国有“制器尚象”的传统,“象”与“道”一样有抽象的形上性。不同的是,“象”还与“器”“用”紧密相连,体用不二,象又表征于器。“象”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价值和意义,融“宗教的,道德的,审美的,实用的”为一体,正因为“象”涵摄周广,范型万物,故能称之为“法象”。“法象”有如下性质和特征:
首先,法象为中和之正象。宗白华说,“法象者,即此‘正’象也。中正,中和之象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运行规律不能有偏差,各正其位,万物化育,并行而不悖,正体现了“中和”之“正”象。宗白华认为,宇宙生命是一大乐章,音乐的旋律、节奏与中和的“正”象若合契符,此“正”只显示于“乐”。与西方将秩序数理拿来把握现象界不同,中国有音乐性的中和“正”象,直接探寻的是宇宙生命的“意味情趣与价值”。“乐”象征的就是宇宙人生中正的德性。“正”作为“法象”的一个重要的规定,有两个基本内涵:中、和。具体而言,“中”,指生命核心;“和”,指完形和谐的机能结构。生命运化、完形过程中,归趋于和谐有序,便称之为“正”。因此,宗白华说,“象”,“则由中和之生命,直感直观之力,透入其核心(中),而体会其‘完形的,和谐的机构’(和)。”以中和之生命,体会宇宙人生的中和本质即为“正”。
其次,法象作为天则,是指示人生的范型,是人生最高的衡量法则。宗白华指出,“象”作为法象,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蒸民》),“是天则,懿德之完满底实现意境”。就社会人生而言,生民立命必然有所依归,人生行动需要指引,需要依循一定的原则,于是观象取法于天地,并以其为遵循。而“法象”就是这个遵循的最高准则、懿范,故称之为“天则”。因此,宗白华说“象”“由仰观天象,反身而诚以得之生命范型”。对天象的仰观俯察,最后取法过来观照生命,正心诚意,形成宇宙生命和人生的准则。易的卦象,正是从人道意义上,“指示‘人生’(示吉凶……)在世界中之地位,状态及行动之规律、趋向”。所以,“象”在中国就是一门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生哲学。
再次,法象作为条理,是宇宙人生创化的构成原理。宗白华明确指出,“象之构成原理,是生生条理。”象是生命绵延创化的动态规定、结构,而非西方形上学体系中作为对概念和现象秩序进行的静态分析与确定的数。宗白华在《艺术学》中提出:“凡一切生命的表现,皆有节奏和条理”。“生生条理”是宗白华生命哲学的总纲。从形而上本体论讲,宇宙生命在运动变化中都有规律。从形而下的器、用来讲,人生、艺术也蕴含这一规律。其中,深藏着具有音乐节奏的艺术与宇宙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宗白华说,中国人所说的“‘正’及‘条理’,其序秩理数,皆为人生性的,皆为音乐性的。”故孟子赞孔子“金声玉振”之语,说明生命变动不居,生生不已,条理化的生命充满节奏和韵律。无条理,生命构成就无章可循,乱象横生,无始无终。因而宗白华说,孟子称赞孔子集大成,以“金声而玉振”贯穿始终,就是从智识的层面体悟到形上之道,又从伦理实践层面以形下之器为载体体认了形上之道。
宗白华从“正”“天则”“条理”三个重要方面规定了“象”作为最高尺度的形上性,明确了“象”作为其生命哲学体系的依据所在,并由此证明了“象”作为形上学的合法性。综上可以看出,这三个规定共同构成“象”的本质属性,即“中和序秩理数”。可以说,宗白华关于中国的形上学就是观照生命条理创化的“象”哲学,其关于“象”的艺术思想亦以此为基础。
二、艺“象”乃生命时空合体境
于宗白华,作为“中和序秩理数”的法象,是艺术之象的本体。这也是中国形而上学的第一个研究对象。他认为,从价值论来看,艺象还呈现为“时空合体境”。诗画等艺术生命中的时空境界即源于此。就此,他提出“万物生生不已”之说,即“‘四时自成岁’之历律哲学”。这也是中国形而上学的第二研究对象。由于宇宙生命一定是在时空中展开的,生命之流不是时间上的线性绵延,而是有其位置的,因而有其空间向度。宗白华在《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中指出,一年12个月24个节气构成的时间节奏,率领着东西南北构成的空间方位,统一构成了我们的宇宙,也就是由时间统摄空间的“时空合体”。宗白华认为,诗画从这时间空间统一的“生生条理”世界进行取象,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六十四卦里的革卦和鼎卦。“革与鼎,生命时空之谓象也。”在宗白华看来,革卦与鼎卦是宇宙生命时间与空间合一的“象”。
从时间之维来看,革卦为“治历明时”的中国时间之象。宗白华在《形上学》开篇就明确指出,“革卦为时间生命之象。”从革卦卦象来看,离下兑上,《易经》下经解释革卦:“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离为火,兑为泽,“泽中有火”,水火不容,相互对立,必生颠覆性变化,因而促成了四季的时序更替和人类历史的推移。圣人仰观天象,俯察时变,斗转星移,岁月如梭,其中变数就是时间流转的规律,用“象”表示,就是“革卦”。这其中存在两组重要的关系:一是革与时间的关系。革,从字面上看,有变革、革新、革命的意思,其核心内涵是“变”。《易传》有言,“变通莫大于四时”,宇宙人生的变化莫过于四季分明,交相更替,时间最能体现变化之道。“革”就是这种时间变化之道的“象”。二是革与历法的关系。时间的变化,并非无序地流逝,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秩序井然,圣人君子根据这种时间变化规律,制定立法,展现了其变革的征象。前一组关系,实则将时间与生命联系了起来,时间的变化流逝,指的就是生命的“生生”;后一组关系,实则将历法与秩序联系了起来,节候历数的更替规律,指的就是生命中的“条理”。两者合观,就是“生生条理”。而在中国“生生条理”的时间观中,历法还与音律进行了融通。《大戴礼记·曾子天圆》阐述了古代“律历迭相治”的思想,历法与音律的共通之处,就在于其音乐性的节奏,宇宙乐章与制礼作乐因其节奏、条理而相通,正所谓“大乐与天地相和”。所以象征生命时间的革卦,本质上契合了形上哲学的第一个研究对象——中和序秩理数。
从空间之维来看,鼎卦为“正位凝命”的中国空间之象。宇宙生命的变化,天地万物的生息,需要在一定空间位置中展开。位置不正,万物无以立。因此,宗白华认为,“天地位,万物育”是以“‘序秩理数’创造‘生命之结构’”。时间律历揭示了生命的条理节奏,“天地位”则为生命昭明了空间结构。宗白华认为,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从作为“中和序秩理数”的形上之道,向下以器载道的贯通。天地各居其“位”,万物才能相育,生命有了“序秩理数”这一条理结构,则作为文章、机械之器的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等才有立足之据,才能以文载道、以器载道。这里作为空间的“位”,就是流动不居的生命在创造过程中的规定、秩序。这样指示人生的“法象”,用“象”表示,就是“鼎卦”。宗白华指出,“鼎卦为中国空间之象。”“‘鼎’有观于空间鼎象之‘正位’以凝命。”鼎卦,从卦象来看,巽木在下,上有离火,《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饪也。”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解释“鼎”有二义:“一有亨饪之用,二有物象之法,故《彖》曰:‘鼎,象也。明其有法象也。’”其一,鼎卦木下火上,象征燃木煮食,以鼎食祭祀、待宾客,供养神人,有安身养命的生命意识。其二,食物由生变熟,发生质变,革故而鼎新,从革卦对故旧事物进行变化,到鼎卦建立完成新的局面,含有创新完成之义。其三,鼎除为卦象外,本身也是器物之象,器型端正稳定,有空间形态,象征局势稳固,君子观鼎,以此为“法象”,就能从中体察到创新成就人生事业,以至于严整天地性命,永保禄命的法则。如果说,革卦象征的是生命内在的序秩数理,那鼎卦象征的则是生命外在的序秩数理,所以宗白华明确指出,“鼎是生命型体化、形式化之象征”。“正位凝命”的“鼎”,就是“中国空间天地定位之意象,表示于‘器’中,显示‘生命中天则(天序天秩)之凝定’。”宗白华从现代生命哲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认为鼎是烹调之器,生活中最重要的器物,制器尚象,将之作为生命意义和天地境界的象征最为恰当。其中的逻辑就是,鼎有养人之用,就与生命相关;有创成之义,就与化成天下相关;有端正之形,就与位置空间相关。因此,宗白华说,“正位凝命”四个字,是人生行动的鹄的法则,是“中国空间意识之最具体最真确之表现”,中国“求正位凝命,是即生命之空间化,法则化,典型化。亦为空间之生命化,意义化,表情化。空间与生命打通,亦即与时间打通矣”。西方几何学只求几何量化空间,并没有与生命联系起来。中国哲学讲空间的“正位”,目的在“凝命”,“正位”表示空间的序秩;“凝命”表示生命的中和。鼎卦的“正位凝命”之象,将生生条理化、“空间化、法则化、典型化”,生命时间空间化了。反过来,空间与生命打通后,空间就实现了“生命化、意义化、表情化”了。同时,生命是时间的生命,空间在与生命打通联系起来时,就与时间打通、联系了起来,于是时空就统一了起来。所以,宗白华认为人生就是不断地求形式,将自己放在合适的位置以完成自身的生命、使命的过程。这就是中国的空间意识。
从时空合一之维来看,革卦与鼎卦合为“时空合体境”之象。正如前文所述,宗白华用“革”象征生命的时间化,用“鼎”象征生命的空间化,革故鼎新包含的“治历明时”与“正位凝命”之道,则将生命的时间与空间统一了起来。所以,宗白华指出,分别对应“治历明时”与“正位凝命”的“革”与“鼎”,是中国人人生观的两大原理和法象,前者象征时间境界,后者象征空间境界,革与鼎合观,实为“时空合体境”。时空是生命的二维,革与鼎二象,便是象征中国人人生观中生命时空二维的两大原理和法象。
这样一来,中国“时空合体境”就有了与西方纯粹空间观和纯粹时间观迥异的内涵和意义了。西方纯粹的空间是对有几何矢量的世界进行理智抽象的结果,纯粹时间是线性绵延的物理概念,二者并没有统一于一体。而中国的时空观,“乃四时之序,春夏秋冬、东南西北之合奏的历律也,斯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具体的全景也”,东西南北的空间,在春夏秋冬四季的时间序列中周流不息,时间已空间化,空间亦时间化。以时间统摄空间,时空之象不再是抽象的数理,而是天地世界浑整无分的具象。宗白华指出:“象者,有层次,有等级,完形的,有机的,能尽意的创构。成象之乾,效法之坤。天地是象!而圣人以鼎象之,君子以正位凝命。”这是他融合“象即形而上之道”、象是“时空合体境”、象是“指示人生的范型”等定义,最完整、最集中的表述。象的性质、结构和功能都蕴含其中。由此可知,以此为内在精神的中国诗画艺术,绝非纯粹数理形式,而是时空合一和生命情趣兼具的感性呈现,是内在生生条理的宇宙乐章。
三、艺“象”由体到用的贯通
在宗白华的哲学—艺术致思路径中,中国传统艺术与人生的精神内核,正是中国“尚象”的形上哲学向下的贯通。宗白华说,“‘示物法象,惟新其制’(艺术精神),永在创造进化中,是空间之意象化,表情化,结构化,音乐化。”这进一步阐释了“象”的性质与结构,也指出了“象”与艺术精神之间的关系。意象化的过程,是对天象、物象以及事象等法象进行取象、拟象、模象,在哲学上成易象,在艺术上则成审美形象。象既是生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存在的状态。“象”指示人生范型的道器不离特性,决定了其功能价值为体用不二。
“象”的体用关系,在宗白华那里,乃中国形而上学的第三个研究对象。对此,宗白华明确指出,“象”乃“于形下之器,体会其形上之道。于‘文章’显示‘性与天道’。故哲学不欲与宗教艺术(六艺)分道破裂。”宗白华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崇尚从政治道德、礼乐文化等形而下的人生中阐发、体认、“显示其形上(天地)之境界”。“道与人生不离,以全整之人生及人格情趣体‘道’”。与希腊为满足理性,研究几何学推论数理而剥离人生价值不同,中国哲学无论审美性的赏玩,还是日常性的利用,都是在人生实践和实用中体认道,“以显露意义价值与生命轨道”。宗白华在提到中国认识世界的特殊方式时,认为中国儒道好以水喻道的取象方法,用水象征类比“生生不已”之道体和心性本体,这也是一种“于形下之器,体会形上之道”的认识方式。强调中国哲人倾向于“利用厚生”这一实用层面,以及“制礼作乐”这一知识文化层面,从生活实用上升到生活的宗教、道德以及审美境界。礼乐器物,不仅可以供生活所用,更重要的是以“器”为中介,象征中和序秩理数这一形而上的天地境界,以及生命本真的意义,乃至应用于艺术生命至高的境界。这里,“道”与“器”已联系统一了起来。通过作为“小象”的“器”这一媒介,体会和显示了作为“大象”的“道”,大道寓于器用之中。正如鼎,既有烹饪的器用价值,也有作为空间“正位凝命”的法象意义,体用两端,统一于鼎的卦象之中。所以古代圣哲参天地四时之象,“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象有宗教、道德、审美、实用等多种旨意,这些形下的器用文化,本自内蕴着形上之道。
形上本体贯通、运用于形下艺术,最集中的表现就是音乐。是故宗白华认为,“中国生命哲学之真理惟以乐示之”,“乐者天地之和”。中国生命哲学认为,天地相荡,阴阳相摩,二气氤氲和合,交互感通,风雨雷电生发其间,四时交替运转,万物生机勃发,世界如一大和谐乐章。这一中正和谐的生命情调即“德”,而对“德”进行象征的就是“乐”。所谓“乐者所以象德”,“乐”中包含诗、歌、舞三种艺术,以其自身节奏协和宇宙生命的韵律,便显示了蕴于宇宙生命内的真理、德性。
在宗白华看来,中国一切艺术都趋向于音乐,诗、歌、舞、画、建筑作为形下之“器”,都能从“小象”通达作为形上之道的“大象”,其重要的共通性质和特征就在于有音乐那样能显示宇宙生命的中和秩序、时空形式,以及其内在的节奏、条理、和谐。对此,宗白华在《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中明确指出中国的“艺术境界”是以具体的宇宙人生为观照对象的,了解、赏玩这一对象的形式、秩序、节奏和规律,借以反观自我的内心,使对象意象化、具象化、肉身化。宗白华认为,不仅书法、画法有飞舞的趋向,钟鼎彝器也有旋动的形线,连建筑都有表现舞姿的飞檐。舞动的艺术,有其内在的音乐节奏性,正象征了斗转星移、乾坤挪移的九天之舞。所以宗白华指出,“‘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舞”不仅是一切艺术得以表现的最本真的状态,而且是宇宙在运动创化过程中的一种象征。“舞”,其节奏韵律,实际上体现了宇宙“生生条理”中的“条理”,其旋动热情的生命力,则体现了“生生”。
除舞动的音乐节奏外,由艺进道、以艺寓道的另一个致思路径就是时空统一观在道器之间的贯通。宗白华认为中国古代《易经》里的宇宙观与中国绘画境界有着共同特点,即“时空统一体”。这与他用革卦和鼎卦阐释宇宙观的思路一以贯之。气韵生动的绘画,映射了灵气往来的生生条理世界,艺术生命在生生绵延中进而与时间打通了,而作为一定空间的画面并非纯粹静止独立的空间,而是时间化了的空间。于是,作为一定空间的画幅在生命时间的流宕中就体现出了音乐飞舞的节奏。所以,宗白华说:“中国画家所画的自然也就是这音乐境界。他的空间意识和空间表现的就是‘无往不复的天地之际’。”实际上,“时空合一体”的绘画境界还是指向宇宙论中的音乐节奏特性。宗白华在《中国古代时空意识的特点》一文中进一步阐释了古代形上“象”哲学与形下艺术的关系,指明《周易》卦象“‘六时位成’是说在时间的创造历程中立脚的所在形成了位,显现了空间……空间的‘位’是在‘时’中形成的”。卦里的六爻分别代表了六个活动阶段,每一项活动都是在时间的历程中进行,每一项活动也都有其站“位”。宗白华认为,这些凝结时空观的古代哲学思想,实际上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基础,尽管那些艺术家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它。当然,时空合体境的哲学思想能成为艺术精神的基础,其关键之处还在于时间中所固有的音乐节奏,这个关节连通了形上本体与形下层面的器用艺术。正如宗白华在《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所强调的,作为空间有建筑意味的“宇”,和作为时间节奏而有音乐意味的“宙”,是中国画家和诗人在画面中同时想表达和追求的艺术境界。“宇宙”是音乐时间节奏和建筑空间两者的统一,这样的艺术境界即“一个充满音乐情趣的宇宙(时空统一体)”。由此,艺术家能由艺进道,在艺术的“意象”世界中兼得审美功用与宇宙世界的意义与价值。宗白华形而上的“象”哲学也得以上下贯通,揭示了中国艺术体用不二的本质特征。
四、艺“象”的当代中国美学建构
统而论之,宗白华论艺术之象,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和生命哲学的影响,在批判吸收新康德主义和生命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深入玩味中国传统哲学,尝试建构独具中国特色的生命哲学体系和生命艺术体系。宗白华由对文化、艺术的体验与沉思,逐渐上升到对美学、艺术的哲学本体的探寻,经由对中西方形上哲学的反复比较与思索,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拈出一“象”,统摄生命世界,以此为根基建构了独特的艺境大厦。我们认为,“象”作为宗白华艺术哲学的核心范畴,其地位不容忽视。宗白华在西方生命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反观中国生命精神,会通中国哲学、人生、艺术,创新阐释易学中“象”的性质、结构和功能,并以“象”为中心建构了形而上学体系,执其环中以应无穷,由道到器,一以贯之。宗白华从“正、法象、天则”等规定特性证明了“象”作为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并从“革卦”和“鼎卦”中揭示了中国的时空观,还勾连了形而上的“象”哲学与形而下的文化艺术。由此,宗白华提出中国形上学主要研究对象,即“中和序秩理数”“万物生生不已之说”和“体用之关系”,体系完备。
重要的是,宗白华论“象”对于当代中国意象美学思想的建构别有启发。历史地看,宗白华论象,远绍《周易》卦象义理,善于从中国传统易学哲学中获取精髓,并转换为现代象哲学理论,为构建具有中国气质的当代中国哲学、美学以及艺术理论树立了典范;从理论特质来看,宗白华注重建构象的哲学之体与艺术之用,使其象论既具有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之维,又兼具作为形而下的艺术之维,创造性地揭示了象的时空结构及其生命节奏,为艺术意象乃至意境的创构奠定了理论基础。特别是宗白华将“象”提高到道的层面,使之与“气”这样的传统核心范畴等量齐观,但无论是气本体还是道本体,都不如象本体能使体现本质条理的哲学易象与作为感性形态的艺术现象最直接地结合,使两者呈现出理论上必然性的逻辑关联。质言之,宗白华关于象的创见,其重要意义在于,作为“中和序秩理数”的形而上之道的象,揭示了象所具有的普遍性;作为“万物生生不已之说”的象,以其时空统一体呈现了审美意象和艺术意境的创造性;作为“体用之关系”中的象,则表明了艺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性。
总之,宗白华先生围绕艺术本体之象的论说,在中国美学体系的现代创构中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当然,宗先生空灵的理论话语,言有尽而意无穷,尚有无尽的阐释与充实的余地以启来者,正如章启群教授所呼吁的,“如果说在20世纪,中国青年们从阅读朱光潜的书进入美学之门,那么在21世纪,让我们从阅读宗白华的思想为起步,来建立真正的中国美学体系吧!”在肩负文化传承使命的当下,沿着宗白华的致思之路,继续完善并建构有中国血脉的哲学美学体系,大有可为。当然,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与对流的当下,不可能也无必要存在纯粹中国话语的哲学美学体系,从王国维以下,到朱光潜、宗白华、叶朗等,融贯中西,既打开了全球视野,又激活了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精神,让“既济”的中国古老思想,“革”故“鼎”新,生生不已。因而,现代中国哲学美学体系的建构,亦不必固步自封,泾渭分明,既要与古为新,显现中国本土气派,又不妨批判吸收西方优秀思想及方法,让中国的变为世界的,显现出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