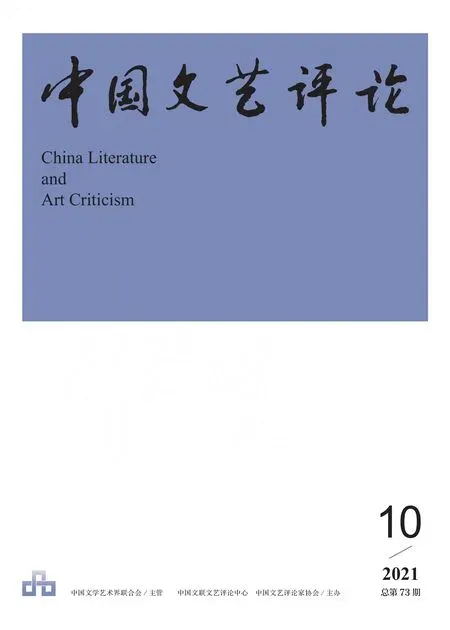赞美型正剧与现实主义
——从话剧《谷文昌》的“创作密码”说开去
麻文琦
2016年12月,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谷文昌》首演,作品由冯静编剧,白皓天导演。之后经过多轮舞台演出的打磨、锤炼,该剧于2019年先后获得文华奖和“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得到了高度肯定。2021年,《谷文昌》因受邀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的在京演出,笔者方才目睹了它已然长成五岁的模样,不得不承认相较其他类似的作品,它更为出众。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说。演出结尾处,谷文昌坚持要离开病房,回到他早年曾经战斗和工作过的东山。他开始挪动沉重的脚步,舞台上则移步换景,病室瞬间变为东山。此时的东山,青翠欲滴,绿荫将阳光过滤,变成地上斑驳的光影。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谷文昌,穿行在这片光影中。他打量着,似乎在回忆;他张望着,似乎在期待;他喘息着:“要是能再多给我点儿时间,我就可以再多干点儿”;他叹着气:“不中用了,老了,让我歇会儿,等起来再接着干”,于是在石头上轻轻一卧,不再起身。老妻走过来,默默伏在他身上;东山百姓走过来,静静围成半圈。创作者就这样让谷文昌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我看来,这个死亡场景充满艺术表现力,它带给我的感受是:创作者让谷文昌石上轻卧,便将那易朽的肉身化为了不朽的山石,斯人已逝,山形依旧,这个场景里就有了一种精神的超迈;创作者让妻子和百姓对谷文昌的哀悼,刻意地避免了任何哭喊、号啕的人声,保持一种静默的纯粹,这个场景里由此就有了一种神圣的肃穆;而最关键的是,这个场景是创作者在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世界里提炼出来的一个意象,现实生活中的时间、空间、人物动作按照一种想象的逻辑被重组,就像“米酿为酒”而“形质尽变”,满满的诗意由此扑面而来。
实际上,这个场景内涵着该剧之所以“高人一头”的创作密码,而且创作者对此“密码”的运用有着高度的自觉,可以这样说,创作者凭借一种有意识的艺术处理方式,成功地收获了既感人又诗意的效果。本文就是想对该剧的“创作密码”进行揭示性的分析,不过话题最后也会聊开去,聊聊自己的一些看法——当我们用“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对《谷文昌》这种类型的剧作 / 演出进行评价时,这种批评策略是否真的合适?
一
1950年5月,解放军南下支队解放了东山,谷文昌受命留任这座离台湾最近的闽南海岛,就此展开了他人生中华彩的篇章。国民党残部在溃败台湾前疯狂抓丁,1.2万余户的东山被抓走4792名青壮年。由于当时两岸特殊的敌对形势,壮丁家属作为“敌伪家属”被当作阶级敌人。正是因为谷文昌的建议和坚持,把“敌伪家属”改成“兵灾家属”,一个称呼的变化为占比东山人口近半的百姓赢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对待。历史上的东山是座孤寂荒岛,春夏苦旱灾,秋冬风沙害,两桶水能当嫁妆,渔民们靠吃木薯过活。正是因为谷文昌的坚韧和实干,带领全县百姓打井引水、植草固沙、种树防沙,421座山头、三万亩沙滩尽披绿装,粮食亩产过千斤,荒岛变绿洲,穷岛成宝岛。
前者是实事求是而达“人和”,后者是脚踏实地而创“地利”,谷文昌的以上事迹为创作者提供了基本的素材,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些素材是如何通过构思和处理转化成为艺术内容的。该剧导演曾这样阐述:“还原生活中谷文昌的平易近人,质朴可亲,将其塑造成为一位有坚定信仰,心中怀有梦想,坚持党性原则,又充满人性关怀的,观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他的温暖气息和亲切关怀的实实在在的‘人’,让谷文昌这样的英雄形象和精神不遥远,不陌生,不概念,不抽象”。显然,他的创作谈向我们透露出了该剧成功的一些堂奥——谷文昌形象的不概念化、不抽象,诚如导演所言,观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人物的温暖、亲切和实在,乃至更多。
譬如从“政达人和”这条事迹线索中锤炼出的两场戏:一场是在关帝庙,谷文昌携妻带头跪拜,跪谢远方的爹娘,真情的告白引来东山百姓的共情呼唤。谷文昌的人物形象在这场戏中得到了有效的塑造,观众不仅感受到了他的情义、胸襟和格局,而且还见识到了他化解矛盾、沟通人心的智慧。另一场是在会议室,创作者设置了一个尖锐的辩论情境,让谷文昌与同事们形成一种观念和思想的对立,一方是谷文昌对将“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的坚持,一方是工作伙伴对此的疑虑、担忧和反对,从而在这种有目的的映衬下,凸显出人物力排众议的大爱、担当、勇气和激情。
再譬如从“斗沙治穷”这条事迹线索中打磨出的两场戏:一场发生在谷文昌的家里,穷得饿肚子的乡亲们成群挤进家中向谷文昌讨要粮食。谷文昌不仅分发了家中的存粮,还自掏腰包将所有工资买粮接济百姓,最后甚至把妻子所珍爱的嫁衣全部送人。这是一场从情理常规上看显得“反常”的戏,创作者利用它恰恰是想描画出谷文昌仁爱温厚性情中“面嫩”“讲脸”的某种可爱的滑稽。另一场演的是木麻黄种上了,水井也打成功了,但风沙卷走了树苗,严寒冻死了树苗,恶劣的自然环境不遂人愿,谷文昌伤心到流泪,绝望至退缩,这场戏的目的很明显是想向观众展现:在人物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坚韧和顽强,也还有脆弱和迷茫。
创作者娴熟地借助了这一场又一场戏,并辅以大量的细微的动作细节,有明确意识地从不同角度变化着为人物赋形,由此谷文昌的艺术形象不仅在政治性方面获得了完整的表现——一个“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楷模式党员,而且在人性层面也拥有了属于他自己的个性表现——一个不乏风趣、颇有机智、偶有脾气、宅心仁厚的可爱的人。面对这样的人物形象,观众当然不可能不对之产生认同感和亲近感,也一定会对之生发出感动和喜爱。
《谷文昌》“高人一头”的创作密码有一部分在于其人物塑造的相对成功。不过从最终的艺术效果来看,种种人物塑造的手段,尽管一个个构思内涵匠心,但终究是敷演出“典型好人”的种种“戏码”。谷文昌这一人物,因为其“好人形象”的属性,不管创作者在他性格结构里、精神纵深处开拓出多少“褶皱”,也只能是在大爱、担当、勇气和激情等这些正面赋形外,融合进某些机智、风趣,乃至某些可爱的滑稽、无伤大雅的颓丧,实际上它们只是对一种正向品质的性格调色,构不成充满张力的、耐人寻味的复杂性格结构。
谷文昌是一个能够让人心生感动的“好人典型”,在当今舞台上层出不穷的好人形象系列中,他的确是出众的,但在楷模性上却是殊途同归。《谷文昌》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创作层面,哪怕这个人物在动作细节的锻造方面更精准、更有艺术表现力,在笔者看来也是不值得加以特别对待的。所以该剧给笔者的最大感受是,除却人物所具有的一定质感外,还有一种让人沉浸其中的诗意,显然,这一特别的艺术效果并非完全来自于人物塑造。
二
《谷文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它的结构:表面上看,该剧大半情节都是把谷文昌的两条行动线索交织起来进行结构,一是“平反”,二是斗沙,但它们最后都极有规律地汇聚到某场家庭戏里。譬如,谷文昌携妻在关帝庙跪拜化解矛盾、融化人心之后,谷文昌自作主张掏钱买粮、赠送嫁衣之后,创作者的笔触便落在了一场夫妻对手戏上。如此安排在后面的结构中再次出现。谷文昌与同事们辩论,坚持要将“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他异常激烈地表态说,不解决就去中央,就去找毛主席!接下来的戏是谷文昌为木麻黄的损失伤心绝望,再之后便又是一场夫妻对手戏。观看此剧时,我被不时触发而生的暖暖的感动,以及我所感受到的从演出中弥散开来的抒情性的诗意,实际上都源于这种结构布局。
先来看第一次夫妻对手戏。该场戏表现的是谷文昌因为前有令妻跪拜、后有掏光家当,所有这些带有一定牺牲性的“好人好事”,他并没有事先询问过妻子史英萍的意见,所以当他面对妻子时难免有些惶然和愧疚,于是他变着法儿地讨妻子欢心。如果我们把写这场戏的目的仅仅理解为是为了表现主人公在私密生活中的丰富侧面,那就完全忽略了该场戏的真正“戏眼”所在。这场戏的“戏眼”是:史英萍真的很生气,她不断转移话题数落着丈夫的种种不是,她命令谷文昌交出藏在身上的所有烟卷,可当她看到丈夫从裤兜里掏出来一块本该作为早餐的面饼时,她的不快瞬间被巨大的心疼所覆盖,夫妻之间的小小矛盾刹那间烟消云散。夫妻俩静静地坐在那儿,相互依偎着,观众能感受到他们彼此的爱意,就像月辉般温柔地发散开来。正是在创作者经营出来的这种美好的静谧里,谷文昌的心扉向妻子敞开,也向观众们音乐般地奏响,他开始倾诉他内心关于未来的东山“举首不见石头山,下看不见飞沙滩,上路不被太阳晒,树林里面找村庄”的梦想。
第二次夫妻对手戏是这样写的:谷文昌在付出种种努力后,无论是在“敌伪家属”问题上,还是在打井治沙的问题上,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不过天灾与他为难,他寄托了满满希望的木麻黄没能迅速实现他绿阴如盖的梦想。憋屈懊丧的谷文昌回到家中,这一次轮到他不断转移话题冲妻子发泄种种邪火和脾气,妻子则变着法儿地跟丈夫逗趣,甚至调皮地有意拱火,最后谷文昌负气离家。就跟前面的夫妻对手戏一样,创作者编排这场戏的目的当然不是仅仅为了表现主人公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情趣,他们把戏核又一次放在了俩人的和解上。妻子交给丈夫一封信,然后离去,留下谷文昌一人在夜色中展信览读。谷文昌读到的只是妻子的几句鼓励、几句叮嘱、几句提醒,但纸短情深,如舒缓人心的几串音符,流淌出来的是知我心者的流水高山、守候永远的相濡以沫。谷文昌的心宁静了,也跳动了,他呼唤着:“英萍,我饿了”,就像孩子呼唤母亲一般,而妻子早早就在家门口站着,端着满满一碗面条,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问题是:这两场戏有什么特别的吗?它们镶嵌在谷文昌种种事迹之中,难道不就是一种简单的事业 / 家庭的线索编排吗?不就是一种社会事功 / 夫妻情深的花开两朵吗?或许在情节发展节奏上起到了一张一弛的节拍效果,在场面组合色彩上达到了一浓一淡的悦目成效,又或许是因为它们的存在,观众能够从中领略到主人公内心更为丰富的律动。以上分析都没有错,但还没有触及到《谷文昌》如此结构所蕴含的真正值得借鉴的地方。
我认为,创作者规律性地将谷文昌的行动线从“平反 / 治沙”变轨到“夫妻情深”,就像白昼 / 黑夜的更替轮转,在这种安排下,我们的主人公一次再一次地从喧嚣走入静谧,如同崇山峻岭间奔腾的河流变为花草月光下蜿蜒的小溪,让该剧在结构上拥有了一个特殊的时间和空间。而创作者利用这一时空,在由谷文昌一件又一件事迹所写就的散文中,开始提炼一首凝练的诗篇,这首诗由舞台上的三个意象构成——“揽妻静坐”“捧碗吞食”,再加上结尾处的“石上轻卧”,它们前后呼应,最终组合形成高度诗化的表达。
换言之,创作者一方面呈现了谷文昌的“好人好事”,另一方面则基于对主人公生命最内在的脉动的理解,用非常精简的场面写就了一首关于谷文昌心灵的诗篇,那就是:梦—家—国。这是《谷文昌》在创作上最值得从理论上加以总结的“奥妙”,它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在于:创作《谷文昌》这种类型的戏剧作品,仅仅写好事迹是不够的,创作者需要让观众从事件的组织中见到“人”;但仅仅“见人”也是不够的,创作者还需要让观众从人物个性的刻画中领略到“心”;但仅仅“识心”仍然是不足的,创作者最终需要通过内心世界的呈现让观众品味到“诗”。
三
《谷文昌》这样的戏剧作品,需要创作者在构思上做到从事到人、从人到心、从心到诗。作出这一判断的原因在于,《谷文昌》是一种赞美型戏剧,它所要发挥的戏剧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观众精神的引领和激励上。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周予援在谈到《谷文昌》的创作初衷时说:“创作《谷文昌》体现了我们国家话剧院的担当。我们讴歌时代英雄,把谷文昌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激励我们继续前行。”作品倘若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讴歌”“激励”的效能,在艺术特征上就必定要做到一种“提纯”性,从而在戏剧情境的选择、冲突方式的设置、人物个性的塑造等方面,并不能完全按照“真”的原则,而更多是要遵循特定时代中“善”的理念来进行艺术构思和处理。它对社会现实复杂性的吸纳程度是有限的,即便可以让人物身处一种更能折射现实复杂性的情境里,但对人物的打造方式一定是“追光”性的,用光亮勾勒和渲染人物,让他能够鲜亮地独立于周边暗黑的环境。
也由此,类似《谷文昌》这样的作品会非常容易因为概念化而抽象生硬。所以创作者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避免因为高蹈而踏空。这个方向就是要背身抽象的呆板,向着让“好人”形象具有人情味儿的方向迈出第一步,但这一步只是“落实”的第一步,还需要在创作上迈出“入虚”的第二步,由实入虚,让观众由道德上的感动步入艺术上的品味,因此如何诗化是赞美型戏剧应该进行艺术冲刺的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谷文昌》成为了一部可资借鉴的作品。
《谷文昌》被笔者称之为赞美型戏剧,其实从戏剧美学的角度来看,它属于特定的戏剧体裁——“正剧”。面对这种类型的戏剧作品,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批评?如果我们用现实主义这一美学概念对它进行评价和要求是否合适?在此,我想从《谷文昌》的创作分析说开去,最后就这一有关批评理论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有评论者评价《谷文昌》,认为它“基本达到了现实主义精神主导下的主旋律创作的要求”,评论者认为其基本达到而不是完全做到的美学评价依据是“现实主义精神”——一种“对人民的生活命运和思想情感的深切关怀,富于人文深度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品格和热烈的理想主义情怀”。《谷文昌》当然具备“深切关怀”和“热烈情怀”,却不具备“富于人文深度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品格”。可问题是,我们用这样一种“批判精神和批判品格”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来要求《谷文昌》是正确的吗?当我们要求《谷文昌》的创作者应该“把人物塑造和情节描写扩展至更大、更广和更深的范畴”时,那么这个“更大、更广和更深”又会将《谷文昌》引导到一种怎样的创作方向上去呢?《谷文昌》的艺术特征恰恰表现为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以及环境的真正复杂性的过滤,表现为一种美学上的提纯性。所以,如果我们让该剧背离它的这种艺术规约性,要求它“更大、更广和更深”,这是否是一种恰当的批评呢?要回答好这个问题,需要返回到一段也许我们并不陌生的历史中去,在正剧发生以及现实主义美学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去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
四
历史上首倡正剧实践的是狄德罗。狄德罗意图用正剧驱赶主导法国当时剧坛的古典主义悲剧,他为正剧勾勒了一份粗糙的创作指南,其核心原则可总结为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真实”——通过当下生活的取材、散文化台词的写作、生活化的表演方式以及逼真的舞美设计来达到;另一个是“美德”——通过塑造“资产阶级市民新人”形象来打造一种与王权贵族戏剧相抗争的资产阶级戏剧。显然,正剧的“真实”原则多多少少构成了后来现实主义戏剧美学的理论源头,但更加关键的是“美德”原则,狄德罗对正剧的“美德 / 责任”的美学要求,显示了正剧的真正面貌:一种运用写实性的艺术语言作为包装策略的、以讴歌赞美资产阶级清新形象为目的的戏剧形态。
不管正剧理论与后来的现实主义美学存在着多少缠绕,现实主义美学的发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都是对狄德罗式正剧创作的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所凝练出的现实主义美学的一组核心概念“典型人物 / 典型环境”,可以说完全是在与狄德罗式正剧的核心概念“真实/ 美德”唱着反调。在前者的眼里,后者的“真实”不过是一种刻意营造出的带有逼真性的艺术效果,“美德”也终究只是关于资产阶级英雄形象的道德“P图”,而现实主义的“典型”却是在强调,应该艺术地呈现而不是遮蔽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社会结构和历史矛盾。因此,“典型人物 / 典型环境”的美学诉求是内涵着现实批判性的,后来的卢卡奇对此全然领会,他对现实主义美学继续加以阐发,将其表述为一种“总体化的批判美学”。当然,接下来的故事是布莱希特,他绝不认同卢卡奇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锁定在“典型人物 / 典型环境”的这种做法,而再后来的加罗蒂则用他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将类似荒诞派这样的戏剧作品也纳入到现实主义的艺术阵营之中。
不过,无论他们在理论阐释上有着怎样的变化,其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在内在精神上仍然保持着社会批判性的指向,从而与狄德罗式正剧的“肯定性美学”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否定性美学”。下面的总结能够让我们对正剧与批判现实主义的关系有着更加透彻的把握:正剧美学呼应的是资产阶级起步上升期的那段历史,而批判现实主义美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全面暴露期的一种回应。由此,正剧就像被它所否定的古典主义悲剧一样,无可避免地遭遇了被批判现实主义戏剧所否定的命运,之所以说是无可避免的,是因为发出否定力量的不是一种美学理论,而是社会历史运动所形成的充满深刻矛盾的现实生活。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历史地看,正剧的创作实践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中的奥妙非常有必要加以揭示。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说,正剧理论的源头起始于法国新古典主义,这是因为法国王权在一统封建贵族割据的政治较量过程中,需要建构一套有利于其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新古典主义美学正是由此产生的。像布瓦洛这样的理论者,借用但又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打造出了一套新的悲剧论述,其核心就是塑造拥有服膺王权的理性精神的新贵族英雄形象(路易王朝时期所期望的新人),为此他将悲剧的艺术功能调整为“道德感动”。高乃依的《熙德》正是符合这种美学倡导的一部标准的悲剧作品,但究其实,它不过是顶着悲剧名义的正剧作品。后来的狄德罗,尽管他的正剧是反古典主义悲剧的,但他反对的方法是用资产阶级新人形象替换贵族英雄形象,但在“道德感动”原则上,却让自己的正剧美学与新古典主义美学保持了一致。
从法国新古典主义悲剧到资产阶级正剧,这段历史波折向我们透露的信息是:正剧的艺术实践是与政治实践紧密相关的,需要在美学上创造出与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相配套的新人形象。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又一次重现,但这一次是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美学号召让正剧创作保持了一种历史的延续。梳理这段历史,揭示正剧与政治的关系,目的在于从道理上说明这种塑造“新人”式的、赞美型正剧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它不因对其来自各个角度的美学批判就自动消失,它将始终成为戏剧创作生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一个强大的组成部分。
如上所述,赞美型正剧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下一种美学积淀的结果,它与政治的联系清晰而紧密,遵循的是肯定性原则,发挥的是正向建构秩序的艺术功能。基于此,我认为:运用批判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对类似《谷文昌》这样的戏剧创作进行评价是不合适的,这是一种错误的批评策略。真正进行有效批评的前提,是要对赞美型正剧的原则报以尊重,而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则是要让这类作品的创作在不改变自己艺术规定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朝着更有艺术性的方向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正剧的创作实践,走过了七十多年的历史,期间的道路多有起伏和坎坷,教训需要总结,经验也需要盘点,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正剧的创作,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理论评论工作者如果想在理论上有所开拓和建构,不仅需要对既往历史的创作实践加以厘清,而且需要对当下从创作实践中涌现出的新的经验加以把握。话剧《谷文昌》恰恰创造出了这种新的经验,而对这种经验的辨析和总结,是有助于丰富我们社会主义正剧的创作武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