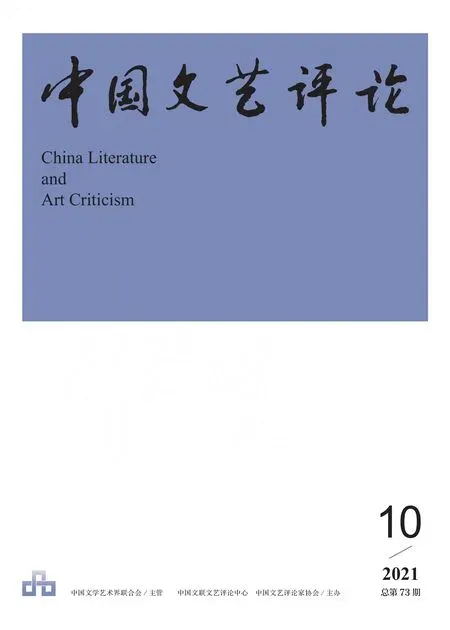从“美术”到“美学”
——关于实用主义与中国美学的建构
殷国明 汤奇云
就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生与构建历程来说,一直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两条线索,而且都是在一种跨文化语境中展开的,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和融通的特点。前者主要受到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借鉴了有关理论观念,通过与中国文论思想的碰撞和磨合,形成了中国化的美学思想表达;后者则主要通过诸如绘画、舞蹈、音乐等具体艺术创作之间的交流和借鉴,形成了一种对于艺术性质、价值和功能的新理解,继而上升到了美学理论层面。可以说,在关于中国美学发展历程的研究中,理论和理念层面的寻根探源比较多,亦有诸多学术成果,但就具体艺术层面的研讨比较少且相对薄弱。而正是在这种情境中,“美术”与“美学”之间的关联和关系,以及它们在20世纪初中国美学发轫期的碰撞与转化,成为一个有必要展开讨论的课题。
一、“美术之学”的命名与“西学为用”的语境
在中国人文学科史上,美学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交融的产物,其发生和来源是复杂多样的。既有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在应合,也有外在思想的影响和介入,还有中国学者根据本土语境进行的各种不同阐释和理解。
单从理论学科来说,中国美学之源起就不能不提到王国维。因为王国维最早意识到中国文学在理论意识方面的缺失,是最早呼吁并致力于美学理论建设的学者。尤其在接触德国哲学思想之后,王国维对中国文化及学术现状进行了反思。他特别感慨于中国缺乏纯粹精神和信仰方面的理论建构,因而容易导致过度追求功利性、实用性的倾向。他说:“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其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更转而观诗歌之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
正是由于这种心境与见解,王国维接触到西方“绝对理念”“纯粹哲学”“纯粹美术”等观念时,就产生了某种“久旱逢甘霖”的共鸣和感悟;并迅速切入对中国美及其美学理论的建构之中,从而把西方美学思想融通于中国传统文学的解读和批评之中。王国维还有一段话也常常被人引用: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以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王国维所强调的是来自哲学和美学的超越实用和功利目的的终极价值,所追寻的也是一种形而上的纯粹理念;但是除了偶尔出现“美学”一词之外,多用“美术”一词来进行表述。显然,这种关于美及对美学的追寻,即便在王国维的论述中,也依然存在混淆不确的地方。显而易见的是,王国维这里所说的“美术”,并不是指绘画,也不是“美的技术”,而是指向了从德国哲学中引入的美学。
其实,就对美的理解及其阐释而言,“学”与“术”有着很大的差异。“学”重在研究,重在理论,重在对普遍原理和价值的探讨,更倾向于以纯粹的认知理性来完成对“真理”的追求;而“术”则重在实用,重在技艺,重在对方法和经验的学习,更倾向于对具体形式和结果的验证。当然,这两者之间并非全然是对立和隔绝的,而是时常纠缠在一起。这种“学”中有“术”、“术”中有“学”的学术范式,已经在晚清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思潮中成为了主流模式。或者说,晚清学者们还在下意识地拒绝把西方哲学与美学当成真正的学术本体,以免冲击他们所熟稔的传统道德之学和政治之学。
但是,在任何一门学科的发轫期,我们并不能过度地强调这种“术”“学”差异,而是要理解它们之间时而相互矛盾冲突、时而相互交叉借助的情形。所以,就“美学”和“美术”来说,我们并不能过分指责王国维的意指不明或在混淆这两个不同概念。在20世纪初较长一段时间内,“美术”和“美学”都是从外国文化中“假借”而来的,都还没有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生根,所以在很多相关论述中,“美学”和“美术”是并存互通的。它们也经常被阴差阳错地放置在一起,表达着相同或不同的意义。
王国维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曾写了《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专门讨论这一学术概念翻译所面临的难题。他首先指出,不同国度的国民在思想和语言上有精粗广狭之别,而我们用“近世之语言,至翻译西籍时又苦其不足,是非独两国民之言语间有广狭精粗之异焉而已,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或繁于此而简于彼,或精于甲而疎于乙,此在文化相若之国犹然,况其稍有轩轾者乎!”他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而造成了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他分析道:
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见其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况于我国夙无之学,言语之不足用,岂待论哉!
在这里,王国维不仅指出了中西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差异,而且还注意到了“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差别,并希望中国文化在“学”的方面有所开拓。所以,如果按照王国维所说,“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美学当属中国之“夙无之学”,且正逢中国理论思考方面的短板,故其输入和生发自然首先就面临语言和话语方面的挑战。因此,努力弥补中西文化的差异,为新思想和新学说找到适当的新言语,就成为了当时学界最迫切的问题。
然而,这无疑是困难的。就拿王国维所常用的“美术”来说,实不能确切表达出“抽象与分类”的意味,与形而上的纯粹理念范式亦有隔膜。因为传统文化中的“术”,原本就是一种“具体的知识”,为满足具体实际之需;故而它不能被称为理论,也不能成为一种学问。王国维为什么频频使用“美术”而不是“美学”?这里还存在一个不能不重视的文化机缘,即中国很多现代学术名词和话语都是从日本转译而来,于是带有某种先入之见的优势。这也是王国维极为关注新学语输入问题的原因。他指出:
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
日译对近代中国学术的影响,早就受到学界的重视。20世纪初,取道日本学习和转译输入西方文化思想,已经形成了一种潮流,致使中国新思想、新艺术和新学术的形成无不受到近代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但是对其所产生的误译、误释和误导现象,还缺乏深入细致的辨析和研究。这里可以看出,对于新学语的转译,王国维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看到了其不妥、不适,乃至不满意之处甚多;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接受“先我而定之”的现实,来满足“非增新语不可”之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中,王国维使用了“新学语”而不是“新术语”,似乎有意识拉开了“学”与“术”的距离,为此后学界用“美学”取代“美术”埋下了伏笔。随着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日渐增多,国人本土文化意识的增强,“美术”一词逐渐回归于具体的绘画领域之中,而“美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建构也渐渐被确立。
二、“美术之用”与美学的实践品格
自19世纪末以来,很多中国学子游学日本,目睹和感受到日本思想学术和艺术领域所发生的重大转折和变化,引发了他们对诸多艺术变革的思考。显然,日本近代社会变革,与激进、彻底的实用主义取向有很大的关系,其引进西方文化思想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加速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对于具有实用性的西方美术技艺与理念显示出浓厚兴趣。他们最初深受西方“美术”(Fine arts)思潮的影响,而不是“美学”(Aesthetics)理论。据相关研究,日本最初就是从实用目的出发而引进西方美术的,通过创办“工部美术学校”以促进“劝业”;而学习西洋画技能,也是为绘制机械制图、医学解剖图、兵器船舶制造剖面图和结构图等等,一开始并不包括音乐和诗等艺术教育,更不要说追求纯粹艺术和纯粹理性了。
这种出于实用之需的学术风气,不仅影响了日本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影响到了中国美学思想的选择和建构。据相关研究,“美术”(Fine art)一词原本就是从日本转译而来的。而“美学”与“美术”在中国的混用和互动现象,就打上了这种转译的文化烙印。这种情形在1888年康有为所著《日本书目志》中也能略见一斑。此书目之引进乃是为了改变“以大地万国皆更新,而中国尚守旧故也”的状态。所谓“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黯;新则洁,旧则败”,也正是那个时代国人们所能意识到的“天之理也”。就在这个书目志中,他不仅选录了诸如《维氏美学》《美术新书》《美术应用》《美术画谱》《美术世界》《美术木版画》等书籍,而且以“美术门”为类别,总括了绘画、雕刻、舞蹈、音乐、书法,乃至琴艺、茶道、插花、游戏等多种艺术种类。可见“美术”此时已经成为超越某一具体技艺范畴的概念。尽管“美学”概念也已被引入和认同,却与“美术”形成了某种相互映照又互相博弈的微妙关系。
这当然造成了“美术”与“美学”混用的现象。而从康有为的自序中也不难看出,这一切都是为了“……汲汲思自强而改其旧矣”。他希望通过“尽译其书”,达到“以我温带之地,千数百万之士,四万五之农、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驾于英、美而逾越于俄、日……”的目的。显然在他的逻辑里,只有通过引进多种多样的西洋“美术”,才能起到智民强国之用。
至于“美术”与“美学”的杂糅和代用,还可见于鲁迅发表于1913年2月的《儗播布美术意见书》。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开篇便确认:“美术为词,中国古所不道,此之所用,译自英之爱忒(art or fine art)”;继而又说:“顾在今兹,则词中函有美丽之意,凡是者不当以美术称。”为此,鲁迅辨析了“美”与“美术”之间的异同。他说:一是“主美者”,即以美为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无关系”;二是“主用者”,“……以为美术必有利于世,傥其不尔。即不足存”。鲁迅之文无疑也是奔“美术之用”而来,一切只为探寻一种“实践此目的之方术”。所以,其播布的目的也很明了,即“谓不更幽秘,而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正是20世纪初中国美学初创时期的特点。在这方面,金松岑的《文学上的美术观》(1907)也显示出了大致相同的学术认知。他从美术出发去探讨美学的存在及其意义,认为“美术”与“美学”可以合二为一:“世界之有文学,所以表人心之美术也;而文学者之心,实有时含第二之美术性。”如果由此扩展到更宽广的领域,我们就会发现,关于美及其美学在中国的生发,既有对形而上纯粹哲学层面的理念追求,也有出于物质生活实践层面的迫切需要,甚至还有实用技艺方面的考量。
因此,人们普遍从社会实用角度去引进、理解和借鉴西方美学思想,也就不难理解了。同样受到德国哲学美学影响的蔡元培,原本也有把美学归于“心界哲学”的想法;但由于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方面的需要,也很快转向了对更具可操作性的美学教育的提倡与推广。他还提出要认真研究美之原理与各种科学领域之间的关系。他曾在《哲学要领》一书中说:“好美恶丑,人之情也,然而美者何谓耶?此美者何以现于世界耶?美之原理如何耶?吾人何由而感于美耶?美学家所见、与其他科学家所见差别如何耶?此皆吾人于自然界及人为之美术界所当研究之问题也。”显然,蔡元培也同样关注到了美术与美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他说:
美术界Art,德人谓之坤士Kunst,制造品之不关工业者也。其所涵之美,于美学对象中,为特别之部。故美学者,又当即溥通美术之性质、及其各种相区别、相交互之关系而研究之。
所谓“美术界”,当是西方18世纪逐渐形成的概念。它指的是“绘画、诗歌、舞蹈、音乐、戏剧和雕塑,到头来被视为‘美的艺术’(Fine arts)——一般写起来,首字母要大写”。在另一篇讨论美术教育课程的文章中,蔡元培甚至认为:“文学者,亦谓之美术学,《春秋》所谓文致太平,而《肄业要览》称为玩物适情之学者,以音乐为最显,移风易俗,言者详矣。”
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尽管很早就接触到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哲学美学思想,但是触发其转向美学研究的机缘,却是从美术绘画开始的。据说,在德国的一次美术课观摩中,他受到了很大触动,不仅打开了以往从“寄情于山水花鸟”去理解绘画艺术的狭窄视域,而且拓展了其美学研究和美学教育的道路——这或许就是1912年他要把美育引入中国的机缘与契机。
事实上,蔡元培所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之说,也带有强烈的实用色彩。由此可以说,中国美学建构的实用之路已经敞开。当然,与王国维相比较,蔡元培的美学思想,或者说他所追寻的美学建构,并不像王国维那般具有纯粹的理论色彩,而是有更鲜明的社会实用性特征,也不乏从社会具体需要出发去建构适合于中国实际的美学系统的意图和勇气。他不仅在美学理论方面有深入的思考,更注重从社会变革的需要出发,探索美学介入具体社会实践的可行性。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堪称是“实践”美学最早的实验者。他把美的理论带入了具体的、有可操作性的社会文化和教育领域,具有人文性与工具性相融通的特征,从而打通了从“理论”美学走向“实践”美学的道路。
当然,蔡氏的“实践”指向了文学艺术家通过其创作活动介入现实生活的艺术活动,而非人类改造世界的社会生产生活行动。因此,蔡元培从文学艺术方面着手的美学探索,就体现了其力图从工具理性向精神理性转型的倾向;或者更准确地说,体现了其企图把两者融通起来的努力和尝试,以解决王国维所认定的中国文化长于“实践”而短于“理论”所带来的困扰。由此可见,20世纪初中国美学的创建之路,是同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向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美术作为一种更为直观和接近实用目的的艺术形式,就无疑是中国美学建构历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起步点和聚焦点。
其实,在清末民初这一段时间内的学术思考与表达中,不仅“美学”和“美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用和互译;在美学的“美”和美术的“美”之间、在哲学之美和艺术之美之间,都存在着多方面的相互认同与融通的特点。中国美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明显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再从理性到实践等多次反复再造的过程。因此,在中国美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初期,“美学”和“美术”存在多种误译、混用、误读和误解的现象也在所难免。从美术到美学,从实用之术到无用之学,无疑是中国美学的建构之路;其价值取向表现出一种从“重精神”到“重实用”的转型和转向特征。这既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也是工具理性与精神理性博弈的结果。因此,如果说作为理论观念和学科建制的美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是在对“绝对理念”和“纯粹美术”的追问和探讨中,使得中国美学对传统“美”的阐释有了哲学思辨和理论思维的特点;那么,时代文化变革的需要所引发的对于“实用美术”的引进与注重,则为中国美学理论的建构夯实了现实生活的基础,让中国美学自诞生起,就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发生了紧密联系。而这种理论与生活紧密关联的学术路径的建立,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乃至“生活美学”的产生铺设了道路。
三、 实用主义传统与美学的转向
其实,既重“精神”也重“实用”,既重“精神理性”也重“工具理性”,是20世纪初中国美学理论原初建构的目的与特色;也是中国第一代美学家自一开始就强调“学”“术”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范式所带来的结果。他们在中西文化的对照和比较中,即便对西方的美学观念有所借鉴,也没有忽视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中国国情在实用方面的需求。甚至可以说,随着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需要,对于美学实用价值的注重和追求,一直是刺激和推动美学思想变迁的重要驱动力。因此,实用主义已成为了促发中国美学转向、转型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
中国文化原本就有着源远流长的实用主义传统,洋务运动中所谓的“西学为用”就是这种实用主义价值取向最为明显的体现。因此,在由美术走向美学的历程中,以工艺美术为代表的实用美术,或者说美术中的实用价值,在中国尤其受到青睐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了。“美术”概念伴随着“西学为用”的潮流进入中国,自然比纯粹的“美学”概念更容易得到响应。
诚如刘师培在1907年《国粹学报》上发表的《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所言:“夫音乐、图画诸端,后世均视为美术。皇古之世,则仅为实用之学,而实用之学,即寓于美术之中。舞以适体,以强民躯。歌以和声,以宣民疾。而图画之作,又为行军考地所必需,推之书契既作,万民以昭,衣裳既垂,尊卑乃别,则当此之时,舍实用而外,固无所谓美术之学也。”确实,离开了“实用”,也就无所谓中国美学。尽管他讲的是“皇古之世”,实则也是在说他自己所处的时代。
显然,刘师培的“美术之学”已经十分接近现代“美学”概念。以现代美学眼光来看,中国人的美学观念与审美趣味从来就寄寓于本民族的音乐、绘画、歌舞等艺术门类之中。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仅就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而言,中国并不乏丰厚的艺术遗产,创作和论说也都有精彩的传承和展演。然而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刘师培、蔡元培等所期待的美学。比如,宋代郭若虚就继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而作《图画见闻志》,其在《叙诸家文字》(卷一)中就列举了南齐高帝撰《名画集》、谢赫撰《古画品录》等三十余部关于画论的作品,其后出现的更是难计其数。这些主流的艺论画论也从来没有完成过自己的美学建构。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界在热衷于西方美学理念与美术思潮时,极少将自己的美学思考建立在这些传统艺术资源之上。除了少数新式文人士子依然在采用传统的书画艺术用以怡情养性外,创作界也较少采用这些传统的艺术形式。
是传统艺术太“征实”,太“功利”,从而阻碍了中国美学迈向“形而上”的精神之思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与陈独秀一道首倡“美术革命”的吕瀓看来,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恰恰是因太脱离实际,过于远离现实生活,才使得它们远离了理论家的视野。况且,从蔡元培和刘师培的论说中也不难看出,“实用哲学”或“实用主义”并非美学的敌人。相反,是实用主义中的现实情怀促成了中国美学的理论构型。事实上,理论界一直在试图与西方现代美学(包括实用主义美学)接轨。比如,吕瀓、陈望道、范寿康在编著同名著作《美学概论》时,几乎不约而同地略过曾经对中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康德、叔本华、席勒、歌德、尼采等人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罗素、杜威、利普斯、克罗齐、丹纳等人的思想。尤其是吕瀓,他在其《现代美学思潮》一书中,提出了中国美学的两条发展路向:“第一,趋向综合的研究,而组织全体的美学。第二,美学的和人生的关系密切,而其确定规范的性质。”
显然,自“西学东渐”以来,实用美术与实用美学思潮仍然在主宰着创作与理论两个领域。只不过,20世纪的“实用”并非“皇古之世”的“实用”。它早已不再囿于道德礼教层面或个人的修身养性,甚至也不再局限于生产和生活领域,而是扩展到了社会变革和意识形态的各个层面。实际上,正是实用主义思潮的这种弥漫效应,让艺术家们在艺术的表现形态、形式和途径上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不再囿于传统的艺术形态和艺术门类。比如,中国最早建立的工艺美术教育体系,就是在传承中国传统技艺基础上,借鉴和吸收西方实用美术理念而形成的。
这种实用美学赖以生发的实用美术潮流,是在最早受到西方商业文明影响的上海和广州兴起的,并在美术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继1874年美国传教士创办《小孩月报》画报和1884年英国人爱恩斯特·梅杰(Ernest Major)在上海创办《点石斋画报》之后,中国人也开始在画报的创办方面有所作为。其中,1905年潘达微、高剑父、何剑士、陈垣等人在广州创办的《时事画报》颇为引人注目。尽管此画报几度停刊、迁移和更名,但是在推动社会变革、更新美术艺术观念方面,一直在持续发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时事画报》创办和编辑的邓尔雅、陈树人、高剑父、高奇峰等人,都曾赴日本游学,深受日本实用美术思潮影响,回国后积极仿效和引进日本的方式。比如,通过成立“美术会”、开设“时事画楼”、举办美术展览等方式,传播新兴美术观念,进行新式美术教育,不断探讨以美术振兴工艺、振兴民族工业的途径,突显了“实业救国”“物质救国”的实用主义价值追求。正如陈树人在留日期间摘译英人《美术概论》(The Fine Arts
)时所感言,中国将来要富强,就要有发达的工商业,而“惟商业之发达,非间接于工艺不能,工艺之发达,非间接于美术不可”。所以,他在倡导振兴“美术之风”时,却在大力呼吁有志之士致力于研求商业,讲习工艺,或赴西欧,或赴东瀛,学习域外新的美术理念与技法。显然,就整个艺术领域来说,这种实用美术风潮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当时文化整体转向的一部分。出于社会变革的需要,中国各个艺术领域都在重估传统的艺术观念价值,寻找振兴华夏、改造社会的途径和方式。文艺也从过去注重空灵和精神慰藉的艺术追求,转向参与社会变革的价值追求,以不同方式进行新的艺术探索,来满足新的时代要求。
当然,作为一种最初生发于西方并关切着形而上问题的新理论和新学科,美学此时也不能不受到这种“实用之学”的挑战。“实用之学”的畅行,一方面拉近了美学与中国国情的联系,助长了工具理性思维;另一方面却冲淡了对于人文精神的探求。这是20世纪初中国人文学术所面临的普遍问题。这也体现在具体的美学论述中,理论家们不仅淡化了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延滞了对美学的终极意义与形而上意味的探讨。
对此,傅斯年曾有《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一文痛陈其弊。他说:“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又曰:“凡治学术,必有用以为学之器。”这或许就是王国维美学思想遭到冷遇的原因。王国维致力于纯粹美学的研究,实际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即便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关于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美学建构也依然处于一种沉寂的状态。
宗白华的美学研究就是这种状态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他是在深受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家影响下进入美学领域的。但在至少两年的时间中,他都沉迷于唯心、唯物等世界观、认识论观念中,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美学领域中关于“美”的价值。只是在1919年,他在一篇讨论法国伯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创化论”的文章中,才似乎在无意中触及到了“美术”,也就是美学问题。他说:“盖图画美术是一种直接表示宇宙意想的器具,哲学用文字概念写出宇宙意想,如伯格森、叔本华等书,也可以说是一种美术。近代哲学名著很多文字优美的,如罗怡的《小宇宙》,费希勒的《实现世界中寻非现实世界》,都是有美术兴味的哲学书。”这当然也是“五四”启蒙运动大氛围下其个人意趣的流露。
但在实用主义的推动下,从美术绘画进入美学,再走向艺术理论,这是中国美学生发与理论建构的一条独特途径,只是论述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皆有不同。这种情形在蔡元培、周作人、鲁迅、李叔同等人的文章中也都留下了不同的痕迹。因为他们早期几乎都受到西方美术绘画的影响,只是后来他们文学的审美取向和对审美意识的理论认知各自不同。
还必须看到,文艺理论的输入与美学批评实践之间的交错转换,很快又被实用主义重新推入到新学与旧学、传统与反传统的冲突和对峙之中。因此,自王国维以来,尽管强调非功利的审美认知及其主体论美学已经在“西学东渐”中种下了根芽,但是将一切文艺视为“术”的实用主义思维依然是主流。以实用为美而非以人的理性自觉和情感自觉为美的理论态势,虽然强化了文艺家的现实责任感和社会担当意识,但在客观上也屏蔽了人们对审美主体及文艺自身的美学思考。
当然,中国美学话语建构中的这种延滞,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实用主义文化,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应该归结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速发展。只要看到中国“美术革命”与“文学革命”的这种伴生性,就不难发现,致力于社会变革与改造的“五四”文学革命浪潮,事实上已经迅速波及到了美术领域以及其他艺术领域和层面。一个“术”与“学”、“实践”与“实用”交错发展、相互促发的美学格局,一直延伸并贯穿了整个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