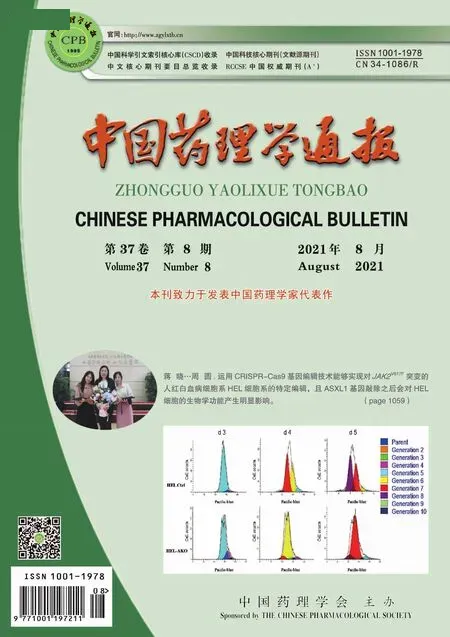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进入细胞抑制剂的研究进展
龙昕雁,罗荣华,郑永唐
(1.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动物模型与人类疾病机理重点实验室,云南 昆明 650223;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是一种与SARS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SARS-CoV)具较高同源性的冠状病毒,其感染导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19, COVID-19 )。SARS-CoV-2是具有囊膜结构且基因组为单股正链RNA的β属冠状病毒。该病毒具有4个结构蛋白及多个非结构蛋白,结构蛋白包括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S)、膜蛋白(membrane protein,M)、囊膜蛋白(envelope protein,E)、核衣壳蛋白(nucleocapsid protein,N),非结构蛋白包括主蛋白酶 main protease,Mpro)、木瓜样蛋白酶(papain-like protease,PLpro)、RNA依赖的RNA聚合酶(RNA-dependent RNA-polymerase,RdRp)等。当前新冠疫情仍然严峻,截止2021年3月底,全球累计确诊的SARS-CoV-2感染者超过1.2亿,累计死亡人数超过270万[1]。
虽然多种新冠疫苗已被批准上市,但抗病毒药物治疗仍是应对新冠疫情的重要手段。当前仅有瑞德西韦(remdesivir)获得FDA批准用于临床治疗,但瑞德西韦在临床试验中并未对COVID-19取得显著治疗效果[2],因此仍需开发出有效的治疗药物。SARS-CoV-2进入细胞是病毒生命周期中研究相对清楚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分子是重要的治疗靶点。进入抑制剂对COVID-19的治疗和预防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结合SARS-CoV-2进入细胞的分子机制,对SARS-CoV-2进入抑制剂的研究进展进行介绍。
1 SARS-CoV-2进入细胞的分子机制
SARS-CoV-2使用其表面的刺突蛋白作为配体,与宿主细胞膜表面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ACE2)、硫酸乙酰肝素(heparan sulfate,HS)、神经纤毛蛋白(neuropilin-1,NRP-1)、B族Ⅰ型清道夫受体(scavenger receptor class B type 1,SR-B1)、CD147、酪氨酸蛋白激酶受体UFO(tyrosine-protein kinase receptor UFO,AXL)等膜蛋白结合,并由弗林蛋白酶(furin)、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 (transmembrane serine protease 2,TMPRSS2)、组织蛋白酶B (Cathepsin B,CatB)、组织蛋白酶L (Cathepsin C,CatL)等蛋白酶对S蛋白进行切割激活,进而发生膜融合,使得SARS-CoV-2能够进入细胞(Fig 1)。

Fig 1 Replication cycle of SARS-CoV-2
1.1 刺突蛋白S蛋白由同源三聚体组成,其单体被分为S1亚基和S2亚基两个部分。S1亚基包含N末端域(N-terminal domain,NTD)、受体结合域( receptor binding domain,RBD)、亚区域1 (subdomain 1,SD1)和亚区域2 (subdomain 2,SD2)。S2亚基包含融合肽(fusion peptide,FP)、七肽重复序列1 (heptad repeat 1,HR1)、七肽重复序列2 (heptad repeat 2,HR2)、跨膜结构域( transmembrane region,TM)和胞质结构域(intracellular domain,IC)。
与SARS-CoV类似,SARS-CoV-2以RBD作为与细胞膜上功能性受体ACE2结合的主要区域[3]。由于SARS-CoV-2与ACE2的接触面积更大,在促进蛋白间原子互作的同时保持了两者结合的稳定性,使得SARS-CoV-2与ACE2的结合亲和力较SARS-CoV更高[3]。通常情况下,S蛋白的RBD隐藏在其内部,当S蛋白发生构象改变使得RBD暴露在S蛋白表面时,S蛋白才能与ACE2结合[4]。
S蛋白结合受体后,S2亚基介导膜融合发生。由于S2亚基位于S蛋白的中部,在膜融合发生前需要宿主细胞内TMPRSS2或CatB/L对S蛋白进行切割释放S2亚基[5]。随后,S2亚基的HR1和HR2通过互相识别并形成六螺旋束,促使病毒囊膜与细胞膜或内体膜紧密结合继而发生膜融合。
1.2 细胞膜表面受体ACE2作为SARS-CoV-2的功能性受体通常保持二聚体形态,其与S蛋白的结合是一动态过程。ACE2偏好与开放构象的S蛋白结合,同时ACE2与S蛋白的结合能促进S蛋白形成更为开放的构象[6]。除ACE2外,另外一些分子也可能参与了SARS-CoV-2进入细胞的过程。
有研究证明HS能与SARS-CoV-2 S蛋白的RBD结合并由此促进S蛋白与ACE2的结合,进而增加吸附于细胞表面的病毒数量,促进病毒进入细胞[7]。NRP-1能与S蛋白的S1亚基结合并增强病毒进入细胞及感染细胞的能力,但仅当ACE2存在时NRP-1才可促进病毒进入细胞[8]。SR-B1是在多种细胞上表达的高密度脂蛋白(high-density lipoprotein,HDL)受体,SARS-CoV-2 S蛋白能通过NTD与HDL结合,随后借助HDL间接与SR-B1发生互作。但与NRP-1类似,SR-B1促进SARS-CoV-2吸附并进入细胞需要ACE2的帮助[9]。此外,AXL能与SARS-CoV-2的NTD结合而有效促进病毒进入细胞,这一受体在病毒进入人肺上皮细胞时至关重要[10]。除上述分子外,Wang等[11]研究表明CD147是能与SARS-CoV-2 RBD区域结合的细胞表面蛋白,通过介导内吞作用促进病毒进入细胞,可作为ACE2的替代受体有效促进病毒感染 。
综上,ACE2是SARS-CoV-2的功能性受体,HS、SR-B1、NRP-1等作为潜在辅助受体,其中HS促进病毒吸附,NRP-1促进病毒进入细胞,SR-B1则起到双重作用。此外,CD147、AXL则是除ACE2外病毒进入细胞的膜表面蛋白。除上述受体外,SARS-CoV-2还能与细胞膜表面的许多分子进行结合,其受体偏好性仍待进一步探究。
1.3 辅助蛋白在SARS-CoV-2进入细胞的过程中,宿主细胞蛋白酶对病毒的进入起到重要作用。TMPRSS2通过切割S蛋白FP区域前S2’位点而促进病毒囊膜与细胞膜的融合,TMPRSS家族的成员同时表达能促进SARS-CoV-2的感染[5]。存在于次级内体或溶酶体膜上的CatB和CatL在病毒进入细胞时能对S蛋白进行切割激活,使病毒颗粒释放到细胞质中,其中CatL对SARS-CoV-2的进入起主要的作用[5]。弗林蛋白酶在细胞内分布范围广,它通过切割S蛋白的S1/S2位点,使S蛋白呈现开放构象达到预激活S蛋白目的,促进病毒与细胞结合并使得感染细胞形成合胞体[12]。除弗林蛋白酶外,胰蛋白酶也能够有效切割S1/S2位点,但无胰蛋白酶存在时病毒仍能进行膜融合步骤,因此,胰蛋白酶在病毒感染细胞中的作用有待明确。
2 靶向刺突蛋白(S)的抑制剂
2.1 蛋白多肽抑制剂当前,靶向S蛋白的多肽抑制剂(Tab 1)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以RBD为靶点阻断病毒与受体的结合,一类以HR1为靶点阻断病毒的膜融合。

Tab 1 Peptidic inhibitors of spike protein
以RBD为靶点的多肽抑制剂包括两类,一类基于ACE2设计,另一类则从头合成。人源化可溶性ACE2 (human recombinant soluble ACE2,hrsACE2)通过重组表达ACE2蛋白获得,最初主要用于降低血管紧张素2水平并减少急性肺损伤。将hrsACE2用于治疗COVID-19时,hrsACE2有效降低了血浆中病毒载量及炎症因子的水平,同时对肺等脏器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患者并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具有良好的临床治疗潜力[13]。由于ACE2肽酶区域的α螺旋是RBD结合的重要区域,根据这一序列合成的多肽能与RBD结合从而抑制病毒吸附与细胞表面。基于这一原理,Zhang等[14]合成了与RBD具微摩尔亲和力的多肽SBP1 。随后,Cao等[15]以同一原理设计得到多肽AHB1和AHB2,对SARS-CoV-2表现出较好亲和力,但Cao等[15]采用从头合成的方法得到的多肽LCB1和LCB3能以更高的亲和力结合病毒并抑制病毒进入细胞。因此与基于ACE2序列开发的多肽相比较而言,从头合成的多肽抗病毒活性更佳,表明从头合成的抑制多肽更具治疗潜力。除从头合成外,Zhao等[16]将抗病毒多肽P9R进行交联获得的多肽8P9R与病毒的结合能力更强,其抗病毒活性更高。因此,将单个多肽交联形成多聚体是多肽抑制剂改进的有效方式。
阻断病毒膜融合发生的进入抑制多肽是对HR2的氨基酸序列进行修饰后得到的。由于冠状病毒的S2亚基高度保守,因此基于HCoV-OC43 HR2开发的多肽抑制剂EK1能有效抑制SARS-CoV-2的感染[17]。随后基于EK1修饰得到的HR2P[17]、EK1C4[18]则对病毒感染表现出更强的抑制作用,表明氨基酸修饰和脂类修饰是改善多肽进入抑制剂抗病毒效果的有效方式。胆固醇修饰后的多肽IPB02具有比未修饰多肽IBP01更好的抗病毒效果,这可能是由于SARS-CoV-2的S蛋白除NTD外,其RBD区域或许也能与脂类结合,因此脂类修饰能够提高肽段的抗病毒活性[19]。但这些肽类药物的安全性如何仍需进一步的验证。
2.2 小分子抑制剂用作抗凝剂的肝素( heparin ) (IC50=5.99 μmol·L-1)以及用于预防和治疗静脉血栓及肺栓塞的依诺肝素( enoxaparin ) (IC50=1.08 mmol·L-1),能够模仿SARS-CoV-2进入细胞所需蛋白HS而与S蛋白RBD区域竞争性结合,抑制病毒与细胞膜表面受体结合。同时这两种小分子化合物能与S2水解切割位点进行互作,进一步抑制S蛋白的膜融合步骤[7]。已证明使用肝素对COVID-19患者进行治疗能有效降低患者的死亡率,减少感染引起的血栓形成,但尚未有证据显示肝素能直接对病毒起效而降低患者的死亡率[20]。此外,肝素及依诺肝素在治疗过程中会提高患者出现大出血症状的概率,需要谨慎使用[20]。
3 靶向细胞受体的抑制剂
3.1 靶向ACE2的抑制剂作为SARS-CoV-2主要受体,靶向ACE2进行SARS-CoV-2感染的治疗是一个有效途径。但ACE2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体组织器官免受炎症损伤。因此,靶向ACE2进行COVID-19治疗仍需慎重考虑。
氯碘羟喹(clioquinol)被用于研究及治疗前列腺癌和神经退行性疾病,氯碘羟喹(EC50=12.62 μmol·L-1)及其类似物CLBQ14(EC50=14.69 μmol·L-1)、CLCQ(EC50=16.30 μmol·L-1),能与S蛋白竞争性结合ACE2从而有效抑制SARS-CoV-2对细胞的感染[21],但这一化合物在体内抗病毒效果如何尚待进一步研究。达巴万星(dabavancin)是一种糖肽类抗生素,已被美国FD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革兰氏阳性菌导致的皮肤感染性疾病。我们的研究表明,达巴万星能直接与ACE2结合从而抑制病毒S蛋白与ACE2的互作。这一抗生素药物在细胞水平(EC50=12 nmol·L-1)及两种动物模型中均具有良好的抑制病毒效果,且对肺等脏器发挥了保护作用,具有进入临床试验的良好潜力[22]。
3.2 其他除ACE2外,HS、NRP1、SR-B1、CD147和AXL是近期发现的SARS-CoV-2进入细胞相关膜蛋白,由于这些蛋白与SARS-CoV-2的相互作用刚发现,尚未针对这些靶标进行专一性抗病毒药物的研究。但已有研究显示,以这些蛋白作为靶点可得到有效的病毒抑制剂。例如,抗肿瘤药物米托蒽醌(mitoxantrone)能与HS结合并抑制HS依赖的内吞作用,从而阻断病毒进入细胞[7]。但米托蒽醌使用后会引起消化系统不适、降低血小板和白细胞数量,且具有一定心脏毒性,在用于COVID-19临床治疗前需谨慎评估。
4 靶向SARS-CoV-2辅助蛋白的抑制剂
4.1 靶向TMPRSS2的抑制剂当前,靶向TMPRSS2治疗COVID-19的小分子化合物包括卡莫司他(camostat mesylate)和萘莫司他(nafamostat mesylate)。卡莫司他在日本被用于治疗慢性胰腺炎及反流性食管炎,是跨膜丝氨酸蛋白酶的广谱抑制剂,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地抑制SARS-CoV-2的进入[5]。萘莫司他在日本被用于治疗急性胰腺炎和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与卡莫司他类似,萘莫司他也通过结合TMPRSS2而抑制SARS-CoV-2进入细胞。同等浓度下,萘莫司他的体外抗病毒效果比卡莫司他好[23]。将这两种药物用于治疗COVID-19患者,会导致脑出血、过敏反应、心脏骤停等[24],因此将这两种药物用于COVID-19的治疗尚需评估。
由于SARS-CoV-2可通过两种不同途径进入细胞,因此,仅当病毒是通过与细胞膜发生膜融合进入细胞时,TMPRSS2抑制剂才能对病毒发挥有效的抑制作用。在以内吞为病毒进入途径的Vero E6细胞中,TMPRSS2抑制剂无法抑制病毒感染细胞,但在以细胞膜膜融合为病毒进入途径的Calu-3、Caco2细胞中,TMPRSS2抑制剂对病毒具良好抑制效果[5]。因此,TMPRSS2抑制剂是否可作为有效的临床药物进行广泛应用,尚待进一步验证。
4.2 靶向CatB/L的抑制剂由于组织蛋白酶主要存在于内体、溶酶体等细胞器中,因此组织蛋白酶抑制剂对病毒的抑制效果仅在病毒以内吞为主要进入途径的细胞系中起效。阿洛司他丁(aloxistatin, E-64d)是一种已知的CatB/L抑制剂,在Vero E6细胞、HEK 293 / hACE2细胞中被证实能够有效抑制SARS-CoV-2的进入[5]。但这一化合物尚未进入临床试验,要将其应用到COVID-19的治疗中存在一定的困难。替考拉宁(teicoplanin) (EC50=1.66 μmol·L-1)主要被用于治疗葡萄球菌感染,人体对该药物的耐受性良好,使用后仅少数人群会出现过敏等不良反应。替考拉宁能通过抑制CatL对内体中病毒S蛋白的酶切激活而抑制病毒的膜融合过程,阻止SARS-CoV-2感染细胞[25],但当前尚未将替考拉宁应用至COVID-19的临床治疗中。
CatB/L的酶活性受到内体的PH值的影响,因此对内体pH值有影响的化合物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病毒感染起到抑制作用。阿比朵尔(arbidol)是一种抗流感病毒的药物,已在体外证明其能有效阻止SARS-CoV-2进入细胞并抑制病毒在细胞内的转运(EC50=4.11 μmol·L-1)[16]。先前猜测阿比朵尔可能通过与SARS-CoV-2的S蛋白进行结合而发挥活性,但最近的研究显示,阿比朵尔主要通过改变内体pH,调节CatB/L的酶活性而起效[16]。阿比朵尔在用于治疗COVID-19是能显著降低病毒载量,个别患者出现白细胞数量激增,但经治疗后可恢复,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26]。但阿比朵尔并未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评估,其疗效尚待进一步确定。氯喹和羟氯喹作为抗疟疾药物被广泛使用,在新冠疫情爆发早期就已证实能有效抑制SARS-CoV-2感染细胞。早期猜测氯喹(chloroquine)和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能通过抑制ACE2糖基化或结合ACE2而起到抗病毒效果,但近期研究证实氯喹和羟氯喹主要通过抑制内体酸化而抑制CatB/L的酶活性,进而抑制病毒进入细胞[16]。世界卫生组织对氯喹及羟氯喹疗效的临床试验证明氯喹和羟氯喹并未能对COVID-19起到显著的治疗效果[2],表明这一类抑制剂的抗病毒活性受到病毒进入细胞方式的影响,在尚不清楚SARS-CoV-2感染人体细胞的具体进入方式前,单独使用这一类抑制剂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4.3 靶向furin的抑制剂目前针对furin进行的抗病毒药物研究较少,但已证实弗林蛋白酶抑制剂CKM(decanoyl-RVKR-chloromethylketone,CMK ) (EC50=0.057 μmol·L-1)能够有效抑制furin对S蛋白的酶切激活从而抑制病毒进入,具有作为预防药物的潜力[12]。此外,CKM能够降低CPE,抑制具感染力的子代病毒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12]。但弗林蛋白酶抑制剂D6R(hexa-D-arginine amide,D6R)及SSM3 (SSM 3 trifluoroacetate,SSM3)未能阻止S蛋白的酶切激活而对病毒无抑制效果,因此弗林蛋白酶在病毒进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尚待进一步明确,以furin为靶点的SARS-CoV-2进入抑制剂仍需进一步研究。
5 结语与展望
进入细胞对病毒而言是极为重要一步,S蛋白作为病毒进入细胞的重要元件,是极易突变的结构蛋白。D614G突变株、A501Y突变株等均具有较原始病毒株更强的传播能力与感染能力,现有疫苗对突变毒株的预防能力尚待评估,因此仍需加大对COVID-19药物的研发力度。进入抑制剂作为能起到治疗和预防双重作用的药物,具有很高的开发价值。当前投入COVID-19临床治疗及试验中的多为已上市药物或经过临床试验验证的药物。虽然老药新用是治疗COVID-19的一个主要方式,但对天然化合物进行筛选评估仍是开发进入抑制剂的有效方式。
当前SARS-CoV-2进入抑制剂的开发还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处于临床试验评估的进入抑制剂中,hrsACE2价格较高,卡莫司他、萘莫司他及阿比朵尔的临床相关实验尚未得到最终结果且均会导致不良反应的出现,尚无法有效用于COVID-19的治疗。其次,随着研究的深入,SARS-CoV-2的其他受体也被进一步发现,许多蛋白酶在病毒感染过程中的作用也被进一步明确。同时由于病毒感染是多分子互作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复杂性使得针对单个靶点开发的抑制剂在临床治疗中不一定具有可靠疗效,无法进一步推广。
因此,仍需加大对药物开发的力度,并在开发过程中对药物进行多层次评估,从而为COVID-19的治疗提供依据。同时,在治疗中应将不同靶点的药物进行联用,以达到预期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