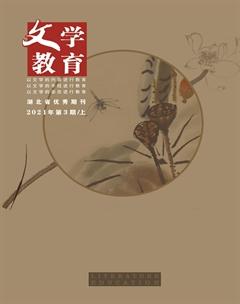论中岛敦《山月记》的叙事魅力
赵彩云
内容摘要:日本作家中岛敦的《山月记》取材于中国唐传奇《人虎传》,其借用中国古典素材,在不同视角交替转换的叙述中,从人物的荒诞离奇的命运中传达出深刻而独具意蕴的现世思考,反思现代社会中自我与命运,个体与社会,现实与未来等问题,以此反观物欲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
关键词:《山月记》 叙述艺术 人文关怀
美国文学批评家梅·斯温逊认为,文学作品经验的发现是基于下列热望:想穿过屏幕看透事物所表现的内涵,想触及真实存在的事物,并且想深入到正在演变的事物之更广大空间。日本作家中岛敦的“经验”即具有这样的品格,他擅长借用客观素材进行文学创作,尤其喜欢借用中国古典素材。《山月记》取材于唐传奇《人虎传》中的人物,情节上也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中岛敦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传达出对现世的思考,荒诞命运下对人“异化”的反思,探讨自我与命运,反观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存在与人性的变化。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文学创作都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关系中,社会空间赋予了作家创作的灵感。作家的自觉性,即在于将文学与生活相联系,在文学表述中反映“人学思想”,予以对现世的深刻洞察与关怀。中岛敦以其自我素养和社会空间经历与情感体验,借中国古典素材,审视与体察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及精神体验问题。
一.不同视角的交替转换
法国学者热奈特借用“摄影术语”一词来指叙述者讲述故事的角度,它在小说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读者观察故事世界赖以凭借的眼光,也通常被文学评论家称为叙事视角或视点。[i]《山月记》采用的是俯视角的第三人称叙述,整体上叙述者纵观故事的发展,这样的叙述便于作者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统观、审视和把握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活动。“西方经典叙事学认为,第三人称可以同时具有外视角和内视角。外视角指故事外叙述者用自己的旁观眼光叙事,内视角指用故事内人物的眼光来叙事。故事内人物的眼光往往较为主观,带有偏见和情感色彩,而故事外的敘述者的眼光往往较为冷静。叙述者仅仅是叙述话语中的一个代码,而这个代码不是一成不变的。小说家为了使作品有限的文字展现出更大的信息量,往往会变换视角,从不同视角中引申出意味深长的主题。”[ii]《山月记》虽然总体上是第三人称叙述,但其中也从人物视角出发去观察、叙述与描写。
1.全聚焦叙述视角
全聚焦叙述视角也被称作“全知全能型的第三人称视角”,是一种传统的无所不知的视角类型,叙述者的观察位置处于故事之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不但知道人物的过去经历,还知道人物现在正在发生的经历体验与未来状况,且能洞察并熟知人物的想法与内心感受,可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iii](P201—202)西方经典叙事学认为,第三人称叙述同时可以具有外视角和内视角。外视角是指故事外的叙述者用自己旁观眼光来叙述,内视角是指叙述者采用故事内人物眼光来叙述。故事内人物眼光往往较为主观,带有偏见和感情色彩,而故事外人物眼光往往较为冷静、客观、可靠。[iv](P217)《山月记》中“陇西县人李徵聪颖博学,天宝末年间,以弱冠之龄连登进士,补江南尉,旋即上任。只是其性狷介,自恃才厚,遇事则率性为之,不甘居于区区贱吏。遂竟辞官而去,归来故乡虢略,息交绝游,耽心诗作......李徵终日怏怏不乐,难抑心中狂悖性格。比至一年之后,公事出旅,驿宿汝水之时,终于发狂作状。夜半时分,面色忽变,一跃而起于床,叫嚷言语,不知何意,疾入夜色之中,一去不返。或搜于山林,亦无所获。此后事况如何,究竟无人知晓。”开篇部分,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介绍了人物、时间、地点等,叙述者俯瞰主人公李徵变虎前的人生经历,还进入其内心,洞察人物的心理想法,以此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李徵聪颖博学、连登进士,本可靠其才华步步高升,但因其性格孤傲、遇事率性,不会为人处事,不懂处世之道,因而弃官归乡,喜好诗作。但单纯靠作诗养活不了一家人,李徵再次屈任地方官,与昔日同僚的对比下,自尊心受挫,倍感屈辱与愤慨。一年之后,在公事出旅的夜晚发狂进入山林。“其性狷介”“自恃才厚”“率性”“不甘”“怏怏不乐”“狂悖性格”等,叙述者仿佛上帝一样透视主人公李徵,以旁观者的姿态通过主人公的经历赋予主人公性格特征,并可以感知主人公的心理与情绪体验。叙述者以在场的方式叙述主人公变虎前的细节与动作等“夜半时分,面色忽变,一跃而起于床,叫嚷言语,不知何意,疾入夜色之中,一去不返”,叙述者似上帝一样目击了李徵的一系列变化,好像叙述者就在李徵身边,没有错过任何一丝一缕的细节。全聚焦叙述视角下,透视了人物的情感体验与心理境况,向读者展示了饱满的情节内容,故事的发展也更加完整,让读者跟随叙述者的节奏走,循循渐进地被故事所感染。莱辛说:“一切与性格无关的东西,作家都可以置之不顾。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性格是神圣的,加强性格,鲜明地表现性格,是作家在表现人物特征的过程中最当着力用笔之处。”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下,叙述者纵观整个故事的发展,审视人物活动,在因果必然的人物经历中,展示并塑造出了丰满圆润的人物形象和极具特色的人物性格,也使得人物更具立体感与层次感。
2.内聚焦——叙述者的第一人称视角
内聚焦即叙述者好像寄居于某个人物中,用故事内人物的眼光来叙事,借着他的意识与感官在视、听、感、想。[2](P223)《山月记》中,主人公的第一人称自白,“今前一年,余因公事出旅,驿宿汝水。夜中觉醒,忽闻门外似有谁人唤我......而我人间之心目之为无上恐惧,呜呼,恐惧悲哀,切思我为人时记忆亡毁!此种心情无人可知,无人可知。除非有经历同我者。然而,再言,于全然非人之前,我更有一事相托。” “先刻所言,不知何故,离此命运。然而转念,亦非全无思绪。当余之为人也,逃避交游。而人以我倨傲尊大。其实无人知晓,乃是近乎羞耻。当然,我曾为乡里奇才,固有自尊之心。只是斯是懦弱之自尊心而已。余虽欲以诗成名,而不肯进师求友,相与切磋琢磨。其外又以与俗物伍而不洁。是懦弱之自尊心与尊大之羞耻心所为也。患己不为明珠而不敢琢磨,又将信己是明珠,故不与碌碌砖瓦为伍,已而离人远世,饲其懦弱,育我自尊以愤懑羞怒......纵使悲叹,呼天抢地,亦无知音,正如我为人时,脆弱易伤之内心无人能解。己身毛皮濡湿,并非夜露之故。”主人公李徵的第一人称自我独白中,叙述者似乎隐藏起来,控制了叙述者的活动范围和权限,把读者带入主人公的真实世界,跟随主人公的自白深入体会其所想所感所情,从而使得作品的真实感加强,感染力加强。在主人公的自白中,叙述者知道的跟主人公一样多,进入主人公的独白话语世界,了解其变虎后的经历,“然而又见一兔驰过眼前。余之为人姿态一瞬消失,及其复觉,只有口中兔血与地上兔毛而已。是余为虎最初之状”等。内聚焦视角中,通过人物的自我独白和内心活动,对于揭示人物思想和深化主题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主人公的自白会潜移默化的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很快地将读者代入情节中,并通过自白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人物的性格特征。李徵的荒诞化悲剧命运,是其社会环境造成的,更是其自身原因的结果。正如他自白中所说,羞耻心与自卑感使其逃避入世、不与人交游;孤僻自傲,喜好作诗却又不肯进诗求友;强烈的自尊心与懦弱愤慨的性情使他远离人世,无法适应并融入世俗生活。最后通过主人公自我独白的亲身经历,引出:“人生不为一事太短,为一事则太长”的人生警句,以此来深化小说的主题意蕴,也更能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从人物的亲身经历与切身体验中与人物产生共鸣。
其次,主人公的自白中叙述了他之前所做的百篇诗作及诗业未竟的感慨。而透过友人袁傪的心理描写“长短诗作凡三十篇,格调高雅,意趣卓逸,令人初读便想见作者才华。只是袁傪于感叹之余又觉他意。作者诗性无疑当属一流。然而如若只见如此,则仍有阙于一流诗作。此所阙者极其微妙。”可见李徵的才情突出,作诗一流。叙述者的第一人称视角,在加强作品真实感的同时,也在小说中造成了一些空白与疑问,给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弱冠之龄就能连登进士的人,其才华必是出众的。况且李徵生活在“以诗为重”的盛唐时期,所做诗篇数百,如此之一流才华,又为何被埋没于世,无人问津呢?除了李徵自白中的个人性格原因之外,繁华盛唐时期是否平等对待满腹经纶的贤士呢?李徵在官场在仕途中到底经历了多少次不为人知的屈辱与打击,体味了多少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抑或是还有来自家人的不理解......只言片语,满腔愤慨,痛苦悲泣背后该是经历了多少他人无法承受之重击才使一个活人异化成山林中的虎。内聚焦视角下,主人公第一人称自白中,人物情感彻底爆发,随着向友人讲述变虎的前因后果,逐步使读者感知人物命运的变化,进入主人公的自我独白世界,产生情绪情感的感染化体验,以此达到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在双方的共鸣中,升华了小说的主题意义,加深了读者对文本内涵的理解。
二.独立存在的叙述者
第三人称小说《山月记》中,叙述者是独立存在的。小说中虽采用了主人公独白的内聚焦视角,但叙述者并未完全隐身,而在不同人物视角之间切换,甚至在李徵遇友人袁傪之后,向其讲述变虎的经历中,叙述者如上帝一样,感知人物的情感变化。“俄頃草丛中作人声,嘟囔自语‘险哉此刻。闻斯人声,袁傪只觉似曾相识。忽有电光闪念起于惊惧,袁傪大呼:‘斯人语者,莫非吾友李徵乎?袁傪与其原系同年,李徵友人甚少,袁傪当为至亲密友。盖袁傪温和,李徵峻峭,性情之下不易相冲。”袁傪惊遇草丛中的猛虎,听见人声,猜到是故友李徵,“俄而人声低答:‘信矣,我乃陇西李徵。”李徵随即也肯定了袁傪的猜测。然而后文中的“独与无形之声对谈”“丛中人声历历道来”“听闻丛中人声语此不可思议之事。人声续有接言”“随丛中人声而作诗录”等,明知是友人李徵,却用“......的声音”来叙述。可见,叙述者是独立于主人公存在的,区分了主人公的第一人称视角,叙述者并未彻底隐藏,而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文本中隐性化的存在。
其次,叙事者穿插在全视角与不同人物视角中,在时间与空间上体现了其独立存在。“袁傪事后回忆,亦觉不可思议,而当时却确以素直实态,容受超自然之现象,无所怪异。”穿插在主人公第一人称视角自白中的这句话,即是叙述者全视角的体现,叙述者不仅知道现在,还知道未来。在时间与空间上,叙述者都清楚地把控情节发展,了解人物所想。“袁傪一行屏息静气,听闻丛中人声语此不可思议之事。”“是时,残月光冷,白露地寒,凉风吹度树间,拂晓将告临近。众人已然忘却事况离奇,肃然慨叹诗人不幸。李徵之声续有接言。”“众人行至丘上,依言顾首,果见猛虎跃出。月色无光,而猛虎仰月,咆哮数声,复又跃入草丛,莫能再见。”全视角叙述中,叙述者是超越时空独立存在的。环境描写体现了叙述者对空间的统观,众人的神态、心理、动作等描写,体现了叙述者对人物活动的审视与观察。叙述者在全视角与不同人物视角中交替转换,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使小说中的故事产生了一种立体感与层次感,不但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而且丰富了小说的内涵,使小说情节更加自然、清晰、完整且合乎逻辑。
三.独特而深刻的人文关怀
《山月记》叙述了一个独特怪诞、叫人乍舌、神秘而通俗的故事。这样的通俗故事背后映射出了对“人”、对“命运”、对“人性”、对“社会”、对“现实”等的思考。小说通过全叙述与人物的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丰富了主人公李徵的性格特征,使其人物形象更加饱满。最骄傲的人,往往输得最惨,李徵因为过于骄傲,不愿放低自己的内心苟且地活着,最终被心中的猛虎吞灭。世界本是由很多的残缺和不完美所构成,当一个人过度孤傲而远离尘世,无法正确看待并接纳世俗中的残缺,从而容易受“他者”的挤压与影响,无法正视真实的自我,必会导致悲剧性的命运。这不由让人深思,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在经济与科技迅速发展,加快全球化、一体化的现今,个体的存在面对来自不同层面的越来越多的压力。在外界物欲时代浪潮的冲击下,现代人惨遭被异化的命运,被物质、科技、网络等所异化,甚至被大的社会环境所同化,丢失了原始的本真面貌,从而失去了自我真正的存在意义。
小说毕竟是叙述出来的客体世界。只有从叙述入手才能最后抵达文本内在的构成。[v]《山月记》通过不同视角的交替转换,往往会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超越作品主人公的俯视角。阅读这样的作品,会让读者形成自身审美价值的心理机制。在文学批评中,作家通过审美距离掌控读者对作品的情绪体验及对作品中人物喜怒哀乐的心理层面的感知距离。《山月记》中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个体性格中的优与劣,面对内在与外在的压力,社会观、人生观与处世观等,这些在任何时代,只要有社会的存在,对于个体而言,必会有或多或少相似的地方,抑或是产生共鸣之处。必须承认,今天的读者在作者带有时代痕迹的小说叙述中,依然会有共性的审美价值点存在。纵观全文,中岛敦的《山月记》以其富有张力性的叙述方式,在艺术魅力中纳入对现世的关怀与思考,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投去深深一瞥,其文本的反思性、深刻性、现代性等具有深厚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参考文献
[i]张琳.《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多元叙事聚焦[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06):170-172.
[ii]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ii]热奈特.叙事话语[M].王文融,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iv]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v]刘俐俐著.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0.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