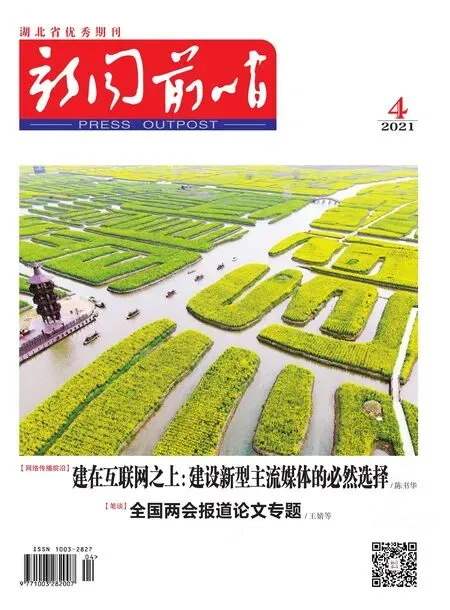汉学研究与跨文化传播探析
——以汉学家顾彬“误解”观念为例
◎司 可
在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语境中,单波称以顾彬为代表的汉学家为“基于中国文化的介入者”,认为顾彬的汉学研究与其他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将与中国的跨文化体验融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同时也利用自己的文化实践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这正是顾彬中国文化“在场”身份的体现。作为一位德裔的汉学家,他有着丰富的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经验,也有系统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支撑,对“误解”的阐释,便是其最核心的理论之一。
一、“误解”与“他者”
顾彬在《误解的重要性:重新思考中西相遇》一文中,首先论述了“误解”的必然性问题:
第一,顾彬说中国学者可以自由地概括自己文化的特点,而外国学者却不可以。他认为中国学者面对“他者”文化群体的评价,很难把他们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站在“他者”立场上来换位思考。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对待“他者”文化群体的评价可能存在着跨文化的误解,或者面对“他者”文化群体的评价缺乏客观的接受态度。
第二,顾彬认为中国学者理解和描绘的欧洲是片面的。中国学者往往缺乏留学的经历,对“他者”文化并不是真正的深入了解;同时他认为了解一门语言就能开启一个新的世界,而中国大部分学者既不能说也不能写任何一门外语,这使中国学者的眼界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能设身处地地站在“他者”文化的立场上来理解一种文化,就很可能制造出一种只存在于自己观念世界里的“他者”文化,一种造成了误解的“他者”文化。
第三,顾彬还指出不管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中看到了什么也喜欢在另外一种文化中找到什么,或者在其他国家的文化中看到了什么,也希望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中找到什么。比如看到西方的现代解释学,中国学者就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也寻找解释学的影子,这样做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若是生拉硬拽,生搬硬套就没有意义了。
面对“他者”文化,尽量地消除不必要的误解,顾彬站在西方学者的立场上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概括地说,要消除偏见,加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具体表现为:其一,要考虑到历史的一切方面,全面地看待“他者”文化。这与他的汉学研究坚持历史性的学术立场是分不开的。其二,从对待“他者”的态度来说,要客观公正地评价其他文化。顾彬认为,对“他者”文化的评价有可能是评价者对自己文化的遮遮掩掩的评判。其三,对“误解”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认识,顾彬认为,对“他者”的完全理解是不可能的;“误解”是不可避免的,“误解”也是有着广泛的正面意义的。

二、“误解”的“理解”和“解释”
“文化依靠彼此的接触,没有什么文化是自治的。因此,文化由对话和翻译组成。”这是顾彬文化观的重要组成,在他看来,对话和翻译是文化间接触的“形象化说法”,而这其中“误解”是在所难免的。从译者的角度来看,造成误解的原因有三:其一是不同的时间或者不同的时代造成的理解不同;其二是不同的翻译注重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其三是翻译者主观理解的加入;从读者角度出发来说,原因也有三:其一同样在于时间的变化,顾彬认为阅读做出的某些判断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随着多次的理解和考虑,原本对文章的理解可能会慢慢变成误解;其二,读者阅读不同的译本可以发现不同文本的丰富性;其三,由读者理解的不充分造成的“误解”。
面对“误解”,顾彬开始从解释学的角度进行阐释。他在《误解的重要性:重新思考中西相遇》里提出跨文化问题中有三种解释学模式:“等同的解释模式”、“完全不同模式”和“类比性质的解释学模式”。他认为,最能解决当今时代跨文化理解问题的是这种“类比性质的解释学模式”,它具有以下三点特征:其一,不存在固定的和最终的知识,没有人能够实现对自身文化或其他任何一种文化的最终理解。“理解”和“解释”永远只是一个过程,而非最终的结果;其二,我们必须容忍别人的意见,如同对自己的宽容那样;其三,“理解”需要一定量的“误解”才能产生,“误解”也来源于大量的“理解”,在这个角度看“理解”即“误解”的观点是完全成立的。同时,“误解”的产生,是“理解”和“解释”的结果,换言之,“理解”、“解释”和“误解”之间存在着“理解”通过“解释”产生“误解”,而“误解”可以反过来能动地充实着“理解”这样一种逻辑。首先,顾彬认为,“理解”和“解释”之间,“解释”是诠释“理解”的过程,由于“理解”不同,“解释”也会不同。所以,就像刘小枫所说“没有最终的陈述,只有瞬时的理解”。其次,顾彬认为作者的意图是永远没有办法搞清楚的,因为任何“理解”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生存的时代,既然“我在”总是有着时间或空间的限制,那么对文本的“理解”也是同样受限的。所有“理解”都是瞬时的,所以“理解”也就是“误解”。但“理解”和“误解”之间却是相互成就的,因为有“理解”才有“误解”,“理解”需要存在一定的量才能产生“误解”。最后,“解释”和“误解”之间,“解释”只是“误解”形成的一个过程或途径,“解释”也是“误解”产生的直接结果。因此,“理解”、“解释”、“误解”三者之间构成了如下的一种循环关系。
三、“误解”观念的哲学基础
刘小枫在《“误解”因“瞬时的理解”而称义》一文章中提出顾彬这种“理解即误解”的看法与伽达默尔解释学所谓的“正当偏见”十分类似。顾彬对待“误解”的态度,就如同伽达默尔对于“偏见”的肯定,顾彬所寻求的“误解”的正面意义,只有在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本体论解释学中才能展现出来,而顾彬对“误解”与“理解”和“解释”之间关系的阐释,可以明显地看出伽达默尔解释学中“前理解”、“效果历史”和“视域融合”等概念的影子。
“前理解”在伽达默尔的理解三原则中居于首位,又称为“偏见”,指的是人们在理解某事物之前已经预设的想法。在这一概念上伽达默尔则是承自海德格尔提出的“理解”的三个先决条件:“前有”,“前见”和“前概念”。它们代表的都是一些在语言和知识方面的预设。这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他的理解相应地会受到预设条件的约束。正如我们不能离开知识去理解,抛开语言去解读一样。因此,这些“前理解”或“偏见”,正是顾彬所谓“误解”产生的原因之一。
关于“视域融合”,伽达默尔强调的是理解者与理解对象发生“视域融合”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是译者与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对话”,译者是原文本的理解者,读者是译本的理解者,也同时是译者和原文本的理解者。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视域”是因为原作者、译者和读者都会有不同的“前理解”,使这些不同的“视域”相互“融合”,才能形成最佳的理解状态。那么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的“对话”这一概念一定是不同于施莱尔马赫所谓通过避免“误解”以达到对一般文本的正确理解。之所以要进行“对话”是因为“视域”的不同和不断变化,“视域融合”的过程也是离不开理解和“对话”的。而一旦肯定了“视域融合”和“对话”过程的存在,就不可否认译者和读者对于原文本拥有“误解”的权利,从而佐证了顾彬“理解即误解”的观点。
“效果历史”认为读者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会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顾彬在对“误解”产生过程的解读中,一再提出时间的变化是“误解”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在”受到时间的限制,那么对文本的阐述也是同样受限的,在此过程中所谓的“误解”,不过是一些过时的观点,所以“误解”并不可怕,也不必消除。
顾彬的“误解”观念确实一定程度上借鉴于伽达默尔解释学,但却不止于此。顾彬基于跨文化传播实践认识到的这种“误解”,比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解释学有更深一层的意味,那就是这种“误解”是超越个体文化的,“误解”产生的原因更多的是来源于“自我”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空间距离产生的“误解”。正如思竹所说:“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解释学没有真正认真关注和审视过跨文化的理解和解释及其对于人之存在的意味。”那么能够解释顾彬的“误解”观的,只有跨文化的解释学,西蒙·潘尼卡称它为“历地的解释学”,这是继“形态解释学”和“历时解释学”之后第三个阶段的解释学,在这一阶段,解释学要解决的不只是时间上的距离,还要解决空间上的距离。所以有学者认为,“西方传统的阐释学无法为跨文化阐释学提供理论支持,因为跨文化阐释学只有在不同于西方阐释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因此,也只有在跨文化解释学的领域才可以为顾彬“误解”观念提供一个空间维度上的理论支撑。
顾彬对“误解”的跨文化阐释学解释,是他在对中国文学进行丰富的跨文化实践中总结升华出来的观念,也是将跨文化解释学与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体现,对中国文化进行更具包容性的跨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