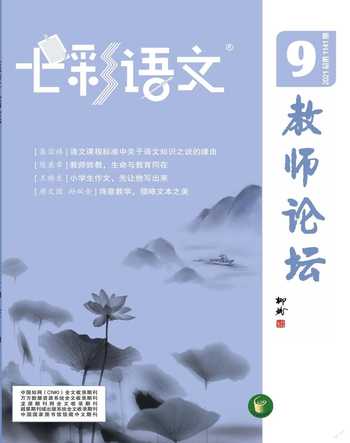谢公才业自超群
颜家明
《咏雪》出自《世说新语·言语》,寥寥数语,让人感受到了古代儿童的聪慧机智和良好的家庭教养。这个故事的主角之一就是“旧時王谢堂前燕”一诗中的谢安,其主要功绩是指挥了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败了强大的后秦,巩固了东晋的政权;“王谢”中的“王”,指的是东晋的开国元勋王导。王、谢两大家族均居住在京城建康的乌衣巷,是当时最显赫的士族。
什么叫士族?士族又称衣冠、世家、门阀等,是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门阀制度曾经是唐以前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士族所垄断,出身背景对个人仕途的影响,远大于自身的才能与专长。直到唐代,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门阀制度在用人选人上的局限性,决定着它被科举制度所取代,是一种必然。但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居然能够延续六七百年,它的存在又有一定的合理性。本文尝试对《咏雪》一文进行抽丝剥茧,以谢家为例,管窥门阀士族的一些基本特征,为门阀制度曾经的大行其道提供必要的逻辑依据。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短文的第一句信息量就很大。可以看出,谢家比较重视教育,士族子弟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如果说经济条件是士族阶层存在的物质基础,那么文化条件则决定了士族阶层的发展前途。有些雄强一方的世家巨族,在政治、经济上可以称霸一方,但由于缺乏文化修养,其社会地位很难为世所重,也难以长久保持。相反,读书人出身寒微,一旦入仕,却可以逐步发展家族势力,以至跻身士族阶层,谢家就属于此类。据《晋书》卷四九《谢鲲传》,谢家先世只能上溯两代,真正使谢氏成为东晋最高门第之一的是谢安。《咏雪》故事的时间背景是冬天,这时一般是书塾放假的时候,“寒雪日”还要把家里人聚集在一起,说明谢家子弟读书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比普通人家更加严格。其教学的内容是“讲论文义”,超越一般的蒙学教育——认识几个字,而是要能了解文章的义理。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学童除了要学习《孝经》《论语》《五经》之外,还要读《老子》《庄子》等显学,这种书不容易读懂,需要讲解、阐释,对学童的知识积累要求较高,说明谢家子弟的学习内容难度较大。谢家接受教育的儿童不分性别,有教无类,甚至女孩子的表现丝毫不逊色于男孩子,这种开明豁达确实难能可贵。这些女孩子一旦成人,做了母亲,相夫教子,她的文化修养对其子女后代的学业引导,乃至家族学术文化的传承都颇有助益。同时,她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与其他士族大家相匹配,能为门阀之间缔结更牢固的婚姻纽带。要维持士族的地位和影响力,家族中既要有举足轻重的代表人物,也要有为数众多的家族成员,大家相互砥砺、互相提携,家族才能绵延兴旺。门阀取士,除了门第的先天优势,更要靠真才实学的支撑,只有真正注重家族教育,才能保证士族的兴盛发达,绵绵不绝。
“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谢安的教学方式非常灵活,能够及时引入生活这个源头活水,在实际情境中培养儿童的想象力,其关注的是思维品质的培养,而不是简单的记诵,或纯粹的知识掌握。他用温和可亲的方式激发儿童的表现欲,使他们畅所欲言,无所顾忌,充分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也显示了谢安自身的学识涵养和教育机制。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一个片段: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寿镜吾先生是“渊博的宿儒”,专业素养很高,但教学方法不免呆板僵化,一味地严厉,师道尊严,跟小孩子格格不入,不能满足他们的求知欲,甚至压抑了儿童的好奇心,课堂气氛沉闷。但谢安的脸上没有“怒色”,更没有故作深沉的严厉,而是“欣然”“大笑乐”。他的课堂活泼灵动,有温度,有激情。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幸福指数估计不如谢氏儿女在私塾里的读书生活。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可以想象,谢安的教学效果似乎应该更好一些,更有利于儿童的成长。
“白雪纷纷”的景色到底是像“撒盐空中”,还是更像“柳絮因风起”?见仁见智,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当侄女谢道韫发言完,“公大笑乐”,其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后来,谢道韫成为东晋著名的诗人,也变相地证明了谢安的文学修养之高,指导之得法。把白雪分别比作盐和柳絮,都用了比喻修辞格,到底哪个效果更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赵毅衡教授在《重访新批评》一书中分析过这个问题。什么是比喻?他引用了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瑞恰慈的话:比喻是“语境间的交易”。如果我们要使比喻有力,就需要把非常不同的语境联系在一起。书中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狗像野兽般嗥叫”,这个比喻无力量,两个语境距离太近;“人像野兽般嗥叫”,就生动得多;“大海像野兽般咆哮”,就更有力量。把从属于不同经验领域内的东西放置在一起,就会有一种强大的张力。如此说来,在儿童的生活经验中,盐跟白雪的距离更近,柳絮与白雪的距离要远一些。把盐撒到空中,这本身不够自然,不符合生活的逻辑和常态,扭捏做作;把白雪比作柳絮,形神兼备,更有一种美感。谢安的文学观契合审美的规律,显示了较高的学术修养,为士族的文化传承起到了引领的作用,以至谢氏后代中出现像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也就不会让人觉得意外了。
《咏雪》大概发生在什么年代?故事中有三个人物,谢安的生卒年为320~385,教材上有注释;谢道韫是谢安长兄谢奕的女儿,生卒年不详;谢朗是谢安次兄谢据的长子,谢据早卒,由三叔谢安抚养长大,生卒年为338~361,官至东阳太守,英年早逝。根据故事情节,这时谢朗八九岁,由此可以推断谢安不到三十岁。这时的谢安正隐遁在会稽,或吟啸山林,或教导子弟。书中称他为“太傅”,那是他去世后朝廷的追赠。
谢安隐居期间,曾多次拒绝征辟,有家族的庇护,他有十足的底气过悠游自在的生活。因为堂兄谢尚是司州都督,长兄谢奕是豫州刺史,弟弟谢万是吴兴太守。不幸的是,在357年到358年一年多的时间里,谢尚、谢奕相继离世,谢万升任豫州刺史。对于谢万的这次任命,作为左将军的王羲之分别给最高军事长官桓温和谢万本人写信,表示不同意见和注意事项。简要言之,豫州是边境地带,兵荒马乱,谢万有经世治国之才,可以身居朝廷出谋划策,但不适合带兵打仗,因为他清高自傲,不屑于琐碎事务,不能与将士同甘共苦。359年冬季,朝廷诏令谢万率军攻打前燕。谢安深感忧虑,亲自深入谢万的部队,笼络将士。第一次出征,谢万就打了败仗,有人想乘机算计他,但考虑到谢安的人情,才作罢。等到谢万逃回建康,立刻被削职为民。谢家的参天大树瞬间折断,谢氏一族危机之重,前所未有。据《通鉴·卷第一百一》记载:“及弟万废黜,安始有仕进之志,时已年四十余。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安乃赴召,温大喜,深礼重之。”
由此可见,谢安无论是隐居山林,还是出将入相,变化的是处世方式,不变的是士族利益。寓居乡野,教育子弟,立足长远,是为家族培育人才;在谢万身边纠偏补过,或不避征辟,出山赴任,是为了维护士族地位—— 必须有本族的代表人物居于实力的位置,才能使士族门阀利益得到政治保障。
谢安,字安石。这个名字对于谢氏家族来说,名副其实。谢安的去就,其内在动机就是为了谢氏家族繁荣昌盛,代代相传,安如磐石。王安石曾赋诗称赞:“谢公才业自超群。”确实如此,谢安善行书,懂音乐,知人善任,神识沉敏,长于辩论,风度潇洒,才能之高,冠盖一时。谢安处变不惊,从容自若,制止了桓温的篡晋野心,挫败了苻坚的大举南犯,追赠太傅,实至名归。谢安既重个体之自由,又重群体之纲纪,知进退,明荣辱,流风余韵,福泽后辈。
反复咀嚼《咏雪》一文,“窥一斑而见全豹”,古代门阀制度的长期存在,有其自身的历史意义,即使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家庭的建设也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