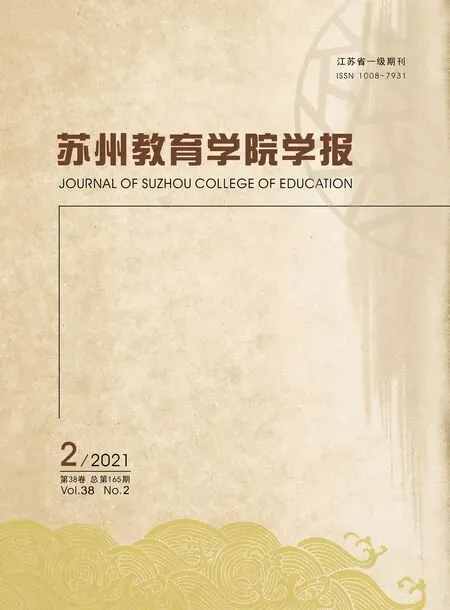栏目特邀主持人:黄景春
主持人简介:黄景春,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主要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民间信仰、古代小说、道教等。承担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发表论文80多篇。代表作有《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信仰》《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以买地券、镇墓文、衣物疏为主》等,分别于2015年、2019年获得第十二届、十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之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

主持人语:民间文学,又称口头文学,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态。民间文学是依靠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语言艺术,它所赖以生成的材料是口头语言。跟作家文学相比,民间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从口中说或唱出来的,而不是用文字写出来的。人类使用文字只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说话的历史至少有几十万年了。通过口头表达方式叙述事件、抒发情感、表达愿望,其中就孕育着口头文学。不管是神话还是歌谣,都是人们经验、情感、信仰和愿望的直接表达。它直接展现人们的所思所愿,无需借助于其他技术手段或中介符号,所以口头文学出现得最早,可以说它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一种艺术形态。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民间文学既是文学,也是知识。传统社会的知识经常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出现,是一种文学化的知识,而不是科学知识。这种知识包含了想象、信仰、习俗的成分,也含有理想和愿望的表达,当然也有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在诸如女娲造人、后羿射日、嫦娥奔月、西王母掌管不死药、大禹治水等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以及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当然还有祭祀、法律、习俗等方面的知识。即便到明清时期乃至当代,民间文学仍是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来源,口耳相传的故事仍然充当地方常识或知识背景的作用。地方传统知识、习俗和文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哪怕是一则传说,从文学的角度去欣赏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我们还可以从地方知识、习俗、信仰的角度去认识它。当我们只把它当作文学来对待时,难免会对它作出片面理解,而忽略了其他的(或许是更重要的)价值和功能。
因此,民间文学研究应该有更加宽广的视角,更加多样的方法。我们研究作家文学,经常要分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细节中解读人物性格,但从民间故事中分析人物形象很难,因为民间文学是类型化文本,每个故事都有多种异文,每种异文又会有多种讲法,我们依据哪一个讲法来分析人物形象呢?再者,按照普罗普的说法,故事中的人物角色是可变因素,是可以被替换的,它只是临时承担起完成某项功能(情节)的作用,这个角色也可以被换成另一个名字,甚至可以被一个迥异的人物替换掉。所以,对故事中的角色作形象分析是徒劳的。
从芬兰学派产生以来,对民间文学的研究逐渐走向类型学、形态学的共时研究路径,关注的重点是故事的母题、情节、结构。同样,从帕里、洛德开始,对歌谣的研究开始转向口头程式和表演。这些研究在国内有很多尝试,是当代民间文学研究的新面相。
同时,民间文学的知识性特征,又跟地方信仰、习俗紧密结合,以至于各地都把本境内的民间文学当作文化资源加以开发利用。特别是在当今提倡文化旅游的背景下,很多神话、传说、史诗都被列入产业化开发计划,有的甚至已经建成旅游景区了。地方社会如何挖掘民间文学资源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也是当下民间文学研究重要的关注点。
总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民间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用开放的视角看待民间文学,运用更多元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民间文学。《苏州教育学院学报》开设“民间文学研究”专栏,也是给民间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个展示研究成果的平台,大家可以介绍各种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可以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分析具体的民间文学作品,也可以对民间文学资源转化的案例加以分析。本期开栏首发陈勤建《非文学的民间文学》、毛巧晖《民间传说、文化景观与地域认同——以大禹传说为中心的讨论》、林玲《高平炎帝陵及其神话产业化开发研究》三篇文章,期待得到同好的响应,积极投稿,让我们把这个栏目开起来,办下去,使之成为国内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新一代江格尔奇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