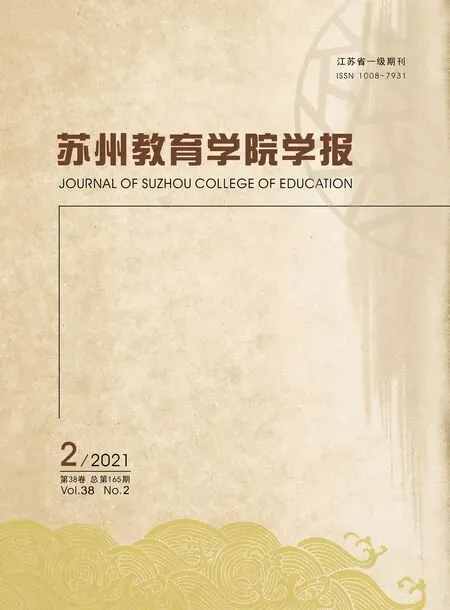高平炎帝陵及其神话产业化开发研究
林 玲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山西高平是炎帝神话的主要传承地之一,当地以炎帝陵为中心,保存了较多的炎帝文化遗址,如羊头山、神农城、炎帝高庙、炎帝行宫、炎帝中庙等;有很多与炎帝有关的地名,如跑马岭、换马村、庄里村等;还有孩子满月“围羊”、农历正月初七“抓羊”、农历七月十五“送羊”、“逼炎帝下雨”等民间习俗,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高平炎帝文化体系。近年来,随着高平文化经济的发展,炎帝陵的建设也逐渐进入快车道。本文所讨论的高平炎帝陵神话产业化开发,偏重于对文化经济实践的探讨,关注的重点是炎帝陵的产业化现状,试图揭示炎帝陵开发背后的文化动力机制。
一、羊头山与神农庙
炎帝庙也叫“神农庙”,原在羊头山上。“羊头山,在今山西之南境,泽、潞二郡交界,高平、长子、长治三邑之间。”[1]116北齐《羊头山五佛碑》载:“……神农,圣灵所托,远嘱太行……地称唐公,山号羊头。”[2]4唐《泽州高平县羊头山清华寺碑》亦载:“又乃羊头沐□□□□□山水盖□此山炎帝之所居也。”[2]6《元和郡县志》载:“羊头山在县东五十六里……神农城在羊头山上,山下有神农泉,即神农得嘉谷之所。”①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十九《长子县》,钦定四库全书本,乾隆四十六年(1781)。《明一统志》载:“相传神农尝五谷于此山。”②李贤等:《明一统志》卷二十一《潞州》,钦定四库全书本,乾隆四十五年(1780)。但在早期文献中,炎帝所在之山实为常羊山。如《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母曰佳姒,有娇氏女,名□登……生神农于裳③裳,通“常”。裳羊山即常羊山。羊山。”[3]陕西宝鸡、湖南会同等地也都以常羊山为炎帝出生地。不过,高平人认为,羊头山即常羊山。④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多次问询当地村民,他们大都认为羊头山是炎帝居住之所,“常羊山”是羊头山的别名。羊头山因“上有石,状如羊头”⑤同②。而得名,当地传此处就是炎帝发明五谷、尝百草之处。
明《羊头山新记》云:“(山巅)石之西南一百七十步,有庙一所,正殿五间,殿中塑神农及后妃太子像。”[1]116-117此处提及的“庙”即羊头山的神农庙,成化本《山西通志》①李侃、胡谧:《山西通志》,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称作“上庙”,顺治本、乾隆本《高平县志》②范绳祖修、庞太朴纂:《高平县志》,顺治十五年(1658)刻本;傅德宜修、戴纯纂:《高平县志》,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亦承此说;同治本《高平县志》③龙汝霖:《高平县志》,同治六年(1867)刻本。、光绪本《续高平县志》④陈学富、庆钟:《续高平县志》,光绪六年(1880)刻本。称羊头山神农庙为“高庙”。笔者据县志及碑刻记载,将俗称所谓的“上庙”“高庙”“中庙”“下庙”略作梳理,详见表1:

表1 清代高平县神农庙称谓统计
⑤ 下太村:即今下台村,也称“中庙村”。
乾隆三十九年至同治六年,羊头山神农庙由“上庙”改称“高庙”,换马岭神农庙由“中庙”改称“上庙”,下台村神农庙则被冠以“中庙”之称。各庙名或是根据庙宇所处地势高低命名:高平东、西、北三面环山,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羊头山神农庙的“上庙”或“高庙”之称,概因其居于北部羊头山上,位置最高;换马岭神农庙在羊头山神农庙东南方向,相隔约六公里,地势相对较低,故称“中庙”或“上庙”;下台村神农庙在同治六年前后出现,因为它恰好位于换马岭神农庙与东关神农庙之间,所以也称“中庙”;而东关神农庙距离羊头山神农庙最远,地势最低,因此,其“下庙”之称从未变过。
羊头山神农庙与换马岭神农庙关系密切。成化本《山西通志》载:“(神农庙)在县北三十五里故关村羊头山上,元初徙建山下坟侧。”⑥同①,卷五《祠庙》。其中所提及的坟,当是神农冢。元初羊头山神农庙迁建时,可能也将“上庙”之称转移给了换马岭神农庙。至于徙庙缘由文献所载不详。据《迁修炎帝神农庙碑记》记载,高平焦河村炎帝神农庙从西北高岗迁于村北古道之因:“庙之故址高峻崎岖,人皆苦其升降。”[2]19同理,高庙位居羊头山巅,官民祭祀不便,故徙庙于山下,新建换马岭神农庙以方便祭拜。
总之,不管庙址、庙名如何变化,当地民众对炎帝的信仰从未间断,炎帝、神农神话也一直在当地流传。
二、五谷庙与炎帝陵重建
换马岭神农庙有“神农遗冢”[4]132之称。乾隆本《高平县志》载:“上古炎帝陵在县北换马镇……陵后有庙,春秋供祀。”①傅德宜修、戴纯纂:《高平县志》卷五《陵墓》,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此处庙宇即换马岭神农庙,庙前有炎帝陵。前文已述,换马岭神农庙沿袭了羊头山神农庙的“上庙”之称。但笔者在调查时发现,当地人并不把换马岭神农庙称作“上庙”,而是称“五谷庙”。那么,五谷庙和换马岭神农庙又有何联系呢?
(一)五谷庙的前身
换马岭神农庙始建于元初,明、清两代均有重修,庙名也经过多次更改。这应该与历代文献中“炎帝”与“神农”使用混乱有关。嘉靖五年(1536),《续修炎帝后妃像增制暖宫记》载:“炎帝神农陵庙,历代相传,载在祀典。”[5]24天启七年(1627),《补修神农炎帝庙三稯殿碑记》称“神农炎帝庙”:“高平县故关里换马镇迤南,神农炎帝庙内西北角,原系庄里村善人修盖。”[5]29崇祯四年(1631),《重修炎帝庙太子殿碑记》称“炎帝庙”:“泫邑北越故关里换马东南,有炎帝庙古址也。”[5]31顺治本、乾隆本、同治本《高平县志》和光绪本《续高平县志》均称换马岭神农庙为“神农庙”,但俗称又有“上庙”“中庙”之不同。从现存的明清文献来看,换马岭神农庙的名称不断发生变化,主要差异是“神农”“炎帝”,但在1941年的《重修炎帝庙各神殿禅房并补修桥梁扩大舞楼彩绘工竣及叙述款项来源碑记》中,又出现了“五谷庙”之名:“换马岭炎帝庙为上庙,有炎帝冢在焉,后人建五谷庙于此。”[5]38因无相关文献佐证,当地人将五谷庙视作炎帝庙的原因难以定论。但据笔者实地调研,当地人有“炎帝就是五谷老爷,五谷庙其实就是炎帝庙”②访谈对象:于SF,77岁,高平神农镇庄里村人;访谈人:林玲;时间:2019年5月11日;地点:庄里村。的解释,同时,据当地人讲述,羊头山神农庙就是五谷庙的前身:
高庙是长子、长治、高平三个地方的群众共同捐款修建的,但是因为它地势太高,不太方便祭祀,到后来就慢慢荒废了。荒废了以后,各县的人们就上去你拿一片瓦,我拿一个梁啊,就把这个庙给拆了,然后他们又到自己的地方再建了一个炎帝庙。现在我们炎帝陵有一个五谷殿,五谷殿就是高庙迁到那里的。③访谈对象:刘Y,山西高平人;访谈人:林玲;时间:2018年8月25日;地点:去往羊头山的途中。另据长治市色头镇色头村炎帝庙看庙人崔ZT述:“长子从高庙里拿走了碑刻,长治拿走了钟,高平拿走了塑像,色头去晚了,什么都没有拿到。”
在当地人的讲述中,五谷庙是由羊头山神农庙迁建而成,所以将五谷庙视同换马岭神农庙。五谷庙中供奉炎帝、夫人、三太子④访谈对象:张M,27岁,炎帝陵工作人员;访谈人:林玲;时间:2018年8月24日;地点:五谷殿。“在高平当地,流传着有关炎帝三太子的各类传说。三太子即炎帝的第三个儿子,他继承了炎帝的农业衣钵,成功培育了百种谷物、蔬菜。”。当地人认为,炎帝与五谷老爷具有相同的神格,炎帝发明了五谷,而“五谷老爷”是以炎帝培植五谷的功绩而称之。故当地人将换马岭神农庙当作(或改名)五谷庙也就不足为奇了。
换马岭神农庙一变而为“神农炎帝庙”,再变而为“炎帝庙”,又变而为“五谷庙”,当代重建后又被称为“炎帝陵”。
(二)炎帝陵的修葺重建
高平炎帝陵相传为金元时期所建,但当代炎帝陵是在五谷庙旧址上再造的,是以仿古建筑为主的新文化景观。
古代有炎帝陵,最早见载于《羊头山新记》:“(换马)镇东南一里许,有古塚。垣址东西广六十步,南北袤百步,松柏茂密,相传为炎帝陵。”[1]120结合乾隆本《高平县志》记载及现有的碑刻记录来看,明清时期,炎帝陵中的各庙宇不断修葺扩建,规模也随之发生改变。嘉靖五年,庄里、团池等村的民众集资续修陵中炎帝庙的后妃像;天启七年,庄里乡约申朝卿、信士郭岱等捐资补修神农炎帝庙三稯殿、彩绘神像;崇祯四年,庄里乡约申崇修等捐款修葺炎帝庙太子殿;崇祯十六年(1643)信士李希孔等创修子孙祠、彩画金妆神像;顺治六年(1649),当地官民士绅补修炎帝陵中殿宇,创建奇楼;咸丰八年(1858),庄里、口则、故关、长畛、岭东、换马六村捐资重修炎帝陵西陪房。1949年,村民仍集资重修炎帝庙各神殿禅房并补修桥梁,扩大舞楼彩绘。但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当时政策的影响,炎帝陵中各庙宇日渐倾颓,神像凋零,仅剩一座五谷庙。1993年,炎帝陵墓碑在羊头山被发现,此碑勒石于万历三十九年(1161),石碑身首一体,正中镌刻“炎帝陵”三个大字,落款“生员申道统立”。2014年,高平市政府、台商叶HD、煤矿企业等共同集资修复炎帝陵。
在官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双重合力下,炎帝陵在非遗保护语境下得以重建。当地以炎帝陵为中心,形成了炎帝神话传说圈与信仰圈,除炎帝农业神话、发明神话外,还衍生出家事型、出生型、死亡型、显灵型等叙事类型。开发商综合利用现有的炎帝神话、信仰资源,对炎帝陵进行了景观建设,将炎帝神话转化为文化资源加以开发。
三、炎帝陵文化资源的开发模式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资本的形式》[6]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资本”概念。文化资本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有形的文化资本往往存在于建筑、遗址、雕塑、绘画等实体中,而群体的观念、信仰等则属于无形的文化资本,这两类文化财富一旦产生流通,便会形成私人消费,导致新的文化资本出现。“文化作为一种潜在的可利用的对象,它还只是文化资本;当出于某种目的(包括经济目的)而被利用,它就转变为一种资源。”[7]在文化产业中,文化资源被转化为文化产品,即实物产品、服务产品及衍生产品,高平炎帝陵文化资源的产业化主要涉及前两类,景区不仅依托建筑、壁画、雕塑等神话资源打造景观,也依据民众的炎帝信仰为其提供宗教服务产品。
(一)炎帝神话景观的打造
高平炎帝陵景区将炎帝神话和建筑等景观融为一体,打造了一个新的文化场域,即民众的“记忆之场”。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认为:“记忆之场诞生并维系于这样一种意识:自发的记忆不再存在,应该创建档案,应该维持周年纪念活动、组织庆典、发表葬礼演讲、对文件进行公证,因为这些活动已不再是自然的了。”[8]显然,建筑、壁画、雕塑等都属于记忆场中的实体,其携带的文化信息是由炎帝神话所赋予的,但其本身并不构筑记忆,仅作为记忆的“储存器”①参见:阿莱达·阿斯曼著、袁斯乔译:《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存在,提供记忆场域,营造特定的文化氛围。客体(文化景观)必须通过激发主体(人)的直观感触,使主体认知到景观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文化景观需要拥有特定文化背景的人去感触,他们的既有知识是激活文化记忆的前提。
通过对炎帝神话的挖掘、重构,开发商赋予了雕塑、壁画等景观以文化意义,吸引游客前来体验。一方面,将炎帝陵中的雕塑、壁画以可视化的形式呈现,实现对炎帝神话的直观展示,既给人以视觉冲击,也兼顾了政治、文化等因素。开发商依据炎帝发明五谷、教民耕作、尝百草等神话进行景观打造,使功德殿、炎帝大殿壁画及炎帝雕塑成为“看得见的神话”。另一方面,景观的文化魅力也是激发游客热情的主要动力。集体记忆“通过不同层次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对不同的、甚至互相对立的个体和集团的记忆,或利用、或弘扬、或篡改、或抹杀、或压抑”[9]。作为一种文化资源,“炎帝”在当代被重新征用,民众记忆也因此被唤醒。曾经在民众间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借助壁画、雕塑、展览馆等实体被呈现出来,这类文化景观也因此承载了炎帝神话。可以说,相关的典籍文献与口承文本是炎帝景观得以存续的历史依据,而“炎帝显灵”等信仰则是文化景观得以生存的现实土壤。
炎帝神话、仪式、遗迹等的重构与重建激活了当地民众对炎帝的文化记忆。开发商通过景观化的方式构建起新的文化空间,原有的炎帝叙事被重述,并由精神之物变为了民众丰富文化生活的场所。
(二)提供宗教服务产品
随着开发进程的加快,炎帝陵的商业氛围越来越浓厚,它不再仅仅是当地民众祭祀炎帝的场所,也成为了面向大众的休闲文化景区。景区推出了供奉光明灯、私人祭祀等宗教性服务,吸引了众多游客。
炎帝陵大殿内放置着巨型的光明灯塔,灯塔分为立柱式、壁式等,均有多层,每层由众多小龛组成,每龛放有一尊神像和一盏灯,外嵌透明小窗,上附供奉人姓名。在民众的信仰认知中,姓名代表对应的“人”本身,供奉光明灯意味着“人神同在”,由此便可获得神灵庇佑。开发商正是抓住了信众的这种情感补偿心理,通过营造神灵“在场”的氛围,赋予光明灯以宗教意义,增加经济交易的神圣性。除此之外,宗教服务还体现在对炎帝祭祀仪式的复现、展演中。开发商利用民众“敬拜祖先”“祈福”的心理,为他们提供私人定制的祭祀仪式,但这类祭祀活动更偏重于商业性和娱乐性,属于文化实践层面的“民俗主义”。开发商将这种私人定制的祭祀仪式明码标价,分为不同的等级,并将这种等级暗喻为与炎帝神灵的亲疏关系,将信仰与利益挂钩—出资越多,祭祀规格就越高,意味着信仰愈加虔诚,与神灵的关系也就愈加密切。与光明灯不同的是,它所针对的消费对象往往是团体,但因为价格昂贵而销量有限。
作为市场经济形势下新生的文化“遗迹”,炎帝陵神话景观开发要充分考虑地方信仰与文化市场之间的平衡,既不可过分受外来因素的掣肘,造成景区的雷同化;也不可完全沉醉于对炎帝文化地方感的建构,导致对现代地理景观、人文精神的忽视。真正意义上的炎帝陵开发,不是披着文化外衣的经济运作,而是在进行“发明性”文化征用的同时,也能注重地方性与现代性的互融。
四、炎帝陵开发的差异性动力分析
高平炎帝陵开发实际上是一场关乎当地政府、开发商、民俗精英、普通民众的文化经济实践,背后隐藏着个体与群体间的利益关系,政治、文化、经济间的渗透关系,历史与现实的互构关系。陈泳超强调:“要在田野调查的情景语境中去探讨地方性知识存在的传说,尤其注重于考察那些具有明显动机的传说变异过程。”[10]130他的着力点在于对“人”的研究,即关注主体对传说的能动建构与话语权力问题。笔者在此借鉴“传说动力学”理论,对炎帝陵神话产业化开发背后的差异性动力进行分析。从调查情况来看,炎帝陵产业化开发的时代性、地方性动力较为薄弱,层级性动力才是关键。笔者试图通过关注行为主体如何参与炎帝陵产业化开发,分析他们在经济开发中扮演的角色及其话语权问题,来探讨影响炎帝陵产业化开发发展走向的动力因素,最终揭示高平炎帝陵复兴背后隐藏的动力机制。
(一)时代性动力
时代性动力是高平炎帝陵能够实现产业化开发的前提条件,具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国内政治文化环境的改变;二是国家对非遗保护的深入。前者是将传统记忆中的神话人物先祖化,并将其纳入现代国家的象征范围;后者则是对传统文化的再记忆与新激活。
20世纪60年代时,炎帝陵祭祀活动不复存在,炎帝陵也被毁坏。改革开放后,民间信仰、庙会祭祀重新兴盛。1994年,炎帝陵墓碑被重新发现,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翌年,当地开始着手挖掘炎帝文化,并进行旅游开发规划。2002年,当地翻修了羊头山上的六名寺,并将其更名为“神农庙”。2004年,高平市出资修建神农祭祀广场,并举办了多场全国性的神农炎帝公祭活动。此外,大陆与台湾间的民间交往也是炎帝陵神话产业化开发的重要的时代性因素,2012年,台商叶HD提出重修高平炎帝陵,国台办和山西省政府均给予大力支持。2016年,炎帝陵修复建成后,高平市举办了主题为“问祖炎帝,寻根高平”的海峡两岸神农炎帝民间拜祖典礼,此后,每年都举行。截至2019年,高平市每年都会邀请台湾信众参加拜祖典礼。此外,高平神农炎帝祖庙圣驾还曾赴台巡境赐福。在非遗保护方面,2004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掀起了非遗申报与保护热潮。炎帝神话虽尚未进入高平市非遗名录,但据高平炎帝文化研究会介绍,他们拟把“炎帝陵祭祀礼仪”作为市级申遗项目,届时,炎帝陵将成为重要的文化空间。①访谈对象:王J,炎帝文化研究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访谈人:林玲;时间:2019年10月3日;访谈方式:线上访谈。
(二)地方性动力
炎帝陵周围的村落通过多种方式联合,从产业开发的角度看,这种行为扩大了地方文化影响力,增加地方文化的意蕴。作为炎帝陵开发的外部因素,地方性动力主要起到了建构传承场域的作用。炎帝陵周围的各村落名有的来源于相关的炎帝传说,有的因相关炎帝传说组成了“亲属”关系,从而形成了一套日常交际的地方话语体系,这也是炎帝陵产业化开发的前提条件。
村落联合的第一种方式是村落直接以炎帝传说命名,如有关“庄里”得名的俗说:“传说炎帝游各地,尝百草,路经北营、换马,死于此(庄里),遂将遗体装入棺里,进行安葬,故将村名称为装里,后改为庄里。”②山西省高平县地名办公室:《高平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8年,第145页。“装里”“庄里”之称,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庄里村与炎帝墓冢的密切联系。因此,近几年每逢农历四月初八进行炎帝祭祀仪式时,庄里村都要唱戏三天,并设集市,周围村民都会前来赶会。但故关村赵SJ却认为,故关村炎帝庙是炎帝行宫,早前四月初八祭祀时故关村是首社,地位要比庄里村高一些,故关村供奉着炎帝三太子,又是早年祭祀的首社,理应在开发时得到更多的重视。③访谈对象:赵SJ,故关村人;访谈人:林玲;访谈时间:2019年5月11日;访谈地点:故关村炎帝行官门前。但炎帝祭祀中心的转移,既受时代因素影响,同时也与炎帝陵修复开发的规划有关。炎帝陵是以五谷庙为基础重建的新文化景观,其地址在庄里村管辖范围内,庄里村自然也就成为了新的祭祀中心。
第二种方式是各村落因“向炎帝求雨”而结为神亲,即“村落之间以共同信奉的民间神灵为纽带而形成的一种虚拟亲属关系”[11]。各村落以炎帝为核心,通过与炎帝“攀亲”结成了一个“亲属团体”:长畛村是炎帝的岳母家,朴村为炎帝二女儿的婆家,团西村为炎帝二女儿的娘家。上述三个村落或与炎帝生平经历有关,或因炎帝传说而得名,并基于炎帝神话信仰互攀“亲戚”,极大地丰富了高平炎帝文化的内涵。客观地说,炎帝陵内主要以新建景观为主,景区的文化内涵稍显不足,而周围村落与炎帝相关的碑刻、庙宇、口头叙事众多,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这些也成为炎帝陵神话产业化开发的重要地方性动力。
(三)层级性动力
作为炎帝神话传说存在的重要场域,当地存在着一个客观的文化系统,即高平各村落通过不同的联合方式将自己与炎帝勾连,并以炎帝陵为中心构成了炎帝文化场域。炎帝文化场域与民众惯习相互影响、形塑,又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话语权力。“每个场域都是一个充满动态关系的争夺空间,各个行动者(个人或集体)据有不同的文化资本,依凭惯习来选择策略,用以保证和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12]作为影响民俗活动实际走向的核心要素,层级性动力是明确人物与事物对应关系、群体基本认知立场的关键,其主体包括政府官员、民间知识分子、普通村民等。笔者从高平炎帝陵产业化开发的实际出发,按照“身份—资本”所产生的动力因素大小,重点分析地方政府、民俗精英、普通民众在炎帝陵开发当中的角色及其话语权问题。
政府和开发商是炎帝陵产业化发展的主要决策者,他们在文化资源化的民俗实践中拥有主要的话语权。1994年至2000年,高平市政府一直在宣传炎帝文化,特别是1995年央视新闻报道了炎帝陵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市政府一方面出资整修炎帝陵、炎帝行宫、炎帝寝宫、炎帝中庙、炎帝高庙等遗迹古建;另一方面则积极引入外资。自2016年起,高平市成功举办了多届民间拜祖典礼,其背后其实是“海峡两岸神农炎帝经贸文化旅游招商系列”行为。对炎帝陵、炎帝神话的修复打造,不在于恢复旧有的民俗,而是以政治、经济为主导方向,致力于当地经济增长与两岸民众团结。
陈泳超对“民俗精英”的定义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占据民间知识话语权”;二是“引领民间知识变异的走向”,他们往往分属不同的阶层群体,但对某一民俗事项都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感。[12]米DM在高平炎帝文化圈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曾任多个职务,退休后致力于炎帝陵的修复、宣传工作,现任高平炎帝文化研究会会长,是促进高平炎帝陵产业化开发的关键人物。首先,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与经济背景使他有能力号召村主任、村支书参与炎帝文化的保护,并邀请各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同时,通过各种途径募化修陵款。其次,他退休后担任高平炎帝文化研究会会长,致力于当地的炎帝文化保护、整理工作,组织研究会印发《炎帝文化》(高平炎帝文化研究会会刊)、《炎帝古庙》、《炎帝故事与传说》等内部资料,并积极申报“炎帝陵祭祀礼仪”非遗项目。他的政治身份是其成为民间权威的重要保障,因而他对高平炎帝陵开发有着“明显的话语权与支配力”[10]155。他前期筹资修复炎帝陵,后期挖掘、宣传炎帝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高平炎帝文化的发展走向。
俗民群体的构成相对复杂,既有普通民众,也有香客信众。普通民众对炎帝陵产业化开发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他们对炎帝文化话语权的掌控主要源于生活经验,他们无意于对炎帝文化进行深入理解或宣传,仅是将其视为某种地方文化来对待,属于炎帝文化的消极传播者。但当他们切身感受到产业化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或情感满足时,往往又会变得异常热情,转变为炎帝文化的积极传播者—香客信众。他们不断炮制出新的灵验传说,以获得听众的信仰认同,凸显神灵的神异性与可信性。他们通常会把任意愿望附加于炎帝,一旦获得情感满足,便将一切都归因于“炎帝的安排”。这类香客信众与“优异村民”和“巫性村民”[12]不同,他们虽熟悉本地的风土人情,但在普通民众中也不一定具有权威性;虽然信仰炎帝,但也不具备“通灵”的能力,仅在祭祀或遇事时才会前往炎帝陵敬香祈祷。
炎帝陵在神话产业化开发过程中,以区域旅游为主要开发方式,景区周围也出现了“农家乐”、特色小吃、纪念品售卖等商业行为,但未涉及影视领域,也没有打造炎帝文化符号的自觉,发展后劲稍显不足。开发商在进行炎帝陵产业化开发时,如何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炎帝符号、如何在保持地方文化特色的基础上避免趋同、如何平衡不同群体间的利益与文化需求,等等,这都是神话景区持续开发的关键。高平炎帝陵神话产业是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开发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激活和利用,本质上属于文化消费。我国对文化遗产的策略是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强调在保护中传承文化精神。高平炎帝陵神话产业化开发模式在我国并不少见,但也为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因而值得学界持续追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