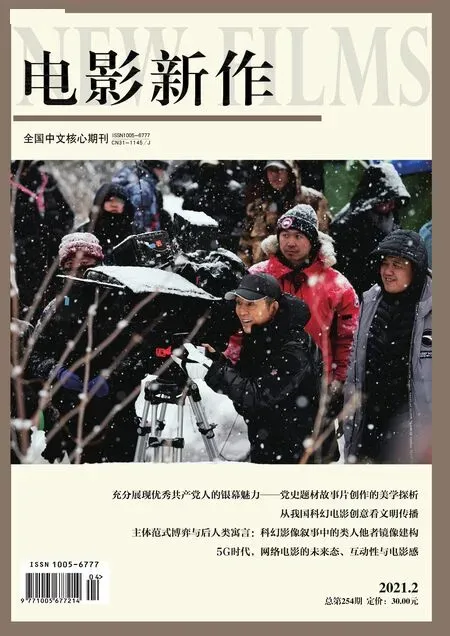面向未来的现在:科幻电影的城市危机
康文钟
广义而言,城市所承载的是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生态、空间,而作为工业革命和近代城市兴起的直接产物——电影——自诞生之日起便在连接城市方面承担了重要的角色。学者张经武在其著作《电影的“城市性”》中提到,“城市诞生电影,电影呈现城市;城市消费电影,电影塑造城市,这样的互动关系在电影初生时期已经铸就。”几组简单的对照,清晰地勾勒出电影的发展与城市的演进之间一直保持着的极强联姻性。
单就影像层面来说,大多数叙事类型电影对于城市的表现属于记忆的持留,较此而言,科幻电影则热衷于摧毁这种记忆持留,在科幻电影中,城市经常遭受着自然灾害、科学故障、外星生物侵入以及怪兽攻击。“毁灭”成了科幻电影的一个主题,但不能忽略的是,科幻电影在“毁灭”之外呈现更多的,是对于城市未来的发现与想象的表达。也正因为如此,科幻电影不仅依然与城市保持着亲密联系,更重要的是,城市正逐渐成为科幻电影的考古现场。
伴随科学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关于城市空间的呈现,科幻电影在物质现实之外构建出了可悬置日常的“现实”拟像。尽管近些年的科幻电影类型出现了一些式微,但其构建的拟像依然作为时间和差异的物质能指,冲击着观众的视觉经验的同时,也表达出了一些当代城市正在面临的危机,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机器运作、恐怖袭击等。由此,本文将以科幻电影对于未来城市的描绘作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属于科幻电影中人工打造的未来城市影像,反思技术主义影响下的当代城市正在面临的危机。
一、悖论迷宫:科幻电影中的城市考古
一直以来,科幻电影呈现的虽然属于未来的情景,但它从未描写一种真实的未来制度,相反,科幻电影是在将现在转换成一种未来的确定性过去式。在科幻电影中,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城市可以直接勾连起我们所处当前客观世界中的直接体验。或者说,通过城市中的一些镜像,我们可以感受到科幻电影是如何坚持借用“过去的”形象来承载未来的某种突变,如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银翼杀手》(1982)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影片开场,戴克警官驾驶着空中警车飞行在天空中,镜头顺着他的视线俯瞰夜晚的城市,除了几座喷吐火焰的哥特式塔型建筑外,黑暗中亮起灯光的城市群落与现代人乘坐飞机看到的深夜城市并无差异。但紧接着的镜头由俯转仰拍下了闪耀着刺眼光芒的、矗立在更上空的金字形神塔。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未来主义寺庙、悬停着的警车以及20世纪的模拟群落共享着天空,作为权力代表性场所的金字神塔,一个国家形象象征的空中警车,两者都是源于“古代神话史”对于权力自然化表达的一种奇观形式呈现。金字塔和空中警车——属于科幻电影中的人工制品,此刻拥有了类似叙事本身的功能,而科幻电影中的城市考古正是在这种想象未来的历史话语中找寻其中的矛盾和裂缝。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科幻(电影)隐藏了另一个更为复杂的时间结构:(它)并非提供给我们未来的‘影像’——不管这些‘影像’对于必然会对其提前‘物化’的观众意味着什么——而是对我们此刻的经验进行了陌生化和重构处理。”《黑客帝国》(1999)里的主人公尼奥进入真实世界后,当他震惊于眼前那破败不堪的场景时,耳边适时地出现了反动军领袖墨菲斯包含讥讽的解释,“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对于习惯了虚拟现实生活的尼奥而言,眼前经历大战摧毁的芝加哥的残垣断壁的陌生呈现,对于隔着银幕沉浸在舒适的都市生活的观众而言,亦是一种陌生的影像。齐泽克将《黑客帝国》的这一场景和21世纪初世贸中心从纽约天际上空消失联系了起来,“一直出没于屏幕的幻象性幽灵进入了我们的现实。不是现实进入了我们的意象,而是意象进入并粉碎了我们的现实。”
事实证明,科幻电影是应付近期危机的一种灵活媒介,它回应技术现代性的强化和全球扩展并非以一种崭新形式,而是从该类型的历史中解脱出来以消除社会的文化焦虑。世贸中心“消亡”的物质、时间和文化上的接近,加之它属于一个极为独特的事件,都为科幻电影提出了相当的挑战,寓言与反思成了面对这种挑战的两个面向,因为除了媒体,很难再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呈现,因此后9/11时期的科幻电影,尤其是灾难类科幻电影都在借用9/11事件及其影响作为叙事的背景,来填补事件和影像表现之间的空白。往前追溯,是1933年的梅里安·库珀执导的《金刚》,一只被送往纽约展览的大猩猩,为了追寻它心爱的女人而大闹纽约城,它与现代武器在对抗中,无意间将纽约变得有些破败不堪;属于后9/11时期的是罗兰·艾默里奇执导的《后天》(2004)以及马特·里夫斯执导的《科洛佛档案》(2008),前一部电影中,地球的第二次冰河期到来,整个纽约城被海啸、地震、寒潮包围着,人们开始代表城市与自然进行抗争;第二部则是用伪纪录片的手法记录了纽约城遭受不明怪物袭击的日与夜,84分钟的影片有至少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纯粹呈现现代武器与未知怪力的角逐,而城市也在双方的对抗下变得面目全非——自由女神像直接摔落在逃跑人亦是银幕前,满目的疮痍让人在感慨的同时还要承受未知生物来袭的惊恐,即便乘坐直升机飞上天空的主人公们,也被怪物轻松地拽下了天空,影片最后轻轻传来一声“救我”(help me)的信号,让人们感受到了一丝希望。如果说早期的《金刚》是一篇透明的寓言的话,那么《后天》同《科洛佛档案》则是对于危机发生后的沉重反思。无论是寓言还是反思,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后两部,更是成了可转移一些真实事件的微妙替代物。这也使得科幻电影在影像奇观之余为城市考古提供了间接的解读手段。城市作为一个考古元素,成为科幻电影的一个重要依托。
二、文明冲击:科幻电影城市缺席与焦虑
科幻电影中,城市不仅会作为考古的直接元素参与叙事,其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也时常作为一个关键元素参与到叙事当中。在《变形金刚2》里,一开场便是公元前17000年,拿着长矛的、渺小的原始人与浑身金属且巨大的塞伯坦星人为了资源的争斗。在社会科学中,暴力的概念不仅限于物理意义,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等主要社会结构产生的经济与政治差距基础上提出了“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的术语概念,结构性暴力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上的潜意识力量最终还是要诉诸攻击、战争等物理性暴力之中。《变形金刚2》(2009)开场拿着长矛、渺小的原始人与浑身金属且巨大的塞伯坦星人的对抗即是如此。资源枯竭的塞伯坦星人发现了地球上的丰富资源后不惜发动力量来掠夺,最终埋下的引导矩阵也变为现在的霸天虎等反派塞伯坦星人苦寻的指引。在现代环境下,正义与反派的斗争从美国的城市群落发展到了古代文明遗迹,一次是前往佩特拉古城的探险,一次是在埃及金字塔找寻为大型杀伤武器提供燃料的设备,一次是擎天柱与霸天虎在吉萨高原上的搏斗,显性意义上是扩大了山姆与擎天柱作为正义一方对于地球的更广泛的英雄气概;而在隐性层面上,却是加尔通“结构性暴力”的体现——正恶双方的争斗同时也演变成了现代文明为求发展对古代文明遗迹的巨大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暴力的不平等结构演变成为拯救霸权形象,但观众的共情与正义一方在文明遗迹上行使暴力的目标一致,却自然化了所有的暴力结构。这些叙事,在媒体学者坦纳·米尔莱斯(Tanner Mirrlees)看来,通常被戏剧地描述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冲突和危机,他们制造威胁和挑战,激发全世界的希望和恐惧。”通过这样的一种结构暴力对抗呈现,使得城市考古成了缺席的一方,转而进化为一种社会文明的“祛魅”——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便建有一座仿制的金字塔,如《银翼杀手》中的金字塔建筑也依然是权力的象征。过去不再让人类产生恐惧,而是恐惧于一切未知,这正是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关于“启蒙”理念的呈现,“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同样作为一部现代文明对原始文明的掠夺题材的科幻片,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2009)却有着不一样的结果。
2154年资源枯竭的地球,无意中在潘多拉星球上发现了矿产,想要移民却发现那里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球,便用尽办法想要在那里获得资源。轮椅上的杰克·萨利幸运地成为克隆人的匹配者,并以一名说客的身份进入潘多拉星球劝说纳威人离开。不料人类因为资源紧张而提前发动了对潘多拉星球的攻击,被潘多拉星球深深吸引着的萨利率领纳威人向现代文明发起了反抗,最终以人类被驱逐、纳威人胜利告终。影片里城市虽然同样处于缺席状态,但巨型的开采工具、先进的科学技术、精良的武器装备都代表着现代文明,从侧面交代了极度发达的未来城市,却在最后的战争中败给了手持弓箭长矛的纳威人。影片从反向的角度表达出技术决定论所呈现的暴力面貌的焦虑,表达着人对于未知的恐惧以及克服恐惧的勇气和能力,以此在叙事空间之外重建起了社会秩序。正如擎天柱在结尾所说,“我是擎天柱,我向大家宣告,我们的过去将被铭记,我们将活在他们的记忆中。”它所倡导的这种记忆逻辑虽显薄弱,但无形中是希望观众在惊叹动作场景与动作空间之余,在时间、物质和文化表现上,保持着对城市文明的结构性暴力的警觉。在科幻电影中,城市更表现出了其多面性以及所带有的文化内涵。
三、多面之城:科幻电影中的城市类型
当人们的想象力被自己身处世界的经验所严格限制时,人只能同与自己世界密切相关的周围环境接触。因此,“声光色像的奇巧翻新和城际线的日新月异一直是大都会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与‘奇’诱引着人们的‘窥视’与‘再窥视’。”从被摧毁城市的“惨烈现状”到新兴起城市的“未来想象”,科幻电影在影像吸引力方面保持着天然优势,那些繁复多变的特效、无法“引得”的影像,超越“日新月异”的速度,罔顾观众已有的视觉经验,刺激着他们的窥视欲望,激发了他们对于未知的好奇。这些影像冲击更多是来自于科幻电影中所表现的现在或未来的、已实现或意图实现的技术,比如基因工程、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脑神经科学、时间旅行等高概念技术,对比之下,尽管城市无法作为一个单独类型出现在科幻题材电影中,但又不可否认,它在电影中却是无处不在的。“在各种虚构的生气勃勃的世界中,城市能够成为前沿和中心,其特征对于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迫使和抑制人物作出种种选择。”
苏珊·桑塔格对于科幻电影保持着这样一种态度,“我们只是观众,我们只能观看”,一言唤醒了科幻电影的美学特性——陌生化带来的乐趣以及政治意味。即便是熟悉的城市状态,在科幻电影中也被附上了一层陌生的面纱,而它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呈现,则是站在未来角度对现在的一种外化形式及内在审视。有过战争创伤和纽约经历的导演弗列兹·朗,将他眼中的未来城市塑造为一座巨型的完全受引擎和机器驱动的样貌。拥有大堂、图书馆、剧院和运动场的“子民俱乐部”的地上高塔就在劳动之城的上方如巨人般“凝视”着地下城的工人,黑暗狭窄的工人居住地与明亮宽敞的子民俱乐部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几何形状切割的都会带来的陌生感让人感到敬畏,而高耸的墙面更是将不同的阶级进行了严格的划分,不容任何人僭越。在现代科幻电影中,巨型城市也时常会出现在影像中,比如2018年的《掠食城市》,经过灾难后,新的人类文明逐渐出现,海陆空出现了新的城市,陆地上的巨型伦敦城化身为钢铁巨兽,靠吞噬小型牵引城掠夺资源已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一座巨型的山体形的城市彻底解构了我们对于城市的既定印象,受自然制约和发展需要,伦敦城必须不断前行寻找可以吞噬的牵引城,因为“它用持续性取代了永久性,用长期性取代了固定性”。
相较而言,这种地面的巨型城市与小型城在水平方向上的对比显然比不上高科技城市与破落城镇在垂直方向的对比更能突显城市中人对于阶级难以突破的僵化。《银翼杀手》(1982)、《第五元素》(1997)、《星球大战:西斯的复仇》(2005)等都形构出高耸入云的神话建筑,《未来学大会》(2013)在地面之上用一架热气球作为城市文明最后的栖居地。《阿丽塔:战斗天使》(2019)更进一步,高空的撒冷与地面的联系只用几条运输货物的通道,想要通过正常渠道通向高空撒冷城的可能几乎没有,最终为去撒冷而只保留了大脑、双手和心脏的绮莲证明了阶级剥削的残酷。然而在影片里,无论是影片内的角色或者银幕外的观众,对于撒冷的观感只有外部运转机器的冰冷,任谁也没有见过它的内部结构如何,撒冷的代言人诺瓦双瞳散发着蓝光,言语的冰凉拉开撒冷与地面钢铁城距离的同时,又无时不在“展现着人类关于未来城市空间具体面貌的乌托邦畅想”。这种保持着垂直极远距离的高空城市不仅作为乌托邦的幻想,同样也代表“一个执行社会和政治目的的制度机器”。像全景敞视监狱一样,悬在空中的撒冷借助地面钢铁城内安置的各类摄像头,甚至是机械人的脑中植入的监控芯片,保持自身主流意识形态对地面居民的霸权体系统治,即便地面的居民已经在社会的限制融入自我意识当中,但空中城市依然不敢放松警惕。
全景敞视不仅属于同一空间的空中与地面,更属于现实与虚拟之间。《黑客帝国》里尚未醒来的“尼奥”们生活在繁华的都市中,他们尚不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处在人工智能的监视当中,雨果·维文饰演的史密斯特警便是全景敞视监狱的执行者,作为计算机的杀毒程序,他监控着每一个生活在这城市里的个体,当尼奥苏醒之后,得知他是救世主的史密斯必须在尼奥的救世主身份苏醒之前消灭他,否则虚拟城市将遭受破坏,控制这一切属于现实的人工智能系统也将遭受破坏。但现实生活的枯燥乏味单调会让人忆起矩阵内城市的迷人与生活的愉悦,生活在虚拟里的人或许都已得知自己所处环境的虚假,但那里有美味的牛排和可口的红酒,又有多少拥有美好的人愿意舍弃眼前一切呢?塞弗便是其中的一员,他在现实中的暗红色毛衣在矩阵虚拟里转换为了艳丽的红色皮衣,他不惜背叛墨菲斯只为获得虚拟世界里的名人身份。阿尔都塞将这种解释为他们已将属于社会的限制性价值观与自我意识进行了融合,不用特别明确的外部控制,人们也会遵从社会和文化标示的规范行事。简言之,人依靠自我约束,便能保证一切有条不紊的顺利进行。
关于城市的虚拟和现实对抗在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头号玩家》(2018)里变成了浸入与逃避的对照。影片开场时,当男主人公索德·沃兹穿过哥伦布的破落城镇来到废车堆中间的虚拟平台的过程当中,镜头扫过了落败的、破坏规划的城镇,它没有任何淳朴或乡村风,而是充满着紧着与不安。“在2045年,现实令人失望,人人都想办法逃离,所以詹姆斯·哈利迪才成了我们的大英雄。他向我们展示了只需原地不动就能周游世界。只要有台具有压力感的全方位跑步机,你无需亲身前往任何地方,哈利迪看到了未来,并将其打造出来,他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成为‘绿洲’。”影片中已经发展至垂直集装箱群落的荒芜城镇,与绿洲里体现着技术现代性的高科技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虚拟化的城市将属于不同层级的城市内容进行了扁平与压缩处理,因此可以看到自由女神像和诸多大厦排列在一起,女神手举的火炬成了号令枪,城市里同时出现了侏罗纪恐龙与金刚。现实中的经济两极化让高新城市彻底从人们视野中消失,转而用虚拟现实里的城市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深度分化的结果是破落镇里的人们无心向意识形态发起攻击,而是集体无意识并且单向度地默认了这一已经物化的世界观,对于大众而言,批判与反抗已经失去了效力,“(文化工业)越是能够成功地凭借技术制造出与现实课题想象的复制品,它就越能使人轻易相信外部世界只是电影所展现世界的简单延伸……现实生活不再可能与电影相互区别”。直到最后虚拟世界里的帕西法尔(泰德的虚拟化身)引爆了炸弹,所有人从虚拟的横流物欲中苏醒,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现实荒芜。
我们看到,科幻电影中的城市,从高耸入云的巨型城市、可移动的城堡,发展到取代了现实荒芜的虚拟城市建设,虽然都将时间设定在了数十或者百年之后,但其所指向的无一不是随着经济、科技、文化进步而迅速演进的现代城市现状。

图1.电影《头号玩家》剧照
四、技术乌托邦:科幻电影的城市镜像
卡尔·阿博特(Carl Abbott)提出过一个关于科幻和和城市的三段论,“科幻小说是关于未来的,人类未来是属于城市的,因此,科幻小说应当是关于城市未来的。”科幻电影对于城市是多样化的描写,如《流浪地球》(2017)中太阳即将毁灭,地球被寒冷的冰川覆盖,人们生活在拥挤的地下城中,地面上只能凭借地标建筑——电视台总部大楼、东方明珠、金茂大厦辨别地理位置,地下城变成了无地域划分的复合型空间,家庭空间、工作空间以及休闲空间拥挤在一起,让城市出现了一种无地域化趋势。呈现在银幕上的城市“交融时间与空间、客观与主观、真实与想象……既虚幻又真实,既是梦想又是现实,既遥不可及又近在咫尺,它能同时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发生影响”。
正是这种城市的不同空间形式的迅速交融,允诺科幻电影中的城市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表现出未来主义的氛围,这在肖恩·库比特(Sean Cubit)看来,无论技术如何,都不能忽视乌托邦主义想改变的目标,也不能只限于同旧事物斗争,“技术被当作一种规划工具进行管理,意在规划出一个与不久前的过去神似的未来”。现代城市在发展的进程中的确出现了许多现实性问题,诸如经济的两极分化、资源的无尽挖掘、自然的破坏失衡、文化的进步缓慢等,这些问题在科幻电影中以一种彻底的毁灭与重建的形式呈现在银幕上,如《2012》里全球遭受海浪淹没,《流浪地球》中地球的整体迁移,《星际穿越》中郊区遭受的巨型暴风袭击等,是科幻电影站在未来的角度上给予着现代人的警示。
1975年的《气候变化:我们是否正处于全球变暖的边缘?》一文严肃的提出了全球变暖问题,随后学界业界关注这一焦点问题——因全球变暖致使了大量的动植物灭绝,一方面是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则是城市进程的加快与覆盖面的拓宽,两者共同指向了一个人类命题——对经济利益的盲目崇拜。澳洲的烈火、南极冰川断裂、欧洲致命热浪,海平面不断上升等,以往出现在科幻电影的景观正真实地发生在城市或距城市不远的地域时,曾让人向往的城市正在出现极为复杂的转变,各种可能与变化催生出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时,人类也依然没有停滞甚至放缓推进城市发展的速度。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的危机意识并没有及时的与大众产生互动,这也使得集体出现在一种城市的沉浸状态之中恍然却不知。正如黄鸣奋所言,“变异意识、危机意识和大局意识可以统一起来……它既是危机的根源,也是机遇的来源……未来的世界不是魔法的世界,也不是神仙的世界,而是科技所引导的世界。科幻电影所乐道的是凛然大度、处变不惊、别开生面。”当然,我们也希望科幻电影中虚拟的美丽城市想象能够成为城市发展的方向,所有毁灭的幻想只停留在幻想,那样便是无论沧桑如何变迁,城市都依然绚丽多彩、星光绚烂。
【注释】
① 张经武.电影的“城市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57.
② Fredric Jameson.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M].New York:Verso,2005:286.③ [斯洛文]斯拉沃热·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M].季广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15.
④ Galtung,Johan.‘Violence,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6.3(1969),167-91.⑤ Tanner Mirrlees.Global Entertainment Media:Between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M].New York:Routledge,2013.188⑥[德]马克思·霍克海姆,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
⑦ 孙绍谊.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5.
⑧ “引得”,为“引得性”(indexical)的动词化转变,“indexical”还常译为“索引性”,但“引得”更能体现观者的对影像和现实比较的主动性。
⑨[美]卡尔·阿博特.未来之城:科幻小说中的城市[M].上海社会科学院全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创新团队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8.
⑪Susan Sontag.‘Th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
.’In Redmond, 2004, 43.⑪同9,86.
⑫同1,164.
⑬同9,113.
⑭[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M].方尔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48
⑮同9,3.
⑯同1,162.
⑰[新西兰]肖恩·库比特.数字美学[M].赵文书、王玉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02.
⑱黄鸣奋.危机叙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