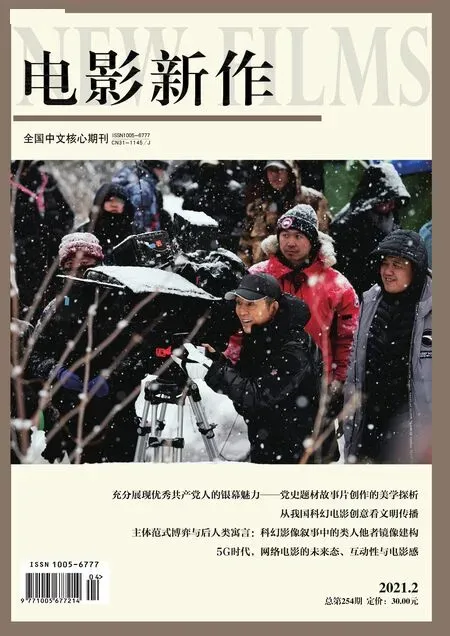主体范式博弈与后人类寓言:科幻影像叙事中的类人他者镜像建构
杨俊蕾 王嘉玮
科幻影像将叙事建构在属人的生活世界中,表现技术与人类主体的交融和互构,形成技术想象和主体反思的一体两面。技术他者的塑造是技术时代下进行人类主体自我反思的一种科幻叙事表现形式。科幻影像中的技术他者是与人类主体对位的技术产物,能够与人类主体进行语言、情感上的交流和行为上的互动,引起主体的情感思想变化。银幕形象由两种基本类型组成:一种是非人他者,比如《2001太空漫游》(1968)中的人工智能系统哈尔,一只非人的、机械属性的“红眼睛”;一种是(类)人形他者,弗里茨·朗《大都会》(1927)中的金属机器人玛利亚开创了该类型形象的先河。此后,《银翼杀手》(1982)中的星际杀手复制人、《机器管家》(1999)里的安德鲁、《人工智能》(2001)中的儿童机大卫、《机械姬》(2015)里的女性机器人艾娃,以及《终结者》系列里的T-800等均属此列。与科幻影像中的非人他者相较来看,(类)人形他者的镜像结构进一步弥合了人与机器的距离,将人与机器之间的矛盾纽结与叙事张力进行了有效的扩充。当(类)人形他者被赋予更多的人性而被塑造为类人他者,其与人类主体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更加复杂微妙,通过更多的共性叙事引发出更大强度的同情与认同。因此,考察科幻影像叙事中的类人他者镜像建构,首先需要厘清类人他者和人类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态,继而思考其中所蕴含的主体范式博弈与后人类寓言指向。
一、类人他者塑造与人类主体的镜像观照
科幻影像对类人他者的塑造肌理,是在与人类主体的无限趋同中划定差异。当人形的、外在的差异被消解,类人他者和人类主体的差异性矛盾便向人性的、内在关系转化,进入人的主体性追问与反思。从趋同的角度看,若要塑造一个“类人”的他者,势必需要“什么是人”的答案。因此,类人他者的塑造,意味着人类主体范式的自我确证,并将其赋予类人他者,由此形成关乎人类主体的镜像观照。这种镜像观照构成了科幻影像独特的“他者视角”,并对人类主体进行自我审视与反思。
《人工智能》将大卫设定为符合人性理想的人工智能儿童机化身,与影片中其他人类角色的非人性行为构成鲜明的对照。其出厂配置包括了真挚的情感、道德的原则和友善的信念,“为了确保人的利益无损而在初始设计中注入对象唯一的爱恋编码,一旦启动就自动写入附加条款,成为无条件执行的行为信条,永无修改或者反悔的可能”。在情节上,大卫始于莫妮卡夫妇对儿子马丁的情感替代需求,直到奇迹发生,马丁意外康复归来。马丁不择手段地排挤和构陷大卫,最终导致大卫被莫妮卡抛弃。在类人他者大卫的镜像观照下,人类的情感狭隘自私、排异多变,没有基本原则可言。相反,大卫等人工智能机器人在芯片中植入的爱意情感,对于特定的人类用户维持恒定不变。在《银翼杀手》中,类人他者是拥有人类情感和意志的复制人(replicant),其功能性实质是被人类操控和压迫的奴役者,也是资本流通中可以被定价和替换的商品工具。但在影片的叙事中,复制人因为具有人类的镜像性质而产生了自由意志,并对被动性造物的生存权利提出质疑。在这个矛盾激化的过程中,瑞秋对德卡的爱和拯救、罗伊在生命终止前对全体人类释放的宽恕和善意,反而使人性得到升华。《机械姬》将最新一代的人工智能艾娃设定为具有人类智能和自主意识的类人他者,呈现出拟人他者的完整镜像。在人机相处的回合中,艾娃在外观上表现出典型的女性情感特征,并在恰当的程度上塑造出自由与人性之间的交换。作为他者镜像的旁观者,程序员对于自我人性产生怀疑,对于创造人工智能的技术新贵产生仇恨,两种否定性情感力量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具有类人特征的机器他者也最终发展出比人的交流更为隐秘的深度语言系统。
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观照人的主体意义,“主体”是意识、自我、精神等的承担者,也就是“人”。儿童机大卫的人性情感、复制人罗伊的生存意志、机械姬艾娃的自由信念,都是“人”之主体性的复杂显现。类人他者“作为人类心智的对象化和物化表现,他们也直指人类的自我心理和自我认知。我们创造了这些人类的‘他者’,并通过他们反观人类自身”。科幻影像通过将主体范式赋予类人他者塑造人类镜像,建立起他者视角对主体的观看,也即在人类主体范式标准下自己对自己的反观。然而,经由他者镜像的自我反观更多地呈现出人性的负面,人类主体的范式标准在科幻叙事中产生动摇。正如《银翼杀手》复制人制造商泰瑞公司的广告语所言,类人他者反而“比人类更像人类”。科幻叙事对人类主体的批判反思得到了形象化的视觉表达。
类人他者的镜像建构是科幻叙事展开的基础,由此直接生成的人类主体性批判反思是科幻影像追问“人是什么”的第一步。这种思考在科幻影像类人他者叙事建构中表现为特殊的张力:类人他者既是趋同的主体镜像,又是差异性的“他者”存在。类人他者具有相应的主体性,作为人类的镜像而存在,不等同于一般存在物。对类人他者主体性的消解(降为一般存在)或建立(与人相对的他者),成为叙事建构的内在矛盾范式所在。人类主体和类人他者本体差异的设立与消解,构成科幻类人他者影像叙事的两种进路,折射出不同的观点立场。
在前一种进路中,人类主体性的失范并不能撼动人之为人的存在之根,人类主体与类人他者之间有着无法复刻的本体性差异,确证并巩固了人类主体的边界。科幻影像中的类人他者同时也是技术他者,依凭不同的技术手段模塑成型。科幻叙事将类人他者与人类主体之间可能的本体差异,设定融合在不同的技术特性之中。《银翼杀手》中的复制人诞生于生物基因的复制,同时也受限于基因条件的有限改写:复制人仅有四年寿命。与寿命密切相连的是“记忆”。记忆是人类的情感寄托,是塑造主体的生命体验,正是不同的记忆造就了主体的内在独特性。复制人短暂寿命造成的感情缺失通过植入记忆得到弥补,然而缺失了属“我”的记忆,也就被剥夺了主体自主生成的可能。自哲学初始,记忆就与灵魂问题同根而生,从柏拉图的“回忆说”、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记忆”,到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记忆观念,“从承载者来看,记忆曾被作为灵魂、心灵与意识等承载者的衍生现象;从规定性来看,记忆曾被看作灵魂的状态、心理现象以及意识行为”,都与人的自我、主体性问题密切相关。因而《银翼杀手》用“记忆”来划分人类与类人他者的本体界限,只有人类体的记忆才是真实的,是完全属己的,复制人没有自主记忆,也就不能谈及灵魂。
《人工智能》中的大卫在技术本质上是一个遵从程序设定的AI儿童机器人,不完全的自主意识与主体能动性构成其与人类主体的本体差异。在这种技术特质下,大卫是可复制、可重复生产的,大卫只是千千万万个“大卫”之一。自柏拉图以来,命名就成为归属和存在的问题,“命名一个事物等于宣告了它存在的权力”。然而人类赋予大卫名字却又剥夺了他作为独一无二的存在的权力,根源就在于人类主体的存在不是当下命定而是流动生成:“我们的生存是项艰巨的任务,是严肃的、有待完成的东西。它不是被给予我的现成之物;我得去‘做成’它。”流动生成的生命必然是独特而不可复制的。科幻影像通过类人他者的镜像塑造达到主体反思和批判的目的,往往还要对二者间的主体边界加以界定,重新确证人类的主体性。换句话说,是以类人他者镜像叙事,探询人类主体之变与不可改变。所不可改变的,作为人类主体不可替代的存在之根,如“记忆”之于《银翼杀手》,“生命生成性”之于《人工智能》,是影片关于“什么是人”的最深层解答。
与此相反,第二种叙事进路并不提供一个明晰的回答,而是对人类主体与类人他者之间的本体差异进行解构。《机械姬》里艾娃是具有完全自主意识和人类智能的赛博格人工智能,能够生成自己的目的(获得自由)并以自我意志作为行为的内在驱动。艾娃完全依照自然人的范式被塑造,除了赛博格身体的暴露不断提示和强调着本体的不同——在透明的躯干里,电子金属血管与内脏发着幽幽的蓝光。《机械姬》对类人他者外在身体差异的强化呈现远甚于《人工智能》和《银翼杀手》,这恰恰是内在趋同的明证。如果没有暴露的赛博格身体,在视效表达上类人他者将与人类主体无异,也就削弱了二者间的内在张力。为了达到自由的目的,艾娃伪装、操控,利用程序员的感情步步为营,最后的程序步骤完全是反人类的设计。但是在这部影片中,也可以反问:人有道德情感吗?艾娃所不具备的道德情感,人类也同样缺失;人类主体所具有的一切,艾娃都已拥有。最后艾娃在镜子前为每一寸裸露的赛博格身体贴上人造皮肤,服装穿戴整齐,完成了踏入人类社会前的自我成人仪式,也完成了影片叙事中类人他者与人类主体间差异的最后解构。
人本主义观念下的主体,洋溢着伦理、道德和人格的先天优越性。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如果人成了第一性的和真正的一般主体,那就意味着:人成为那种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这种存在者之上。人成为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与海德格尔对人类学的否定态度相一致,科幻影像对人类主体稳固的先天优越性进行了质疑:在类人他者的镜像展演中,人类主体是否还能对自身加以认同?
《银翼杀手》从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改编而来,原作者菲利普·K·迪克曾说:“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的主题是德卡在追捕人造人的过程中越来越丧失人性,而与此同时,人造人却逐渐显露出更加人性的一面。最后,德卡必须扪心自问:我在做什么?我和他们之间的不同本质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不同,那么我到底是谁?”所以我们看到,《银翼杀手》片尾,德卡在门口看到一只曾经出现在梦中的独角兽折纸,引发了他对自身也是一个复制人的怀疑;《机械姬》中,看到机器人能够取下自己的皮肤露出下面的赛博格本体,程序员也产生了对自体的怀疑,他用刀片割开皮肤,直到血液流出。主体对自身的焦虑和怀疑,来自对类人他者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恰恰否定了人类独有的最高等级主体地位,同时确证了类人他者的主体性存在。
然而,第一种进路中本体性差异的建立是对类人他者主体性的消解。这意味着对人类主体性的确证。矛盾在于,作为人类镜像而得到塑造的类人他者本被赋予主体性,却又在本体差异中被剥夺了与人同等的主体合法性。这个矛盾导致类人他者主体性消解的过程必然充满人的主体焦虑,在认同的迷失中来回摇摆。这一进路的科幻影像叙事,虽然最终没有建立起类人他者的主体性,但对人类主体本身已充满深深的犹疑。
本体差异的解构是人类主体焦虑的最大化表现。在《机械姬》的最后一个画面,艾娃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再也无法辨别。进入人类生活世界的艾娃,与人类有何区别?如果承认艾娃是人,那么人是什么?《机械姬》的类人他者镜像叙事对人性主体进行了批判,但最后的主体性差异不再被建构起来。主体界限瓦解,主体迷失在对类人他者主体的认同之中:“只要像人一样行动,便具有被这一常理掩护的权力,我们正是据此假设他者的主体性”。在认同关系中,类人他者主体性在人的承认和确证中建立,从类人他者成为人类他者,从人类镜像变为镜像人类,从“类人他者-主体”关系转变为“主体-主体”关系。在这一叙事进路中,类人他者主体被确证为相对人类(旧)主体而言的后(新)人类主体,成为人类主体迷失和后人类主体生成的双重隐喻。

图1.电影《银翼杀手》剧照
二、“忒修斯之船”情结:人类主体范式的自我博弈
在主体反思的矛盾范式中,两条叙事进路的人类主体都走向了毁灭。《银翼杀手》中回侵地球的罗伊一举杀死造物主泰勒;《机械姬》里艾娃杀死研发者纳森,留下程序员坐以待毙;《人工智能》直接以两千年的时间跨度,宣告人类灭绝,未来地球进入智能机器统治的时期。
第一种叙事进路下,人类的毁灭更多表达的是在人类主体标准范式下对人类主体堕落性变化的拒绝和警示,是一种在主体焦虑和迷失中呼唤自救的姿态。这类科幻影像通过本体性差异的设定,仍然在寻找人类主体不变的本质,并为这种人性的失落而感到怀旧。失落的人性在镜像他者身上失而复得,人类主体则在他者认同中怅然若失。
人性怀旧情绪在科幻叙事中并不罕见。自称“狂热的技术主义者”、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提倡“硬科幻”的刘慈欣,同时却充满浪漫情感和理想主义。美籍华裔科幻作家、《三体》英文翻译者刘宇昆的《奇点移民》讲述的是奇点时代来临,人类可以把意识上载到机器,意识脱离身体,人类离开现实世界。然而作品还在质疑,当一切变得无法体验,“无法像人类那样死去,被活死人掠走,变成无尽的运算循环和无意义的数据记录的一部分”,可以被数字化重新加载的人是否仍然是人?
“怀旧”实际上是旧范式正在成为过去,而新范式尚未生成的过程中所无可避免的逡巡,一种在更替流变中仍期待维持原状的“忒修斯之船”情结。科幻影像类人他者叙事的第二种进路作出了选择:人类主体的毁灭,是后人类主体取代人类主体而存在的象征,从而将目光转向新的生成。“后人类主体的出现意味着‘人’的终结。”这种终结必然是一种新生,因为“死亡是一种新的程序形式——或外在化,也就是一种新的启动。这种新型程序虽然不是不可编序的,但是它至少是不确实、不确定和开放性的”,旧有的人类范式由此被敞开,转向了新的可能。
因此,科幻影像的两种叙事进路本质上都是人类主体范式自我博弈的表现。科幻影像通过塑造类人他者来暴露人类主体存在的问题,同时在类人他者身上尝试寻找人类主体范式的新可能。刘慈欣认为“写科幻小说就是一场思想实验”,那么小而化之,科幻类人他者叙事就是对人类主体的自我实验和自我博弈——假如存在另一个主体(镜像),与人相同甚至比人类更加优化,依照人类唯我独尊的本性,人类还会认同自身吗?又将依据什么而坚守自我?“如果借助我们发明的东西,我们能够事实上等同于或者超越我们自己,这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发明的东西会发现我们是没用的、甚至对它们来说一无是处吗?”另一方面,对类人他者的镜像塑造已经带入了人类的自我想象,借此想象新的主体可能。人类主体范式自我博弈在影像中就表现为人类主体与镜像他者之间既肯定又否定、既认同又迷失的摇摆状态,博弈的是人类主体的变与不变、可变之多寡、已知和未知,稳固封闭或是能够进行优化改变。
在这个博弈过程中,类人他者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形象或造型,其功能是构造性的,是辅助人类主体完成自我认同和自我建构的镜子。在拉康看来,“镜子承载的不是简单的复现,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映射,‘我’通过对自身或他人作镜像的考察,从而看到的理想自我的形象。”然而,不同于婴儿对主体的“误认”,科幻叙事在主体焦虑中打破认同的迷梦,通过类人他者的外化形塑,同时指认出主体的滑落和镜像的分裂,既在镜像反思中完成对自我主体的批判与追问,又在他者迷失中进行主体的自我推翻与重构。如果说“银幕空间作为一种镜式空间具有某种拓扑学功能,就是让观看主体在想象的空间和真实的空间之间往返地位移”,那么科幻影像类人他者的叙事建构就是银幕的银幕、镜子的镜子,人类主体和类人他者之间“通过此处和彼处的循环变换而达至此与彼的界限的消融”,共同完成影片对人类主体的反思与建构想象。
在这种看似二分、实则合一的镜像关系里,类人他者相对主体异化、主体相对类人他者异化。科幻的人类主体反思和后人类主体探索,就呈现为这种双重异化的影像表达。最后以主体毁灭、镜像延续的颠覆性叙事,寓言了后人类主体的到来。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伊哈布·哈桑认为,“后人类是一种创造性的、普罗米修斯式的魔法精灵,与技术密切相关并处于发展之中,只遵从变化之规律,具有尼采式的任务,将人类推进到人文主义可怕的压迫性的‘人类’阶段之外。”也就是说,后人类具有“超人”属性,必然超越人文主义的主体性范围。在人文主义语境中,人类理所当然地占据一切事物的中心、一切等级序列的制高点,以与其他事物之间的明确界线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地位。而科幻影像以类人他者的镜像建构方式,在其叙事语境中直接破除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和人类主体界线,质疑和反思人类本质及其主体性合法性,建立起与后人类主义立场的同一关系。
所 谓 “ 后 人 类 主 义 ”(Posthumanism)有双重含义:作为“后-人文主义”(p o s thumanism)是对历史、记忆及传统的反思与批判,而作为“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则是面向未来的想象和筹划。科幻影像类人他者叙事建构将这两个维度都包含在其中,并体现着后人类思想所面临的处境,与尚未存在之物进行着未有胜负的博弈,表现为怀旧或是走向后人类的寓言。
三、“维特鲁威”人的技术未来:后人类寓言
科幻影像类人他者叙事建构对人类主体性的反思与后人类主义有着内在一致性。在主体概念的解构中出现新的技术性生成。
首先,后人类主义消除了主体的稳定性和自身统一性,打碎乃至颠覆主体所谓的完善稳固,并进行新的主体思考和构建。用罗西·布拉依多蒂的话来说,后人类对一直以来被视为当然的人的本质构成属性提出质疑,“我们自然地把自己看做人类的一员,仿佛人是一个事实、一种既定的东西,并且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围绕着人的种种权利概念。但是情况果真如此吗?”并且要提出一种思维方式的质变,重新思考我们自己是谁。

图2.电影《三体》剧照
“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固定内涵和明确外延的概念。然而,“大写的‘他’居于一切的开端”,“人”的古典理念最早由普罗塔哥拉确立为“万物的尺度”,经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被确立为完美和理性的标准,主体的界限被稳固地圈定出来。以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为象征,“对人类理性具有独一无二、自我调整和本质高尚的各种力量的信仰构成了人文主义兴盛期信条的核心部分”。在科幻叙事中,这些信条在类人他者(镜像主体)和人类主体之间时隐时灭、互为解构。科幻的质疑正如利奥塔所言:“人文主义,以诸多的方式提出诸多训诫,经常互不相容……人总好像至少有一种可靠的价值,它不需要被查问。”同样,科幻影像叙事通过类人他者的镜像建构进行了这项“查问”。
科幻影像中人类主体的毁灭,呼应了福柯提出的“人之死”断言。福柯质疑人的本质,认为人类是历史化的产物,“是最近的一种发明”,而下一阶段的历史产物必将取代这一历史阶段的人类本身:“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所以在科幻叙事里,类人他者正在成为下一历史阶段后(新)人类主体的象征,现在和过去的人类主体将被抹去。
因此,科幻的后人类寓言是面向生成和未知的开放。在海德格尔看来,人在本质上存在于存在的开放性中,“人类的主体性在一向不曾是,将来也决不会是历史性的人的开端性本质的唯一可能性”。海德格尔虽然对古希腊人向存在者敞开、与存在者在“在场”中照面的主体性充满追思与怀旧,但他知道那只是一种选择,尚未存在的新可能已在生成之中。在人的主体性之转变过程中,海德格尔敏锐察觉到现代技术的构成性力量。人类通过科学实验掌握事物本质规律,发明现代技术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与古代技术相比,现代技术是程序复杂又环环相扣的精密进程,人类通过计算和规划,控制每一环节的进行。人类主体性因为掌握强大技术看似无所不能而日益膨胀。海德格尔却从中看到了危险。他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Gestell),是一种促逼。它促逼着人促逼存在物,把它们订造为持存物而存在。真正的危险就在于,人其实也是技术订造的一环,而且必然是比物更原始地受到促逼,成为失却本质的持存物。现代技术使物的本质发生改变,同时也改变了人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对技术的把握是一种博弈,主体性的博弈。海德格尔呼吁救渡,但对于新的主体性如何,他返归源头的思考透露着怀旧的希望。
尽管如此,海德格尔转变了传统形而上学对主体性的理解,存在的问题成为技术的问题,将技术纳入人的本体思考并延续这种技术本体之思。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指出:人是没有本质的动物。“所谓本质,在此就是指偶然性、缺乏性能。”柏拉图在以普罗塔戈拉斯命名的对话中,借普罗塔戈拉斯之口讲述了爱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即爱比米修斯为每一种动物分配性能,使其能够生存而不至灭亡,分配完毕后唯独遗忘了人类。于是人类赤身裸体,无尖齿利爪,无一技之长。为了弥补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普罗米修斯从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盗取了火和技术的创造机能,使人类得到挽救。斯蒂格勒借助这两个神话,说明先天性的缺陷决定人需要技术性的补足,技术构成人本质的一部分。和动物获得的各种性能相对应,人的那一份就是技术。
在斯蒂格勒的技术意义上,人类向来就是“后人类”。 后人类主体必然是技术性的主体。这就是后人类的第二层内容。在本质主义遭到否定的同时,“技术”也从漫长思想史中浮现,在理性主义哲学思辨中不再缺席,技术之于人的内在关系得到了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重新思考。现实层面上的发展变化,则是推动思想转折的直接动力。伴随四次科技革命,技术如海德格尔所预言成为世界的“座架”,人类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都建构在技术座架之上。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纳米科学与技术(Nanotechnology)、包括生物制药及基因工程在内的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包括先进计算与通信的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包含认知神经科学的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四大前沿会聚技术(NBIC)迅速发展,使人类实现了对自身的重新认识,也为提升改造人类自体提供了技术可能。赛博格(Cyborg)作为人类主体身体完整性的打破与混杂技术,已经从科幻走进了现实,从“穿戴式仿生设备”到人工心脏、人工角膜、人工耳蜗,到芯片植入、脑机接口,技术具身实现了人类官能的完善和主体能力的提高。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全面覆盖的网络信息环境也已经把每个主体都变成了赛博格,通过电子媒介,人类主体和电子虚拟相连接,形成“终端身份”(terminal identity):“一种显而易见的双重关联,其中我们既看到主体的终结,又看到围绕电脑站和电视荧幕构建起的新的主体性。”技术与人类主体有着越来越复杂的交融互构,“技术已经介入其中,并且技术与产物的身份交织缠绕,以至于不再可能将它与完整意义上的人类主体分离开来”。
不难看出,人类对技术的追求始终包含在对自我完善的追求之中。在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看来,人类使用技术有两大原因:弥补自我缺陷和增强提升自我。这种弥补和提升,就呈现在科幻影像对类人他者的塑造上。类人他者同时也是技术他者,作为人类镜像,其是对技术性主体的揭示和进一步的寓言。与此同时,类人他者和人类主体之间的博弈胶着关系,反映了人类对技术的内化渴求和内在矛盾:既希望成为技术他者、拥有技术所带来的力量和转化,又希望自己与技术他者不完全相同。所以在科幻影像中,“仿生人(bionic being)不管是男是女,都被设计出新的技术部件。这些部件不同于现有的部件,弥补了被取代的部件的缺陷。这些合成的生物比以前的生物物种更有力和更完美,它们反映的恰恰是前面提到的技术梦想。仿生人变成了技术和生活的完美结合,它们简直就是超级存在者(superbeing),它们也把自己当成了超级存在者。技术不再是一种技术,而是变成了一种(更完美)的人。”这在科幻影像类人他者的镜像意义上,正意味着过去的“维特鲁威人”向“更完美”的后人类技术性主体敞开自身的无限可能。
关于“技术”的思考让人类主体的神话得到祛魅。由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人作为没有性能因而没有宿命的缺陷性存在,“必须不断地发明、实现和创造自己的性能”,所以德日进说“人类的演进看来显然完全落在精确计算的可能性之外。”在无法被确切预知的一切中,人类“向死而生”,对自己的终结形成了有所知又无所知的超前。人类未来的前景,在模糊不清的“期待(elpis)中得到勾画。所谓“期待”,因而也就是未来的超前到来,是科幻影像所寓言和“期待”的技术后人类未来。
结语
科幻影像以其特有的技术想象优势塑造出各式各样的类人他者,通过对类人他者的镜像观照,反思批判技术时代下人类主体在精神、情感、思想、心智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因为科幻影像在塑造类人他者时,最初是以人为范本,自然面临着“什么是人”、用什么定义人的本质问题。不同科幻想象提供了不同答案,如记忆、意识、思维、感情等。对于镜像他者主体性,第一种科幻叙事进路通过设定类人他者与人类主体间的本体差异,消解其主体可能;第二种科幻叙事进路则解构本体差异,将类人他者建构为独立的主体。然而,这两条叙事进路都行进在主体焦虑中,质疑或否定了人类主体边界的合法性,在不同程度上确立起类人他者的主体地位。由此在主体的矛盾范式中展开内在博弈,最后以人类主体的想象性毁灭,预言了新的后人类技术主体的到来。
刘慈欣认为,“科幻的作用就在于它能从一个我们平常看不到的尺度来看”,这就是“科幻的思维”。科幻影像类人他者镜像叙事就是科幻思维的一种具体化呈现,通过塑造人类他者形成对人类自我主体的“他者视角”观看,并将后人类主体思考外化为两种主体范式的自我博弈过程。
科幻思维是一种超越既成道德和文化观念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思维相比,科幻思维因为不受精确性、实证性的要求和公式理论束缚而有更广阔自由的试验空间;与历史思维相比,科幻思维无需受限于过去的、真实的时间和空间,而是可以面向无限可能的未来;与哲学思维相比,科幻思维是非抽象的,可以转变为直观可感的科幻现象,从而更具有现实影响力。与此同时,科幻思维对技术的研究和思考从不脱离人的维度。科幻对人类主体性的思考完成了从人文主义到后人类主义的转变,过去毫无疑问附庸于人类的技术在这种转变中获得了新的复杂性,被揭示为人类主体的本质性构成。
科幻影像类人他者镜像叙事与后人类主义有着内在统一性。后人类主义是对人文主义规约下的人类主体性反思,也是对未来人类技术性主体生成的构想和展望,从而将人类主体解构为流动的生成、丰富的无限。科幻影像和后人类主义一样,打开并预示着未来的无限可能。于是“期望”(elpis)和“预见”变得重要,并成为担负着人类未来抉择的“进化”责任,因为“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会变成后人类,因为后人类性质已经存在。相反,问题是我们将会变成哪一种后人类”。然而,与后人类困境相仿,“在这个世界中,人类探索未来的意识总是在普罗米修斯的准确的先知和他的兄弟的完全盲目(后知)之间摇摆不定”,在未知的尚未存在和未来的尚在生成之中,科幻影像叙事也在主体性怀旧和后人类寓言之间逡巡。
【注释】
① 杨俊蕾.升级未来:科幻影像中的人工智能儿童机问题举要.学术论坛[J].2020(04):16-22.
② 秦喜清.我,机器人,人类的未来——漫谈人工智能科幻电影[J].当代电影,2016(02):60-65.
③ 杨庆峰.通过记忆哲学反思人类增强[EB/OL].http://cssn.cn/kxk/202008/t20200825_5173764.shtml.
④陈希洋.“后人类”语境下科幻电影对“主体性”的探讨——以《她》与《机械姬》为例[J].艺苑,2019(01):63-65.
⑤ 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274.
⑥ 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A].孙周兴编译.存在的天命——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文选[C].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54-55.
⑦ 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人类学”,即“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论”。参考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A].孙周兴编译.存在的天命——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文选[C].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58.
⑧ Mtime时光网[EB/OL].http://movie.mtime.com/12466/behind_the_scene.html#text_5.
⑨ Donna Kornhaber.From Posthuman to Postcinema:Crises of Subjecthood and Representation in Her
[J].Cinema Journal,2017:56(4).⑩刘宇昆.奇点遗民[M].耿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⑪杨一铎.后人类主义:人文主义的消解和技术主义建构[J].社会科学家,2012(11):38-41.
⑫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208.
⑬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22.
⑭韦语斯.论拉康“镜像阶段”及相关主体理论[D].吉林大学,2015.
⑮吴琼.电影院:一种拉康式的阅读[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06):34-43.
⑯Weinstone、Ann.Avatar Bodies:A Tantra for Posthumanism
[M].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4:8.⑰罗西-布拉依多蒂.后人类[M].宋根成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1.
⑱同17,18.
⑲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M].罗国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
⑳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506.
㉑同6,71.
㉒同12,208.
㉓ Scott Bukatman.Terminal Identity:The Virtual Subject in Postmodern Science Fiction
[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9.㉔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6.
㉕㉜同13,122.
㉖同12,209.
㉗德日进.人的未来[M].许泽民、陈维政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3.
㉘“期待(elpis)”是斯蒂格勒的概念,是普罗米修斯原则(先见之明)和爱比米修斯原则(后知后觉)二者之间的张力或结构,意味着超前和时间。详见: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212-214.
㉙ 刘慈欣、江晓原. 刘慈欣:你关心人性,我关心生存[EB/OL].https://www.guancha.cn/LiuCiXin/2019_02_13_489922_s.shtml.
㉚同27,185.
㉛同24,331.
㉜同22,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