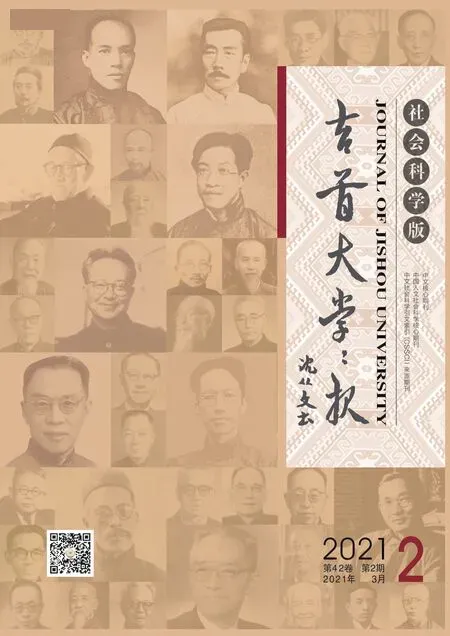郭象玄学的礼学特质*
罗 彩
(广东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汉末以降,礼逐渐流于外在形式化、虚伪化,而使“名教”陷入危机。魏晋玄学家们试图以道家之“自然”来解救儒家之“名教”存在的危机,以此建构一种合乎“自然”的新礼教秩序。作为魏晋玄学集大成的郭象,看重礼之教化治国的实用功效,将礼内化为个体自性的内容,强调对真实道德情感的“礼意”的回归,用性本论为礼的合理化存在寻求形上依据,同时把个体的“各安其性”“各守其分”视为对天然秩序的遵循,把君主的“圣王合一”“游外冥内”视为对天然秩序的践行,从而建构起其独具礼学特质的玄学思想体系。
一、仁义为个体自性之内容的性本论——礼之形上基础的建构
王弼以“无”为本,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以此调和儒家之“名教”与道家之“自然”的矛盾。但其对“无”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体和具体事物之间的隔阂,仁义之礼也沦为普遍道德本体的抽象化、超验化概念[1]。有鉴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的虚伪,嵇康和阮籍等竹林名士更是以激进的方式批判礼教,高扬个体情性,即所谓“非汤武而薄周公”“礼岂为我辈设也”。他们以一种违背礼教的方式与虚伪的名教相抗争,虽凸显了真实道德意识的重要性,但并没从本质上解决“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元康名士则打着“贵无派”的旗号走到了极端,他们虚诞放达,无所事事,甚至裸裎戏谑,破坏了社会礼法秩序,对当时政治危害极大。基于此,如何把自然本性与仁义之礼结合起来成了当时最紧要的时代任务。
郭象为解决“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消除“贵无论”导致的本体与具体事物之间的隔阂,提出了“自生说”。他说:
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无,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2]50
在郭象看来,抽象的“无”与“有”皆不是万物的本体,都不能生物,万物是自生的。万物生成变化是自然而然的。“自然”就是万物各自的本性,即“言自然则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2]694。自然本性亦被称为“本”,所谓“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2]9,“夫物各有足,足于本也”[2]239。万物不分大小,皆以适性为足,物各自足,足于“本”也。合而言之,“性”即“本”也,这就将“性”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3]。
郭象以性本论为基础,进一步将仁义之礼内化为个体自性的内容,并强调时人不能执著于礼的外在形式,而要回归礼的真实道德情感——“礼意”。他说:
夫仁义者,人之性也。人性有变,古今不同也。故游寄而过去则冥,若滞而系于一方则见。见则伪生,伪生而责多矣。随时而变,无常迹也。有为则非仁义。[2]522
夫知礼意者,必游外以经内,守母以存子,称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声,牵乎形制,则孝不任诚,慈不任实,父子兄弟,怀情相欺,岂礼之大意哉![2]267
夫圣迹既彰,则仁义不真而礼乐离性,徒得其形表而已矣。有圣人即有斯弊,吾若是何哉![2]337
这里,郭象将仁义视为自然人性的内容,认为仁义之礼跟天地万物一样,也是自然而然自生的,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若世人执守于过时的礼之外在形迹,则会导致“礼意”本质的丧失而陷入伪礼的弊端中,所谓“礼乐离性,徒得其形表而已矣”。由此可见,在郭象看来,现实社会的仁义礼序从它的发端开始,就是天成于自然秩序,而对礼意的回归与真礼的践行就是对自然人性的成就。故他说:“德者,得其性也;礼者,体其情也。情有可(所)耻而性有所本。得其性,则本至;体其情,则知至。知耻则无刑而自齐;本至则无制而自正。是以‘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4]“刑者,治之体,非我为。礼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知者,时之动,非我唱。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2]244刑的产生是源于社会治理的需要,礼的产生是社会自然运行的结果,知是随时代的变化自然衍生的,德也是万物之情的自然流露,人类社会这一肌体与天地万物一样自然运行,遵循着自然界的客观准则,与时变化,有统有序。同时,礼作为个体自性的内容,得性体情本是礼之初衷,只是世人往往执著于追求礼的外在形式而导致礼的失真。
此外,郭象还主张礼产生于“约定俗成”,故他一再强调要“因俗”“顺俗”与“变俗”。他说:
直是陈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为安故而习常也。[2]941
时变则俗情亦变,乘物以游心者,岂异于俗哉![2]944
言俗不为尊严于君亲而从俗,俗不谓之谄,明尊严不足以服物,则服物者更在于从俗也。是以圣人未尝独异于世,必与时消息,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岂有背俗而用我哉![2]453
在郭象看来,礼是由共同习俗与习惯自然形成,不是为君亲而设,是人们共同遵循的自然法则,是为满足人们生活安定的需要而产生的,即“约定俗成”,圣人只是“因俗”“顺俗”而已。同时,礼既源于“约定俗成”,而“俗”又是与时变化,故礼也要与俗俱变,即“与时消息,在皇为皇,在王为王”,才不至于沦为过时的形迹而丧失内在的礼意精神。
由此可知,郭象在确立自然之性的本体地位基础上,将仁义之礼安放到个体自性的内部,并认为现实社会之礼是源于众人意愿的“民俗”“习惯”(符合众人之性)自生的结果。它的存在与天地万物有序运行一样自然而然,发乎天光,合乎情性。因此,礼序就是天序,或者说是天序的自然延伸。这就为礼寻求到了合理化存在的形上依据,同时也消除了本体与具体事物之间的隔阂。
二、“依性而为即自为”“安性守分即逍遥”的性分论——礼之教化向度的阐释
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派”为挽救元康名士虚浮放荡之风给当时社会与政治造成的严重危害,主张“无”是什么都没有的“零”,是不能生“有”的,而“有”是自生的。裴頠着眼于现实,在“崇有”的基础上,认为礼法名教本身也是自生的“有”,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所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餐,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无过用”[5]1044,其意在强调礼之外在规范对于重整当时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但裴頠的理论并不为当时士人所接受,也未能给名教提供心性论方面的论证。那么问题的症结何在?正如东晋戴逵所说:
且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怀情丧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者,欲以笃实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检之行。情礼俱亏,则仰咏兼忘,其弊必至于本薄。夫伪薄者,非二本之失,而为弊者必托二本以自通。[5]2458
儒家之礼应是内在真实道德情感的礼质与外在社会规范的礼文的统一,如果丧失了真实道德情感,就会出现表面和形式上守礼的虚假行为。道家反对外在形式的礼仪规范,倡导笃实和内心的真诚,但难免又容易出现有些人打着道家的旗号实行越礼纵欲之行为,最终导致情礼俱失,作为礼质的真实道德情感反而得不到落实。嵇康、阮籍为反对仅有外在形式的虚伪名教而主张因任自然情性的放达人生,这被元康名士发挥到虚浮放诞的极端而致“情礼俱亏”“至于本薄”。裴頠有见于元康名士虚浮放诞之害而凸显礼之外在规范,但外在形式之礼文若无重视真实道德情感之礼质的心性修养功夫,亦难防“容貌相欺”“至于末伪”之祸。
为解决这一难题,郭象结合老庄“人性自然”论与黄老“名分”说提出了性分论的思想[6],以此统一作为真实道德情感的礼质和作为外在社会规范的礼文。他说:
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2]128
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终,而愚者抱愚以至死,岂有能中易其性者也。[2]65
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则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夫臣妾但各当其分耳,未为不足以相治也。相治也,若手足耳目,四肢百体,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夫时之所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岂有递哉!虽无错于当而必自当也。[2]64
每个事物自生而各得性分。性分(才能/等级/职位/禀赋等)是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不可加,不可逃,亦不可改变。这里,郭象否定了一切外在造物者的存在,认为事物的性分就是其存在的依据和原因,大鹏之能高,斥鷃之能下,椿木之能短,皆由其性分所定。此外,就连君臣夫妇尊卑上下之“分”也如天地、手足耳目、四肢百体各司其职发挥自己的固有功能一样,属于天理自然。可见,郭象的“性分”中既有才智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的君臣夫妇及尊卑上下等礼的外在规范。这样就大大扩展了“自然本性”的范围,将先天的自然本性与后天社会的名分思想融为一体了。在郭象这里,“仁义之礼”乃人的“自然之性”,尽“自然之性”,则自然地显示自然分位,所谓“夫尊卑先后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无也,非但人伦所尚也”[2]475。尊卑先后之序既是人伦,也是天序,它们是自然存在的,非某种强权意志加以维持的结果[7],更不是人为刻意设立的结果,而是万事万物自然而然都具有的至理与运行规则。
由此可见,在郭象看来,人伦即天序,个体对礼序(礼的外在规范)的遵循即是对自然之性的成就,所谓“参天地之化育”。但郭象也强调个体对礼的外在规范的遵循不是无条件的,应“依乎本性”,随顺自然,强调物之“自为”与“自正”。他说:
夫为为者不能为,而为自为耳;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则知出于不知矣;自为耳,不为也,不为也则为出于不为矣。[2]229
用其自用,为其自为,恣其性内而无纤芥于分外,此无为之至易也。[2]190
郭象认为,“为为”者不是在于“为”,而在于“自为”,“为知”者不是在于“知”,而在于“自知”;“为”出于“不为”,“自为”乃“不为”;“知”出于“不知”,“自知”乃“不知”。在郭象看来,根据性分所允许的“为”即是“自为”。“自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依性”“顺性”与“安性”的一种特殊的“为”。这种特殊的“为”就等同于“无为”,以此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地。这就将“无为”与“有为”统一了起来。这正如郭象所说“凡自为者,皆无事之业也”[2]662,“率性而动,故谓之无为也”[2]470。可见,郭象的“依性而为即自为”重在凸显“性分”之“无”的功能意义,即“无”不是“空无”,只是让事物完全的、毫无隐蔽地按其性分自然生成与变化,不受外在事物干扰地按照本来面目存在而不被异变。故个体对礼之外在道德规范的遵循也是如此,更应注重对礼之真实道德情感的回归,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礼发生异变。这正如郭象所说“质全而仁义者”[2]525,“仁者,兼爱之名耳;无爱,故无所称仁”[2]467。
如果说,郭象性分论中“依性而为即自为”的思想意在强调个体应注重礼之真实道德情感(自然之性)的话,那么,“安性”“守分”的心性修养功夫则更侧重个体对礼之外在社会规范(名分)的遵循。他说:
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2]1
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涂也;如斯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所遇斯乘,又将恶乎待!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苟有待焉,则虽列子之轻妙,犹不能以无风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而况大鹏乎!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2]23
在郭象看来,每个事物与个体都有自己不同的“性分”与“理”,性分没有大小优劣之别,所谓“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即可。不管是像大鹏乘风而行的“有待自通”还是神人圣人的“无待常通”,只要行为与自己的位分相匹配,并安于自己的位分,不越出自己本分的范围去羡慕效仿他人,那么,从足性与得性的角度看,均可冥极逍遥、道通为一,没有本质区别。可见,达至逍遥的关键在于“安性”“守分”的心性修养功夫。而这最终是为了教导众人更好地在践行礼之外在社会规范与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范围内实现有限的个体自由。
为此,郭象先以牛马之性来作铺垫。他注《庄子·秋水》“(河伯)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说:“人之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2]590按照庄子本意,光着身子的牛马属于自然,被穿了鼻子套上笼头给人乘骑的牛马属于人为。庄子以此抨击人为而推崇自然。而到了郭象这里,却变成了牛被穿鼻、马被带笼头恰恰是体现和成就了牛马供人乘骑受人役使的性分。人类驯服牛马不是人为,而是顺应牛马的自然本性。在此基础上,郭象进一步引申到人之性分。在他看来,君臣夫妇尊卑上下的礼之外在规范与等级秩序都成了天理自然。他说:
夫时之所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谓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2]58
凡得真性,用其自为者,虽复皂隶,犹不顾毁誉而自安其业。故知与不知,皆自若也。若乃开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丧其真,人忘其本,则毁誉之间,俯仰失错也。[2]64
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鸟兽万物,各足于所受;帝尧许由,各静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实,又何所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尧许之行虽异,其于逍遥一也。[2]29
这里,郭象认为,个体只有安于自己的“性分”,即“安其所司”“足于所受”“静其所遇”才不至于越其位分以失真性。这是达至逍遥境地的必备修养功夫。而“安性”“守分”则具体表现为对君臣上下尊卑之礼的外在规范的遵循与践行。也就是说,无论个体在现实中处于什么样的位分,都具有天然合理性,无法改变,对礼序的遵循即是对自然人性的成就。可见,“安性守分即逍遥”的心性修养功夫重在凸显“性分”之“有”的功用意义,目的是为了避免“以下冒上,物丧其真”的局面,以此实现“贤愚袭情而贵贱履位,君臣上下,莫匪尔极”[2]385的社会秩序。至此,郭象先是将仁义之礼安放到个体自性内部,因此践行礼的精神(礼意)即是依性而为的“自为”;同时又进一步以“安性守分即逍遥”的心性修养功夫来保证礼之外在规范的实行,认为人人“各安其性”“各守其分”“各司其职”的循礼就可得性与逍遥。这就实现了从礼的内外两个向度展开对礼之教化功用的阐发。
综合而言,郭象的性分论以天地万物个体之性皆“自生”为起点,以“依性而为即自为”为原则,以“安性”“守分”为实践路径,以足性逍遥为最终境界,其实质是对礼之教化向度的另类阐释。这既为维护封建纲常名教提供了理论依据,又为每个个体实现有限的逍遥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性。
三、“神人即圣王”“游外即冥内”的圣王观——礼之治国向度的阐释
为匡正“贵无派”带来的虚浮放诞之风,郭象对圣王形象的设定,虽冠以道家“无为”之名,但又以儒家“无不为”的观念加以解释,重在发挥礼之治国的功用,以此重整社会秩序。他注《庄子·逍遥游》中“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句:
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耳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将明世所无由识,故乃托之于绝垠之外,而推之于视听之表耳。处子者,不以外伤内。[2]32
这里,郭象把《庄子》原文中超尘脱俗的“神人”形象进行了改造,将其与“圣人”等同,所谓“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耳”“神人即圣人也,圣言其内,神言其外”[2]937。在郭象看来,圣人无心无欲的内在高深境界正是通过应对外在事务的状态显现出来。圣人虽然表现为务事,实际上却能不累于物而达至“游心”。他说:
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宏)[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见]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夫见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睹其与群物并行,则莫能谓之遗物而离人矣;睹其体化而应务,则莫能谓之坐忘而自得矣。岂直谓圣人不然哉?乃必谓至理之无此……则夫游外(宏)[冥]内之道坦然自明,而《庄子》之书,故是涉俗盖世之谈矣。[2]273
夫游外者依内,离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无以天下为也。是以遗物而后能入群,坐忘而后能应务,愈遗之,愈得之。苟居斯极,则虽欲释之而理固自来,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2]277
郭象认为,游外者必冥内,冥内者必游外。“圣人”并非要远离世俗隐居山林,而是“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与群物并行而遗物离人”“体化应务而坐忘自得”。此外,在郭象看来,《庄子》一书其实是涉俗盖世之谈,所谓“游外者依内”“离人者合俗”,大抵是正言若反之意。因此,“游外”与“冥内”是一致的,不可分割。其实,郭象将“圣人”设计成“外内相冥”的形象,目的仍在追求无为而无不为、天下太平的社会理想,即“故有天下,无以天下为也。是以遗物而后能入群,坐忘而后能应务,愈遗之,愈得之”“所造虽异,其於由无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内”[2]277。所以,在郭象这里,圣人“无为”不再是无所作为地拱默山林,而是身处朝廷、治平天下却又保持淡泊出世的心灵境界。他说:
所谓无为之业,非拱默而已;所谓尘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所以游外共内之意。夫与内冥者,游于外也。独能由外以冥内,任万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于人而侔于天也。[2]276-278
在郭象眼里,圣人和理想的君王几乎没有区别。圣人并非高藐超世不食人间烟火,也不是一味地逃离俗世隐遁山林,恰恰是寓“无为”于“有为”,“外天下”实是“治天下”,“即世间而出世间”。这俨然就是儒家积极入世的理想君王模样。由此,郭象就从“神人即圣人”过渡到“圣人即圣王”,将神人与圣王等同。故郭象对唐尧之类的圣王才抱以大加赞赏的态度,而在这一点与庄子有着很大区别。他注“尧让许由”条: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尧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许由方明既治,则无所代之。而治实由尧,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寻其所况。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尧也;不治而尧得以治者,许由也。斯失之远矣。夫治之由乎不治,为之出乎无为也,取于尧而足,岂借之许由哉!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后得称无为者,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当涂者]自必于有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夫自任者对物,而顺物者与物无对,故尧无对于天下,而许由与稷契为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与物冥者,故群物之所不能离也。[2]27-28
《庄子》原文本意是批评尧之“有为”而赞赏许由之“无为”,而到了郭象这里却相反:他认为尧才是以“不治治之”的“无为”,而许由仅仅拱默于山林并非真正做到“外天下”,其恰恰是“以天下为对”“殉名慕高”的“有为”,因为“治之由乎不治,为之出乎无为”“与物冥者,故群物之所不能离也”。郭象这种冥不离迹、高不离俗的思想完全体现了儒家的“道在百姓日用伦常之间”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旨趣。
郭象之所以主张圣王“不离世间”与“游外必弘内”实是出于强调圣王以礼治天下的必要性。他说:
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赏罚而九,此自然先后之序。治人者必顺序。治道先明天,不为弃赏罚也,但当不失其先后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顺序之道。寄此事于群才,斯乃畜下也。[2]478-479
明夫尊卑先后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无也。言非但人伦所尚也。所以取道,为[其]有序[也]。[2]475
郭象认为,人伦礼序如天序一样自然而然,居于上位的圣王之本性就是要取法自然之道,因任众人之性而使众人践行君臣夫妇尊卑上下之礼序,实现“各得其性”的理想境地。同时,圣王在用天下达至“父父子子各归其所”[2]873“尊卑有别,旅酬有次”[2]165的过程中,根据时势变化纵使不得已采取刑名赏罚或施行仁义教化,都属于“无为”。因此,他说:“昔日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2]384。“夫黄帝非为仁义也,直与物冥,则仁义之迹自见。迹自见,则后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黄帝之迹使物撄也……故夫尧舜者,岂直一尧舜而已哉!是以虽有矜愁之貌,仁义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2]384“比古今,则尧舜无为而汤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机玄发,则古今上下无为,谁有为也。”[2]470也就是说,圣王本不是为了仁义,但在治国过程中仁义之迹自然显现。圣王有为的治国功绩也只是百姓追述过时的圣王之迹给予的名号而已,圣王顺应时代的需要,虽然采取的方式不一,但从全性的角度而言是一样的。因此,郭象本质上是从圣王能够让百姓“各得其性”“各守其分”的角度来阐发礼之治国的功用,所谓“若夫任自然而居当,则贤愚袭情而贵贱履位,君臣上下,莫匪尔极,而天下无患矣”[2]387,“自然应礼,非由忌讳。事以礼[理]接,能否自任,应动而动,无所辞让”[2]408。郭象认为,圣王以礼治天下的原则就是让事事都符合礼序,让众人都处于自己适合的社会分位中,而非逃避与辞让,从而实现“贤愚袭情”“贵贱履位”与“君臣上下,莫匪尔极”的理想礼教秩序。为此,郭象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夫工人无为于刻木而有为于用斧,主上无为于亲事而有为于用臣。臣能亲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当其能,则天理自然,非有为也。若乃主代臣事,则非主矣;臣秉主用,则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则上下咸得而无为之理至矣……但上之无为则用下,下之无为则自用也。[2]470-471
在郭象看来,臣子能亲事、君主能用臣好比斧头能刻木、工匠能用斧一样,就是在自己特定的位分上发挥各自所能,且不能越居位分而行,这是天理自然。这里,郭象用自然分工的不同将社会礼序的等级位分合理化,认为人人只要按照社会固有的位分行事即是无为,所谓“上之无为则用下,下之无为则自用”,并以此实现“君逸臣劳”“君主无为即臣民自为”及“天下自宾”的政治理想。
由此可知,郭象将“神人”与“圣王”等同、“游外”与“冥内”融为一体,重在凸显君主积极有为的特质,是为君主实施以礼治天下奠定理论基础。郭象以其独特的圣王观展开对礼之治国向度的阐发,认为圣王施行仁义礼教使社会众人伦次有等是取法自然之道,亦是符合众人自然本性与社会发展内在需要的无为,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四、结语
郭象玄学的重点与旨归最终体现在其礼学特质上,这与他所处的动荡时代及政治抱负(1)《晋书·郭象传》载郭象“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掾,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薰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论十二篇”。由此可见,郭象不甘于早期清谈之空名,遂待价而沽,后成为司马越之幕僚,先是被辟为司空掾,后被用升至黄门侍郎,最后成为司马越集团身居要职(太傅主薄)的人物之一。息息相关。当时获得短暂稳定的西晋王朝为实现“守天下”的局面,极为看重礼之教化与治国的实用功效,并急于为建立一种重整社会秩序及安顿个人身心的新礼教寻求理论支撑。于是,郭象尝试重建一种符合自然的新礼学,以此纠正汉末以来礼的虚伪化弊端及重拾人们对礼教的信心,并为维护统治阶级封建纲常名教提供一套理论方案。郭象以万物自生的性本论为起点,将仁义之礼纳为自然人性的内容,认为礼是源于自然人性的内在需要或民众约定俗成的结果,这就为礼的合理化存在寻求到了依据。郭象以“依性而为即自为”“安性守分即逍遥”的性分论为现实路径,统合老庄的“自然人性”说与黄老的“名分”思想,从内外两个方面展开对礼之教化向度的阐释。郭象“依性而为即自为”意在揭示性分之“无”的功用意义,遵循自然之性的“自为”功夫是践行礼之精神(礼质)。“安性守分即逍遥”意在揭示性分之“有”的功用意义,遵从礼之外在规范(礼文)的“安性守分”是达至逍遥的必备心性修养,对现实社会礼序的遵循是对自然人性的成就,礼序是天序的延伸,以此统一礼质与礼文。郭象以君主实现“圣王合一”“内外相冥”为最终政治理想,用天性及分工的不同解释现实社会礼序中等级分位的不同,并认为君主因时势变化实行的礼教刑罚等都属于任众人之性的“无为”。这实是通过寓“无为”于“有为”来展开对礼之治国向度的阐释,最终为君主成就治天下的礼序有等局面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