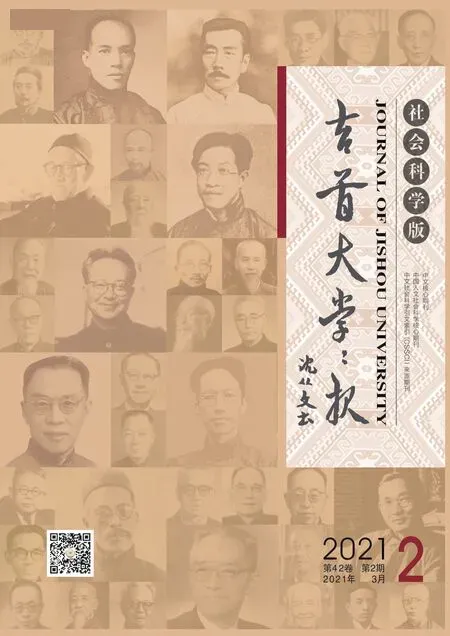论我国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
——以英国为参照*
刘晓兵,王和民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00)
商业秘密领域所谓的“公共利益抗辩”(或称出于公共利益的侵权阻却事由),一般是指负有或不负有保密义务的自然人及法人,将某项构成商业秘密的信息通过某种方式予以公开,该行为本应承担商业秘密的侵权责任,但由于该商业秘密侵害公共利益,而使得行为人免于承担侵权责任的制度。
这样的一种制度在域外(如英美欧洲大陆等),均有立法或司法上比较成熟的制度加以诠释。在我国,虽然学界多有呼吁,但在立法和司法实务界,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20年6月10日最高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才对这一制度的建立进行了积极探索。其第十九条提出了建立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被诉侵权人为维护公共利益、制止犯罪行为,向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等披露相关商业秘密,权利人主张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由于这一制度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该条文至少存在三个争议之处:一是如何明确“公共利益”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二是我国拟定公共利益抗辩限制披露对象(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等),这一做法是否恰当?三是条文中将免除责任表述为“权利人主张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如何理解其中的“一般”?结合英国对于公共利益抗辩的实务经验,拟对该条文中的争议之处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商业秘密领域公共利益抗辩的特殊性及价值
(一)商业秘密领域公共利益抗辩的特殊性
从我国立法来看,公共利益抗辩在合同法领域、名誉权领域都有涉及,虽然名称不同但内涵相似,比如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遵纪守法原则(反映在《民法典》第6条、第7条),以及名誉权领域豁免对于公共利益的公正评论[1]。二者与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的共同点是:行为因涉及公共利益,法律通过一些方式(如法律行为无效)免除了行为人可能的侵权责任。但是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相比之下还具有比较明显的五点特殊性:
一是商业秘密的公开状态与二者不同,缺乏有效监督。不管是合同还是评论,都会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故存在对公共利益侵害的“监督方”,比如合同相对方和第三方、评论发布后面对的社会公众等。但是商业秘密不对外公开,也不存在备案或登记,事实上处于“不受外界监督”的状态,从制度上来说更可能滋生对公共利益进行腐蚀而不为人知的不正当行为。所以,我国实务界有人主张建立一种“商业秘密备案制度”,通过备案的方式对是否侵害公共利益予以审查[2]。
二是平衡的公共利益不同。一般来说,合同法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偏向“以秩序底线和伦理底线为表征的非特定当事人的利益”[3]。在名誉权的抗辩中,公共利益更体现于对于公众正常自由言论的保护。对于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而言,其所平衡的应当是私权范围内对于信息流动的限制和公共利益上对于信息流动的需求,即法律虽然在制度上允许某一信息成为“秘密”而给予一定程度的垄断,但是其目的是为了这一垄断给社会作出贡献,并且这一贡献应当大于赋予垄断所带来的私权收益[4]。如果这一秘密不仅没有给社会发展带来收益,反而产生了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则应当允许甚至鼓励知情者予以披露,以保护公共利益。
三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不同。虽然在三个领域内,公共利益抗辩的存在都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但是其保护的公共利益的重要程度不同。如上文所述,无论是合同还是对名誉权的评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公开,因为公开从而存在一定的“监督”,所以造成侵害公共利益的可能性、危害性较低。而商业秘密则不同,可能涉及的侵害公共利益的情形,包括市场不当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如可能的危害公共安全),理论上这些行为产生的危害程度显然更高。在此前提下,行为人为了公共利益的合法披露行为应当予以特殊的豁免。
四是商业秘密的获取难度更高。通常来说,商业秘密构成企业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比如客户信息等),此时若该秘密包含对公共利益的侵害,权利人可能加强对这一秘密的保护,使其不为人知。故商业秘密领域中的这一信息的获得难度比合同领域和名誉权领域更大。放任对公共利益的侵害显然是不合理的。少数的知情者在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通过合法方式予以披露,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不应当因此承担侵权责任。
五是受到恶意追诉的可能性更高。知情者对侵害公共利益的商业秘密予以披露,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商业收入和商誉受损,可能对其造成比较大的经济损失。此时该知情人受到恶意追诉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合同领域和名誉权领域,赋予披露者一种法律上的豁免具有比较强的现实意义。
总而言之,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是一种基于公共利益的侵权阻却理由。相比我国现存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具有比较强的特殊性。
(二)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的存在价值
我国学界的一般通说认为,公共利益抗辩是限制商业秘密作为一种私权而可能引起滥用的限制规则,是平衡商业秘密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重要手段[5]。商业秘密作为一种知识产权,其保护方式与专利等需经公开而获得保护的客体不同。知识产权的立法一般会设置公共领域保留制度,创造性的成果不能给予无限期的独占权利,阻碍他人进行新的创造[6]。比如专利的立法,是通过给予一定时间的“垄断”以换取该技术在公共领域内的公开,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鼓励创造、实现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对公共利益的平衡条款,如专利的强制许可制度等。而商业秘密具有比较强的保密性,且一般而言没有所谓的“时间限制”。为防止对于商业秘密的过度保护,理应在制度设计上针对私权和公共利益的平衡设置某种方式,在保护私权的同时兼顾公共利益的衡量[7]。也就是说,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对于某种秘密信息流动的限制,最终的目标是在保护的同时,不妨碍信息的流动和对创新的鼓励,并应当防止因给予一种长期的垄断而使得危害公共利益的情况发生[8]。在域外的司法理论发展中,一方面承认商业秘密的保护是一种重要的通过司法控制信息流动的方式,另一方面,其同样认可在这样的私权对抗公共利益时,公共利益更重要,此时该商业秘密应当被公开[9]。
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一种重要平衡手段,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空白”状态。这一规则在立法和实务上的缺失,的确可能产生不当挤压社会公共利益空间的现实情形。比如曾经发生过的云南白药事件,在2009年曾有律师将云南白药诉至法庭,诉称云南白药在配方中使用了一种名为“乌草”的有害原料,但云南白药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交证据,最终该案诉讼请求也被驳回[10]。巧合的是,2018年云南白药又涉及了一个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的案件。在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与阳槟灿二审行政判决书([2018]京行终1925号行政判决书)中,被上诉人申请公开云南白药生产的非特殊用途化妆品的配方信息,最终法院认可这一配方信息为商业秘密,且不公开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从这两个案件的对比来看,在第一个案件中涉及“公共健康”以及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这两项重大公共利益[11],若损害公共利益可以被充分证明,则相关机关或个人通过某种方式予以披露合情合理,甚至该产品如果确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可能涉及刑事犯罪。而在第二个案件中,因为“非特殊用途化妆品”一般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巨大影响,最终不予公开也是对于私权和公共利益比较好的衡量。若以英美法系为司法环境,其认为当商业秘密的披露与公共健康、安全或犯罪等公众关注的焦点事件有关时,该披露行为适用公共利益抗辩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12]。
作为市场主体而言,其所拥有的商业秘密在市场竞争中一般构成该市场主体的核心竞争力,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竞争价值[13]。每个市场主体都会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免受侵犯。这使得该商业秘密很难受到监督,很可能产生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如不正当竞争行为等)。甚至有的市场主体为了维护自己商业秘密的竞争力,蓄意隐瞒商业秘密中的不法行为。当下的学术和实务界对商业秘密的私人占有予以一定限制已经形成通说[14],以免造成资源闲置或浪费,甚至造成危害公共利益的结果。而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正是为解决公私利益平衡而产生的。市场中对商业秘密危害或可能危害公共利益这一信息有掌控能力的主体,在法定的框架内披露这一信息,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这样的行为理应受到鼓励而不是受到掣肘而显得“投鼠忌器”。为了防止商业秘密在市场中的滥用和不受限制地对公共利益的挤压,我国应当尝试建立公共利益抗辩制度,即在法定条件下,某些事关公共利益的披露行为,其披露人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免除侵权责任。
二、我国商业秘密领域公共利益抗辩制度现状
(一)商业秘密公共利益抗辩的立法现状
从国际条约的角度来看,中国加入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中第8条规定,各成员国可以制定保护公共健康和营养,以及至关重要的公共利益的具体措施。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大多是通过国内立法或司法判例对公共利益抗辩予以规定,从而实现该条款。
我国比较早直接提出公共利益抗辩的文件是1998年最高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对名誉权等问题侵权认定的回答中,规定对于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发表“合理评论”或“诚实评论”,免除侵权责任(这一规定也反映在《民法典》第1025条)。偏向公共利益保护的思想,也体现在其他的民事单行法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条(禁止权利滥用)、第58条(无效民事行为)、《合同法》第52条(合同无效情形)等。在我国2020年5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32条中也规定了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公共利益。
从我国目前商业秘密领域的立法情况来看,《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直接规定任何针对商业秘密侵权的抗辩。针对商业秘密的条文中,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只有第十五条:“监督检查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调查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本条文至多可以理解成监督检查部门在维护公共利益时,对于商业秘密有可能的“知情权”,但与公共利益抗辩毫不相干。
除去单行法以外,部分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意见中也体现出在保护商业秘密的同时偏向公共利益的价值衡量,比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5条“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第9条“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技术秘密,不在本条例的保护范围”以及2009年最高院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14点中明确提出了“严格审查被申请人的社会公共利益抗辩,一般只有在涉及公众健康、环保及其他重大社会利益的情况下才予以考虑”。
(二)公共利益抗辩制度的拟定尝试及争议
对于商业秘密这一特殊领域,尽管学术界一直有学者呼吁建立我国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但是在立法上迟迟没有体现。直到202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第19条规定:“被诉侵权人为维护公共利益、制止犯罪行为,向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等披露相关商业秘密,权利人主张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而这对于我国商业秘密领域而言,第一次拟定我国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从条文文义来看,该条文对适用公共利益抗辩制度做出了三个比较重要的限定:一是“为维护公共利益、制止犯罪行为”。如果说制止犯罪行为还比较容易理解,那么公共利益的具体范围还有待明确。从理论上来说,“制止犯罪行为”应当是“维护公共利益”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处予以单独列举,笔者认为是制定者试图对公共利益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定,以免造成各地法院理解不统一而形成“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但不论如何,在这一并列关系的表述中,公共利益的内涵还必须进一步明确。二是其披露的对象必须是“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等”。也就是说我国拟定的公共利益抗辩中的披露不是对社会公众的公开,而是一种“有限度、有目标”的公开。笔者认为这样的拟定是一种比较具有实践意义的规定方式,但也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三是在对于免除侵权责任的表述中,该条文使用了“一般不予支持”的表述,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个案中衡量公共利益和私利之间的平衡,是很难通过法条予以直接规定的。笔者支持此处赋予各地法院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但是由于公共利益抗辩制度事关公共利益(甚至是重大公共利益),对于披露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例外情形,应当加以明确更为妥当,否则知情者又容易陷入“投鼠忌器”的困境。下文通过对英国公共利益抗辩制度的研究,对以上三个问题提出建议。
三、英国商业秘密领域公共利益抗辩制度的实践
从英国的立法情况来看,对商业秘密也没有单独立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是通过由大量判例所组成的系统(breach of confidence),将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作为一种侵权行为(tort)予以规制[15]。而公共利益抗辩被誉为是被告最重要的抗辩手段之一,在揭露或者使用商业秘密时都有可能涉及[16]。在英国司法理论中,认为商业秘密的权利不是绝对的,当公共利益要求公开其商业秘密时,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必须让位(1)Phillips法官曾表达如下观点:“The right of confidentiality … is not absolute,it must give away where it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hat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shall be made public.”。应当说明的是,由于国情存在差异,英国保护商业秘密的系统(breach of confidence)并不只适用于商业秘密案件,只要构成秘密信息即可提供保护(如个人私密信息等),范围远比我国意义上的商业秘密更大。以下对英国判例的研究中,部分判例的涉案秘密在我国法律上不一定能构成商业秘密,但是其贯彻的原则和精神适用于英国的商业秘密案件,对商业秘密案件的审理具有提纲挈领、总领全局的重要作用。我国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对于原则性案件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司法探究“公共利益”等概念的范围和外延。
(一)英国公共利益抗辩发展的路径
1.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偏向打击违法犯罪
公共利益抗辩这一制度在英国已经由来已久,在1856年的Gartside v. Outram([1856] 26 L J Ch113)一案中就已经确立。在本案中,雇主篡改某些顾客的交易信息(在英国法中构成欺诈罪),并要求雇员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一行为。而雇员最终向顾客告知了这一行为,雇主以侵犯商业秘密为由起诉雇员。法院最终认可了雇员的这一行为,并做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原则性的论断,即“对于邪恶的公开中没有秘密可言”(在判决中法官总结为:“There is no confidence in the disclosure of iniquity.”)。这一原则被在后的案件反复引用,被认为是英国公共利益抗辩发展的开篇之案。本案之后英国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的发展,基本上是对这一原则的深化和适用。但就本案而言,没有对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做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诠释,只是确定了公共利益抵消秘密性的原则。有学者将其总结为两个部分,一是要有违法行为,二是该违法行为影响到了公共福利(public welfare)[17]。本案虽不是直接针对商业秘密所作出的判决,但是这一原则性的论断在英国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的实践中得以深化贯彻和发展。
2.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扩大到商业不当行为
在1968年的Initial Service v. Putterill([1968] 1 Q.B. 396)一案中,雇员在雇主公司(一家洗衣公司)工作期间,获悉该公司秘密使用了一种价格垄断协议(price fixing agreement)。按照英国法律规定,这样的协议应当在反垄断机构登记并公开,而该公司没有这么做。雇员在离开雇主公司后,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一家报社并发表文章,雇主公司因此起诉雇员侵犯其商业秘密。在法院的判决中,对前述原则有一项重要的深化,即英国法院认为前述原则中的“邪恶”不应当仅仅限定于犯罪或欺诈,还应当包含不正当的商业行为(2)Denning法官论述道:“The defence was not limited to crime or fraud,but rather covered any misconduct of such a nature that it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disclose.”。在本案中该不正当行为是对法律规定义务的不履行,员工不应当对本应公开的信息承担保密义务,因此员工对应当收知方的公开行为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所谓的秘密不能构成我国法律所保护的商业秘密,不履行法律的登记公开义务本身为非法,不需公共利益抗辩知情人的公开在我国也不会受到追究。但本案对我国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于:公共利益所涵盖的范围不仅仅在于违法犯罪,还包含了不法的商业行为(如我国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3.从公私权利平衡界定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
1985年,英国的公共利益抗辩又有新的进展,集中体现在Lion Laboratories v. Evans([1985] Q.B. 526)一案中。原告A公司是制造测试酒驾(酒精含量)装置的公司,在1984年有两位A公司的技术人员离职后,联系了一家全国性的报社,曝光了A公司某些内部通讯中,关于该测试装置可能不准确和出现错误的情况。法院在本案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是,适用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的情况不仅限于在先不当行为(wrongdoing),而是在考虑四个因素(3)四个考虑因素为:In deciding whether it could be raised the court had to take into account (a) the wid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was interesting to the public and what wa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make known;(b) the fact that the media had a private interest in publishing what appealed to the public in order to increase circulation;(c) that the public interest might be best served by the information being given to the police or other responsible body rather than to the press and (d) that a defendant ought not to be restrained solely because the matter to be published did not show misconduct.之后,扩张到了“正当理由”(Just causes or excuses)[18],即哪怕没有不当行为,只要披露人有正当理由,就可以主张适用公共利益抗辩,并且明确了法官在审理这一案件时要着重考虑公共利益和私权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要么保护个人及组织的权利,保持秘密不公开,或者考虑公共利益而向公众公开的正当性。以本案为例,该装置的测试结果会对酒驾这一行为的认定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而原告作为唯一的授权制造这一装置的厂商,对于公众应当承担提供最高准确性装置的义务,以免执法伤及无辜。法院认为这个装置可能产生错误的信息是“毫无疑问的公共利益”,则这一秘密信息应当公之于众。在本案中可以看出,原告公司的秘密文件显然符合商业秘密的定义,并且原告公司没有比较严重的不当行为,但是法院在逐步扩大公共利益抗辩的适用范围,只要是对危害公共利益秘密的公开,都可以主张适用该抗辩。本案涉及的公司内部技术文件,属于我国保护的商业秘密范畴,如果该信息被知情人通过合法途径揭露并合理证明,其侵害了公共利益或者有侵害公共利益的高度可能性,则该知情人可以适用公共利益抗辩免受侵权责任的追究。
(二)英国司法针对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的考量因素
总的来说,英国的判例发展历程从简单的犯罪行为,到商业不当行为,再到公私权利平衡,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的范围在一百年间逐渐扩大,英国司法逐步倾向于保护公共利益,限制私权。商业秘密领域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在多年发展期间范围也在发生变化。这样一种主张原告不当行为的抗辩,在英国实践中其实没有形成一致的判断标准,而是通过多种考量因素在个案中加以判断[19]。目前英国对于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的考量因素,明确规定于1998年颁布的《公共利益公开法案》(PublicInterestDisclosureAct1998)中,加上商业秘密判例中总结的经验,一般来说有七个考量因素[20]。
1.该商业秘密本身的性质(nature)。简单来说,知情人的披露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in the public interest)而不是仅仅是“公众对该秘密感兴趣”(interesting to the public)。一般来说,如果这一商业秘密涉及的公共利益比较重大,或者跟国家利益相关,则更有可能被界定为公共利益。比如揭露犯罪行为、不履行法定义务、可能危害公共健康或者环境等,一般来说公共娱乐则不在此列。但在娱乐这一点上,英国的法院也有认定公共利益的先例,比如Woodward v. Hutchins([1977] 1 W.L.R. 760)一案,原告将某些明星真实的私生活曝光给了报社。法院认可了这一行为,因为这些流行乐明星塑造虚假的“人设”是在误导公众。法院认为这是在“保护秘密”和“维护公众对于真相的知情权”之间做出平衡(4)在本案中Denning法官论述道:“it is a question of balancing the public interest in maintaining the confidence against public interest in knowing the truth.”。有学者曾经总结,对于这样的案件来说,真相才是最好的抗辩[21]。
2.若不公开(揭露)该商业秘密将会带来的后果。即便被揭露的主体没有犯罪或不当行为,也可能侵害公共利益。比如前文的Lion Laboratories v. Evans一案,如果该信息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可能导致社会主体的自由和人身权利受到不正当对待,甚至导致错案的产生。本案法院在考虑此因素后,进而认为这样的重大公共利益从报社公开是合理的,因为仅仅向公安部门公开可能是不够的。
3.该披露者对该商业秘密所具有的保密义务。英国法院比较重视存在保密义务的情况,如果在合同中有明示的保密义务,则公共利益抗辩就难以实现。同时在英国司法中对此也有区分不同职业的做法(比如医生或者牧师很难适用公共利益抗辩)。
4.披露者披露商业秘密的主观信念。在《公共利益公开法案》中,不止一次提到了揭露者应当“善意”(good faith),而非恶意损害他人的商业秘密。一般观点认为,当披露者有足够合理的理由相信,他正在揭露一个“邪恶”的行为即可。
5.披露的对象。在《公共利益公开法案》中,43条的C-H共6个条款分别列举了不同披露对象构成公共利益抗辩的要件,包括“雇主、法律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国家规定的人员以及其他情况”。总体来说,公开的对象应当是对于该秘密的知悉有正当利益的主体。虽然上文列举的案件很多通过报社公开秘密,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通过报社的公开是不被英国法院认可的。因为法院认为报社的报道可能是不公正的,带有舆论引导性质的,并且如果公开是为了个人收入等因素,也难言“善意”。对社会公众的公开披露,只有两种情况可以被法院接受:一是该公共利益过于重要,以至于需要让社会公众快速知悉(涉及生命、自由等重大公共利益);二是国家机关有充分理由被认为构成“同谋”的情形下。
6.对于公私利益的衡量。从理论上说,公共利益抗辩制度本身就是为了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公共利益抗辩的成立与否,但这一影响因素没有统一的标准,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
7.其他因素。比如在Francome v. Mirror Group Newspaper([1984] 1 W.L.R. 892)一案中,法院考虑了该信息获得的途径。再比如假设揭露者披露时为了获得比较高的收入,虽然不直接导致公共利益抗辩的失败,但是法院会倾向于认为该披露混淆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以上考量因素在英国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运用,比如在Schering Chemicals Ltd v. Falkman Ltd([1982] Q.B. 1)一案中,原告开发了一种验孕检测药物,但是被证明可能对胎儿产生副作用,原告遂下架了该药物。之后某电视台制作了关于这一药物的电影,双方因此产生纠纷,原告诉称被告侵犯其商业秘密,被告则提起公共利益抗辩,认为这一药物是对人身安全这一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法院在考虑上述影响因素后,认为本案不能适用公共利益抗辩:一是该商业秘密没有侵害公共利益(因为药物已经下架),而是公众感兴趣的信息;二是电视台有充分的理由获悉关于药物的信息属于商业秘密,因此承担保密义务;三是这一药物已经不会对公共利益或者个人健康产生危害,不公开也不会产生危害结果;四是法院认为本案对于信息保密的重要性超过公众知悉的重要性。故综上所述,法院没有支持公共利益抗辩,而是颁发禁止令禁止电视台公布这些秘密信息。
总之,就像英国学者总结的,英国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是一个上到刑事犯罪,下到明星私下生活都可以涉及的一种“常用的抗辩形式”,并且其必须是在公共利益之内的,符合一定条件的披露[22]。对于我国刚起步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而言,有值得学习的有益经验。
四、针对我国公共利益抗辩制度提出的建议
(一)对于侵害公共利益的界定
虽然我国还没有建立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权利的行使都不得对于公共利益造成损害[23]。目前我国司法界的一大争议即是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解释,当下我国还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答案。立法上也是如此,虽然多处规定了公共利益,但对其具体的内容却从未达成过统一意见。在司法实践中,最高院曾经表达过“公共利益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观点([2017]最高法行申8518号裁定书)。目前学界对于公共利益的诸多解释,接受范围比较广的一种是将其解释成“不特定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24]。我们认为,公共利益客观存在,但是高度抽象,直接正面定义有比较大的困难。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应该考虑为“对社会一般公众有益的,正当的利益”,并且应当联系当时当地的社会道德、传统文化等因素加以判断。由于界定的困难,各国在商业秘密的公共利益抗辩实践中,认定公共利益一般是结合案情并加以某些原则性的考量因素予以界定。
对于认定公共利益的考量因素,在商业秘密领域没有直接规定的前提下,其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可以尝试借鉴其他知识产权形式的规定,因为对于公共利益的让步是知识产权领域的普遍做法[25],比如我国商标法上的公共利益可以解释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26]。由于商业秘密不存在注册或公开,所以这一领域的“公共利益”应当比传统知识产权法所维护的公共利益更宽泛。可以比较确定的是,诸如“制止犯罪行为(如诈骗)、破坏公共环境”等因素都可以成为商业秘密领域的公共利益。
在仅仅借鉴其他知识产权形式还不足以概括的前提下,英国经长期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的公共利益抗辩的考量因素可以为我国所借鉴。在商业秘密侵害道德、政治、公共健康、社会福利以及国家利益等因素时,可以被认为是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并且严格区分“公共利益”和“对于公众感兴趣”这一相对概念。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正面直接考虑比较困难,也可以学习英国的实践,对不公开所带来的后果进行考量。如此一来,结合我国目前对于公私权利平衡的实践原则(如比例原则等)[27],方可对于是否侵害公共利益得出比较肯定的结论。
《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的条文于维护公共利益提出了“制止犯罪行为”这一要求。这是我国对于损害公共利益应当存在某种在先“不当行为”的一种变相肯定,也就是构成公共利益侵害时,该商业秘密应当构成或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不当行为”。在我国公共利益抗辩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判断体系时,要求某种程度的“不当行为”是对于司法实践操作上的考虑。若直接学习英国商业秘密领域实践中,所有行为都可能适用公共利益抗辩的方法,在我国会形成比较严重的判断标准不一,加剧我国“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如果对于“制止犯罪行为”作出要求,则便于操作,因为犯罪行为相对比较明确,而且对于公共利益一定构成很大的侵害,在法官判断上也比较容易执行。但是从理论上说,这一限定缩小了公共利益应有的范围,因在市场竞争中对于公共利益的侵害不一定都构成犯罪(如不正当竞争行为)。如果此时知情者符合法律规范的披露行为将被侵权责任所威胁,有违我国维护社会公平、促进市场竞争的立法初衷。
我国对于公共利益抗辩的发展,可能也会经历如英国一般的路径,即逐步扩大“公共利益”的范围。因为犯罪行为通常是社会行为的最底线,而某些处于尚不构成犯罪,但是对公共利益可能有所侵害的行为,在日后也可能会构成保护公共利益所规制的对象。
(二)对于披露对象的限定
在《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我国拟定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目前对于披露对象限定为“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等”。在英国实践中也有对于披露对象的限定,但是对于该对象的限定相对我国的拟定来说,范围更大。
在我国的国情下,对于披露对象进行限制的做法是完全必要且可行的。理由有二:
一是对于我国舆论环境稳定的考量。由于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如公共健康等),一般是比较重大、社会关注度高的信息,如果不限定披露对象允许随意向公众公开,容易在社会层面引起恐慌,造成我国社会的不稳定,即便事后予以澄清,也很难挽回造成的舆论负面影响。而限定披露对象在这一点上有两个好处,一来若该披露者所掌握的信息为不实信息(但披露者有理由相信为真实),则通过国家机关的调查,最终不予向社会公众披露,自然不会造成舆论的不良后果;二来即便该披露者掌握的信息为真实,但是直接通过媒体发布往往容易产生舆论引导,不完全还原事实。而通过国家机关,参考合理的“利益衡量标准”[28]后,在恰当的时机通过合适的方式予以公布,可以在尽量保证真实的前提下避免引起舆论的混乱。
二是商业秘密的不可复原性。如果允许知情人随意在社会公众层面公开,就可能出现被公开的商业秘密为真,但是没有侵犯公共利益的情形。此时即便事后追究民事或刑事责任,被公开的秘密也不可能再重新成为商业秘密了,对于商业秘密的所有人来说其损害是完全不可逆的。因此,对于商业秘密的披露应当慎重,限定披露对象是一个比较方便且公正的方式。
当然,相对来说我国目前拟定的条文对于披露对象的限定还比较狭窄,中国的实践可以学习英国的对于该秘密的知悉有正当利益的做法。在日后对于披露主体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比如对于自然环境这一公共利益的侵害,若有市场主体将其作为商业秘密的一部分予以隐瞒,知情者对环保公益组织披露,也并无不妥。
(三)合理限定“一般不予支持”
在本条文中的最后,编纂者使用了“一般不予支持”的表述方式,颇有些“耐人寻味”的意思。但这一例外性的规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直接规定一律不予支持,可能会出现在实践中不够灵活的现象。当然,就法律条文的编纂来说,“一般不予支持”的表述毕竟表述模糊,应当具体确定几种例外情况。在此,结合英国有益经验,尝试提出一些建议:
1.考虑披露者的主观状态。从英国的实践来看,一般对于该类信息的公开以“善意(good faith)”为要件。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不要求披露者的善意,则可能助长市场主体窥探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商业秘密通常都是媒体报道的兴趣所在,通过某种方式窥探商业秘密从而“售卖”给媒体,其行为人还免受侵权责任的追究,这未免有失公平。
2.考虑披露者获取该商业秘密的方式。如果是通过侵权的方式不当获取的,应当认为即便该商业秘密侵犯公共利益,该披露者也应当对于该秘密的公开承担侵权责任。在英国法上认为,如果信息获取的过程构成侵权(offence),则该公开将是非正义的。
3.考虑公共利益和私利之间的平衡。如果该公开所保护的公共利益较小,但是从而侵犯到更大的私人利益,或者说公开此商业秘密对于秘密所有者的损害超出了合理的比例,则该披露者也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五、结语
在商业秘密保护领域,对于公私利益平衡非常重要的公共利益抗辩制度,是一国法律体制下对于社会利益的重要保护措施。从这个方面来说,在《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公共利益抗辩的拟定无疑是中国商业秘密保护的一大进步。应当说这一制度的建立为我国更好地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提供了制度基础,也体现了国家开始更加重视保护公共利益的态度。从此以后,对于侵害公共利益的秘密的知情人,可以没有后顾之忧、通过合法方式披露该秘密,以保护公共利益。
可以理解的是,在条文编纂之初,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我国这一拟定公共利益抗辩制度的条文中,还存在至少三处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地方。在公共利益抗辩制度发展过程中,参考这一制度比较完善的英国地区的司法实践,对于我国“蹒跚学步”的状态而言有很大的价值。无论是英国对于侵害公共利益行为的理解,还是对于公共利益抗辩的考量因素,都可能成为我国商业秘密领域的未来司法的一部分。具体来说,我国对于英国维护公共利益的考量、披露对象的限定原则,以及对于承担侵权责任的例外情形三个方面,皆可加以借鉴,从而解决目前拟制公共利益抗辩制度条文中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