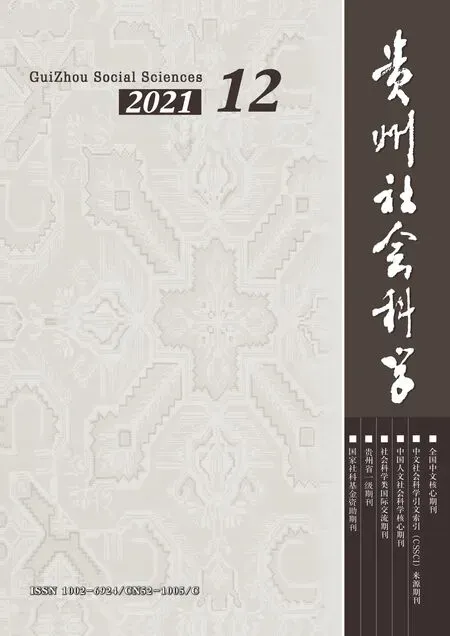封授与华夏化:从外封官爵的分类看汉代的民族整合
尤 佳
(东南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6)
在中国古代的民族管理实践中,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经常向周边民族和政权首领赐予各类官爵名号。从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来看,对边疆民族首领的封赐始于先秦,秦、西汉时期逐渐体系化,东汉魏晋时趋于完备。这些官爵名号既不同于周边民族及政权已有的职官,又有别于中原王朝内部官僚体系的爵职,因而有学者将其称作“外封官爵名号”,[1]本文也沿用这种提法。
关于汉代外封官爵的分类,一些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意见。黄盛璋研究汉代匈奴官印时,根据印文将王朝所授职官分为两类:一类为匈奴语官号,仅用汉字音译;另一类为汉语官号,采用汉字意译。[2]若将黄先生的分类方法推而广之,则汉王朝封赐民族首领的职官名号基本上都可依印文分作汉语音译与意译两大类。李文学则根据官爵的性质与职掌,将外封名号先分成爵位和职官两大体系,继而又在外封职官体系内细分出文官、武官两类。[3]
黄、李两位先生关于外封官爵的分类各有理据,对我们研究王朝的官爵制度以及民族政策等也颇有启示,但其中似也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黄盛璋的汉分类标准易于操作,但却可能会将不同文化传统的职官混为一类,不利于明晰各类官称的渊源与特点。李文学的分类方法逻辑清晰,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却会遇到一些难题:如官与爵难以确分,(1)王朝外封的爵位与官职往往交织在一起,不少名号的性质究竟是爵还是官实际上很难区分清楚。譬如“王侯君长”序列中的“君”“长”能否视为爵位,其实就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所以,李氏自己也承认,汉魏外封官爵体制在官与爵之间进行完全的区分是困难的。参见李文学:《汉魏外封武官制度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67页。文、武职的界定存在模糊区域,等等。
鉴于此,很有必要为外封官爵设立一套更为合理、可行的分类标准,以便能深刻揭示外封职官的制度渊源、演变规律及其深层次原因,理解和把握王朝对周边民族的治理策略、整合措施以及边疆族群的认同转型与华夏化进程等。本文拟以制度来源为标准将汉王朝的外封官爵名号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源于王朝内部官爵体系的职官,如都尉、中郎将等;二是根据华夏文化传统专门创设的官称,如大都尉、大都护等;三是取自周边民族及政权职官体系的名号,如邑君、邑长、仟长、佰长等。(2)在考古资料方面,本文主要以罗福颐的《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周晓陆的《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与王人聪、叶其峰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0年)中所收录的民族官印、封泥为研究素材。
一、王朝内部官爵体系的职官
王朝内部官爵体系的职官因通常授予内臣,故也被称作“内臣官爵”。但实际上它们并不全授予内臣,统治者可能会将某些内臣职衔借以封赐边疆民族首领,如都尉、中郎将等,只不过这些职衔前通常会冠以“率善”“守善”“亲汉”“归义”等嘉称,以与内臣职官相区别。据罗新先生研究,中古北族职官名号一般由官号和官称两部分构成,这也成为其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4]实际上,汉晋时期赐予异族首领的官爵名号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即修饰性的嘉称(官号)与具体职衔(官称)共同构成完整的外封官爵名号的主体。
汉王朝封赐民族首领时常选用的内臣职官是“都尉”。但若以长时段的视角分析,能看到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职衔种类的增多
西汉王朝外封时,所授内臣职衔基本为“都尉”。如西域的车师前国有“归汉都尉”,龟兹国有 “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危须国有“击胡都尉”,乌孙国有“坚守都尉”,等等。[5]3876-3932东汉时,朝廷封授的内臣职官可能又增加了“中郎将”。《出三藏记集》载:“支谦,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氏人也。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拜率善中郎将。”[6]设若这则史料记载属实,则东汉末“中郎将”之职也已用于外封。(3)此外,东汉初还有“大将军”的外封。《后汉书》卷88《西域传》载:“(建武)十四年,(莎车王)贤与鄯善王安并遣使诣闻贡献,于是西域始通。葱领以东诸国皆属贤。十七年,贤复遣使奉献,请都护。天子以问大司空窦融,以为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加号位以镇安之。帝乃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诏书收还都护印绶,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其使不肯易,遵迫夺之,贤由是始恨。而犹诈称大都护,移书诸国,诸国悉服属焉,号贤为单于。”(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2—2923页)早在建武五年(29),莎车王贤的父亲康就被汉廷封为“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第2922页)至建武十七年(41),贤复遣使奉献,光武帝与窦融遂商议赐贤为“西域都护”,以图镇抚。然“西域都护”在西域诸国中颇具实权与影响,故裴遵以“夷狄不可假以大权”为由建议朝廷收回诏命,光武帝遂更以“大将军”印相赐。所以,莎车王贤最终受封的名号是“大将军”。“大将军”为汉武帝所设,至光武时亦被用以外授,但汉代史籍中只记有莎车王贤一例。这到底是特殊历史背景与条件下的权宜之举,还是近于制度化的封授举措,目前还难以确判,姑且存疑。
若将时限下延,我们对外封职官种类的扩张会有更深刻的体会。曹魏时,不仅确定已有“中郎将”的外授,还新增了“校尉”一职。景初二年(238),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派遣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等人来使。魏明帝下诏,赐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7]857正始四年(243),倭王再次遣使向魏齐王进献倭人、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短弓矢等物,倭使掖邪狗等人亦被赐予“率善中郎将”印绶。[7]857
(二)封赐范围的扩大
西汉王朝外授“都尉”时,主要施用于西域诸国。至东汉,范围至少已扩大至北方的乌桓、西北的氐人等。如乌桓首领戎朱廆受封为“乌桓亲汉都尉”,[8]2988汉阳氐人酋豪蒲密获赐“率善都尉”。[9]至曹魏时,“中郎将”“校尉”等职还被授予了日本列岛的倭人使者,封授对象不断增多,职衔级别亦有所提高。
通观上述封赐事例可以发现,汉朝统治者选用何种内臣职衔外授有多方面的考量。首先,这些职官须为周边民族所熟悉;其次,它们要有一定的权力依托,否则徒有虚名的名号即便授予了,恐也难以实行长久。譬如“都尉”,近塞的属国都尉与边郡都尉恐怕是汉王朝与周边民族接触最多的长吏之一;又如“中郎将”,“在汉代即经常性地充当使者,来往于周边民族和汉族政权之间,尤其是汉与匈奴的使者往来,基本由中郎将来职掌”。[10]67上述王朝边吏与民族首领及其部众常相接触,为其所熟悉,在受封群体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同时,此类职衔在王朝职官等级体系内居于中层以上,在民族地区享有较高的认可度。此外,这些较有实权的内臣职官又不属于权力很大者,用作外封亦较合适。
二、王朝专门设立的官爵名号
第二类外封职官是汉王朝专为封授民族首领而设置的官爵名号。由于此类名号的创设基于华夏制度传统,故从官称上看,它与第一类内臣职官颇有形似之处。但实际上二者区别明显,关键是看该职衔是否本就存在于王朝内部官爵体系中。以“大都尉”为例,尽管汉代内臣职官序列中有“都尉”之职,各类都尉还因职掌不同而官称各异,但却从未出现过“大都尉”职衔,故而也从无内臣获拜过该职。可见,“大都尉”是统治者专为周边民族首领特设的名号,故从设置伊始仅向异族首领封赐,下文便对这类职官名号分作阐析。
(一)“大都尉”
汉代对“大都尉”的封授集中于东汉,史籍中记有以下四则事例。“大都尉”最早的外封应发生在光武初年。“(莎车王)康率傍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乃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国皆属焉。”[8]2923光武以后,该职时有封授。明帝永平元年(58),“以谒者窦林领护羌校尉,居狄道。林为诸羌所信,而滇岸遂诣林降。林为下吏所欺,谬奏上滇岸以为大豪,承制封为归义侯,加号汉大都尉”。[8]2880安帝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8]2851顺帝永建二年(127),“(疏勒王)臣磐遣使奉献,帝拜臣磐为汉大都尉”。[8]2927
分析上述诸例,我们能得出以下几点重要认识。
1.从封授范围上说,“大都尉”主要赐予王朝北部边疆的民族首领,尤其是西北地区。上述四则事例中,两例发生于西域,一例出现在西羌。掸国王雍由调的情况较为特殊,其身份为西南徼外藩属首领,并非汉王朝西南夷地区的民族首领。所以就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所见,西南夷乃至南方地区似无获拜“大都尉”的事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代民族职官封授的区域性差异。
2.异族首领能否获得加号的关键是其势力大小,即是否为“大豪”。汉明帝时,护羌校尉窦林为下吏所欺,以滇岸为羌人“大豪”表奏,朝廷遂赐其“汉大都尉”。再联系之后滇岸实非“豪酋”、窦林此举属谬奏欺君而遭惩处等历史情节能够看出,朝廷外授“大都尉”是有其考量依据的,关键因素便是受赐者当为势力较强的民族部落或政权的首领。
3.封授异族首领为“大都尉”在汉代业已制度化。不论是莎车王康还是羌豪滇岸,均系“承制”封赐,这表明至迟在建武五年(29),王朝已有外授“大都尉”的成制。其时天下纷扰,光武帝尚未完成全国统一,尚无暇大规模地建章立制和实施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不少治边制度都袭自西汉。所以,不排除西汉时可能已存在外授“大都尉”之制,只不过史载有阙。汉代赐号“大都尉”的做法还对其后的民族首领封授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曹魏统治者亦沿袭汉制,对西域地区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实行了此类封授,如车师后部王壹多杂即被赐予“大都尉”。[7]865
(二)“大都护”
除“大都尉”外,汉王朝特设的外封名号还有“大都护”。史籍所见汉代赐号“大都护”者都为鲜卑首领,最早的封赐可能发生在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光武帝时,匈奴势盛,鲜卑、乌桓等部族处于匈奴控制下,常随其寇塞抄略。辽东太守祭彤建议朝廷,对北边诸族的入侵应当采取分化瓦解、以夷制夷的策略。建武二十五年,汉廷遂对鲜卑遣使招诱,示以财利。是年“鲜卑始通驿使”,“其大都护偏何亦遣使奉献,愿得归化,肜慰纳赏赐,稍复亲附”。[8]745
观上,史籍记载偏何遣使奉献时径称其“大都护”,再联系建武二十五年汉与鲜卑“始通驿使”,则赐偏何为“大都护”很可能便在此年,属汉廷对鲜卑酋豪招诱赏赐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东汉封授的另一位大都护是活跃于和帝时期的鲜卑首领苏拔廆,其因常从护乌丸校尉任尚击匈奴叛者,后被封为“率众王”。[8]2956
在汉代民族职官的封授实践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官爵双授”,即受封者可获赐两项(或以上)的官爵名号。这些名号中,通常一个为爵位,一个为官职。譬如,前文所列举的四位大都尉和两位大都护中,莎车王康、归义侯滇岸、掸国王雍由调、疏勒王臣磐、率众王苏拔廆五人都属于此类情形。(4)关于鲜卑大都护偏何,囿于史料记载简略,我们尚不清楚他是否也获封过王、侯等爵,姑且不计。而且,两项官爵名号既可以同时授予,如康与滇岸;也可先后颁赐,如雍由调、臣磐与苏拔廆。
外封过程中为何会出现上述“双授”现象?主要原因恐怕是,统治者希望通过官爵双授显示朝廷对受赐者的特恩优宠,以抚循怀柔之。为彰显这种恩遇,王朝往往会崇其名号,如所赐官称中多带有“大”字,“大都尉”“大都护”等即是如此。这样既遵从了少数民族的习俗传统,[11]36又增加了受封者的权势,提升了他们在本族或政权内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在部族间竞争的优势地位,自然容易被民族首领所接受和认可。
三、周边民族及政权原有的官爵名号
我们所熟悉的“王侯君长”序列就是典型的源于周边民族及政权职官体系的外封官爵名号。汉王朝南北边疆的不少民族有其自身的制度传统与文化习俗,一些民族政权还建立了较为系统、繁密的职官制度。
譬如匈奴的职官制度就比较完备,两汉书对此俱有详细记载。《汉书·匈奴传》:“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最大国,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禅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之属。”[5]3751《后汉书·南匈奴传》:“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禹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8]2944
此外,西域诸国的官爵体系亦较发达。《汉书·西域传》载:“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缓,凡三百七十六人。”[5]3928《西域传》还对各国的职官设置进行了详细描述,所涉官爵大大超出了上述列举的这些,其来源多途,明显融汇了汉朝和匈奴的制度传统。[10]65(5)如李文学认为,西域诸国官制其实是汉官制度、西域各国制度传统和匈奴官僚制度共同影响的结果。参见李文学:《汉魏外封武官制度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65页。
在名目繁多的民族职官中,汉王朝只选取了一部分纳入到外封官爵体系中,即以“王侯君长”为代表的爵职序列。《续汉书·百官志》曰:“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8]3631《续志》对“王侯君长”的记载十分简略,以至于我们对它们的了解还很有限。譬如等级问题,是否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可比郡,邑君、邑长可比县呢?又如,“王侯君长”实际只是笼统的称谓,除去《续志》所录上述爵职外,还包括哪些职官呢?凡此种种,我们并不清楚。有赖于近年来玺印封泥、简牍碑刻等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与整理,使我们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成为可能,下文即对“王侯君长”官爵体系涵盖的具体官称作一初步探讨。
(一)“王”与“侯”
汉代,在“王”“侯”等高级爵号的封授上,未体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边疆地区的众多民族及政权首领都获赐过此类封爵,只不过具体封号会因族属或颁授主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例甚多,恕不备举。(6)详参《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汉书》卷94《匈奴传》、《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汉书》卷96《西域传》、《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后汉书》卷87《西羌传》、《后汉书》卷88《西域传》、《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等。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侯”在传世文献和玺印封泥中亦或书为“邑侯”。如“归义賨邑侯”“汉归义賨邑侯”“汉秽邑侯”“新保塞乌桓西黎邑率众侯”,等等。其中,“新保塞乌桓西黎邑率众侯”印章除了反映封授者、受封者族属、爵称等信息外,还特别书明了邑名,“西黎”盖为此乌桓邑侯的驻牧地。
(二)“君”
与“侯”相似,“君”在文献中或会称作“邑君”。尽管该封号也赐予北部边疆的民族首领,如“汉匈奴归义亲汉君”“归义车师君”“汉归义羌邑君”等,但与“王”“侯”外封几无地域性差别不同的是,其授予对象主要还是广大南方地区的民族首领,如“越贸阳君”“新越三阳君”“新越馀壇君”“奉通邑君”“越青邑君”,等等。
(三)“长”
“长”的情况较为复杂,涵盖的职官亦属繁多。除了通常我们所认为的“长”“邑长”等官称外,至少“仟长”“佰长”应也包含在内,“小长”很可能也属于该序列。
在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中,“长”或“邑长”的例子很多。譬如,南方地区的“越归汉蜻蛉长”“板盾夷长”“汉叟邑长”“汉归义叟邑长”等。在北部边疆,汉廷对各族酋豪也多有封赐。譬如,授予羌人的有“汉归义羌长”“汉归义羌邑长”“汉率善羌长”“汉破虏羌长”“汉青羌长”“汉青羌邑长”“汉青羌夷长”等;对氐人的封赐有“汉归义氐邑长”“汉青芙邑长”等;(7)瞿中溶认为,“青芙”即青氐之类,所以“汉青芙邑长”实即“汉青氐邑长”。详见(清)瞿中溶:《集古官印考》卷9《汉代官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8页。授予匈奴的如“汉匈奴归义亲汉长”“汉匈奴守善长”“汉匈奴破虏长”等;赐予乌桓的有“汉乌桓率众长”“汉保塞乌桓率众长”“汉保塞乌丸率众长”等;封授鲜卑的如“汉鲜卑率众长”等。由此可见,汉廷对“(邑)长”的封授未显示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8)关于“邑长”,周伟洲等认为,西南夷系“邑聚而居”,故设邑长。周伟洲、(日)间所香熾:《陕西出土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古代印玺杂考》,见《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第87页)。而罗继祖认为,邑长之邑,当即少数民族中的部落,汉族统治者命官,所以改称为邑,见罗继祖:《汉魏晋少数民族的官印》,《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5期,第13页。可见,北方民族部落也可称邑,故部落酋豪亦可授邑长。盖在中原王朝统治者看来,尽管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各民族生活方式与居住格局的不同,但北方的部落与南方的邑聚可大致比附,故也赐予同样的官爵名号。而这与仟长、佰长的外封形成了巨大反差。
汉王朝对“仟长”的封授既有笼统的以所谓“蛮夷”“胡”为赐予对象的情形,如“汉归义夷仟长”“汉蛮夷归义仟长”“胡仟长”“蛮夷仟长”等;也有明确受封者族属的众多例子,主要为北方诸族,如“汉归义羌仟长”“汉氐仟长”“汉归义氐仟长”“汉乌丸归义仟长”“汉归义乌桓仟长”“汉丁零仟长”“汉卢水仟长”“汉鲜卑归义仟长”“汉高句丽率义仟长”“汉叟仟长”,等等。汉廷外授“佰长”亦体现出相似的地域性特点,如“汉归义氐佰长”“汉率善氐佰长”“胡归义氐佰长”“汉归义车师佰长”“汉归义穢佰长”“汉归义羌佰长”“汉青羌佰长”“汉卢水佰长”“汉乌桓归义佰长”“汉归义叟佰长”“新五属左佰长”“新西河左佰长”“新西河右佰长”,等等。
以上“仟长”“佰长”的封授事例中,不论是氐、羌、卢水(胡)、乌桓、鲜卑、穢(韩)、高句丽等部族名,还是“五属”“西河”等反映王朝所置属国的印文,都表明此类官称的受赐者主要还是北部边疆的民族首领。(9)在“仟长”“佰长”的封授对象中,除叟人外,其他多属传统的北方民族。汉魏之“叟”乃西南夷的一种泛称,主要指今四川西部、甘肃东南等地民族,故有氐叟、蜀叟、賨叟、青叟、越嶲叟等。详参周伟洲、(日)间所香熾:《陕西出土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古代印玺杂考》,《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第87页。此外,“左(右)佰长”的印文表明,“佰长”有左右之分,这也契合少数民族的习俗传统。
“小长”原为西域诸国常设职官。《汉书·西域传》曰:“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享汉使者。”[5]3891“小长”后被纳入王朝外封官爵体系内,现存的实物印章以新莽时期为多,如“新西国安千制外羌佰右小长”“新保塞渔阳左小长”“安定右小长”“新前胡小长”等。观上述印例,小长的授予对象以族属而论,除羌人外,还多见“胡人”,“胡”在汉魏时期一般指匈奴。[12]从隶属关系上讲,小长当为佰长之属官,且也设有左右,“新西国安千制外羌佰右小长”之印表明,受封者应为羌人佰长之下的右小长。可见,“小长”应属于民族职官封授体系中的低级别官称,主要授予匈奴、羌等安置于王朝北部边疆属国、边郡或近塞分布的少数民族首领。
综上,在来源广泛、名目繁多的民族职官中,汉王朝只吸收了一部分整合入王朝的外封官爵体系中。这类民族官称除了前文所论需要具有封授范围的普遍性外,从形式上看,它们通常是意译的民族职衔。对于异族官称,华夏史官有的采用意译,有的采用音译,这并不是随意选择的。通过众多事例的比较能够发现,使用意译的民族职衔,要么源于华夏官制,要么也与华夏职官有相当程度的可比性。双方的制度差异较小,这无疑为它们的交流与互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此情形下,一些意译的民族职官便可能会朝着制度融合的主流——华夏式官爵体制的方向发展。而音译的民族职衔,往往来自本族或周边民族的文化传统,它们与华夏制度差异较大,融入王朝外封官爵体系的难度自然很高,因而在王朝的封授实践中逐渐呈萎缩之势。
四、华夏式与非华夏式:官爵制度分类的又一视角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非汉王朝授予异族首领的职衔都属于本文所讨论的外封官爵名号。在此,有必要区分两类民族职官。一类是被汉王朝吸收、整合进外封官爵体系内的职衔,另一类是除前者外的其他少数民族爵职。两者的性质迥然不同。
第一类职官虽然源于少数民族的制度文化,但已融入汉王朝的外封官爵体制中,被常态化地授予边疆地区的诸民族首领,并成为王朝边疆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性质上讲,这类民族职官与中原政权内部职官一样同属于华夏式官爵体系,并成为王朝官僚制度的重要基石。
第二类民族职官尽管也有可能被赐予异族首领,但实际上它们并不属于王朝的外封官爵体制。
从封授原因上分析,这类封赐仅是中原王朝统治者对周边民族及政权首领政治名分的承认而已,旨在笼络羁縻和确立双方的统属关系(有些还仅仅是名义上的)。从封授对象上讲,此类职官往往只授予某一民族(政权)或某一地区的若干民族(政权)首领,不具有第一类职官在封授范围上的普遍性,这也是两类民族职官区别的关键所在。大体上说,几乎全部的音译民族职官和多数的意译民族职官都属于第二类。(10)民族职官依据印文的表述形式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民族语言的音译官号,如匈奴的且渠、当户等;另一种为意译官号,如匈奴的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西域的译长、城长等。实际上,前者中几乎全部以及后者中的大部分都未被整合进王朝外封官爵体系内。从性质上论,它们仍是少数民族职官,并不在汉王朝的外封爵职体制内,属于非华夏式官爵制度。
既然提到华夏式与非华夏式官爵制度,就有必要对二者的辨别标准作一说明。质言之,判断某种官爵体制属于华夏式还是非华夏式,关键要看其制定主体为谁。如果官爵体制的制定主体是华夏政权,哪怕其中一些内容采自周边民族,我们仍应将其视为华夏式官爵制度,譬如前文讨论的“王侯君长”的爵职体系;反之,若制度的创立主体是边疆民族和政权,尽管他们可能会吸收某些中原王朝的制度因素,譬如“将”“相”“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等西域、匈奴职官都鉴用了华夏文化传统,我们宜当将其归入非华夏式官爵制度。进而言之,尽管制度来源、封授对象与王朝外封官爵体制的创设与实施关系密切,但它们并不成为其制度属性的判断依据,制定主体才应是区别华夏式与非华夏式官爵制度的合理标准。
根据以上判断标准,华夏式官爵制度主要涵盖王朝内部官爵制度与外封官爵制度两类;非华夏式官爵制度则是未整合进外封爵职体系内的少数民族职官制度。但需要明晰的是,在华夏式官爵体制内,各系统的华夏化程度可能并不相同。王朝内臣职官体系的华夏化程度无疑是最高的;外封官爵体系来源有三,取自少数民族制度文化的职官序列是华夏化程度最低的,其他两类封授名号要么选自内臣官称,要么根据中原制度文化专门创设,其华夏化色彩自然也很浓厚。
五、外封官爵制度与汉代的文化互鉴和民族融合
以制度属性和华夏化程度的角度来考察、分析外封官爵制度当为值得尝试的新视角。这不仅有助于明晰民族职官封授体制的性质、特点,还能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其演变规律及深层次原因,洞悉外封官爵制度对汉代的文化交流与互鉴、民族交往与融合等方面的作用与意义。
以上述视角纵向考察汉王朝的封授实践能够发现:越往后期发展,统治者授出的非华夏式官称就越少,至汉末几至绝迹;(11)以两汉魏晋时期的匈奴官印为例,依印文的表述形式可将其分为两类:官爵名号为匈奴语之印、汉语官号之印。由于匈奴无文字,所以上述两类官印所用皆为汉字。据黄盛璋研究,第一类官印所见皆为汉代,汉以后除个别例外,皆为第二类汉语官印,魏晋尤为多见,并且同名之官印很多。(黄盛璋:《关于博物馆藏传世汉匈奴语官印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4期,第16页)第一类民族官印的减少乃至消失、第二类印章的普遍增多,实则反映了汉匈交往、联系的密切,以及周边民族在中原王朝的管理、整合下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日益融合的趋势。而外封官爵序列则成为王朝封赐异族首领的主流,且所授名号呈现出向华夏式官爵体系的主轴——内臣职官体系靠拢的趋势。
具体来说,中原统治者在封赐民族职官时,选择外封官爵体系内前两类职官的情况日益增多,尤其是内臣职衔的封授频率明显增加;与此相伴的是,源于周边民族文化传统的名号在封授实践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最终的结果便是,汉王朝外封官爵体制的华夏化程度不断提高,外封职官与内臣职衔的区别日渐减少。(12)魏晋南朝时,蛮夷首领获授为左郡左县之长官亦称守令,职衔名号上与内臣的差异性已大为减小。外封官爵体制的变迁不仅反映了少数民族与汉王朝交往联系的日益增强,华夏制度文化对周边民族的吸引力与影响力的明显提升,还折射出边疆民族在汉王朝的统治整合下,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其自身的华夏化程度亦日渐提高。
实际上,华夏式与非华夏式官爵系统一直处于不断交流、互鉴和融合的状态中,不论是汉民族的还是少数民族的制度往往都是不同文化传统相互融合凝聚的产物。一方面,汉政权的外封官爵体系吸收了不少源自周边民族职官制度的名号,如邑君、邑长、仟长、佰长等。另一方面,华夏式职官的外授对少数民族进一步吸纳汉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整体层面上讲,周边民族及政权的制度变革和社会发展都不同程度地选择了汉王朝的制度成果为其资源。
譬如,西域诸国往往置有“将”“相”“都尉”等职;[5]3751匈奴的“二十四长”包括“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二十四长”之下又各自置“相”“都尉”等。[5]3928上述“将”“相”“都尉”等职衔都是借用了中原职官。进而言之,官爵名号的外封实际上是一种华夏文化的输出,是中原王朝对周边民族一种重要的整合手段。最终的实施结果不仅使边疆民族认可和接受了华夏式职官,还相当程度地接受了华夏文化,并深刻影响了本部族及政权的制度建设。
以匈奴为例,其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分封制,尽管它以部落为实行基础,但与西周的分封制相似,匈奴的分封制也与宗法制紧密结合,实行所谓“家国一体”的统治模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匈奴的分封制是吸收了中原分封制的某些要素,并结合本政权实际而形成的。[13]随着与汉王朝交往的日益密切,匈奴统治者不断借鉴、吸收华夏制度因素,其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政权结构与组织形式也越来越完备、复杂。至南匈奴时,匈奴已从早期的单于处于最高级、四大国为第二级、二十四长为第三级的军事色彩浓厚的政权结构,发展成单于为顶级、四角为第二级、六角为第三级、裨小王等为更次一级的军事意味相对淡化的政权组织形式。所以,有学者认为,匈奴统治结构的变化应是其统治者渐渐懂得中原诸朝的体制后融汇参用的结果。[11]51
六、结 语
汉代的外封官爵制度就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和融合的典型例证。统治者在取材华夏职官制度的同时,还积极吸收、融入了匈奴、乌桓、鲜卑、羌与西域地区等北方民族以及南方苗蛮、百越等民族和政权的制度传统。从文化的多样性与互补性这个角度上讲,民族职官封授制度尽管是由汉王朝制定和推行的,但实际上是由当时不同地区的众多民族共同参与和创造的,是以汉文化为主的多种文化交融凝聚的结果,它的实施为此期民族的交流、融合和汉族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周边民族在与汉文化不断接触、交流、吸收与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变迁与民族意识的变化,进而导致对汉文化认同的提升,引发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民族融合和汉族群体的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