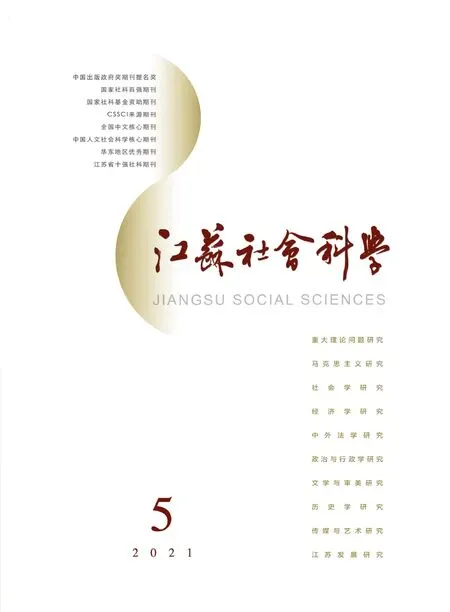论宋代哲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诸葛忆兵
内容提要 宋代哲宗朝科举制度随着新旧党派的此起彼伏而震荡改变。首先,旧党中的主流意见是反对省试经义取士制度,要求恢复诗赋取士。不过,许多旧党大臣仍然支持经义取士,唯独对王安石以一家之说为准的科场录取标准提出批评。朝廷最终采取折中立场,经义和诗赋两存之,然偏向诗赋取士。宋哲宗亲政,再废诗赋取士,而设“宏词科”弥补之。同时,司马光从乡举里选的立场出发,新设经明行修科。此举在专制体制下不可行,所以在元祐年间并无多大作为。部分旧党大臣还对殿试用策、三舍取士等熙丰新法提出批评意见,要求恢复殿试诗赋论三题,废除上舍取士。旧党人士对这两点依然争论很大,最终保留殿试用策而废三舍法。宋哲宗亲政,三舍法同样得以恢复。
宋哲宗赵煦于公元1085年4月登基,卒于公元1100年2月,在位15年。哲宗朝之科举制度,之前经历了太祖至真宗三朝的变革完善、仁宗朝的平稳实施和神宗朝的刻意改变,其纷争和摇摆大都是回应神宗朝的作为。哲宗在位期间,朝政分为两个阶段:元祐年间,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旧党得势;元祐之后,哲宗亲政,新党当政。哲宗朝之科举制度,也随着新旧党派的此起彼伏而震荡改变。
一、经义与诗赋之争
哲宗以八岁幼龄登基,高氏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等旧党,朝政逆转,神宗朝的多数变革举措被废除或部分废除,包括科举制度的系列变革。
首先引起部分旧党关注的是省试经义取士制度,这是哲宗朝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一项制度。即使在旧党内部,对此也是分歧巨大。旧党中的主流意见是要求恢复诗赋取士。元祐元年(1086),重新主政的旧党大臣立即开始对经义取士制度进行批判。尚书省执政班子进言:
伏见朝廷用经术设科,盖欲人知礼义,学探原本。近岁以来,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其患在于治经者专守一家,而略去诸儒传记之说;为文者惟务解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深虑人材不继,而适用之文,从此遂熄。兼一经之内,凡可以为义题者,牢笼殆尽,当有司引试之际,不免重复。若不别议更张,浸久必成大弊。欲乞朝廷于取士之法,更加裁定。[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第15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858页,第8858—8859页,第8861页。
大臣们从两个角度批评经义取士:考生“闻见浅陋”,考题“不免重复”。以此番言论,为恢复诗赋取士张目。
尚书省进言的同时,侍御史刘挚单独上奏疏,其核心内容是批评经义取士、主张恢复诗赋取士:
今之治经,以应科举,则与古异矣。以阴阳性命为之说,以泛滥荒诞为之辞,专诵熙宁所颁《新经》《字说》,而佐以《庄》、《列》、佛氏之书,不可究诘之论,争相夸尚。场屋之间,群辈百千,浑用一律。主司临之,珉玉朱紫,困于眩惑。其中虽有深知圣人本旨、该通先儒旧说,苟不合于所谓《新经》《字说》之学者,一切在所弃而已。至于蹈袭他人,剽窃旧作,主司猝然亦莫可辨。盖其无所统纪,无所檃括,非若诗、赋之有声律、法度,其是非工拙,一披卷而尽得知也。诗、赋命题,杂出于六经、诸子、历代史记,故重复者寡。经义之题,出于所治一经。一经之中可为题者,举子皆能类聚,裒括其数,豫为义说,左右逢之。才十余年,数榜之间,所在义题,往往相犯。然则文章之体,贡举之法,于此其弊极矣。诗赋之与经义,要之,其实皆曰取人以言而已。贤之与不肖,正之与邪,终不在诗赋、经义之异。取于诗赋,不害其为贤;取于经义,不害其为邪……臣愚欲乞试法复诗赋,与经义兼用之。[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第15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858页,第8858—8859页,第8861页。
刘挚的观点也是两个方面。其一,经义取士,考生专用一家观点,甚至荒唐不经、蹈袭剽窃。而诗赋有声律法度,便于考官取舍。其二,诗赋命题多样,不会重复。而经义命题只出一经,必然重复。刘挚归纳云:“诗赋之与经义,要之,其实皆曰取人以言而已。”即是说,经义取士,并不能使得考生品德更加纯正或高尚。而以往攻击诗赋取士、主张经义取士者,都是从考生将来的品德修养、为官素质角度立论的。刘挚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经义取士的合理性。刘挚的科举考试方案是经义、诗赋两存,其实,偏重诗赋的立场非常明确。
朝廷很快就此颁布诏令:“礼部与两省学士、待制、御史台、国子司业集议闻奏。所有将来科场,且依旧法施行。”[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第15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858页,第8858—8859页,第8861页。虽然要求大臣们发表意见,同时明确科举制度将“依旧法施行”,即恢复诗赋取士的旧法。苏轼为此创作《复改科赋》,云:
新天子兮,继体承乾;老相国兮,更张孰先?悯科场之积弊,复诗赋以求贤。探经义之渊源,是非纷若;考辞章之声律,去取昭然。原夫诗之作也,始于虞舜之朝;赋之兴也,本于两京之世。迤逦陈齐之代,绵邈隋唐之裔。故遒人狥路,为察治之本;历代用之,为取士之制。追古不易,高风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号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之,不胜其弊。……三舍既兴,贿赂公行于庠序;一年为限,孤寒半老于山林。[4]〔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一第1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9、30页。
“新天子”是哲宗,“老相国”指司马光。苏轼对熙丰科举新制“经义取士”“三舍法”等都有批判,并将恢复旧法的功劳归于老相国司马光。旧党领袖司马光是元祐初首相,上述尚书省集体意见本来应该体现司马光的意志,苏轼如此颂扬也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熙丰新旧两派并不是事事对立,水火不容。在科举制度变革方面,司马光诸多意见与王安石一致。元祐初司马光依然坚持原来的立场,云:
至于以赋诗、论策试进士,及其末流,专用律赋格诗取舍过落,摘其落韵,失平侧,偏枯不对,蜂腰鹤膝,以进退天下士,不问其贤不肖。虽顽如跖、跷,苟程试合格,不废高第;行如渊、骞,程试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举人专尚辞华,不根道德,涉猎钞节,怀挟剿袭,以取科名。诘之以圣人之道,未必皆知。其中或游处放荡,容止轻儇,言行丑恶,靡所不至者,不能无之。其为弊亦极矣!神宗皇帝深鉴其失,于是悉罢诗赋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乃革历代之积弊,复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掩盖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己者取,异己者黜。[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一第15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975—8979页。
司马光立场非常鲜明,明确反对“诗赋取士”,坚持“经义取士”,同时肯定殿试论策,唯独对王安石以一家之说为准的科场录取标准提出批评。司马光的意见与前面叙说的尚书省班子意见明显有分歧,这是非常奇怪的。只能解释为尚书省旧党宰辅班子多数成员要求恢复“诗赋取士”,司马光是屈从者。事后不甘心,故再单独上奏疏。
司马光的意见同样获得许多旧党大臣的支持。旧党另一领袖人物吕公著,神宗朝就赞成经义取士。此时云:“先帝更新法度,如试进士以经术,最为近古。且仲尼六经何负于后世?特安石课试之法为谬尔。安石解经亦未必不善,惟其欲人同己为大谬尔。”[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八第16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939页。同样将神宗朝科举制度变革之重大失误归之于王安石个人。
又,监察御史上官均言:
经术以理为主,诗赋以文为工。以理者于言为实而所根者本,以文者于言为华而所逐者末。先帝去数百年之弊,不为不艰,而议者不计本末,乃欲袭前日诗赋之弊,未见其为得也。源深流长,事大体重,张官置吏之原,安危理乱之本,愿陛下详听而谨行之。[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四第15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060、9061页,第9060页。
朱光庭有《请用经术取士奏》:
臣窃以圣朝用经术取士,冠越前代。止是不当专用王安石之学,使后生习为一律,不复穷究圣人之蕴,此为失矣。若谓学经术不能为文,须学诗赋而后能文,臣以为不然。[4]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〇一二第9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99页。王存也说:“比废进士专经一科,参以诗赋,失先帝黜词律、崇经术之意。”[5]〔宋〕曾肇:《王学士存墓志铭》,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三八四第11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中书舍人彭汝砺言:“朝廷取士非古,其陋至于用诗赋,极矣。先皇帝受天明命,悼道之郁滞,奋于独断,初用经术造士,以革数百千年之弊,士知本且向方……诗赋不经,可以无辨,是犹滑稽俳优之戏,门巷讴唱之辞而已。”[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七第17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123页。
这些旧党大臣的意见与司马光都一致,仍旧主张“经义取士”。换言之,元祐朝政更化,全面推翻神宗朝变革举措,恢复种种旧制,“诗赋取士”为其中之一。然而,旧党许多头面人物立即具体到科举制度这一个问题上,认为“经义取士”制度是合理的,仅仅是王安石个人失误,予以小小纠正便可以了,不必大动干戈,恢复旧制。
旧党中更有调和者。右司谏苏辙面对“欲复诗赋,议上未决”的现状,主张“来年科场一切如旧,但所对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之学”。实际上是主张诗赋、经义两存,因为“先是,言者请兼用诗赋,尽黜经义,太学生改业者十四五”[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四第15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060、9061页,第9060页。。考生已经大量跟进朝廷“诗赋取士”的举措,坚持“经义取士”已经不现实。苏辙两存之的建议得到众多朝臣的赞同。毕仲游《经术诗赋取士议》云:“为今之策,莫若复诗赋以取士,而不累于科举,以进治经之人。……析诗赋、经义为两科,学诗赋者举进士,治经者举明经。”[8]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四〇〇第11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纷争过大,反而是折中者意见获得通过,即:朝廷最终采用苏辙、毕仲游等的调和意见。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三省奏立经义、词赋两科,下群臣议,从之”[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二第16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533页。。元祐二年(1087)十一月,朝廷又诏令云:“进士以经义、诗赋、论策通定去取,……将来一次科场,未习诗赋人依旧法取应,解发不得过元额三分之一。令礼部立诗赋格式以闻。”[2]〔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五之二五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508页。元祐三年(1088)是贡举年,朝廷两次诏令为诗赋、经义之争暂时画上句号。
经义和诗赋虽然两存之,但是,元祐三年(1088)是苏轼主持贡举,其偏颇诗赋的立场当然非常明显,因此再度引起众多朝臣的不满。这次贡举考试结束之后,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殿中侍御史翟思以及监察御史赵挺之、王彭年等谏官集体上奏:
见行科场诏条称:将来一次科场,如有未习诗赋举人,许依旧法取应解发合格人,不得过解额三分之一。以此观之,则是朝廷更无用经术设科取人之理,止以旧人未习诗赋,且于将来一次科场,量以分数收取,而欲阴消之故也。……伏望陛下深加省察,必存经义一科,令与诗赋并行均取,以为万世之利。[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〇第17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168—10172页,第10169页。
他们认为此前经义、诗赋两存之的数道诏令,只不过是消除经义科的过渡措施,故要求朝廷最终确立经义、诗赋两科取士的制度,并提出两科具体考试内容。他们的奏疏中,还有大段论证经义取士之必要性、诗赋取士之荒谬性的文字,虽然他们要求经义、诗赋两科“并行均取”,但这显然是一种折中调和的姿态。奏疏言及考生现实状况,则云:“臣等窃闻今太学举人与四方之士,观望朝廷意旨,已皆不复治经旨。凡干义理之书,一皆斥而不谈。博士所讲,与其父兄之训,不复更及高远。群居切磨,惟是论声韵,调平仄,事属对,校比拟,以轻巧靡丽为务。”[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〇第17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168—10172页,第10169页。宋代考生更加喜欢诗赋科,一直是不争的事实。
毕仲游是元祐三年(1088)殿试复考官,上《理会科场奏状》,自称:“守官以来,累蒙差入试院对读考校,熟见举人科场文字,颇知诗赋、经义取士利害之实。”他认为经义、诗赋之争的原因在于“诗赋、经义之利害固已未决,而又各匿其所短,暴其所长,此所以更相不信而无定说也。”他的辨析云:“盖经术者,古学也,可以谋道而不可以为科举之用;诗赋者,今学也,可以为科举之用而不足以谋道。”毕仲游最终坚持的是诗赋取士立场:“专复诗赋以取士,设嘉祐明经之科以待不能为诗赋之人,而又诏天下求穷经谋道、不累科举者,使传道于诸生,则政有并举,才无或弃,亦可以释民疑矣。”[5]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三八九第11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217页。
换言之,哲宗即位后首次贡举结束之后,经义与诗赋之争再起战端,争论不休。元祐四年(1089)三月,中书侍郎刘挚上书曰:“近日又将科场一事,摇动荧惑。昨元祐元年,两制、侍从、台省臣僚,讲议定夺,凡一年有余,又经圣览,方此施行。亦是将祖宗先帝之法,合诗赋、经义为一科,是万世有利无害可行之法。今人情已定,止是安石之党,力要用经义。臣愿陛下坚守已行之法,勿为浮议所动。”[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三第17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246页。此言将主张经义取士者,一棍子打入“安石之党”,赋予这场争论以特殊的党争政治意义。赵挺之等少数人固然可以归入“安石之党”,然而,谏官正副首长李常和盛陶都不是新党,刘挚欲从党争角度干脆利落地结束这场争论,其说辞牵强附会,难以服众。
旧党中有大量的主张经义取士者,刘挚故意抹黑法解决不了争端。元祐四年(1089)四月,礼部只得出台一个“经义兼诗赋”调和方案,具体如下:“经义兼诗赋进士听习一经: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赋及律诗一道;第三场论一道;第四场子史、时务策二道。经义进士并习两经:……不以人数多寡,各取五分。”[1]〔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五〇、五一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286—4287页。此方案获朝廷通过,确立为制度。
此方案一出台,又遭反对,尤其是针对诗赋、经义五五平分的录取原则。是年六月,左谏议大夫梁焘建议:
臣伏睹科举之制,以经义、词赋进士各取五分。窃闻进士多从词科,十常七人,或举州无应经义者。如此,则五分之限固不可行。臣愚欲乞圣慈特赐指挥,更不以两科分取,止以两科入试人数多寡,用解额均取合格之人。南省奏名依此。所贵事归乎一,允协至公,上副陛下乐育英材之意焉。[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九第17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377页。
此奏章说明一个事实:诗赋科一经恢复,多数考生皆选择此科。梁焘要求按实际参试人数的比例录取,那么,录取当然以诗赋科居多。
元祐四年(1089)苏轼外放知杭州,他以杭州及以往见闻为例,阐述经义、诗赋平分名额的不合理性。云:
天下学者日夜竞习诗赋举业,率皆成就,虽降平分取人之法,缘业已习熟,不愿再有改更。兼学者亦以朝廷追复祖宗取士故事,以词学为优,故士人皆以不能赋诗为耻。比来专习经义者十无二三,若平分解名,委是有亏诗赋进士,……臣在都下,见太学生习诗赋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闻蜀中进士习诗赋者,十人而九。及出守东南,亲历十郡,又多见江南、福建士人皆争作诗赋,其间工者,已自追继前人。专习经义,士以此为耻。以此知前言天下学者不乐诗赋,皆妄也。……欲乞朝廷参详众意,特许将来一举,随诗赋、经义数多少,各纽分数发解。[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四第17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466、10467页。
苏轼以具体见闻和数字统计,证实梁焘的奏疏,所以苏轼的意见与梁焘一致。
是年十二月,礼部据众人所奏,称诗赋、经义两科“就试人数不定,则解额难以均当,终非通法,似不可久行。”朝廷随即诏令:“来年科场,以试毕举人分数均取。后一次科场,其不兼诗赋人解额,依元祐三年六月五日所降朝旨。如有未习诗赋举人,许依旧法取应解发合格人,不得过解额三分之一。已后并依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敕命。”[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六第17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07页。此完全采用梁焘、苏轼等人意见,录取名额倾向诗赋科。
综上所述,高后垂帘、旧党当政之元祐期间,经义取士和诗赋取士争论虽然非常激烈,朝廷也反复推敲,频频修正制度,但是,偏向诗赋的立场非常明显。
哲宗亲政,启用新党,朝政再度反转,在科举制度上也得以直接表现。绍圣元年(1094)五月,朝廷颁布诏令:“进士罢试诗赋,专治经术。”[5]〔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五五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289页。诗赋科又一次被取消。然而,朝廷需要文学人才,起草诏诰之类四六公文。作为补救手段,罢诗赋科当日就设立了“宏词科”。史载:
中书省言:“有唐随事设科,其名不一,故有词藻宏丽、文章秀异之属,皆以众之所难,劝率学者。今来既复旧法,纯用经术取士,其应用文词,如诏、诰、章、表、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之类,凡诸文体,施之于时,不可阙者。在先朝亦尝留意,未及设科。”诏:“别立宏词一科。每科场后,许进士登科人,经礼部投状乞试。依试进士法差官考校,试诏、诰或表、章、杂文共三篇。应者虽多,所取不过十人。”[6]〔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二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448页,第4449页。
是年七月,再诏云:“宏词今后每年许经礼部投状,仍附春试。虽多,所取不得过五人。”[7]〔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二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448页,第4449页。是年秋,再罢制科,宏词科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绍圣二年(1095)正月,礼部颁布宏词科考试具体规则,云:
宏词除诏、诰、赦、敕不试外,今拟立程试考校格。一,试格十条:章、表,依见行体式;赋,如唐人《斩白蛇》《幽兰》《渥洼马赋》之类;颂,如韩愈《元和圣德诗》、柳宗元《平淮夷雅》之类;箴,如扬雄《官箴》《九州箴》之类;铭,如柳宗元《涂山铭》、张孟杨《剑阁铭》之类;诫谕,如近体《诫谕风俗》《戒百官》之类;露布,如唐人《破蕃贼露布》之类;檄书,如司马相如《喻蜀檄》之类;序,如颜延之、王融《曲水诗序》之类;记,亦用四六。以上考试官临时取三题作一场试。其章、表、颂、檄书、露布、诫谕、序、记,并限二百字以上成;箴、铭并限一百字以上成;赋八韵,限三百字以上。一,考格三条:词理俱优者为上等,词理次优者为次等,词理超异者取旨。[1]〔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三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449页。按:此段文字之错、缺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〇第1册第419页补正。
是年三月,首次举行宏词科考试。三省言:“试宏词衡州司法参军黄符、滁州司法参军罗畸、开封县主簿高茂华、真定府户曹参军赵鼎臣、瀛州防御推官知鄂州崇阳县事慕容彦逢,考入次等,各循一资。”[2]〔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四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449页。然而,此后每年都举行宏词科考试,不同于进士三年一贡举制度。
二、经明行修取士
司马光对于科举制度之变革,有两个坚持不懈的基本立场——经义取士和乡举里选,这都是从考生道德品质取舍的角度考虑问题,哪怕在实践中一再被证明是不可行的,是荒谬可笑的。完全推行经义取士或乡举里选,司马光也明白是不可操作的,于是,他推出修改版:经明行修科取士。
经明行修,原指通晓经学、品行端正。经明,回应了经义取士的立场;行修,回应了乡举里选的立场,这都是司马光所醉心的。于是,在元祐初科举制度向“诗赋取士”一定程度回归之同时,司马光又提出“经明行修取士”的补充建议:
每岁委升朝文官保举一人,不拘见在任不在任,是本部非本部,各举所知。……臣窃料此法初行,其奔竞属请,固不能免。若朝廷必坐举主,无有所赦,行三五人后,自皆审择其人,不敢妄举。如此则士之居乡、居家,独处暗室,立身行己,不敢不审,惟惧玷缺有闻于外矣。……第一场先试《孝经》《论语》大义五道,内《孝经》一道、《论语》四道。……次场试《尚书》,次场试《诗》,次场试《周礼》,次场试《仪礼》,次场试《礼记》,次场试《春秋》,次场试《周易》大义,各五道。令举人各随所习经书就试,考校过落,如《孝经》《论语》法。次场试论二道:一道于儒家诸子书内出题,一道于历代正史内出题。次场试策三道,皆问时务。考策之日,方依解额及奏名人数定去留,编排高下。以经数多者在上;经数均,以论、策理长文优者在上。其余经明行修举人,并于进士前,别作一项出榜解发。及奏名,至御前试时务策一道,千字以上,弥封官于号上题所明经数及举主人数。候校考详定毕,编排之时,亦以经数多者在上;经数均,以策理长文优者在上;文理均,以举主多者在上。其经明行修举人,亦于进士前别作一项编排,先放及第。其推恩注官,比进士特加优异。他时选择清要官、馆阁、台谏等,并须先取经明行修人。[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一第15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976—8978页。
经明行修科有以下要点:其一,必须经过推荐,数量不大;其二,考试过程,采用弥封、誊录等保密措施;其三,考试以经义为主,旁及策论;其四,其录取和升迁都“别作一项”,“特加优异”。司马光明白推行这项考试之后,必然造成“奔竞属请”之现状,但他认为严格执行“必坐举主”制度,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在“人治”独裁专制社会,企图通过推荐制公正选拔人才,完全是痴心妄想,这是一再被汉代以来的察举制等所证明了的。司马光等身处独裁体制之下,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所谓的时代局限性。苏轼、刘攽等官员已经从现实操作中领悟到乡举里选之不可行,比之司马光等冬烘,观念领先一步。
司马光也知道现行的进士试是不能废除的,所以特别强调:
臣所乞置经明行修科者,欲使举人知向去科场,朝廷崇尚行义,不专取文学,所以美教化、厚风俗。比于经义、文体,尤为要切,宜使举人预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况与进士旧法两不相妨。[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六第15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117—9118页,第9117页。
司马光是元祐初年主持朝政者,他的政治理念能够一定程度得以落实。所以,元祐元年(1086)四月,朝廷颁布诏令:
每遇科举诏下,令文官升朝以上、无赃罪及无私罪者,于应进士举人,不拘路分,不系有服亲,各奏举经明行修一名。候将来解发及南省奏名内,每人名下注“经明行修”字,至殿试唱名日,各升一甲姓名。[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六第15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117—9118页,第9117页。
司马光的建议正式成为朝廷诏令,就会有许多附庸者跟进,或为政见相同,或为阿谀时相,他们的意见甚至更加极端。曾肇《上哲宗论经明行修科宜罢投牒乞试糊名誊录之制》云:
今设经义、诗赋等科,施之一时则可矣。然皆取人以言,而不本其行,方之于古,臣窃以为未也。至于诏内外官举经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稍优其礼,则不独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其意庶乎近古。然徒使举之,而不由乡里之选,又无考察之实。与斯举者,随众投牒,试于有司,糊名、誊录,校一日之长。则不唯士失自重之谊,且于课试之际,无以别异于众人。则所谓本其行者,亦徒为虚文而已,恐未称所以命官荐举、优其恩典之意也。……则经明行修谓宜别立一科,稍仿三代、两汉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损益,要之,无失古意而已。至于投牒乞试、糊名誊录之类非古制者,一切罢之。……人才既盛,风俗既美,则所谓经义、诗赋等科,非以行谊进者,人将耻为之,不期于废而自废矣。如此,则经明行修之举,有得士之实,不为虚文而已也。[3]〔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八一上册,吴小如等校点,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78—879页。
既然是重士人品德之乡举里选,当然就没必要糊名誊录,司马光的复古建议还是不彻底。所以,曾肇干脆要求“投牒乞试、糊名誊录之类非古制者,一切罢之”。王安石之三舍法,司马光之经明行修科,都不敢取缔糊名誊录,实际上是意识到“人治”体制下人才选拔过程中这些保密制度的独特效能。只有泥古不化如曾肇者,才有这样荒唐的建议。其结论云:士人将“耻为”经义、诗赋等进士试,进士考试“不期于废而自废”。换言之,完全回归到汉代的察举古制,彻底废除科举制度。曾肇之妄想,证之后世史实,完全是痴人说梦。
朝廷中许多行政经验丰富的旧党大臣,深知贯彻乡举里选宗旨之经明行修不可取,又不能直接驳回司马光的主张,便提出修正意见。是年六月,御史中丞刘挚奏疏云:
然使升朝官举之,不若使州郡以上举之便。……然则选举之利未见,而奔竞之俗先成,此不可四也。……故臣愿每遇科场诏下,委逐州长吏奏举经明行修进士一名。仍以应举实数二百人为率,不满二百人听举一名。每二百人加一名,至三人止。监司转运判官以上于本路,在京台谏以上于开封府、国子监,各许奏举一名。非乡贯及不经学校,或无可应诏,并听勿举。自余升等推恩、理举主同罪犯等,并依元降朝旨。[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〇第15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223—9224页,第9224页。
追溯乡举里选之本意,当然是州郡地方推荐更加合适。刘挚列举升朝官举荐的四大弊病,其中“选举之利未见,而奔竞之俗先成”是要害之所在。在“人治”专制社会,通过“人治”手段选拔人才,肯定无公正可言,必然落入“奔竞贿赂”的陷阱,无论是三舍法还是经明行修科。所以,刘挚补充说“三代乡举之制未易遽复”[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〇第15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223—9224页,第9224页。,可以看出刘挚事实上是反对乡举里选的,只是碍于司马光政坛大佬的脸面,只能提出相对折中的调整方案。
刘挚的建议不久得到落实。元祐二年(1087)正月,朝廷诏令云:
及举经明行修,京东西、河北、陕西路各五人,淮南、江南东西、福建、河东、两浙、成都府路各四人,荆湖南路、广南东西、梓州路各二人,荆湖北路、夔州、利州各一人,委知县当职官司同保任申监司,监司再加考察以闻。仍充本州解额,无其人则阙之。[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四第16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593页。
诏令限定各路举荐经明行修科的确切人数,并说明占原来地方进士发解试名额。因此,设立经明行修科,就不会增加朝廷取士负担,只是从原来进士试中割出极小的份额,分配给经明行修科。经明行修科作为选拔官员的一种尝试,不影响科举大局,被朝廷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当然,其作用也变得可有可无,实际上被销解了。
与司马光意见相同者,看出朝廷此举对经明行修科之危害性,提出反对意见。右司谏王觌云:“使经明行修而被举者遂夺其解额,则后进之士视其乡之经明行修者,其势必有内怀忌嫉,而谤读言诋讦,无不为者矣。如此,则学者之完人益少,而经明行修之举不几于废乎?盖必然之理也。”王觌要求“于本州解额外解发”[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五第16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630—9631页。,为经明行修科另外设立解额,朝廷并没有予以理会。那么,“经明行修之举不几于废”的结局就是必然的。
经明行修科出发点与三舍法相同,重“人治”荐举,一经实施,立见弊端。苏轼元祐三年(1088)权知贡举,省试之后,归纳此年科举制度变革得失,其中一条云:
经明行修,尤是弊法。其间权势请托,无所不有,侵夺解额,崇奖虚名,有何功能,复令升甲?……其经明行修一科,亦乞详议,早行废罢。[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九第17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960页。
哲宗即位初,苏轼因司马光荐举入朝。然而,针对司马光的错误意见和改制,苏轼丝毫不留情面,斥其为“弊法”,要求早日废罢。苏轼的耿直敢言,是其仕途屡屡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
经明行修确实是“弊法”,元祐四年(1089),朝廷再对经明行修科做出限制,诏令云:“今后并遇降诏方许奏举,所有岁举知州人及每遇科场奏举经明行修指挥,并不施行。”[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八第17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337页。这是将前几年关于荐举经明行修的诏令一概废除。但是,元祐八年(1093)二月,监察御史黄庆基又批评当时的经明行修科有“侥幸之徒,因缘请托,不容无滥进者”的弊端,要求“凡荐经明行修之士,必须精加考察,委有术业行谊为乡党所尊、士论所服者,乃许奏荐”[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一第19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450页。。可见,元祐年间经明行修科荐举方式反复有所改变,科目考试则一直存在。
三、科举制度其他方面的讨论
神宗朝科举制度变革,大致为四项内容:省试经义取士,殿试对策,三舍法,废除制科。针对后三项内容,哲宗朝同样出现众多讨论或政策反复。
哲宗朝首次贡举,殿试用策则不变。元祐三年(1088)二月诏:“殿试经义、辞赋举人,并试策一道。”[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八第16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938页。这一年九月贡举结束之后,朝廷才诏令:“尚书、侍郎、学士、待制,两省、御史台官,国子监长、贰,详议殿试用三题法。”[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四第17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060页。这一次讨论,朝臣又产生严重分歧。反对殿试用策者言:
用策以来,其弊不一。其始用也,骤以政务赐问于廷,即未测知,可使人自献其说。然既著为定例,诸生在外,莫不宿造预作之,文不工者可以假托他人,学不充者可以累集古语,试日就所问目贯穿以成文尔。……人主临轩,其所询访,必当时之大务也。如今春殿试,必问去冬寒雪之异及官冗之弊。此类皆举子所知,故宿造预作者可以应对而无疑。考校之官凭此以辨优劣,以第高下,安得实也?惟三题散出诸书,不可前料,诗赋以见其才,论以知其识,且无以伸佞时之说焉。盖对策之流,本缘进取而来,利害交其前,得失撄其心,于是佞辞以取说,妄意以希合者,比比皆是,如昨对策以阴雪为瑞之类者是也。……臣请将来殿试,即用祖宗试三题之制,仍预赐指挥,以信学者。[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五第17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101—10102页,第10102—10103页。
殿试用策,考试的内容是时政,考生可以预测。考生为求取功名,自然不敢批评时政,唯有迎合阿谀。反对用策者指出殿试策问两大弊病:宿造预作和佞辞以取说,切中要害。与用策比较,诗赋论三题相对合理。其一,题目“散出诸书,不可前料”;其二,能够考察士人才与识之多种能力;其三,无法“伸佞时之说”。所以,这些大臣建议恢复三题考试。
坚持试策者则云:
诗赋之用,因沿至今,莫之能改。神宗皇帝以为非,天子临轩,所以延见贡士,询求治道之体。熙宁三年始改问策,迄于元丰,五赐策矣。乃者陛下遵先帝之旧,亲策进士,所问灾异、侵伐、官冗、财费之类,皆今日急务,不可以已。……议者徒知对策之宿造预作,不知辞律之学亦有记诵类集之患;知进士之备问,不知贤良茂才之备问尤详也。臣等以谓学校教诸生,州郡发解,礼部考贡士,今已悉用诗赋,足以审其辞。所有御前试进士,宜一依先帝故事试策,合于古义,于体为允。其御试对策,虽有文采,而于所问义不相当,若词涉谀媚及文理疏浅者,宜约旧制量定分数,取旨黜落,不得雷同入等。如此则士无滥中,而考官不敢率意升降矣。[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五第17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101—10102页,第10102—10103页。
他们竭力反驳关于试策“宿造预作”和“词涉谀媚”的批评意见。他们认为:诗赋同样可以预先记诵准备,且殿试之前已经有足够的诗赋考试。同时,原来的“贤良茂才”制科考试内容也是时政,参试者“备问尤详”。因此,他们认为神宗朝变革是正确的,今后殿试都应该“依先帝故事试策”。这里,他们含糊了两个问题。其一,诗赋和用策的预先记诵,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诗赋题目无法预料,所以不可能针对性地记诵;策题大致可以估摸出来,完全可以针对性记诵。其二,制科“备问尤详”,不能说明其合理性,这同样是弊病。不应该其他科目考试存在弊病,殿试用策也可以参照。
元祐六年(1091)殿试依然用策,上述讨论没有带来改变。元祐八年(1093)三月,中书执政班子再次要求殿试恢复诗赋论三题,批评殿试对策,诏令同意中书建言。史载:
中书省言:“进士御试答策,多系在外准备之文,工拙不甚相远,难于考校。祖宗旧制,御试进士赋、诗、论三题,施行已远,前后得人不少。况今朝廷见行文字多系声律对偶,非学问该洽,不能成章。若不复行祖宗三题旧法,则学者未知朝廷所向。检会已降指挥,将来一次科场,如有未习诗赋举人,许依旧法取应,解发合格人不得过解额三分之一,已后并兼试诗赋。取到国子监状,太学见管生员二千一百七十五人,内二千九十三人习诗赋,八十二人经义不兼诗赋,以此可见中外学者习诗赋人数极多。”诏:“来年御试,将诗赋举人复试三题,经义举人且令试策,此后全试三题。”[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二第19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472—11473页。
经元祐年间引导,考生绝大多数选择诗赋科,经义科已经销解殆尽。宣仁太后垂帘末年,最终下决心恢复殿试诗赋论三题,且规定再经过一届销解,此后殿试“全试三题”。宣仁太后元祐八年(1093)九月去世,她主导的朝政还持续了数月。绍圣元年(1094)二月,礼部要求“立《御试三题条》,并约束”,获朝廷同意[2]〔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选举》八之三七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392页,第4392页。。次月,朝廷再次诏令:“令次御试举人,依旧试策。”[3]〔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选举》八之三七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392页,第4392页。将之前的决策推翻。即:宣仁太后主政末年规定的殿试改用诗赋论三题,未得一次执行,就被废除了。由此,形成熙宁三年(1070)殿试用策之后一直没有改变的现状。
针对熙丰新法,部分旧党的另一批判对象是三舍法。元祐元年(1086)四月,左司谏王岩叟奏云:
三舍之法立,虽有高材异能,未见能取而得之,而奔竞之患起。奔竞之患起,而贿赂之私行;贿赂之私行,而狱讼之祸兴;狱讼之祸兴,而防猜之禁繁。博士劳于簿书,诸生困于文法,非复浑然养士之体,而庠序之风或几乎息,此识者之所共叹也。臣窃谓庠序者,所以萃群材而乐育之,以定其志业,养其名誉,优游舒徐,以待科举也。不必以科举之外,别开进取之门,多岐以支离其心而激其争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战于胸中,损育德善道之淳意,非所以笃教化、成人材也。臣愚乞鉴已然之弊,罢三舍法,开先生弟子不相见之禁,示学士大夫以不疑。[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四第15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059页。
三舍法之种种弊端,在神宗朝已经引起广泛非议。王岩叟这里更是具体罗列了“奔竞”“贿赂”“狱讼”“防猜”等等,要求取消三舍法,“不必以科举之外,别开进取之门”。这是对三舍法的彻底否定,所言皆切中肯綮。三舍法元祐以后时兴时废,始终不成气候,就是与奔竞、贿赂等根本性的弊病相关。
元祐初亦有大臣赞同三舍法者。毕仲游《学校议》云:
盖闻熙宁之初,变诗赋为经义以取士,增太学郡国学官,设三舍,改定式令,以布行之。四方之人至京师者几数千,而是非不明,好恶不一,道艺进取未有异也。今复欲变经义为诗赋,退学官,更定式令以从事,则学士大夫之所以自得者果安在耶?试略言之。三代乡举里选之法虽难卒行,宜亦仿其大者,使学士大夫有以自得。而后诏先生博士,卒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长幼之序,与夫是非、好恶、道艺之正。而诗赋、经义则如古以射取士之法,行同能偶,然后序之。别为贡举,以待科举之士,存之而勿论。[5]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四〇〇第11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毕仲游顺应元祐初政治形势,对神宗朝之三舍法有所批评,但是,批评相当轻描淡写,只是提到生员的“是非不明,好恶不一”。毕仲游醉心于乡举里选之古法,赞成三舍法的态度比较明显,要求“别为贡举”,进士试和三舍法两存之。御史中丞胡宗愈意见则更为直接,坚持三舍法可行:“先帝聚士以学,教人以经,三舍科条固已精密,宜一切仍旧。”[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四第16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831页。
神宗朝三舍法一直没有形成相应的规模,元祐初对此争论也不多。根据绍圣年间重新掌政的新党要求恢复“上舍推恩”,元祐初肯定废除了三舍法直接取士,或称上舍释褐。不过,元祐年间三舍法作为太学教学升级方法一直没有被废止,一直是进士试考生的来源之一。元祐七年(1092)六月,礼部讨论太学解额问题,就言及“上舍一百人,内舍三百人,外舍二千人”[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四第19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305页。,这是当时太学三舍保持的规模。
哲宗亲政数月之后,全面恢复熙丰新政。绍圣元年(1094)三月:
监察御史郭知章言:“先皇帝隆尚儒术,增广庠序,设三舍之法,应上舍生上等中选者,有取旨推恩之例。然择之至精,俟之至久,故其得者亦难。自元丰以来,十余年间,上舍生推恩者林自一名而已。诱进激劝之法,莫善于此。元祐新令,推恩之例已罢,士论惜之。宜复元丰上舍推恩之例。”诏:“太学合格上舍生上等推恩,免省试。每次科场不得过二人,仍附春榜人数。余依元丰二年十二月指挥。”[2]〔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一二第3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977页。
三舍法自此得以完整恢复,通过三舍选拔,可以直接释褐进入官场。最终结果为:上舍“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一第12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328页。。
此外,旧党要求恢复制科考试。太常少卿鲜于侁进言云:“制举,诚取士之要,国朝尤为得人。王安石用事,讳人诋訾新政,遂废其科。今方搜罗俊贤,廓通言路,宜复六科之旧。”[5]〔元〕脱脱等:《鲜于侁传》,载《宋史》卷三四四第31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938页。元祐二年(1087)四月,朝廷即下诏:“今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自今年为始。”[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九第16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730页。元祐三年(1088)九月,“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谢悰”[7]〔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一六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434页。,哲宗朝的首次制科考试就是按照仁宗朝惯例,在贡举年的秋季举行。
绍圣元年(1094)秋,制举考试结束之后,亲政的哲宗与执政新党大臣议论制举,史载:
上曰:“前日观所试策,亦与进士策何异?先朝尝罢此科,何时复置?”章惇等对曰:“先朝初御试进士策,即罢制科。元祐二年复置,诚无所补。初举得谢悰,次举得王当、司马槱等,闻极疏谬。”上曰:“极不成文理。”李清臣对曰:“在汉亦不设科,遇选获异材,或因材、或因灾异,策问大事,即临时特召。”上曰:“今已复进士殿试策,此科既无异进士策,况进士策其文理有过于此者。”郑雍对曰:“顾其人何如尔。然自来多言时政阙失。”上曰:“今进士策亦可言时政阙失。”因诏罢制科。[8]〔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二〇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436页。
新党重新执政,制科再度被废除。
就科举制度而言,新旧两党领袖大臣有诸多共同主张。实际上,在科举制度变革方面,没有新旧党争之区别。然而,元祐初旧党当政,全盘否定新法,神宗朝科举制度之举措受池鱼之殃。当时,因为众多旧党领袖人物的主张与熙丰新党一致,元祐年间只是有限度地恢复旧法。具体而言,诗赋与经义取士两存而偏向诗赋取士,殿试用策不变,三舍法并没有完全废除,制科考试恢复。哲宗亲政,全面恢复熙丰新法。曾布论及科举解额时,云:“近岁奸憸之立朝者,多以元丰之法为不可改,一有议论及此,则指以为异意,欲以罗织善类,又或挟此以遂其私意。”[9]〔宋〕曾布撰、程郁整理:《曾公遗录》卷七,载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八,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143页。即是说,新党重新执政后,熙丰新法执行得更加彻底。哲宗朝在新旧党争的反复中,科举制度也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