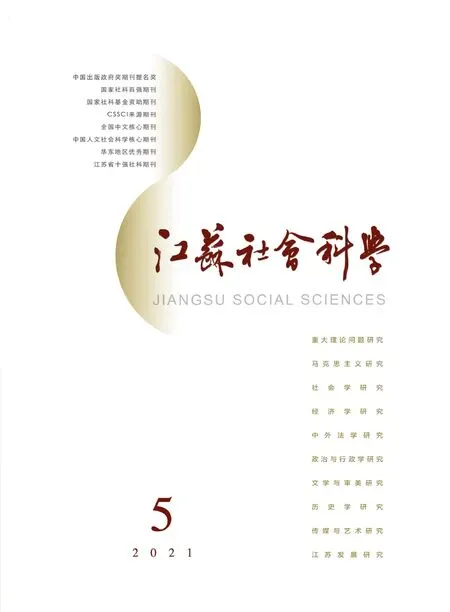城乡中国时代的村庄再组织化
周 立 王晓飞
内容提要 城乡中国时代已经到来,对于乡村发展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正如今天,城市居民消费升级所带来的“四洗三慢两养”新需求,不仅为村庄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为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宏观结构,以及微观个体的去组织化困境带来了巨大挑战。然而,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发现,西方的集体行动理论观点无法有效解释城乡中国时代村庄再组织化现象。为此,我们论证了宏观结构变化与微观个体理性选择在村庄场域的交织互动过程,发现“中心人物-关键群体-后续参与者”通过理性选择而渐次行动,将创造乡村新供给的设想付诸实践,促成了城乡互为供求、有序互动的融合,并巩固了传统村庄社会结构,形成现代性与乡土性相结合的新村庄社会结构,实现了村庄再组织化的不断升级。我们认为,聚焦村庄这一中观场域,将微观的脱离社会情境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与宏观的抽象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结合起来,从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探究乡村发展问题,才更加符合中国实际。
在我国由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的背景下讨论乡村发展问题,必须同时具备城市和乡村两种视野。正如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带来的新需求,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那样,城乡中国正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然而,长期的去组织化,使得大多数村庄呈现低组织化状态,而无法为这一变化提供新的发展机遇。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认为,只有实现村庄再组织化,才有可能抓住城乡中国时代的新机遇,战胜村庄低组织化的挑战。或者说,是以组织振兴促进乡村振兴。下面,本文将在城乡中国时代背景下,讨论村庄再组织化是否必要和如何可能,以及由此带来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机遇: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乡土中国”命题,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1、13页。费孝通提出的“乡土中国”内涵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乡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二是农民生产的土地黏着;三是社会生活的终老是乡[2]周立:《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福建日报》2018年6月27日。。当时,中国的城市化率不足10%,到了80年代《乡土中国》一书修订之时,中国的城镇化率也不过20%,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把城乡之间的各个大门都关得严严实实[3]周其仁:《城乡中国(下)》,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页。。
是改革开放打开了城乡之间的重重大门,使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从三级所有到两权分离、再到三权分置的转变。与此同时,农业经营制度也经历了从统一经营到双层经营、再到多元经营的转变[4]郑淋议、罗箭飞、洪甘霖:《新中国成立70年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历史演进与发展取向——基于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经营制度的改革联动视角》,《中国土地科学》2019年第12期。。工业化经历了从国家工业化到乡村工业化、再到沿海工业化的转变[5]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经过长期的结构变迁,在21世纪的近20年间,上述三个内涵已经转变为:一是乡村人口不再占绝大多数,或是人口城乡各半;二是农民收入不再以土地产出为主,而是收入多元;三是社会生活已经高度流动,不再是终老是乡[6]周立:《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福建日报》2 0 1 8年6月2 7日。。中国社会已经从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进入到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7]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城乡中国时代的到来,使生产要素从由乡到城的单向流动,转变为由城到乡的反向流动,再到城乡要素双向互动,更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契机。首先,国家政策鼓励并引导人才、资金等回流乡村。比如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2009、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提鼓励农民工回流,2015、2016年还分别发布了《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2020年初,国家发改委等19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更进一步提出“鼓励地方建设返乡入乡创业园和孵化实训基地”。中央如此密集出台推动返乡入乡创业政策,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提供了足够的政策支持。在资金上,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此后连续八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再提这一政策,且鼓励投资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其次,当大量农村人口“离土又离乡”时,工商资本也以其特有的敏锐性,看到了农村以土地为主的资源型资产的巨大价值,以及资源要素再定价的巨大升值空间,同时也看到了农村正以金字塔型的产业结构对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以及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发挥重要价值,进行着由城市到乡村的要素流动[8]周立:《“城乡中国”时代的资本下乡》,《人民论坛》2018年第28期。。伴随着工商资本下乡,人才、技术、先进的管理理念等也不断注入乡村。与此同时,饱受城市病困扰的市民把下乡体验生活作为一种新潮流,并催生出“四洗三慢两养”的新需求。据粗略估算,这一新需求的消费额每年将超过12万亿元[9]“四洗三慢两养”中的“四洗”是指乡村社会可以帮助城市人“洗胃、洗肺、洗眼、洗心”;“三慢”则与国际上兴起的“三慢”运动密切相关,是指乡村社会可以帮助城市人享受慢食、慢村、慢生活的一种方式;“两养”是指乡村可以提供养老、养生空间,帮助城市人安度退休和休闲时光,实现与自然共生、与社会和谐。参见周立:《乡村振兴的核心机制与产业融合研究》,《行政管理改革》2 0 1 8年第8期。。即农业的多功能性使得乡村具有满足城市居民新需求的潜力。如果乡村能够利用下乡资本,提供满足城市居民新需求的有效供给,则城乡良好互动的格局将有可能实现。
二、挑战:村庄低组织化
然而,面对城乡中国时代的发展机遇,我们也看到,只有少数村庄抓住机遇并脱颖而出,但更多的情形是村庄缺乏满足新需求的供给能力。究其原因,这与当前村庄低组织化的现状有关[1]组织化的含义可以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进行理解:从动态角度来看,组织化是指不同的个人因共同目标,依据一定的规则和程序,集合成一个组织的活动体;从静态角度来看,组织化是指一定时期的组织化活动过程的结果表现,即通常所说程度高或低的组织化。参见吴琦:《农民组织化:内涵与衡量》,《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至21世纪全面取消农业税,国家逐步退出了对乡村社会的直接控制和干预,甚至退出了对农业农村的公共服务。由于国家不再直接提供组织资源,且又经历了长时期的去组织化过程,导致乡村社会呈现出低组织化的状态[2]吴重庆、张慧鹏:《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今天,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各地普遍设立,特别是设立了各类专业合作社等,乡村社会的低组织化更加明显。如有学者对陕西关中地区果蔬专业合作社进行调研发现,社员们并没有看到合作社在统一销售、纵向发展(如二次加工、分拣、定级等)等方面发挥作用,约70%的社员完全不了解合作社的运营,他们与组织之间的利益关联松散[3]李敏、王礼力、郭海丽:《农民组织化程度衡量及其评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在农村,多年经营的经济领域的组织化程度尚且不高,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组织化更是不足。
随着城乡中国时代的到来,低组织化的弊端逐渐显现。如在乡村经济发展方面的弊端主要有:第一,乡村缺少对接国家财政转移资源的组织,目前国家财政转移资源主要通过“项目制”或直接“一卡通”到户的形式进入乡村社会[4]贺雪峰:《农民组织化与再造村社集体》,《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一方面,国家转移资源与亿万分散的小农户直接对接的形式,带来过高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阶层分化的乡村社会,进村的项目会被农村精英所“俘获”,无法惠及真正需要的群体,使得资源输入的效果大打折扣[5]温铁军、杨帅:《农民组织化的困境与破解——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人民论坛》2011年第29期。。第二,“原子化”的小农户难以有效对接大市场[6]李霖、郭红东:《小农户集体行动研究文献综述——基于市场准入视角》,《中国农村观察》2014年第6期。。一方面,小农户在面对下乡工商资本时,缺乏谈判能力,往往会沦为资本的雇佣者,只能为资本提供土地和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小农户在销售农产品时作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承担着农业生产的高风险,却只能得到被市场空间挤压的低利润。第三,低组织化的状态导致村庄难以形成内生发展的动力,村庄的发展举步维艰,使得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这反过来又进一步阻碍了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的形成。总之,低组织化导致外部资源无法“为我所用”,以及内部发展动力不足。内外交困的困境,使乡村社会无法对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以满足城乡中国时代市民对乡村“四洗三慢两养”的新需求,阻碍了城乡良好互动格局的形成。
三、应对:村庄再组织化
(一)村庄再组织化的内涵界定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看到,学界对于乡村组织化的探讨,多以宏观意义上的农民组织化居多,即具有“农民”身份的“人”的组织化,其有着具体而明确的行动目标,但没有明显的地域界限。当然,也有少数学者聚焦到中观层次,从村社集体再造的角度进行了探讨[1]贺雪峰:《如何再造村社集体》,《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但本文认为,此类探讨可以归结为村庄组织化,即以村庄或村落聚合体为参与单元、以全面建设乡村生活为手段、以提升乡村生活价值为目标、以村庄成员全员参与的农民组织化为实现形式,且具有明显的地域界限。也就是说,农民组织化与村庄组织化在组织目标、参与成员、治理形式、组织资源、参与成本与收益以及农民主体性的实现程度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别[2]毛刚强:《新农村建设:农民组织化还是村庄组织化》,《中国乡村发现》2007年第5期。。笔者在全国多地进行乡村调研发现,现阶段乡村组织化实际上更多的是以村庄全面建设与发展为目标,村庄内集体成员平等参与,充分利用村庄的各类资源实现发展,并建立起利益关联紧密的共同体,即村庄组织化。如陕西的袁家村、浙江的鲁家村与何斯路村。本文认为,村庄组织化可以被视为实现农民组织化的一个重要形式。
一般而言,再组织化,即指重新组织化,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不适应新的治理情景的原有组织进行解构、更新或者改造;二是社会中的个体或者群体基于新的一致性目标而组织起来,从而重构出新型社会组织[3]胡重明:《再组织化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以浙江舟山“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3年第1期。。而村庄再组织化,则是指村民以个人利益为主导、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建立起具有合作意识、公私兼顾的关系模式和以群体为单位的社会组织[4]王颖:《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是村民集体行动的结果。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再组织化,还有另外两层含义:一是两种时代背景下的组织化有所不同,城乡中国时代的村庄组织化是以自下而上的自愿发起为主导的,其组织是典型的自组织;而建国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是国家行政力量主导、通过自上而下的推动来实现的,其组织是典型的他组织[5]罗家德、孙瑜、谢朝霞、和珊珊:《自组织运作过程中的能人现象》,《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二是表明村庄组织化的动态过程,自人民公社解体至21世纪初取消农业税,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长时期的去组织化进程,城乡中国时代的村庄组织化是“组织化(他组织)—去组织化—再组织化(自组织)”动态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
(二)村庄再组织化的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乡村发展不充分。面对这一结构性困境,多数农民在理性的驱动下,做出离土又离乡、进城难回乡的无奈选择。有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9亿人,其中“80后”和“90后”农民工占比达48.6%[6]国家统计局:《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0年4月30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30_1742724.html。。近年来,返乡入乡创业的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据农业农村部2021年3月发布的数据,2020年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已达1010万[7]人民网:《去年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超千万 三部门多措并举部署今年重点工作》,2021年3月1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4355709367915136&wfr=spider&for=pc。。此外,出于子女教育、在城市安家落户的考虑,全家迁入各级城市的农民工家庭也日益增多[1]周少来:《从失衡到融合:乡村结构之变及其治理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相较于留守农村,进城农民虽然能获得更高收入,但其返乡创业意愿也会处境化地浮现。一方面,农民工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却拿着与付出不相称的工资,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仍然悬殊,当农民工将自己的投入/产出与参照对象的投入/产出进行比较时,会产生不公平感[2]方学梅:《不平等归因、社会比较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另一方面,当支配城市发展的强逻辑对弱逻辑进行压制,使得有能力、想参与社会活动的群体失去公平竞争的机会时,在特定群体中便会产生被排斥感[3]张广利、赵云亭:《特大城市社会心态风险:特征、机制与治理》,《长白学刊》2018年第5期。。离开乡村的熟人社会网络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农民不仅难以融入新环境,更无法享受到与市民均等化的社会服务,这种来自社会关系和参与方面的不对等,使得农民产生强烈的被排斥感。留守村庄的村民,大多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4]“三八六一九九”是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九九重阳节的缩写,学术研究中用“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指代留守农村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发展意识与能力等方面都较为欠缺,经济收入不容乐观。同时,由于村庄人口的大量外流,村民之间基于血缘、地缘、人情形成的社会联结不断弱化。更为重要的是,村庄空心化、村民原子化的状态,导致村庄无法抓住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村民们也无法改善自身的境遇。
我们认为,要突破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宏观结构性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微观个体的去组织化(或曰“原子化”)困境,亟须实现村庄再组织化。根据集体行动中的宏观结构主义理论可知,社会资源占有不平等带来的阶级分化,会让处于弱势或者被统治地位的阶级或群体感知到被剥夺感、不公正感,从而导致集体行动的爆发[5]曾鹏、罗观翠:《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关于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文献综述》,《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如此看来,宏观的结构性困境与由此带来的微观个体困境的叠加,似乎为村庄再组织化发出了强烈呼吁。然而,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宏观结构性问题导致的个体行动者不公平感与被排斥感的积累,并没有促成普遍意义上个体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的产生,多数农民采用了“半工半耕”的适应策略,或“用脚投票”外出打工。因此,村庄再组织化并不像宏观理论所预期的那样会自发产生。因此我们需要进入实践层面,进一步讨论再组织化如何可能,反思为何集体行动中的宏观结构主义理论在指导中国乡村实践问题时会出现解释无效。
(三)村庄再组织化的可能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政策近些年正有序引导生产要素回流乡村。首先是人才回流。前文历数了2007年以来各类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2020年初,国家发改委等19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入乡创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到2025年,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一二三产发展的返乡入乡创业产业园、示范区(县),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1500万人以上,带动就业人数6000万人左右”的目标。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对返乡入乡人员的引导范围从最初的农民工,到各类人员,政策逐步进入对返乡入乡人员素质与数量并重的新阶段。人才的背后,往往有着与其实力相当的团队资源,人才不断回流乡村,附着在人才身上的资金以及技术、管理才能等优势要素也随之流入乡村。其次是资本回流。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此后,连续多年的政策文件都明确提出鼓励工商资本下乡,鼓励投资的范围从“种养业”到“农业全产业链”和“三产融合”。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2019年10月,资本下乡主体超过15万家,累计投资额超过2万亿元[1]何展雄、吕蕾莉:《工商资本下乡:历史演进及文献梳理》,《生产力研究》2020年第11期。。
从农业本身来看,作为唯一一个与自然直接进行交换的产业,其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功能,即农业具有多功能性。具体来讲,农业至少具有八大功能:生态环境功能,物种多样性功能,农民生活、就业与社会保障功能,社会稳定与社会调节功能,国家安全功能,文化教育功能,医疗休闲功能,经济产业功能。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经济产业功能都是农业唯一被强调的功能,也仅有此功能得到了价格支付[2]周立、王彩虹、方平:《供给侧改革中农业多功能性、农业4.0与生态农业发展创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今天,随着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带来“四洗三慢两养”新需求,人们对农业多功能性认识不断加深,农业的各种功能开始逐渐被开发,并得到财政和资本的支持。
总之,有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有农业农村本身的发展潜力,也有城市居民的巨大需求,乡村成为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已成为可能,这也使得上千万的微观个体开始返乡入乡创业。多地调研发现,当前发展较好的典型村庄,大多都有返乡入乡创业的中心人物,如陕西袁家村的郭占武、浙江鲁家村的朱仁斌和何斯路村的何允辉。这些乡村中心人物一般是本村在外发展较好的青壮年人才,“土生土长”的经历使他们对家乡有着充分的了解,对家乡和家乡人也有着深厚的情感,而多年在城市打拼的经历,更让他们对城市人的需求,以及城乡中国的转型机遇有着充分的认识。这些特质,使得乡村中心人物在社会理性的驱动下率先返乡。中心人物返乡后,开始不断重建村庄原已衰落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打感情牌、利益赋予等方式动员关键群体;关键群体出于对中心人物的信任以及经济利益的考量做出响应。例如,陕西袁家村的关键群体,主要是村中留守的、有传统生产技艺的老人与党员,以及郭占武的好友;浙江鲁家村的关键群体主要是本村的乡贤,以及朱仁斌的亲友;浙江何斯路村的何允辉则组织一些干部建设“功德银行”包干区,对善言善行进行积分鼓励。当中心人物与关键群体行动起来,且形成一定示范效应后,后续参与者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加入其中,并在实际经营中将多种社会因素纳入行为选择中。中心人物公益导向的社会理性,激发了关键群体的强社会理性、弱经济理性,进而带动后续参与者的强经济理性、弱社会理性。由此,实现了人才、资金、土地、管理、技术等要素的重新组合,使得乡村能够在再组织化基础上发展起新产业,创造新供给,从而满足了城乡中国时代的新需求。
四、总结与反思
(一)实践总结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转型。在城乡中国时代,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不再是对立竞争,而是融合互补。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是城乡时代的重要目标和鲜明特色。一方面,城市生活的快节奏、高压力,以及城市病等系列问题,催生了城市居民“四洗三慢两养”的新需求,为全国近70万个村庄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3]此处的村庄指行政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统计,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国范围内行政村总数为691510个。;另一方面,只有深化对农业多功能性的认识,推动农业除生产以外的其他功能的逐步开发,促进乡村产业多元化,才能使乡村成为满足城市新需求的重要场所。
就当前中国乡村的发展实践来看,村庄低组织化是多数乡村无法抓住新时代机遇的重要原因。在村庄这一端,只有组织起来,才有提供新供给的可能性。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家对城市给予了更多的照顾,城市发展欣欣向荣;乡村则是处于被动付出地位,且逐渐“空壳”或凋敝。“离土又离乡”的农民正深深体会着“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的困境。面对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宏观结构性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微观个体离土离乡、难以回流的困境,村庄只有再组织起来,才能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
可以这么说,国家政策的引导与支持、农业多功能性显化,以及微观个体渐次被激发的理性选择,为村庄再组织化提供了可能性。正是这些宏观结构因素与微观个体的理性选择在村庄这一中观场域中的汇合与碰撞,村庄场域中的“中心人物-关键群体-后续参与者”基于理性选择的渐次行动,创造了新供给,促成了城乡互为供求、有序互动的融合。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原本的村庄空心化、村民原子化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传统村庄社会结构得以巩固,并形成了现代性与乡土性相结合的新村庄社会结构,从而推动了村庄再组织化不断升级。
(二)理论反思
奥斯特罗姆曾将集体行动定义为:社会成员为实现共同目标而采取的协同行动[1]Ostrom,E.,"A Behavioral Approach to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Presidential Addres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7,92(1),pp.1-22.。根据前文的定义我们可知,城乡中国时代村庄再组织化可被视为是村庄场域中的集体行动。这种宏观的结构主义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宏观结构所导致的微观个体的不公平感与被排斥感的累积,会促使集体行动爆发。然而,面对中国村庄再组织化的集体行动,这一理论观点却失效了。同样,关注微观的理性选择理论强调集体行动中个人的力量,也无法得到解释。无论是亚当·斯密所代表的乐观理性选择理论,即个体理性会带来集体理性,个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行为选择会促进社会共同利益的实现;还是奥尔森所代表的悲观理性选择理论,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并非总是一致的,较大规模群体的集体中“搭便车”行为会阻碍为实现共同利益的集体行动的发生[2]李培林:《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其出路》,《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都忽视了个体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即城乡中国时代的村庄再组织化是宏观结构性因素与微观个体理性选择交织互动的结果;而村庄为二者的交织互动,提供了中观的实践场域。因此,本文认为,聚焦中观场域,将脱离社会情境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抽象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结合起来,形成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3]刘少杰:《理性选择研究在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与方法错位》,《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6期。,去探讨乡村发展问题,更符合中国乡村的发展实践。而中国的乡村发展实践,也将成为新经济社会学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实践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