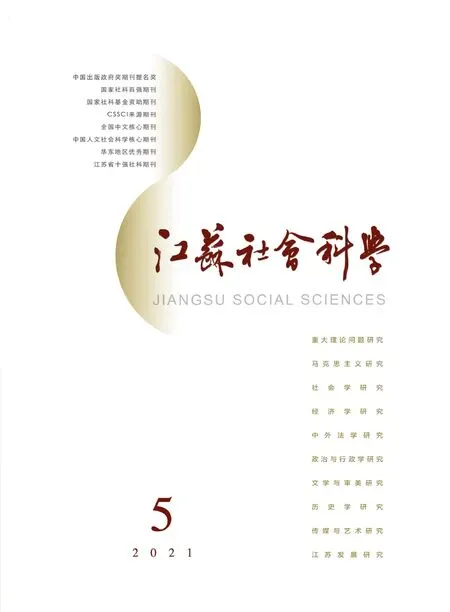高空抛物罪的刑法教义学分析
姜 涛
内容提要 个罪的保护法益并不完全依据个罪的构成要件确立,而是对个罪的构成要件具有矫正功能;高空抛物罪的保护法益是公共安全而不是社会管理秩序。高空抛物罪的实行行为是在高位随意抛掷可能导致他人伤亡或财产损失的物品而危及公共安全,或多次实施高空抛物的行为;高空抛物不同于高空坠物;成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成立高空抛物罪的间接正犯或不作为犯。司法解释应当依据伤害标准、概率标准与行为标准确立“情节严重”的类型。
高空抛物被媒体称之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随着近年来高空抛物行为造成的伤害事件不断出现,《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修十一》)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两高2021年2月26日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七)》将其罪名确定为高空抛物罪。在立法尘埃落定后,高空抛物罪的司法适用成为关注焦点,高空抛物罪也是司法实践中的高发犯罪。为了保证刑法独特社会功能的实现,刑法适用必然地需要刑法教义学。刑法教义学的任务是解释与体系化。其中,体系化所面临的问题是,高空抛物罪的保护法益是什么;解释所面临的问题是,本罪的实行行为应如何界定,“情节严重”的标准应如何建构。本文拟对此进行教义学分析,以期有助于高空抛物罪的正确适用。
一、高空抛物罪的保护法益
高空抛物罪的保护法益是公共安全抑或社会秩序?《修十一》(草案)将其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中,将其理解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修十一》把高空抛物罪规定在《刑法》第291条当中,理解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如果对高空抛物罪保护的法益没有清晰界定,刑法修正案增设高空抛物罪的规定将会导致刑法条文内部不协调[1]张明楷:《增设新罪的原则——对〈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修改意见》,《政法论丛》2020年第6期。,同时会导致司法适用上的困境。
(一)个罪之保护法益与个罪之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
刑法是法益保护法,法益保护是刑法存在或正当化的根据。但是,个罪的保护法益是什么并不容易确定。个罪的保护法益与个罪的构成要件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但个罪的保护法益并不是判断个罪的构成要件之唯一要素。就个罪的保护法益与个罪的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而言,两者分别属于刑法的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个罪的保护法益是关于个罪之性质的思考,属于刑法的内在体系;个罪的构成要件是为刑法条文中的概念、文字、语言等所划定的要素,具有法定性,属于刑法的外在体系,也是衡量个罪之保护法益的法定标准。个罪之保护法益的证成除了依据个罪之构成要件的法定标准外,尚需结合刑事政策、社会变迁、社会生活等予以确定,以使个罪之保护法益在个罪解释论上发挥调节阀作用。例如,随着社会变迁,个罪之构成要件所涵摄的行为已经不具有法益保护的真实性或必要性,则应当对个罪之构成要件做出限制解释[2]参见姜涛:《法益衡量中的事实还原运用:刑法解释的视角》,《法律科学》2021年第2期。。
个罪的保护法益具有立法论上的批判机能与司法论上的解释机能。其中,解释机能是法益概念的体系内含(systemimmanent)功能,司法者在进行个别刑罚法规之解释、适用时,应将个罪之保护法益的合理存在视为前提,直接以该刑法规定所保护的法益为依据,而不是质疑该刑法规定所预设的法益;立法批判机能则是超越体系(systemtranszendent)的功能或体系批判(systemkritisch)功能,基于法益概念所具有的前于实证法的实质内涵,而可据以检视既存刑罚法规所预设之保护法益是否适格,如果不具备这种适格性,那么该刑罚规定即欠缺正当性根据[3]参见黄宗旻:《法益论的局限与困境:无法发展立法论机能的历史因素解明》,载《台大法学论丛》2019年第48卷第1期。。就立法论上的批判机能而言,个罪的保护法益固然与个罪的构成要件有关,但又不局限于个罪的构成要件;就司法论上的解释机能而言,主要是强调从个罪的构成要件理解个罪的保护法益,但如果刑法规定的个罪之构成要件导致犯罪圈过大时,则依据个罪的保护法益对其进行限制解释。但是,如果刑法规定的个罪之构成要件不能涵摄新出现的犯罪,依据个罪的保护法益对其进行扩大解释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已经背离了法益论的自由主义机能。然而,由于刑法中多使用不明确概念、文字,例如,高空抛物罪中的“情节严重”,这将导致个罪的构成要件难以发挥定型化作用,反而因其属于未定式犯罪而富有开放性,这就为司法实践中的扩张解释或类推解释打开了方便之门。
为此,形式解释论强调基于罪刑法定原则所倡导的形式理性,通过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要件,将实质上值得科处刑罚但缺乏刑法规定的行为排斥在犯罪范围之外[4]参见陈兴良:《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形式解释论的立论前提是,正是法益论导致了刑法中的不当扩张解释,因为就犯罪判断而言,法益论在个罪之构成要件的形式标准外,添加了是否侵害法益或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实质标准,而这一实质标准缺乏必要的客观性,导致司法上的入罪解释扩张化。笔者认为,把司法解释或司法实践中的犯罪化扩张归咎于法益论,其实掩盖了司法权力扩张的实质,真正导致司法解释或司法实践上犯罪化扩大的根源是过于依赖刑法处理社会矛盾,而罪刑法定原则并没有真正进入司法实践。法益论的真正价值在于回答什么不是刑法保护的法益,把不具有法益侵害的真实性、价值性和必要性的行为排除掉,但是,这并不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把实质上具有法益侵害或侵害危险,但形式上不符合个罪之构成要件的行为解释为犯罪。有了上述基本定位之后,我们再来审视高空抛物罪的保护法益是什么,也就有了基本方向,即高空抛物罪之保护法益当从限制犯罪成立角度存在,而不是从证成犯罪成立角度存在。
(二)高空抛物罪的保护法益是公共安全
作为前提,社会管理秩序与公共安全的内涵不同,但两者之间又有交叉。首先,在我国现有分则体系之下,公共安全与社会管理秩序属于不同类的法益,两者首先具有犯罪分类功能。其次,对不同的法益类型,刑法的保护要求不同。对于故意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法中的犯罪多属于危险犯、行为犯,鲜有情节犯。例外的情况是,危险驾驶罪中有“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规定。对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而言,刑法中的犯罪多属于情节犯或行为犯。其中,行为犯是两类罪较多的犯罪类型,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劫持航空器罪、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帮助恐怖活动罪、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妨害公务罪、招摇撞骗罪、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等,都是行为犯。行为犯的特点是行为本身即具有法益实害或实害的危险,具有可罚性基础,只是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的行为犯危害对象具有不特定性,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行为犯危害对象是特定的。最后,情节犯与危险犯的关系比较复杂,如果说公共安全本身就是值得保护的法益,那么高空抛物罪是实害犯;如果说人身法益或财产法益才是本罪值得保护的法益,那么高空抛物罪当属于危险犯。从刑法及司法解释本身规定来看,情节严重的背后包括结果发生或结果发生的危险,与之对应,情节犯包括危险犯,但并不一定是危险犯,也包括造成轻伤以下人身伤害或非严重财产损失等情况。就此而言,不能因为高空抛物罪中有“情节严重”限制而把其个罪的保护法益解释为社会管理秩序,这并不是立法者规定高空抛物罪最为实质的初衷,立法者设置本罪旨在保护民众“头顶上的安全”。
从概念适用上分析,公共安全是高度抽象的概念。什么是公共安全?目前最新的观点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等方面的安全,但《刑法》第114条所保护的只能是不特定且多数人的生命、身体的安全。其中的‘不特定’并非指行为对象的不确定,而是指危险的不特定扩大。”[1]张明楷:《高空抛物案的刑法学分析》,《法学评论》2020年第3期。因此有学者认为:“绝大部分高空抛物行为一般仅可能造成不特定的单个人的侵害,即使连续的多次抛物行为可能侵害不特定且多数人的安全,但其本质并不具有结果的开放性和扩张性,因而都不适宜认定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2]林维:《高空抛物罪的立法反思与教义适用》,《法学》2021年第3期。由于高空抛物不具有危及公共安全的性质,高空抛物的行为对象往往是不特定的人,但既不是危险的不特定扩大,也往往不是多数人的生命、身体的安全,这正是《修十一》最终将高空抛物罪放置在《刑法》第291条而不是《刑法》第114条的法理解释。上述分析是在事前设定了一个衡量公共安全的标准,但是设定这一衡量标准是否恰当仍有待深入讨论。论者也承认,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犯罪也有危害不特定对象但并未必属于多数的情况,如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等。建立在法益前置化保护理论下的抽象危险犯,其处罚基础通常有两种论证思路,一是推定的具体危险结果;二是定型化的行为本身的典型危险[3]参见周漾沂:《重新理解抽象危险犯的处罚基础——以安全性理论为中心》,载《台北大学法学评论》2019年第109期。。后者为当前对抽象危险犯处罚基础及其性质的通说见解。但是,在由情节严重限制的犯罪类型中,前者的论证思路更为合理。如果说高空抛物罪是情节犯,那么人身法益或财产法益等才是高空抛物罪最终值得保护的法益,尽管高空抛物行为对人身法益或财产法益的损害还只是一种具体的、现实的危险。
首先,把公共安全理解为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等方面的安全,这是恰当的。因为公共安全不是个人法益,而是超个人法益(包括人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等),关键是如何看待和定义超个人法益。上述观点把“不特定”理解为并非指行为对象的不确定,而是指危险的不特定扩大,这仍是一种客观的结果论,即根据放火、爆炸等行为的杀伤力进行判断,但这在司法操作上存在困难。例如,在危险驾驶领域中,如果针对酒驾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时皆要求具体危险结果事实上存在,那么势必会陷入高度的麻烦,等于司法者自缚手脚,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会存有证明困难,这将使得法律欠缺可实践性[1]Horst Schröder,"Die Gefährdungsdelikteim Strafrecht",ZStW,1969,S.16.。笔者认为,就危险犯而言,危险状态的证明采取客观的结果论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应当采取主观的结果论,即潜在被害人得于无合理忧虑下放心使用支配法益的状态。所谓公共安全等安全诉求是指法益持有者能够安心支配使用其人身、财产等法益的状态,之所以必须以法律保护公共安全,是因为法益持有者对于法益的支配不仅会因为法益何时受损的不确定而担忧,也会因为法益持有者基于有关法益受损的集体恐惧等,而以刑法保证公共安全正是要除去这种集体恐惧[2]Urs Kindhäuser,"Sicherheitsstrafrecht-Gefahren des Strafrechts in der Risikogesellschaft",Universitas,1992,S.228;Urs Kindhäuser,Gefährdung als Straftat,1989,S.19.。具体而言,这是以行为是否带来集体恐惧作为不特定或多数人的判断标准。公共安全具有不特定或多数人受害的特点,不特定意味着行为危及对象的不确定性,在某一时空范围内出现的人都具有被害可能,因此会导致集体恐惧;多数人意味着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被害人数量较多,也与集体恐惧相关。以“朝人群开枪”为例,即便该行为具有造成他人死伤的唯一性,也不适用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而是适用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为它会导致集体恐惧。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点在于对象的不确定性,而不在于多数人特征,且此类行为会导致集体恐惧,这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有别于其他犯罪的最明显特征。例如,就刑法目前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交通肇事罪侵害的人身法益而言,只具有不特定特征,并不具有多数特征,依据刑法及司法解释,交通肇事罪危及的交通安全只有不特定特征,并不具有多数特征。
其次,上述观点也存在某种误解。就《刑法》第114条规定来看,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具体危险犯,即行为具有导致不特定的一人生命处于危险状态即可成立犯罪,至于危险的扩大对定罪没有影响,而是量刑加重的理由。例如,居住在单元楼的张某点燃自家的房屋,这就构成了放火罪,至于火势扩大(危险的扩大)烧毁邻居家的房屋,这是量刑加重的情节,与定罪之间没有关联。这涉及表象法益与实存法益的辩证关系,国内和日本学者将其称之为阻挡层法益与保护层法益。在刑法中,大量存在为了保护A法益(背后层)而保护B法益(阻挡层)的立法现象。这便是各国刑法中普遍存在的“阻挡层法益构造”。显然,只要有效地保护阻挡层法益,背后层法益就能够得到保护[3]参见张明楷:《污染环境罪的争议问题》,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日〕和田俊宪:《贿赂罪の见方》,载〔日〕高山佳奈子、岛田聪一郎编:《山口厚先生献呈文集》,成文堂2014年版,第367—375页。。同时,从常识角度看,放火罪、爆炸罪等危及不特定且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但从刑法本身的规定来看,放火罪、爆炸罪等之构成要件并不包含“多数人”特征。例如,某个共同使用的井内投毒,但因住户大都选择使用自来水,该井仅有一位孤寡老人在用,这并不能因为只有造成一人中毒的危险而否定其成立投放危险物质罪。
再次,个罪的保护法益是以刚达到入罪标准的行为为依据而确立,而不是依据过限的行为而确立。高空抛物罪的保护法益是公共安全,公共安全的特点是会导致集体恐惧,而导致集体恐惧的原因是行为所涉及对象的不特定性,如果涉及对象为多数人,则是加重处罚情节。例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4月6日《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因为交通肇事,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交通肇事导致两人死亡,是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加重处罚情节。
最后,即使《刑法》第114条所保护的只能是不特定且多数人的生命、身体的安全,也不意味着在《刑法》第114条之后,不能增设高空抛物罪。法条区分不同情况而导致混合罪名的情况,在刑法分则中比较常见。例如,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犯罪,不仅被放在原有《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之后,且危险驾驶罪之构成要件规定也被区分为“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情节严重的”两种类型。
尽管《刑法》第291条中“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有“情节严重”的限制,但是,如果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之类法益出发解释高空抛物罪的实行行为与情节严重等入罪标准,仍存在诸多疑问。
第一,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属于典型的行政犯,即违反国家的行政管理规定而实施的犯罪。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高空抛物没有明文规定,唯一可以依据的是将高空抛物行为解释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的“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这在解释论上存在不当嫁接问题。
第二,《刑法》第291条规定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均具有聚众性或涉众型特点,即引起公共秩序混乱,这才会对公共秩序有所破坏。同时,刑法对于公共利益、社会制度或社会秩序等超个人法益的保障,是为保障一些与具体个人的人身法益、财产法益等无直接关联的抽象法益。但是,高空抛物罪并不具有这一特点,因为高空抛物与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的区别在于,它的行为对象不特定,但并不是多数人;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的行为对象不特定,且是多数人。如果不把高空抛物行为与人的人身法益、财产法益关联起来思考,就很难定义高空抛物罪的实行行为。
第三,《刑法》第291条中涉及的三个犯罪,都是以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交通秩序、公共场所秩序等为入罪标准,高空抛物罪并不涉及这些,而是以是否具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危险为入罪标准,可见高空抛物罪与《刑法》第291条其他犯罪保护的法益并不相同。同时,行为人若实施“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而造成人员伤亡的,对这些犯罪而言,只是加重处罚情节[1]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9月18日《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的‘造成严重后果’,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一)造成三人以上轻伤或者一人以上重伤的;(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因为这种严重后果与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等行为之间只具有间接因果关系,而高空抛物致人死亡或重伤的结果,是高空抛物行为直接导致,依据《修十一》有关法条竞合的规定,当另行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第四,把高空抛物罪规定在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由于侵犯法益是公共场所秩序,远较公共安全的意蕴宽泛,故不仅会不可避免地扩展高空抛物的行为范畴,例如,从具体危险犯退化到形式犯,而且将高空抛物罪规定为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情节犯,就需要考虑诸多影响定罪的情节,这会加重司法机关的负担,影响司法的可操作性和一致性,无法确保刑法体系的一致性,反过来会对高空抛物入罪的立法价值产生消极影响[1]参见彭文华:《〈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高空抛物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由上可见,《修十一》把高空抛物罪放在《刑法》第291条当中存在定性上的偏误,如何矫正这一偏误带来的体系矛盾及司法适用难题,则需要从个罪之保护法益定义上予以必要的矫正,而矫正的路径是把高空抛物罪的保护法益解释为公共安全,这包含两个逻辑相关的组成部分:一是实质法益,即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等人身法益、财产法益;二是表象法益,即与前述人身法益、财产法益相关的公共安全的保障。因此,将高空抛物罪放置于《刑法》第114条当中,比放置在《刑法》第291条更为合理。
二、高空抛物罪的实行行为
犯罪成立与否的检验,无论如何必须以行为作为对象。什么是高空抛物罪的实行行为,这是高空抛物罪之构成要件的核心问题。传统观点把实行行为作为区分预备与未遂、正犯与狭义共犯的标准。然而,刑法既然是法益保护法,就应当以保护法益为指导解释高空抛物罪的实行行为,对于危险犯而言,实行行为是个罪之构成要件中的关键内容,是因果关系确立的起点,也是从事前观点看具有实质危险的行为。
实行行为(危害行为)是构成要件之行为,其以该当于法律上构成要件之现实行为来定义实行行为[2]参见〔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の理论》,有斐阁1953年版,第235页。,这是形式说的观点。实质说认为,实行行为与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的行为对应[3]参见〔日〕井田良:《日本因果关系论的现状——从相当因果关系说道危险现实化说》,林琬珊译,载《月旦法学杂志》2018年第276期。,或者强调个罪的实行行为取决于保护法益的内容。在危险实现判断上,是对犯罪之因果关系判断基准的具体化。也有观点认为,所谓实行行为是形式上该当个罪之构成要件,实质上具有实现构成要件之类型性危险的行为[4]参见〔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第5版)》,成文堂2018年版,第71页。;或者主张以特定构成要件所保护的法益为基准,要求行为要符合构成要件所预想的定型性[5]参见〔日〕团滕重光:《刑法纲要总论》,创文社1990年版,第121—123页。。笔者坚持综合说,这是因为:一方面,刑法是法益保护法,而法益侵害或侵害危险是由行为人实施符合个罪之构成要件的行为所导致的,因为刑事不法行为为法益侵害行为,那么用以描述法益侵害的构成要件形态以及构成要件要素皆须与法益侵害有关,所有一切和法益侵害无关的要素,皆不应成为设置构成要件的考虑[6]参见周漾沂:《重新理解抽象危险犯的处罚基础——以安全性理论为中心》,《台北大学法学评论》2019年第109期。。单一的形式说并没有明确行为类型判断的实质标准,这种基于刑法文义或概念理解实行行为的立场过于简单化,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单一的实质说,存在以个罪的保护法益决定犯罪性质,以此取代了行为类型决定犯罪性质的原则,即以结果定罪而非以行为定罪[7]参见陈兴良:《刑法定罪思维模式与司法解释创制方式的反思——以窨井盖司法解释为视角》,《法学》2020年第10期。,虽然追求实质出罪,但也容易导致实质入罪,这需要进行限制。形式说则提供了限制的标准,即不能突破刑法规定。就此而言,刑法目的在于通过调和法益保护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来维护社会秩序,为实现这一目的,刑法需要把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通过刑法明文规定对其予以类型化为高空抛物罪的实行行为。由于高空抛物罪并不需要造成现实的危害结果,只需要造成现实危害结果的危险,故高空抛物罪之因果关系判断的重心在于定义高空抛物行为是否具有实质危险,只是这种实质危险的范围不能突破刑法的明文规定。
从综合说提供的判断基准出发,被定义为高空抛物罪之实行行为,除了在形式上该当高空抛物罪之构成要件外,仍需判断该行为是否具备该当高空抛物罪之构成要件所包含的引起法益侵害的类型性和现实的危险。或者说,看行为是否制造了一个虽未达到实害程度,但对所要保护的客体或法益具有相当的、且不被允许的实害风险存在(即具体危险),这一实害风险通常是潜在的被侵害人具有人身、财产等被侵害的不确定性集体恐惧。然而,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由于立法者对高空抛物罪之构成要件采取相对明确的概念表达,如高空、抛掷、物品等,导致高空抛物罪之构成要件的类型性不明确,比如,向高空扔足以打伤行人的小石头的行为是否属于高空抛物?拿弹弓打鸟的行为是否属于高空抛物?笔者认为,从实质角度判断高空抛物罪之实行行为所包含的危险性,就成为关键。这种危险判断并不能立足于抽象危险犯的法理进行判断。抽象危险犯的存在,是立法者为了避免个人利益的支配可能性得以实现的条件遭到攻击或陷入危险,而透过法律化的方式所做的保证。这样的保证,也是建立在个人对于利益实现的安全感与确定感(Sicherheit)的要求之上的[1]Kindhäuser,Gefährdung als Straftat,Rechts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Dogmatik der abstrakten und konkreten Gefährdungsdelikte,1989,S.132 ff.。立法者对高空抛物罪设置有“情节严重”的限制,这意味着高空抛物罪之实行行为所包含的危险性是现实的法益侵害的危险,应当以实害发生为参照来确立,而不是抽象的法益侵害的危险;是一种事前的危险性判断,而不是事后的危险性判断,即行为人在实施高空抛物时必须具备足以让一般人感受到现实上的危险性。这就不仅对所抛物品的性质有一定的要求,必须是具有杀伤性或侮辱性的物品,而不能是一支玫瑰花或一枚求婚戒指,而且对抛物的高度也有一定要求,可根据物理学原理计算物体抛落时所处的高度,即根据所抛物品自由落体过程中形成的冲击力为标准,通过物品的质量与物体抛落时所处的高度之间的换算关系得出物体抛落时所处的高度。当然,这种实质解释并不能突破《修十一》规定的“从建筑物或其他高空”之文义,例如,开车在高速公路上扔可以升空的气球而导致其他车辆躲避造成重大事故的,则不能被定义为高空抛物罪的实行行为。
什么样的、何种程度的高空抛物行为才是对人的人身、财产法益产生实质危险的实行行为?这并不太容易确定。实行行为就是与实际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结果具有因果关系的行为,如何界定高空抛物罪的实行行为,当以高空抛物罪之不法结果发生样态确立。这首先涉及高空抛物罪之行为犯、危险犯与结果犯之间关系的认识。张明楷教授指出,“行为犯与结果犯并不是前者不需要结果发生、后者需要结果发生,而是均要求结果发生,只不过行为犯中的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或者说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实行行为就同时发生构成要件结果,故对实行行为的判断与结果的判断是同一的:有实行行为就有结果,有结果就有实行行为;结果犯中的行为与结果相分离,有实行行为不等于有构成要件结果,故需要在实行行为之外独立判断结果是否发生,以及结果能否归属于实行行为。”“结果犯与危险犯是根据不同区分标准得出的子项,二者必然是一种交叉关系。结果犯既可能是侵害犯,也可能是危险犯,同样,危险犯既可能是行为犯也可能是结果犯。”[2]张明楷:《高空抛物案的刑法学分析》,《法学评论》2020年第3期。笔者赞同这一观点,高空抛物罪的实行行为有两种类型:一是在密集人群高空抛物,这种高空抛物行为具有行为犯特征,即在高处朝密集人群抛物即成立犯罪,二是在非密集人群高空抛物,这种高空抛物行为具有结果犯特征,需要判断结果发生的危险与高空抛物行为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对第一种情况一般不存在争议,有争议的是第二种情况,可以预见,这也会成为未来有关高空抛物罪之司法解释面临的难题。
高空抛物行为的现实结果体现为危害对象的随机性、不特定性,但通常不具有多数性。立基于此,高空抛物罪的实行行为是行为人站在高处故意向楼下抛掷物品的行为,这一行为不仅有高度的要求,即要有一定的空间落差,使所抛掷物品在运行过程中,因为加速度而增加其杀伤力,如果高度不够。比如,站在一楼抛物,站在楼下的人往往可以发现抛物人,也容易被所抛物品打中,则很难被认定为高空抛物。而且对所抛掷物品本身的属性亦有要求,即根据生活经验,所抛物品有致人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可能性,例如,在五楼向楼下扔菜刀、铁饼等。如果缺乏这种致人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可能性,则不属于高空抛物罪的实行行为。例如,甲某把一盆洗脚水或宠物的粪便从十二楼倒下去了,这一行为通常侮辱性极强,但造成的损害往往不大。就此而言,高空抛物罪之实行行为的界定是结果导向的,即从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之量化指标的建构角度,去具体判断高空抛物罪之实行行为。同时,高空抛物之实行行为判断,也有一个情景判断问题。例如,如果行人乙发现有人从高处往楼下倒水,为匆忙躲避而摔倒导致骨折等伤害结果的,则可以解释为高空抛物罪的实行行为。
三、高空抛物罪之“情节严重”认定
“情节严重”作为刑法中的不明确规定,旨在于确保刑法灵活适应社会变迁的社会功能,也在于体现限制行为犯或危险犯处罚范围过度的法律功能。《修十一》对高空抛物罪有“情节严重”的限制,也离不开上述功能期待。因此,“情节严重”的涵摄类型是什么,就需要结合立法者的设定目的及个罪的保护法益等予以明确。
(一)“情节严重”的三个确立标准
情节严重本质上是体现法益侵害危险程度的主、客观事实。立法者在立法时,之所以在刑法条文中附加一个导致危险的客观要件,其理由往往是因为某些行为本身,尚不足以被认定为对所要保护的客体或法益具有典型危险性,所以必须附加上“情节严重”作为要件[1]参见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下),元照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620页。。在界定高空抛物罪之“情节严重”的涵摄范围时,应兼具有行为刑法到行为人刑法的立场,既需要将高空抛物行为转换为可能的危害结果的具体样态类型化,又因为多次高空抛物具有累积危险,属于“情节严重”的体现。
刑法对个罪设置“情节严重”,属于刑法规定中的不明确条款,需要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21日《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5条规定:“对于高空抛物行为,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抛物场所、抛掷物的情况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全面考量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准确判断行为性质,正确适用罪名,准确裁量刑罚。”第6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一般不得适用缓刑:(1)多次实施的;(2)经劝阻仍继续实施的;(3)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又实施的;(4)在人员密集场所实施的;(5)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可见,《意见》区分了定罪情节与量刑加重情节,不仅考虑了抛物场所、抛掷物的情况以及造成的后果等涉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客观事实,而且考虑了行为人的动机等高空抛物的主观情况,兼具有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立场。笔者认为,《意见》有关“情节严重”的解释,不能适用于《修十一》规定的高空抛物罪,这是因为:一方面,《修十一》规定的“情节严重”属于定罪情节;另一方面,《意见》是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角度进行的入罪标准解释,《修十一》将高空抛物罪归类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由此导致对“情节严重”解释上的困难。
第一,伤害标准。伤害标准是判断高空抛物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大小及其伤害结果,既包括高空抛物行为带来的公共安全危险,也包括因高空抛物行为直接或间接而给人身法益或财产法益等造成一定程度实害的情形,但是排除造成严重实害的情况,如轻伤以上的人身伤害或重大财产损失。这涉及正向判断与负向判断两个维度:从正向判断看,抛出物品对人体或财物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很小,或者造成有关人员死亡、轻伤以上结果或严重财产损失的可能性很小,这主要是一个常识问题,也是一个科学标准,如扔出垃圾袋等软体物或者是食物残渣等,或者说,扔出物品完全不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如气球等。相反,扔出的物品很重或者很锋利,如苹果、菜刀、碗碟等,则一旦砸中行人导致伤害的可能性很大。从负向判断看,高空抛物罪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之间属于互斥性构成要件,而处于一种排他关系,某种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就不可能符合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不可能两者均为该当。如果高空抛物造成有关人员死亡、轻伤以上结果或严重财产损失的,则不属于高空抛物罪中的情节严重,而是涉及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只是伤害标准中造成的伤害,未必是高空抛物行为直接造成的结果。如,行人甲看到高空有厨房残余物等垃圾(如塑料饭盒等轻物品)不断抛下,为躲避被垃圾砸中,快速躲避,结果把从路边经过的老人撞倒,造成老人被摔成骨折。这一因果关系未重大偏离的结果,也应当归责于高空抛物者,并不产生阻却犯罪故意的效果,因为客观上所存在的事实,就其自身而言是明确、单义的,然而这绝非意味着人类可以将存在于某个时点的所有客观事实完整地描述出来[1]参见蔡圣伟:《重新检视因果历程偏离之难题》,载《东吴法律学报》2008年第20卷第1期,第7页。。就此而言,伤害标准尽管可以由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但主要是一个根据社会生活经验进行个别化判断的问题,司法解释本身只能明确其中的判断方法,而不宜予以更为精确的类型化处理。
第二,概率标准。概率标准是平衡抛物地点的具体状况,以评判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可能性大小。从个罪的保护法益入手,高空抛物罪并不处罚没有法益侵害或侵害危险的危险,高空抛物罪表面上保护社会管理秩序或民众头顶上的安全,但实质上借助对社会管理秩序的保护,最终保护民众的生命、健康或财产安全等。如果行为人在人员密集场所实施高空抛物,则致人损害的概率就高。相反,如果抛物地点是通常不可能有人经过或出现的地点,即导致人员伤亡的概率几乎是零,这一行为固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但并不宜解释为犯罪。例如,向小区楼下的绿化带扔垃圾,一般不宜将其解释为“情节严重”。
第三,次数标准。从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二元论观点看,刑法中因多次实施某种行为而被定罪的情况,包括多次盗窃、多次抢夺。此类“多次型犯罪”处罚的根据是行为人自身的人身危险性,是一种行为人刑法观。即基于多次实施某种行为,刑法需要予以干预以免其由多次型犯罪向数额较大型犯罪转变,避免出现犯罪上的破窗效应。对于高空抛物罪而言,如果行为人多次实施高空抛物行为,例如行为人经常从十楼往楼下倒宠物的粪便,就表明其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且一旦有了抛物行为的惯性后,从犯罪学角度看行为人很容易出现违法行为递进发展的态势,即从无序到违法、再由违法到犯罪的转变。例如,行为人起初抛下的可能是塑料垃圾或一个纸盒子,后期可能是玻璃、钉子等其他重物。就此而言,多次实施的、经劝阻仍继续实施的、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又实施的,都应当解释为高空抛物罪的“情节严重”。
基于上述标准,就高空抛物行为而言,所抛出物品性质、抛物的高度、抛物的次数、抛物时有无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等,是判断“情节严重”的标准,而不包括可能伤及人员的范围、数量、伤害程度等。
(二)“情节严重”的四类排除情况
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是以文字描述的具有典型危险性的行为类型,所以逻辑上可能存在的情况是,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法条文字描述,但实际上并不具备法条所要禁止的典型危险性,这就需要借助对“情节严重”的解释予以排除。从学理上明确“情节严重”的排除情况,旨在合理定义高空抛物罪的处罚范围,把不属于犯罪的情况排除,这主要是立足于行为人刑法立场,把行为人行为动机、注意义务等作为考虑因素。
第一,针对特定对象实施的高空抛物,当不属于高空抛物罪。例如,丈夫要外出和朋友喝酒,妻子看到丈夫已经到楼下,随后在三楼对楼下的丈夫吼道,“你要离开,我就拿苹果砸死你”,其丈夫不加理睬,妻子随之把一个苹果抛向其丈夫,但并没有砸中或虽有砸中,但其丈夫仅有轻微伤的。这种针对特定对象的高空抛物行为,具有加害对象的特定性,尽管符合从高空抛掷物品的行为,但是解释为高空抛物罪并不妥当,因为它并不具有伤害的随机性或不特定性,而且往往也尽到了不伤害其他人的注意义务。
第二,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高空抛物行为,当对“情节严重”进行严格限制解释。例如,楼下即为垃圾场,张某为避免下楼扔垃圾直接往楼下扔垃圾,在丢垃圾的过程中观察路过的行人,在没有行人的情况下才实施上述行为。在此类案件中,行为人尽到了避免他人损害的注意义务,能否以此为由免责?笔者认为,对此类行为当对“情节严重”进行严格限制解释。以浙江省首例高空抛物案为例,韩某作为装修人员为贪图方便,将部分拆卸后的板材等建筑垃圾从三楼窗口直接抛掷到地面,现场并无设置警戒线或提示语,最终被浙江省上虞区人民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罚金三千元[1]案件详情见“上虞检察”官方微博。。这一案件判决对“情节严重”的严格限制解释具有启发意义,即仅限于多次高空抛物或所抛之物杀伤力强,且没有设置警戒线或提示语的情况,以免导致高空抛物罪的不当扩张适用。
第三,以高空抛物方式实施的正当防卫,不构成高空抛物罪。例如,某小偷在五楼盗窃后逃跑,被害人在五楼发现小偷已经到了楼下,为阻止其逃跑,向其抛掷物体的。再如,某甲夜晚发现某小偷顺着楼道的下水管攀爬欲行窃,为阻止其行为,从楼上向其扔掷物品的。此类行为均具有防卫性质,如果没有造成他人伤亡或财产严重损失的结果,当属于违法阻却事由。
第四,向不走行人的封闭平台抛物,一般不构成高空抛物罪。现在不少高层建筑的一楼是商铺,若商铺的顶部是全封闭的平台,向这些平台抛物通常并不具有致人伤亡的危险。但是,也有不少开发商把二楼的平台,给居住二楼的房主使用,这里的房主可能会在平台上活动,如果向这些非封闭的平台抛物,则可能构成高空抛物罪。就此而言,即使立法者对高空抛物罪规定为情节犯,但也需要坚持结果无价值的立场,把有无法益侵害或侵害危险作为评判高空抛物罪之可罚性的根据。
结合前述次数标准,上述四类排除情况仅限于首次实施高空抛物行为,对于多次实施上述行为者,并不能免除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