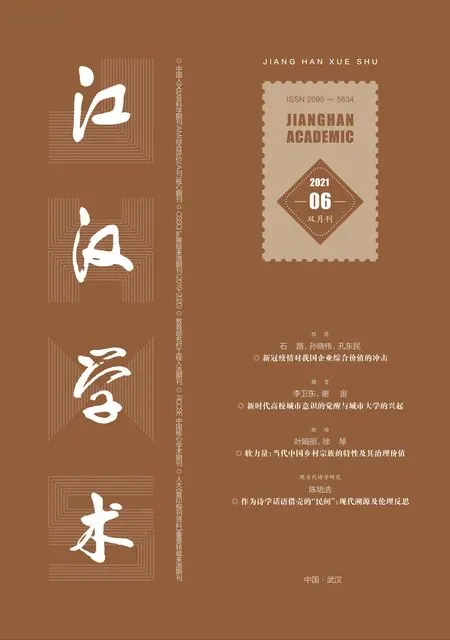从功能论角度对保险合同目的之探究
钱思雯
(常熟理工学院 商学院,江苏 苏州215500)
一、问题的提出
问题一:投保人对自身身体、生命具有保险利益,且身体、生命无价,但投保高额寿险时,保险公司仍会对投保人收入水平、财务状况等进行调查审核,要求投保人经济实力与保险金额匹配,传统保险利益理论无法对此进行合理解释,是否存在更好的解释基础?
问题二:投保人购买投资连结险,在“投保目的”一栏中勾选“储蓄”选项,在事后出现本金亏损的情况下,可否以保险人违反投保目的为由要求赔偿损失[1]?
问题三:美国长期寿险保单二级市场发达,保单贴现人通过购买生命垂危或患有重大疾病的投保人的保单,取得该保单的收益权,从而赚取差价,但将寿险保单转让给无保险利益者的行为颠覆了传统保险利益原则,被保险人的同意是否足以防范道德风险并使此种行为正当化?
问题一反映了传统保险利益制度在实践中面临的解释困境,问题二反映了投保动机与保险合同目的之间存在区别,问题三反映了动机与保险利益在确定转让行为合法性方面的不同作用。保险利益、投保动机、保险合同目的等概念在理论与实践中的碰撞引发了我们对保险合同更本质层面的思考。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合同目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保险合同目的这一概念体系。除发挥传统保险利益制度确定保险补偿范围、区分赌博及防范道德风险功能,避免保险利益制度面临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2]之外,更将合同目的在区分合同性质、确定合同及条款效力、限制解除权行使与进行合同解释等方面的功能引入保险合同领域。保险合同概念体系将目光流连于合同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提供了一个观察保险合同本质的新维度。
二、保险合同目的概念体系
合同目的被认为是当事人真意的核心,是决定合同内容的重要指针[3]。保险合同作为一类特殊合同,在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遵循一般规定,2021年生效的《民法典》承袭了原《合同法》相关规定,在条文中多次出现“合同目的”一语,涵盖合同订立、合同效力、合同履行、合同解除、合同解释等领域。两相比较,保险合同目的在《保险法》中“身份未明”,需回溯至《民法典》合同编大框架中研究合同目的的共性问题,进而针对保险合同进行专门研究。
(一)合同目的概念体系
对“合同目的”这一概念,我国立法中并未有定义性的描述,在合同法律制度发展史上也经历了逐步形成并广泛运用的过程。1981年《经济合同法》第2条及1993年修正后该法第2条以“经济目的”进行表述,1989年《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5条和第43条首次出现“合同目的”用语。至1999年正式施行《合同法》,合同目的开始频繁出现于合同效力、解释、变更与解除等多项制度中。《民法典》在多个条文中延续了“合同目的”的表述,合同目的贯穿合同从“生”至“死”的全过程,在合同法律制度中居重要地位。
尽管“合同目的”在合同立法上出现的频率不断提高,但对合同目的概念仍缺乏规范性表述,学者对合同目的内涵各自展开解读。如江平认为:“合同目的是指当事人通过订立合同的行为所想要得到的结果,这种结果通常表现为一种经济利益。”[4]施天涛认为:“所谓合同目的,是指当事人希望通过合同达到的目标、结果。”[5]崔建远认为:“合同目的,首先是合同的典型交易目的,即给予所欲实现的法律效果。这种典型交易目的在每一类合同中是相同的,不因当事人订立某一具体合同的动机不同而改变”;其次,则是“特定的当事人订立特定合同的主观目的”。[6]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04年版)》英文文本中“Purpose”被译为“目的”,“Intention”被译为“意图”或“旨意”,类似于“动机”[7]。从语义上,前者更为客观明确,后者主观性更强。由于合同目的与动机二者有时难以区分,形成阶段亦紧密相连难于切断,即便在立法上也有混用情况,如原《合同法》第52条第3项中“非法目的”实际上应为当事人之“动机”。因此,在构建合同目的概念体系的过程中,首要任务是对合同目的与动机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明确。
传统民商法理论并无针对合同目的专门论述,可追溯至大陆法系的意思表示理论。从意思表示过程看,“自表意人为意思表示之过程言之,必先有一定动机,次有目的意思,次有法效意思,次有表示行为”[8],在“动机—目的意思—效果意思—表示行为”这一过程中,前三项系一方当事人缔约目的形成链,原则上,未经明示的动机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作为主观意思要素的目的意思及效果意思经历客观化和外化的演变过程后,才可能成为经法律认可的合同目的[9]。但特殊情况下,动机违法(包括违反善良风俗、诚实信用等)或该动机为合同相对方所明知等情况都将对法律行为效力产生影响[10]。
综上所述,根据合同目的一般理论,本文将合同目的分为两大层次:一是客观目的,即典型交易目的。即合同给付所欲实现的法律效果,在每一类合同中表现均为相同。合同典型交易目的在典型合同(有名合同)和非典型合同(无名合同)中均有体现,在非典型合同中需要根据个案综合考虑。二是主观目的,即某些情况下的动机。合同任何一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都有各自的目的或意图,多数情况下当事人动机并不能作为合同目的,但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合同目的进行讨论。包括:双方在合同中一致确认并构成交易基础或合同条件的;动机违法(包括违反善良风俗、诚实信用等);对方明知或应知并构成交易基础或合同条件等情况。此外,对一些非典型合同的合同目的,需要对子合同、亚合同的典型交易目的进行综合考虑,确定居主要地位的合同目的[11]。
(二)保险合同目的概念体系
“无风险则无保险”“无损失则无赔偿”,保险合同基于一方交付保费、另一方为损失补偿之承诺的对价,使危险从个别经济单位转移到多数经济单位集合之团体,从而转移风险、补偿损失,确保个别经济单位生活之安定[12]52-56。参照合同目的概念体系,保险合同目的也可分为典型交易目的和主观目的两大层次。此外,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除传统以损失补偿为典型交易目的的传统保险合同外,又衍生了一系以“保险合同”为名,行“混合合同”之实的新型保险合同,实质上为传统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合同与储蓄合同、医疗服务合同等非典型合同结合的混合合同,应结合各亚合同典型交易目的综合考虑。
1.典型交易目的
典型交易目的具有客观性,在每一类型合同中均为相同,如买卖合同的典型交易目的是通过买卖转移标的物所有权,赠与合同的典型交易目的是转移赠与物所有权[11]。保险合同与买卖合同存在相似之处,买卖合同的标的系财产,而保险合同的标的则是一项危险或危险导致的损失,对投保人来说,付出一笔金钱买进一个“安全”;对保险人来说,是收受一笔金钱而承担一个“危险”[13],即投保人为获得保险人在特定情况下的保障而支付相应对价。因此,保险合同的典型交易目的,对保险人而言在于收取保费,对投保人而言则在于特定情况下获得保险金作为“赔偿”或者“给付”,可统称为“损失补偿”(Indemnity)。保险人与投保人通过保险合同的订立,转移危险、补偿损失,从而确保个别经济单位经济生活的安定,手段主要是基于概率和大数法则进行风险的分散[12]52-53。保险合同的损失补偿目的主要体现为财产保险中对具体损失的补偿和人身保险中对抽象损失的补偿,前者以金钱评价实际价值的损失,后者则以定额保险金作为补偿[14]17-21。
在保险法领域,传统保险法以保险利益为核心,发挥了限制损害填补程度、避免赌博行为与防范道德风险的功能[14]58。随着保险利益制度日渐式微,保险利益上述三方面功能均不同程度遭到否定,保险合同损失补偿这一典型交易目的成为更合理的选择。首先,对损害填补程度的限制乃保险合同目的之本质。即便人寿保险中,也不可一味执着于“人身无价之迷思”[15],保险公司需要审查衡量投保人的经济实力与保费、保险金额是否相当。在存在金钱关系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保险金额更是受金钱关系数额限制①。问题一中对投保高额寿险的审核限制即是保险合同损失补偿目的的实际体现,生命虽然无价但亦可用金钱衡量。其次,损失补偿系区分保险与赌博的根本标准。区分保险与赌博的根本标准不在于保险利益,而在于合同目的[16]381,“损失”比“利益”更接近于保险的本质。再次,财产保险损失补偿的内在机制比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同意对防范道德风险更为有效。保险利益与道德风险并无必然联系,反而人为制造合同效力的不确定性,并引发逆向道德风险[17]。
2.主观目的
保险合同的典型交易目的系外化的客观目的,而主观目的更多反映当事人内在心理状态,表现为特定情况下当事人动机。由于保险合同领域道德风险集中,故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与保险人未经明示的动机的审查尤为重要。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可能存在欺诈、骗保的动机,其主观动机是否“善意”(Good Faith)成为判断保险合同合法性、区分赌博合同的重要因素,主观动机在何种程度上构成“故意”是确定能否得到保险赔偿的关键;在保险人一方,亦有明知投保人虚假陈述,但为获取保险费而承保无保险利益之保险的逆向道德风险。对上述未经明示的主观动机可通过一些外在的方式加以探寻,如立足于保险合同损失补偿的典型交易目的,对当事人动机合法性、合理性进行推断。又如美国判例法在环境综合责任保险的适用过程中,对被保险人造成环境损害的主观意图认定综合考虑以下因素:排污持续时间;排放行为出于故意、过失或意外;被保险人关于污染物的知识程度;监管当局是否试图阻止被保险人行为;是否对造成可能的损害具备主观知识[18]。在制度设计上,保险合同作为最大诚信合同(Utmost Good Faith)依托如实告知义务、说明义务、禁止反言等制度均对保险合同当事人动机加以规范,防止通过保险合同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出现。
3.特殊目的
保险合同系《保险法》明确规定的有名合同,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系保险合同最典型的形式。然而,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保险产品的种类愈发增多,保险合同名目愈发复杂,如万能险、分红险、投资连结险、商业养老保险等等,实质为传统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合同与储蓄合同等非典型合同结合的混合合同。严格意义上讲,此类综合性、多重性的合同目的并非传统保险合同典型交易目的,而是保险产品在传统保险合同基础上混合其他类型合同的结果,但实践中,此类合同往往以“保险合同”为名,因此可将投资储蓄、财富管理乃至社会保障等目的作为广义保险合同特殊目的进行讨论,综合考虑各亚合同目的,从而正确认定合同性质并适用法律。
三、保险合同目的的功能
作为一种分析维度,功能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法律制度的新角度,即法律在社会中做什么及如何发挥作用[19]。从功能论角度看,保险合同目的不仅能发挥传统保险利益制度的功能,更统合于合同法律制度一般理论,发挥了合同目的在确定合同及合同条款效力、认定合同义务的履行、限制解除权行使和解释合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表现为区分功能、确定功能、限制功能和解释功能四方面。
(一)区分功能
合同典型交易目的在每一个保险合同中都相同,不因当事人具体动机而改变,据此可锁定合同的性质与种类,损失补偿作为保险合同典型交易目的有效发挥了区分保险合同与类似合同的功能。
1.区分赌博合同
对保险与赌博界限的争论伴随着保险的产生与发展,二者虽同为射幸合同,但法律评价截然不同:前者分散风险,保障安全,被称为“经济助推器”与“社会稳定器”;后者则制造额外风险,影响经济运行并导致社会不稳定。传统保险法以保险利益区分保险与赌博,但保险利益制度并不能为保险与赌博划定客观明确的界限,并且也无法彻底避免以保险为名行赌博之实的行为。保险合同的典型交易目的在于损失补偿,补偿金额以损失为上限,不存在通过保险获利的可能性。即便是在投资型保险中,其特殊目的也只是获得一定比例的投资收益,此种投资收益源于保险公司对投资账户的运作,与投资项目、市场行情、管理能力等因素密切相关,围绕同类产品市场投资收益率波动,并未脱离保险合同损失补偿的典型交易目的。相反,赌博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不确定性获利。以“股票跌停险”为例,持有股票的投保人对股票价格涨跌具有实际利益,从保险利益角度很难判断股票跌停险是保险还是赌博,而从保险合同目的角度看,由于保险赔付只和股票跌停挂钩,而非同损失挂钩,存在套利风险,仍属于赌博。可见,较之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典型交易目的在区别保险与赌博上发挥了更好的作用。
此外,保险合同的主观目的通常被认为是区分保险与赌博的重要考量。投保人的“善意”成为剔除以保险为名的赌博合同的试金石,被认为是人寿保险合同有效性的“逻辑检测”。但对善意的判断具有主观性,易导致误读,应采取客观化解释,如人寿保险被保险人受到欺骗、胁迫、错误等作出同意,即非善意动机的表现[16]404-406。在保单转让过程中,通过保单转让获得利益的多少也是衡量被转让人动机的重要标准,如陌生人寿险(Stranger-Originated Life Insurance,STOLI)②中,受益人意图以少量保费支出获得巨额保险金,保费支出与保险金价值不成正比,可以认定动机并非善意;而保单贴现交易中,被保险人以获取保单现值为目的转让保单,被转让人出于获取一定投资回报目的受让保单,贴现率根据被保险人预期寿命、保单现金价值等确定,可以认定动机善意。问题三中是否承认保单转让与贴现的合法效力与转让目的直接相关,“人寿保险中并无阻碍被保险人为自身利益出卖保单的理由,被保险人出于善意以获取保单现值为目的转让保单可以转移衡平法利益;被转让人不具备保险利益并不构成非法交易的决定性或初步证据”③。
2.区分保障性合同
实践中,一些混合合同在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同时允诺给予一定保障,此种具有保障性质的混合合同典型交易目的往往为买卖、租赁、服务等,损失补偿仅为其次要目的。因此,该类合同本质上并非保险合同,不受保险法规范。对此,美国保险法实践中主要通过三个测试对此类合同与保险合同进行区分:第一个测试是“实质控制测试”(Substantial Control Test),认为保险合同需符合传统的“赔偿”概念,并在偶然事件发生时转移分散风险;第二个测试是“主要对象和目的测试”(Principal Object and Purpose Test),应明确相关交易的主要目的是赔偿还是提供相关服务,风险的转移和分配是否属于核心特征;第三个测试是“监管价值测试”(Regulatory Value Test),主要从公共利益角度证明企业作出的某些保障承诺是否应受保险法监管。其中,前两个测试方式在区分保险合同与类似保障性合同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④如车辆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签订租赁合同,同时约定“车辆碰撞险”(Collision Damage Waiver,CDW),承租人无需对1000美元内的车损负责。美国加州法院根据“主要对象和目的测试”认为对车辆碰撞损失的补偿仅属于租赁合同的次要目的,并不能将上述风险分配安排视作保险。此外,从监管价值的角度,CDW仅涉及车辆承租人与出租人两方主体,并不涉及第三人与公共利益,亦无需通过保险法进行规制[20];又如企业提供的家庭医疗保险计划,其主要目的在于向会员提供低成本的家庭保健服务,而非在不确定突发事件中提供补偿与保障,并不符合保险合同损失补偿目的。
以“主要对象和目的测试”区分保险与其他保障性合同有利于防止保险制度扩大化,避免将所有涉及风险转移和承担的安排机制都纳入保险监管中,防止保险合同扩张适用。尽管附加条件买卖合同、风险服务合同等同样具备风险分配因素,但这些合同主要目的在于买卖或提供服务,与保险合同有本质区别。⑤因此,应将合同主要目的作为判断合同性质的首要标准,不可仅关注风险分散或偶然因素,否则保险与其他类型的法律安排和经济功能之间的界限会变得模糊,导致一些具有保障条件合同均被谬误地认为是保险合同⑥。
(二)确定功能
合同目的是确定合同及合同条款效力的依据:对合同本身而言,合同目的违反法律或公共政策将导致合同无效;对合同条款而言,合同目的是否难以实现是格式条款是否构成“限制对方主要权利或者自身主要责任”的必要条件,从而影响对格式条款效力的判断。
1.确定保险合同效力
对保险合同而言,根据传统合同法律制度理论,非法的合同目的导致合同无效;此外,违反保险合同明示、默示目的也将影响保险合同效力。
(1)目的非法
具体而言,保险合同目的非法包括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保险标的本身违法或违反公共政策、善良风俗。如承保非法获得或违禁走私物品的保险合同无效[21];唐提式养老保险合同具有赌博目的也被认为无效;对婚姻存在负面影响的“婚姻利益保险”通常因违反公共政策被认定无效[22]9;已婚当事人为保持与其情妇的通奸关系,指定情妇为其人寿保险合同受益人,也因合同目的违反善良风俗而无效[23]。第二种情况是财产本身合法但被用于非法目的。此种情况包括非法占有的财产、合法占有但用于非法活动的财产,如对赌博用具、盗窃工具、未获生产许可的产品库存投保的保险合同无效。多数观点认为,若投保人本人并未卷入非法活动中,对用于非法目的的财产投保的保险合同仍有效。例如,抵押权人或留置权人可对债务人的汽车投保,只要其并未卷入非法运营,即便该汽车被债务人用于非法运输,保险合同仍有效[22]9-13。第三种情况是当事人存在非法行为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非法行为并不导致合同无效,在保险合同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通常构成保险人免责事由,但是否有效仍取决于对保险人说明义务和格式条款本身公平性的审核。⑦
(2)违反明示的目的:未经被保险人同意
被保险人同意系人身保险合同主观目的之明示,起到防范道德风险、判断标准明确、投保人控制风险等作用。我国《保险法》第31条采折中主义模式,一方面,为《保险法》第31条第1款规定范围以外主体投保人身保险合同需经被保险人同意;另一方面,为《保险法》第31条第1款规定范围主体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也需被保险人同意,未获得“被保险人同意”的保险合同被认为不具有保险利益而无效。被保险人同意是保险合同明示目的的具体体现,违反保险合同明示目的导致合同无效。
(3)违反默示的目的:超额保险与复保险
损失补偿系保险合同典型交易目的,也是保险合同默示目的,部分投保人恶意高估保险金额或重复投保意图获得超过保险价值的利益,潜藏道德风险。域外立法例大多区分投保人主观目的,对恶意超额保险或重复保险效力进行区分,而我国《保险法》并未进行区分,缺乏对恶意投保人的惩治作用。应区分主观目的:一方面,规定恶意超额保险合同全部无效。对主观目的的判断上,因保险合同订立后保险标的价值下跌等客观因素以及投保时对保险价值的误判等主观因素导致的超额保险系善意超额保险,而当事人以虚报价格、欺诈等方式意图获取超额利益的保险则为恶意超额保险,并结合投保时的客观情况以及询问回答过程进行具体判断。另一方面,规定恶意重复保险全部无效。在判断方式上,借鉴台湾地区“保险法”明确将恶意重复保险的情形区分为不为通知和意图不当得利两类,形成可操作性标准。
2.确定格式条款效力
合同目的在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上主要体现在公平性方面,当格式条款限制合同主要权利或义务导致合同目的难以达成,可推定其违反公平原则导致格式条款无效。更有观点认为,在判断格式条款是否构成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时,须同时满足合同目的因该条款难以实现这一条件,才能推定格式条款违反公平原则因而无效[24]。如医院“住院条款”规定住院病人放置于病房且自行保管的物品遗失、被窃或毁损、灭失时,医院仅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承担责任。住院合同主要目的在于诊疗患者,并非照顾其财产安全,上述条款虽限制了医院的注意义务,但并非其主要义务,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并不影响格式条款效力[25]。
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公平性的认定上,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并未形成类型化标准,法院往往直接套用《保险法》第19条规定认定条款“不公平”,导致该条款沦为无视保险惯例和行业特征、片面维护弱势消费者的“口袋条款”[26]。在借鉴域外立法对不公平条款划分“黑名单”“白名单”的类型化过程中,应以合同目的能否实现作为判断保险合同条款公平性的重要标准。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规定的家庭成员伤亡免责条款,虽然保险公司认为此举意在防止道德风险,但将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排除在第三者责任保险外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合同保障受害者的特殊目的相悖,当被否定⑧。相反,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往往对投保人职业进行限定,本质上是基于风险概率精算限制投保风险,并不违背保险合同目的,应肯定此类条款效力。而司法实践中对此往往混淆,片面维护消费者一方权益而无视保险人利益。
(三)限制功能
合同目的的限制功能主要体现为对法定解除权与变更权的限制,防止一方滥用权利动摇合同关系。一方面,在发生不可抗力或者一方当事人违约的情形下,只有后果严重即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合同才可以被解除。另一方面,在情势变更情况下,只有继续履行合同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当事人才可以请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在保险法语境下,合同法定解除权事由中的“不可抗力”在保险法中多表现为约定的保险事故,构成赔付保险金事由而非合同解除事由;而“情势变更”往往转化为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情况下当事人的通知义务;更多情况下,保险人解除权的产生是基于另一方当事人违约。
保险合同典型交易目的能否实现往往影响着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在一起案件中,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在恢复原状与金钱补偿两种补偿手段中间选择恢复建筑,但后来因地方政府命令导致建筑物被拆除,保险人认为此种情况属于情势变更,故请求免除责任。但法院认为此时只是提高了履行成本,保险人并不能因此免责。保险合同以损失补偿为目的,可用金钱进行补偿,即便恢复原状的履行方式遭受阻碍,保险人也不得以情势变更为由请求解除合同及免除责任。⑨
保险合同主观目的也影响着解除权的行使及其法律后果。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等违约行为导致保险人行使法定解除权,并产生保险费或人身保险现金价值的返还等一系列法律后果,返还范围与投保人主观目的密切相关。如在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若投保人系故意,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若投保人系重大过失,保险人尽管同样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情况下,保险人可解除保险合同,并且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若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投保人并不具有非法获取保险金目的,应限制保险人行使解除权,保障无辜受益人利益。在被保险人投保两年内自杀的情况下,若能证明其不具有非法获取保险金目的,也应对保险人解除权加以限制。
(四)解释功能
作为典型格式合同,保险合同由保险公司一方制定并提供,投保人对条款内容的形成缺乏影响力,缔约双方地位并不平等,因此,适用目的解释时客观化倾向更为明显。保险合同往往是消费者合同,在主观目的的价值评判上更尊重作为消费者的投保人利益。
1.典型交易目的与特殊目的:客观准则
保险合同典型交易目的在于损失补偿,是确定保险合同性质、效力、补偿范围的客观标准,从典型交易目的出发进行解释可用于确定保险补偿范围,而不拘泥于保险合同文字。如当财产保险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对于保险项目约定的“随身财产”一致确认是指“随身财产所致损失”,在对因行程延误导致退税未果是否属于财产损失产生争议时,法院以财产保险合同损失补偿目的为由否定了投保人该项诉讼请求⑩。
在混合合同中,除传统保险合同损失补偿典型交易目的外,还存在如投资储蓄、社会保障等特殊目的,必须结合各亚合同目的对作为混合合同的保险合同目的进行整体判断。如机动车责任保险合同的特殊目的在于保障受害人合法权益,在受害人损失得到全面补偿之前,未足额投保的机动车责任保险条款中的“他保条款”(Oth⁃er Insurance Clause)应属无效[27]。又如雇主责任保险的特殊目的是缓冲雇主责任,而雇主责任险条款中往往以“意外(Accident)”或“发生(Occur⁃rence)”对赔偿范围进行限制,对“意外”“发生”的解释应强调雇主利益的保障,一味扩大雇员对意外事件预见性范围将违反雇主责任保险合同的特殊目的[28]。
2.主观目的:辅助判断
保险合同典型交易目的对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具有指引作用,但个案中也离不开对主观目的的解释。然而,主观目的对合同解释的作用仅起到辅助功能,用于印证其他解释方式结果是否正确。尤其是在格式条款的解释上,由于格式条款系一方当事人制定,缺乏双方合意,当事人动机对格式条款解释影响更小。问题二中投保人在格式合同上勾选“储蓄”仅为投保人一方动机,并未构成合同交易基础,保险合同达成合意的合同目的乃投资,当保险人尽到说明义务时,投保人不得以“储蓄”动机要求损害赔偿。
在对当事人动机即主观目的的解释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存在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争,保险法领域亦是如此。实践中,法院往往通过理性第三人的标准对当事人缔结保险合同的主观目的进行评判[29],并结合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等多种手段对免责范围进行综合认定,主观目的仅起到辅助判断作用。
3.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限缩作用
《保险法》第30条在《民法典》第498条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以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被保险人。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应建立在穷尽合同法一般解释原则的基础上[30],包括目的解释在内的合同一般解释原则在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进行解释的过程中,起到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限制作用。如《车上货物责任险条款》通常约定:“因保险车辆驾驶人的故意行为、紧急刹车引起保险车辆上所载货物遭受损失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但当保险车辆驾驶人因紧急情况避让行人、车辆而紧急刹车避险导致车辆货物损失时,保险人可否以上述条款约定拒绝赔偿?从合同目的进行分析,紧急刹车是机动车正常行驶遇到突发状况采取的常规避险措施,紧急刹车一概不赔有违投保人预期目的[31]。尽管此案运用目的解释与不利解释规则得出的结论相同,但在方法论上有显著区别,不利解释原则应坚持“最后一道防线”的适用定位。
4.对合理期待原则的规范作用
合理期待原则并不以保险合同有疑义为前提,在合同条款文义明确的情况下,法院可探求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做出与条款文义不同的解释[32]。合理期待原则偏离了传统合同法一般原理,包括疑义利益解释在内的保险合同解释一般规则均遵循“明示合同条款必须严守和履行”的基本思想,而合理期待原则却对此进行突破,不管保单文义如何规定,若保险人承担的危险是被保险人正当、合理的期待,则不可被剥夺,被保险人的订约目的亦不容落空[33]。在语义上,“期待”指人对一个特定行为将会产生某种特定结果的可能性的估计,而“目的”指人在行动之前根据需要在观念上为自己设计的要达到的目标或结果[34]。二者相比,目的更具有主动性、根本性、内生性,而期待则建立于合同相对方缔约行为与缔约环境等因素使缔约方产生的信赖上,具有被动性、依附性、外部性,保障投保人基于缔约过程产生的合理期待,有利于推动其缔约目的的最终实现。虽然我国《保险法》尚未引入合理期待原则,但司法实践中已大量适用,集中于对保险合同定义条款、除外责任和条件条款的解释上[35]。
然而反对意见认为合理期待原则是“法庭判决的保险”[36],增加法官判决的主观因素与法律适用不确定性,提高保险公司经营成本。为防止合理期待原则滥用,除将适用主体限于普通投保人,并在位阶上慎重考虑外,对期待“合理”性的规范成为关键:第一,“合理期待”必须具有客观合理性。只有理性人的合理期待才可被认可,过分的、不符合保险商业运作的合同目的不可视为合同内容。第二,“合理期待”必须符合投保目的。投保人购买保险产品与其投保目的是否匹配,特别是免责条款或限制性条款的含义是否满足投保人的保险需要,成为确认期待合理性的重要因素[35]。第三,“合理期待”必须综合判断。由于合理期待原则否认了保险合同条款字面意思,必须结合保险合同当事人缔约地点、时间、交易方式、保险代理人误导、履约情况等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真实目的进行判断[37]。由此可见,保险合同目的从主客观两方面对“合理期待”的合理性进行了规范,防止出现过于主观的、特殊的、无法预测、无法通过保单实现的“期待”。
四、结 语
“合同的本质目标是使人们能实现其私人目的。”[38]对合同目的的研究至今仍不够深入,对保险合同目的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合同本身系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合同目的也包括主观合同目的与客观合同目的两方面:客观方面的合同目的表现为典型交易目的,就是合同给付所欲实现的法律效果;合同的主观目的则是某些情况下当事人的动机。主客观融合的合同目的概念体系,既尊重了合同的外在形式,又尊重了当事人主观意愿,为研究合同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维度。在保险合同领域,保险合同的客观目的在于损失补偿,包括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对具体损失的补偿和人身保险合同中对抽象损失的补偿,损失补偿这一典型交易目的对正确判断保险合同性质、防范道德风险、防止不当得利起到重要作用。保险合同的主观目的是特定情况下保险合同当事人的主观动机,对动机的审查通过保险法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说明义务、禁止反言等制度实现,从而防范道德风险,确保实质正义。此外,实践中存在大量名为“保险合同”实为传统保险合同与储蓄合同等非典型合同的混合合同,此类合同目的应结合各亚合同目的进行综合判断,以正确认识合同性质并决定法律适用。
对保险合同目的的思考源于保险利益制度在实践中面临的困惑,保险利益既无法对保单转让行为合法性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又无法避免在判断保险合同性质与效力时的主观性与模糊性。而保险合同目的则克服了保险利益的弊端,并为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构建了统一的基础,构建保险合同目的理论体系的意义在于通过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结合,对保险法和保险合同的基本问题进行更为全面的思考,而非对保险法基本原则与制度的罗列组合。保险合同目的理论的实际适用过程,系目光集中于合同形式与当事人主观意思的过程,与保险合同损失补偿原则、保险利益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的单一适用具有本质区别。保险合同目的的主要功能包括区分功能、确定功能、限制功能和解释功能,即对保险合同与类似合同性质的区分、对保险合同与条款效力的认定、对合同法定解除权等行使的限制、对保险合同的深层次解释等。通过在具体适用中将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保险合同目的成为理解保险制度与保险合同的新维度,在调和保险法作为商事法律的形式主义与保护消费者的实质正义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文通过从功能论角度对保险合同目的进行阐述,旨在提供一个新的审视保险合同本质的维度,对保险实践及法律适用中的困惑进行解答,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注释:
① Cronin v.Vermont Life Ins.Co.40A.497(RI1898)。
② 陌生人寿险中,投机者专门以老弱者作为被保险人投保人寿保险,为其支付保险费并给予补偿,保险合同成立后立即将保单转移给并无保险利益的投机者。此类保险合同目的在于剥夺老弱者权利,也易引发道德风险,被美国多数州禁止。
③ 参见Mutual Life Ins.Co.v.Allen,138 Mass.24,31(Mass.1844)
④ Liberty Care Plan v.Department of Ins.,710 So.2d 202.
⑤ Jordan v.Group Health Ass’n,107 F.2d 239,1939 U.S.App.LEXIS4670,71 App.D.C.38.
⑥ Transportation Guarantee Co.v.Jellins,29 Cal.2d 242,174 P.2d 625,1946 Cal.LEXIS295.
⑦ 参见《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0条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保险条款中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作为除外责任含义的批复》(保监发〔2015〕90号)。
⑧ Bishop v.Allstate Insurance Company,623 S.W.2d p.866(Ky 1981);参见赵兴武、张议文:《法院:“三者险”排除家庭成员的免责条款无效》,见《人民法院报》2013年6月28日第003版。
⑨ Brown v.Royal Insurance Co.,(1859)1 E.&E.
⑩ 见(2012)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38号。
——与林刚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