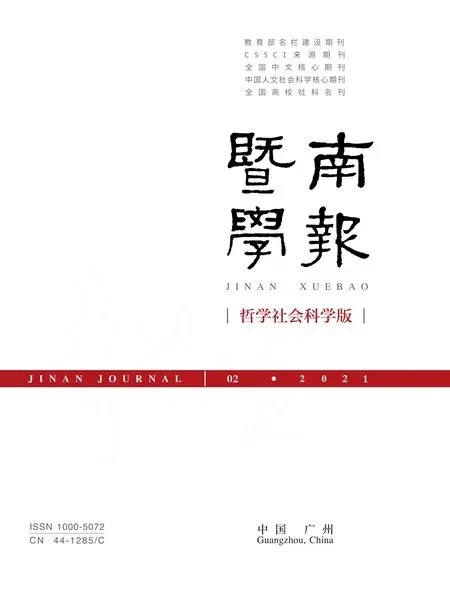变异学视域下的日本近世绘画中的李渔形象
蒋述卓, 李 治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中年改名渔,字笠鸿,号笠翁,别署觉世稗官、随庵主人、湖上笠翁等,江苏雉皋(今江苏如皋)人,祖籍浙江兰溪。明代考中秀才,入清后绝意仕途,带领家庭戏班至各地演出。41岁去杭州,后移居金陵,游历四方。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复移家杭州。在明清鼎革时期的名士中,李渔的一生折射出那个时代独有的社会文化蜕变之特征:一方面,为了糊口养家,养姬蓄妾,带领家庭戏班穿梭于达官显贵之门,靠“打抽丰”过活,带有旧时轻贱文人的习气;另一方面,追求生活闲情,深谙实用美学之道,在曲坛梨园唱出了传世之音,成为通俗文艺大家。因此,他的作品和文艺思想被认为是明代后期以“浪漫主义、经验主义及个人主义”为主的文艺美学思潮的体现。明中叶以来,追求个性自由、崇尚真情的具有近代色彩的思想萌芽,并与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相抵牾,人们对李渔的评价不可避免地被二分,毁誉参半,褒贬天壤:赞之者,如芥子园主人《弁言》所云“海内文人,无不奉为宗匠,鸡林词客,孰不视为指南”,把他视作与晚明大家李卓吾、陈眉公等同之人;贬之者斥其为“明教罪人”,如黄启太《词曲闲评》所记,将他视为“畜生道变相出来”之“恶孽魔障”。与李渔同时代的人对其“离经叛道”的言行批判不可避免地成为后进研究者衡量李渔文艺成就的重要参考。伴随清朝为巩固统治施行高压政策活动的愈演愈烈,李渔部分不遁道学之途的行为的弊端逐渐被扩大化,以至于其生前居所的地方方志对其生平都少有提及。然而,在李渔离世六十余年后,其作品远播东瀛,在日本近世文人的手中或被辗转翻阅,或被仿写改编。一时间,呈现出“德川时代,苟言及中国戏曲,无有不立举湖上笠翁者”之盛景。在日本,近世文人不仅沉迷于他诙谐滑稽的传奇,而且对他的诗词史论也爱不释卷,甚至有人把他倡编的《芥子园画传》称为“笠翁画传”。这种文学传播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变异现象是“跨文化文学交流、对话中,由于接受主体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历史背景、审美习惯等原因而造成接收者有意无意地对交流信息选择、变形、伪装、渗透、创新等作用,从而造成源交流信息在内容、形式上发生变异”,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过滤”。李渔的作品在日本近世传播的过程中,因两国文化背景、审美习惯的不同,导致李渔形象被改写、变形、再创造,呈现出别于国内的一面。这种现象在日本近世绘画作品中尤为明显。注目于“异”,有助于我们厘清李渔形象在近世出版物画像中定型的轨迹,从而挖掘出变异发生的深层文化机制。
一、日本近世出版物中的李渔画像
言及古代学者的画像集,最有名的当属《清代学者像传》。晚清名宿番禺人士叶衍兰(1823—1897)积三十年之功搜集清代学者画像,去世后,由其孙叶恭绰(1881—1968)冠以名称“清代学者像传”,于1928年将第一集交付商务印书馆影印,之后,该原稿被多次影印出版。据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版来看,像传里面收录了顾炎武、黄宗羲等共计169位学者(171幅)的画像,并且每幅画像后各附小传。一般而言,古代学者有画像传世的多为文人士大夫。对于被古代正统文学排斥、不屑的戏曲小说而言,其创作者的画像传世的也寥寥无几。虽然作为戏剧家、小说家出身的李渔并没有机会出现在该像传里,但是江户时代在日本却流传着一幅他的画像(图1)。孙楷第在日本访书之行结束不久后,撰文《李笠翁与十二楼》发表李渔小说版本研究的相关成果时,将此画一并刊印。后来,该画在国内外广泛流传。德国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在将东京尊经阁文库所藏的《无声戏》十二回影印出版时,就直接引用了孙楷第文中所载的那幅画像。另外,日本李渔研究专家冈晴夫寄送给李渔研究会的一张“日本书刊上李渔像”亦是此画像。可见,该画像在日本传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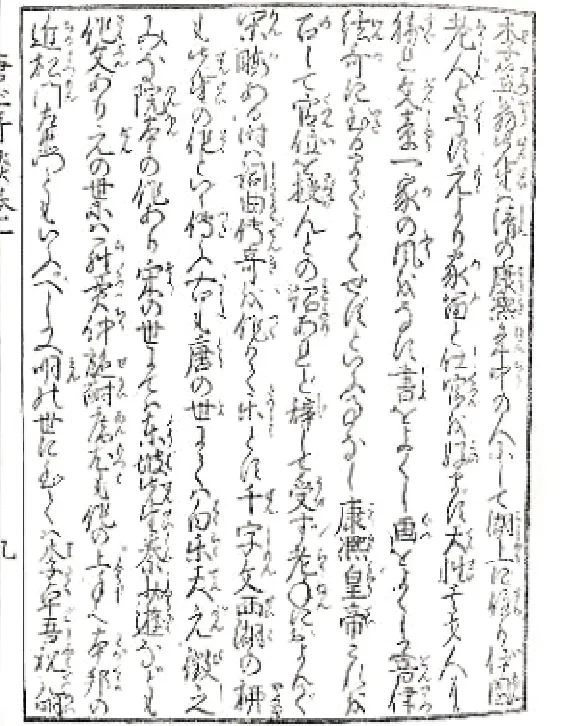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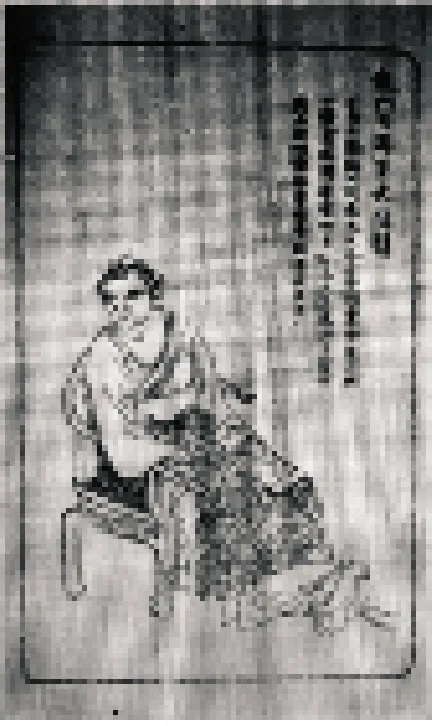
图3
学者伊藤漱平在其文章《李笠翁的肖像画》中对此画的来源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发现该画最早的出处是铜脉先生的作品《唐土奇谈》,画的作者为西邨楠亭,画像上写有“杂剧作者湖上笠翁先生画像”两行字,旁边附上署名“祇园张新炳”的七绝《题笠翁先生画像》:“芒鞋竹杖见天子,龙舰春湖赐玉巵。一曲怀仙人不解,声声惟有沙鸥知。”并附上笠翁的人物简介,曰:
李笠翁先生乃清康熙年间之人,家住西湖畔,号伊园老人。家业殷实,无心出仕,天生才高过人,文章自成一家风范,书画兼长,至若音律传奇,风流之事则无所不长。康熙皇帝召见,下旨赐官,坚辞不受。年老之际,每于闲暇时作诗曲传奇为乐。千字文西湖之柳即为先生之作。
以上七绝古诗描述的是康熙皇帝南巡坐在西湖的龙船内召见李渔。李渔却以芒鞋竹杖的形象前来拜谒,并得御赐美酒,之后,吩咐戏班伶人扮演描写自己仰慕的同姓之人诗仙李白的戏曲的逸闻。显然,诗句的描述与所载生平简历中“下旨赐官”的文字均与李渔的真实经历大相径庭。李渔早年参加科举,却屡试不第,后又遭逢明清易代战乱流离,最终绝意仕途,躬耕梨园,砚田糊口。在《玉搔头传奇》黄鹤山农序中就有记载:“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久之中落,始挟册走吴越间,卖赋以糊其口。”另外,李渔在《复柯岸初掌科》一信中也曾直言:“渔无半亩之田,而有数十口之家。砚田笔耒,止靠一人,一人徂东则东向以待,一人徂西则西向以待。今来至北则皆北面待哺矣。”
因此,与史实相对照,这是一种典型的艺术虚构,虚构部分凸显出李渔淡泊名利的自由和潇洒。但是,相比而言,这种推测和虚构的结果明显与国内专家的评论语调不同,譬如,针对“李渔绝意仕途”这一点,孙楷第先生曾说:“笠翁为什么不应举呢?大概他的脾气不耐心做举业,或者是因为浪迹江湖举业废罢了的缘故罢。”另外,杜书瀛先生在其著作《戏看人间:李渔传》的“前言”部分中指出“李渔有一颗不安定的越荡的灵魂”。国内学者的研究多是基于史实的推测并将“不仕”视为李渔人生规划上的某种“缺失”。然而,李渔的绝意仕途是其自主的、必然的人生道路抉择。在《笠翁别集》卷9有“论汲黯不拜大将军”,讲述的是中年以降,遭逢满清入主中原,虽不求做官,为的是讲求民族气节的故事;在同卷《论汉高祖为义帝发丧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同异》中李渔更是明确提倡“忠臣义士做得到头”,坚决反对做“两截人”。因此,可以说李渔的“不仕”是其深思熟虑后对明代遗民身份的自我认同。与此相对,日本文人的描述则是一种虚构的想象,里面包含的“不仕”、“拒受封官”迎合了当时世人的好奇心理。
在伊藤漱平研究的基础上,针对铜脉先生转载的那张肖像,研究者吉田惠理在文章《江户中期的李渔形象》中详细地考证,得出结论“其人物画像并非李渔本人。画中人物实际上是作者西邨楠亭在宋紫石《古今画薮后八种》卷六收录的清初浙派版画《无双谱》里的“龙门司马子长”(司马迁)的人物形象(图3)基础上,添上双髯和斗笠而成的伪作,其他均未作修改,还指出“添加斗笠是为了与笠翁的名字呼应,添加须髯则是要强调笠翁的高贵贤者的形象”。
可见,承接伊藤氏的研究,后继的研究者肯定了李渔这幅肖像画的研究价值,并认为西邨以及铜脉的杜撰是研究当时江户时期人们对李渔形象研究的重要线索之一。然而,先前研究者们的考察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有关画中人物原型的选定问题。作者西邨楠亭是以擅长人物画著称的江户后期元山派代表画家之一,他对画中人物的造型、神态的把握肯定是胜人一筹的。选择司马子长为原型的西村应当是以司马子长与李渔身上的共性为依据的。研究二者身上的“共性”能为我们把握江户时代李渔形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西邨所用的人物画像原型来源于宋紫石《古今画薮后八种》卷六收录的浙派版画《无双谱》。《无双谱》又名《南陵无双谱》,绘画者是擅长人物画创作的浙派画师金古良,镌刻者是康熙时期的御殿刻工朱圭。该画谱刊刻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绘者从汉代到宋代约1 400年间出现的40位家喻户晓的名人,如项羽、苏武、李白、司马迁等,将所录人物绘成绣像呈现并题诗文。因辑录在册的人物事迹举世无双,故得名“无双谱”。其中,司马子长的画像出现在“龙门悲司马”一页。司马迁是著名的西汉史学家,生前遭受酷刑后仍然发愤著史。“龙门悲司马”这个命名与司马迁生前“发愤著史”的事迹不无关系。针对“写史”这一方面,李渔虽然没有“发愤”著书,但是的确有撰写史论以及以史传文体写作的经历。譬如,《笠翁一家言》中收录的《论古》。该作品主要以时间为序针对某个历史人物、事件展开论述,属于专论性评点的史料汇编,共计130余篇。评论皆以“笠翁曰”开始,模仿《史记》“太史公曰”的形式,采用反诘式的意见提出方法,分析透辟,将不同时代的人物、事件进行对比,极富启发性。王仕云曾为其作序云:
李子笠翁,博物洽闻。其于二十一史,靡不根盘节解,条入叶贯,间取其源流同异,而以意断之。有翻案,有定案,不执己见,不依人墙宇,不立非非之堂而矜察察之照,而究归于理之所然,心之所安而止。
另外,李渔还编纂了一部《古今史略》。从盘古开天地写起,到明末崇祯帝自尽,继承了《论古》的史学观,一方面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时别出心裁;另一方面拈出重要时期进行详论,夹杂逸闻,整体而言,结构严谨,其风格文体有效仿同时代名人学士为吸引更多民众读者编写史书时盛行的“纲鉴”之风,堪称“通史性”的大众历史读物。
由此可见,李渔史论的眼光独到之处绝非草草几笔可以带过。在日本,李渔的史论创作也常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每当提及李渔其人,都不会忘记这一点。譬如,江户时期的读本巨匠、李渔作品的忠实读者曲亭马琴曾在与友人的往来书信中提及李渔的生平,介绍道:“李笠翁乃清初人士,家住西湖畔,故称湖上笠翁。家业本富,于湖畔造书斋,取扇形窗,宛若折扇扇面,倚窗凭机,以写作诗文及稗史传奇自娱。”另外,才识通达、学贯古今的日本近世汉学家斋藤拙堂曾称赞《笠翁一家言》中的史论“间有可取”“亦不敢废”,在言及“笠翁论陈平不对决狱钱谷”之问时,指称:“前篇甚正,后篇甚确,语并剀切。使起陈平于九原之下,亦将愧赧而不置辨矣。不意笠翁而有斯论也。”在同页评李渔著作《资治新书》时,指出“书载祥刑,末议慎狱。刍言数十则,皆笠翁所著,颇有条理”,并由此揭示“乃知笠翁非徒滑稽之雄”“笠翁亦欲以事业显者”。另外,在李渔的交友圈中,也不乏历史学家的身影,如“参加《明史》编纂活动的王鸿绪(1645—1723),《(清)太宗 文皇帝实录》的编辑李蔚(1625—1684),《钦定大清一统志》的总编徐乾学(1631—1694),《中山沿革志》和《使琉球杂录》的作者王楫(1636—1699),众所周知的《明史纪事本末》编撰人谷应泰以及因撰《崇祯五十宰相传》而成为历史名家的曹溶(1613—1685)”。与这些史界名人交友,无怪乎李渔的史论兴趣颇高。
近代戏剧理论专家笹川临风在其编著的《中国文学大纲》卷三“李笠翁卷”中专门辟一章研究李渔的史论,直言“笠翁多才,善取材于上至五帝下至明崇祯的历史故事进行简短的评论”,还选取了李渔论说“汉高祖为义帝发丧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性质是一样的”等例子,认为“笠翁论史的眼光不高,无法跟史学家相比,但是其观点新颖、方法奇特,仍有可取之处”。另外,当以假名垣鲁文为代表的戏作者们联名登报发文,向明治政府人教部建言,为“戏作文学”正名的时候,亦提及笠翁,文中将其与罗贯中并置:“抑戏作之形式乃以虚为实,或以实为虚,或借用事迹名籍,或将正史脱胎换骨,中国的罗贯中、李笠翁等人的小说与我源氏狭衣等其他物语皆如此。”由此可见,自江户时代以来,人们对李渔的史论创作还是耳熟能详的。对李渔的稗史传奇作者身份的一面也是有清晰的认识的。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当时西村选择早于李渔几百年的司马子长的形象为原型时,除了考虑人物的年龄、神情外,还兼顾了李渔稗史传奇作者的身份。难怪擅长考据的伊藤漱平对马琴著作《犬夷评判记》的卷首插图中的马琴画像存疑时,首先联想到了李渔所著《闲情偶寄》卷十二“器玩部”暖椅图中的“李渔”画像。伊藤漱平在其文《李笠翁的肖像画》中曾明确指出柳川重信负责绘制的《犬夷评判记》卷首插图中的马琴形象是根据李渔《闲情偶寄》卷十二之“器玩部”暖椅图中的李渔形象杜撰而成。然而,后面经过细川晴子、服部仁、向井信夫等人的查证,与马琴古稀寿像进行对比,确认《评判记》里的马琴形象是他本人。虽然最后被证明两幅画像无关,但是由此可以看出以伊藤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对李渔与马琴的相似程度的认可。从司马子长到曲亭马琴,江户时代人们对李渔的形象的认知承载了那个时代合理性的想象。
二、《十便十宜帖》与李渔形象雅味的确立
李渔跟日本近世画坛之间有一段不解之缘。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纪念馆里珍藏着一件日本国宝级的画册《十便十宜帖》。该画册是由日本近世文人画的集大成者池大雅与日本近世著名的俳人、文人画画家与谢芜村根据《笠翁诗集》(卷七)《十便十二宜诗》合作而成。池大雅(1723—1776)是江户时期文人画的集大成者,他的作品多取决于描绘中国文人的理想居住方式,其画法尤以“指墨”著称。与谢芜村(1716—1784)是江户时期著名的俳人、画家,“芜村”是他的俳号,相传取自陶渊明的抒情小赋《归去来兮辞》“田园将芜”之句。可见,《十便十宜帖》的两位作者都“对中国文人隐居式的生活满怀憧憬”。池大雅和与谢芜村都是代表日本近世文人画的第二代巨匠。虽然二位都不是武士出身,也不是侍奉大名或大寺院的专用画师,但是,他们作为具有独创意识的职业画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该画帖是在受到尾张藩素封家下乡学海的委托下,池大雅和与谢芜村即兴合作而成的,创作时间为明和八年(1771),池大雅时年四十九岁,芜村五十六岁。
作为该画帖的创作素材的《十便十宜诗》是被收录在《笠翁一家言诗词集》里李渔诗作,目录记载名称为《伊园十便》《伊园十二宜》,但实际上都各存十首,合称为“伊园十便十宜诗”。针对诗篇,李渔在序中还特意阐明了创作的缘由:
伊园主人结庐山麓,杜门扫轨,弃世若遗,有客过而问之曰:“子离群索居静则静矣,其如取耠未便何?”主人对曰:“余受山水自然之利,享花鸟殷勤之奉,其便实多未能悉数,子何云之左也!”客请其目,主人信口答之,不觉成韵。
崇祯十三年(1640)到十五年(1642),李渔结庐伊山,深居简出,追求“采菊东篱下”的远离尘世喧嚣的田园之趣。这段辋川桃源般的生活冲淡了科举落第的失意落魄。这部歌颂伊园生活的诗歌描写的恰恰是这段山居生活。《闲情偶寄》卷六也有记载:
追忆明朝失政以后,大清革命之先,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夏不谒客,亦无客至,匪止头巾不设,并衫履而废之。或处乱荷之中,妻孥觅之不得;或偃卧长松之下,猿鹤过而不知。洗砚石于飞泉,试茗奴以积雪;欲食瓜而瓜生户外,思啖果而果落树头。可谓极人世之奇闻,擅有生之至乐者矣。后此则徙居城市,酬应日纷,虽无利欲熏人,亦觉浮名致累。计我一生,得享仙列福者,仅有三年。今欲续之,求为闰余而不可得矣。伤哉!
显然,李渔描绘桃源式的伊园隐居生活的文字打动了具有相似境遇的文人墨客,令其羡慕向往之果然,在漂洋过海抵达东瀛后,在为后世尊敬的文人画画家“双璧”——池大雅、与谢芜村的笔下,终于幻化成《十便帖》《十宜帖》,最后合为《十便十宜帖》。其中,“十便”包括:“耕便(山田十亩傍柴关,护绿全凭水一湾。唱罢午鸡农就食,何劳妇子馌田间)、课农便(山窗四面总玲珑,绿野青畴一望中。凭几课农农力尽,何曾妨却读书工)、钓便(不蓑不笠不乘乘舠,日坐东轩学钓鳌。客遇相过常载酒,徐投香饵出轻鲦)、灌园便(筑成小圃近方塘,果易生成菜易长。抱瓮太痴机太巧,从中酌取灌园方)、汲便(飞瀑山厨只隔墙,竹鞘一片引流长。旋烹佳茗供家客,犹带源头石髓香)、浣濯便(浣尘不用绕溪行,门里潺门里潺湲分外清。非是幽人偏爱洁,沧浪引我濯冠缨)、樵便(臧婢秋来总不闲,拾枝扫叶满林间。抛书往课樵青事,步出柴扉便是山)、防夜便(寒素人家冷落邨,只凭泌水护卫门。抽桥断却黄昏路,山犬高眠古树根)、吟便(雨扉无意对山开,不去寻诗诗自来。 莫怪囊悭题咏富,只因家住小蓬莱)、眺便”;“十宜”包括“宜春(方塘未敢拟西湖,桃柳曾栽百十株。只少楼船载歌舞,风光原不甚相殊)、宜夏(绕屋都将绿树遮,炎蒸不许到山家。日长闲却羲皇枕,相对忘眠水上花)、宜秋(门外时时列锦屏,千林非复旧时青。一从浇罢重阳酒,醉杀秋山便不醒)、宜冬(茂林宜夏更宜冬,御却寒威当折冲。小筑近阳春信早,梅花十月案头供)、宜晓(开窗放出隔宵云,近水楼台易得昕。不向池中观日色,但从壁上看波纹)、宜晚(牧儿归去钓翁休,画上无人分外幽。对面好山才别去,当头明月又相留)、宜晴(水淡山浓瀑布寒,不须登眺自然宽。谁将一幅王摩诘,晒向当门倩我看)、宜阴(烟雾濛濛莫展开,好诗凭着黑云催。卷簾放却观天眼,多少奇风作意来)、宜雨(小涨新添欲吼灘,渔樵散去野索寒。西山多少空濛色,付于诗人独自看)、宜风(鸟皈芳树蝶过墙,花与邻花贸易香。听罢松涛观水面,残红皱处又成章)”。根据诗文的内容,可以看出“十便”体现的是李渔在伊园生活的便利之处,“十宜”是描述伊园四季昼夜的自然变化。前者讲人事,后者状自然。就《十便十宜帖》而言,两位作者各有千秋:池大雅的运笔更加柔和舒展,清新飘逸;而与谢芜村的画法则稍显突兀,别有一番风味。芜村在创作《十宜帖》中的“宜晓(开窗放出隔宵云,近水楼台易得昕。不向池中观日色,但从壁上看波纹)”帖时,竟能结合《笠翁诗集》中李渔针对“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提出的有别于杜甫绝句的观点,在进行绘画时,将阳光洒在池中照亮房壁映出波纹的样子生动地展现于画卷。可见,画家在创作时对李渔及其作品的熟悉程度和领悟能力。对此,日本美术史学家吉泽忠曾评价道:“虽然根据笠翁的传记描述来看,笠翁称不上传统意义上的隐遁者,但是透过大雅和芜村的创作,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画中的笠翁超脱世俗的隐者气质。”另外,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小林忠、德田武也认为:“大雅是受到笠翁诗文的启发,沉浸在平易恬淡的田园山水氛围之中(耕便、课农便、浣濯便、樵便、防夜便),换言之就是桃源乡的境界,这里有弥漫着一种老庄先哲无为思想图景下的自在生活气息(钓便、灌园便、汲便、樵便、吟便、眺便)。”李渔的作品在其去世后六十余年才漂洋过海到达东瀛。日本近世的人们只能通过他的生前之作去勾勒他的形象、遥想他的创作生涯。“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李渔生命中最美好的三年伊园小隐时光虽然短暂,但是在时间信使的帮助下,那些流淌着真情的文字被诉说给作为满怀“中国憧憬”的文人画家倾听,让他们感受到了李渔生命中确曾拥有的辋川之意、桃源之思。因此,在日本文人画世界里,李渔的形象多了几分自由恬淡、洒脱闲适。按照品鉴古诗的传统标准,李渔的这篇诗文,无论意境的创造还是用词的推敲、用韵的斟酌都难称绝妙之作。但是,历来以“诗书画”三绝著称,“中国趣味浓重”的文人画画家却能在中国古典诗词海洋中挑选出李渔之作绘制成传世名画,这种独特的亲近感不得不引发人们的思索。原来,李渔之名在日本近世画坛上早就借着其倡编的《芥子园画传》远播普及,成为“笠翁画传”里那位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笠翁”。
三、《芥子园画传》东渡日本与李渔雅致形象的放大
《芥子园画传》又名《芥子园画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绘画技法图谱,有“传统绘画教科书”之称。从1679—1701年的20多年间,《芥子园画传》一共出版了三集。李渔作序的是《芥子园画传》第一集,主要是山水图谱,共五卷。卷一为《画学浅说·设色》,卷二为《树谱》,卷三为《山石谱》,卷四为《人物屋宇谱》,卷五为《名家山水画谱》,几乎将中国画的基本画法和传统流派都囊括在内。据载,李渔女婿沈心友家中收藏着明代著名山水画家李流芳用来教授学生的“课徒山水画稿”43页。为使“世间爱山水者,皆有山水之乐”,他请当时居住在金陵的书画名家王概进行整理增编。王概用了3年多的时间,将画稿增编到133页,将中国传统画的各种技法分门别类地介绍出来,并附上40幅临摹古人的各式山水画。后来,在李渔的支持下,采用当时先进的木板彩色套版印刷技术将此书刊行天下。沈心友为感念岳父之恩,取书名为“芥子园画传”并请其作序。《芥子园画传》主要采用中国南宗派的画技、画法,另采撷历代画论之精要,以绘画的方式来阐释写生、笔法、构图的技巧,堪称山水画理论实践的宝典。现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芥子园画传》初集初刻初印本一书的装帧古朴典雅,墨蓝色的封面上题写着“芥子园画传”以及卷帙。翻开书,发黄的纸张上虽略有缺损,但是整体看来,楷书工整,插图清晰,堪为难得一见的善本古籍。而且,书中每页均有统一的定制,图文均在框中。框高21.4厘米,宽14.6厘米,书名“芥子园画传”,题在版心。单黑鱼尾,鱼尾下篆刻卷帙和页码。此书付梓以来供不应求,之后芥子园相继出版了续编的第二集、第三集。乾隆四十七年间由于多次刊印,到清末光绪年间图画已失去原有的光鲜度,所有损毁,于是,巢勋从师张熊处获得精印版的初集、二集、三集,用复印刊刻,版权属上海鸿文书局,初印时间为光绪十四年(1888)。
由此可见,《芥子园画传》初集的主要编纂者应该是康熙年间著名的金陵画家王概,确非李渔。并且,李渔去世后,续编的《芥子园画传》二集、三集也主要是由王概、王蓍、王臬三兄弟负责,之后的增编负责人也主要由巢勋担任。从沿用的“芥子园画传”的称谓也可看出,李渔的身份最多就是该画传倡编者以及初级序的编写者。
有关《芥子园画传》东渡日本的时间有三种说法:其一,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安西云烟著作《鑑禅画适》(又名《近世名家书画谈三篇》)。该文详细记载了宽永年间1624—1628年间由黄檗僧徒初到日本时将画传带去。但是,正如《芥子园画传》日译本作者山本元所讲:“《芥子园画传》初集是在清康熙十八年(1679)付梓刊刻的,所以,云烟所言有误。”其二,江户时期的“岸派”画家代表人物白井华阳在其著作《画乗要略》中讲道:“梅泉曰、元禄年间(1688—1703)、徂徕先生得清人李渔芥子园画谱,大奇,进献幕府纳于官库。”其三,江户时期的狩野派画家代表人物林守笃曾在他的著作《画筌》序里多次提及并将其列为引用书目,并且其中有“笠翁画传”的字样。该序作于正德二年(1712)。另外,学者小林広光的以下推测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考:
当时毫无名气的林守笃只是直方藩黑田家的武士,能亲眼目睹《画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很可能林是从老师黑田家的画师狩野守房或从狩野派高徒那里听闻画谱的名字,并了解某些画论后,才知道此画谱的重要性,遂特意添加几笔有关画谱的文字。因此,江户狩野派里有威望和地位的画师应该很早有机会接触过画谱初集。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初集传日的最晚时间应该在正德二年。另根据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的相关数据以及戚印平《日本江户时代中国画谱传入考》中有关《芥子园画传》部分内容进行校对整理后,可以粗略统计,江户时期日本经由长崎引进的《芥子园画传》达几百部。上至幕府将军下至普通的绘画爱好者都曾领略过《芥子园画传》的风采,并深深为其吸引。在如今的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内,保存着当时江户幕府图书馆整理的业务日志,里面曾详细地记载了“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吉宗于享保八年(1723)阅览过《芥子园画传》初集”的情况,以及书库“鉴于吉宗对《芥子园画传》的关心,特于第二年收藏了两种《芥子园画传》:康熙十八年出版的山水树石谱,共计五册以及画传前三集,共十三册”的情况。针对《芥子园画传》广受欢迎的原因,王伯敏曾在《中国版画史》中总结道:
第一,这是一部绘画的教科书。在清代来说,文人在诗文之余,都喜欢画几笔。这部画传说的既是画理画法,画的又大都是示意图式,年青的学者除了得老师的传授之外,参考一下这部书,多少有着一些得益。(中略)第二,当时没有照相机,又无玻璃版的影印,一般学画者,要想看到古代名家的作品,确实不容易。(中略)《芥子园画传》既摹绘了古代各家的画法于一册,如何不教一般学画者急于要购买。第三,《芥子园画传》不只是绘画的教科书,也是一部诗画谱,其中有许多幅图画,必录古人诗词于其上,这就迎合了好多文人雅士,置书一册,放在案头,偶然翻阅,既为“卧游”。(中略)第四,绘、刻、印三者的精美巧丽,也就是在版画的水印套色上有其卓越的成就。
可见,《芥子园画传》的制作在绘、刻、印三方面的技术水准都堪称卓越。当《芥子园画传》初集搭乘中日贸易的大船抵达长崎港后,日本文人多以“笠翁画传”称之。江户中期正德二年,狩野派画师林守笃在《画筌》的参考书目中记有“立(笠)翁画传”,并在序中写有“一凡引用书又不多图绘宝鉴。立(笠)翁画传。图绘宗彝(中略)等摄其要为画工之一助也”。不用“芥子园画传”的名称,而独选“笠翁画传”称呼之,可见对“笠翁”的亲切感,或者说内心已经把它当作笠翁之作。无独有偶,汤浅元祯曾在《文会杂记》卷三上《南郭老之说》记载,服部南郭(1683—1759)多次提及《芥子园画传》, “《八种画谱》为至俗之绘画,不足予评。与立(笠)翁画传相比,乃今日日本之町画,怎样也算不上是佳作”。江户中期以后,随着日本版画技术的提高,平安河南楼刊行的前三集和刻本的普及,日本近世美术界掀起了引用《芥子园画传》里的画论、画谈的热潮。对此,樱井雪馆在其著《画则杂话》里回答门人有关学习《芥子园画传》的笔意相关的疑问时曾讲道:“(学画者)多与笠翁亲近,喜欢附录之古人山水之图法,则易失其笔意。若知其笔意后再观,则益处甚多。”这里也是使用了“笠翁画传”的称谓。 由此可见,《芥子园画传》东渡日本以来,其中的画论受到日本画坛包括诸多流派名家的青睐,以至于都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著作里或引用或提及之。其中,将画论视作“笠翁画论即笠翁”之言的类似表现在国内尚未发现。
上述提及的江户名家个个汉学学养深厚。其中,服部南郭等人对日本文人画的形成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由此,《芥子园画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文人画的形成和发展。于是,在这个汉学教养文人圈(汉学家、俳谐作家、画家)里,“笠翁”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眼中的那位画论造诣高深的“文人”的代名词。虽然李渔并非《画传》的作者,只是倡编者以及初集序的撰写者,但是在日本文人眼中,能集结历代名家的代表性画论,重金倾囊请名家执笔,并采用最先进的彩色套印技术发行如此一部优秀的画谱,“李渔的眼光和功劳是概莫能外的”。就连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在中日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内刊行的相关书籍中,提及李渔都会对其高瞻远瞩,倡编画传之举大加褒扬。由此可见,日本人眼中的《芥子园画传》与李渔关系之一斑。
四、文化过滤机制下李渔形象的雅味考辨
“辞官不仕”的湖上笠翁、隐居山林的伊园主人,日本近世文人对李渔形象的独特接受方式隐含着那个时代的审美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在文学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过滤机制的影响产生的。文化交流和比较是在选择和扬弃过程中进行的,信息接收方为了使被遮蔽的信息敞开,通常将传播方在文化传播中附加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从而更好地接受、吸收。因此,在文化背景与审美需求的双向制约下产生的“期待视域”是“阅读理解得以可能的基础,又是其限制”。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德川幕府的武家政权统治稳固。在后期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其社会内部孕育着新的阶级。经济上,随着农产品交易的商品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的发展,以大阪商人为中心的商人群体逐渐成长为新生的阶级,丰厚的物质资本是该阶级最大的优越性;文化上,随着武士阶级采用的朱子学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町人阶层逐渐建构起满足自身伦理诉求的“石门心学”,另外,以教师、医生为主的儒学知识分子与“萱园学派”对中国的舶来学问和艺术展开新的探讨,以图挣脱儒教伦理的束缚,为自身的文化和艺术的价值寻找逻辑自洽的出路。但是,由于在元禄、享保时期,幕府大力推行鼓励文教政策,掌握文化知识、通晓自然科学技术的文人群不断扩大,形成了“海内文章落布衣”的庞大的民间知识分子群。在世袭制的诸多弊端影响下,知识分子群体的构成随之改变。一方面,在民间随着“作养子入仕”机会的减少,有才之辈多流落在野。即便有招纳在野才子的现象出现,被招纳的这群人也碍于正统身份的缺乏受阻于官场,仕途短暂,只能返回民间舌耕鬻学,继续苦等伯乐的出现。而此时,活跃于京阪间的以商人、手工业者为代表的町人们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后,逐渐关心起自身的修养问题,并渴求构建属于自己阶层的知识话语文化圈,于是,资重金邀请在野学者至町人自设的讲堂,传授知识、启迪思想;另一方面,随着文教的普及,追求自由思想的世袭子弟逐渐厌倦世袭主业的枯燥无味,转而在业余的兴趣爱好中寻求自适之境。
因此,在世袭制的阴影下,下层知识分子为谋生计不得不迎合町人喜好,远离阳春白雪而委身下里巴人,抛弃枯燥的经世之学而推崇有趣的实用之道;上层知识分子苦于世袭家业阻碍自身才能的自由发挥,寄情于儒学之外的诸学。于是,分执诸端的知识分子们怀着对自由思想的执着向往,掀起了“游于艺”的风潮,并形成对抗朱子学权威的潜流,影响着日本近世文艺的发展。随着“游于艺”风气的蔓延,知识分子舞文弄墨、欣赏文人古玩的兴致渐浓。作为学养的汉学典籍被细化,从宽文期的“外典”“诗并联句”“字典”的扩展到宝历期“经书儒书”“诸子”“文集”“尺牍”“诗文”“历史并纪年”“传记”“故事并杂书”“小说”“类书并字典”“印谱”“书法”“拓本”。在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与艺”的孔门修学四课的启发下,不得志的文人知识分子们或痴迷于汉诗,或热衷于唐话研究,或精于小说编写,或长于书法、篆刻,或喜好外来的乐器研究,在儒学之外开辟出一方可以离俗自适的精神乐土。
此时的美术界,正如加藤周一描述的那样:
世袭的宗家独占鳌头,独恃特权,固步自封,毫无创造力,动辄将毫无意义的作品挂以“秘传”字样,故弄玄虚,以博眼球。人们创作的抒情诗大多是乏味无聊的德川时代的宫廷和歌;日本传统戏剧能乐舞台亦缺乏新作死气沉沉;绘画领域则以土佐光信为宗的追求“探幽”趣味的狩野派为主。总之,整个文艺界到处充斥着权力的恶臭,好像罹患了“动脉硬化”。
在此背景下,新生的阶级力量积极酝酿打破旧有格局的能量。在画坛,一方面,由京都御用和服商人世家的尾形光琳受表屋宗达装饰画和雪舟泼墨技法的影响,开创“宗达—光琳”画派,满足了上层町人群体的艺术需求;另一方面,迎合下层町人艺术趣味的浮世绘画师继续研磨浮世绘画法技巧,促进了木版画艺术的发展。与此相对,儒者知识分子阶层也以积极的姿态展开与狩野派的对抗,再次把目光投向中国,将上方的武家的艺术追求与大众审美需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独具日本文化特色的“文人画”。《芥子园画传》集历代诸多名家画论、画作于一体,广泛流布,滋养了众多绘画爱好者。这批画坛新秀终于揭开绘画“世袭”“秘传”的神秘面纱,并以撕破云天之势与画坛世袭制做对抗,为民间布衣陶冶“文人趣味”争得方寸乐土。于是,绘画成为御用画师之外的画师可以享受的艺术熏陶,并成为画师之外的平民都可以享受的文艺盛宴。因此,笠翁的画谱倡编之功产生了改写日本近世美术史的效果。在此文化背景下,身为文人画名家,池大雅和与谢芜村在艺术海洋中徜徉,经过选择、扬弃,最终瞩目李渔并拈取其诗作绘制《十便十宜帖》。
与此相对,在庶民文艺的世界,小说、戏剧常受到正统文学的排挤,被视为“末技”。“润笔”谋生的庶民文艺创作者多是在书商的催促下挥笔疾书,这一点颇像李渔“挟策走吴越间,卖赋以糊其口”的奔波生活。自八文字选译《蜃中楼》开日译中国剧本之先河以来,民间掀起了中国戏曲热,甚至出现了劝告都下儒士切莫沉溺传奇、俗语小说荒废学业的警语。李渔专擅传奇小说创作。被视作“史之余”的稗官小说是“头巾褦襶,章句腐儒”所不知之事,因此,在西邨楠亭以司马迁的画像为粉本,凸显出李渔文史兼长的优点的同时,铜脉先生杜撰其“辞官不受”携戏班游走天下的潇洒文字,满足了边缘儒士、下层町人的阅读期待,并与其心目中理想的笠翁形象做回应。最后,在与审美需求高度契合的文化过滤,或可称“文化误读”的作用下,终成跨越时空的深信不疑。
五、结 语
诚如李渔好友许茗车所言:“笠翁岂易知哉!此以词曲知笠翁,即不知笠翁也。”江户文人们在 “一夫不笑是吾忧”的戏剧家身份之外,感悟出笠翁的另一种形象。这种形象,通过以上对西邨楠亭杜撰的李渔肖像画的解读、日本国宝《十便十宜帖》与李渔隐世形象的剖析以及《芥子园画传》东渡日本对作为倡编者李渔形象的影响的研究变得渐渐清晰,那就是一位文史兼长、离俗隐逸、独具慧眼和有雅致品味的艺术家形象。这种形象与“躬耕梨园、砚田糊口”的戏剧家笠翁的“俗”味是完全不同的。以比较文学变异学为理论视角,通过“文化过滤”研究机制探析“异”的产生,可以发现,这是“世袭制”文化语境与日本近世文人审美需求过滤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