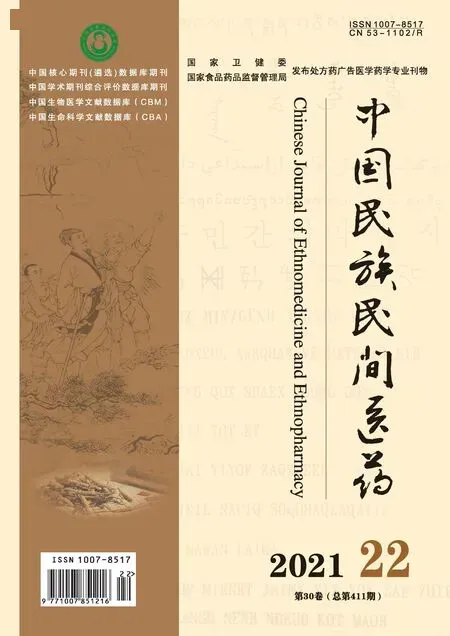张景岳“邪正”理论在不寐中的运用与局限
魏泾纹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 成都 610075
不寐,现又称失眠,临床上主要以难以入睡,或眠而复醒,或寐而不酣,或彻夜不眠等为表现。不寐的原因有很多,从古至今,许多医家多从情志失调、心虚胆怯、阴虚火旺、痰湿壅遏、饮食积滞等角度施以方药。在众多医家中,张景岳独出心裁,以有邪无邪作为不寐的辨证纲领,化繁为简,为后世医家治疗不寐提供了新的思路,但限于种种原因,张景岳的理论也有其局限。
1 张景岳对不寐的认识
张景岳对“不寐”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景岳全书》、《类经》两书中,以《景岳全书》为主。其中,张景岳的“邪正”思想在《类经》中已可管窥一二,在《类经·不卧多卧》篇中,他提到:“凡不寐之证,有邪实者属外因,有营虚者多属内因”。这一思想在《景岳全书》中得到了充分地论述与运用,他在该书中强调,不寐虽然病因病机各异,然而总体而言可用“邪正”二字概括,有邪者多属实,无邪者多属虚[1],因此,在不寐的治疗上,他主要遵从补虚、驱邪两大方针。
1.1 无邪而不寐者,审其虚而补之 在《景岳全书·不寐》篇中,张景岳认为,在没有邪气的侵扰下,不寐的原因是营气不足。他认为,营主血,心藏神,营气不足则血虚,血虚则心失其养,故神魂不安以致不寐。诊疗上,他以脏腑辨证为主,审其虚之所在而施治。
在具体论治里,张景岳认为无邪而不寐的主要病因是思虑劳倦过度,因心主神、脾主思,且心和脾与气血的流转和生成有直接联系,故其将病位主要定位于心脾二脏。具体病机上,张景岳多考虑心气虚,或心血过耗、心脾两伤、气虚精陷等。治疗上,张景岳重在养营养气,视具体病机,或兼滋阴清热,或兼补益中气,所用方药多以养心汤、寿脾煎、天王补心丹、补中益气汤为主。
若涉及他脏,如肝脾虚损、精血不足,或五脏气血亏虚等,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新方八阵》中自创三阴煎、五福饮、七褔饮等方剂,旨在益各脏之气血,积精全神,故神安而人自寐。
1.2 有邪而不寐者,随其实而去之 引起不寐的实邪,主要被张景岳分为风寒、火热、痰饮、饮食、水湿、气逆、阴寒七类。《景岳全书·不寐》篇里谈到:“有邪而不寐者,去其邪而神自安”,故治疗上以驱邪为主。如诸风寒者,以柴胡饮及麻黄、桂枝、紫苏、干葛等散之;火热者,竹叶石膏汤及黄芩、黄连、栀子、黄柏等凉之;痰饮者,温胆汤、导痰汤、六安煎之类化之;水湿者,五苓散、五皮散之类分利之;食饮者,大和中饮、平胃散之属消之;气逆者,四磨饮、排气饮之属行之;阴寒者,理阴煎、理中汤辈温之。诸如此类,皆以去邪为要,邪去则神安,乃能卧。
1.3 大虚兼小邪者,补虚为其本 除了单纯的正虚和实邪致病外,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不寐》篇中还考虑到,当患者处于因思虑劳倦过极而致血液妄耗,或素来体弱,或大病后、产后等状态时,虽然兼有微痰微火等实邪,仍当固本为要,法当培养气血,待血气来复则诸症自去。
2 张景岳“邪正”理论在不寐中的局限
尽管不寐的病因病机被张景岳用“邪正”二字做了归纳,但笔者认为,张景岳的理论尚有不完善之处。首先,在《景岳全书》“无邪而不寐”的论述中,张景岳主要将病位定在心、脾,对肝、肾病变所致不寐缺乏足够认识。其次,在上书“有邪而不寐”的论述中,张景岳列举的邪气颇多,却缺少瘀血一类。另外,纵观张景岳对不寐的认知,其仅将不寐的病因病机局限在营气不足与邪气侵扰两个角度,却对机体本身寤寐机制失调致病描述了了。以上几点便是张景岳“邪正”理论在不寐中的局限。
2.1 肾水不足而致心烦不得卧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提到,肾精不足可致不寐,但他仅从恐畏伤肾一个角度简要说明了肾亏致病的机理;另外,他治疗不寐的方药,如三阴煎、五福饮、七褔饮等,多以补益心、脾、肝虚损为主,并未看到直接针对肾精亏耗的相关方药。其为张景岳的局限之一。
实际上,从古至今,情志内伤并不是导致肾精亏耗的唯一原因,专门针对肾精亏虚的方药也有被医家发掘。《素问·上古天真论》云“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肾藏五脏六腑之精,内寓元阴元阳,除了张景岳所说的情志内伤可致精亏外,若其人素体亏损,或房劳不节,或过食辛热,或外感温热,皆可导致精伤气耗。肾水不足,从而火亢于上,水火未济,阴虚不受阳纳,从而心中烦而不得卧。临床上主要以不寐伴见口干乏津、脉细数、舌红绛、梦遗、健忘等为具体表现。针对此病机的方药为黄连阿胶汤,意在育阴清热,交通心肾。其中,黄芩、黄连直折心火、内坚真阴,阿胶、白芍育阴和阳,佐以鸡子黄补血滋肾。除黄连阿胶汤外,也可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交泰丸、知柏地黄丸等方药。
2.2 将军之官谋虑太过而致不寐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里提到了思虑致病,并且将思虑太过作为不寐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张景岳将其重心放于心、脾,却忽视了肝作为“将军之官”,也与思考谋虑有着一定联系。这一点上,无论是古代医学经典,还是后世医家,他们从理论到治法方药上均对肝与不寐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
《素问·灵兰秘典论》中记载“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素问·举痛论》记载“思则气结”。肝属风木、主疏泄,性动而急,因此,谋虑太过、思虑不已会导致肝郁气结,气机无以正常运转,气滞血停,血无以布,阳无所依,故不得眠[2]。此外,思虑日久可耗伤精血,人卧血本应归于肝,精血耗损,肝藏血功能不能正常运行,魂无所依,故见不寐。临床上常见不寐多梦,伴有易怒、头晕、耳鸣、口苦等。治疗上,《素问·脏气法时论》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因而在具体用药上,后世医家针对肝采取疏养并施、体用兼顾的治则,在《素问》的理论基础上运用丹栀逍遥散加香附、白蒺藜、沙苑子疏肝理气,清除郁热[3]。
2.3 瘀血致不寐 在张景岳之前,已经有医家提出了不寐与瘀血有关的理论和方药,张景岳在《景岳全书·血证篇》中指出了瘀血的治法:“血有蓄而结者,宜破之逐之,血有涩者宜利之,血有虚而滞者宜补之活之。”但张景岳却并未将瘀血归纳在造成不寐的邪气里,此为张景岳的又一局限。
在长期顽固性不寐中,瘀血既是病因也是病理产物,其客于脉中,阻滞气机,令血脉不通,新血不生;由于气血运行不畅,久而久之又会形成新的瘀血,营卫气血不能正常运行,故导致不寐[4],临床上表现为难以入眠,或是睡意了了,伴见心烦,记忆力减退,舌质偏暗、有瘀点等。其治宜活血化瘀,后世医家多采用血府逐瘀汤一类,令血脉和利,气血运行通畅,神有所归,睡眠乃至。
2.4 自身寤寐机制失调而不得卧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正常的睡眠建立在机体本身的寤寐调节机制上,即卫气的正常运行[5]。《灵枢·口问》载:“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行于阴……阳气尽,阴气盛,则目暝,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人体不寐的原因是卫气在夜间不得入于阴,以致阳气盛,阴气虚,故引发不寐。因此,根据《黄帝内经》所给的方案,治疗不寐法当调节阴阳,所用方剂为半夏汤,方用半夏五合,秫米一升,煎用长流水,炊用苇薪。
张景岳在解读《黄帝内经》时,虽然也认可卫气运行失常可致不寐,但在诊治不寐上,他仍以“邪正”理论为主导,在《类经》中,他认为“邪气感人,令人寐无从生……半夏汤一法,盖专为去邪者设耳”,这使其局限了半夏的作用。根据《景岳全书·本草正》的描述,张景岳仅认为半夏可燥湿降痰、止咳消痞、滑润通便,可实际上,清代张锡纯分析本方时认为:半夏并非用来利痰,而是起到交通阴阳,和其表里的作用,人体因机体阴阳失和导致不寐,正需要生长于夏半由阳转阴之时的半夏来调和。
后人有用小柴胡汤治疗不寐者,其原理也大多来源于半夏汤。该类患者多因少阳枢机不利,气机升降失调,卫气不能出阳入阴而致不寐[6],小柴胡汤与半夏汤类似,是调和阴阳、沟通表里之祖方,运用小柴胡汤沟通表里,则阴阳自和,其卧立至。
反观张景岳,他在其“邪正”理论的框架的限制下,过分强调驱邪,却忽视了《黄帝内经》治疗不寐的重点并非在于驱邪,而在于调和机体自身阴阳。这也是张景岳的局限之一,让他既局限了半夏的功效,也没体悟出调和机体阴阳而治不寐的治法。
3 结语
张景岳化繁为简,将不寐的病因病机以“邪正”二字归纳,无邪而不寐者多补其营血,兼补心脾;有邪而不寐者祛其邪气;在补虚祛邪的同时,张景岳也注意到了标本缓急,若逢气血大耗和病后产后等,法当培养气血,固本为要。但是,张景岳也有其局限,对于肝肾有病、瘀血所致不寐缺乏认识,对治疗不寐时调和阴阳的大法认知不足。在后世的临床上,可借鉴张景岳的“邪正”思想,但也须熟读经典,兼收百家,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