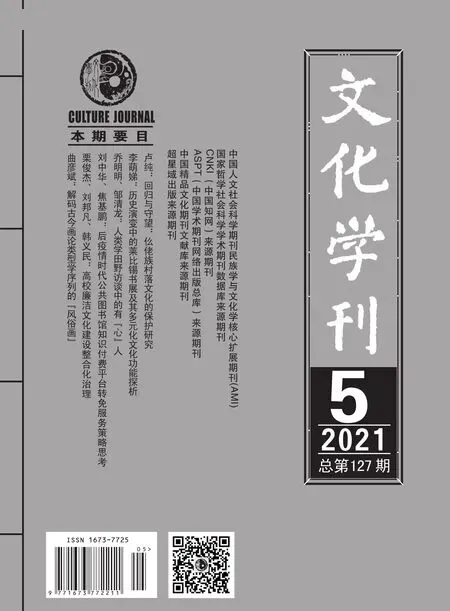“言”能否用来把握“道”?
——以《逍遥游》为中心
党富鹏
在道家哲学体系中,“道”是最根本的范畴,“言”在《庄子》哲学中,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而“道”和“言”之间,从《老子》开始,就蕴含着“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章》)的矛盾;继而到了《庄子》,关于“道”和“言”两对范畴的叙述也大量出现,并被后来研究者归纳为“道”“言”关系、“名”“实”关系、“言”“意”关系等。以《逍遥游》为例,文中较明显地表达出这种对立关系的语句有“圣人无名”“名者实之宾也”,暗含这种对立关系的语句亦有多处。
随着学界研究的深入,以及西方语言哲学思想的影响,针对“道”“言”这对范畴的研究越来越多,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将《庄子》中蕴含的思想同西方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但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言”能否用来把握“道”——似乎没有盖棺定论的答案。有的学者认为,“道”与“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道”的把握依赖于“言”;还有的学者认为,“言”有损于对“道”的把握,如果想接近“道”,就不能依赖语言。本文拟从以下三点对“‘言’是否能够把握‘道’”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第一是论述“道”“言”间的矛盾是什么;第二是论述《庄子》如何从认识和思维的狭隘性否定“言”的作用的;第三是论述《庄子》如何从语言带有的目的性否定“言”的作用的。
一、“道”与“言”的矛盾究竟在何处?
从哲学层面来探究“道”与“言”的矛盾,无法避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道”是什么?《老子》一书中认为:“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章》)也就是说,可以用言辞表达的道就不是常道。庄子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道”的奇妙就在于,它不可以被人的感官把握,甚至很难用理性去思考。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道家思想中,“道”是一种客观实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地万物由“道”而生,万物也效法“道”运行,人也应如此。所以,“道”总的来说,是一个不可被感官把握的客观实在。
第二个问题就是:“言”是什么?“言”就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语言,包括口头诉说形式的语言和书面记录形式的语言。同样是声音,人类的口头语言和动物的叫声的区别就在于,相比于叫声,人类的语言可以更精确地传达其内在含义,而记录在书面的语言则具有延续性。无论是君王贤者之言,还是诸子百家的著作,都属于“言”的范畴。“语言和心灵、精神的关系十分密切。……语言对人的重要性几乎怎么说都不为过,用不着有什么时尚潮流,自古以来,喜欢反省思辨的人鲜有不被人丰富而有趣的语言现象所吸引的。”[1]不过,无论是何种“言”,其表达的都是思维的活动,都是主体性的一种体现。
基于以上两点,引出了一个问题——基于人的主体性的感官和思维,能否准确把握客观存在的、先天而生的“道”?这是“道”“言”关系矛盾中的根本矛盾之一。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认识问题悬置后,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基于人的主体性的语言能否准确客观地描述“道”?这其中蕴含着“道”“言”之间的二律背反:“一方面,道有言说之意,但言说并不是‘道’,因为语言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表达‘道’;另一方面,道必须借助语言进行言说,否则‘道’无法展现自己。”[2]《庄子》中认为我们可以认识“道”,不过是以一种不同于感性和理性的方法认识。若用普通人的方法去认识“道”,最终会沦为“小大之辩”,由此而来的对“道”的解释是不完整的。再者无论人是否准确认识了“道”,基于主体性的语言表达中总是带有个人的目的性,因此对“道”的把握是歪曲的。庄子对语言本身进行了反思,笔者将从《逍遥游》中寻找证据,来佐证《庄子》中的“‘言’无法把握‘道’”。
二、语言中有因认识和思维能力带来的限制
首先,欲对语言所能把握的范围作出界定,就需要对人的认识范围作出界定。《庄子》中有这样一句描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庄子·逍遥游》)“晦朔”和“春秋”是普通人可以认识的,但是对于“朝菌”和“蟪蛄”来说,它们的生命不如普通人来得久,于是无法认识到普通人可以认识到的“日”和“年”的概念。相比“朝菌”“蟪蛄”,普通人的认识范围更广;但是相比“冥灵”“大椿”“彭祖”,普通人的认识范围又狭窄了许多;再与不生不灭的“道”相比,“冥灵”“大椿”“彭祖”的认识范围依然很渺小。因此,普通人的认识范围具有局限性。
其次,我们的认识决定了我们的思维。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则会导致思维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会最终表现在语言上。《庄子》中以肩吾和连叔之间的对比来论证了这个观点。对于接舆说的同一段话,肩吾和连叔两人对其表达的态度不同。肩吾对其的态度是:“大而无当,往而不返。……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庄子·逍遥游》)而连叔的态度却是:“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礡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分分然以物为是。”(《庄子·逍遥游》)肩吾的思维停留在普通人的角度,认为语言应该适当、缄言、符合逻辑、符合世俗;而连叔站在更高的思维水平来看待接舆的话,因此,肩吾和连叔对接舆的评价是不同的。对于同一段文字,处在不同思维层次的人所做的评论都是不同的,那么对于更加奥妙的“道”,不同思维层次的人更会有不同的理解,那么针对“道”而表达出的语言更是不同的。于是,这就会造成对“道”的认识的蒙蔽。对认识不充分的事物做出的表达必然也是片面的。
《庄子》中还有一段描述可以作证以上观点:对于“鹏”来说,“九万里而南为”是正常的,但是对于“蜩与学鸠”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它们无法理解“鹏”的这种行为,于是嘲笑说:“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庄子·逍遥游》)这正是认识的差异导致了思维的差异,并体现在了语言上。反过来看,从片面的语言中,必定无法把握“道”。笔者十分赞同安徽大学汪秀丽的观点:“实际上,庄子的思路贯彻了这么一条路线: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以大知否弃小知,主张弃小知求大知,即知道,而道又是不可知不可言,要不,则‘隐道’‘亏道’,因此大知之道在于不知,即放弃一切认知,而通过内在修性,达到‘无’的逍遥境界,这才是知道的方式。由以大知否弃小知,以无知取代大知,以净性实践无知,这就是庄子不可知论的逻辑脉络。”[3]
但是,学者任立认为:“‘言’指的是‘小知’,即一般的知识,‘一’并不是脱离‘言’而存在的,而是‘言’的集合。如果两者二分会造成无穷划分的谬误,正如古希腊艾利亚学派提出的‘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悖论,可看出‘大知’和‘小知’的关系是:‘大知’是‘小知’的全体,‘小知’之内、之上都无法得到‘大知’的知识。因而庄子认识论中,并不完全否定一般知识论的内容,反而承认了‘道’与一般知识有着紧密联系。”[4]笔者不认同任立的观点。面对这段话,笔者不由得提出一个问题:将“言”集合起来,真的就能把握到“道”了吗?也就是说,“小知”的集合便是“大知”是真的吗?“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的悖论的内在矛盾是逻辑与经验事实的矛盾,而“道”和“言”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这个。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小知”和“大知”之间存在一道“叹息之墙”也不为过。在《逍遥游》中,我们可以试想,所有的“蜩与学鸠”的认识加在一起,是否能够得到“鹏”的认识?所有的“朝菌”“蟪蛄”的认识加在一起,是否能够得到“人”的认识?以上两者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又凭什么可以说,“小知”的集合便是“大知”呢?
三、语言中有因目的性带来的限制
语言作为一种主观的行为产物,往往会主动或被动地带有言说者本人的目的性,而这种含有目的性的表述恰恰会歪曲“道”的本身。在对《庄子》语言哲学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提出了“名实观”的观点。学者吴福友和吴根友认为:“正因为形名制度对于社会、政治而言仅仅是‘末技’,因此圣人之治从根本上就不需要形名这一套东西。所以,庄子对于有形的社会制度采取了一种非常极端而又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否定态度:‘圣人无名。’”[5]笔者十分赞同他们对“名实观”的态度,但是,笔者对“名”的解释角度略有不同。笔者认为,“名”指名誉、地位,亦可以指人的愿望和期待,这正是一种目的性。而“实”为“道”,为人应效法的形而上者,是一种自然而然,不带目的的终极。庄子所处的时代被形容是百家争鸣,百家都期望自己的理论能被当权者采用,以此获得名望,如果百家对真理与至善的探求仅以加官进爵为目的,便落入下乘。从尧和许由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尧的目的在于“天下治”,许由拒绝尧的理由是:“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庄子·逍遥游》)许由将替代尧而治理天下视作“为名”,这其中就包含了对目的性的否定。这种含有目的性的行为被许由贬喻做“鹪鹩巢于深林”“偃鼠饮河”,而许由所追求的境界远高于此。这也正是庄子对出于目的性而做出的行为的一种贬损。
这种带有目的性的心理被庄子称为“有所待者”,这是《庄子》所反对的。《庄子》说:“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庄子·逍遥游》)列子不能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有所待者”——“致福”;同样,宋荣子的入世也是一种“所待者”,因此无法成为“圣人”;更不用谈那些“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庄子·逍遥游》)了。而他们的言语、学说和著作等,都是出于某种目的性,正是因为这些目的性,与“道”的“自然”性相违背,所以这些语言是无法把握“道”的。
但是,这种目的性似乎普通人都有,也似乎是普通人思考问题的习惯思维。在惠子和庄子的对话中,对于“大瓠”,惠子会认为:“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逍遥游》)而庄子的观点却是:“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庄子·逍遥游》)在普通人眼里,“大瓠”这一客观对象需要符合人所给他预设的目的,如果不符合,则会被打上无用的标签。但是庄子反对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目的论,他认为“至人无己”,也就是说“没有偏执的我见;即去除自我中心。”对于“樗”,庄子也是同样的态度。惠子认为:“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逍遥游》)庄子却反驳道:“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庄子·逍遥游》)按照相同的思维模式,普通人对于语言的运用也会习惯性地带有目的性,会主动或被动地考虑自己说的话能否起到应有的影响,能否给自己带来预想的名誉,于是,基于主观的“言”和客观的“道”之间的矛盾便产生了。因此,《庄子·逍遥游》第一部分的最后提到“圣人无名”,没有因期待所累的“游无穷者”,才是效法“道”的圣人;反过来,正因为圣人没有“所待者”,自然就不会利用与自然之道相违背的,基于主观的语言来妄图把握“道”。
四、结语
“言”能否把握“道”这一问题是《庄子》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之一。笔者认为,“言”是无法用来把握“道”的。首先,通过“道”和“言”的概念分析,可以看出“言”“道”之间的矛盾在于“基于人的主体性的感官和思维,能否准确把握客观存在的、先天而生的‘道’”和“基于人的主体性的语言能否准确客观地描述‘道’”;其次,因为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局限,作为主体的人很难完全认识到作为客体的“道”,那么人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道”也总是狭隘的,这体现在《庄子》对“小大之辩”的描述中;再次,人言往往带有目的性,这与“道”的自然性相违背,出于这种目的性而表达出的语言也总是歪曲的,这体现在《庄子》的“名实观”和惠子与庄子的论辩中。
但是在庄子否定语言的作用同时,他同时也著书立说,通过语言的形式为受众阐述自己对“道”的认识。其本人的行为和主张难道不是相悖的吗?既然语言不能把握“道”,那么语言本身可以把握的范围又在那里?超出语言范围之外的内容又应该通过哪些手段可以把握?如果只是通过修行和境界等个人化的方法把握“道”,那么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是否已经把握了“道”呢?这种神秘主义是否也有蒙蔽大众之嫌?
本文基于《庄子·逍遥游》文本来分析问题,而没有基于写作手法——“三言”——来分析问题,这将是笔者接下来的研究方向之一。仅基于《逍遥游》而寻找到的证据在面对“言”“道”问题时,或许略有狭隘,对于《庄子》乃至道家学说对于“道”“言”关系整体态度以及是否能用道家的思想来解决现代语言哲学所面对的问题也是笔者希望能够钻研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