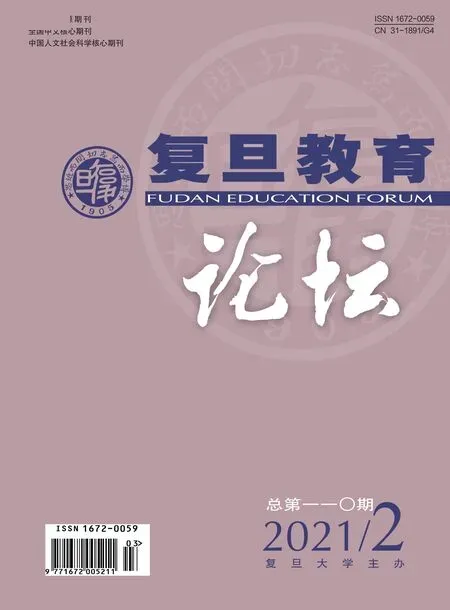德育的学术研究
陆 一
对于我国教育研究来说,“德育”是个高挑战性的命题。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经验化、表面化、学术含量不高的问题。特别是在国家层面的方针政策已经将德育确立为教育工作的首要议题的背景下,在统一规范的政策要求与千变万化的教育实践之间,学术界还没有充分发挥其思想纽带的作用,因为高屋建瓴的政策话语并不等同于学术理论。极富时代特色的德育政策论述如何能够嵌入到可以被学术理论解释的框架之中?
大学是人类社会理性文明的结晶。在高度理性化的现代社会,德育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且有效的?一些经典的西方德育思想或许能够提供富有启发的观察。涂尔干曾做出一套自洽的论述。他认为要从传统中剥离各种宗教仪轨与符号的桎梏,用理性还原他们本来的样子,使道德教育成为合乎理性的教育。由于道德行动具有常规性与权威性,那么养成“纪律”便是实现道德的首要要素。“纪律是作为父亲的社会,对我们发号施令,促使我们尽职尽责;而对群体的依恋是作为母亲的社会,是善的化身,吸引着我们。”在论证了道德权威来源的基础上,自主性也被重点阐明,确切意义上自主的道德行为所指向的不是自我,它必须超出个人之外,指向“大我”,即群体和社会。可见这种自主性不是天然的,而是通过教育养成的。
涂尔干进一步点明,教师是社会的代理人,通过教育教学活动,创造一种社会的、道德的存在。理性化的德育是教师的“任务和光荣”。在做法上,教师不应当权威式地道德说教,而要展示他本人对规范的服从,并且和所有遵守规范者一样受惠于此。唯有如此,才能唤起学生对公共良知的尊重,实现德育的效果。
韦伯的观点则与涂尔干的道德教育学说构成微妙的张力。韦伯同样反对教师在学校里扮演道德权威的角色。“祛魅”使现代人身处于价值选择的自由与困境之中,韦伯因而指出,“只要他是一名正直的教师,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教会他的学生承认‘令人不舒服的’事实”,而这种涉及价值的教育便超出了单纯的“知识成就”,达到了“道德成就”。并且,这种不急于做出价值判断的教育方式最适用于大学,能够培养科学工作者永不停止地追求对事实的充分理解。
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上,道德教育始终没有摆脱理论困境。托克维尔曾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描绘过早期的美国人是多么热衷结社。二战后,美国迎来了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敏锐地洞察到焦虑与漠然是这个时代的主要困境。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独具慧眼地描写了美国人对公共事业热心不再。曾经盛极一时的社群主义和集体生活的吸引力已经消退,日趋衰落的集体情感难以抵制个人之于社会的“离心化”倾向,道德上的麻木在美国社会蔓延。
这些问题并非美国独有,高速发展的科技与飞快成长的经济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构成瓦解道德凝聚力的压力。韦伯或许早已认识到,随着宗教影响力的消退,道德问题退出课堂,那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并不美好,生产一方的专家“没有灵魂”,而享用一方的纵欲者“没有心肝”。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并不以摆脱宗教羁绊为指归,而是发端于对传统思想与文化的重新塑造,以及对现代西方思想的借鉴与消化。虽然中国也面临着现代性的巨大挑战,然而“立德树人”是我们古今一致的教育信仰,需要不断更新的是其具体内涵。构建德育理论既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也是一项崭新的挑战:用当代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再造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之间的联结,为翻开中国教育的新一页提供核心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