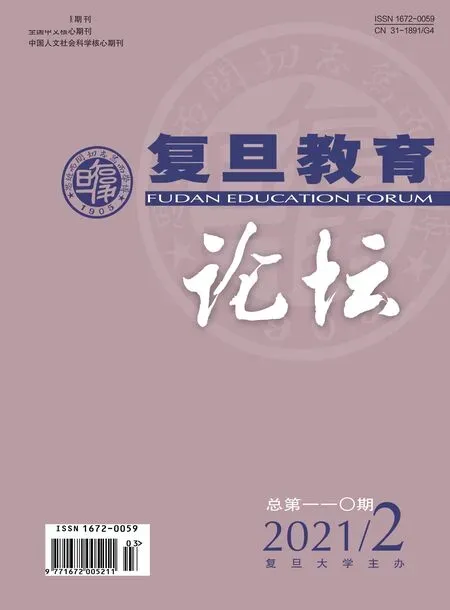批判性思维量表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与展望
崔丽媛,朱亚鑫,曲 波
(1.中国医科大学国际医学教育研究院,辽宁沈阳 110122;2.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辽宁沈阳 110122)
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一词最早起源于哲学,也被译为“审辩式思维”或“评判性思维”等[1]。根据美国批判性思维国家高层理事会主席理查德·保罗(Richard Paul)的定义,“批判性思维是建立在良好判断的基础上,使用恰当的评估标准对事物的真实价值进行判断与思考”[2]。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3]。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创新的基础与前提,对培养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和认知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4]。美国教育机构一直积极倡导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美国高校联盟、美国教育研究院、美国教育目标小组共同提出在K-12、大学教育、STEM 教育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5]。目前,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评估结果被许多国家作为入学考试、入职考试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学科,对临床操作技能及批判性思维能力要求较高,它比一般的自然科学具有更高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学者乔纳森·夏帕(Jonathan M.Sharples)在《英国医学杂志》(The BMJ)发文表示,批判性思维是医生的必需技能,是基础医疗及医学教育实践的关键技能[6]。在临床环境下,医生需要面对不同问题及复杂的临床情况,如临床决策、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医院资源不足、人际冲突等,这时需要突破常规性思维,以批判性思维进行思考,以获得新的医学发现和医学经验。国际医学教育组织(IIME)、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等先后明确提出将培养医学生批判性思维作为教育目标,批判性思维评价成为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重要指标[7]。2019年6月第39届批判性思维国际研讨年会在比利时召开,会议强调在各行业中使用批判性思维测量工具解决问题及制定决策[8]。批判性思维测量工具有利于检验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效果,使教师有针对性地设置教学重点;有利于衡量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水平,激励学生主动学习。目前,国内外批判性思维的测评工具有20余种,常用的批判性思维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条目式评定法、情景选择式评定法、开放式评定法、混合式评定法[9]。我国关于医学生批判性思维量表的研究起步较晚,采用的评价工具比较有限,少数自主研发的工具不够成熟,适用性有待验证。本文对批判性思维工具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与整理,旨在为我国医学教育中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测量与评估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条目式量表开发现状及应用
条目式评定法采用李克特等级量表测量多维度的复杂概念或态度。被试者在15~30分钟内对量表中每个条目做出单项选择,快速量化受试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由于可操作性强,条目式评定法成为被普遍采用的一种评估方式。常用的条目式量表包括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测试(The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CCTDI)、批判性思维诊断测试(The Critical Thinking Diagnostic,CTD)、中文版批判性思维倾向测试(The Chinese Vers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CTDI-CV)、尹氏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The Yoon's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strument,YCTD)等。
(一)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测试(CCTDI)
1994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护理研究者诺琳·费希万(Noreen C.Facione)博士以美国哲学学会形成的批判性思维理论为基础开发CCTDI量表。CCTDI作为检测批判性思维情感与态度的测量工具,受试人群为普通群体及大学生。量表共计7 个维度、75 个条目,7 个维度分别为寻求真理、思想开放、分析、系统、自信、好问与成熟。CCTDI量表的克朗巴哈α 系数为0.90,量表效度较好。该量表已形成多语种版本,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10]。
CCTDI 常与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The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est,CCTST)及医学科学推理测试(The Health Sciences Reasoning Test,HSRT)联合测量学生的学业成绩及学习成果与批判性思维的相关性。美国的多项调查结果显示,批判性思维技能与倾向与药剂学博士生、口腔本科生、护理专业本科生的学业成绩相关,同时与美国执业医师考试(USMLE)的临床知识部分、美国注册护士考试(NCLEX-RN)的分数具有关联性[11]。
(二)批判性思维诊断测试(CTD)
2009 年,美国护理行政中心研究人员开发了CTD 量表,其目的是便于美国护理机构管理者测量护理人员的批判性思维水平,评估护士是否有能力成为批判性思考者。量表共计5 个维度、25 个条目,5 个维度分别是问题识别、临床决策、优先权、临床应用及反思。CTD 量表的克朗巴哈α 系数为0.97。CTD 作为美国护理专业咨询委员会指定的批判性思维评估工具,常用于评估及检验护士工作的有效性及劳动成果[12]。
CTD 主要应用于美国护士群体的批判性思维情况评估。由于美国护理机构管理者很难确定一线护士所需要提高的具体能力,采用CTD 可评估离散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便于管理层为个体提供有针对性的、自我导向的发展机会,以提高护士群体的批判性思维水平[13]。CTD 可以实现在线评估,管理者可以在报告页面查看护士个体、团队的评估结果。根据实际情况,CTD也可以采取纸质方式填写。
(三)中文版批判性思维倾向测试(CTDI-CV)
我国香港理工大学彭美慈教授领衔开发了CTDICV量表,以便更加客观地评估中国护理课程的设置与教学方法。量表共计7 个维度、70 个条目,7 个维度分别是寻找真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自信心、求知欲与认知成熟度。CTDI-CV量表的克朗巴哈α系数为0.90,内部一致性较高[14]。
CTDI-CV 多与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PBL)、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CBL)、概念地图等教学方式相关,常作为批判性思维量表的校标关联效度测量工具。我国学者广泛采用此量表测量中国护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水平,科学系统衡量我国高等教育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情况并检验学习成果。杭州师范大学的洪少华采用CTDI-CV 测量中国护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水平时发现,延展式案例教学促进了护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发展[15]。
(四)尹氏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YCTD)
韩国学者尹珍(Yoon J)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形成初始量表,后经修改检验形成正式的YCTD 量表。量表共计5 个维度、27 个条目,5 个维度分别为客观性、审慎、系统性、求知欲、智力公平性、健康的存疑态度、批判性思维自信心。受试者得分越高代表批判性思维倾向越强。该量表的克朗巴哈α系数为0.84[16]。
在测量韩国大学生群体的批判性思维倾向水平时,多采用YCTD 量表。基于尹珍的原始量表,又衍生出两种量表,分别是YCTD 与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The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Questionnaire,CTDQ)。在一项YCTD验证性研究中,研究者调查了3所不同韩国大学的345 名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倾向情况,发现在护理教学中模拟仿真课件的应用可能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的审慎方面产生积极影响[16]。
二、情景选择式量表开发现状及应用
情景选择式评定法是指受试者在一段叙述性描述的语句下,根据自己的理解,在4~5个备选答案之中选择1项。在批判性思维测评中,情景分为两种:一是适用于普通人群的通用情景,另一种是具有医学背景的专业情景。常用的评估量表主要包括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CCTST)、医学科学推理测试(HSRT)、沃森-格拉泽批判性思维评价(The Watson-Glaser Critical Thinking Appraisal,WGCTA)等。
(一)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CCTST)
1992 年,CCTST 量表由美国诺琳·费希万(Noreen C.Facione)博士开发,采用通用情景测量成人及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水平。量表内容趋于中性,不受学科、性别、专业和文化背景的限制。CCTST 量表的单项选择方式在结构和形式层面保证测试的效度。量表共计5 个维度、34 道选择题,5 个维度分别是阐明、分析、推论、评价、解析和自我调节。CCTST 量表的克朗巴哈α系数为0.87,在国际上得到较广泛应用。
CCTST 多与课程评价相关,研究人员采用概念图、反思写作来衡量CCTST 的准则效度。费列什泰赫·埃恩(Fereshteh Aein)采用CCTST 测量护理学生在概念图教学方法的前后分数。研究显示,概念图作为一项教学活动,促进了护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发展[17]。奈伯·杰西卡(Naber Jessica)的研究采用CCTDI 与CCTST 联合测量护理本科生的反思写作水平,发现反思写作对批判性思维有促进作用[18]。
(二)医学科学推理测试(HSRT)
2007 年,美国诺琳·费希万(Noreen C.Facione)博士基于CCTST 量表开发适用于测量健康科学专业学生及相关人员的批判性思维及临床推理技能的HSRT量表。受试者根据专业的医学情景描述选择答案。量表共计5 个维度、33 道单项选择题,5 个维度为分析、推理、解释、归纳、演绎。HSRT 量表的克朗巴哈α系数为0.81,总体可靠性系数为0.81[19]。
HSRT 多用于测量医学领域科研人员及健康科学专业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水平及临床推理能力。澳大利亚的一项横断面研究,调查了269 名护理专业本科生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发现批判性思维水平与年级正相关[20]。然而,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调查接受过PBL 教学的144名口腔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水平,采用HSRT 进行测评后发现,接受PBL 教学的学生批判性思维与年龄无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21]。
(三)沃森-格拉泽批判性思维评价(WGCTA)
1980 年,沃森·古德温(Watson Goodwin)与格拉泽·爱德华(Glaser Edward)联合开发WGCTA批判性思维评估量表,测量九年级以上群体的批判性思维技能程度。量表共计80 道题,1~16 题采用李克特5 点量表,17~80 题为判断对错题。共计5 个维度,分别为推理、辨认假设、演绎、解释、论据评估能力,属于自评式量表。
有国外文献报道WGCTA 量表的分半信度系数为0.69~0.85,我国学者研究表明其分半信度系数为0.54,未达到通常有意义的信度系数值0.70[22]。伊朗的一项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WGCTA量表测量了125名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水平,发现批判性思维水平与性别、居住地及年级相关[23]。
三、开放式量表开发现状及应用
开放式评定法是指受试者在开放性的语境下,自己组织语言回答问题。由接受过专业培训的计分人员对受试者答案赋予相应分数。
(一)批判性思维评估测试(CAT)
美国科学基金会为批判性思维评估测试(The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 Test,CAT)量表的开发提供资金支持,由美国田纳西科技大学负责研发,旨在采用通用的问题情景测量普通人群的批判性思维水平。量表共15 道开放式问题,测量4 个维度,分别为信息的评价与解释、解决问题、创造性思维、有效的沟通。由接受过专业培训的计分人员对受试者答案赋予1~5 分[24]。在美国已有超过50 所机构使用CAT 量表测量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水平。美国伯明翰南方学院的一项调查,采用CAT 测量翻转课堂开展前后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水平情况,发现翻转课堂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水平[25]。学者卡森·苏珊(Carson Susan)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采用CAT调查本科生课程,发现参与情景活动的学生在撰写研究论文时表现出更高的批判性思维水平[26]。
(二)恩尼斯-威尔批判性思维写作测试(EWCTET)
1985 年,学者恩尼斯·罗伯特(Ennis Robert)与威尔·埃里克(Weir Eric)共同开发了恩尼斯-威尔批判性思维写作测试(The Ennis-Weir Critical Thinking Essay Test,EWCTET)量表,旨在通过写作方式测量高中及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1988 年及2005 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的恩尼斯·罗伯特对量表进行了两次数据补充。该测试要求受试者根据一个场景,写出8 段评价文字及1段总体评价。受试者需要在每段文字中阐述自己评价的理由,评分者根据标准对每一段文字评分,由评分员对8段文字分别赋予-1到3分,同时根据回答的总体评估情况一次性赋予-1到5分[27]。假设某受试者的8 段文字均被赋予-1 分,总体评估为-1分,即某受试者的总分为-1×8+(-1)=-9 分。因此EWCTET 的总分为各段文字得分、总体评估得分之和,总分范围为-9~29 分[28]。EWCTET 量表的内容相关度较高,在通用情况下情景的有效性及信度较高,以检查学生发现设置在场景中的推理缺陷以及辩护个人论点的能力。但有研究表明,EWCTET 高度具体的情景与严格的结构限制了受试者的作答,可能无法显示受试者的批判性思维倾向。评分者主观的评分过程可能会影响分数的客观性,同时受试者写作能力强弱可能会使测试结果产生偏倚。
四、混合式量表开发现状及应用
条目式评定法、情景选择式评定法、开放式评定在测量批判性思维时,各具优势,但同时存在局限性。2010年,学者哈尔彭·黛安(Halpern Diane)结合开放式及情景选择式评定法,开发了哈尔彭批判性思维测评(The Halpern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HCTA)量表。该量表共计5个维度,分别是论证分析技能、语言推理技能、假设检验技能、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判断技能、决策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25 道开放问题和25 道情景选择题。被试者围绕健康、教育、工作等日常生活情景回答开放式问题,随后回答相关的选择题。由3 名接受专业培训的计分人员,根据受试者的相关文字描述赋予0~2 分[29]。HCTA 量表的克朗巴哈α 系数为0.79,量表效度良好。努恩·克里斯(Noone-Chris)的研究采用五因素正念问卷与HCTA 联合测量178 名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情况,发现正念促进了批判性思维的发展[30]。
条目式、情景选择式、开放式及混合式评定法的批判性思维量表均可测量受试者批判性思维水平,但在其内部结构、适用人群、评分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详见表1。
五、我国批判性思维量表应用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批判性思维量表研究中存在中国文化元素缺失、特异性学科量表有待开发以及量表不能覆盖教育的全周期全过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国批判性思维测量仍是以西方国家成熟的经验、模式、量表体系或结构为主,本土化的改造不足,缺乏本土文化的融合。由于多数批判性思维量表是在单一的西方文化背景下开发的,我国在引进与修订国外批判性思维评价量表过程中,其隐含的理论与文化之根仍然属于他国。西方文化核心要素是个体实现的物质有偿文化,强调精致的利己主义。然而,东方文化的核心要素为集体的道德观念和奉献精神,注重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因此,以西方文化为基础开发的批判性思维量表,缺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中国文化元素的话语表达。有研究表明,在以中国人群为样本的批判性思维调查中,条目式量表CCTDI 的内部一致性较低,通常在语义和概念之间表现出较少的平等性、公平性和差异性,心理计量学指标评价结果较差,不适用于中国人群的批判性思维测量,为使用者带来一定程度的困扰[31]。因此,西方批判性思维量表的某些条目、维度在引入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中国文化元素的融入,对量表相关内容进行替代或修改。

表1 批判性思维量表的特点及量表间差异
第二,造成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学科特异性的批判性思维测评工具。目前,缺少适用于医学专业背景的特异性批判性思维评估工具。通用型批判性思维评价工具,如CCTDI、CCTST、WGCTA的测量群体为普通人群,不能充分反映医学学科的特殊性。社会的进步对医生的职业要求逐渐提高,不仅要求熟练掌握临床知识和操作技能,还要求运用批判性思维解决临床问题。现有的普适性批判性思维量表,一方面忽视了医学生构建自己学习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需要根据学科特点对低负荷项目及条目数量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在普适性批判性思维的开放式评估工具中,特定的上下文与严格的写作结构,无法评价医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的批判性思维水平[32]。
第三,我国医学院校开展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大体系”和“小逻辑”仍不健全。“大体系”方面的缺失在于,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高等医学教育、继续医学教育等教育全周期全过程中缺乏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小逻辑”的失衡主要在于阶段性、穿插在课程体系中的院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知识连贯一致性的需求。目前,我国的批判性思维培养多采取单独设置一门综合性思维训练课程的方式,存在批判性思维培养缺失、知识点不健全等问题。
六、批判性思维量表的本土化开发与应用
第一,为解决批判性思维量表测量时的不足,未来批判性思维测评需要以中国文化和国情为基础。中西方批判性思维的表现形式差异,并不是有无批判性思维的差异,而是批判性思维技能和倾向如何在不同地方由不同文化的群体表现出来。美国哲学协会认为,批判性思维人格倾向包含寻求真理、开放性、系统性、自信心、好奇心、认知成熟度等方面。东方批判性思维的某些特征可以防止或弥补西方批判性思维以逻辑和论证分析为核心的不足,主要包括社会和谐、人文关怀、理解先于批判、不伤感情且温和有礼[33]。我国批判性思维量表的开发可结合西方研究基础和中国文化背景,求同存异,去伪存真。对于隶属不同国籍、文化背景的人,人们更容易形成负面意见,这是圈内偏见(in-group bias)的一种表现,可能扭曲和误导我们的认知和判断。对西方文化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国文化的人生态度、处事哲学、思维方式、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和伦理共识,诠释批判性思维内涵。我国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教育中,应批判性地借鉴国际经验,引进与修订国外成熟的批判性思维评价工具。将国外成熟的批判性思维评价工具引进与修订需要根据WHO 的量表翻译与调适的流程进行跨文化调试,即前译、专家小组讨论、回译、预测试和认知访谈与最终定版[34]。在跨文化调试过程中结合我国文化元素,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批判性思维量表,以便更好地衡量我国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水平。
第二,批判性思维特异性量表的开发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潜力。批判性思维培养是学生构建和解构论证的过程,包括培养医学生的推理能力和识别事物的能力,关注问题的优先次序,超越表面化的记忆,进行深度学习,重新评估自己思考和学习水平,分析跨学科、跨领域、不同专业的批判性思维模型的差异等。当前,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开展新医科视角下的医学生批判性思维现状和问题调研分析;同时,结合国内外文献以及对学生、教师、临床专家的深度访谈,建立初步的医学生批判性思维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最终形成我国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评价体系。在我国开展医学生学习成果评估,提倡采用多元化的评价工具。进一步探索情景化、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医学生批判性思维评估工具,满足新医科、卓越医生2.0、健康中国的医学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第三,加强批判性思维的全过程评价,并为医学人才的全周期培养提供连贯的、持续的保障。全过程是指人的发展全过程,在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医学教育、继续医学教育阶段,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呈现不同的特点。在不同教育阶段采用的批判性思维量表应有所区别,在保持一些共性的条目内容基础上,要随着教育程度的加深,逐渐加入特性条目。在批判性思维量表开发过程中,结合生理、心智情况,包括记忆水平、认知水平,设计不同阶段的量表,使批判性思维量表符合人的身心发展规律,以便持续跟踪与反馈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水平。同时,开展全周期的医学生批判性思维教育,能够优化医学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素质结构,为医学院校本科教育、毕业后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等不同阶段的医学教育批判性思维评价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