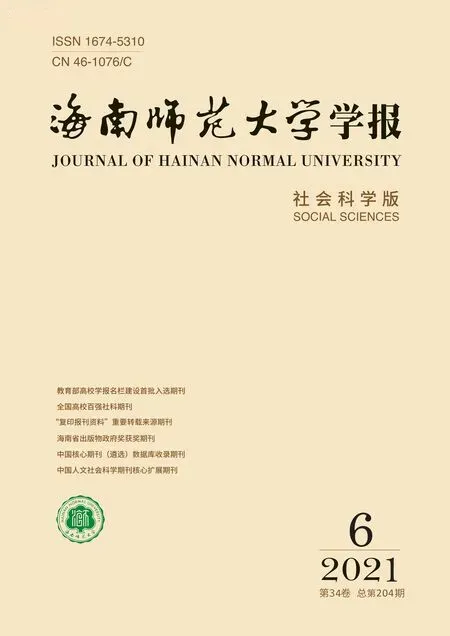符号的建构与文学的真实
——丁玲延安时期的形象塑造
杜 睿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陕西 西安 710065)
从“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丁玲的形象经历了较大变化,而这一变化的转折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女作家之一,丁玲的形象应当和她的作品一样受到关注。丁玲形象的变迁与她创作的转变息息相关,从《梦珂》被大众熟知开始,丁玲的形象就处于不断变化且在自我和他我之间共同建构的过程中。进入延安之前的丁玲是在寻找自我身份的认同,即在作品中主动改变自己单一的形象,这一点从丁玲在左翼时期主动改变自己的创作并实时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女作家便可看出。到延安之后的丁玲,身份的塑造则不仅仅是主动地转变,更带有客体(1)这里的“客体”是指带有政治色彩的媒介话语,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宣介。延安对于丁玲而言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集体”中的一员,其身份不再单属于自己,而是与延安时期整个文化建设、抗战宣传有密切关系,她的形象也从主动改变到被动建构,实现了质的改变。
英国媒介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提出:“媒介是表意的工具。”媒介通过表意过程建构现实,制定‘情境的意义’,给受众提供一个世界的图景。”(2)刘建明:《西方媒介批评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4页。这里的“意”即指“意识形态”。媒介作为“生产者”,通过表意过程建构现实,制定“形势的定义”,给观众(听众)提供一个建构了的世界的图景。媒介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通过框架、文本和语言等形式塑造出来的“符号真实”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弦外之音,而这种声音也正是影响媒介建构现实的“意识形态”。与真实相比,符号则是被建构了的“真实”,这里的“真实”可以是文学的真实,也可以是想象的真实,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认为国家权力的实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强制性和镇压性国家机器,如政府、警察、监狱等;另一种则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宗教、教育、传媒、文化等形式通过媒介的传播达到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信息媒介传递。而媒介传播带来的意识形态的认定和形成往往具有更大的效力,人们会不自觉地在媒介传播过程中形成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从而把心理的真实认定为社会的真实。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处于战乱的特殊环境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当时主要的话语喉舌掌握在具有话语主导权的国民党手中,中共的话语建构实际上是从江西苏区转移到陕北之后才逐渐开始的。1935年10月,从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吴起镇开始,延安就开启了自塑和他塑的过程,直至1937年1月,中共从保安县迁到延安城,延安在各个方面都要重新建立。延安初期,除了对内的全面改革,争取苏区的发展,对外则要争取一切力量,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援助。自然条件的先天不足,环境的闭塞与恶劣,仅仅依靠当地百姓无法实现延安的全面“翻身”,延安形象“合法化”的重要依据,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和抗战宣传、形象重塑、话语建构都需要大量的人才,通过广泛吸引人才达到为“革命”所用之目的成为当时中共的一项重要任务,无论是毛泽东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还是《解放日报》头版刊登的社论《救救大后方的青年》(《解放日报》1941年6月8日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解放日报》1941年6月10日社论),都可看出中共对人才的态度和决心。但是这其中应当被重点说明的是,被延安大量吸引的“人才”和“五四”时期自由发展的人才是有本质区别的。延安时期的“人才”是为“我”(延安)所用,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是来“做事情的”(3)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谈到,三年以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发展了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大的成绩。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拚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8页。。为了帮助中共在革命工作和社会建设中取得胜利,也为了中共落脚延安以后的形象塑造,这一时期的“人才”不再与“五四”时期带有启蒙色彩的知识分子划等号。这些人才也在随后的中共文化建设中被重塑、改造,其中就包括第一个来延安的女作家——丁玲(4)作为当时已经名声大噪且不为国民党威逼利诱的女共产党员,同时又是第一个不畏艰险奔赴延安的革命女作家,她对延安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一个“作家”的身份,而是对延安有正面形象的“女共产党员”形象。。
丁玲作为20世纪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从20世纪初崭露头角成为一个“一出台就挂头牌”的青年女作家,到延安时期革命作家身份,再到“女作家”“女革命家”“女领导”的多重身份,最终成为延安时期文化界的一个重要名片。这一时期的“丁玲”从单纯的个人身份,逐渐被符号化,成为一个抽象的“丁玲”,而这一抽象的“丁玲”又在不断地影响着作为个人的丁玲,构成了丁玲在延安时期复杂的存在,在这一复杂存在中既有丁玲自身的矛盾性,也有作为文化人的丁玲与中共党内关系的复杂性。正如鲁迅在延安时期作为一个被塑造、包装甚至夸大的“符号”一样,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形象同样在“符号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之间不断被建构,丁玲的女作家身份逐步被共产党女领导的身份所遮蔽,她不为国民党威逼利诱所动毅然决然奔赴延安的特殊身份,成为最合规的文学人物,在延安不断被演变、重构,直至“中共妇女的领袖、共产党女巨头、中共诸女角”的文学符号,从个人身份逐渐演变为一个文化的名片、公众的符号。当我们再回到延安时期,从本我的“丁玲”到符号“丁玲”之间的关系与演变去观照,正是我们对延安文艺一个侧面的释读与思考。
一、从自我到他我:丁玲延安初期的形象生成
作家在文学的世界里建构人物,而作家本身也在媒介的世界中被建构。丁玲早期的文学形象是建立在其文学作品之上的,早在 1927 年她就已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最早发表在《小说月报》头条的是处女作《梦珂》,之后《莎菲女士的日记》,都藏着她丰富的情感和个性,同时也带有“五四”性别解放的时代烙印。因为契合时代特征又有独到的写作手法,从《梦珂》开始的四篇小说(5)这四篇小说分别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都是《小说月报》头条,有朋友笑称说:“我们都是背棍打旗出身,你是一出台就挂头牌,比我们运气好多了。”(6)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60页。注重性别解放的“五四”把丁玲推到了文坛中心,同时“莎菲”也成就了她在文坛上的一席之地,当时的丁玲还处于性别写作的“五四”之风中,有媒介评价其为“中国枯燥的文坛上的一颗异星:她的造句新颖,结构别致,风格特殊;她在脱不尽中古世纪风味习惯的新中国,在一切解放都不彻底的今日,在有名无实处被压迫限制的现在政府之下,给新中国的文艺前途带来了希望”(7)穆修:《坐有女作家交椅的丁玲女士及其作品》,《燕京月刊》1931年8月2日,第143-153页。。但这一时期的丁玲内心已经想要改变,并急于寻求自己的革命诉求。于是,她的小说创作很快转向了《水》《田家冲》这类带有明显革命气息和底层写作的风格。她在寻求革命之路时,革命也选择了她,因此,丁玲加入“左联”,成为中共的同路人,而丈夫胡也频的牺牲则成为丁玲与中共建立关系的契机。1931年2月7日,胡也频被捕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柔石、殷夫、李伟森、冯铿等四人。作为事业上的同志和生活上的伴侣,胡也频的突然被捕牺牲,对丁玲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她失去了精神支撑,即她之前从胡也频那里得到的精神信仰,现在需要她自己去重建。丁玲在胡也频牺牲后,迅速从中共的同路人转变为共产党中的一员,投身到了革命事业中,国民党对其实施的三年逮捕和幽禁更使丁玲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这一时期的丁玲是主动朝着中共党员的方向迈进,并自觉让自己成为一名革命作家,从母辈(母亲于曼贞和九姨向警予)和友人(来自瞿秋白的精神引导)那里所汲取的革命意识以及潜藏着的革命思想,在胡也频牺牲之后被激发,带着胡也频的遗志和满腔的愤怒成为共产党的一份子。她在主动改变和努力靠近中完成了角色转变,而这一转变也让她与延安更进一步,即在随后的延安时期,丁玲的形象塑造是一种双向选择。她选择了延安,成为首位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作家,延安同时也选择了她。
初到延安时的丁玲,其身份仍然是“负有盛名的女作家”(8)参见沈从文:《记丁玲》,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张惟夫:《关于丁玲女士》,立达书局,1933年。(在上海被捕后的三年,丁玲已经成为一个左翼女作家,但她的身份首先仍是一个作家,而非革命者),但丁玲很快就开始了在延安时期的塑造过程,即身份转变过程。一方面,是延安对丁玲的重新塑造,让她彻底融入到“集体”中,成为一个有“政治身份”的中共女作家。延安成为丁玲人生的转折期,同样也成为中共在“人才”上的一个突破口,丁玲对于延安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1936年7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保安(今延安志丹县),仅仅过了几个月,11月11日丁玲到达保安,成为第一个历经千难万险从国统区主动奔赴延安(保安)的著名作家。更重要的是,她是刚从国民党威逼利诱下挣脱出来、毅然奔赴延安的著名文人。丁玲被国民党逮捕软禁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期间不仅有中共高层的抗议、营救,还有鲁迅等党外著名人士的呼吁、谴责。因此,这样一位作家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决然地奔赴延安,本身就具有了非常特殊的意义和正面价值。到达延安之后的半个月,丁玲在11月24日便请缨去上前线,这在整个延安知识分子中是少有的。丁玲的特殊遭遇和选择不仅成为中共对外宣传的正面形象,还受到了同为湖南老乡的毛泽东的赏识和抬爱。在丁玲还在前线时,毛泽东亲自题词并发电报给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女作家题词。而这首著名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也成为丁玲延安符号化建构过程的开始。可以想见,在此之后丁玲的身份就不再是以她个人而出现,而是代表中共对外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
反观这一时期丁玲的行动轨迹,其实和她被建构的形象是相契合的。丁玲在初入延安时以满腔热血想要马上融入到革命中,进入延安之后其没有即刻投入到写作之中,而是开始了“女战士”的生活。在丁玲到达延安之后两个月即随军到前线,在这一过程中,她虽然创作了一些作品,但都不算是“主业”,而主要是深入前线,了解抗战最真实的情况。她在前线结识了一批红军将领,搜集了许多抗战素材,同时也在军队中和其他战士一样的生活。之后,丁玲随同史沫特莱回到延安,不久又再一次深入到军队中去,希望 “能真实了解红军的内在生活”(9)L. Insun(朱正明):《丁玲在陕北》,《女战士丁玲》,每日译报出版社,1938年,第34页。。在毛泽东的引荐下,丁玲担任了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短短几个月时间,从著名女作家转变为“女战士”“带有头衔的女领导”,丁玲的身份发生了“质”的转变。这一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是延安通过建构文人形象而达到对自身形象的建构,对丁玲形象初期何以成功塑造呢?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党的领导人对丁玲的首肯。1936年底,丁玲还在前线时,毛泽东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发电报到前线: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不仅是党的领导人对丁玲身份的认定,也是外界对丁玲身份评价的重要参照。贺龙在定边前线欢迎丁玲时说道:“几百年的老地主家里出了一个革命作家,不容易啊。”(10)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第160页。另一方面是媒体对丁玲的宣传和报道。当时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还很少,所以丁玲的独特出场自然引起了媒介的关注,她从国民党软禁中逃离出来也成为媒介关注的重点。比如在1937年《抗日画报》上就报道:“投笔从戎之左翼女作家丁玲女士”(11)《国共合作之感言:投笔从戎之左翼作家丁玲女士》,《抗日画报》1937年9月10日。。斯诺在《活的中国》中说她和茅盾是“新写实运动突然崛起的领导人”(12)李向东 、王增如:《丁玲传》上,第170页。。
担任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一职仅一个月,她就因难以融入到红军战士的生活而辞职。辞职以后一心想要投入到写作中的丁玲,又因抗战需要成立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并担任领导。1937—1938年间,丁玲是西战团的领导者和主要参与者。她为西战团创作的剧本《重逢》《河内一郎》都是因抗战需要而作,而非她自己的沉淀之作。丁玲当时的主要身份俨然从女作家转变为女战士、女领导、女英雄。毛泽东在1937年8月15日欢送西战团出发前线的晚会上说道:“战地服务团随红军出发前方工作,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仗,我们要从文的方面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长此覆亡下去。”(13)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26页。丁玲也回答道:“我们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虽小,但是它好像小河流一样慢慢流入大河,聚汇着若干河的水,变成了一个洪流,我们誓死要打退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诸位见面。”(14)姚喜平:《丁玲与西北战地服务团》,《湘潮·上半月》2011年6月。中共最高领导人对西战团给予了很高的期望,这不仅是因为西战团在宣传方面的重要性,还在于丁玲作为西战团的领导深受毛泽东的赏识。而丁玲的回答则富有深意,虽然毛泽东要求西战团以笔杆子为武器到前线去,但“誓死打退日寇”的豪言从一个女作家口中说出,仍是相当不寻常。这也从侧面证明在延安初期作家所承担的任务已经不仅是写作。此时的丁玲被委以重任,其形象塑造得以初显。很快,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媒介就开始了报道,《中华(上海)》在丁玲的照片下配写的是“中国战时女英雄:第一流女作家,现在是西北战地的第一线女战士”(15)赵定明:《中国战时女英雄:第一流女作家丁玲,現在是西北战地的第一线女战士》,《中华(上海)》1940年第85期,第26页。的标题;在《展望》的报道中,标题则用了“战时新女性:领导西北战地青年服务团活跃于陕北之女作家丁玲”(16)《战时新女性:领导西北战地青年服务团活跃于陕北之女作家丁玲》,《展望》1939年1期,第8页。。1938年出版的《女战士丁玲》给予丁玲 “新中国的先驱者”这一高度评价,并称其为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转变,“中国女性的英雄主义”(丁玲到达延安后,其笔锋重新活跃了起来,她更希望中国各党、各派的联合阵线能给她以权利去重新发表她的小说和论著……在这个大学里的许多女学生以及其他在红军中的少女,当她们在软弱和寂寞的时候就来看丁玲,希望从她的帮助和领导之下获得新的灵感和新的希望)。(17)Earl H. Leaf:《丁玲——新中国的先驱者》,《女战士丁玲》,《每日译报丛书》,1938年,第20页。这些加诸在其中的身份俨然已经成为女性之希望,也成为中共吸引更多女性前来的重要动因。
《上海妇女》1939年第2卷第8期中有“女作家印象记——女战士丁玲”的报道,把丁玲称之为“说话很勇敢,敢说别的女人们不敢而不愿意说的话”(18)开露:《女作家印象记——女战士丁玲》, 《上海妇女》第2卷第8期,1939年2月5日,第27页。的女战士。《妇女生活》多次进行“丁玲在延安”(19)海燕:《丁玲去延安》,《妇女生活》第4卷第9期,1938年,第5页。“丁玲在前线”(20)徐盈:《丁玲在前线》,《妇女生活》第5卷第6期,1938年,第31页。的报道,以及出版书籍《民族女战士丁玲传》《丁玲在西北》《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等,几乎无一例外对丁玲投笔从戎进行了赞赏和歌颂。
从1936年11月至1938年11月,丁玲的形象已经从“著名女作家”转变为“女战士”,而后又成为“女英雄”和“女领导”,并逐渐在中共文化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一身份认同并非完全是丁玲主动而为,其中很大因素来自中共对丁玲的塑造以及其后媒介对丁玲的报道。丁玲在逐渐接近革命和政治的过程中,深感自己并不适合,她还是想要一心从事写作。丁玲在前线时并不十分适应,她与战士之间实际上是存在巨大鸿沟的,她后来回忆道:“毛主席说,我看你呀,还是习惯和知识分子一起,他们喜欢你,你也喜欢他们,你们处得很好。当战士嘛,和你还有距离,你们还不能打成一片。”(21)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第166页。由于长期在大城市生活的经历和知识分子的特征,让丁玲很难真正融入到红军战士的生活当中,她曾向萧军抱怨在前线时常常感觉到冷漠。多年后,她回忆起这段历史,仍有不满,“她随军行走……给她一个十几岁的小鬼,跛脚马,她只好和小鬼们步行三十里路,她的脚出泡了。夜间宿营,并没有人照顾她,常常是睡在没有门的马房里,没有警戒的对面山头。但是她忍受着,不乐意向谁去诉苦……”(22)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第166页。担任西战团领导期间,丁玲也深感自己无法安心写作。和被建构起来的高大形象不同,丁玲本身仍是一个爱思考、很感性、健谈和思想单纯的女作家。虽然丁玲极力克制甚至弱化作为女性的敏感,但在骨子里其仍然是一个带着强烈启蒙意识的知识女性,也不太懂得政治上的“权谋”和“眼光”。萧军在《延安日记》中曾多次谈到丁玲是一个非常率真、情绪非常敏感的人。丁玲本人也多次表示自己并不喜欢担任太多职务,想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写作上。应该说,这一时期丁玲的女英雄形象塑造必然要和她不畏生死、脱离国民党魔爪奔赴延安相一致,即使在其中她作为真实的“本我”和媒介建构的“他我”之间有出入。
按照阿尔都塞关于“压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已经不是某种既定的社会结构的后续反映,它伴随着建构社会秩序的全过程,而参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则是媒介。因此,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一方面通过压制性国家机器,使用武器进行对抗;另一方面则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使用媒介进行宣传。而对于文人形象的建构,恰好是一种文化策略。延安时期,从鲁迅被推崇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便可看出其意识形态作为战时的喉舌意义非同小可,而丁玲的特殊性在于,她是一个毅然选择中共的知名女作家,在她身上具备了“知名度+革命信仰”两个重要因素,同时作为毛泽东、贺龙等多位领导人的老乡,丁玲的形象塑造的意义更具有政治性因素。因此,在1938年之前的两年时间,丁玲一步步被政治塑造,又被媒介推上“神坛”,朝着“符号”化形象迈进。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一个情形:这一时期的丁玲的个人经历与“符号的丁玲”两者基本上是相契合的,延安初期的丁玲带着“七月的延安太好了。青春的心/燃烧着。”(23)丁玲:《七月的延安(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于延安)》,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6-327页。的热情,无论是从行动上还是文字上,都是支持延安、歌颂光明的,内心的隐忍相对较小。因此,初入延安的丁玲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备受尊崇的日子。
二、被动调整:合规的形象建构
1938年之后,许多知识分子陆续到达延安,丁玲不再是初入延安时的一枝独秀,陈学昭、草明、白朗等女作家都参与到延安文艺建设之中,但同时文人之间的矛盾也悄然增多。这一时期,丁玲与中共的嫌隙拉大,其本我形象与正面符号化丁玲形象走向了背离。1938—1942年,丁玲从初入延安时的激动与踌躇满志转而充满内心的矛盾与犹豫,当她发现未到延安时想象的真实和到达后所见真实之间实际上仍有较大差距,一涌而入的文人之间又产生了许多龃龉,根植在内心的启蒙意识使她意识到了延安深处的“不和谐”。于是,小说《我在霞村的日子》《在医院中》《夜》,杂文《三八节有感》《干部衣服》,散文《风雨中忆萧红》成为丁玲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然而,这几篇带有批判性的文章无论从内容,还是情感,都和中共所塑造的“革命作家”“女战士”丁玲形象相差甚远,且与中共对外宣传的指归并不契合。文章发表之后不久,丁玲不仅被多位高层领导所指摘,而且成为国民党“良心话”中攻击中共的靶子,其性质已经不仅是“暴露黑暗”这么简单了。如果当时的延安文人承担的是延安的政治宣传和形象塑造的功能,那么所有的“暴露黑暗”或者抒发情感,便成了不和谐之音。而作为逐渐被塑造和重构了的文学符号——丁玲,在革命作家与女英雄的头衔下,其形象与其作品都应当是合规的,应该是与“延安道路”相一致的。她的形象不再是个人身份,而是纳入到“集体”中作为国共对抗的重要利器,稍有不慎便会影响中共对外形象,甚至是抗战整体大局。“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已经不再适应于延安在地性空间需求,丁玲如何让自我与“符号化形象”相契合成为她必须要面对的阵痛和调整。
当符号化的形象与本我真实相冲突,丁玲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就必须要做出调整和改造。她所创作的几部作品和其中流露出来的思想,与当时中共所要构建的意识形态话语,特别是外界对丁玲形象的认知形成了冲突,如丁玲在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而写的《我们需要杂文》:
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监督,见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接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应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24)丁玲:《我们需要杂文》,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7页。
这篇文章的特殊之处在于借用了鲁迅逝世五周年这一契机,而“鲁迅”作为中共宣传的“文化革命主将”,其形象更不能被随意“曲解”(25)这里所谓的“曲解”,意思是没有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传播体系中,是不合规的。。文学意识如果不能有利于战时特殊宣传环境,自然是要被合规的,这种合规不仅包括文人的作品,还包括文人本身。对文人的建构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不仅必须注意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区别,而且还要注意另一类明显支持(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实体,但一定不要把这些实体同(强制性)国家机器混淆起来。(我)将这类实体称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26)[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84页。而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政治无意识”所依附的真正的物质基础,是对个体进行体制化“规训”和合法化“生产”的领地,是一套看似温和却弥漫着神秘暴力的社会调控工具。而这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最重要的载体便是“媒介”。媒介通过报刊对丁玲形象的建构,正是无形中的意识形态话语主导。在这一体系下,无论是丁玲,还是鲁迅,或者是其他文人都要被“合规”,所以,整风运动不仅要求丁玲被改造,其他文人也处于同样的境地。
丁玲的形象建构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即她是一位女性。丁玲的正面形象符合作为一个独立、勇敢的革命女性形象,代表着解放区妇女的“整体形象”(这个整体形象在此应该是一个符合对外宣传的光辉形象,而非真实存在的实际形象)。在每日译报社出版的《女战士丁玲》中,丁玲是“给女学生了新的灵感和新的希望”女战士;在《战时妇女手册》中,丁玲在近代女性作家列位第一,成为给“娜拉出走后迷茫”的青年女性一条出路的女性,“圣地延安”的形象在正面的作家形象建构中逐渐凸显,而这正是“符号化”丁玲的作用和价值。《抗战大学》刊登了丁玲在西北苏区的文学活动,并从正面形象进行的宣传。从表面上来看,媒介是在报道事实,但实际上这种事实是《抗战大学》认为有价值、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有意义的、被建构了的事实,同时也无形中带上属于共产党所属阶级的文化特色。同样,1946年,《北方文化》刊登了“作家丁玲,现正着手写长篇报告‘延安难民工厂’”。(27)《文化消息:(三)作家丁玲,现正着手写长篇报告“延安难民工厂”》,《北方文化》1946年第1卷第2期。这则消息在选择报道内容之时,《北方文化》由其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所支配,从而影响在新闻建构中的思想体系和新闻观念。丁玲的形象这一时期已经在媒介中被塑造为“女战士”“女英雄”、延安文艺界的“女领导”,她的形象甚至关乎到国共两党对外形象。因此,丁玲思想中的不和谐因素必然需要合规。
这种被动的合规与丁玲本身是带有启蒙思想的独立女性之间,显然存在巨大冲突和矛盾。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力保,丁玲的命运恐怕在1942年前后就会不同,但即使是毛泽东保护了丁玲,后者同样也经历了十分压抑、黑暗,甚至不得不沉默,到最后“说谎”的过程。特别是在审干期间,丁玲几乎是惊弓之鸟,她想要给毛泽东写信,却被彭真告知:你以为毛主席喜欢你,你犯了错误他也喜欢你?(28)丁玲:《重大事实的辩正》,转引自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307页。于是,她在一个人(当时陈明不在她身边)最艰难的日子里,开始了自我形象的重新审视。如果说最初来延安时的革命热情是因为她对中共和革命充满了想象,那么在经历了“符号化”形象与“自我”想象逐渐产生不和谐,最终被“合规”之后,她(1942年后)努力让自己主动建构一种符合规范的形象,在经历了无比艰难的阵痛期之后,她认同了这个道路,甚至一直坚守至她生命的终结。
三、新形象之风:革命情绪的自我异化
如果研究丁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学形象,不难发现她走向了一条自我异化之路,这条路是带有革命信仰的,是无条件服从和支持共产党,甚至丁玲在经历了多年苦难之后,她依然坚信自己所选择的信仰。这和她之前敏感多思的性格是截然相反的。而这一对信仰的支撑应该是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开始了自我的塑造。这个塑造并不是逐步转变的,而是在一个很短时间内迅速完成的。特别是经历了审干运动之后,丁玲开始感到害怕和彷徨,从而意识到了自己之前思想上的不合时宜,也看到了自己作为延安文人所承担的责任和承受的压力,“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实也正应和了延安文人对‘真诚’的呼唤和歌颂,进而言之,因应了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所期待着的至诚人格建构心理。”(29)袁盛勇:《延安文人的真诚与说谎》,《粤海风》2005年4期,第1页。1936—1942年,是意识形态对丁玲形象的建构时期;1942年之后,是丁玲被动和主动地“合规”到意识形态之中,逐渐向“延安”意识形态靠拢的时期,她收起了先前的敏感和锋芒,主动深入到陕北农户家中,文学风格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创作了《三日杂记》《田保霖》《民间艺人李卜》,主动把革命情绪带入到自我形象的转变中,从而让形象“合规”。1945年,丁玲离开了延安,与杨朔、陈明等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前往东北,后因国共战事,她在张家口停留,参加土改,从事写作,但在其内心深处仍然与延安的情结连接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成功正是其自我塑造的“正面”形象获得普遍认可的结果。虽然这部享誉国内外的长篇小说是她离开延安之后(到河北张家口)写就的,但实际上仍是属于延安时期文人自我形象转变的成功案例。丁玲不仅在文学创作中成为一个适应大众、接近工农兵的作家,而且在思想上也摒弃了之前的知识分子的敏感和尖锐,不再充当一个“拯救者”和“批判者”的身份,甚至带有某种“崇拜”的色彩甘愿融入到农民大众的生活中。
而这一时期中共对丁玲的包容也正说明丁玲的形象仍在媒介宣传的正面形象之列,她成为延安妇联的重要人物、中共著名作家,特别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名声大噪,让她成功地转入到工农兵写作中。她作为中共对外宣传“符号”和“名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当《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以后,丁玲在党内的形象不再是革命女作家,而转变为“共产党女巨头”(30)莫耶:《女共产党两巨头:丁玲与邓颖超》,《海晶》1946年第2期,第9页。。在《海晶》中曾经有一篇报道以《女共产党两巨头:丁玲与邓颖超》为题,分别详细介绍了丁玲与邓颖超的经历,单看其中的题目就已经说明了丁玲在当时党内的地位。“女巨头”的形象不仅出现在《海晶》中,同时在《国际新闻画报》中也曾有“一人而兼二要职,威风可知”(31)邱吉吾:《赤色女作家:襄助林彪李立三,丁玲祕密赴哈》,《国际新闻画报》1946年第59期,第7页。。在《中国革命的女性》(32)钱塘编:《中国革命的女性》,群泉社,1949年9月。一书中,丁玲位列其中,而这本书中被列举的革命女性仅有7位,包括邓颖超、康克清、蔡畅、刘群先、李建贞、蓝蘋(江青)等,除了丁玲,其他几位女性都是中共高层领导夫人,且身份特殊。可见丁玲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党内地位更加凸显。《解放日报》在1946年刊登《解放区妇联选出蔡畅、邓颖超、丁玲三位代表参加国际妇联理事会》(33)《解放区妇联选出蔡畅、邓颖超、丁玲三位代表参加国际妇联理事会》,《解放日报》1946年4月20日第 1版。,《民族呼声》中刊登了《丁玲等致美国文化新闻界电》(34)《丁玲等致美国文化新闻界电》,中国外交研究所编:《民族呼声》,中国外交研究所,1946年,第59页。,都能看出丁玲当时在延安地位非同寻常。这一时期,丁玲的形象建构无论是在党内媒介还是在党外媒介中都得到了稳固,并逐渐成为延安妇女界的代表性人物。从著名女作家——女战士——女领导——妇联代表——知名作家,看似是一个回环,实则是丁玲延安时期“符号化”形象的最终形成。
与其说丁玲在1942年之后的创作是一种被动的迎合,不如说是自我的异化,真实的“谎言”,她在1942年之后看到了“合规”的唯一性和重要性。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甚至是经历了各种打击和磨难之后,她依然以《杜晚香》这样作品达意,正如此,“符号化”的丁玲得以真正完成。
四、结 语
作为跨越了大半个世纪、有着传奇和复杂经历、多个头衔的丁玲,其实是经历了个人——文学——符号的转变过程,而这一转变是从1936年她进入延安集体开始的,当时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时代,自然要求文人“合规”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正如鲁迅作为“新文化主将”不断被重塑、推崇,甚至被“神化”一样。作为有着特殊经历的革命女作家,丁玲从延安时期开始就已经在一步步地适应并调整建构“丁玲”形象,从自我到他我,从个人的“丁玲”与符号化的“丁玲”,直至逐渐“合规”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去,适应并接受“丁玲”形象的不断改变、被传播,甚至她经历了一段痛苦的黑暗时期,直至她从真诚的“谎言”中说服自己,并努力实现自我异化,个人的“丁玲”已非显性的存在了,文学的“丁玲”也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符号”的丁玲,而这一过程中,她已经适应并改造了自己,并接受了“符号”丁玲与自我的融合与异化。《七月的延安》是她个人内心的激动与兴奋,而《在医院中》《风雨中忆萧红》是她两者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已经愉快地接受自己作为“女巨头”的光辉形象,直至《杜晚香》经历了百般磨砺之后,她彻底成了一个“符号”,也彻底认同了“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