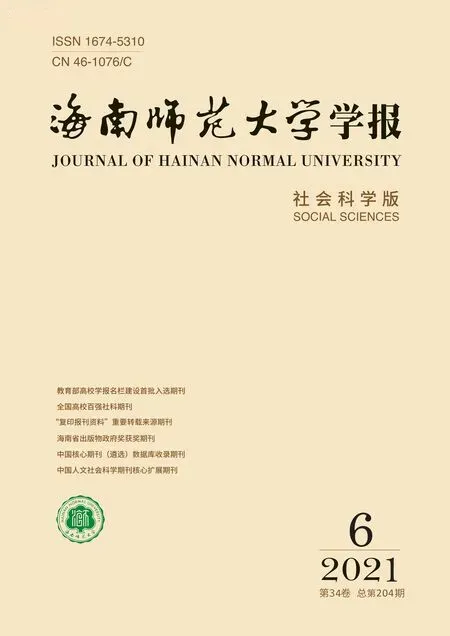从匿名性到易容术
——现代都市与侦探小说起源关系初探
战玉冰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侦探小说是一种诞生于现代都市中的小说类型。借鉴齐美尔、本雅明、克拉考尔等西方学者的论述,现代都市的“匿名性”特征与都市罪案频发和侦探小说诞生都有密切关联。一方面,现代都市中的陌生感受、“惊惧体验”与心理焦虑呼唤着身为现代“理性之子”的侦探形象的诞生,同时也确认了侦探小说自身文类的早期内在规定性;另一方面,作为滋生犯罪的温床,现代都市既为侦探小说的书写提供了题材基础,又将“罪恶之都”的概念具像化为小说中的关键形象要素(巴黎的杀人红毛猩猩或者伦敦街头的大雾)。此外,现代都市“匿名性”特征又常演化为侦探小说中关于“易容术”的传奇书写,并延续发展成一个相对固定的文学脉络。
一、现代都市生活的“匿名性”
19世纪中期,随着欧美各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和新一轮城市化发展的浪潮,大型现代化都市纷纷出现,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城市当属伦敦和巴黎。半个世纪以后,崛起中的中国上海则被称为“东方巴黎”与“远东之都”。在人口数量庞大、人员流动频繁、职业分工细密、生活节奏加快的现代都市中,人们身份的多重性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彼此了解的片面性与认知的破碎性。人们的出身、来历和过往似乎都可以隐藏许多“不为人所知”与“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所描述的传统中国彼此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大不相同,或者我们可以借用“熟人社会”的命名,将其称之为“陌生人社会”(Stranger Society)。这里所谈到的“陌生人社会”主要特点有二:一是个体过往经历的匿名性,二是个体当下身份的多重、片面与破碎,二者互为表里。在现代大都市的“陌生人社会”——克拉考尔将其形容为“酒店大堂”,即“散落于大堂的人们则不具疑问地接受东道主的隐匿身份(Inkognito)”(1)[德]德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侦探小说:哲学论文》,黎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0页。——之中,人们很难真正完整地去了解一个人,更难彻底把握一件事情背后的最终真相与来龙去脉,而这种匿名性与破碎性既是滋生犯罪的温床,也是侦探得以诞生且发挥其功能的场域。包天笑在《上海春秋》开篇便说道:“都市者,文明之渊而罪恶之薮也。觇一国之文化者必于都市,而种种穷奇梼杌变幻魍魉之事,亦惟潜伏横行于都市。”(2)包天笑:《上海春秋·赘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恰如程小青笔下的侦探霍桑和助手包朗对上海的认识一样:“像上海这般地方,人家都称为‘奸恶制造所’的。”所以霍桑才最终决意从苏州搬到上海,“既然决意从事侦探的事业,则上海比苏州容易活动。”“才就爱文路七十七号里设立了私家侦探办事处,预备从事侦探职务。”(3)程小青:《长春妓》(又名:《沾泥花》),《礼拜六》第一百一十三期,1921年。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英国作家切斯特顿为何会称侦探小说是“城市的犯罪诗篇”(4)转引自詹宏志:《詹宏志私房谋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
这方面颇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爱伦·坡的《玛丽·罗杰疑案》。在这篇小说里,侦探杜邦在反驳《商业报》所认为的“像这样一位受到好几千人注意的年轻妇女走过三个街区竟没有一个人看见,是不可能的”(5)[美]埃德加·爱伦·坡:《玛丽·罗杰疑案》,孙法理译,《爱伦·坡短篇小说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时,就明确指出“就我而言,我倒是觉得,玛丽在任何时候从自己住处去姨妈家,无论在众多的路里选了哪一条,一个熟人也没有遇见的可能性不但是有的,而且非常大。在充分地、恰当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必须在心里坚持一条:即使是巴黎最知名的人士,他的熟人数目与巴黎的整个人口相比也都微乎其微。”(6)[美]埃德加·爱伦·坡:《玛丽·罗杰疑案》,孙法理译,《爱伦·坡短篇小说集》,第171页。即道出了现代化大都市的人口体量绝非一般个人交际圈所能比拟和想象。类似的,在陆澹盦的“李飞探案”中,侦探李飞在判断出夏尔康仍然躲在上海之后,也只能感叹:“偌大的上海城,要找一个人倒也很不容易。”(7)陆澹盦:《密码字典》,《红杂志》第28、29期,1923年。而柯南·道尔《血字的研究》中,华生偶遇小斯坦佛的一段话也可作为杜邦和李飞上述观点的另一佐证:“当我站在克莱蒂里安酒吧门口时,有人忽然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竟是小斯坦佛,我在巴茨时的助手,对一个孤独的人来说,在人海茫茫的伦敦能碰到一个熟人,无疑是天大的快事。”(8)[英]阿瑟·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血字的研究》,王逢振、许德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页。
此外,柯南·道尔笔下《证券经纪人的书记员》一篇中,犯罪分子抓住银行通过材料审核录取了新的书记员却没见过其本人的空档,趁机冒名顶替并在其中展开犯罪。在这个故事里,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同事”之间素未谋面的“陌生”与彼此认知的“片面”和“破碎”,从而制造出犯罪的机会,而这在人与人之间彼此熟悉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类似的,在张碧梧的“家庭侦探宋悟奇新探案”系列中的《鸿飞冥冥》一篇当中,邮差周阿福每周都送挂号信到吴家,还需收信人在回单上盖章留证,但即使如此的“定期见面”,周阿福其实“只晓得把信交给人家,自然不注意人家的面貌”(9)张碧梧:《鸿飞冥冥》,《半月》第3卷第6期,1923年12月8日。,因而让犯罪者从中钻了空子。作为在都市中送信的邮差,虽然每天都在和人打交道,但他们从来不曾真正注意究竟是谁收了这些信。他们看似与这些收信人打过交道,实际上却是彼此陌生的。甚至于在程小青的《怪房客》中,房东、二房东、邻居都对与自己朝夕生活在一幢小楼里的叶姓租客的身份、职业、来历和为人一无所知。(10)程小青:《怪房客》,《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程小青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33-250页。
更加将“匿名性”凸显到极致的案件当属张无诤的侦探小说《X》(11)张无诤:《X》,《半月》第3卷第6期,1923年12月8日。:故事一方面紧紧围绕一个不知道自己姓名和来历而自称为X的人展开,并且不断追寻他身份之谜的真相。另一方面,X的身份之谜也引起了媒体的兴趣与趋之若鹜的跟踪报道,这又被利用作为犯罪分子间彼此联络和传递消息的手段,并在小说结尾处引发了多次情节上的反转。这篇小说中的主角X是对现代都市个体身份“匿名性”的隐喻式展现,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一切悬疑、犯罪与情节铺排都是围绕他的名字/身份而产生并被不断推向高潮。而这篇小说本身也可以被视为是侦探小说在表现“匿名性”意义上的一篇“元小说”,即一切侦探小说本质上都是在追寻一个关于X身份的真相,X的身份既是所有悬疑产生的源头,也是诸位侦探得以存在的关键。
都市生活的匿名性是隐匿行踪与滋生犯罪的沃土。恩格斯曾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对当时伦敦这座现代化都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表示过担忧和批判:“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12)[德]恩格斯:《大城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8-59页。恩格斯所说的这种“冷淡”与“孤僻”被齐美尔称之为“矜持”,“是一种拘谨和排斥”(13)[德]齐美尔:《大城市与精神生活》,[德]G.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涯鸿、宇声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第267页。。在齐美尔看来,这种大城市中个体的“矜持”态度和表现具有某种精神反应上的必然性,即“他们要面对大城市进行自卫,这就要求他们表现出社会性的消极行为。大城市人们相互之间的这种心理状态一般可以叫作矜持。在小城市里人人都几乎认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而且跟每一个人都有积极的关系。在大城市里,如果跟如此众多的人的不断表面接触中都要像小城市里的人那样做出内心反应,那么他除非要会分身术,否则将陷于完全不可设想的心理状态”(14)[德]齐美尔:《大城市与精神生活》,[德]G.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涯鸿、宇声等译,第266-267页。。但无论如何,伦敦的快速发展、人口激增与都市中人们态度冷漠和彼此隔绝同时发生,共同形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组有趣吊诡。对此,本雅明也曾援引一名巴黎秘密警察的话并对其加以引申:“1798年,一位巴黎秘密警察写道:‘在一个人口稠密而又彼此不相识,因而不会在他人面前脸红的地方,要保持品行端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大众仿佛是避难所,使得那些反社会分子得以免遭追逐,在大众的各种令人不安的方面,最先显现的便是这一点,这也是侦探小说得以兴起的原因所在。”(15)[德]瓦尔特·本雅明:《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48-49页。进而本雅明认为“侦探小说最初的社会内涵是使个人踪迹在大都市人群中变得模糊。”(16)[德]瓦尔特·本雅明:《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第53-54页。也正是从这一理解出发,本雅明才会对爱伦·坡的小说《人群中的人》(TheManoftheCrowd)予以高度评价,后世很多侦探小说研究者也将这篇小说看成是侦探小说的“雏形”之作。
关于清末民初时期中国人对于现代性的感受,正如学者李怡所说:“现代中国的‘现代’意识既是一种时间观念,又是一种空间体验,在更主要的意义上则可以说是一种空间体验。对于现代中国的思想形态是如此,对于文学创作就更是如此。”(17)李怡主编:《词语的历史与思想的嬗变——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概念》,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第15页。比如刘半农的小说《女侦探》开篇对于女主角出场的描写就确实带有一种爱伦·坡“人群中的人”的意味:“滨江,关外之热闹市场也。地当交通之点,人物凑杂,旅馆如云,日既幕,电光灿烂,旅客咸出游,纸醉金迷,几忘天涯浪迹,车龙马水,宛若海上繁华。有革命党中某少年者,着革履,服西装,口含雪茄,徐步街上。至一杂货店门首,有少女出,目注少年良久,少年忽现惊讶色。已而再行,女随其后,少年频频回顾,女亦目送之。行过半里许,过一空马车,少年跃登车上,叱车夫曰:‘速往某戏园。’意若欲使此声浪传入女耳鼓。俾女知其去向者。女殊不顾,竟向前疾行,殆少年回首时,已不见矣。”(18)刘半农:《女侦探》,《小说海》第3卷第1期,1917年1月5日。刘半农的这篇以“侦探”为名的小说本质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侦探小说,而更近似于当时流行的虚无党小说,但其开场这一段对于女主角“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描写,却恰好体现出了侦探小说的某些都市化与匿名性特点。
二、隐藏在都市中的未知的罪恶与恐惧
隐匿在都市中的“人群中的人”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未知、悬疑、恐怖与罪恶,而在公认的世界第一篇侦探小说,美国作家爱伦·坡于1841年5月发表在《格雷姆杂志》上的《莫格路凶杀案》中,便将这种徘徊于都市与人群之中的罪恶与恐惧感成功具象化了。小说中的杀人凶手,那只穿梭在巴黎的红毛大猩猩,它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奇闻怪谈,而是更为隐喻性地表达了在陌生都市里穿行的“惊颤体验”和死亡恐惧。红毛猩猩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现代都市中人的兽性、欲望与暴力的象征物,是都市人们对于都市生活恐惧感的投射与集合体。学者付景川、苏加宁更进一步指出:“‘黑猩猩进入家宅’这一事件恰恰隐喻了极端异己性入侵私人空间的可能,而它非理性的杀戮本身,更可以看作现代都市空间焦虑的浪漫化表达。”(19)付景川、苏加宁:《城市、媒体与“异托邦”——爱伦·坡侦探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北方论丛》2016年第4期。此外,小说里所有人(邻居/现场证人)都好像听见了它的声音,但所有人又都不知道它究竟说的是哪国语言(他们分别指认凶手说的是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德语和俄语),大家各执一词,却又都模棱两可,这一巴别塔与罗生门式的证词其实是现代都市中人与人之间极度陌生化的体现与虚妄的世界性想象。爱伦·坡第一篇侦探小说似乎想借助在巴黎游荡且杀人的一只红毛猩猩告诉读者:侦探小说在诞生之初就是属于现代都市的小说类型,同时小说里侦探所要面对和解决的正是现代都市中潜伏于人群之中的、人们内心所隐藏的兽性、暴力、犯罪与恶。
和巴黎一样令人感到难以捉摸的现代化大都市当然还有伦敦,弥漫于伦敦街头的大雾就往往被作家用作体现这座都市神秘性与犯罪温床的象征之物:“1895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黄色的浓雾笼罩着英国,从周一到周四,我怀疑能否从我们位于贝克街的窗户看到对面那若隐若现的房子。”(20)[英]阿瑟·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最后致意·布鲁斯-帕廷顿计划》,王逢振、许德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650页。伦敦的“大雾”在某种意义上和巴黎街头的“人群”有着相类似的作用,它们共同为犯罪者隐匿行踪提供了便利与可能。福尔摩斯就曾说:“你看窗外,华生,人若隐若现,又融入浓雾之中。这样的天气,盗贼和杀人犯可以在伦敦随意游逛,就像老虎在丛林里一样,谁也看不见,除非他向受害者猛扑过去,当然只有受害人才能看清楚。”(21)[英]阿瑟·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最后致意·布鲁斯-帕廷顿计划》,王逢振、许德金译,第650页。同样,在小说《四签名》中,华生也被这伦敦浓雾笼罩之下匆匆逝过的行人面孔弄得紧张不安:“这是一个九月的傍晚。尽管还不到七点钟,天气却已阴沉下来,一场浓雾低低地罩在城市的上空。泥泞的街道上空飘浮着乌云,吊着的路灯变成了一个个模糊的小点,发出的淡淡的光照在潮湿泥泞的人行道上。从商店窗户里射出来的黄光,透过层层雾气照到了拥挤的大道上。连绵不断的行人的面孔有悲伤的、憔悴的,也有高兴的。每一张脸就像人类的历史一样,从黑暗转到光明,又从光明转到黑暗。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在这样一个阴暗沉重的夜晚,加上我们担负的奇怪的任务,使我变得紧张不安起来。”(22)[英]阿瑟·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四签名》,王逢振、许德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63页。和爱伦·坡笔下“人群中的人”与红毛猩猩异曲同工,柯南·道尔利用伦敦浓雾使得人与人之间彼此看不清楚的这一客观天气现象,作为现代化都市“惊颤体验”与不安感受的另一具象化表征。而这种弥漫于都市中的罪恶同样存在于东方的现代都市之中,正如孙了红在小说中所说:“太阳在东半球的办公时间将毕。慈悲的夜之神,不忍见这大都市的种种罪恶,她在整理着广大的暗幕,准备把一切丑恶,完全遮掩起来。”(23)孙了红:《航空邮件》(又名:《鸦鸣声》),《大侦探》第16期至第17期,1947年12月至1948年2月。
三、“匿名性”与侦探的登场
犯罪分子在现代都市“陌生人社会”中的匿名性呼唤着侦探的出现,甚至我们可以把侦探小说的情节模式视为是发生在罪犯与侦探之间,一场关于试图隐藏身份与努力追查身份的角逐和较量。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来看福尔摩斯与华生的首次相遇,则会有一番更加深入的理解:福尔摩斯在《血字的研究》中初次见到华生医生的时候就推断出他曾经在阿富汗当过军医,其理由就是根据华生身上的种种细节特点(气质硬朗、肤色黝黑、受过外伤、行动不便等等),经过观察、发现、推理所得出的结论。如果说现代都市中人的身份具有某种“匿名性”,那么侦探的功能就是借助当下所能观察到的诸多细节揭示出其过往的种种隐匿的经历(将当下有限空间中所观察到的内容转换为对观察对象过往时间中经历的推测);如果说现代都市中人的认知是片段、破碎且模糊的,那么侦探的特殊本领就是将这种片段、破碎与模糊重新整合并形成完整认知链条的能力。早期侦探小说中侦探经常通过种种蛛丝马迹(足印、烟灰、血迹、泥点、毛发、伤口、服饰、眼镜、鞋子、神态等等)来推断出凶手的特点与身份,为最终破案提供关键性线索或方向指引的例子实在是多到不胜枚举,从绝大多数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到中国的霍桑探案、徐常云探案等等,都不厌其烦地对侦探的这一特殊能力展开过细致的铺陈和描写。而侦探们这种对细节观察、整合与推演的能力,正是基于现代化都市这个“陌生人社会”里人们身份上普遍存在的“匿名性”与“破碎性”特点而产生的。将破碎的认知还原成完整的因果逻辑,揭示出匿名凶手背后的真实身份,就是所有早期侦探小说中侦探们所努力完成的工作和目标。
庞大且密集的城市人口为犯罪者的犯罪和藏匿提供了最好的遮掩。而都市空间本身更可以视为是一个巨大的人造的犯罪场域,其间错综复杂、交织环绕的城市内部道路宛如迷宫般地令追踪犯人的侦探感到“头晕目眩”(24)单纯从物理空间的角度来讲,都市之内的道路与建筑迷宫对罪犯施行犯罪而言也是一个挑战,比如在《血字的研究》中,从美国而来的凶手在伦敦城里追踪被害人,被捕后就表示“最困难的事情是记不清道路,在所有的道路复杂的城市中,我觉得伦敦城的街道是最复杂难认的了,我就随身带上一张地图,后来我熟悉了一些大的旅馆和几个主要车站,工作慢慢开始顺利了。”。或者我们可以说,都市道路的复杂性即是犯罪案件复杂性的空间性外显与物质化寄托,而侦探们则正是在这迷宫般的都市街道中追寻真凶,就如同他们面对同样复杂的案件而进行抽丝剥茧,追查真相一样。
开始我还能认清马车行驶的方向,但很快,随着速度逐渐加快,外面的大雾,还有我对伦敦道路的不熟悉,我的脑子里就一团迷糊,只知道这段旅程很长。福尔摩斯却没有迷失方向,车子经过广场或是曲折的街道时,他还能小声地说出地名来。
他道:“罗切斯特路,现在是文森特广场。我们现在到了沃克斯豪尔桥路,马车好像正在驶往萨利区。我想我是对的,现在我们到了桥上,你们还可以看到河水。”
泰晤士河被路灯照着的宽阔、平静的河面在我们眼前很快地一闪而过。但是马车还是在继续行驶,很快就消失在桥对岸迷宫一样的街道中。(25)[英]阿瑟·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四签名》,王逢振、许德金译,第63页。
这里对于城市道路的描写并非仅仅是单纯地在渲染一种悬疑与紧张的气氛,更是对整个案件复杂与惊险的空间隐喻。“对伦敦道路的不熟悉”“脑子里就一团迷糊”的华生对后来扑朔迷离的案情也同样是一头雾水。而“没有迷失方向”,甚至“还能小声地说出地名来”的福尔摩斯则始终保持着警惕、敏锐和正确的查案方向。从这一点看来,对城市内复杂道路的了然于胸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于复杂案情的清楚把握。如果我们从整个福尔摩斯系列探案故事中来看伦敦街道的迷宫隐喻,甚至可以寻找到其与福尔摩斯最具标志性地仔细观察案发现场这一行为之间的深层关联:福尔摩斯查案时往往要对案发现场进行一番非常精细的观察,而他对整个伦敦街道地图的熟稔于心或许就可以看作是他对于这个犯罪欲望的集合之地与幻象之城精细观察的结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侦探以理性的目光掌控城市,他们查清案情真相的同时即意味着城市从局部的混乱到秩序的恢复,侦探角色的成功更表示都市是可以被掌控与被秩序化的,而这种秩序的前提即是侦探对城市内部每一条街道路线的了若指掌。毕竟,对于福尔摩斯来说,“他喜欢住在五百万人口的正中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每一个悬而未决的小小传闻或猜疑都作出反应。”(26)[英]阿瑟·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回忆录·住院的病人》,王逢振、许德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299-300页。此外,这种对城市内街道的了解也需要侦探不断地熟悉和记忆,福尔摩斯就经常告诫华生:“所以说,我的朋友。了解你所居住的城市是多么的重要!”(27)[英]阿瑟·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历险记·波西米亚丑闻》,王逢振、许德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
了解一座城市必然需要侦探做出专门的留心和仔细的观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侦探视为是一座城市的“阅读者”。在小说《红发会》中,福尔摩斯在了解到“红发会”的奇怪事件之后,就亲自动身赴现场进行考察,开始了对当地几个街区的“阅读”:
“我的亲爱的华生,请原谅我现在并不是和你悠闲地散步聊天,在我留心观察环境的时候是不能同时回答你这么多问题的。而且,我想你应该知道,这是在敌人领土里进行的侦查活动。好的,广场这里的情况基本了解了,我们绕到后面去吧。”
……
福尔摩斯避让着行人,刚好停在拐角处顺着一排店铺望去,说:“现在我要做的是记住这些店铺的顺序。嗯,让我想想看。华生,你知道,我一直希望能准确无误地了解伦敦的一草一木。莫蒂然烟草店!恩,那边是一家报亭!后面呢?哦,市区银行的科伯格分行、素食饭店、麦克法兰马车制造厂,没有其他店铺了吧,那已经是另外一个街区了。”(28)[英]阿瑟·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历险记·红发会》,王逢振、许德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122页。
正是基于侦探的“阅读”,甚至需要记住“店铺的顺序”,福尔摩斯才能够最终真正做到“准确无误地了解伦敦的一草一木”。而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份苦功的积累,才会有上面所引述的《四签名》中所呈现出来的侦探对于整座城市的熟稔于心。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存在于现代都市中的“人潮”或“大雾”对犯罪分子所起到的遮蔽效果,有时也会令侦探们感到为难和无能为力。比如福尔摩斯时时警惕自己的追查行动被犯罪分子发现,因为一旦犯罪分子有所警觉,潜入都市人群之中,则将使案情查办变得格外困难,以至于无从下手:“只要凶手没觉得有人发现线索,我就有机会捉住他。但是,要是他稍有怀疑,他就会隐姓埋名,立即消失在这个大都市里,想想看,四百万居民,到哪里去找?”(29)[英]阿瑟·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血字的研究》,王逢振、许德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27页。又如福尔摩斯曾对他的委托人表示过:“我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您在伦敦被人跟踪。在这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很难发现这些人是谁或者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们的目的是邪恶的,他们可能会伤害您。我们没有能力阻止。您不知道,默蒂医生,今天早晨你们从我家出来,就被人跟踪了。”(30)[英]阿瑟·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巴斯克维尔猎犬》,王逢振、许德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487页。都市人口众多与人流密集对案件查办与保护当事人所带来的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四、匿名性的传奇化想象——“易容术”
将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匿名性”特点发展到极致便产生了侦探小说里的易容术,易容术无疑可以看作是侦探小说里隐藏身份(匿名)的浪漫化想象。无论是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还是勒伯朗笔下的亚森·罗苹,亦或是其在中国的后继者——程小青笔下的侦探霍桑与孙了红笔下的侠盗鲁平,都是此一方面的个中好手。福尔摩斯自己就曾多次乔装易容成为老人(《四签名》)、流浪者(《歪嘴男人》)、病人(《临终的侦探》),甚至用留声机录下并播放自己拉小提琴的声音,以使得犯罪分子误以为他仍在房间内(31)这可以视为某种对声音的伪装与“易容”。(《王冠宝石案》)。而福尔摩斯的对手们也经常通过易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血字的研究》中的马车夫和依循失物招领前来领取戒指的“老太太”、《波西米亚丑闻》中的艾琳·艾德勒小姐、《身份案》中邪恶的继父等等。在勒伯朗笔下,亚森·罗苹更是经常通过神乎其神的“易容术”把福尔摩斯、华生和警察们骗得团团转(当然,这和勒伯朗本人曾经做过舞台化妆师,对化妆术颇为熟悉有关,而其小说中的人物亚森·罗苹则被塑造为曾在皮肤科实习,因而学会了换脸的技术)。
在中国的侦探小说中,易容术也经常被使用和渲染。程小青就曾在《案中案》中专门强调过霍桑易容手法的熟练与迅速:“霍桑有一种特技,在紧急的关头,举动的敏捷会出于人们的意想之外。有一次我见他卸去西装,换上一身苦力装来,又用颜料涂染了脸部,前后不过两分另六秒钟。”(32)程小青:《案中案》,程小青著、范伯群编:《民初都市通俗小说3:侦探泰斗——程小青》,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年,第55页。此外,侠盗鲁平也非常擅长易容术,《眼镜会》中作者孙了红便借小说人物杨国栋之口说道:“总之鲁平的化妆术是神出鬼没的,任是他假充着我们的父母兄弟,也许要被他瞒过咧。”(33)孙了红:《眼镜会》,《半月》第三卷第十八期,1924年。甚至于在《鬼手》和《鸦鸣案》中,鲁平还曾经假扮霍桑,进而以调查案件为由深入私宅,以寻求盗宝的机会。当然,“易容术”在科学和实际运用层面是否真的能如此“随心所欲”和“惟妙惟肖”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其实早在1927年,就已经有人对侦探小说里过度依仗和滥用“易容术”提出了质疑和批评:“用化妆术的侦探小说固属无赖的作品,就是用催眠术和其他是似而非的科学侦探也是不对的。因为出于侦探化妆或使用他种手段不过描写人智幼稚底反照,并不算是名家。所以列宁说侦探须以平常手段使人惊讶,不许用奇异手段使人转疑其作伪。现代科学普及,人人皆有侦探底可能性,若一涉神奇和幻术,在幼稚社会中,或有人肯信,而移在科学昌明的地方,就没有人过问了。”(34)陈景新:《小说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7年,第127-128页。本文也并非将“易容术”作为侦探小说的科学手段之一来进行考察,而是将其视为侦探小说所呈现出的都市“匿名性”的一种象征性表达和浪漫化想象来予以理解:在现代都市之中,每个人都主动或被动地借助陌生人潮而成为“匿名者”,而“匿名”的极致便是“易容”——改变容貌,进而改变身份,把自己装扮作他者,使自己更容易混迹在人潮之中。
从现代都市中的陌生人关系与“匿名性”特点,到都市罪案的频发与人们对于都市生活危险的恐惧与焦虑,这种伴随着现代都市普遍兴起而产生的时代性感觉结构在文学类型上呼唤着“侦探形象”的登场与侦探小说的诞生,这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欧美与中国早期侦探小说故事通常发生在巴黎、伦敦或者上海等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一方面,侦探作为城市“阅读者”与“漫游者”,其核心功能就在于发现城市表象背后所隐藏的秘密,寻找出藏匿在“人群中的人”,以理性代言人的形象来驱散读者内心的恐惧,打造出一种一切案件终将可水落石出的安定幻象;另一方面,都市“匿名性”又进一步在侦探小说中具象化为“易容术”,并且被中外侦探小说家反复渲染得神乎其神,而这种传奇化的犯案/侦破手段,在本质上却又是反科学、反理性的。由此,从“科学化的文学”角度来看,世界早期侦探小说在主要内容与核心意象上就构成了自身一组有趣的背反,而解释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重新审视和强调现代都市与侦探小说起源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