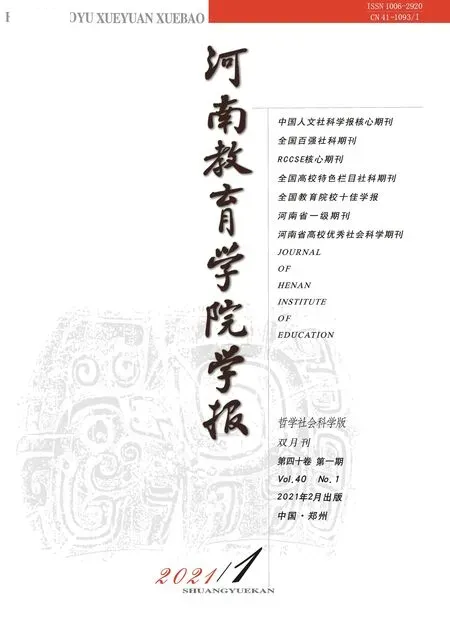论《弗兰肯斯坦》中自然观与地理空间的嵌套
张姗姗
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是科幻小说的鼻祖。如今,这则天才科学家被其创造物报复的寓言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在后现代批评理论中,不管是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人类批评,还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小说主人公弗兰肯斯坦屡屡被当作人类中心主义、父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成为批判的靶子。现有研究呈现出将弗兰肯斯坦这一人物及其自然观扁平化的倾向,忽视了小说文本中弗兰肯斯坦自然观念的复杂性和前后的变化。在小说中,“自然(nature)”一词出现了55次,包含多重含义。生态哲学家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指出,这部小说解构了早期生态批评所歌颂的纯净自然,其中的“生态联想,与正统的自然观信仰相比,如此离奇,以至于没有人直接面对这部小说”[1]145。莫顿认为,小说中的自然一词前后矛盾、无法自洽。本文认同莫顿对小说中自然观复杂性的判断,并将其归结于主人公弗兰肯斯坦自然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小说中的地理空间相嵌套。因此,本文运用人文地理学理论和生态批评理论,结合19世纪初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当下的景观理论与环境美学,探究不同地理空间带来的不同体验对弗兰肯斯坦自然观的影响。
一、不同自然观与地理空间的嵌套分布
现代英语当中的“na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natura”。“natura”是希腊词“physis”的拉丁语译名。“在早期古希腊思想家那里,physis首先意味着万物发生和成长的过程,由此引申出万物的起始和事物的始基的意思。”[2]在此意义上,自然是有生命的、有机的,是理性与物质性的统一。此后,犹太-基督教信仰改变了这种西方原始的自然观,西方人开始普遍相信上帝从无中创造世界,人与非人的物质世界是分开创造的,存在等级的差别。自此,自然本身不再具有内在的完善性,“渐渐失去了其目的论的性质……去目的论的‘自然’概念几乎就是纯粹的物质或实在”[2]。基督教信仰导致人与作为纯粹物质世界的自然的分离。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总结出现代意义上自然的三种内涵,分别是:“(ⅰ)某个事物的基本性质与特性;(ⅱ)支配世界或人类的内在力量;(ⅲ)物质世界本身,可包括或不包括人类。”[3]326《弗兰肯斯坦》中用到的“nature”可以涵盖威廉斯归纳出的“自然”的所有含义,自然既用来指人的天性(human nature),也用来指自然法则(the law of nature),或者以大写N来标识,用来指超自然的神旨(Nature),同时,也用来指有人或非人的物质世界。玛丽·雪莱笔下自然的复杂性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西方自然观的转型密切相关。
直到18世纪,掌控自然为人类服务的机械自然观依然流行。文艺复兴后期的科学革命增强了西方人征服自然的信心,这一时期“科学已经将自然等同于一个僵死的、空间上无限且到处充满了运动的物质世界,它没有质的差别,并被普遍而纯粹数量的力所驱动”[4]。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家普遍认为“研究自然界的全部目的便是‘认识自然,就可以掌控自然、管理自然、为人类生活福祉而利用自然’”[5]16。18世纪后半期,英国的工业革命促使社会向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导致人与自然进一步隔绝,也使得自然逐渐具有了“人的初始状态”和“自然景观”的含义,“对自然的体验替代了关于自然的知识,情感替代了思想,身体替代了头脑”,“‘自然’被视为一种未被污染的、未被人类之手接触过的、远离城市的东西”[6]34-35。18世纪后半期,自然逐渐被赋予审美的价值,以及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善的力量。
小说主人公弗兰肯斯坦被设定为18世纪的科学天才,他的自然观最初带有一定的复杂性。在18世纪,自然科学家与哲学家仍旧可以是一个群体,“自然哲学仍旧是哲学的一部分,仍然在奋力解决诸如关于灵魂的存在、物质的能动性与被动性、意志自由以及上帝的存在之类的哲学问题”[7]13。弗兰肯斯坦并不满足于将自然看作精密仪器。一方面,他认识到了自然的神秘性,因此对神秘学家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和炼金术士帕拉塞尔瑟斯等人的研究充满兴趣;另一方面,他仍旧将自然作为认知和征服的对象,这种主客体关系,以及为人类服务的论调仍旧是培根自然观念的延续。弗兰肯斯坦的命运与他的这一自然观念休戚相关。这种观念在小说中不断经受挑战,不断改变,而改变的原因与人物的空间体验紧密相关。
小说中,弗兰肯斯坦自然观的转变与文中基于地理空间转移的叙事结构紧密相关。《弗兰肯斯坦》采用了三层嵌套的叙事结构,沃尔顿的叙事嵌套着弗兰肯斯坦的叙事,弗兰肯斯坦的叙事中又包含有怪物的叙事。小说中的场景不断变换,且每一个叙事单元都设置在相应的地理空间之中。小说的主要叙事单元以弗兰肯斯坦的视角展开,他的叙事跨越了从日内瓦到北极的广袤的欧洲大陆。这些地理空间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日内瓦的乡村庄园所代表的中间景观,这里有弗兰肯斯坦的童年生活;第二种是德国的因戈尔施塔特大学代表的城市景观,这里是他悲剧的发生地;第三种是以阿尔卑斯山为代表的荒野景观,这一部分将弗兰肯斯坦的叙事与怪物的叙事嵌套起来,最终导致了弗兰肯斯坦自然观的改变。由此可以看到,在弗兰肯斯坦成长过程中个人地理空间的转换客观上带来了其自然观的改变,对待自然的态度又决定了他的命运走向。
二、中间景观:机械自然观的形成
小说中,弗兰肯斯坦一再提起他童年幸福的家庭生活,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是小说中唯一温馨的画面。弗兰肯斯坦生长在风光旖旎的日内瓦,父亲是城市显贵,却热爱乡村生活,全家大部分时间住在“日内瓦湖的东岸,离城约三英里的贝尔里韦湖畔”的乡村庄园(campagne)中,在这里他们“过着遗世索居的生活”。[8]27这处离城市不远的乡村庄园正是批评家里奥·马克斯(Leo Marx)和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笔下典型的“中间景观(middle landscape)”。马克斯将主要位于城市与荒野之间的田园景观称为中间景观;而段义孚则将中间景观的外延扩大,认为“处于人造大都市与大自然这两个端点之间”,包括“农田、郊区、花园城市、花园示范镇”等的人类居住地都可以称作中间景观,并“将中间景观称作人类栖息地的典范”。[9]29
这种对宁静乡村生活的喜爱和怀旧,往往将乡村的淳朴与城市的堕落相对立。在18世纪上半叶,人们普遍喜爱被驯化的、被人为修饰过的自然或花园。在这种中间景观中,人类对所居住的自然环境进行设计和改造,并设法维护自然的活力。这里兼容了城市和乡村生活的益处,自然呈现出秩序和丰美,文明也并不堕落,人与自然呈现出和谐统一的理想状态。正如段义孚所说,“与大自然和大都市这两个端点相比,中间景观看起来更加真实,更富有生活气息,而且更像是生活的本来面目”[9]29。
中间景观作为人类的理想居所,寄托着弗兰肯斯坦对于童年和家宅的温暖回忆。小说中,弗兰肯斯坦的家宅如同巴什拉笔下的鸟巢、贝壳类的寄居空间,是尚且弱小的生物的“一个巨大的摇篮”,“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10]6。同时,巴什拉也指出,“家宅庇护着梦想”[10]5,在家宅中,“激情的存在者酝酿着他的爆发和壮举”[10]9。实际上,家宅所依附的中间景观也具有不稳定性,它“有可能转化为自然,或者更为糟糕的是,不管它有多努力地想保持自己原有的状态,它都将一步步地转化为城市中的人造物”,这样一来,“中间景观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和价值”[9]29。中间景观中的人与自然、乡村与城市的平衡是脆弱的。与人类的美好童年往往是短暂的一样,中间景观的改变迟早会发生,天灾、人祸或城市势力随时会侵扰这种中间景观。
这一时期,弗兰肯斯坦并不欣赏庄园周围的如画美景。他坦称:“当我的同伴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情专心致志地观察事物的华丽外表时,我却在探索事物的成因。”[8]26与伊丽莎白相比,弗兰肯斯坦此时对于自然并没有审美的和情感的依恋,只是将自然当作认知和思维的客体。对于他来说,自然只是一个“谜”,他要“解开它的奥秘”[8]26。虽然他显然意识到了自然(Nature)背后的超自然力量,并称其为 “她(her)”,但他对这种神力并无敬畏之意,而是强烈地渴望“进入大自然这座城堡的层层壁垒,道道屏障”[8]30。此处原文中使用的“洞穿(penetrate)”和“堡垒(citadel)”等词暗含着暴力或战争的手段,他对待自然的侵略性态度也类似于男性对女性的侵犯。青少年时期的弗兰肯斯坦视自己为积极进攻的一方,而自然是被动防卫的一方。在他眼中,自然是无机的、机械的、惰性的物质存在,是他认识并征服的对象。这是一种典型的机械论自然观。
早期弗兰肯斯坦的这种机械自然观中包含着明显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如家宅与世界、内在与外在、自我与他者、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弗兰肯斯坦认为伊丽莎白是属于自己的,与家人和唯一的朋友克莱瓦尔一样,是他“保护、爱和珍惜”的对象。[8]25自然,是与自我和家宅相对立的存在,被弗兰肯斯坦视为进攻和征服的对象,而非珍爱和保护的对象。弗兰肯斯坦对自然表现出求知欲和征服欲,这种欲望促使他走出舒适的家宅内部。即使他母亲刚刚去世,他仍旧因为离开家乡而感到兴奋,称“我年纪轻轻的,若久居一处,把自己禁锢起来,那可真叫人难以忍受”[8]36。他受到了城市所代表的文明与知识的吸引,急迫地希望去大学学习征服自然的本领,渴望尽快实现他征服自然的雄心。
三、城市怪诞空间:机械自然观解体
弗兰肯斯坦十七岁时前往位于巴伐利亚的因戈尔施塔特大学读书。他的命运在此地发生了重要转变。来到这座城市后,弗兰肯斯坦看到的第一座建筑是“高耸的白色尖塔”[8]36,即因戈尔施塔特市久负盛名的圣母玛利亚教堂。这是一座典型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对于19世纪多数英国人来说,天主教堂象征着罪恶、黑暗、怪诞和神秘。城中的因戈尔施塔特大学始建于1472年,曾久负盛名,但在1800年被关停。在18世纪,这里有欧洲领先的医学院,配备有当时最先进的解剖学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和草药园。这里是弗兰肯斯坦探究生命奥秘的理想学堂。除了是科学圣地,这所大学也是神秘组织光明会(Order of the Illuminati)的诞生地。该组织的创始人亚当·魏萨普(Adam Weishaupt)是这座大学的法学教授。光明会视天主教会为敌人,崇尚科学,将撒旦视为“光明的使者”——偷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这一点与《弗兰肯斯坦》的子标题《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暗相呼应。玛丽·雪莱选择因戈尔施塔特大学这处场所,正是因为这一地理空间将科学与迷狂、理性与非理性、崇高与怪诞、光明与黑暗等特质融为一体。这些特质显然对弗兰肯斯坦的心智带来了影响,促使其走向悲剧。
在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求学期间,弗兰肯斯坦在一处套房里独居了六年。与他人、与自然隔绝的城市生活,强化了他征服自然的偏执心理。弗兰肯斯坦将住宅的阁楼打造成他的实验室,“那是一间斗室,与其它房间隔着一条长廊和楼梯”[8]46。这是一处典型的哥特式怪诞空间:密闭阴森,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罪恶和阴谋。弗兰肯斯坦白天闭门不出,夜晚涉足墓穴、藏尸间、屠宰场等地,寻找制造新人类的材料。他在阁楼里藏着各种奇异的化学实验器具和用于解剖的人类或动物的尸体。在这样一处密闭空间里,弗兰肯斯坦与自然完全隔绝且对立。弗兰肯斯坦被征服自然的执念所控制,处于近乎疯魔的状态中,将原本理性的科学研究推向非理性的极端。在此期间,他对自然美景毫不关注,“大地原野从未赐予人们如此丰盈的收获,葡萄的收成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然而,我对大自然的魅力视而不见,对周围的景致无动于衷;出于同样的心情,我把远方阔别已久的亲朋好友也忘得一干二净”[8]46。人与自然的隔绝,往往会导致与他人、与本真自我的隔绝。对知识和智性的极端追求,使弗兰肯斯坦忽视了四季的变迁与家人的关心,也使他无视自己作为身体性存在对食物、健康和情感的本能需求。他以这种极端手段所制造的新物种,最终颠覆了他对自然的原本理解。
在这个怪诞的空间中,弗兰肯斯坦按计划制造出了新物种,但又将其抛弃。他自我辩护称是因为新物种的面容过于丑陋骇人。事实上,弗兰肯斯坦无法接受的并非只是外形。丑陋和畸形背后是怪物身份的不确定性。怪物的身体既有人的躯干,也有动物的内脏或器官,是人与动物的杂糅,打破了人与非人的界限。蒂莫西·莫顿指出 :“它(怪物)是‘自然的’,它并不是人类,同时,它又是‘非自然的’,因它不符合人对自然物的期待,是人为制造的。”[1]146-147怪物作为人造人,既不是人,又不是自然物,不符合对立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任何一方,处于二者之间的混杂的、模糊的阈限空间。它呈现出一种进化论者所提出的畸形(monstrosity)状态。这个畸形的怪物打破了物种的界限,造成了人对自身身份的怀疑。这个怪物客观上粉碎了他原本保有的机械自然观,使他意识到自然的偶然性、复杂性和不可控制性,瓦解了他对人与非人之间的等级秩序的坚守。
怪物虽丑陋,但将人类的情感、智力、体能等各项机能强化,俨然是能力被技术强化的“超人类”(transhuman)。怪物称自己天性良善,具有丰富的情感、理性、智性和自制力,进一步瓦解了人类对于自身伦理意识的优越感。同时,它还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对于自然界的万物具有仁善之心,正如批评家卡罗尔·亚当斯(Carol J. Adams)所说,“怪物的素食主义确认了它内在的、原初的善意”[11]149。这一素食行为,一方面表明它将自己与自然结成共同体;另一方面,说明它确证自己的善的良知,希望被人类接纳。怪物俨然比人类更为进化。这个新物种面目可憎,具有可怕的力量,无法预料,难以约束,似乎昭示着自然所包含的野性和原始力量。弗兰肯斯坦将创造物称为“魔鬼(devil)”“怪物(monster)”“恶魔(demon)”“妖怪(spectre)”等,既表现出他的厌恶之情,又表现出他的恐惧。弗兰肯斯坦根本无力驾驭它释放出来的自然的可怕力量。这也给弗兰肯斯坦带来了认知上的挫败感。
弗兰肯斯坦渴望通过科学技术控制自然,却发现自己所获得的一点线索不过是自然真相的冰山一角,背后的深渊仍旧无从探知。他抛弃怪物,暗含着俯视深渊时的畏惧和退却。人并无能力和资格充当自然的管理者,这种意识最终瓦解了弗兰肯斯坦旧有的机械自然观。但此时的弗兰肯斯坦内心仍旧在挣扎。他选择逃避也是为了保存他作为人类的最后的一丝优越感,他对怪物的畏惧同时也带有对于启蒙者提出的自然秩序问题的逃避。弗兰肯斯坦自然观最终的改变发生在他走出城市、回归自然之后。
四、荒野空间:有机整体自然观的确立
弗兰肯斯坦在返回家乡后,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在家中获得温暖与安慰,唯一能使他灵魂稍获平静的唯有险峻的阿尔卑斯山景。在家人被害后,他便开始了注定失败的追捕怪物的旅程。小说的后半部分主要发生在险峻的自然空间中,弗兰肯斯坦的足迹遍及蛮荒的高山、大海、沙漠和北极等地,对于原始自然的切身体验,真正改变了他对自然的认知,促使他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18世纪之前,森林、山岳与雪山在西方代表着野蛮、黑暗与上帝的惩戒。工业革命的兴起带来了对自然的新认识,自然获得了审美功能,全欧洲范围内兴起了探访高山峡谷的旅游热。玛丽·雪莱在创作《弗兰肯斯坦》时,正与丈夫雪莱和诗人拜伦一道旅居在阿尔卑斯山下。勃兰兑斯评价浪漫主义者时说:“当自然对人们有用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它美;他们发现自然在蛮荒状态中,或者当它在他们身上引起模糊的恐怖感的时候,才是最美的。”[12]139小说的第九章和第十章详细记述了弗兰肯斯坦从沙慕尼峡谷攀登到山顶的漫游历程。小说详细描绘了阿尔卑斯山巍峨冷峻的自然景观,包括冷峻森严的峡谷、陡峭险峻的山峰、突兀奇崛的山岩、响彻山间的波涛怒吼。这种对于自然的崇高美(sublime)体验影响了弗兰肯斯坦对于自然的认知。
在18世纪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看来,对崇高美的体验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包含着痛感和快感,“惊惧是崇高的最高效果,次要的效果是欣羡和崇敬”[13]13。伯克所说的这种崇高体验主要是以生理和情感反应为基础,表现为“面对自然环境时的被征服感、谦逊感”[14]。小说中,弗兰肯斯坦详陈了在阿尔卑斯山漫游对他产生的影响:“这一派壮丽雄伟的景色给了我能接受的最大安慰,同时荡涤了我心中渺小卑微的念头,使我的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虽然我心中的悲哀尚未消除,但还是有所缓解,我的心情也因此趋于平静。”[8]91雄浑壮阔的崇高之美使他意识到人类的渺小卑微。崇高之美缓解了他的烦恼,但自然带来的慰藉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情感的层面,还触动深层次的心灵和精神。弗兰肯斯坦对于蛮荒的沉浸式体验,带来了更深层次的对宇宙万物的领悟和接纳,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知。
弗兰肯斯坦对人与自然相连接的领悟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启蒙者的机械自然观,转而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者所拥护的有机整体自然观。弗兰肯斯坦在遁入蛮荒自然后,“通过每一次心灵的体验,获得对‘万物的生命’的一次又一次的新的领悟”[15]237。当自然的欣赏者融入到所在环境中时,自然的博大包容便会促使欣赏者全身心地接纳自然带来的各种体验,促使人与自然在情感和精神层面互融互通,使人感受到坚韧、冷峻和忍耐的原始精神力量。这样一来,自然便不会再被看作无生命的或无机的存在。韦勒克曾指出,“所有浪漫主义诗人都把自然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把自然当作类似于人而不是原子的组合”[16]175。浪漫主义者几乎一致反对机械宇宙观,普遍相信自然的有机性和活力性,相信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连接,崇尚回归自然。这种浪漫主义自然观在弗兰肯斯坦后期思想中同样可见。他最终意识到了自然力量对于自己心灵能量的输入,体会到人与自然的相互连接,认识到人的渺小脆弱,并开始反思征服自然这一念头的虚妄。
弗兰肯斯坦的崇高感既包含精神的深度体验,也包含对自然、对所处环境的理性认知,表现出桑德拉·莎普莎提出的“深崇高”美学体验特征。莎普莎提出的“深崇高”体验“既是情感的,也是知性的。它涉及更一般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14]10。它要求人反思其与自然关系,要求人将自然看作自然本身,将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而非对立的主客体。深崇高要求人加深对自然的理性认知,只是认知目的并非为了征服自然为人类服务,而是更好地适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深崇高体验的人眼中的自然,既非惰性的机械,也不是人类情感的投射或显现,而是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界本身。在小说中,弗兰肯斯坦作为科学全才,在欣赏崇高美景时,也密切关注自然的变化,他能够知晓“其中有一种山石非常危险,只要有一丁点声响,哪怕是说话声大一点,也会引起空气的震荡而足以给说话者带来灭顶之灾”[8]92。弗兰肯斯坦融入自然环境中之后,才意识到人只有取得与自然的某种共振,才能更好地适应自然,只有敬畏自然并能够解读自然界发出的各种信息,才能够与自然和平共处。
由浅入深的崇高体验彻底瓦解了弗兰肯斯坦旧有的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他在死亡之前,已彻底转变为一位自然的崇拜者。沃尔顿在信中描述,此时“他(弗兰肯斯坦)尽管心灰意冷,可没有谁比他更能深切地感受大自然的美。那星空、大海,以及这一奇妙地区所展示的每一幅图景,似乎仍能使他的心灵升腾,飞离尘世”[8]19。在最荒芜险恶的荒野中跋涉虽耗尽了他的体力,却似乎治愈了他的心灵。弗兰肯斯坦最终从自然中感到一种神性的力量,称自然的“这一切,显示出一种伟大的力量,似乎欲与无所不能的上帝分庭抗礼”[8]89。他从自然之中体验到了超自然的神圣意志,产生了对于自然的敬畏之心,彻底放弃了将自然视为客体的机械自然观。最终,弗兰肯斯坦在与自然融为一体中获得了灵魂的救赎。当他听到沃尔顿发誓要“征服自然这一人类的顽敌,并使子孙万代成为大自然的主人”[8]17-18时,不禁大哭起来,他意识到他的朋友如果也将自然视为顽敌,最终只有自取灭亡。临终前,弗兰肯斯坦与自然达成和解,也与本真的自我达成了和解,获得了灵魂的平静与救赎。
五、结语
《弗兰肯斯坦》以地理空间为尺度,通过弗兰肯斯坦不同成长时期自然观念的转变,告诉人们:人与自然隔绝将带来悲剧,而回归自然则是对人类本身的救赎。反观当下,机械自然观并未退场,小说中所呈现出的机械自然观与有机自然观的并置和对比,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当下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危机。当现代人对自然的掠夺已经反噬人类自身的身体、心理和精神健康时,我们应当与弗兰肯斯坦一样,重新认识自然,反思自身与自然关系,并切实构建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