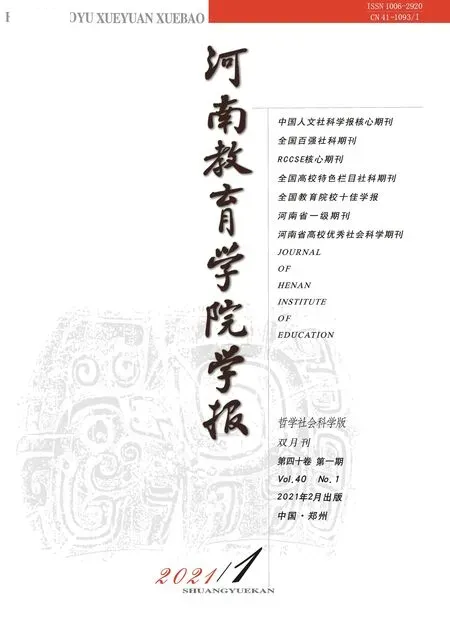《种芹人曹霑画册》八幅图与《红楼梦》之关系探微
张惠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经常用绘画来表现人物。例如,第五回中,《燃藜图》反衬了宝玉对仕途经济的反感,唐寅的《海棠春睡图》暗指秦可卿的奢靡与艳情;第四十回中,秋爽斋里悬挂的米芾的《烟雨图》烘托了探春高雅的情趣;第五十回中,仇英的《双艳图》凸显了宝琴的美貌。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也经常用绘画的手法来描写情节。脂砚斋、畸笏叟在评《红楼梦》过程中一再指出曹雪芹深得绘画的“秘诀”[1]607,称“林黛玉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竟画出《金闺夜坐图》来了”[1]608。曹雪芹在第四十二回中集中展现了自己的画论:对画题、立意、布局、界划、人物、用笔的见解,对画具——画笔、颜料等的熟悉,以及对矾绢、飞色、泥金泥银、出胶等的在行。善于绘画的曹雪芹,在其自作的《种芹人曹霑画册》中,也隐含了不少《红楼梦》的情节和人物元素,可与之对看。
一、《芜菁》隐喻薛宝钗
芜菁是一种较为常见、廉价的蔬菜,乍一看,以此为喻似乎唐突了宝钗。依香草美人的传统文化,宝钗的喻象更接近于她的别号“蘅芜君”中的“蘼芜”。《红楼梦》第十七、十八回中,贾政、宝玉和众清客来到蘅芜苑,但见一株花木也无,只有许多香草。小说通过宝玉之口说出这些香草是杜若蘅芜,其中,蘅芜是两种植物“杜衡”“蘼芜”的简称。“蘼芜”这种香草,在古典诗歌中经常与弃妇联系在一起。例如,“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玉台新咏·古诗八首》其一);“提筐红叶下,度日采蘼芜。掬翠香盈袖,看花忆故夫”(唐·赵嘏《昔昔盐二十首·蘼芜叶复齐》);“蘼芜盈手泣斜晖,闻道邻家夫婿归”(唐·鱼玄机《闺怨》)。宝钗住处的“蘼芜”似乎在暗示她未来成为弃妇的命运。[2]

《谷风》中的妻子全无失德之处,却无端被丈夫抛弃。宝钗也正像芜菁一样,才情、容貌、谈吐、女红、家世,无一不美。她嫁给宝玉后,也无任何失德之处,甚至还秉持“停机之德”,时时以“仕途经济”的“德音”规箴宝玉,却遭受了宝玉离家出走、遁入空门的残酷打击。
我国古代有诗歌将葑菲直接跟弃妇相联系,如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四十四首《绿萝纷葳蕤》:“奈何夭桃色,坐叹葑菲诗。玉颜艳红彩,云发非素丝。君子恩已毕,贱妾将何为。”[6]64诗中的弃妇容貌艳若夭桃,而且《诗经·周南·桃夭》又是歌颂新嫁娘的名篇,故李白此诗似隐含此弃妇并非淫奔之女,而是明媒正娶得到家族认同的女子。正值青春,鬓发如云,绮年玉貌,红颜未老,却无端被弃,色未衰而爱已弛,彷徨无措。《红楼梦》中宝钗的遭遇与之非常相似。《红楼梦》中,林黛玉教香菱学诗时明确提出取法之道,让她认真研读李白、杜甫、王维的诗。所以,曹雪芹对李白之诗一定并不生疏。葑菲和李白弃妇诗的紧密联系,亦可佐证,《芜菁》与成为弃妇的宝钗有一定的关联。
由此,我们可推测曹雪芹对“芜菁”的构想:在表层意义上,用谐音指出宝钗“无情”的一面,她对宝玉并无心灵上的吸引和精神上的共鸣,无法“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在深层意义上,借“葑菲被弃”“中心有违”的引诗暗示她将成为弃妇的命运。
二、《芋艿》暗喻林黛玉
对于第二幅《芋艿》为何暗喻黛玉,沈治钧先生曾经结合第二幅画的题诗“浓阴柳色罩轻纱”做了推演。他认为,由于曹雪芹告诉过闵大章,林黛玉的原型之一是王虞凤,因此闵大章为画册题诗时看到芋艿就题上了王虞凤的《春日闲居》。[7]
笔者认为,在《红楼梦》文本中,曹雪芹已经将黛玉曲折地和“香芋”建立了联系。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中,宝玉因林黛玉才吃了饭就睡午觉,怕她睡出病来,所以编个小耗子偷香芋的故事来替她解闷儿混过困去。小耗子说自己要变成一个香芋混进香芋堆里偷偷搬运,谁知摇身一变却变成一个美貌标致的小姐,围观的众耗子都说变错了,小耗子现形说,“我说你们没见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香玉呢”[1]434。黛玉娇嗔宝玉编派自己,宝玉辩白说是因为闻到黛玉身上的香气想到的故事。实际上,“香”指黛玉袖中幽香,“芋”则谐音了林黛玉的“玉”,其推导方式为:林黛玉→“香玉”→香芋。因此,和《红楼梦》文本对看,《芋艿》含有林黛玉人物元素。
三、《残荷》隐指林黛玉无望的爱情
《红楼梦》第四十回写贾母带着刘姥姥大宴大观园,在园里坐了一次船,众人看到了池中的枯荷,宝玉嫌“破荷叶可恨”,嚷着要把池中的破荷叶拔去。林黛玉却道自己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宝玉立即表示别叫人拔了。这个细节,早期用来形容宝玉对黛玉用情之深,张笑侠先生评价道:“宝玉听了又忙说不叫拔了,真能听黛玉的话。”[8]277亦有学者指出,曹雪芹用李商隐句,却把“留得枯荷听雨声”改成“留得残荷听雨声”,其中大有深意。李商隐本身就经历过创伤深重的爱情悲剧。“枯”的本义是草木枯槁,是植物随着天气变冷自然地凋零。“残”的本义则是“毁坏、破坏”,指因外力而发生改变。雪芹变“枯”为“残”,暗示宝黛爱情可能受到外力破坏,以李商隐其人、其诗暗示林黛玉的爱情只能是无望的爱情。[9]不管所关联的是宝黛的情深还是缘浅,都说明“残荷”在《红楼梦》中是极为重要的意象,曹雪芹念兹在兹,形诸图画。
四、《茄子》借指《红楼梦》中的“茄鲞”
红楼盛馔虽然数以百计,但知名度最高的当数《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中提到的“茄鲞”。其中,凤姐夸耀性地提到了其配料昂贵、工艺繁复的制作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凤姐、刘姥姥和红楼众人都用“茄子”而非拗口的“茄鲞”指称这道菜。[1]937-938
“茄鲞”这道菜是中国菜肴中极为精致的菜品。“茄鲞”反映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精髓,也演绎着中国伦理精神的和谐观、人格平等观。“茄鲞”中,各种食材荤素搭配,每种食材都是平等的,各种原料同时亮相。最后,茄子吸收了其他原料的精华,从低贱而普通的菜变成一道精致的菜肴,这正是中国餐饮“和”文化的体现。[10]“茄鲞”以其化腐朽为神奇的粗菜精做,以及和谐平等的中国伦理精神体现,成为《红楼梦》中最令人难忘,也恐怕是曹雪芹最得意的美馔之一,故以“茄子”曲笔代之。
五、《秋海棠》指海棠诗社,同时暗喻湘云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中,贾芸忽见有白海棠一种,比较珍异,因此特地弄得两盆来孝敬宝玉,适逢探春下笺发愿开诗社,李纨道:“方才我来时,看见他们抬进两盆白海棠来,倒很好,你们何不就咏起他来呢?”[1]843从贾芸所奉书帖我们可知:其一,白海棠是珍贵难得之花;其二,贾芸送花时正值花开,知其为“白色”海棠,而且还是暑热时节。第七十回中,湘云说到起海棠诗社是在秋天,推知此海棠的开花时间在初秋。蔷薇科苹果属的植物中,并不存在秋季开白花的海棠,扩大到蔷薇科木瓜属,虽存在开白花的贴梗海棠和倭海棠,但花期在3~5月间,与暑热天气不符。暑热天气又开白花的海棠,就只有秋海棠科秋海棠属的植物了。[11]78-86《红楼梦》中其余各处提到的白海棠实际上都是指秋海棠的白花品种。秋海棠又称八月春、相思草、断肠红,夏秋季开花,花色多为红色,也有白色。传说“昔有妇人,怀人不见。恒洒泪于北墙之下,后洒处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妇面。其叶正绿反红,秋开,名曰断肠花。即今秋海棠也”[12]。
《红楼梦》一书有二十回涉及海棠,但最集中的是在第三十七回。该回中的六首海棠诗,含蓄蕴藉,托物言志,暗喻了书中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探春远嫁,有家难归;宝钗守寡,凄冷孤寂。[13]66宝玉的诗嵌入和他关系最密切的宝钗和黛玉。黛玉的诗也“不脱落自己”[1]847,自认兼梨花和梅花之长,但是只能寂寞独自向黄昏。[14]109
当然,海棠在这里最重要的功能还是暗喻湘云。湘云在《红楼梦》中被比喻成海棠,她抽到的花签画的是海棠,题写的是“香梦沉酣”,“只恐夜深花睡去”,用的是苏轼诗关于海棠花的典故。湘云在海棠诗社举办后来到贾府,填写的两首海棠诗,是海棠诗社压卷之作。众人看一句,惊讶一句,看到了,赞到了,都说,“这个不枉作了海棠诗,真该要起海棠社了”[1]857。
湘云的“海棠诗”是“自况”。在湘云第一首白海棠诗之“自是霜娥偏爱冷”句下,脂砚斋批道:“又不脱自己将来形景。”[1]856可知湘云将来是爱冷的“霜娥”。“白首双星”回目预伏湘云将来像织女,白海棠诗暗示她将来像嫦娥。织女与嫦娥的婚姻同属一个类型,都有丈夫,但又都离开了自己的丈夫!湘云“霁月光风”,“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却蒙受不贞之冤……“幽情欲向嫦娥诉,无奈虚廊夜色昏”,她只好抱着满腔的幽恨,像蜡炬一样滴干最后一滴眼泪,结束自己的生命。[15]117-118由此可见海棠尤其是秋海棠在《红楼梦》中的重要性。
六、《东陵瓜》借指贾府兴衰
有很多学者就《东陵瓜》展开激烈争论。顾斌先生在《贵州图书馆藏〈种芹人曹霑画册〉考释》一文中认为此瓜为“西瓜”,“表达了对自由、闲适生活的向往”[16]。季稚跃先生认为,“《种芹人曹霑画册》中的画作实难恭维,靠它来养家糊口恐有难度”[17]。刘梦溪先生也认为,第六幅图画功低下,题诗水平不高,疑恐非曹雪芹所作:
“种芹人曹霑并题”的第六图,笔墨臃堆鄙俗,无论如何无法与“击石作歌声琅琅”(敦诚《佩刀质酒歌》)而又善画石的雪芹曹子联系起来。而所题之“冷雨寒烟卧碧尘,秋田蔓底摘来新。披图空羡东门味,渴死许多烦热人”诗句,更与写有“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奇句而具有李贺遗风的雪芹诗作相差天壤。[18]
吴佩林、杨仲佑、胡铁岩、邵琳等学者或质疑画中之瓜的形与叶均与西瓜不同,或质疑初秋时北京是否还有西瓜,从而认为“种芹人曹霑”应非曹雪芹。[19]樊志斌先生认为《本草纲目》中记载的北京西瓜成熟时间符合《种芹人曹霑画册》中“秋田”“冷雨寒烟”的描述,但认为不能以画中之瓜是否为西瓜来判断画家是否为曹雪芹,同时提出了此瓜为甜瓜的可能。[19]
拾井磊先生认为,画家未必照着实物完全还原,《种芹人曹霑画册》作者有以东陵瓜寓意归隐田园之意,“种芹人”“东陵瓜”及所绘田园蔬果,都足证《种芹人曹霑画册》作者具有遁世情怀。[20]
笔者认为,《东陵瓜》或借指贾府兴衰。《红楼梦》中的贾家亦如东陵之瓜,其坐落在类似“青门”的帝都,四大家族“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1]81,如同瓜蔓盘根错节,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冠盖云集,辐辏盈门”之时,正如东陵之瓜五色曜日。然而,祸福无门,唯人自召,昔日王侯贵族,呼喇喇似大厦倾倒,最终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有似东陵侯召平沦为布衣。
以曹家家事而论,曹家由包衣奴才入关,到曹寅因母亲是康熙的乳母成为康熙的奶兄弟,而被赋予江宁织造的宠衔,曹家四次接驾,荣宠已极。之后,因亏空无法填补,雍正上台后曹家惨遭抄家。曹家起伏曲线亦如东陵之瓜。
《红楼梦》小说第十八回林黛玉有诗曰:“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黄一农先生指出,第六幅有曹雪芹的题诗:“冷雨寒烟卧碧尘,秋田蔓底摘来新。披图空羡东门味,渴死许多烦热人。”该诗和林黛玉诗的用韵全同。其中的“尘”“新”“人”“频”皆属上平十一真韵。虽然前人之诗亦偶见有韵脚甚至用字均相同者,但这种难得的巧合,有可能说明“种芹人曹霑”与《红楼梦》作者有一定联系。[21]
张志先生不同意黄一农先生的论断。他认为,首先,曹雪芹的诗才不至于仅仅局限于“尘”“新”“人”“频”的上平十一真韵;其次,黛玉此诗是“颂圣”,显然和“种芹人曹霑”要表达的“归隐之情”没有关联;再次,曹雪芹连自己是《红楼梦》作者的身份都不愿在书中明示,又何必用书中的一首诗的韵脚来题写画册曲折地暗示自己是《红楼梦》的作者呢?[22]
笔者认为,《东陵瓜》与曹雪芹关系甚密。其一,曹雪芹诗才不仅于此,那他选了同韵脚岂非更能说明他对此诗念念于心?其二,曹雪芹对《红楼梦》中的情节人物烂熟于心,画册之诗与小说之诗韵脚相同恰恰说明二者有关联。其三,曹雪芹并非有意暗示自己是《红楼梦》的作者。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红楼梦》是他萦绕于心、无时或忘的所思所想。那么,惯以隐喻、写意见长的曹雪芹,在精心结撰一本画册的时候,其所思所感又焉能不有所流泻?
七、《渔翁》暗指“宝玉”
《红楼梦》第四十五回中,宝玉头上戴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黛玉见了,不觉笑道:“那里来的这么个渔翁?”[1]1045宝玉回说是北静王所送,并提出也弄一套给黛玉。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了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那渔婆儿了。”[1]1046-1047黛玉和宝玉说话,不自觉地把“渔翁”与“渔婆”说到一块儿,而引起了自己的后悔与羞涩,但“宝玉却不留心”。确知宝黛命运的脂砚斋,情知宝黛爱情是落了空的幻影,认为黛玉的失言相当于“直说出夫妻来,却又云画的扮的,本是闲谈,却是暗隐不吉之兆”[1]1047。这种“未完成”的悲剧感,横亘在作者甚至评点者心中。
张志先生不同意第七幅图和《红楼梦》的联系:
图中虽有蓑衣,但“老叟”却没戴斗笠,不仅画中人物无法让人联想到宝玉或黛玉形象来,而且小说中这段二人戏称“渔翁”“渔婆”故事的关键道具“大箬笠”在图中也没有出现。[22]
然而,第七幅船侧的确是放着一个斗笠的,而且《画册》本身就是写意画,讲究遗貌取神,以简驭多,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假如事无巨细表现无遗,那就是工笔画而非写意了。正如胡德平先生所言:
《画册》的八幅图属文人没骨写意画,不是工笔画,不是商品画,均属作者抒情自娱的文人画,均反映了“种芹人”的心态与情趣。[23]
八、《峭石与灵芝》指“木石前盟”
以顽石喻宝玉大约没有异议。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对顽石情有独钟,其《坐弘济石壁下及暮而去》云:“我有千里游,爱此一片石。徘徊不能去,川原俄向夕。浮光自容与,天风鼓空碧。露坐闻遥钟,冥心寄飞翮。”[24]卷1《巫峡石歌》:“巫峡石,黝且斓,周老囊中携一片,状如猛士剖余肝。……娲皇采炼古所遗,廉角磨砻用不得。”[24]卷8他认为这一片石也是女娲炼石所遗,却因不被使用而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巫峡石歌》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情节安排和思想内容都有不少启发之处。有朋友曾见他画石寄意,敦敏《题芹圃画石》诗:“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25]40因此,曹雪芹在《画册》之中描绘顽石不足为奇。可是林黛玉明明是“绛珠仙草”,怎么是灵芝呢?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26]472日月所入,象征宇宙的起点与终点,曹雪芹就取此地作为《红楼梦》故事世界的始元。《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又东二百里,曰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瑶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26]171瑶姬是炎帝的第三个女儿,是一个才色兼备的上古巫山女神。传说瑶姬刚到出嫁的年龄,就不幸去世了。她的仙体被葬在巫山上,而她的灵魂则飞到姑瑶山上,化成一棵灵芝仙草,名为瑶草。龚鹏程先生等指出,《红楼梦》处处透露与《山海经》的紧密联结:“绛珠草,据《山海经·中山经》讲,原是天帝之女所化;大荒山无稽崖,则显然出自《山海经》的《大荒经》。 这一切神话原材,经作者变造后,即成为一种全新的神话结构,作者对人生宇宙的体悟和他所欲传达的全部意旨,均借此神话结构来表现。”[27]40在古人的诗赋中,灵芝草被称为灵草、不死药,如班固《西都赋》中说:“于是灵草冬荣,神木丛生。”李善注:“神木、灵草,谓不死药也。”[28]19据说服后可令人长生不死。张衡《西京赋》谈到了它的状貌:“神木灵草,朱实离离。”[28]52-53晋人葛洪《抱朴子》之《仙药》篇列有“诸芝”,分为五类,总称“五芝”:石芝、木芝、草芝、肉芝和菌芝。张华《博物志》也说:“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为车马,中芝人形,下芝六畜形。”[29]88古人深信服食灵芝草可以成仙,《上清明鉴要经》第七部分《老子玉匣中种芝经神仙秘事》中说,在特殊时令、特别地点埋入不同原料,百日之后即可分别收获不同种类的灵芝,服食可以“飞行登仙,上朝天皇”[30]。灵芝草还可以生死人而肉白骨,白素贞现出原形吓死许仙后,为救活他去昆仑山盗仙草,那仙草也是灵芝。
灵芝中有一种果实如李而紫色、垂如贯珠的,名为“紫芝”[31]201。“紫”本“绛”(红)色之一种。西汉初有《紫芝歌》:“晔晔紫芝,可以疗饥。”[32]38陆龟蒙《新沙》:“蓬莱有路教人到,应亦年年税紫芝。”[32]2246《和袭美怀鹿门县名离合》:“田种紫芝餐可寿,春来何事恋江南。”[33]2450曹雪芹祖父曹寅《楝亭集·诗钞》卷七有《栗花歌》咏及紫芝。
绛珠仙草画为灵芝始于清代。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版画第一幅《石头》,画的就是一块顽石之畔,灵芝仙草偎依在旁。道光十二年(1832)双清仙馆刻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插图六十四幅,一人一图,皆为左右结构,右图为人物,左图为相配的花草。其中,黛玉的配图就是“灵芝”,评句是《西厢记》中的“多愁多病身”。[34]虽然清代评点者也多有猜度和偏颇,但他们的中鹄率却颇为不低,而且这些评论也更接近当时的看官听众所理解的原意。[35]前言10-11
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提出:“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36]114
虽然曹雪芹在北京西郊穷困潦倒,但是富贵温柔的金陵生活景象却时常萦绕脑海,所以他在创作《红楼梦》时,才将金陵十二钗作为全书的重要关目。[37]224《种芹人曹霑画册》八幅画作中,《芜菁》《芋艿》《渔翁》分别暗含宝钗、黛玉、宝玉的元素;《残荷》隐指林黛玉无望的爱情;《茄子》代指《红楼梦》中的“茄鲞”;《秋海棠》隐指海棠诗社,又隐喻湘云的命运,尤其以隐喻湘云为主;《东陵瓜》借指贾府兴衰;《峭石与灵芝》隐喻宝黛的木石前盟。综合来看,《种芹人曹霑画册》八幅画作皆与《红楼梦》重要的人物、关键的情节有联系,而尤其以黛玉为主,这和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悲金悼玉”“大厦将倾”的原意也是比较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