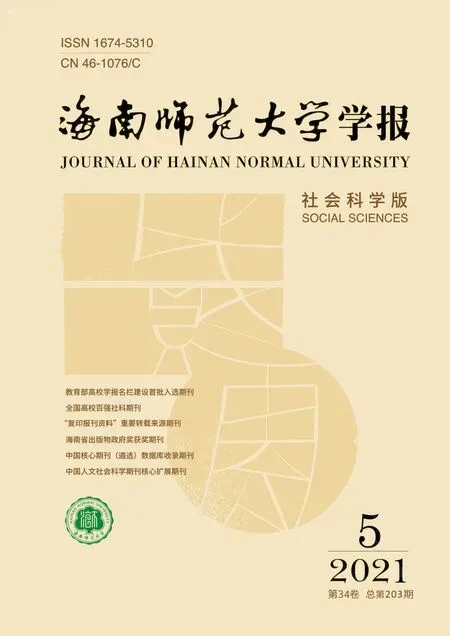笛福小说的内部研究和英国小说的起源
王晓雄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众所周知,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在近花甲之年才开始创作小说,在此之前,他经过商,做过政治间谍,创办过杂志,写过无数小册子。理查蒂(John Richetti)指出笛福从未停止过思考和质疑,其叙事的关键议题包括商业、性别、心理学、政治、宗教、帝国、犯罪等。(1)John Richetti,“Introducti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niel Defoe, ed. John Richetti,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以上议题构成了笛福研究的基本视角,但这些视角如伦德(Roger D. Lund)所说,关心的都是“思想观念上的笛福”(2)Roger D. Lund, “Introduction”, Critical Essays on Daniel Defoe, ed. Roger D. Lund,New York:G.K.Hall&Co,1997, p. 2.。这些在韦勒克看来都是文学的外部研究,虽然这些研究也很重要,但是,它们也要为文学的内部研究即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服务。(3)[美]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徵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76页。故而,对笛福的研究也必然要求我们回到其小说本身。再者,哈蒙德(J. R. Hammond)曾指出,笛福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一个中心位置,有理由成为英国第一位小说家和小说之父,(4)J. R. Hammond,A Defoe Companion, Basingstoke: Macmillian, 1993, p. ix.因此,我们看到笛福名号的第一反应,必定是将他的功绩与小说的建立联系起来。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小说”这一文类究竟是指什么?二、笛福作品为何被称为小说?其特质究竟为何?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必然要求我们将笛福研究放置到英国小说起源的大背景中,对笛福作品做具体的内部研究,以便寻找到其中的“决定性结构”(structure of determination),(5)韦勒克认为我们对艺术品的认知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必须要找寻到其中的一个标准,所谓“决定性结构”。René Wellek,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New York:Penguin Books, 1985,p.152.来确定笛福小说的真正特质。因此,本文将综述各家在英国小说起源问题上的争辩,梳理出两条基本路径,用以概括近年来笛福小说内部研究的展开境况。
一、英国小说起源视域下的笛福研究
如上所述,如今我们总是把笛福称作“小说之父”,但是,考察英国小说起源视域下的笛福研究,便可发现其中仍留有争论的余地。
同出版于1957年的弗莱的《批评的解剖》和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一道构成了此话题的基本观点。弗莱在“散文体虚构作品”一节中区分了小说(novel)和传奇(romance):“小说与传奇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人物刻画抱着不同观念,传奇故事的作者不去努力塑造‘真实的人’,而是将其人物程式化使之扩展为心理原型……小说家则描写人物的性格,其笔下人物都是戴着社会面具的角色……小说家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作为框架。”(6)[加]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53页。据此,弗莱认为传奇是与小说截然不同的虚构形式,应加以区分,在这一点上,瓦特秉持了和弗莱相同的观点,并做了一定的拓展。他指出“小说的基本标准对个人经验而言是真实的——个人经验总是独特的,因此也是新鲜的,因而,小说是一种文化的合乎逻辑的文学工具,在前几个世纪中,它给予了独创性,新奇性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它也因此而定名”(7)[美]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6页。;而古典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史诗的情节,都是以过去的历史或传说为基础,小说因为要传达人类经验的精确印象,所以,耽于任何先定的形式常规都是危险的。(8)[美]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等译,第6页。因此,瓦特认为小说区别于古典文学之“新奇性”即在于拒绝了模式化叙事,主张个人经验的书写。此后,瓦特提出形式现实主义概念,以之为小说形式中固有的前提式的叙述体现,包括特殊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自然逼真的行动序列以及在文字和节奏上尽可能与被描述物对等。具体展开则有:人物名字的具体化,时间的具体化,空间的具体化等。依此标准,瓦特把小说的起源大致限定于1740年前后。在此,笔者认为需要特别注意瓦特提出的新奇性概念,此后,许多学者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点与瓦特形成对话。
如果说瓦特更加强调小说的特质,而直接将之从往昔文类中分离出来,那么戴维斯(Lennard J. Davis)在追溯小说起源的时候,则借用福柯的术语,把虚构作品看做话语(discourse)——构建小说的一整套文本,于是就涵括了传统里排除于小说之外的体裁,包括报章、歌谣等。因此,小说也就不是来源于某一文类,而是肇始于一种一致话语,即新闻/小说话语(news/novel discourse),这一话语与英国印刷技术,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法律条文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戴维斯看来,把小说看作话语不是为了探索因果上的联系或者影响,而是为了寻找某种断裂和转化。(9)Lennard J. Davis, Factual Fictions: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9.近代早期的小说和新闻话语没有太大区别,而在18世纪新出现的小说的真实和虚构的不确定性,才成为小说的特质。(10)Lennard J.Davis,Factual Fictions: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p.51,24.故而,小说来自于“事实和虚构的分离,新闻和小说的分离”,这其实正是戴维斯所说的话语的“断裂”,小说也因而成为一种“含混的形式,一种坚称真实的虚构”。(11)Lennard J. Davis,Factual Fictions: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 p.223, 36.应该说,戴维斯对小说起源的探究,严格地限定于真实和虚构的范畴,是发人深省的。但是,似乎仍存在缺憾之处:首先他排除了传奇等早先文类的影响,因为在他看来,传奇文学根本与新闻/小说话语无涉;第二,戴维斯将小说完全与新闻报业相连,选取的几位作家(笛福、菲尔丁、理查逊等)也都与报业、新闻业密切相关,其中联系的必然性令人生疑。
如果戴维斯的研究仅限于新闻报业及真实问题,稍嫌迮狭的话,那么麦基恩(Michael McKeon)对小说起源的追究可能更为氵项洞浩瀚,也更具野心。他回顾前人的研究,认为弗莱的理论结构过于静态,泯灭了差异,瓦特则忽视了传奇在18世纪小说兴起中的影响,同时过于夸大差异。(12)Michael McKeon,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 1600-1740,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但实际上,在两者之间,麦基恩的方法更近于瓦特,他认为对18世纪小说的理解,要与其他文类结合起来看待,以马克思辩证方法来阐发。他认为小说作为一种简单抽象物(simple abstraction)可用以解释复杂的历史进程。小说能达到如今体例上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是因为它能够极好地展现和解释早期现代经验中的一系列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关于“范畴分类上的不稳定性”问题:其一是文类类型(generic categories),涉及认识论危机,虚构叙述和历史真实的关系,即真理问题(questions of truth);其二是社会类型(social categories),涉及个体道德和社会地位的关系,即美德问题(questions of virtue)。这两个问题的联系是麦基恩用来解决危机的主要方式,其中两者之间的类比性是小说能动性的基础,即小说作为一种文化工具,可以反映和协调这相互依存又对立的因素。(13)Michael McKeon,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1600-1740,p.20.在这两个问题中,分别存在两条对应的序列。认识论序列(真实问题):传奇理想主义—天真经验主义—极端怀疑主义;社会关系序列(美德问题):贵族意识—进步意识—保守意识。在麦基恩看来,两条线索以类同的走向互为表里,成为小说要面对和调解的语境。因“文学模式既结构经验过的历史,也在经验中塑造出自己的形式”(14)Michael McKeon,The Origins oftheEnglishNovel,1600-1740,p.238.,麦基恩便成功地将小说引入宏大的历史背景,借人口统计、科学技术、社会关系、宗教变化等具体议题探析小说的源流。因为麦基恩认为小说在与17世纪叙述形式的辩证关系中才得以展开建构自身,因而,我们可以大致认为,麦基恩将小说的起源置于17世纪晚期。
虽然,麦基恩的论述视野开阔,笔力排奡,但是,从其真实和美德两条序列来看,其所谓历史似乎完全是思想史,小说也完全成为思想观念的载体。当然,在如此浩大的语境中,对小说的解读必然无法做到精细,但是,完全以思想观念指称小说,似乎无法回归到小说本身的特质。
经过麦基恩大开大合的探索之后,迈尔(Robert Mayer)则将焦点收缩到和戴维斯一样,只关注虚构问题。然而,不同于戴维斯对新闻业的执着,也不同于麦基恩在此话题中对经验主义的聚焦,迈尔将小说的起源诉诸历史写作。他用很大篇幅阐释了“培根式历史编纂”的表现特征:“对非凡事物的爱好,依赖于个人记忆和流言,一种功利的算计,一种好辩的风格,为了实际目的可加入一些未经验证的材料,这一切都允许虚构作为历史的一种再现。”(15)Robert Mayer,History and the Early English Novel: Matters of Fact from Bacon to Defo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4.他指出,在追求理性和真实的历史书写之外,还存在一种逆反的类似上述培根式编纂的形式,在这种形式的历史书写中充满了虚构。(16)Robert Mayer,History and the Early English Novel: Matters of Fact from Bacon to Defoe, p.27.因此,历史和虚构之间的对话既是那个时代历史写作的特征,也是英国小说的基本特征。(17)Robert Mayer,History and the Early English Novel: Matters of Fact from Bacon to Defoe,p.140.当年,吉尔顿曾发表对《鲁滨孙飘流记》的诘难,指责笛福罔顾事实而任意虚构,这恰恰体现了迈尔的观点——正是因为笛福,读者才意识到小说是虚构的。(18)Robert Mayer,History and the Early English Novel: Matters of Fact from Bacon to Defoe,p.183, 238-239.所以,迈尔认为笛福的小说重塑了读者的印象,使得虚构的小说话语得以流播,因而,他把小说的起源定为《鲁滨孙飘流记》出版的1719年。
不同于过往论者,西尔(Geoffrey Sill)将英国小说的起源和对激情的治疗联系在一起。他回顾了麦基恩的观点,认为麦基恩的两条序列——真理和美德问题之外,还存在着一条更加根本的序列,即激情问题。他指出:在西方经典中,到处都是对于人类激情的讨论——关于激情的本质,激情引领我们步入的错误以及借以治疗灵魂疾病的叙述策略,而小说的起源就隐含于这些议题中。(19)Geoffrey Sill, The Cure of the Pass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7, 55.就此看来,西尔对小说的判定方法可以汇入瓦特的话语,他事实上将小说看作叙述日常生活的文类,并在此叙述中透视角色的精神状态,从而达到治疗激情的作用。因而,在西尔看来,笛福在小说的起源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原因是他通过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使得对激情的治疗成为英国散文虚构的一个焦点。但是,假如小说就是一种关注激情治疗的叙述文类,那么,它又该如何与过去的虚构文类区分呢?事实上,西尔的论述更加注重激情相关的部分,对于英国小说的起源似乎只是捎带讲述。真正落实到这个问题时,他只是含糊地表示,不能将起源武断地限定在1740年之前,具体应放在哪个节点则没有说明。
综上,关于英国小说起源问题,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三个答案,麦基恩的17世纪晚期,瓦特和戴维斯的18世纪,迈尔的1719年。其中麦基恩、戴维斯、迈尔和西尔都在英国小说起源中给了笛福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迈尔更是直接将《鲁滨孙飘流记》的出版作为小说出现的节点;但是,瓦特认为只有当现实主义的叙述既保持笛福的生动性,又有内在的一致性,小说才能说得到真正的建立,向前迈出这一步的是理查逊,而不是笛福,(20)[美]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等译,第143页。因此,在他看来,笛福不能算是小说之父,而只是小说的一个先驱。所以,瓦特关于英国小说起源问题的答案限定在1740年左右。当然,执着于具体年份并无太大意义,而更应关注论者的划分依据。或可大致总结如下:戴维斯、迈尔关注虚构与真实问题,戴维斯以小说伪装历史,并与新闻话语断裂为大致界限;迈尔以《鲁滨孙飘流记》的出世,确立读者对小说虚构性的期待视野为界限;麦基恩以真理问题和美德问题的纷乱语境的产生为界;瓦特以小说新奇性的出现,即描摹个体经验,并形成形式现实主义美学范式为界。
如上,综述各家在英国小说起源问题上的争辩之后,笔者认为可梳理出两条基本路径:一、麦基恩、戴维斯和迈尔共同建立的虚构性话语;二、瓦特建立的新奇性及形式现实主义话语。这两条路径可互为补充地完成对小说的定义,也可用以概括近年来笛福小说的内部研究的展开境况。
二、笛福小说的虚构性研究
如上所述,戴维斯和迈尔都把虚构性作为小说得以建立的重要因素,而麦基恩的真理问题事实上也是在探讨真实与虚构的问题,小说作为经验主义和怀疑论的调和物,最终宣称创造的并不是历史,而是类历史(history-like),从而规避了怀疑论的诘难。(21)Michael McKeon,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 1600-1740, p. 121.因此,上述三位的理论都在历史真实和虚构间寻找依托,其他论者就此展开的议题也多在两者间作审慎的辨析。
哈伦(Virginia Harlan)详细考察了笛福的叙述,认为需要关注两点:其营造奇闻、冒险、传记逼真效果的手段以及如何从真实和虚构的问题分离出来,成功地写出吸引人的作品。(22)Virginia Harlan, “Defoe’s Narrative Style”, 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Vol. 30, No. 1, 1931, p.57.她指出,笛福通过塑造叙述权威和不断介入叙事甚至给出大量不必要的细节来营造逼真效果;但同时又运用预兆、梦境、迷信来招徕读者,(23)Virginia Harlan,“Defoe’s Narrative Style”,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Vol. 30, No. 1, 1931,p.60-61.这实际上涉及了真实和虚构的问题,营造逼真效果和运用预兆、梦境等非经验主义因素是笛福小说中的矛盾所在,其根本的认识论源起在于经验和宗教的对立。但是,哈伦没有如此挖掘,而是引用笛福自己的话来表示,当他在写作时,他对节奏和风格的统一是有点随意的,他要满足自己在准确、平静、自由和朴素上的追求,而其他的,他并不太在乎。(24)Virginia Harlan,“Defoe’s Narrative Style”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Vol. 30, No. 1, 1931,p.72.可见,笛福对自身文风的不统一是有所意识的,但是,对他所追求的,这四个词语还是略显含糊。或许,我们可以推想笛福的原始意图,他所想要的只是以最能吸引人的方式讲述真实的故事,进而传达道德等领域的理念,而关于小说美学的部分,可能相对没那么关注。(25)这也是瓦特的观点。[美]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等译,第73页。但是,笛福自己的美学意识的强弱,并不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美学发掘。在这一点上,瓦特就显得过于执着作者意图,(26)瓦特曾经反对柯勒律治和伍尔夫对《鲁滨孙飘流记》的解读,认为这超出了笛福的粗糙文体,也是笛福不可能考虑到的。以及,他指出笛福小说本身并无意于讽刺,但是当代读者却多将之当做讽刺之作。[美]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等译,第129-131页,第138页。也许,戴维斯和舍曼(Sandra Sherman)的说法更加令人信服,他们都指出作者笛福在作品中的退场,权威移交给了作品本身,(27)Sandra Sherman,Finance and Fictionality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6,p.9;Lennard J.Davis,Factual Fictions: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p.16.那么,用以解读的文本便成为读者自由出入的嬉戏场所。
回到笛福小说的历史和虚构问题,博德曼(Michael M. Boardman)以历史和虚构的分野来划分笛福的创作时段。他指出,历史是指那些确实发生过的事情,是我们需求知晓并想重新经历的那些永久逝去的瞬间;而小说则营造一个遵循因果律,闭合,完整,充满幻象的,可被我们理解的世界。(28)Michael M.Boardman,Defoe and the Uses of Narrative,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3,p.95.因此,他认为《瘟疫年纪事》全然不是小说,因其处理的是确然的历史事件,而不是可然的虚构世界。(29)Michael M.Boardman,Defoe and the Uses of Narrative, p.156.
当博德曼还在以历史和虚构辨析笛福作品是否为小说的时候,阿尔康(Paul K. Alkon)则关注历史和虚构的互动关系,同时把虚构作为意义增值的手段。他要探究的是叙述的时间背景如何和外部世界的物理时间联系起来,文化的时间概念如何影响小说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期待,以及叙述如何塑造读者经验的时间。(30)Paul K. Alkon, Defoe and Fictional Time,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79, p.2.首先,阿尔康讨论了笛福小说的年代错置(anachronism)问题,指出笛福故意模糊小说开展的具体时间,比如,在《瘟疫年纪事》中,出现的建筑皆是在1665年和1720年两个时空中都存在的;再比如,《罗克珊娜》中的故事也可以同时置于18世纪和查尔斯二世时期。如此,笛福就建立了一种跨越过去和当下的双重时间结构,可以使读者既贴近故事,又产生距离,在进入人物,生出谴责之情时,又抽离出来,产生恐惧和怜悯的效果。(31)Paul K. Alkon,Defoe and Fictional Time, p.52.在虚构如何塑造读者的经验方面,阿尔康指出读者阅读时会实时地感受和记忆,而读者的记忆模式又和笛福的叙述密切相关,笛福通过叙述事件的切断和继续来唤醒读者的记忆。(32)Paul K. Alkon,Defoe and Fictional Time,p.120-121.此后,阿尔康又精辟地分析了《瘟疫年纪事》的速度,认为小说的进程通过“中断时间”来达成,即小说主角叙述的串联从一个主题奔向另一个主题,是非线性时间的,这种随意的节奏真实地描摹出当时世界的无序。(33)Paul K. Alkon,Defoe and Fictional Time,p.183-184, 227.
以上,阿尔康还是将笛福作品的虚构性作为开拓文本意义的手段,而接下来的布林克(André Brink)和梅里特(Robert James Merrett)则将虚构本身作为议题,颇具后现代色彩。布林克认为,《摩尔·弗兰德斯》中,语言成为一个性别陷阱,摩尔通过操控语言的虚构方式,来应对性别、经济和社会制度困境。所以,在他看来,笛福宣称的整个真实的历史,都在摩尔这样谎言连篇的主角的映照下,一步步沦为杜撰的故事。鉴于小说中存在的历史走向故事的冲力,布林克宣称笛福的这个文本已和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小说联系起来。(34)[南非]布林克:《小说的语言和叙事:从塞万提斯到卡尔维诺》,汪洪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4页。梅里特则考察了笛福文本经常出现的语义上的模糊,认为笛福及其主人公都认识到了语言可能会表达相反的意思,于是梅里特借此发挥,主张语言通常会分散和混淆意义,使得叙述出现不断的循环递归。(35)Robert James Merrett,Daniel Defoe: Contrari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3,p.9.因而,我们可以说,布林克和梅里特对笛福小说的解读汇入到了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无法指称自身之外的事物,话语一旦说出即变成谎言——有意识的建构。这种认识其实是对小说虚构性本身的认识,它瓦解了历史文本和虚构文本的对立,并将小说叙述作为人存于此世界的边界,即语言之边界的一个表征。
因此,或许我们可以概括出在虚构性这一条线上的大致走向:近现代小说如笛福作品区别于《堂吉诃德》等虚构故事的特质在于后者直言自己是在虚构,而前者将虚构伪装成历史话语,却又在呈现中暴露出虚构(戴维斯、迈尔、麦基恩);此历史与虚构的分野可用以判定小说的成熟程度(博德曼);小说的虚构能力促进了小说意义的增值(阿尔康);笛福小说对语言问题和叙述问题的指涉已有后现代意味(梅里特、布林克)。
三、笛福小说的新奇性研究
在综述笛福小说的新奇性研究之前,我们需要先回顾一下瓦特的观点。他提出:古典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史诗的情节,都以过去的历史或传说为基础;而小说,其基本标准为对个人经验而言必须是真实的,因为要传达人类经验的精确印象,所以,它不能耽于任何先定的形式常规。所以,瓦特给出形式现实主义的概念,以之为小说叙述之前提,包括特殊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自然逼真的行动序列以及在文字和节奏上尽可能与被描述物对等。瓦特考察了笛福小说后,得出的结论是笛福作品擅长插曲式展现,并未达到人物和情节内在的一致性。因此,他认为英国小说奠基人的称号,应该授予理查逊,而非笛福。故此,我们可以把新奇性这一条线索细分为两部分:一、新奇性问题,包括叙述者之主体的建立和叙述内容向个体独特经验的转变;二、形式现实主义问题,即成熟小说形式的判定问题。
新奇性之叙述主体的建立问题,其实应该关注的是小说的叙述主体和以往虚构叙述人的差别。伯奇(Janet Bertsch)认为小说叙述主体的建立来自于对圣经叙事的模仿,叙述者进行叙述的行为和上帝以语词创造世界是同质的。虽然,此种说法非常动人,但是,却没能在叙述主体上对小说和畴昔的虚构故事作出区分,因为我们同样可以宣称,过去的虚构叙事也一样来自对圣经的模仿。伯奇其后指出,《鲁滨孙飘流记》中对具体细节高度逼真的描写,证明对灵性世界的阐释已经转向对经验世界的观察,现实主义的细节证明了作品摆脱先前文学的程式,成为作者自我证明的必要手段。(36)Janet Bertsch,Storytelling in the Works of Bunyan, Grimmelshausen, Defoe, and Schnabel,Rochester,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4,p.136.现实主义细节的转变,其实是在题材上进行区分,已经进入叙述内容的领域。真正在叙述主体上作出区分的是斯诺(Malinda Snow)。他指出瓦特在论述小说的兴起时忽略了17世纪晚期的科技文写作。斯诺认为,笛福对日常语言的技巧性运用,客观化的描写以及用一个统一的第一人称叙述来组织话语,都是师法于科技文写作的。17世纪末的科技文创作,不像现代科学写作,它更加饶舌和私人化,有着个人化的引用、旁白,甚至偶尔会突然冒出宗教话语;读者可以听到一个明显的声音,它的存在使一系列的实验和发现变得统一。斯诺认为这些作品的特质和笛福小说的特质是相通的,它和小说的兴起密切相关。(37)Malinda Snow,“The Origins of Defoe’s First-Person Narrative Technique: An Overlooked Aspect of the Rise of the Novel”,The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Vol. 6, No. 3, 1976,p.175-176.他还比较了17世纪宗教自传和笛福小说的差别,宣称宗教自传强调神学反思,总是用抽象的主体规避掉一个强有力的个体,但是笛福小说却和科技文写作一样,总是让叙述者和客体世界亲密互动,能让读者清楚地觉知叙述者的喜好、弱点和信念。(38)Malinda Snow,“The Origins of Defoe’s First-Person Narrative Technique: An Overlooked Aspect of the Rise of the Novel”,The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Vol. 6, No. 3, 1976,p.180-181.因此,斯诺的发现其实部分地与迈尔类似。迈尔认为17世纪的历史写作存在着虚构性,历史叙述者并不冷静地保持中立,而是凭借个人喜好添油加醋,表现出极强的个人化风格。显然,斯诺从科技文里追究到的叙述者模型也是如此。因而,我们可以在小说的新奇性中增添叙述主体的个人主义倾向一项,其叙述主体的私人化、个性化与叙述题材的个人经验转向互为表里,标志了现代小说的转变。
如今,我们重新检视瓦特提出的现代小说题材上的新奇性,可以发现其根本基点在于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现实主义对个体经验的重视其实是把古典主义认为卑下的日常题材用严肃形式表现出来,因此,18世纪笛福等人的创举可视为奥尔巴赫所谓“第二次文体革命”(39)奥尔巴赫认为19世纪初在法国形成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美学现象,彻底摆脱了古典主义的文体分用,将日常生活的随意性人物限制在当时环境中,将之作为严肃的,问题型的,甚至是悲剧性描述的对象。奥尔巴赫称此为继圣经叙事之后的第二次文体革命。[德]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52页。的先声。如此回到瓦特的这一论点,我们可以看到理查蒂和尹海俊(Hye-Joon Yoon)都以此为基进行了拓展。理查蒂在其专著中首先强调了小说中个体经验和读者阅读经验的重要性。他指责思想观念批评用统一化的结构破坏了叙述的活力,无法解释笛福叙述中鲜活的生存经验。理查蒂要做的是跟随着叙述的情节和情境,让小说中的人物的生存模式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进而本真地体会到小说的兴起方式和其中自在飞翔的个体。(40)John Richetti, Defoe’ s Narratives: Situations and Structures,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p.20.于是,理查蒂就通过三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来追究主体的动态变化过程,意在表现主体与外部世界此消彼长的复杂关系。应该说,其主体模式细致地规划了瓦特未及深入展开的个体经验,也确实在讲述中纯以个体出发,追求辩证的动态效应。但是,其关系模式的划分,整饬术语的运用,在多大程度上能规避思想观念对小说阅读经验的侵害,似乎也难作定论。不同于理查蒂,在这个问题上,尹海俊将笛福和狄更斯、乔伊斯放在一起讨论。他首先区分了两个概念:经验 (Erfahrung)和体验(Erlebnis)。前者指哲学上通过理性和感性而获取知识的方式,它虽是个人获得的,却能代际相传;后者则是个体转瞬即逝的感受,只存在于个体的意识中,无法与外人共享。(41)Hye-Joon Yoon, Metropolis and Experience: Defoe, Dickens, Joyce, Newcastle-upon-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2, p. 9, 11.尹海俊认为在笛福笔下,个人的体验是占主导的,当城市的金融市场席卷各处的时候,笛福葆有了对个体的关注。而后,尹海俊指出狄更斯更加注重经验,即城市的公众部分,乔伊斯则进行着一种融合。他认为:在乔伊斯那里,城市小说已步入末路,资本、工业的力量已经将人类个体的经验挤压到角落,意义逐渐失落。应该说,尹海俊的论述给予我们一个回溯的视角,在当今时代,回望笛福小说对个体经验的细致把握,是带有浓重的感伤和补偿色彩的。
在此,我们开始论述新奇性的第二部分内容,即形式现实主义问题。瓦特在这个议题上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范式,博德曼和布鲁伊特(David Blewett)都依循这一范式来判定小说的成熟程度。其中,博德曼融合了亚里士多德式的观点,将瓦特的范式打造得更加精细,即认为小说的情节因果链是最基本的,人物性格决定其行动。他指出,小说即是使人物、事件、理念从属于一种经验模式:这一传统的小说包含信仰等一切东西,来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对不稳定状态的解决。(42)Michael M. Boardman,Defoe and the Uses of Narrative, p.36.如此衡量,显然理查逊和奥斯丁更加符合博德曼的标准,所以,无疑地,他认为笛福既不是小说历史中的第一人,也不是一个逝去传统的从业者,而是一个过渡期的虚构创作者。(43)Michael M. Boardman,Defoe and the Uses of Narrative, p.7.如上文所述,他将笛福的《瘟疫年纪事》等看作是历史,与小说无涉,《摩尔·弗兰德斯》《鲁滨孙飘流记》等虽然已是虚构,但缺乏小说的目的论上的“稳固性”,即没有封闭的,向内指涉的,或然地由因果联结的叙述形式。(44)Michael M. Boardman,Defoe and the Uses of Narrative, p.17-18.而笛福只有在《罗克珊娜》的结尾,才勉强达到了这一要求,其插曲式情节整合于小说的设计框架,达到了角色和行动的统一。(45)Michael M. Boardman,Defoe and the Uses of Narrative, p.151.显然,博德曼对小说形式的看法和对笛福的评判与瓦特如出一辙。他们对笛福插曲式叙述的指责,其实是发现了笛福笔下世界的乱序状态,布鲁伊特也是自此出发展开论述的。他认为,笛福小说的主要结构模式是关键词和关键概念的重复,主题的不断复现,意象群的发展和持续的灾难和救恩汇聚而成的范式。(46)David Blewett,Defoe’ s Art of Fic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9, p.30.因此,布鲁伊特认为笛福的小说都存在一种一致性,关注个体需求和社会力量的冲突,希图寻求解决的办法。(47)David Blewett,Defoe’ s Art of Fiction,p.146.他认为,笛福运用“含混和虚伪的语言”来构建小说世界,因而其构建出的世界是“无常和不稳定”的(48)David Blewett,Defoe’ s Art of Fiction,p.149,133.;但说到笛福的叙述主题时,布鲁伊特又认为,笛福作为一个“道德和社会改革者”,在小说中置入了强烈的道德说教主题,部分地消除了小说的不稳定性。(49)David Blewett,Defoe’ s Art of Fiction,p.147.在此,我们似乎能觉察布鲁伊特细微的犹豫,一方面,他感叹笛福召唤来的无序世界的活力;一方面,他又乞灵于情节、人物和道德互相融合的小说范式。在这一点上,福勒(Lincoln B. Faller)的观点颇为有力。他指出,瓦特认为笛福嘲笑并拒绝文学的有序,阐释了生活的无序状态,这自然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我们就很难从笛福的无序的叙述中看到艺术性,比如瓦特认为笛福小说充满漏洞,其达到的生动性和真实性像是不小心做到的,而不像作者有意识的行为,如此,瓦特就否定了笛福作为小说家的艺术自觉;二、大家倾向于认为笛福是一个幼稚的现实主义者,他不能创造一个有序的世界,因为如果世界是无序的,那么,文学的作用应是提供一个补偿性的有序世界,但是,显然这对笛福以及笛福的读者来说相当陌生。(50)Lincoln B. Faller, Crime and Defoe: A New Kind of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42.最终,福勒总结道,瓦特的话应被翻转,笛福嘲弄的不是文学的有序,而是生活本身的有序。显然,福勒并不信仰瓦特、博德曼甚至布鲁伊特遵循的形式现实主义(传统小说)范式,当后面几位努力以此范式来框定、评判笛福的创作的时候,福勒恰恰认为笛福小说的乱序状态才是对现实最为鲜活的模拟。
四、结 语
综上所述,英国小说起源视域下的笛福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两条路径:一、虚构性路径,探讨了小说话语中历史和虚构的对话;二、新奇性路径,探讨了小说在叙述题材和形式上区别于过往虚构文类的特质。如果说,前者是在本体论上界定小说的意义,那么后者则是在方法论上作了界定。笛福作为英国小说兴起时期不可忽视的一位作家,不断地刺激后来者的想象,也是我们研究小说这一文类的必经之路。于是,综述中笛福小说的内部研究的两条展开路径,就不单单是在新语境中对笛福进行意义的再度挖掘,而更加是对小说这一文类全面而深刻的透视。梅里特曾指出,笛福作品总是包含多重视角,我们不能只做一次一劳永逸的解读,而应不断地介入发掘。(51)Robert James Merrett, Daniel Defoe: Contrarian, p.xvii.这是笛福小说的重要特征,即总是矛盾、悖逆的,它不断呼唤我们对其意义进行再探。事实上,笔者认为在上述两条路径的笛福小说研究中,仍然存在着可待发掘的空白:比如,上述学者大都在与历史相对的意义上讨论虚构,但是,虚构还有着另一重含义,即神话或神圣意义上的虚构;比如,虚构和新奇都只能在单一的向度上定义小说,那该如何融合两者?两者的关系又是如何呢?显然,这些问题在综述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此,对笛福小说进行细致的内部研究极有意义。近年,我国的笛福研究有渐渐兴起的迹象,梳理并关注国外学界的研究进展,对促进我国笛福研究的进步必然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