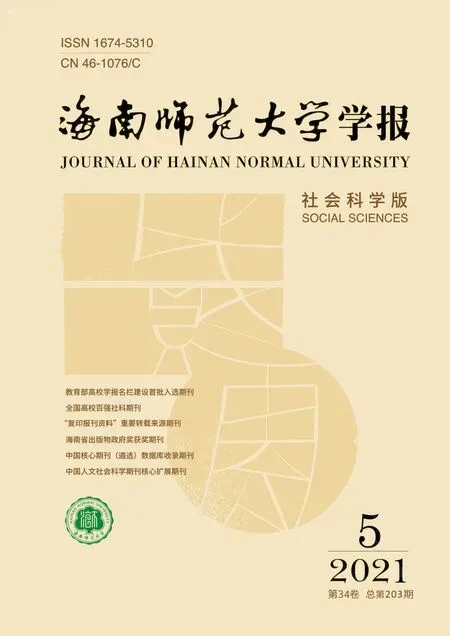国学经验与现代学术的遇合
——论鲁迅的文学史研究
高晓瑞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在目前学界对鲁迅的研究中,鲁迅往往被视作新文化运动的践行者和呐喊者。鲁迅终生致力于改造中国的社会与思想,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和思想启蒙之中,目的在于要把国人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鲁迅被认为是“五四精神”的代表,源于他与传统文化呈现出的决绝姿态。但细察鲁迅的文学生涯,却能发现他始终与国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20世纪10年代他自日本归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潜于搜集金石拓片、辑录校对古籍甚至研究佛学思想之中;20世纪20年代任教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时,则把中国小说史作为授课的内容;20世纪30年代移居上海后,仍坚持校勘《嵇康集》,更遑论鲁迅一生都在购旧书、抄古碑。足以见得,鲁迅始终对传统文化保持了极大的兴趣,并与之密切相关。于是,从鲁迅整体的文学业绩来看,就呈现出思想上的反传统,与学术研究上批判性地继承传统的悖反。因此,要讨论的问题便是,国学传统之于鲁迅到底意味着什么?与他的文学活动和学术尝试又有着什么关系?
一、故土、师承与兴趣:鲁迅的国学经验
鲁迅国学经验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其故乡吴越文化的影响。鲁迅成长的浙东地区是吴越文化的滥觞之地,自先秦以来就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虽与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同属长江流域的南方文化系统,却自有一种独特刚健的风骨。鲁迅生于兹长于兹,对故乡的文化传统亦深有感触,他认为,“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卓然足以自理”(1)鲁迅:《〈越铎〉出世辞》,《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1页。,显示出他对故土文化精神的自豪。与之相应的是,吴越文化在近代的发展和余韵,它们以乡邦文献等形式潜在地影响着鲁迅的文学趣味和研究视角。譬如周作人回忆鲁迅自1910年归国至1925年去职,其间以《新青年》为界,“前期重在辑录研究,下期重在创作”(2)周作人:《关于鲁迅》,《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评价这两个时期的鲁迅,却认为其始终有种“不求闻达”的态度,因为鲁迅喜好抄写和辑录旁人无甚兴趣的书籍,尤其是涉及故里的文献。周作人认为,“鲁迅所最受影响的还是张介侯的《二酉堂丛书》”(3)周作人:《关于鲁迅》,《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20页。,一方面是因为这部书中不仅有乡邦文献,还有刻书字体,是能够唤起后人对故乡的文化记忆,使之不至于“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另一方面,则因“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4)周作人:《关于鲁迅》,《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20页。。由此可见,鲁迅抄写和辑录乡贤文献,实有几重意义,其一是激起了他传承故乡文化精神的使命感;其二则是通过抄写和辑录的体验,极大地训练了鲁迅爬梳历史的能力,这部收藏着汉魏佚文(含古史传、地方志、乡野遗集)的《二酉堂丛书》,从内容的启发到钩沉的方法,都给鲁迅提供了研究的范本,客观上影响了鲁迅《古小说钩沉》的问世。在抄写和辑录之外,鲁迅手迹中还有一份《绍兴八县乡人著作》,“共收入绍兴籍作者所著书78种……从鲁迅后来所购书籍情况看,上述目录中所录,依然是鲁迅购藏书的一大重点。”(5)张杰:《鲁迅杂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0页。显示出鲁迅对故乡传统文化关注视野的扩大。
师承关系同样也影响着鲁迅对国学的态度和观点。在鲁迅少年时期,三味书屋的寿镜吾老先生就对其有巨大的影响。“三味”意属典故,“经如米饭,史如肴馔,子如调味之料。”(6)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2页。但是,寿镜吾对“三味”却有自己的理解,其孙寿宇曾称祖父的解释是“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7)耿传明:《鲁迅与鲁门弟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63-64页。。这种说法证明寿镜吾的教育并不以培养学生科举入仕为目的,而以教学生明理、克己、静心、谨行为上,这对鲁迅成年后厌恶官场、潜心学问的个性有很大影响。在日常学习中,寿老先生亦非常认可鲁迅的资质,“鲁迅在塾,自恃甚高,风度矜贵,从不违反学规,对于同学,从无嬉戏谑浪的事,同学皆敬而畏之。镜吾公执教虽严,对鲁迅从未加以呵责,每称其聪颖过人,品格高贵,自是读书世家子弟”(8)寿洙邻:《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鲁迅回忆录·散编》上册,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选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页。,显示出鲁迅自少年时起,便培养起一套老派读书人的气质。
从鲁迅的文学品味来看,对鲁迅学术观影响更大的当属章太炎。早在1908年,鲁迅就在日本受教于章太炎,听其讲解《说文解字注》《尔雅义疏》《庄子》《楚辞》等。涉及鲁迅与章太炎交集的记载实不多见,唯有许寿裳曾忆及的一段往事,“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鲁迅默默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和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 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9)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5年,第32页。可见鲁迅虽承袭章氏学说,也在其影响下偏爱魏晋文章,但在治学上,却始终有自己的一套观点。除对文学的看法外,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更多的是在文学的对象和视野上。譬如鲁迅在《〈出关〉的“关”》中提到,“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说略》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10)鲁迅:《〈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39页。从此细节可以看出,当鲁迅留学日本接受西方现代文化洗礼时,是章太炎在异乡将他再次引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域,并给他以新的学术视角来重看国学的价值。另外,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提到,“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11)章太炎:《原学》,《国故论衡》,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55页。章氏提出的其实是对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反叛传统、过度追求西化的担忧,章太炎虽主张文化多元,却也在西潮涌动之时,反对全然以西学来评价中国文化。
因此,在鲁迅师承章太炎的经历中,鲁迅就从太炎师处至少习得两种研究国学的思路,其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解,这种观点影响了鲁迅对古典文学的审美取向和基本态度;其二则是文学与学术实为两端,在社会激荡的“五四”时期,更需要有一整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式来取得发展的方向感以及解决中西文化冲突下的困惑。这就需要有对传统文化的新评价标准和随之建立的现代学术范式,而这种范式是不能从西方文化中简单复制的,需要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弊有深厚的了解,在破除儒学中心和标举启蒙主义上亦有新的立场。所以,鲁迅所走的文学道路实是一条思想启蒙与学术重建的艰难之路。
除故乡吴越文化的浸染以及师承关系的影响外,鲁迅的国学经验还来自于他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和实践,其中很重要的是校勘。鲁迅曾花费多年时间校勘《嵇康集》,如鲁迅在1913年10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午后往图书馆寻王佐昌还《易林》,借《嵇康集》一册,是明吴匏庵丛书堂写本。”(12)鲁迅:《癸丑日记·十月一日》,《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1页。吴匏庵即吴宽,是明代学者和藏书家,他的《嵇康集》是各种版本中流传较广的一种。鲁迅得书后迅速抄了一部作底本,如10月15日的日记记载,“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13)鲁迅:《癸丑日记·十月十五日》,《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3页。到10月20日第一次校勘完成,“夜校《嵇康集》毕,作短跋系之。”(14)鲁迅:《癸丑日记·十月二十日》,《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3页。当晚,鲁迅还写下一篇跋语:“右《嵇康集》十卷,从明吴宽丛书堂钞本写出。原钞颇多譌敚,经二三旧校,已可籀读。校者一用墨笔,补阙及改字最多。然删易任心,每每涂去佳字。旧跋谓出吴匏庵手,殆不然矣。二以朱校,一校新,颇谨慎不苟。第所是正,反据俗本。今于原字较佳及义得两通者,仍依原钞,用存其旧。其漫灭不可辨认者,则从校人,可惋惜也。细审此本,似与黄省曾所刻同出一祖。惟黄刻帅意妄改,此本遂得稍稍胜之。然经朱墨校后,则又渐近黄刻。所幸校不甚密,故留遗佳字尚复不少。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癸丑十月二十日周树人灯下记。”(15)鲁迅:《〈嵇康集〉跋》,《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1页。在这篇跋中,鲁迅阐释了所据抄本的基本情况和自己校勘的种种心得,还论述了各版本之间的差异,显示出学术研究的谨严态度。之后数年,鲁迅参考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等刻本,借鉴类书、古注来进行辑校,其间亦为此校本作过序、跋、著录等等,直到1931年11月以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再次校勘《嵇康集》。
除校勘外,鲁迅亦对罗振玉、王国维的“罗王之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从师徒门派的角度看,鲁迅是太炎门生,但他却对将甲骨、金文和新发现的材料与古籍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非常感兴趣,这就是在罗振玉金石学研究基础上,结合王国维研究思路而形成的“罗王之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摇旗呐喊者,鲁迅本应坚守“精神界战士”的身份而远离传统文学;身为章门弟子,亦应与王国维的研究立场保持距离,但由于其学术志趣以及对文学与学术的反思,他仍倾心于“罗王之学”。鲁迅从中汲取的,主要是其研究方式,譬如对新材料的充分运用以及治学的科学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鲁迅对家学和师承的部分背离。除此之外,还有同时代人的成果的影响,比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就对鲁迅的魏晋文学研究意义重大。
重观鲁迅的文学道路,会发现在启蒙者的外衣下,还藏着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鲁迅。“我几乎读过十三经”(16)鲁迅:《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这是鲁迅的自况。鲁迅在幼年受的是最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加之周围的环境和师长的教导,传统经典便构成了鲁迅的文化根基和知识结构,但是家庭的没落又迫使他走上学洋务的道路。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受到了欧风美雨的浸染,外界的冲击使鲁迅的思想发生巨大的改变。等到他回到中国文坛之时,已然成为以笔为刀的“精神界战士”,对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批判。但另一方面,他一直以来的文学积淀与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又使其始终对古籍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因此,鲁迅的国学经验就使其文学业绩呈现出复杂性,即思想上的反传统与学术上继承传统的交织状态。国学对鲁迅而言,既是个人的兴趣也是精神的寄托,而故土、师承以及个人兴趣,则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式乃至研究范式上影响了鲁迅的文学史研究。
二、文学与文化史研究:鲁迅的学术尝试
如前所论,鲁迅的传统文化储备非常精深,对国学研究亦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便始终贯穿在他的文学生命中。鲁迅在公众和文坛同人前的表达与他个人的日常体验构成了一种歧途,其“听将令”的启蒙主义立场与其对传统文化价值意义的反思,就形成了鲁迅思想中极具张力的两端。而他的这种精神焦虑,其实是在考虑新文学从何而来、浸染传统的同时代人又该怎样处理继承和革新的问题。鲁迅便倚靠深厚的国学积淀,并借鉴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从文学和文化史研究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学的由来与发展。
鲁迅学术研究的特点之一,首先在于其采取了朴学的手法。鲁迅逝世后,蔡元培等人曾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名为《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的启事,“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毕生著述,承清季朴学之绪余,奠现代文坛之础石”(17)蔡元培:《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蔡元培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36页。。其中的“朴学之绪余”,就是指鲁迅承袭了包括章太炎在内的清代朴学传统,并以之来进行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研究的架构。鲁迅的研究方式主要来自于其深厚的旧学,在传统研究方式中,他最为熟悉的就是朴学,“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譌敚,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辙亦写出”(18)鲁迅:《〈古小说钩沉〉序》,《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朴学又称考据学,注重资料收集和证据罗列,主要从事辨伪、校勘、注疏、考证等工作。1938年,蔡元培为《鲁迅先生全集》写序时,就已总结过鲁迅的朴学成就,“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象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19)蔡元培:《〈鲁迅全集〉序》,《蔡元培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14页。。具体来看,鲁迅对传统文学的朴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古小说钩沉》等作品中。
细察鲁迅的朴学研究,可看出其中三个着力处。其一是对旧材料的大量的整理、搜集和掌握。譬如《古小说钩沉》的成集,就显示了鲁迅对旧文的珍视。小说一类在古代常被视作小道,是属九家之外的末流,这与其民间、消闲等特点息息相关。明清时期,小说地位虽有提高却未根本改变,这种偏见使得历代小说在流传的过程中流失散佚,鲁迅“惜此旧籍,弥益零落,又虑后此闲暇者尟,爰更比辑,并校定昔人集本,合得如干种”(20)鲁迅:《〈古小说钩沉〉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3页。。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录了自周至隋的散佚小说36种,共计20万余字,相比于其他辑佚的著作,鲁迅自有一套研究方法。鲁迅追求文字的畅达平实,因此,在具体工作中他便把各种版本进行比较,最终订正错漏。譬如在《裴子语林》中,鲁迅记载:“周伯仁在中朝,能饮一斛酒;过江日醉,然未尝饮一斛,以无其对也。后有旧对忽从北来,相得欣然;乃出二斛酒共饮之。既醉,伯仁得睡,睡觉,问共饮者何在,曰:‘西厢。’问:‘得转不?’答:‘不得转。’伯仁曰:‘异事!’使视之,胁腐而死。”(21)鲁迅:《裴子语林》,《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44页。语言生动,情节完整,还在其中用小字加入参校时所用的书籍和原文,比如,“书钞一百四十八引云周伯仁在西彭日饮一斛过江未饮一斛”和“御览四百九十七”(22)鲁迅:《裴子语林》,《鲁迅全集》第8卷,第144页。,意指《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已有相关记载。相较之下,足见鲁迅的《古小说钩沉》不仅搜集了大量相关材料,也在参校中完善了古小说的内容和情节,这也是鲁迅文学研究的第二个着力处,即他要力图清楚地标明每篇佚文的出处。除了辑佚小说专集外,鲁迅最重要的工作是对这些小说在流传过程中,因时代、作者或读者而产生的讹误和失真进行辨伪,最明显就体现在《中国小说史略》之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之中。鲁迅开篇就点明,“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23)鲁迅:《今所见汉人小说》,《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页。。鲁迅的观点鲜明直接,认为现存小说为伪作,此说当属其创见,同时代人或后人多有不同意此观点者,但鲁迅在后文的论证中却有力地为己说寻求依据。比如,“《十洲记》一卷,亦题东方朔撰,记汉武帝闻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等十洲于西王母,乃廷朔问其所有之物名,亦颇仿《山海经》……东方朔虽以滑稽名,然诞谩不至此。”(24)鲁迅:《今所见汉人小说》,《鲁迅全集》第9卷,第35页。鲁迅认为东方朔为人虽诙谐不羁,却也并不至于后世文人所伪饰的那般言行奇怪。除知人论世的考证方式外,鲁迅更多地用到了考察文献时间来定真伪的方法,如《宋元之拟话本》中提到,“《大宋宣和遗事》世多以为宋人作,而文中有吕省元《宣和讲稿》及南儒《咏史诗》,省元南儒皆元代语,则其书或出于元人”(25)鲁迅:《宋元之拟话本》,《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8页。。由此可见,鲁迅的考据和辨伪虽不足以颠覆旧有认识,却在对比和考证中显示出他审慎的态度,在辨伪之后,继续进行版本以及作者的考据,这也是鲁迅朴学研究的第三个着力处。
鲁迅学术研究的第二个特点,在于融汇东西,即借鉴外国文学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自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让鲁迅意识到不仅西方的现代思想能影响和改变中国,而在过去的历史中,各国的文学也在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互相影响,这体现在题材、人物形象等作品的共性上。因此,鲁迅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时,也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究中西文化交流。譬如鲁迅论及六朝的鬼神志怪故事时,提到《续齐谐记》中“阳羡鹅笼”的故事,世人认为此故事过于奇诡,但鲁迅却认为“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26)鲁迅:《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1页。,同时还以《酉阳杂俎》中的故事作对照,意在指出印度文学对中国小说的影响。当然,鲁迅也同样认识到中国文化有向外传播的过程,比如明代小说“《玉娇梨》《平山冷燕》有法文译,又有名《好逑传》者则有法德文译,故在外国特有名,远过于其在中国”(27)鲁迅:《明之人情小说(下)》,《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6页。。或是《游仙窟》,“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28)鲁迅:《唐之传奇文(上)》,《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5页。,强调了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重视和借鉴。在中西互鉴的基础上,鲁迅还把这种比较方法延伸到中国文学研究的内部,用来进行类似情节的梳理。元稹曾作《莺莺传》以记情事,后世文人却争相模仿和续写,“宋赵德麟已取其事作《商调蝶恋花》十阙(见《侯鲭录》),金则有董解园《弦索西厢》,元则有王实甫《西厢记》,关汉卿《续西厢记》,明则有李日华《南西厢记》,陆采《南西厢记》等,其他曰《竟》曰《翻》曰《后》曰《续》者尤繁,至今尚或称道其事”(29)鲁迅:《唐之传奇文(下)》,《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6页。。从中足见各时代的作品中有一脉相承的内容和叙事传统,显示出鲁迅梳理文学史和对材料整体把握的功力。
鲁迅学术研究的第三个特点,则是综合传统文学现象发生的时代、政治、社会来考察一个时期的文学表现。阿英就曾经评价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认为此作“非常看重和社会生活关系的联系”(30)阿英:《关于〈中国小说史略〉》,《小说三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37页。,其实也从侧面证明了鲁迅的文学史著作不仅是考察文学的问题,还要分析一个时期文学之所以如此的内在原因。鲁迅的文学史著作《汉文学史纲要》和《中国小说史略》就体现了鲁迅重历史重梳理的研究思路,例如在评价屈原及《楚辞》《离骚》时就综合了时代、社会、地域等因素来进行考察。鲁迅认为《离骚》的形式文采不同于《诗经》的原因主要有二,“曰时与地”(31)鲁迅:《屈原与宋玉》,《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84页。。一方面是当时游说之风盛行,纵横之士“竞为美辞,以动人主”(32)鲁迅:《屈原与宋玉》,《鲁迅全集》第9卷,第385页。,另一方面则是《离骚》产地与《诗经》不同,“彼有河渭,此则沅湘,彼惟朴樕,此则兰茝;又重巫,浩歌曼舞,足以乐神,盛造歌辞,用于祭祀”(33)鲁迅:《屈原与宋玉》,《鲁迅全集》第9卷,第385页。。从中足以看出,鲁迅在论述楚地文风时,既考察了文人之风与游说之用,又虑及楚地的风土民情和自然环境,综合了历史现实与文学批评来分析楚地文学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又比如讨论小说中“神话与传说”的兴起,鲁迅论道,“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34)鲁迅:《神话与传说》,《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他认为早期神话产生的原因是信仰和敬畏,而后神话演进,原有神话的中心由神转化为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35)鲁迅:《神话与传说》,《鲁迅全集》第9卷,第20页。。从神话与传说的产生和变迁入手,鲁迅梳理出一条因人的认识能力提升而改变文学内容的脉络。
鲁迅后期所作的研究文献《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亦体现出其梳理历史的能力,开篇他即提出,“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36)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3页。。具体论述中,则从魏晋的时代风云出发,以人物为线索,串联起从建安到东晋的文学风貌,同时还穿插文人名士喝酒、吃药与文章创作的关系,将此时期文学评价为“魏晋风度”,显示出鲁迅对魏晋文学的整体把握。除了对传统文学的研究,鲁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文学社团的评价,也体现出这种将文学批评与历史、社会、政治结合起来的独特研究方式。
三、新的两翼:现代文学与现代学术的并立
由此观之,我们能从新文化运动和国学研究中的表现看出鲁迅对国学的不同态度,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抨击国学,一方面他又始终把国学研究当作自己的爱好和志业。所以,需要思考的是,在“批国学”与“张国学”之间,鲁迅到底有着怎样辩证的思考?是否如蔡元培所言,鲁迅虽遵太炎家法,却“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37)蔡元培:《〈鲁迅全集〉序》,《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214页。。因此,需要考察鲁迅如何实现国学经验与现代学术的结合,并回到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立场上来讨论其破立之间的真实动因。
作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者的鲁迅,在批判尊史读经的旧文人时向来是不留余地的。譬如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的演讲上谈道,中国社会虽呼吁天才,但社会风气却摧毁掉了天才诞生的土壤,尤其是近年来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在鲁迅看来,这一批国故倡导者们不仅视影响巨大的新思潮于不顾,反而还以伦理道德的方式来要挟青年,“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38)鲁迅:《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5页。。从中可以看出鲁迅辩证的文学观,他反对的其实不是整理国故本身,而是“老先生”把青年拉去研究国故,让中国从此与世界隔绝。整理国故与倡导西学看似是问题的两端,实际细察鲁迅观点,两者其实并非直接冲突,其关键就在于青年们的选择问题。
从整理国故与师承的关系上看,身为章门弟子的鲁迅实际上是与之关系密切的。“五四”重视整理国故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与“五四”时期倡导的平民文学思潮有关;二是新文学要从民间的传统资源中寻求立足根基。若新文学一直强调西方影响与现实效果,而忽视它存在和衍变的本土资源,那必会成为无源之水。“整理国故”的口号在“五四”时由胡适推出到新文坛,但在他之前,“整理国故”运动的实绩和机构却与章门弟子密切相关。有学者探讨过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为学术研究机构兴起的意义,其认为“国学门的成立,是整理国故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环节”(39)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页。。在国学门之中,大量的精英都是章门弟子,并且也是浙江籍的留日学生,他们进入北大,代替桐城派的遗老成为北大教学与研究的主流人物。他们既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洗礼,又把传到日本的西方思想翻译到中国来。因此,这批知识分子就成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为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做出了巨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胡适从美国归来,他把杜威的实证主义引入中国,在其倡导和实践下,实证主义不再是某种艰深的理论或思想,而成为一种治学的态度和方法。相比于西方著作的译介,这显然更易让人接受。进入北大后,胡适更是示好章门弟子,并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四大纲领之一,放在“研究问题、输入学理”之后,使之成为“再造文明”(40)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1页。的手段,“以期在乾嘉考证学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胡适的这种融合中西的主张,获得大部分同事响应”(41)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324页。。因此,在“整理国故”运动的背后,既有胡适的努力,又隐藏着章太炎及其弟子的影子。他们的合作,使得中国现代学术实现了转折,也有了新的方向。
鲁迅深受其影响,但又对“整理国故”存在着反思。一方面,他亲身实践着对国故的研究和梳理,其实绩甚至早于胡适等人提出口号。按照“整理国故”的定义及内容,鲁迅的辑佚、金石研究皆属其列,但这仅属其研究的一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他采取了融合中西的方式。如对小说史的时间梳理借鉴朴学的方法,按朝代的先后顺序条分缕析、层层铺排;而在概念上,亦借用西方小说的类型研究。因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舍弃了“四大奇书”“才子书”等旧说法,而引入“鬼神志怪”“狭邪小说”“侠义小说”“谴责小说”等概念。他从繁复的传统文学中,找到适应新文学发展规律的古典资源,为“整理国故”运动做出示范,即“五四”时期对待古典资源,既要借用西方学术方法,亦要关照自身文学发展特征。
另一方面,他又非常警惕“五四”文坛突然掀起的这股浪潮,既担心青年被误导,又忧虑商人遗老们会顺势而起,借国学之名“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42)鲁迅:《所谓“国学”》,《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9页。。因此,在为青年推荐必读书目时,鲁迅以“说不出”作为了结,便是怕青年人过多地投身到所谓国学中去,研究国学是遗老们的事,青年人应该向前看。可以看出,鲁迅对待国学实际上是一种矛盾的态度,作为个人的鲁迅需要国学来排遣“寂寞”,而作为新文化运动参与者的鲁迅却要把新文化运动推行下去,尤其是在其根基未稳之时不容有一丝动摇。而在这种矛盾的背后,实则隐藏着鲁迅对新文学建构的思考。
鲁迅在《古书与白话》一文中这样写道:“记得提倡白话那时,受了许多谣诼诬谤,而白话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就有些人改口说:然而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我们自然应该曲谅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悯笑他们这祖传的成法。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这岂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无论什么,在我们的‘古’里竟无不包函了!”(43)鲁迅:《古书与白话》,《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这段话本意是在证明白话文兴起的正确性与必然性,但所述道理则是在告诉读者白话与古文都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再思及鲁迅对白话文学的建构以及古代文学的整理,实可一览鲁迅的现代文学观,那就是他要追本溯源,寻求现代文学的正宗来源,使现代文学能够制度化、经典化、合理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早期的鲁迅钞古碑是为了排遣“寂寞”,而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对国学的研究,则显现出他知己知彼的目的。研究国学传统是为新文学服务,是要用现代或西方的思想来阐释古代文化传统,从而解决新文学从何而来的问题,为其立稳脚跟找到依据。而这个研究国学的过程,就是寻求白话文正宗地位的过程,鲁迅从古到今、从文学到学术、从创作到研究,用现代的观念来阐释传统文化,体现出破与立的新解,最终用文学史研究的新视角新立场来带动现代文学创作和文学启蒙领域的革新。因此,以国学研究为基础的现代学术,与以白话文为基础的现代文学创作,就共同构成了鲁迅理想中新文学的两翼。这也正好回应了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设想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44)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如同有学者论,“从史学观点来检讨传统,则古今中外一切传统没有不变的。文化传统的整体包罗万象,其变化固不待论。”(45)余英时:《传统的变与不变》,《论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93页。意在说明,即使是“五四”时期被新文化倡导者们批判的传统文化,也实有其可取之处,因其在不同时代是不断变化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自有破旧立新的需求,但他们提倡的白话文却依然是传统文学的一部分,“也说明五四文学革命并没有切断与传统的联系,最多与大传统有一定的分离,但却完全背靠了小传统”(46)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4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国学研究其实是在为新文学确立秩序,要为之寻求一个正宗的位置,在大量的用白话文进行创作后,亦要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来审视传统文化。鲁迅亦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寻求着建设新文学的平衡。对于文学史研究,鲁迅体现了拿来主义的原则,立足传统立场又借鉴西方观念。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他对转型期文学变革的深刻思考。鲁迅认为,首先应保护方兴未艾的新文学,但同时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不足,如缺乏文化根基、艺术水平低下等问题亦需纠正。而为新文学找到一条合理的立足与发展的道路,则需要在西方与传统的双重领域内寻求对新文学的新阐释,因此对传统文学的文学史研究也就符合现实需要了。
当然,鲁迅在其文学史撰写过程中亦体现出其独特的“审史”意识,他的文学史研究亦为现代学术的建立提供了一种范式。首先是他擅长在纷繁复杂的材料中整理出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规律,同时还在其中融入自己对文学的品评和看法,筛选每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从而描绘出一个相互联系又独立存在的文学史发展过程。例如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就试图系统地展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脉络,并在其衍变中找寻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因素。他一方面从宏观入手,按时代划分来观照小说主题和内容的变化,另一方面,又从微观出发,以具体的作家、作品、流派来反观这个时代文学的变迁。这样就使其文学史研究能兼顾宏大和细微,显得辩证且深刻。其次,鲁迅的“审史”意识还体现在不拘旧说上。鲁迅对金圣叹的态度就可供一窥,金圣叹自认研究小说有独到见解,鲁迅却认为“清中叶以后的他的名声,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而且经他的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47)鲁迅:《谈金圣叹》,《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42页。,同时他还认为金圣叹之研究小说缺乏独创之说,且其批评还妨碍了原作优点的显现。再次,鲁迅的“审史”意识还表现在他对未受重视的作品及其特点的重新挖掘和解读上。比如对于《游仙窟》,鲁迅就发现其“始以骈俪之语作传奇,前于陈球之《燕山外史》者千载,亦为治文学史者所不能废矣”(48)鲁迅:《〈游仙窟〉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31页。,既看到了《游仙窟》最早以骈体作小说的意义,又从著史的角度提醒后来研究者不能忽略此作的意义。
综上所论,要了解鲁迅真实的文学实践,就不能忽略他的文学史研究,亦不能忽略他对传统文化的辩证态度,革新传统文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看待鲁迅破立之间的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也就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正如他所确信的,保存传统文化精髓的国人,将不仅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更是“开拓者和建设者”(49)鲁迅:《〈引玉集〉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