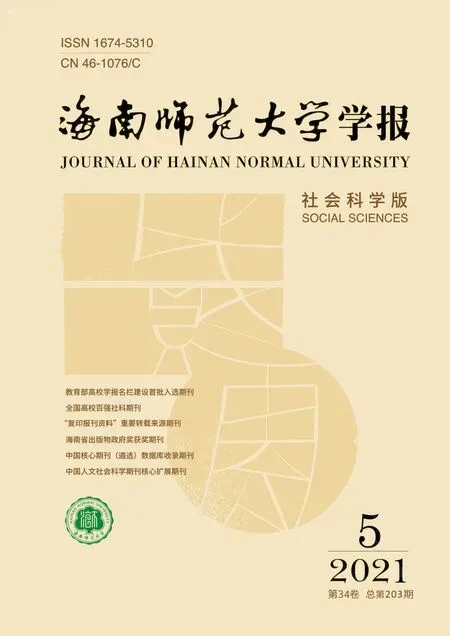在声音的角逐之外
——论鲁迅《离婚》中乡村文化与权力危机的潜在叙事
晏 洁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海南省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海南 海口 571158)
一、引 言
据《鲁迅年谱》记:“(1925年)十一月六日作《离婚》。载十一月二十三日《语丝》周刊第五十四期” 。(1)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53页。这篇小说随后收录于小说集《彷徨》。《彷徨》的篇目顺序根据小说创作时间前后编排,《离婚》是其最后一篇。《离婚》之后虽有《故事新编》延续批判意识、借古讽今,但就创作题材而言,前者可以说是鲁迅以现实主义/乡土题材创作小说的终结之作。《离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鲁迅自己也将《离婚》列为自己满意的作品。然而,正如鲁迅自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所评论的那样,与其他带有强烈启蒙或批判色彩的小说相比,如《狂人日记》《药》等能够“激动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的“忧愤深广”“阴冷”“渺茫”,《离婚》“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2)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46-247页。。因此,自《彷徨》出版后,学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集中在《祝福》《孤独者》《在酒楼上》《伤逝》这类主题明确、思想锋芒更加外露的篇目上,而针对《离婚》的专门评论和研究则相对较少,大多数是在评论鲁迅小说时稍加论及。例如,在《彷徨》出版后不久,董秋芳在其评论中认为《离婚》是“最经济最神奇”的一篇:“离婚的原本事实,都在对话中暗示给读者,全篇便觉灵动,耐人寻味了”(3)董秋芳:《彷徨(续)》(原载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世界日报副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9—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191页。。而当时另一篇评论则认为:“《离婚》一篇用活泼秀拔的笔,写狡猾蛮横的村妇和作威作福的土绅,极能神似。幽默之中含有一种尖酸的讽刺……《离婚》形容乡人的势利,都是对社会不满的一种表示。”(4)苏进:《读鲁迅的〈彷徨〉》(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庸报副刊(天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9—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217页。这些评论基本都是论者阅读的直观感受,而且也只是点到即止,并不深入。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左翼文学的传播和影响,阶级理论也被用于《离婚》的评论上。1935年,李长之在其专著《鲁迅批判》中论及《离婚》时,就以农民与士绅之间的阶级对立来解释爱姑离婚败局的原因:“他们(指爱姑一家:引者注)的锐气完全丧失,简直在威胁与软化之中屈服了”,“农民在经济上的被剥削,在精神上、意志上、人格上,也同样被剥削了,农民已经失掉了自己”(5)李长之:《鲁迅批判》,北新书局,1925年,第76页。。类似的评论延续到了新时期初期,例如,“(《离婚》)形象地启示人们:不推翻封建夫权、族权所赖以维持的政治基础——封建政权,妇女解放是不可能的”(6)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54页;另外,还有吴组缃的《说〈离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与此同时,虽然有的学者对于《离婚》的研究仍带有阶级分析的痕迹,但是已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小说创作本身:“《离婚》的特色在于成功的群体场面:航船中的群体场面和财主厅堂中的群体场面”(7)范伯群、曾鹏:《鲁迅的刻划深切、技巧圆熟之作——论〈肥皂〉和〈离婚〉》,《钟山》1981年第3期。,从这一方面肯定了小说的人物形象刻画与叙事技巧的成熟。近年来,学界对于《离婚》研究的角度与深度均有所增加,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人物形象角度分析爱姑,从而解读鲁迅的启蒙观与妇女观(8)例如秦林芳:《重读鲁迅〈离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张敏:《从〈离婚〉中“爱姑”形象分析鲁迅的妇女观》,《文学界》2012年第6期;杜乐:《鲁迅启蒙视阈下的女性形象:再读〈祝福〉〈离婚〉〈伤逝〉》,《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等论文。;二是较为创新的——从清末民初时期相关婚姻法的角度分析小说中的离婚官司(9)例如贾小瑞、李麒玉:《回到情节本身:鲁迅小说〈离婚〉的法律解读》,《文艺争鸣》2014年第6期。,这一角度使《离婚》的研究视野有所拓宽;三是从社会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研究(10)例如袁红涛:《绅权与中国乡土社会:鲁迅〈离婚〉的一种解读》,《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王本朝:《谁有话语权——〈离婚〉的反讽意味》,《文艺争鸣》2011年第9期;晏洁、宋剑华:《儒变:鲁迅小说中的乡绅叙事》,《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1期等论文。,关注点聚焦在以七大人为首的乡绅群体上,以此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乡绅阶层与文化。
综上所述,无论是直观体验式评论,还是阶级理论视野中所解读出的反封建意味,抑或近年来较为偏重的社会文化视角,都不断地丰富着《离婚》的研究。然而,当我们重新细读文本,却发现小说名为《离婚》,但在通篇文字中却找不到“离婚”二字,文本中的当事者与在场者都没有提过到这两个字,那么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离婚”?另外,在 “离婚”现场,粉墨登场的各方人士形成了一个对话空间和权力空间,乡民与乡绅的声音在此处发生交集、碰撞,在这个复杂场域的背后和看似圆满的结局之外,隐藏着怎样的危机。鲁迅在《离婚》这一现实主义/乡土题材小说的收官之作中究竟想要表达怎样的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地探讨。
二、爱姑的声音:本能而冲动的挑战
小说主人公爱姑是由她及其丈夫、调解判决方这三方所构成的离婚判决场域中的其中一方,也可以说是整个小说中出现的唯一女性(11)虽然小说中有“前舱中的两个老女人也低声哼起佛号来,她们撷着念珠,又都看爱姑,而且互视,努嘴,点头”(参见鲁迅:《离婚》,《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但是从小说整体叙事上来说,这两位老年女性只是起到了一种气氛点缀的功能,未参与到真正的离婚叙事当中。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从文本表面上看,在鲁迅小说乡村女性形象谱系中,爱姑这一形象既不同于尖酸刻薄的“豆腐西施”杨二嫂,也不同于苦命迷惘的祥林嫂和单四嫂子,似乎呈现出某种蒙昧的、未经启蒙的主体意识。正是这种尚未形成理性的主体意识,一方面使爱姑在整个离婚过程的众声喧哗中发出了尽管粗野,但毕竟是自己的声音,而且还是在由男性主导的话语空间中发声较多、声音较大;另一方面也使爱姑在离婚纠纷中始终不甘心、坚持要分出对错,而这也是此事件起起伏伏、悬而未决,持续三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也正因为这种根源于本能的、报复性的、非理性的主体意识,使爱姑在进入离婚调解现场前后表现出一种“瞬间”的冲动。之所以是“瞬间”的冲动,缘于这种本能的报复性的非理性主体意识,与学者汪晖在论述阿Q革命动机时所言的“直觉”类似,“‘直觉’——按照心理学家的分析而言——有着直接性、快速性、跳跃性、个体性、坚信感和或然性等特点:直觉判断是在瞬间作出的综合判断”(12)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1页。。作为一名乡村女性,爱姑只具有乡村生活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伦理道德意识,对于离婚事件的走向是不可能做出严密的、全局性的分析与判断。因此,爱姑的行为出发点在极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她的直觉,而并非是理性的知难而上的勇气。纵观整篇小说,爱姑共有五处较长的说话,这五处发言在全部由男性主导与参与的离婚现场显得相当突兀和尖锐,打破了由乡绅/男性所掌控的话语场域的平衡。这与阿Q以直觉“革命”而成为未庄原有秩序的破坏力量,其本质是相同的。爱姑的五段较长发言分属两个场景,第一段是在船上,其余四段是在慰老爷家的客厅里。由于话语场域的不同,爱姑发言的结果也截然不同,显示出传统乡村多重权力层级在此离婚案中的交汇与博弈。
首先来看爱姑的第一段较长发言。小说是从爱姑与父亲庄木三在新年里坐船前往庞庄继续争论离婚纠纷开始。在船上,乡民们对于爱姑离婚一事议论纷纷,从表面上看八三、蟹壳脸、胖子和汪得贵等乡民与爱姑话语往来密集。八三等人碍于庄木三在乡村中有一定的地位,“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13)鲁迅:《离婚》,《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3页。以下所引此文皆出于此版本,引文后括号内标注页码。,也就是说在此时此刻的船上,庄木三是权威和中心,所以八三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察言观色,以不抵触庄木三父女为准。但爱姑却不并清楚船上乡民的真实想法,错误地以为舆论是站在她这一边的。当八三听说“城里的七大人”也参与离婚调解时,已经预知此次庞庄之行可能的结果,因此八三“顺下眼睛去”,主张“已经把他们的灶都拆掉了,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以及“爱姑回到那边去……也没有什么味儿……”(第149页),建议就此了结。这实际上已经是隐讳的退却和劝告。爱姑对此并不以为然,愤愤发言,自信地认为城里的七大人和乡里的慰老爷是不一样的。爱姑之所以如此在乎孰是孰非,据她自己所言是“赌气”,但“赌气”背后的原因是其被丈夫抛弃后,爱姑本人及娘家在乡村里的颜面受到了损失,于是爱姑一定要通过乡绅评判对错,从而在社会舆论上获得支持和胜利,即“赌气”之后的“出气”。固执己见的意气之争让爱姑未能理解八三的话里之意,反驳了八三的意见。庄木三在船上的地位优势,使爱姑的声音得到了她想要的认同和回应。胖子和汪得贵听出了爱姑的想法,见风使舵地恭维爱姑的想法是对的,即使蟹壳脸提醒爱姑夫家去年年底给慰老爷送了一桌酒席,汪得贵还是故意迎合爱姑:“他们知书识理的人是专门替人家说公道话的……”(第150页),爱姑的盲目加上船上乡民的话语“支持”,使她在之前只要求判断对错之外,又加上了“将来怎样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老畜生’‘小畜生’,全都走投无路”(第151页)的想法。可见被本能支配的爱姑是极易轻信和被蛊惑的。
爱姑的第二至五段较长发言都发生在慰老爷家的客厅里。爱姑在慰老爷家门口看到了四只乌篷船,知道城里的七大人已到慰老爷家中,原来在船上的自信开始有所动摇,但她想起汪得贵所说的“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使她再次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不知怎的总觉得他其实和蔼近人,并不如先前自己所揣测那样的可怕。”(第153页)此处的用语是“总觉得”,事实上,爱姑的“总觉得”是没有根据可言的,完全就是自己做的符合自己意愿的想象而已。这种直觉促使爱姑冲动地在慰老爷家客厅急切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急于得到想象中七大人的支持,达到让自己出气、让夫家“家败人亡”的目的。但是,慰老爷家客厅的权力层级已不是庄木三在乡间的地位所企及的了,此时的权力中心和话语权已经转移到了七大人身上,爱姑的发言受到了压制。
爱姑在客厅里的前两段发言是按照自己既定的想法,首先控诉夫家对她的无理,以期得到乡绅们的同情,从而做出她想要的判断。但事与愿违,她的话很快就被慰老爷和七大人分别打断,周围舆论附和的也是七大人,爱姑的直觉开始受挫:“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慰老爷是原本帮他们的,七大人又不可靠”。(第155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同样使用的是“觉得”,此处的“觉得”对之前的“总觉得”构成了否定。虽然爱姑的直觉发生了变化,但是在没有彻底碰壁之前,她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紧接着,她的第四、五段发言就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作为受害者来控诉丈夫出轨弃妻,而成了单纯的不登大雅之堂的谩骂。第四段发言是爱姑在感到七大人的威严而有所畏惧后开始的,她开始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承认了自己和父亲的无知——“粗人,什么也不知道”,进而口不择言地唾骂自己的丈夫和公公是“小畜生”和“老畜生”(第155页)。对于以“孝”为先的传统乡土社会来说,爱姑在众乡绅面前这样辱骂夫家,显然是犯了大忌,其丈夫趁机以此作为攻击其在夫家也如此不孝不敬,以证明自己弃妻是有理的。爱姑此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被丈夫的辩解激怒后,她的第五段发言把说理完全变成了与丈夫之间的对骂,“回转脸去大声说”更加不堪的话语,好象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场合,以及自己此行的目的,将自己不符合传统乡村女性道德规范的那一面完全暴露在众乡绅面前,坐实了其丈夫的告状。从这一点来看,爱姑的失败早已隐藏在其看似强势有理的发言之中。
在慰老爷家的客厅——这个由男性/乡绅为主导的权力场域中,毫无疑问,爱姑的声音显得突兀与刺耳,与这个充斥着男性声音的场域格格不入,打破了某种既定的权力平衡,但这只是暂时的。从表面上似乎可以把爱姑这些行为解读为敢于挑战乡绅威权,但是爱姑的这些发言是出于其盲目的直觉,她将“觉得”当作了真实和发言的根据,对于所处的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当爱姑的发言得不到支持的回应,屡屡碰壁后,逐渐气急败坏的情绪很快使她从讲理变成了粗俗的无理取闹。因此,当源自直觉的冲动受挫之后,爱姑立即失去了继续挑战的信心。在第五段较长发言之后,爱姑的声音陡然低了下去:“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她的话虽然微细如丝……”(第156页),紧接着,爱姑就此陷入了无声状态,直到最后只说了两句表达接受现实后的道别。
爱姑的无声使这个因离婚而暂时形成的权力场域重新恢复了平衡,“全客厅顿然见得一团和气了”(第157页)。她的败退使其父亲、慰老爷以及夫家如释重负,开始有条不紊地活跃起来,而这恰好说明了爱姑的直觉只是她自己的一厢情愿,她的冲动始终还是无意识的。在她的直觉之外,是乡绅、其父亲和夫家早已预谋好的布局。学者史书美在总结“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于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看法时,正是将中国的“直觉的”与西方的“理性的”(14)[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2页。相对,而这两者也是传统/落后与现代/先进的对立。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爱姑从行为上比祥林嫂、单四嫂子等女性多了张扬、自主的意味,但是在这看似张扬、自主的行为背后则依然未能摆脱非理性的支配。因此,她们从本质上是一样的。也由于此,爱姑的发声根本不具备能够撬动她所处的权力场域的力量,她始终是“胡里胡涂的”(第155页),正如同阿Q“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15)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39页。的“革命”,而暂时的得势也无法改变“从中兴到末路”的结局,爱姑同样也不可能改变乡绅/男性所主导的离婚过程及其结果。
另一方面,爱姑无谓的吵闹虽然没有撼动这个权力场域,也无力改变这个既定结果,但是无论如何,爱姑的行为对乡绅的权威是一种冒犯,犹如一潭死水尽管泛起微澜后又再度恢复平静,也是一种触动。这意味着乡绅在民间日常事务上的权威性正在逐渐减弱,以至于一个普通的乡村女性也可以在乡绅面前大声申诉,而一旁的男性却哑口无言。例如,爱姑就很看不起当地乡绅慰老爷,“她是不放在眼里的,见过两回,不过是一个团头团脑的矮子:这种人本地就很多,无非脸色比他紫黑些”。(第151页)慰老爷失去了权威性,因此他的调解方案,爱姑也就不会接受,这也是前者无力解决后者的离婚纠纷而不得不将城里的七大人请到庞庄主持离婚的理由。七大人就一定可以让爱姑心服口服地接受离婚调解吗?显然乡绅们还是不确定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在围绕这一离婚纠纷周围,乡绅/男性需要如何运作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三、无声的妥协:爱姑父亲与夫家的博弈
无论是在去庞庄的船上,还是在慰老爷家客厅的离婚现场,从视觉和听觉的角度来看,爱姑都处于中心和焦点的位置,其他的男性则退到了附和与次要位置,直到七大人通过发声,与爱姑形成对峙,进而替代爱姑成为叙事中心,但即便如此,七大人成为离婚场域的中心也是从爱姑的视角来观看的。而爱姑的父亲、丈夫及公公退到了叙事边缘,只有寥寥几语和最后退场时的数钱、换帖。可以说,他们处在文本的缝隙之处,似乎并无可阐释的必要。但是,从庄木三、爱姑丈夫和公公在离婚现场近乎沉默的行动来看,双方早已暗地里达到了妥协和默契,实际上将这一离婚纠纷的真正主角爱姑排除在外了,而对此爱姑并不知情。对于爱姑来说,庄木三的行为不啻为一种欺骗。
首先来看庄木三。从庄木三父女一登船,船上乡民纷纷主动打招呼,“其中还有几个人捏着拳头打拱”,立即“空出四人的坐位”(第148页)来看,庄木三在本村一带是有一定社会地位:“这里沿海三六十八村,谁不知道(庄木三)?”(第149页)但小说很快表明了其社会地位的获得应该源于除文化地位之外的其他原因。此处有一细节,即小说对庄木三外貌的描写:“紫糖色的脸上原有许多皱纹”(第148页)。在《故乡》里,少年闰土是“紫色的圆脸”,中年闰土则是“先前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16)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3-506页。。这种紫色或灰黄色的脸上嵌着深而多的皱纹是常年身处户外,受紫外线和海风影响的浙东乡民所特有的。另外,爱姑之所以对慰老爷不以为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慰老爷的脸色也是紫黑的,只是程度稍轻,本村很多人“无非就是脸色比他紫黑些”(第151页)而已。庄木三也同样不把慰老爷放在眼里,后者尽管说和了几次,但庄木三“都不依”,并且还认为“这倒没有什么”(第149页)。脸色深浅在此地是一种外在显性的身份标识,爱姑正是据此来判断其社会地位和权威,同时,这也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经验:真正地位高的乡绅是居于城内和常处室内的,不受浙东乡下劳作中日晒和海风的侵蚀,脸上的皮肤及颜色自然应是细嫩和浅色的。基于这个直觉判断,爱姑才对七大人参与的结果产生了误判。所以,小说对于庄木三外貌的描写表明了他在本村虽然确实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可能是因为经济地位,也有可能是因为家中人多势众(有六个儿子),但这里面并不包含文化地位,也就没有由此带来的权威性地位。
3月28日整地,清除枯枝杂草,做到地平、土碎、无根茬、无残膜。4月1日铺膜。播前种子用清水浸泡6~8 h让其充分吸水,保证出苗。播种期试验分别于5月1日、5月11日、5月21日和6月4日定苗。密度试验均为5月1日定苗,拔除病弱苗或过大过小株,每穴保留1株。整个生育期中耕除草3次,第1次4月25日,第2次6月8日,第3次6月28日,结合中耕培土防止倒伏。播种前覆膜时施复合肥(12-18-15)300 kg/hm2,配施尿素 150 kg/hm2,浇头水时追施尿素150 kg/hm2,施肥量及施肥比例参照贾洪涛等[6]研究结果。
在确定了庄木三的身份之后,再来看他在进入离婚现场的权力场域前后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上船后,八三询问此次庞庄之行是否仍旧为爱姑的事,庄木三充满烦躁地回答流露出他此行的目的和爱姑已然不同——尽快地结束,不愿意再和爱姑夫家闹下去了。因此,当爱姑对汪得贵埋怨:“连爹也看得赔贴的钱有点头昏眼热了……”(第150页)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暗示在此行之前庄木三已有所妥协。而这一次庄木三父女再去慰老爷家解决此事与前几次有不同的因素,即比本地乡绅更具权威的城里的七大人来了,这对庄木三有所震慑,行为上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而庄木三在慰老爷家客厅里的表现也印证了这一点。庄木三对慰老爷的询问只简短回答了“是的”“他们没有工夫”(第153页),便仿佛成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旁观者,再也没有发出声音,以至于爱姑都很奇怪,“平时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的自己的父亲,为什么在这里竟说不出话”(第153页)。庄木三为何会完全无声,其原因有二:一是,反映了其在基层乡民中的地位和声望在这个由乡绅主导的离婚权力场域中是失效的,不会对离婚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二是,当爱姑终于无奈地表示同意听从七大人的吩咐后,庄木三仍然没有说话,但是却迅速行动起来:拿出了早就预备好的红绿帖,立即开始数之前已放在茶几上的赔钱。这两个连贯的动作,充分表明了现在这个离婚结果,庄木三已预先知情和同意。
再来看爱姑丈夫家,即施家父子两人在这个离婚权力场域的行为表现。施家父子直接在慰老爷家客厅出场,小说是从爱姑的视角来描写他们的:“只见她后面,紧挨着门旁的墙壁,正站着‘老畜生’和‘小畜生’。虽然只一瞥,但较之半年前偶然看见的时候,分明都苍老了”。(第152页)施家父子驯服地站在一旁,也是无语状态,对于爱姑的申辩不置可否。在整个离婚调解过程中,施家父子只有唯一的一次发声,即在爱姑大骂施家父子“老畜生”“小畜生”时。爱姑丈夫的这一次“忽然说话”(第155页)是抓住机会向七大人表明,在这场离婚纠纷中,自己并不是完全过错的一方,即使有错,也是因为爱姑在夫家太过泼辣,对长辈不孝、对丈夫不敬造成的,夫家才是这场离婚案中弱势的一方。爱姑丈夫的辩驳引发了爱姑最后一次更为粗俗的咒骂,反而向在场的观众证明了前者所言正确。这不能不说爱姑丈夫还是很有心计的,他非常熟悉爱姑的性格,在关键时刻的发声实际上是进一步置爱姑于不利的境地。在此之后,施家父子一直无声,对于七大人最后的裁决也没有任何异议,和庄木三非常有默契地交换了事先准备好的红绿帖。这一桩持续了三年的离婚案就此了结,这个结果显然是庄木三和施家父子都想要的:“大家的腰骨都似乎直得多,原先收紧着的脸相也宽懈下来,全客厅顿然见得一团和气了。”(第157页)
从表面上来看,庄木三和施家父子在离婚权力场域的表现都是几乎无声的,即使有短促的发言,也并没有对大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整个过程中,他们都是一种服从权威的姿态,没有对慰老爷和七大人的说话表示过任何反对意见。但是反过来看,沉默无语恰好说明了他们无需再争辩发声,因为庄木三和施家父子在场外已经对赔偿解决达成了一致。而爱姑是唯一不知情的,所以她才在奇怪为何“爹不说话,兄弟不敢来”(第155页)的同时,仍然孤注一掷地在离婚现场强烈地表达宁可双方家败人亡,也要分个是非曲直的决心。很显然,爱姑这个两败俱伤的想法损害的不仅是施家,还有庄家自己。庄木三和施家父子都不可能仅仅为了一个对错之分而没完没了闹下去,代价实在太大:一方面,对于庄家来说,庄木三已经带着六个儿子强势地拆了施家的灶,此事已经人尽皆知,让施家受了侮辱,但是施家宁可要寡妇也不要爱姑,这也使庄家颜面尽失;另一方面,对于施家来说,爱姑丈夫姘寡妇在当地民风中也并不那么光彩,灶台也被亲家拆了,这是在乡间舆论中的双重受辱。也就是说,庄、施两家经历了三年的吵闹、讨价还价、各不相让,双方纠缠在这个离婚官司里,不论最后谁对谁错,都已筋疲力尽。以至于施家在去年年底为了促成此事的快速解决而“送给慰老爷一桌酒席”(第150页);爱姑其实也误会了庄木三,以为父亲之前看到赔偿的钱款而“头昏脑热”(第150页),而实际上是庄木三为了早点结束这桩旷日持久又并不体面的离婚纠纷,已经不在乎赔偿多少了,也由于此,庄木三在听到爱姑这样埋怨他时,低声骂了一句:“你这妈的!”(第150页)这也可以从离婚时慰老爷从庄木三数的洋钱里拿出一叠来交还给施家可以得到证明——可见施家担心庄家可能要求更多的赔款而预先准备了超出90元的赔款。然而,庄木三并没有对90元的赔款提出任何异议,干脆利落地接受了这个数字。
至此,庄木三与施家父子之间三年来为了颜面、为了对错、为了金钱的离婚博弈终于以双方共同的退让而画上句号,而这个过程中的双方心理变化并没有通过文本叙事明确地描写出来。这也正是《离婚》叙事策略的巧妙之处:一是,庄木三是爱姑的父亲,理应无条件支持女儿,但作为庄家的家长,也为了庄家的颜面,他的妥协行为和心理必须隐瞒;二是,施家也不能让对手庄家看到其退让的倾向,因此退让也只能是隐秘的。双方这种心照不宣的心理是通过“不写”的方式写出来的,无声而默契的动作与节奏,已经非常充分地将他们幕后的运作暴露出来了。
庄木三与施家父子在离婚权力场域中的不作为,除了双方确实因为持续三年的吵闹和纠纷而有尽快结束的心理,更重要的是,他们之前早已对可能的判决结果了然于胸。离婚双方意见的交换显然需要第三方,即主持调解的乡绅力量的介入,那么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慰老爷三年都没有解决离婚纠纷,并且最后这一次在请城里来的权威更大的七大人来之前,还要进行这样私底下的谋划。这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这样的举动不仅显示了慰老爷在调解屡次受挫之后对于自身权威的不自信,同时也是对七大人权威的怀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威权和金钱解决问题,完全不顾是非曲直,实际上显示了乡绅公信力的丧失和乡村权力结构的崩塌。
四、权威声音的背后:乡绅的隐蔽合谋与权力危机
在爱姑离婚调解的权力场域中,主要发声的乡绅有两位:一是庞庄本地的慰老爷,二是从城里请来的七大人。“乡绅,乡间的绅士。”(17)《汉语大词典》第10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年,第660页。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乡绅是“作为唯一的知识分子阶层”,也是“社会规范的解释者和文字的传播者,教化和教育是赋予他们的最基本任务”(18)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以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为背景》,《法学家》2010年第6期。。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规范带来了威权”,“规范对于社会生活的功效不但是它存在的理由,也是受到社会威权支持的理由。社会威权的另一面就是人民的悦服”(19)费孝通:《皇权与绅权》,《费孝通全集》第6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2-244页。。而乡绅在乡村社会获取社会地位与乡民信任的原因在于他们是知识者,也是熟知乡间礼仪和规范的文化阶层。因此,在传统乡土社会权力结构中,乡绅阶层无疑是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靠自己的文化威权实现着对乡村的控制”(20)秦晖:《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页。。因此,慰老爷调解爱姑离婚纠纷的合法性正是来源于乡绅所具有的文化资本与社会威权。
从传统上来说,依据礼治规范与伦理经验来治理乡间的乡绅,对于调解一桩离婚纠纷应该是一件有例可循的事:一、如果按照乡约族规,那么施家要出妻,那就看爱姑是否触犯了七出之条,即“毋大故勿出妻也:妻之为言齐也,与夫继先启后之义。若犯七出,不得不出。苟非大故,亦当容以存大义”(21)《清道光祁门县锦营郑氏宗族祖训》,卞利编著:《明清徽州族规家法选编》,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69页。;二、如果按照民初时期仍然延用的《大清律例》,那么则有《户例·婚姻》一百一十六条“出妻”中:“凡妻(于七出)无应出之条,及(于夫无)义绝之状,而擅出之者,杖八十……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不坐(情既已离,难强其合)”(22)张荣铮等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由此可见,无论采用乡约族规,还是采用律例,爱姑与丈夫离婚都应该不是一件难以解决的事。但从小说中可以看到的是,慰老爷的文化知识及其身份威权在爱姑的离婚纠纷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既无法以知识之理服人——只会劝爱姑:“走散好走散好”(第149页)这一句毫无实质意义的话;也无法以乡绅之权压人——连爱姑这样一个普通的乡间女性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不过是一个团头团脑的矮子”,庄木三对慰老爷的看法也和爱姑如出一辙:“不足道的”(第151页)。也就是说,慰老爷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其乡绅身份本该在乡间所具有和权威性和社会功能,其无能使他不得不从城里请来地位更高的七大人主持爱姑的离婚纠纷。
在慰老爷家客厅的离婚场域中,声音的往来是紧张而激烈的,其间交织着爱姑与慰老爷、七大人之间的对峙,还有爱姑与其丈夫之间的争执。在七大人发声之前,小说首先从爱姑的视角描写了客厅里的乡绅群像:“还有许多客,只见红青缎子马挂发闪”;以及七大人的形象,虽然和慰老爷一样的“团头团脑”,但是“那脑壳和脸都很红润,油光光地发亮”(第152页)。这样的脸色与本地乡绅紫黑的脸色显然不同,再加上其他乡绅众星捧月般簇拥在一旁,更显示出七大人的身份地位非同一般。这种社会地位的直观视觉展示给爱姑以一种心理上的压迫感,紧接着七大人开口说话——关于古人大殓时使用的“屁塞”,远离乡民日常生活的冷僻知识再给爱姑以文化上的震摄感。此时,七大人在离婚权力场域完成了其社会威权与文化威权的双重展示,从而成为这一场域的实际主持者与最终决定者。因此,在这一前提下,慰老爷也从之前离婚纠纷的主持者转变为七大人声音的传达者,代替七大人发言,除了再次重申之前的意见“走散得好”,强调了这也是七大人的意见,同时还加上了:“可是七大人说,两面都认点晦气罢,叫施家再添十块钱:九十元!”(第153页)然而,由于慰老爷在爱姑面前已彻底失去威信,即使他的发言里增加了七大人的意见,爱姑也并不重视,完全没有回应慰老爷所说的话,而是直接对着七大人诉说她在施家受到的委屈。七大人除了其间看了爱姑一眼,还是不动声色,只有慰老爷与其周旋。在慰老爷自知劝解无用,再次利用七大人的身份地位威胁爱姑:“打官司打到府里,难道官府就不会问问七大人么?那时候是‘公事公办’……”(第154页)。但是,爱姑的固执己见终于使七大人对离婚纠纷正式发声。
首先,七大人说话的语调是缓慢的:“‘那倒不是拼命的事,’七大人这才慢慢地说了”(第154页),表示其比身边一群乡绅的身份地位更加尊贵,这是一种一言九鼎和不容反驳的气势,而且一开口就否定了爱姑“拼命”“大家家败人亡”(第154页)的想法与目的,为这个离婚判决定了基调,看似对解决离婚问题胸有成竹。
其次,七大人从第二句话开始就流露出无知、无理与心虚。乡绅从普遍意义上来界定:“曾经为官的地方精英,或通过科举考试但从未入朝为官的举人老爷,以及其他以财富和地位成为各自地方显赫人物的缙绅。”(23)[美]周锡瑞:《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史金金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页。从七大人从城里来,打官司时官府还要向他询问意见来看,可以推论七大人应该曾科举入仕,且官阶还不低,还是有相当的财产能够留在城里的乡绅。因此,按常理说,城里来的七大人确实应该如爱姑根据她的生活经验与常识所想象的那样,远比留守乡村的慰老爷之流更有见识和文化知识,更具判断力。但令人大失所望的是,七大人的断案水平无论如何都看不出有比慰老爷更高明之处。七大人对离婚纠纷的判决,这几句话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信息,将其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是,无知。七大人判决的唯一原则并不是前文所提到的乡绅应该非常熟悉的传统的乡约族规,也不是有关解除婚约的律例,而是“和气生财”,他的着眼点是“财”,而不是“理”,所以“一添就是十块,那简直已经是‘天外道理’”,这个“理”是七大人自己定的“理”,可以说是毫无道理;二是,威胁。七大人恫吓爱姑如不同意他的意见,就会人财两空:“公婆说‘走!’就得走”;三是,心虚。由于七大人也知道自己的信口开河并没有真凭实据,为了掩盖自己的心虚才又加油添醋地胡说:“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第154页),还要让所谓在北京上洋学堂的少爷证明胡乱判决的正确性。然而,七大人的看似威严、不容反驳的判决并没有让“胡里胡涂”的爱姑立即接受,可见连一个没有知识的乡村普通女性也发现七大人根本就是胡言乱语,只能说明前者实际上比后者更加“胡里胡涂”。七大人的学识和身份显然无法让这个离婚纠纷干脆利落地终结,即将再次落入前几次慰大人无效调解的境地。
最后,爱姑无视七大人的判决和刻意展示的威严,继续以乡妇的尖刻在乡绅满堂的客厅里与丈夫对骂,话语越来越不堪入耳,其实在此时的离婚场域中,只有爱姑一个人的声音,局势有超出慰老爷与七大人掌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七大人终于发出了其在整个离婚过程中最强有力的声音:“来~~兮!”(第155页)小说非常仔细地描写了此次发声的过程和细节:“七大人忽然两眼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了”(第155页)。这声势浩大的一喊与应声而来的“蓝袍子黑背心”“象木棍一样的”顺从的男人,让爱姑见识了七大人“命令的力量”——迅速颠覆了她之前对于七大人的直觉想象——在七大人面前无理可讲,只能服从:“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第157页)。因此,七大人一句简洁的命令:“来~~兮!”完成了其权力、身份、地位的完整展示,从而成为离婚裁决立即生效的一锤定音。
从七大人在整个离婚场域的声音表现来看,从“慢慢地说”毫无道理的“天外道理”到突如其来的“高大摇曳”的“来~~兮”,刻画出了七大人不学无术而又以权压人的跋扈乡绅形象;在七大人通过权力展示对爱姑实施了威慑,并立即扭转了局面后,本来在爱姑面前毫无威信、退到离婚场域角落的慰老爷此时跳了出来,一反前面说话吞吞吐吐的样子而响亮发声,成为继七大人之后的声音焦点。因为请七大人参与离婚判决的目的已然达到,慰老爷得意而忘形地发声,从其话语间正好暴露了他与庄木三、施家父子之间实际上早已达成了私下协议,也就是说三方已经预知了这个结果:“我想你红绿帖是一定带来了的,我通知过你。那么,大家都拿出来……”;“爱姑见她爹便伸手到肚兜里去掏东西……见他(庄木三)已经在茶几上打开一个蓝布包裹,取出洋钱来”(第156页);“庄木三正在数洋钱。慰老爷从那没有数过的一叠里取出来一点,交还了‘老畜生’”。(第157页)以上这些动作连贯、一气呵成,非常迅速、流畅和默契:庄、施两家的红绿帖早已带来;慰老爷话音未落,庄木三就已经准备数钱了;慰老爷早已知道施家带来的钱超过90元。当一切的争执偃旗息鼓时,七大人以“呃啾”的一声喷嚏惊动客厅,手里仍拿着象征其文化身份的“屁塞”,再次提醒众人自己作为权威的存在。持续三年的离婚事件就在这声“呃啾”中平淡结束,无论是庄木三父女,还是施家父子,此时都客气而恭敬地退回了慰老爷家的客厅。
从乡绅这一方面来看,七大人和慰老爷对于此次离婚纠纷的调解,从本质上来看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意味着前者在学识和见解方面也根本没有比后者有更高明之处,这一点慰老爷显然也是清楚的。因此,施家一桌酒席的贿赂让慰老爷想出了请七大人来参与离婚纠纷以期迅速解决,但是七大人只有“威权”而无文化,无法服众。这就不得不使慰老爷在调解之前就先以七大人之名迫使或威胁庄木三同意,而无人支持的爱姑也就孤掌难鸣。也就是说,慰老爷实际上只借用了七大人的“威权”身份,而众人口中的“权威”七大人在离婚现场的行为举动也充分展现了一个无用而腐朽的乡绅形象,正如同他手中把玩的那个古董“屁塞”一样。被慰老爷家客厅里的乡绅们、洋学生们簇拥着的、见过世面的、官府断案都要咨询意见的七大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更多的类似于慰老爷一样的本地乡绅,其水平之低下更可见一斑。而从乡民这一方面来看,以爱姑、庄木三等人的精明,通过七大人在离婚场域中的无稽之谈,也未尝没有发现原来他们所期待的七大人与慰老爷原来只是一丘之貉。因此,爱姑也不再分辩,除了七大人特意展示其权威以权压人之外,也包含有失望的心理——不可能指望七大人给予公正合理的判决。当洋钱、红绿帖等交割完成,慰老爷自认完成了一件大事,留庄、施两家喝新年喜酒时,双方一致拒绝,并且都表现得相当平静,包括刚刚还坚持要“拼着一条命,大家家败人亡”的爱姑。这种表面上的平静实际上反映的是乡民对于乡绅阶层糊涂、无知——七大人也不过如此——的一种蔑视和失望的心理。
清朝除了通过科举和学校等方式选取官员以外,同时还实行“捐纳”制度。虽然“捐纳卖官, 秦汉以来几乎历代都实行过, 但开捐次数, 项目之多, 影响之深, 无过于清代”(24)杜家骥:《清代的官员选任制度述论》,《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而乡绅阶层中的一部分即是通过捐纳入仕后的退休返乡官员,那么这些依靠金钱成为官员后,再下沉到乡里成为乡绅的人,其学养与品格是否与他们的头衔相符合,显然是值得考究的。另外,自晚清以来,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乡里读书人中的有志者或接受新学者纷纷离乡进城,即乡绅中的精英分子越来越少,或者反过来说,乡绅阶层逐渐劣化,正如乡绅刘大鹏所言:“身为绅士而存所在不思为地方除害,俾乡村人民受其福利,乃竟借势为恶,婿官殃民,欺贫谄富,则不得为公正绅士矣。民国以来凡为绅士者非劣衿败商,即痞棍恶徒以充……”(2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95页。。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而“礼是指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26)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全集》第6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8页。,这些规范有赖于拥有文化知识和掌握这些规范的乡绅阶层来付诸于实践。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乡绅阶层的堕落与劣化的速度加剧,自身的失范使其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与维持传统伦理道德方面失去了公信力,在乡村社会原有权力结构被打破的同时,乡村社会与伦理道德也开始失序。正如《离婚》所揭示的那样:乡民不再信任,甚至私底下是鄙视乡绅的;乡绅们对于一个简单的离婚纠纷的判决也束手无策,不得不私下勾结合谋才勉强使之完结;乡绅们的目的虽然达到了,但是他们在离婚场域中的荒唐表演,却更加清楚地暴露了他们本来的面目;乡村中唯一的文化知识阶层——乡绅,其职能的失效不可避免地导致传统乡村社会陷入混乱与危机之中;还有在小说中一闪而过的从北京洋学堂回来的尖下巴少爷,也不过是在新学中滥竽充数,只能充当七大人“博学”的应声虫。旧的传统与秩序已然失落,新的文化与思想荒腔走板,因此,尽管《离婚》只写了乡村里一桩琐碎的离婚纠纷,但实际上却展现了一幅传统乡土社会礼治崩坏与文化没落的画卷。
五、结 语
相较于鲁迅其他的现实题材小说,《离婚》有着鲜明的叙事特点,即声音的表演,在两个叙事场域——船上与慰老爷家客厅中,此起彼伏的声音角逐:在船上,嘈杂的议论声中最为突出和起主导作用的是爱姑的声音;在慰老爷家客厅里,压倒众声喧哗,使众人屏气聆听的声音是七大人简短而威严的“来~~兮”和令众人侧目的一声“呃啾”。从表面上来看,这两个场域有着两个不同的声音主角——爱姑和七大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自庄木三在船上说出七大人要参加后,“七大人是怎样的乡绅”便成为船上乡民们议论的主要内容,因为这将直接影响这场离婚纠纷的结果。这些众说纷纭的声音实际上是对七大人其人其声出场的一种铺垫与烘托:传言中或想象中公正明理的七大人与慰老爷家客厅里的糊涂无知的七大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小说的叙事焦点虽然看似在离婚纠纷上,但真正在落脚点却是展示以七大人为首的一群乡绅利用其身份与威权在乡村里的荒唐治理。可以说,七大人不仅是离婚场域的声音主角,更是整个小说真正的主人公。为了保证七大人在离婚场域的权威不至于受到庄家的反驳与挑战,使调解顺利生效,慰老爷事先运作,拉拢庄木三,孤立爱姑。因此,在乡绅的合谋与七大人虚张声势的声音表演的双重作用之下,七大人的胜利与爱姑的败退是必然的。虽然,在慰老爷家客厅里,七大人的声音似乎成为了代表乡绅威权的符号,但这只是在一众乡绅从场外到场内精心合谋的结果,并且针对的仅仅是爱姑——这样一个非理性的、依靠直觉行事的乡村女性。而这也恰好说明了乡村权力的危机所在:本应以文化、道德以理服人的乡绅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无知无德的乡绅沆瀣一气只能以权压人,这样的乡绅在乡里胡作非为,既得不到乡民的尊重,也不可能维持和稳定传统秩序,毫无疑问会导致乡村社会日益走向混乱与败落。
《离婚》虽名为“离婚”,但提出离婚诉求的双方——爱姑与其丈夫却并未形成真正有效的对话,反而是爱姑与乡绅之间的声音处于博弈之中:一方面,从爱姑的急切、快速、大声到其声音“低下去”“细微如丝”,终至湮没无声,再到恭敬客气,这一系列声音的变化,反映出爱姑从期望、争取再到失望的心理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从慰老爷无用的絮叨,到七大人笃定的缓慢语调,再到“高大摇曳”威镇全场的声音,则表现了乡绅无理亦无礼的尴尬处境。虽然离婚的最终结果是乡绅取得胜利,但是这胜利只证明了乡绅管理乡村的失信、失德与失效。因此,《离婚》之名实际上具有双重的喻意,一是小说中的爱姑与其丈夫的离婚事件;二是作为乡村知识精英的乡绅,他们的文化、权力与乡村的管理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乡绅与乡村的结合是传统乡土社会秩序维持与稳定的保障。当乡绅的文化和社会权力被乡民质疑、挑战时,说明原有的传统乡村社会权力结构正在被解构或重构。如果说那一部分离乡进城转变为新知识分子的乡绅是主动抛离乡村,那么留守乡村的无能乡绅最终将会被乡村所抛离,这两方面的抛离表明了乡绅与乡村的关系正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离婚”,而传统乡土社会也不可避免地陷入文化的真空与权力的混乱之中。从这个意义来说,《离婚》完成了鲁迅以小说的方式对于启蒙和乡土的叙述,即从“呐喊”的孤绝到“彷徨”的迷茫,终于以一种闹剧的形式结束了启蒙的痛苦与困惑,而这正展现了当时乡村社会的荒诞现实与不可预期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