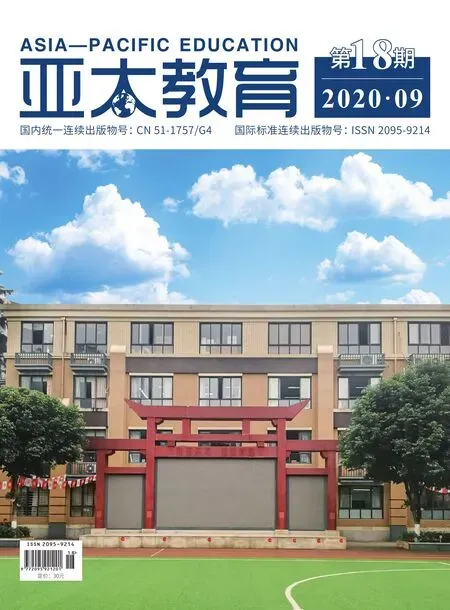日本道德学科化的争议及其启示
成都体育学院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 王莉平
一、道德学科化的演进及基本内涵
(一)从道德时间到道德学科化
自二战“修身科”废止后,日本国内负效应相继出现。为挽救国内道德教育状况,1957 年,岸信介内阁首次提出要推进以弘扬民族精神和国民道义为基础的德育政策。同年8 月,文部大臣松永东在记者会上指出,“为加强民族意识与爱国心,需尽快在小学、初中设立与道义相关的独立教科”,这也成为道德特设问题的开端。同年11 月,教育课程审议会提出了《关于小学、初中道德教育的特设时间》咨询报告,并于次年3 月向文部大臣提出了包括特设道德时间在内的小学、初中教育课程全面改订的咨询报告。1958 年3 月,文部省以通告形式下发了《关于小学、初中“道德”的实施纲领》及其附件《小学“道德”实施纲要》和《初中“道德”实施纲要》,详细规定了道德时间的宗旨、内容及指导方法。迫于现实,文部省在起初特设道德时,以道德时间代替了道德课的说法,且仅将其定位于学校其他教育活动的道德补充、深化和统合。直到1961 年9 月,道德时间才区分于其他学科正式实施,成为专门化的道德教育。然而,与文部省意图相悖,道德时间实施后并未完全渗透学校全体道德教育活动。在此之后,道德教育又经历了多次修订与变革,但道德时间在日本全国形式化倾向依然明显。
2011 年,日本滋贺县大津市一名学生因受欺凌而自杀的事件发生后,“教育再生实行会议”再次将道德学科化提上日程,并于2013 年在“关于充实道德教育的恳谈会”上正式将道德教育提升到特别学科规格上来,取代原有的道德时间,以集中对学生进行“规范意识强化”和“心灵教育”。经过中央教育审议会多次审议,2015 年3 月,道德学科化政策正式启动实施。
(二)道德学科化的基本内涵
道德学科化旨在将德育提升到与国语、数学等学科同等地位,并在指导内容、方法、教材编审、师资培训等方面做整体性的结构转型,以期扭转传统德育散碎化、虚无化的“恶性循环”,进而从根本上充实和改善学校德育。它主张通过学校全体教育活动,实现以“思考、讨论”为主要方式的道德转换,培养学生道德性及道德实践能力。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引入审定教科书,并免费发放给每位同学。
第二,增加欺凌及校园安全相关内容,重视对学生“信息道德”的培养;强调“爱国”“爱家乡”“爱传统文化”等内容,将以往从三年级开始的爱国主义教育变成从一、二年级开始强化。
第三,改变过去“阅读”为主的学习方式,强调问题解决式、体验式学习,重视学生的思考、讨论及实践。
第四,根据学生学习、实践及道德成长情况,采取记录式评价。
第五,在原有“道德指导年级主任”的基础上,增设“道德推进教师”,其他科任教师协助指导。
道德学科化还从多方面对原有德育政策进行修订和补充,对学校整体道德教育实践与操作做出了具体指导。政策规定,全国小学将于2018 年4 月、中学将于2019 年4 月开始全面实施道德学科化。
二、道德学科化的争论
道德学科化作为日本德育探索的新路径,究竟应关注政治价值还是德育本身、应关注知识智力价值还是情感素质价值,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很大争议。
(一)价值归属之辩:政治取向与德育取向
面对不断发生的校园欺凌和犯罪问题,日本政府在2007 年6 月教育再生会议第二次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儿童规范意识,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唤醒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他人的理解,体会劳动的意义,以感受个人在社会中的存在价值。为实现以上目标,有必要实行道德学科化,充实道德时间的指导内容和教材,以强化德育作用。”也即是说,道德学科化政策的制定初衷是要遏制校园欺凌现状,改变教育荒废现象,提高德育对儿童的规范和教育目的。然而,2015年3 月正式提出的道德学科化政策却极其强调对学生“爱祖国、爱家乡”等核心价值观的教导,由此也引发了激烈争辩。支持者认为,道德学科化根本目的在于调整和改造传统道德时间的缺陷,是为德育本身服务。通过学科化的改革,既可以解放过去德育对政治的依赖,回归教育领域,以正面应对孩子的道德问题,也可以解决校园欺凌等社会病态现象,维持学校和社会的正常秩序。反对者认为,国家使用审定教科书加强对学生“爱国心”的核心价值及规范意识养成的举措并非偶然,其作为安倍教育政策的重点之一,是自民党为修改宪法提案所指向和建立能够发动战争的不可或缺的布局,目的是通过向孩子注入殉国的思想以进行人格统制,而绝非仅仅应对欺凌问题。
(二)价值内涵之辩:道德知识与道德素质
日本国内有学者认为,传统道德时间有一种“副读本活用主义”倾向,它强调通过“阅读式”的方法开展“价值传达型”课程。课程的阅读资料都将道德问题限于个人场景之中,继而按照课文内容安排以及教师的课程计划进行并推理得出结论。因此,道德学科化尤其强调由知识灌输转向活动体验,不断充实和活用教材,发挥学生在道德发展中的主体性及心理自觉性,并主张通过教师引导、促进及学生思考、讨论,获得道德素质的整体发展。然而,大阪大学名誉教授藤永芳纯对此提出质疑:使用审定教科书,采用多样的教学指导是否会导致以书本为依赖的统一性教学指导?他认为,德育向体验、实践转向这一提法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强调以审定教科书的编订、使用为基础进行道德教育,反而会加重“用教材教”的传统倾向,导致德育脱离生活实际,只剩下知识的价值式理解。同时,注重“讨论、思考”的道德方式对于没有完全具备思考能力的小学生来说,也不值得探究。总之,反对者认为道德学科化实际更关注道德知识的灌输,对学生道德素质的发展与提高并无实质性改变。
三、启示
早在日本进行“道德学科化”改革前,中国便已经确立了德育的学科地位。从日本改革经验来看,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德育应“立人”为先。历来德育都与政治脱不了关系,因为作为德育对象的人必然归属于一定政治团体。但德育应该成为政治的手段吗?杜威认为,教育应以其本身为目的,要以人的内在需要为目的追求教育本身的内在价值。作为教育道德目的的代表,德育的价值应是“立人”。当然,这里并不排除国家意志对德育的影响,只是“立政治”或“立经济”应放在“立人”之后,作为德育的间接目的。具体来讲,在德育政策制定及实行过程中,要排除特定政党对德育的规划,以人的发展需要为优先考虑,使德育成为“成人”的真德育,而不是“立政治”的伪德育。另一方面,德育课程、内容也宜在不同党派、阶层、团体中尽量“中立”,营造一种和谐的德育课程观与教学观。
第二,德育应聚焦道德素质的提升。德育被“学科化”,意味着道德能够以系统组织的知识、观念,程序化的方法、手段教给学生,德育指导被加强。然而,“学科化”的桎梏也意味着德育价值内涵的缩小以及实际操作中活动体验及其他学科渗透的减少。也即是说,它是一种以体验为基础、思辨及心理自觉为主的德育方式,它更关注学生道德判断力的发展,关注课堂中活跃的讨论场面而忽视了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导致本应生动、活泼的德育课成为道德知识、观念的灌输课堂。从这个意义来讲,学生在道德养成过程中要避免对理性主义的过分赞扬,既要以理论知识为基础,强化道德判断能力,也要超越理性主义,注重实践和体验的渗透,加强道德情感培养,进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道德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