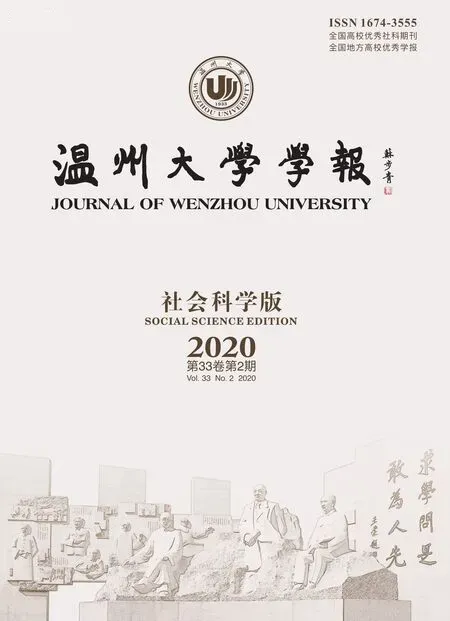丝绸之路视野下的绝句、竹枝词称谓起源研究
陈永霖,叶晓锋
〔1.温州医科大学,浙江温州 325035;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3.温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绝句和竹枝词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诗歌体裁,两者形式相似,都是四句,其起源和形成过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是绝句和竹枝词这两个称谓的起源至今仍不甚清楚,是中古文学史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绝句称谓的起源问题
(一)“绝句”称谓的出现时间、名称演变
绝句,也称“截句”“断句”“绝诗”,每首四句,主要有五言、七言,偶尔有六言绝句[1]。需要注意的是,绝句这种形式的起源和绝句名称的起源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就目前研究而言,一般都认为,绝句这种诗歌形式出现早于绝句这个名称——汉魏时期就已有以绝句形式存在的诗歌,但是当时绝句这个名称还没有出现[2]。绝句这个名称的起源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明代学者胡应麟认为是唐代:“六朝短古,概曰歌行,至唐方曰绝句。”[3]105而清代学者赵翼认为宋梁已有绝句的说法:“今按《南史》,宋晋熙王昶奔魏在道慷慨为断句诗曰:‘白云满鄣来,黄尘半天起。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梁元帝降魏,在幽逼时制诗四绝。其一曰:‘南风且绝唱,西陵最可悲。今日还蒿里,终非封禅时。’曰断句曰绝句,则宋梁时已称绝句也。”[4]457
葛晓音又补充了许多例子。《南史·张彪传》记载:“彪被劫杀,彪友吴中陆山才,嗟泰等翻背,刻吴阊门为诗一绝云。”《南史·临川静惠王传》附《萧正德传》提到萧正德“初去之始,为诗一绝,内火笼中”。《南史·元帝本纪》说萧绎“在幽逼,求酒饮之,制诗四绝”。[5]从这里可以看出宋梁之际已经有了“断句”和“绝句”的说法,而且“断句”出现比“绝句”略早。《玉台新咏》是一部汉代至南梁的诗歌总集,为南朝梁陈诗人徐陵所编,收录了古绝句四首,这四首绝句均为五言绝句。另外,南朝梁代诗人何逊的《何水部集》收录了题为绝句的五言诗七首。葛晓音指出,最初的绝句作者基本上都是梁中叶前后的诗人[5]。
为何把四句的诗歌称为“绝句”或“断句”?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诗法源流》云:‘绝句者,截句也。后两句对者是截前四句,前两句对者是截后四句,全篇皆对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对者是截首尾四句。故唐人称绝句为律诗。观李汉编昌黎集,凡绝句皆收入律诗内,是也。’”[6]赵翼等人基本赞成这个看法[4]457。不过胡应麟并不同意绝句来自律诗,并提出反驳意见:“绝句之义,迄无定说。谓截近体首尾或中二联者,恐不足凭。五言绝起两京,其时未有五言律,七言绝起四杰,其时未有七言律也。”[3]105虽然胡应麟不赞同绝句来自律诗,但认为“绝句”解释为“截句”是可以的,绝句的范围可以提前到汉魏诗歌,如“步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该诗由于和下文的押韵并不一样,也是四句,因此也可以看作截出来的绝句。[3]105吴代芳认为:绝句的名称来源于联句;所谓“绝”者,断也;绝句的命名,乃是因无人续作联句而中断之意[7]。韩成武、吴淑玲提出“绝句”的“绝”是隔断、断绝的意思[8]。总的来看,把绝句、截句、断句直接理解为“断绝”“截取”这一观点,显然认为绝句是从一个更长的诗篇截取出来的。但是从绝句的发展历程看,绝句本身就是独立存在的,四行诗本身就存在。许多更长的诗篇更有可能是四行诗叠加的结果,如律诗出现的时间显然比绝句晚,这样显然更符合事实。面对绝句本身是独立存在的事实,把“绝句”“截绝”“断句”的“绝”“截”“断”,仅仅理解为字面上的“断绝”或“截取”,肯定是不对的。
李长路不同意“绝”是“截”的意思,他认为“绝句”“截绝”“断句”的“绝”“截”“断”,是“简短而又完备”或“小而又足”的意思,并不是“由长减短”的意思[9]。这种解释从语义上讲相对是可以的,但并没有训诂学上的依据,因此也不足为据。
总体而言,绝句的起源存在三个需要解释的问题。第一,这种四句的诗歌体为何被称为“绝句”或“断句”?需要指出的是,“绝句”在南朝宋时其实被称为“断句”,这是“绝句”之前四行诗的称谓。一般都认为“断”和“绝”意思相同,因此可以相互换用。但是为何称四行诗为“断句”或“绝句”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①赵翼指出:“绝句之名,迄无定说,谓截近体诗首尾或中二联者,恐不足为凭。”参见:赵翼:陔余丛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457。。第二,为何这种绝句、断句的称呼在梁代前后突然出现②徐陵《玉台新咏》专列“古绝句四首”一节,这也是目前发现最早出现的绝句。。第三,为何七绝产生的时间晚于五绝,也需要做出解释[5]。
(二)丝绸之路视野下的四行诗和绝句
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语言和文化中,四行诗是很常见的,波斯诗歌、阿拉伯诗歌、突厥诗歌都存在四行诗[10]254-264,[11]41。四行诗是波斯诗歌体裁中最短小的一种。波斯四行诗有两个名字:一个是rubā‘ī,该名字是阿拉伯语,“四个一组”的意思;另一个是tarana。波斯的四行诗押韵方式一共有三种:“二四句押韵”“一二四句押韵”和“四句全押韵”。[10]254-255在突厥诗歌传统中,四行诗也很常见。哈萨克民间诗歌,经常四行为一段,而且是一二四行押韵[12]。这和中国古代的绝句在形式上很相似。阿尔泰语中的murabba诗节,主要表现形式为四行一节,格律为a-a-x-a模式,也就是一二四行押韵[13]。可见,如果拉开时空来看,从中国、中亚一直到波斯都有四行诗。
Bausani、杨宪益、穆宏燕均指出波斯的四行诗是受唐绝句的影响而产生[14-16],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波斯四行诗出现的绝对年代晚于汉语文献”的判断得出的。但是这一判断现在基本上已经被否定:在巴拉维诗歌以及摩尼教文书中的tarana,都存在四行诗,绝对年代可以追溯到3-9世纪[17]。因此,“绝句”最早出现于中国,目前看来是不成立的。现在学界一般认为,中亚突厥语民歌四行诗来自波斯[18]。日本学者护雅夫则提出七言绝句和六言绝句的产生都和中亚和北亚少数民族的民歌(“北歌”)存在密切关系,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不过护雅夫是就形式而言的,并没有直接指出“绝句”的语源[19]。“绝句”和“断句”的语源,在汉语学界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其实,“绝”和“断”仅仅是记音词,本身并不表示词义。在满―通古斯语族中,“四”的读音分别是“满语duin、dyn”[20]621“鄂伦春语dijin”[20]708“锡伯语dujin”[20]927“赫哲语dujin”[20]987。在蒙古语族中,“四”的读音分别是“蒙古语dorob”“东部裕固语de:ren”“保安语deraŋ”“康家语derɔ”[21]。对比可见,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中的“四”和汉语中“断”的读音*duan极其相似,特别是满―通古斯语族的duin。在中古汉语与于阗语的对音中,“桓韵”*uan有时还可以和于阗语的vīṃna对应。如“官”对应vīṃna[22],其中ṃ是鼻音标志,主要是跟后面的n伴随产生,因此可以忽略。换言之,和西域语言对音的时候,汉语桓韵有时可以对应西域语言的vīṃn或uin,从这个角度看,汉语与满―通古斯语族对音是最整齐的。满―通古斯语族中“四”这一系列读音的突出特点是,以齿龈塞音作为韵首辅音,以鼻音n作为韵尾,ŋ是n的音变形式①由此还可以解决波斯语中tarana的语源问题。tarana在语音上和蒙古语族的de:ren(“四”)等形式很相似,而波斯语中并没有类似表示“四”的词语,其语源应该就是四行诗。从这可以看出,波斯诗歌传统和中国草原民族早就存在互动,并借用他们的称谓。可惜的是,草原民族的书写记录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以及释读,因此追溯四行诗最早出现的时间,相对比较受限制。但是通过对词语的语源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波斯传统深受中国草原民族的影响。波斯语中并没有类似表示“四”的词语。。
在伊朗语族中,“四”的读音分别是“吠陀波斯语c˘atur”“巴列维语c˘ahār”“波斯语chār”“巴基斯坦Shina语c˘ar”“普什图语c¯ẖār”“塔吉克语tsavur”[23-26]。在突厥语族中,“四”的读音分别是“古代突厥语dørt”“维吾尔语tøt”“哈萨克语tørt”“柯尔克孜语tørt”“乌兹别克语tørt”“塔塔尔语dørt”“图瓦语dørt”“撒拉语djod”“西部裕固语diort”[11]361,[27]。在汉语和西域语言的对音中,部分汉语从母字可以对应西域语言的齿龈塞音,如“捷枝”对应Dapici[28],“捷”是从母字,但是对应dap。“绝”的中古音为从母薛韵字,因此中古汉语中的“绝”或“截”,完全可以和伊朗语族里的c¯ẖār以及突厥语族中的tort对应。
综而言之,中古汉语文学中突然出现的“断句”和“绝句”,语源其实与北方民族和东伊朗语支民族的语言有关。具体而言,“断”和满―通古斯语族的duin以及蒙古语族中的de:ren等表示“四”的词语有关,“绝”“截”和波斯语以及塔吉克等东伊朗语支语言中的chār等表示“四”的词语有关。
从“断句”的命名这里可以看出,早期拓跋鲜卑语应该和现在的满―通古斯语族接近。从“绝句”“截句”的语源则可以看出波斯语和波斯文化以及突厥文化对中古汉文化的影响。“绝句”“截句”“断句”都是“四句”的意思。
(三)波斯、突厥文化对中古汉文化的影响
“绝句”“截句”“断句”最早都是出现在南朝的史书里,然而这些词语语源不明。不能排除它们是来自中亚和北方民族的借词。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南北朝时期北朝文化和南朝文化彼此接触非常频繁。
阎步克较早就指出了北朝官制对南朝的影响——萧衍所建十八班制及流外七班制等重大更革是对北魏孝文帝所创类似制度的借鉴和模仿[29]。王允亮据《隋书·音乐志》指出,南北朝后期双方皇帝在音乐上的审美趣味,都是南北兼收;而且南朝后主非常欣赏北朝音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30]。童岭也有类似发现,他指出南方社会非常喜欢北方胡族文化,如在《南齐书·柳世隆传》中,“平西将军黄回军至西阳,乘三层舰,作羌胡伎,泝流而进”,这是北方音乐被南方主流社会吸收的明显例子[31]。
在文学方面,曹道衡较早就指出北方文学相对于南朝文学在叙事上的优胜之处[32]。金溪认为,在佛诞节庆典仪式传入南方之后,“佛教石窟和造像”“北方的佛教偈颂、梵呗”传入南方,并最终影响到后来的永明诗歌[33]。此后于涌指出,南方的边塞诗经常出现“陇首”这一北方词语,这显然可以看出北方文学对南方文学的影响[34]。
前文对“绝句”“截句”“断句”语源的探讨为“北朝文学影响南朝文学”的观点提供又一坚固的证据。“绝”“截”“断”均是“音译词”,是中亚和北方民族语言中数词“四”的语音转写。
二、竹枝词称谓的语源问题
竹枝词,也叫“竹枝”或“竹枝子”,属远古、中古民歌遗韵,形式上类似于七绝。作为一种别开生面的诗体,竹枝词自中唐起越来越受到文人的青睐,几乎历代重要文人都曾写过,至清代康乾间蔚为大观。竹枝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唐代七言诗和宋词的形成均有重大影响,中唐诗人刘禹锡运用这种诗体,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使竹枝词从民间登上了文人学士的诗坛,给诗词创作注入了一股新风[35]。
竹枝词的产生时间有多种说法。目前竹枝词的产生时间主要有晋、齐梁、隋、隋唐之际、唐五种说法,尚无定论。竹枝词的起源区域也有多种说法,主要有巴渝巫山说、楚地归州说、沅湘朗州说、蜀地说、夜郎说等几种。学界较为认可的是巴渝巫山说,基本认定竹枝词本是巴渝一带民歌[36]42-48。
但是为何叫“竹枝词”,一直没得到合理的解释,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清代万树《词律》认为“竹枝”是和声,没有实际意义。第二,竹枝词因“手执竹枝歌舞”而得名。任半塘、盐谷温等认为竹枝词和歌舞时手拿竹枝有关。第三,竹枝词因乐府歌名命名。马稚青根据清代王士禛《居易录》所载,认为竹枝词命名来源于古乐府。[35],[36]51-61,[37]
我们认为“竹枝”应该和绝句语源相似,语源也是“四”,竹枝词本义也应该是四行诗。
根据焦甜甜[38]、刘晓南[39]等人研究,唐五代时期,四川地区入声字的韵尾已经出现消失迹象,最早消失的就是-k韵尾。到了宋代的时候,四川地区方言阴声和入声基本上已经高度相混。“竹”中古是知母屋韵三等字,日语吴音是toku,中古音为tok,如果-k韵尾脱落,那么“竹”的实际读音就是to。“枝”是章母支部字,其同音词“支”在梵汉佛教对音中可以对应tye[40]。据此,唐代“竹枝”的读音可能是totye,与突厥语族中表示“四”的词音tøt、tørt、diort几乎一样。也就是说,“竹枝词”的本义可能也是“四行诗”。
三、从绝句的语源看中华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互动
汉唐时期,中亚各民族与中国有着深度互动。《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明确记录了汉朝与中亚民族的交流。张骞出使西域时就看到了来自中国的“筇竹帐”“蜀布”。汉代时胡豆、胡瓜等含“胡”为前缀的物品从波斯传入中国。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对波斯和中国的名物名称的语音对应关系有深入探讨(如“汗血宝马”“苜蓿”“葡萄”等),从语音对应角度揭示了波斯和中国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具有里程碑意义[41]。不过劳费尔偏重对物质文明交流的探讨,其实中华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互鉴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习近平对丝绸之路文明的交流互鉴有精辟的论述:“公元前100多年,中国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西域文化成果。西汉时期,中国的船队就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中国的丝绸换取了琉璃、珍珠等物品。中国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活跃期。据史料记载,唐代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70多个,那时候的首都长安里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成群。这个大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中国。”[42]习近平同时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43]习近平的文明互鉴论对中华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以往我们可能会更多强调中华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影响,但是任何人类文明都是在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的。
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从文学体裁的语源角度探讨西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古前期,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来自西域和北方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并在中国的北方创建了诸多王朝。波斯语言以及北方游牧民族语言对中古汉语,甚至中古南朝汉语产生影响。波斯和中亚文化通过丝绸之路沿线的商贾不断进入中原地区,经由北朝进而影响南朝文化,因此北朝文化不仅包含中国北方文化,也包含来自中亚的文化。而北朝和南朝的合流铸就了隋唐盛世,因此了解波斯和中亚文化有益于更好地了解隋唐盛世。
前文已经讨论了“绝句”和波斯语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并推定“绝”和“截”是波斯语中表示“四”的词语chār,“绝句”就是“四句”的意思。其实除了文体名称,波斯政治名号在中古汉语文学作品也多有出现。如“郎”。该词在中古出现,表示“主人”的意思。江蓝生指出,“郎”在六朝时期的小说中被用来表示“主人”,但是这个词为何突然出现,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到唐代,还有“阿郎”(“主人”之义)之说[44-45]。其实,“郎”来自波斯语rang“王、执政者”,“阿郎”来自波斯语ārang“总督、执政者”。又如“阿堵”ata(表示“这”)。该词是《世说新语》中非常有名的一个词语,并不见于南方民族语言以及汉语方言。其实该词是北方阿尔泰语借词。“这”,蒙古语读为ana。诸此种种无不体现中华文明对中亚和北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吸收和接纳,也正是中华文明的博大胸怀,孕育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繁华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