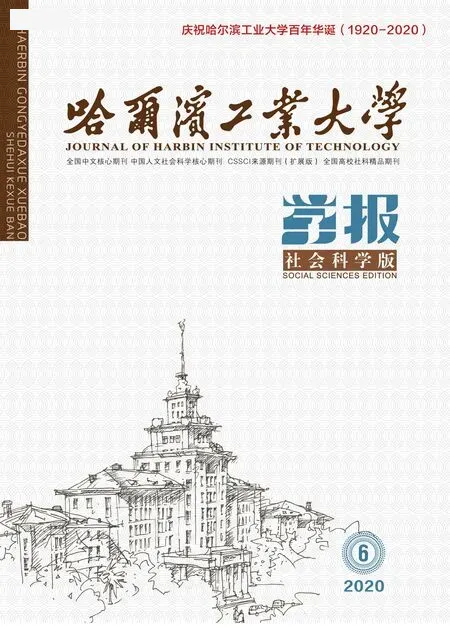论明中叶吴中文学的两极化生存状态
王晓辉
(哈尔滨理工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哈尔滨150080)
万历时,朱曰藩指出:“弘德间,海内数君子者出,读书为文,断自韩欧以上,稍变前习,一时学士大夫,歇然趋焉。 而柄文者顾不之喜……数君子亦抗颜不之恤,各以其志,勒成一家之言,以行于世,然以天下公器趋拾相俏,讥者非之。”[1]朱曰藩所言之“趋拾相俏,讥者非之”,反映出弘正文坛相互抵制、流派纷争的局面。 活跃于这一时期的文坛主要流派有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以及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派。 三派“你方唱罢我登场”,相互承继而又彼此批判,相互学习而又彼此独立。 在这种熙熙攘攘的派别纷争的大背景下,吴中文人却能置身其外,以一种极为宽容的心态对待纷争。 面对强大的异己文学,他们关注的不是双方的隔阂与冲突,而是彼此间的相通与交融。 正是这种豁达的心态和睿智的眼光,使得他们能抛开狭隘的门户之见,积极地与主流文学靠近并交融,从而使吴中文学在坚守本域文化特色的同时,又能博采众长,呈现出博雅大气的地域风貌。
一、对主流文学的认同与追模
(一)吴中文学与台阁体
明代文学发展到永乐年间,台阁体代表着官方主流意识崛起于文坛,代表人物为三位台阁重臣:杨荣、杨士奇、杨溥。 三杨资历深厚,颇具威望,主持文坛数十年,天下文风为之一变。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称:“国初相业称三杨,公为之首。 其诗文号台阁体。”[2]162
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流派,台阁文人的创作大多呈现出一种趋同特征。 其论文重道统,在散文写作上尤推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散文。 杨士奇曰:“至诏韩退之,宋欧阳永叔、曾子固,力于文词,能反求诸经,概得圣人之旨,遂为学者所宗。”[3]在诗歌创作上,他们提倡“和而平,温而厚,怨而不伤”的境界,题材多写“爱亲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怀”,风格以“雍容华贵,平正典雅”为宗。 台阁体的创作因为“三杨”地位的崇高而影响颇巨,称得上一唱百和,天下风靡,“一时公卿大臣类多能言之士……非独职词翰、官馆阁者为然。 凡布列中外政务理捕刑者, 莫不皆然”[4]。
在这种天下士人皆曰“台阁”的狂热氛围中,吴中士人也欣然参与其中。 明建国以来,吴中文人入翰林主台阁者不在少数,如吴宽、王鏊、徐有贞等。 他们在思想上尊崇“三杨”,创作上积极向“三杨”靠拢。 在这些吴中馆阁诸家中,徐有贞、吴宽、王鏊与“三杨”的关系极具代表性。
徐有贞与“三杨”交往甚密。 徐有贞(1407 一1472),字 元 玉, 号 天 全, 吴 县 人。 宣 德 八 年(1433)进士。 景泰八年(1457),因拥立英宗复辟大贵,封武功伯。 后为石亨所构,被逮下狱,亨败释归。 有《武功集》5 卷。 徐有贞以“二十八宿”庶吉士的身份步入仕途,聪敏博学的他立刻引起了“三杨”的瞩目。 吴宽在《天全先生徐公行状》记曰:“一时前辈若杨文贞、文敏诸公皆雅知公(徐有贞)名而器之。”[5]538徐有贞对“三杨”也极为敬重,称杨荣“一代号儒宗”,赞杨士奇“文复古风淳”。 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留有诸多唱和之作。 《武功集》卷二载有多首徐有贞为杨荣、杨士奇巡边雇从所作的颂词;卷四中的《江乡归趣诗序》为杨溥所作;卷五中的《寿杨东里少师二十韵》和《挽杨文敏公二十韵》为杨士奇、杨荣所作。而杨荣的《文敏集》卷二十四《徐处士墓志铭》,是为徐有贞的父亲徐孟声所作的,同时杨士奇也在其文集中为徐父丧作《徐孟声甫墓表》。 可见,徐有贞与“三杨”交往频繁,“三杨”对这位吴门才子也颇为垂青。
继徐有贞之后,吴宽和王鏊二人相继进入台阁,成为新一代吴中文士的馆阁领袖。 吴宽(1435-1504),号匏庵,字原博,长洲人。 成化八年举进士,授修撰,十六年进礼部尚书。 王鏊(1450-1524),字济之,吴县人。 成化十一年举进士第一,授编修。 正德元年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 《明史·文徵明传》载曰:
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驱驰,文风极盛。 徵明及蔡羽、黄省曾、袁袠、皇甫冲兄弟稍后出。而徵明主风雅数十年,与之游者,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谷祥、彭年、周天球、钱谷之属,亦以词翰名于世。[6]
吴、王二人位居台阁,位高权重,声名远播,吴中后劲视之为领袖。 可以说,明中期吴中文学的繁荣与远播,吴、王二人居功甚伟。
吴王二人对“三杨”敬仰之至,奉他们为文坛宗主。 王鏊赞杨士奇:“明兴,作者代起,独杨文贞公为第一,为其醇且则也”[7]272。 因为吴王二公乃吴门后起之秀,文学活动主要在成弘年间,故他们对“三杨”的崇拜更多地体现在创作上。 吴王二公的诗文在诸多方面呈现出台阁体的基本特征。 如吴宽之文“纡徐有欧之态,老成有韩之格”[7]272。 四库阁臣称其为“学有根底,为当时馆阁钜手。 学宗苏氏,字法亦酷肖东坡;缣素流传,赏鉴家视为拱璧”[8]。 他在《送周仲瞻应举诗序》中明确表示文学当以“欧、苏、曾”为正宗:
今之世号为时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对偶。 率腐烂浅陋可厌之言,甚者指挞一字一句以立说,谓之主意。 其说穿凿牵缀若隐语然,使人殆不可测识,苟不出此,则群笑以为不工。 呜呼,文之弊既极,极必变,变必自上之人始。 吾安知今日无若宋之欧阳、永叔者,而一振其陋习哉! 吾又安知无若苏、曾辈出于其下,而还其文于古哉![9]
吴宽将官方推崇备至的八股文称之为“腐烂浅烂”之文,批评其“穿凿附会”“弊端已极”。 他希望有如欧阳修、苏轼、曾巩这样的贤人出现,掀起一场古文运动。 可以看出,吴宽极力地倡导更新时文之弊,主张以古文替代“时文”,而这种古文写作的榜样则是欧、苏为代表的唐宋散文。 这种对欧、苏散文的推崇很可能受到台阁体重文统、崇唐宋文风的影响。
王鏊在文学创作上也积极地向“三杨”靠拢。霍韬序其文曰:“早学于苏,晚学于韩,折中于程朱。”[7]120王鏊对韩、欧的散文亦极为崇拜:
为文必师古,使人读之不知所师,善师古者也。 韩师孟,今读韩文,不见其为孟也。 欧学韩,不觉其为韩也。 若拘拘规傚,如邯郸之学步,里人之效颦,则陋矣。 所谓师其意不师其词,此最为文之妙诀。[10]27-28
字里行间饱溢着对韩、欧的赞誉之词,难怪王阳明评价他:“文规模昌黎,纯而不流于弱、奇而不 涉 于 怪, 雄 伟 俊 洁、 体 裁 截 然, 振 起 一 代之衰。”[11]
王鏊、吴宽秉承“三杨”创作之风,高居馆阁,领袖明中叶吴中文坛,其取向好尚必然会影响到诸多吴中后劲,杨循吉便是深受影响者之一。 杨循吉,成化二十年举进士,授礼部主事,性狂傲,好持人短长,对“三杨”、吴王等馆阁大家极为仰慕。他平生酷爱唐宋散文,尤其推崇韩、柳、欧、苏四大家散文。 刘凤的《续吴先贤赞》评其“文学韩愈氏,似之,而时有恢调,若所善,则有明以来,莫之先矣”[12]。 他在《彭文思公文集后序》一文中称:
自古以文章观时化,盖一代之兴,必有人焉。 夫辅圣主,典制作,秉笔铺张,则昭宣皇猷,裨翼史碟,而以风示天下,此非宗工硕儒不能为。 ……而前代立国,率有文章家传世,其不可忽如此。 唐兴至贞元,韩始出,宋兴至庆历,欧始出,其有所俟又如此。 ……其述作深厚严密,非仁义道德之懿不陈诸口,盖粹如也。 由我圣明言之,则文人之盛,宜在今日,有任其责而无愧者,其非公乎?[13]
杨循吉认为,文学的主要作用就是“观时化”,因此文学必须担负起“昭宣皇猷”、宣传“仁义道德”的使命;至唐宋两朝,能以文章传世的名家,当属韩愈和柳宗元,其作品起到了“风示天下”的教化作用,发挥了“文以载道”的重要功能。杨循吉的这一理论与“三杨”、“吴王”之主张几无异处。
无论是在取法对象上还是创作风格上,吴宽、王鏊、杨循吉都明显地流露出追模“三杨”的痕迹。 这固然有后起之辈尊重文坛前辈、地域文学折服主流文学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吴中文学在传统的延续上本来就具有类似“台阁体”的因素。 例如,吴中诗风平淡和婉,与台阁敦厚雍容的诗风相近。 更重要的是,吴中与“台阁”皆有欲脱离正统诗风的倾向:有意识地回避政治,沉溺于个体的自由生活中,文学的批判性大为减弱。 正是因为这些方面的不谋而合,吴中文人才会折服于“三杨”的领导,才会在创作上或隐或显地体现出台阁之风。 而这种台阁文风的隐现,一部分是吴人刻意学习的结果,一部分是吴中文学自身特性的体现。
(二)吴中文学与茶陵派
茶陵派发韧于成化年间,因其领袖李东阳为湖南茶陵人而得名。 李东阳年少成名,有神骏祥鸾之美誉。 弘治七年入主内阁任宰相之职。 正德后,由于宫廷政治的冲击和文坛风气的转移,茶陵派走向衰退。 李东阳的《麓堂诗话》是茶陵派的理论纲领。 茶陵派的主要成员有两批:一批是与李东阳同年中进士并同入翰林院者,主要有谢铎、张泰、陆、陈音等人;另一批是李东阳的门生,即他担任乡试、会试考官和殿试读卷官时所录取的举子,主要有邵宝、顾清、鲁铎、何孟春、陆深等人。这些人多为翰林出身,后来也多在馆阁任职,创作上多“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为治世之音”,雅音沨沨,气度雍容,几乎步趋于“三杨”台阁体,所以茶陵派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台阁体的延续。
吴中文学与茶陵派有着深远的渊源关系。 在茶陵派第一批成员中,出身吴中太仓的张泰、陆与李东阳进士同年,并且是早期茶陵派的核心成员。 《麓堂诗话》记曰:“原博(吴宽,字原博)之诗,浓郁深厚,自成一家。 与亨父(张泰,字亨父)、鼎仪(陆,字鼎仪),皆脱吴中习尚,天下重之。”[14]两人同为吴中人士,诗歌又皆脱吴中习尚,李东阳将他们合而论之,既表明李东阳对沉郁古雅诗风的要求,也体现出对吴人诗风转向茶陵派的肯定。
身居馆阁,与李东阳同朝为官,相互间宴饮酬唱、交流互赠,这对于身在京师的吴中文人来说并非难事。 难能可贵的是,吴中的在野文人与李东阳也交往频繁。
沈周世隐吴中,终生未仕,但其却凭借精湛的画艺、高雅的品行名闻天下。 沈周仰慕李东阳盛名,对其敬仰之至;李东阳也折服于沈周的画技,对其赞叹不已。 两人虽分处京师、吴中两地,难得一见。 但通过吴宽、吴一鹏等在籍吴中官员的往来沟通,两人得以保持长久的联系。
李东阳以台阁宿主领袖诗坛,弘奖群英,“天下翕然宗之”。 对于这位被天下文人奉为“砥柱”的文坛盟主,身为在野文人的沈周自是甚为敬仰。他曾恳请李东阳为其诗集作序,李东阳记曰:“右石田沈君启南诗稿若干卷……初,文定(按:吴宽)以写本一帙视予,予欲有所序述。 尝观拟古诸歌曲,爱其醇雅有则。 忽忽三十馀年,闻石田年益高诗益富,至若干卷,总之共若干首,间始刻于苏州,而文定已捐馆,会翰林吴编修南夫来自苏,则以石田之意速予。”[15]777李东阳对沈周的画作佩服不已,常为其题诗,如《书杨侍郎所藏沈启南画卷》《题沈启南画二绝》《沈启南墨鹅》,此外还有《题沈启南所藏林和靖真迹追和坡韵》《题沈启南所藏郭忠恕雪霏江行图真迹》等。 李东阳对沈周的折服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是享誉天下的文坛宿主,一个是仆居乡间的在野隐士,二人身份地位相差何其悬殊。 但沈周却能以一介平民身份与天下宗之的文坛盟主交流往来,这一方面归因于沈周的声名远播,另一方面则归因于李东阳对隐逸行为的认可和崇尚。李东阳虽身在庙堂,却崇尚林下生活,《怀麓堂集》中不少诗作反映了其对隐居田园的渴望与向往。 李东阳《倪文僖公集序》言:“山林之文尚志节,远声利,其体则清耸奇峻,涤陈落冗,以成一家之论。 二者固皆天下所不可无。”[15]308居馆阁,却心向林泉;喜为台阁诗,亦不忘“山林气”。 这种“不忘山林、心向林泉”的乐隐心态,成为李东阳与沈周书信往来、平等交流的基础。
与吴中和“三杨”台阁体的关系相似,吴中文学与茶陵派的关系也颇为融洽,这其中当然也有偶像崇拜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两派在某些文学创作观念上的相通。 比较吴中文人与茶陵派的诗作,他们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效法对象上,两者皆以晚唐为主;诗歌题材上,酬唱诗占较大比重,皆具元白、皮陆文风;在审美意趣上,都力图表现一种超凡脱俗、淡雅闲远的高妙格调。 吴宽曰:“予尝观古诗莫胜于唐,其间如元白、韩孟、皮陆,生同其时,各相为偶,固其人才之敌,亦惟其心之合耳;合则其言同,同则其声自有不得不同者。”[5]367因为心合,所以言同、声同,这或许就是吴中文学与茶陵派关系融洽、平等交流的原因吧!
(三)吴中文学与前七子
明代文学发展到弘治、正德年间,“三杨”台阁体已经走向末路。 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力求通过倡导浑雅正大的审美理想,来纠正“三杨”的卑靡之风。 但因李东阳等也属于台阁重臣,创作上仍受馆阁地位的钳制,并没有彻底地纠正“台阁体”的偏颇。 这一任务是由“前七子”派来完成的。 关于此三派的前后起承关系,沈德潜说:“永乐以后诗,茶陵起而振之,如老鹤一鸣,喧啾俱废。 后李、何继起,廓而大之,骎骎乎称一代之盛矣。”[16]
“前七子”是明代弘治、正德之际兴起的一个以李梦阳为首的文学流派。 康海《渼陂先生集序》描述此派曰:“我明文章之盛,莫盛于弘治时。所以返古昔而变流靡者,惟时有六人焉: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鄠杜王敬夫、仪封王子衡、吴兴徐昌谷、济南边庭实,金辉玉映,光照宇内,而予亦幸窃附于诸公之间。”[17]七子皆为弘治间进士,以李梦阳最早(弘治六年),徐祯卿最末(弘治十八年,当时尚属吴中四才子之一)。 任职京师期间,他们政治上以气节“震动一世”,文学上力主复古,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弗道”。 在李梦阳的领导下,“前七子派”阵容不断壮大,生机日见旺盛。 李梦阳《朝正倡和诗跋》对其时强大的阵容进行了描述:
诗倡和莫盛于弘治。 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 此一运会也。 余时承乏郎署,所与倡和则扬州储静夫、赵叔鸣,无锡钱世恩、陈嘉言、秦国声,太原乔希大,宜兴杭氏兄弟,何子元,慈溪杨名父,馀姚王伯安,济南边庭实。 其后又有丹阳殷文济,苏州都玄敬、徐昌谷,信阳何仲默。 其在南都,则顾华玉、朱升之其尤也。 诸在翰林者以人众不叙。[18]534-544
以李梦阳为首的复古运动在北方轰轰烈烈地进行时,在遥远的吴中地区,以吴中四才子为首的“古文辞”运动也同时兴起。 两股文学潮流虽分处南北,却不约而同地举起了复古的旗帜。 相同的时代背景和情感解放的要求,决定了这两个文学群体在复古的基本立场和理论方面存在极大的一致性。 而这种一致性,也为两股潮流的融合和交汇提供了可能,完成这一南北交融任务的便是“吴中四才子”之一——徐祯卿。
当徐祯卿于弘治十八年北上入京之时,李梦阳领导的复古运动已成蔚然之势。 对于这位才华横溢的吴门才俊,李梦阳耳闻已久,并极力想援引其加入“前七子”阵营。 为使徐祯卿尽快脱尽吴中旧习接受自己的复古主张,李梦阳与之“清宵燕寝,共衾而寐”,并不失时机地与之切磋文学、砥砺情志。 《与徐氏论文书》和《与李献吉论文书》中记载了二人一次著名的辩论。
此次论辩主要讲两个问题。 一是李梦阳根据徐祯卿的一句客套话——以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等作比喻,希望与之成为皮、陆那样唱和的诗友。 李梦阳对徐氏的这一比喻大为不满。 他列数三代舜与皋陶、成王与召康公互相庚和歌声的典故,责备祯卿“舍虞、周庚和之义,弗之式……而自附于皮、陆数子”,指斥这种唱和无异是“入市攫金,登场角戏”。 李梦阳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劝徐氏彻底断绝与唐宋文学的联系,纠正路径,直追高古。 二是略述复古要旨:“诗贵宛不贵险,贵质不贵靡,贵情不贵繁,贵融洽不贵工巧……三代以下汉魏最近古。”[18]564所谓的险、靡、繁、巧,似乎是针对吴中文学的。 李梦阳认为:“六朝之调凄宛,故其弊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而吴中文学是崇尚六朝的,由此可见李梦阳对吴中文学的批评态度。
对于李梦阳的批评,徐祯卿并没有进行针锋相对的回应,而是转而申述自己的复古观:
仆少喜声诗,粗通于六艺之学,观时人近世子辞,悉诡于是,惟汉氏不远逾古,遗风流韵犹未有艾,而郊庙闾巷之歌多可诵者,仆以为如是犹可不叛于古,乃摅其口情之愚,窃比于作者之义。 今时人喜趋下,率不信古,与之言,不尽解,故久不输其说,恐为伯牙所笑,乃一日遇足下,而独有取焉,……反复相示,更互详定,或大有疵谬,辄诋毁去,不犹愈于后人之诋笑乎。[19]
徐祯卿表明了自己的文学宗旨是返古,而且取法甚高,“惟汉氏不远逾古”,汉以下当然更不遑论。 这一说法已有向李梦阳复古论靠拢之意。“反复相示,更互详定”一句,实可理解为徐祯卿日后所取的复古立场,并希望得到李氏的进一步指导。
此次沟通后不久,徐祯卿便毅然地加入到前七子阵营,并与李梦阳、何景明鼎足成三,成为复古大潮的中间力量。 徐氏的改弦易辙,不仅仅是他单纯的个人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也代表着吴中文学对中原文学的服膺与接纳。
谈到明中叶南北文风的融合(中原文化对吴中文化的消解)这一问题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徐祯卿。 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徐祯卿虽是调剂南北文风的第一人,但却不是将北方文风带回南方(吴中)的第一人。 也就是说,徐氏离开本土将吴中文风带到了中原,却没有将中原文风带回吴中。 这一任务则是在黄省曾、袁袠、蔡羽、皇甫汸等这些吴中后劲的手里实现的。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余观国初以来,吴中文学,历有源流。 自黄勉之兄弟,心折于北地,降志以从之,而吴地始有北学。 甫氏,黄氏中表兄弟也。”[2]412可见,在实现南北文风的全面交融这一问题上,黄省曾等吴中后劲功不可没。
徐祯卿将吴中文学带到了中原,而黄省曾等则是将中原文化带回到吴中。 正是有了此二人的共同努力,吴中文学才真正实现了与中原文学的交融。 也正是有了此次南北交融的尝试,吴中文学才能够在吸收北地文学之所长后愈发生机勃发。
二、对文学独立性的尊重与坚守
在台阁体、茶陵派、前七子派先后统治文坛的明代中叶,处于边缘一域的吴中文学积极地包容、接纳各派文学,并与之进行广泛交流。 与这种包容豁达的开放性相对,吴中文学也具有一种不容置喙的独立性。 也就是说,即使已经表示接纳或者臣服于某一流派,吴中文学依然会保有一份执着而坚韧的自尊,依然会顽强地维护并认同体现本土特色的创作观、审美观。
(一)文学独立性的追求
台湾学者简锦松在论述台阁文学与吴中文学关系时说:
苏人何以重视古文词? 自苏州前辈提倡古文词前天下未始无古文词;翰林与庶吉士之教养,即以此为目标之一。 苏州此种思潮适与翰林合,而苏州名人如吴宽、王鏊又皆由翰林而阶台阁之重,古文词亦为苏人所慕,古文词之真精神,在于博学与古而能诗文,本为台阁体所大力提倡者。[20]
作者认为台阁文风对吴中文风有导向作用,而吴中文风又进一步丰富、扩大了台阁文风。 特别是在古文词的提倡上,两者彼此暗合而又相互补充。 简氏此论有合理的一面,但其“古文词之真精神,本为台阁所大力提倡者”之论,则失之偏颇。 从明初到明中叶,吴中、台阁虽皆崇尚古文辞,文风较为接近,但内涵却有所不同。 台阁重古文词,文学的成分非常有限,主要是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 明成祖有言:
为学者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并趋班、马、林、欧之间,如此立志,日进不已,未有不成者。 古人文学之至,岂皆天成? 亦积功所致也,汝等勉之。 朕不任尔以事,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尔各食其禄,日就阁中,恣尔玩索,务实得于己,庶几国家将来皆得尔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21]
这是明成祖在诫谕新进进士时所言,不难看出,其倡古文的目的是培养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甚至要时刻警惕文学家的出现。 《明史》载,太子朱高炽喜诗词,杨士奇不以为然,告诫太子:“殿下当留意六经,暇则观两汉诏令。 诗小技,不足为也。”在台阁诸家眼中,六经诗作乃是末流小技,只可一时玩味娱情,而不可真心投入其中,以免误导心志。 台阁作家“诗小技,不足为”之观念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文学创作出现重道德而轻文辞,重说教而轻情感的缺陷。
与“台阁”不同,吴中所倡导的“古文”是指与“八股时文”相对立的,为人性、人生服务的文学。吴宽对古文词情有独钟,而他热衷古文辞的原因是:
时幸先君好购书,始得《文选》读之,知古人乃自有文,及读《史记》、《汉书》与唐宋诸家集,益知古文乃自有人,意颇属之。 适与诸生一再试郡中,偶皆前列,辄自满曰:吾足以取科第矣。 益属意古作。 然既业为举子,势不得脱然弃去。 坐是牵制,学皆不成。 故累举于乡,即与有司意忤,虽平生知友,未免咎予之迁。 予则自信益固,方取向之《文选》及史汉、唐宋之文益读之,研究其立言之意,修词之法, 不复与年少者争进取于场屋间。[5]365
此文颇具趣味。 吴宽研习古文本想有助于举业,可没想到学习古文之后反而加深了对“场屋之文”的厌恶。 在浩如烟海的古文献里,他欣赏的是那些情感丰盈、生机盎然的《文选》《汉书》之类,对那些味若嚼蜡、毫无生气的制艺文章已丝毫不感兴趣。 他的朋友却不能理解其感受,固执地认为习古会妨碍科第举业。 显然,吴宽与朋友所持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习古观。 朋友的习古观,颇似台阁诸家;而吴宽的习古观,已超越经义、科第而带有关注自我生命的进步意义。 这段话向我们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在吴宽心目中,“道”的评判意识在消淡,“古文”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肯定理欲人性、尊重生活情趣的指示符号。其爱好古文和厌弃时文是出于内在自然的要求,而这种内在的自觉性无疑预示着一种时代的新动向。
在台阁诸家力倡“诗小技,不足为”之时,吴中文人并没有盲目地遵从这一训诫,而是在肯定人性的基础上意识到文学应为人性服务的命题。简而言之,服从政治需要还是服从人性需要,是台阁与吴中倡导古文词的根本区别,也是吴中文学肯定文学自身价值、倡导文学独立性的重要表现。
吴中文人肯定文学独立性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王鏊、吴宽等与台阁诸公虽皆强调取法韩欧,但两者取法的重点和用意却截然不同。 这种不同又进一步体现出吴中文人对“文学独立性”的尊重与强调。
台阁诸公尊崇韩欧,重在取法其“施政教、载道义”的一面。 明初的统治者从朱元璋、朱棣到朱高炽,文章皆尊韩欧。 明仁宗喜好诗文,尤其推崇欧阳修,杨士奇在《滁州重建醉翁亭记》中载:“我仁宗皇帝在东宫,览公(欧阳修)奏议,爱重不己,有生不同时之叹。 尝举公所以事君者勉群臣,又曰:‘三代以下之文,惟欧阳修文有雍容醇厚气象。’既尽取公文集命儒臣校定刻之。”[22]可见,明代帝王及台阁诸家之所以喜爱欧阳修的文章,一是欣赏欧阳修忠贞不二的臣子气节,二是喜欢欧阳修华贵雍容的文风,因为此文风特别适用于庙堂文学。
吴中文人推重韩欧,重在取法其“适性情、重审美”的一面。 如王鏊对韩愈一派的皇甫湜和孙樵甚为推崇,两人偏重于韩文的奇崛一路,传统观点历来对“奇崛”一路评价不高。 所谓“学韩愈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湜而不至者为孙樵”。 而王鏊则认为:“观持正(按:皇甫湜)、可之(按:孙樵)集,皆自铸伟词,槎牙突兀,或不能句。 其快语若天心月胁,鲸铿春丽,至是归工。 抉经执圣,皆前人所不能道,后人所不能至也,亦奇甚也。”[7]282像这样高度肯定创作中的“奇崛”之风,对于台阁诸人一味崇尚“平正典雅”的文学风范无疑是一种针砭。 王鏊这样做并不是故意提倡某种不合时代欣赏口味的风格,而是为了突出强调文学的审美特点。 他接着说:“昌黎尝言惟古于词必己出,又论文贵自树立,不蹈袭前人,不取悦今世。 ……则持正、可之之文,亦岂可少哉!”[7]282此处,王鏊把审美性同风格的多样性相统一,已饱含着此一认识:文学应当表现人的多样情感。 情感本身是合理的,即使某些情感的表现不合道德的规则,亦无可厚非。
吴宽、王鏊重视文学独立性、注重情感表达的观点,在吴人后起之辈手里得到了广泛的继承。面对“谓文章小技,绝口不复言诗”的社会风气,文徵明亦深有所感:
近时适道之士,游心高远,标示玄朴,谓文章小技,足为道病,绝口不复言诗。 高视诞言,持其所谓性命之说,号诸人人,谓道有至要,守是足矣。 而奚以诗为! 夫文所以载道,诗故文之精也,皆所以学也,学道者既谓不足为,而守官者又有所不暇为,诗之道日以不竞,良以是夫。[23]
文徵明认为:政务、理学、科举,此三者是导致诗歌何以不兴的根源。 三者皆无关乎诗文,故而世人将其放在无用的位置上。 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三者”皆由人来创作,人是离不开生活和诗歌的。
祝允明也十分重视诗文本身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价值,对忽视诗文价值、视诗文为末技的功利性观念深为不满:
今国家以经术取士,或以为尚文艺、异德行之科。 不知所以取之,特假笔札以代其口陈之义,所主在经术耳,非文艺也。 然其久也,遂视经术文艺为二道。 夫场屋之习,则固可为用世之业矣,而文艺之云,则又何物? 其果无与于兹道耶?[24]
场屋之文有用于道,难道诗歌文艺就无益于道吗? 祝允明的反问一语中的,言语简约而又不失犀利之气。
王鏊等人对文学独立性的尊重,并非是明中叶吴中文人自身的体悟,而是对吴中“重性命、重情趣、重文辞”之文学传统的恪守。 从文采绚烂、浪漫多姿的先秦楚辞,到天然明朗、浅俗鲜丽的南朝吴歌,再到诡奇艳丽、俊逸浓爽的元末“铁崖体”诗歌,吴中文人从未放弃过对文学独立之美的追求。 吴中文学以其明晰的发展轨迹表明:不管何种派别领袖文坛,亦不管何种文风笼罩文坛,吴中文人始终会在交流或融汇的大背景下执着地持守文学的最终使命:文学为人性之学。 文学应该与人性、现实融合在一起,而不是依附于某种抽象的道德理念或政治权威。 文学固然要承载政治,但更应歌咏人生、人性。
(二)诗文体统观的独立
坚持文学形式应有的美感,力主文学为人性、为人生服务,是吴中文学最为突出的特质。 除此之外,不受世俗观念所左右,坚守本域文学的体统观念和创作取向,亦是吴中文学独立性之重要表现。
明前期整个文坛沉浸在一片尊崇“盛唐”的喧闹声中,此种尊尚经高棅的《唐诗品汇》阐发以后,“终明之世,馆阁宗之”,遂成一代风气。 尤其是弘正年间,“崇杜尊李”的浪潮已蔓延到各个角落。 在这一背景下,吴中文人虽也尊崇盛唐,也承认李杜诗风之英伟绝资,但在实际的创作中,他们并不只崇李、杜,对杜甫亦不专推沉郁顿挫一面,反而对匠心独妙、寄兴物外的“韦柳”一派更为钟情。 对此,吴中文人见解独到。 吴宽《题重刻〈缶鸣集〉后序》曰:
诗至于杜子美。 故近代学诗者多以杜为师。 而尤得其三尺者,皮、杨、范三家而已。然文忠又谓:子美以英伟绝世之资,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 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 世以为确论。 若季迪生值元季,非不知有子美者。 独其胸中萧散简远,得山林江湖之趣,发之于言,虽雄不敢当乎子美,高不敢望乎魏晋,然能变其格调以仿佛乎韦、柳、王、岑于数百载之上,以成皇明一代之音,亦诗人之豪者哉![5]451
吴宽认为,虽然“韦柳”诗风不如魏晋之高风绝尘,亦不如杜甫之英伟绝资,但其萧散简远的清新风尚,不仅值得效法,亦足以令世人感到自豪。
谈及吴中文学的审美倾向,王鏊的见解是:
子美之作,有绮丽秾郁者,有平澹醖籍者,有高壮浑涵者,有感慨沉郁者,有顿挫抑扬者,后世有作,不可及矣。 若夫兴寄物外,神解妙悟,绝去笔墨畦径,所谓文不按古,匠心独妙,吾于孟浩然、王摩诘有取焉。[10]27-28
在王鏊看来,杜甫的诗作固然气质雄浑、风格多样,但却不是吴人兴趣之所在,吴中文人的兴趣在匠心独妙的恬淡清雅一路。
明中叶的吴中文人在理论上推崇韦、柳,在现实的文学创作中,也鲜明体现出了此派“闲适、雅淡”的诗文风格。 王世贞《艺苑卮言》有一段话专门来评论吴中诗人,其文如下:
吴匏庵如学究出身人,虽复闲雅,不脱酸习。 沈启南如老农老圃,无非实际,但多俚辞。 祝希哲如盲贾人张肆,颇有珍玩,位置总杂不堪。 蔡九逵如灌莽中蔷薇,汀际小鸟,时复娟然,一览而已。 文徵仲如仕女淡妆,维摩坐语;又如小阁疏窗,位置都雅,而眼境易穷。唐伯虎如乞儿唱莲花落,其少时亦复玉楼金埒。 王履吉如乡少年久游都会,风流详雅,而不尽脱本来面目;又似扬州大宴,虽鲑珍水陆,而时有宿味。 徐昌谷如白云自流,山泉泠然,残雪在地,掩映新月。 又如飞天仙人,偶游下界,不染尘俗。[25]
此评涉及了吴宽、沈周、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王宠、徐祯卿七位吴中名士。 从王世贞对他们创作风格的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雅、闲、淡”等字眼使用频繁,而常用于评价盛唐诗风的“雄、厚、奇、伟”等字眼却一字未见。 而“雅、闲、淡”等正是“韦柳”一派的诗风特点。 可见吴中文人对韦柳一派的尊尚,不仅仅是行之于言的,而且是付之于行的。
吴中文学独立性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能超越“主流认同”而自主选择,更在于他们能践行并固执地坚守这种自主选择。 在这一方面,徐祯卿表现得最为出色。
加入“前七子”派后,受李梦阳影响,徐祯卿的诗风的确有所改变,但并未完全脱尽吴中本色,历代评论家都看到了此点。 四库馆臣评其:“明自弘治以迄嘉靖,前后七子轨范略同,惟(徐)祯卿、(高)叔嗣虽名列七子之中,而泊然于声华驰逐之外。 其人品本高,其诗亦上规陶谢,下摹韦柳,清微婉约,寄托遥深,于七子为别调。”[26]沈德潜《说诗晬语》云:“徐昌釜大不及李,高不及何,而倩朗清润,骨相嵚崟,自独能尊吴体。”[27]赞扬徐氏能够超越“前七子”一派,在“兼师盛唐诸家”的同时“上规陶谢,下摹韦柳”,于七子成员“诗必盛唐”的呐喊声中唱出一曲清新淡雅的江南别调。
其实,吴中文人选择“韦柳”一派,创作清雅恬淡的诗歌,并不是出于标新立异之目的,而是因为此派所体现出的“淡雅、闲适”更契合吴人的心境。 吴中山川秀丽、水产丰富、土地肥沃、风光绮丽,这些优越的环境潜移默化地造就了吴人缘情绮靡的个性气质。 在审美取向上,他们喜绮丽浓郁,而不喜高大雄浑;他们重平和蕴藉,而不重感慨沉郁。 鉴于此,他们才会舍“宏大、浑厚”的李杜之音,而独取清雅幽微的“韦柳”一派。
可以说,从明初到明中叶,吴中文人在文学的审美取向上是很有见地的。 在举国文学风尚与之相悖时,他们会一定程度上向主流意识靠拢,但绝不会完全臣服、融入其中。 因为在吴人眼中,风土清嘉的吴中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求适意、重雅淡”的审美风貌才是最具美感的。 这种美感已经融入每一位吴人的心中,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审美惯性,而这种惯性是不会轻易随地域、风尚、思潮的改变而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