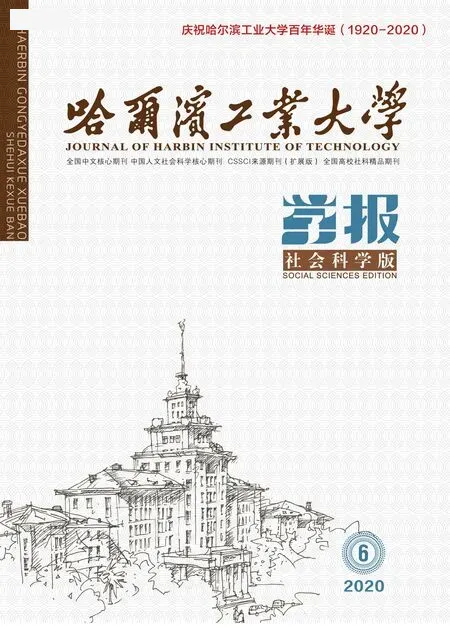《西游记》中的佛教寓意①
[美]赵美真著,雷璐灿译
(1.乔治敦大学 神学系,美国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237;2.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430072)
中国明代(1368—1644)小说《西游记》,我们称之为“Hsi-yu chi”,或“The Journey to the west”,其中蕴含的繁杂叙事, 长期以来给阐释者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西游记》中纷繁冗杂的文化色彩,特别是那些涉及中国三大宗教传统(佛教、儒教和道教)的部分——是如此的繁复多样和恣意交织,以至于它几乎显得是“娱慰或嘲弄读者的文人雅谑”[1]181。 因此,任何阐释都面临着误读或者夸大这些文化和宗教元素重要性的危险,结果往往却发现这些元素不过是作者的戏语罢了。
一、《西游记》的现代阐释
虽然现代阐释者已充分认识到在《西游记》中可能有潜在的内涵或某种未知的背景结构, 然而在世纪之交,以胡适为首的阐释者们,更倾向于只是从表层的叙事层面去看待它。 所以,他们认为《西游记》不过就是表面看上去的那样:一本有趣爆了的读物②这个表述非常生动,感谢主要从事《新约圣经》研究的学者Arthur Droge 为我提供了灵感。(a corking good read)罢了。 然而近来学界却选择了一种不同的解读方式。 例如,夏志清(C.T.Hsia)提出将这三种宗教内涵放在一种“无法协调的紧张情势”中来理解,并认为这种状态是明清小说巅峰期所激发的结果。 但这种肯定文化多样性的积极观点,并没有真正为阐释者们提供一种解读这些元素的方法。 夏志清还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原则——“它(小说)看到的人生,将一切的卑劣和崇高、兽性与神性的东西往往包含在里面。”[2]21——这实际上是表明了读者们所处的整体社会环境从历史的角度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
美国学者浦安迪(Andrew Plaks)也提出了类似的整体环境论(all-compassing)观点,虽然他所讨论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浦安迪提到的“整体性理解”(the intelligibility of the whole)实际上是描述了中国的宗教哲学世界,这也构成了他的中国式寓言理论的基础[1]。 浦安迪的理论中最具有前瞻性和重要性的部分,是指出了应该认真看待三教杂糅的修辞表达:宗教元素绝不仅仅是文学性的装饰品,它们所促成的那种深刻而可以被解读的意涵模式,是一篇小说整体结构的核心。
因此,夏志清(C.T.Hsia)和浦安迪(Andrew Plaks)等学者试图从最初的问题本身入手来寻求解决方案,从而驱除陷入困境的阐释学的阴霾。《西游记》中宗教知识的纷繁复杂不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相反,它为现代学术界提出的明代文人社会的文化融合提供了独特佐证。
综合前人已经讨论过的观点,本文提出,尽管《西游记》中确实存在且反映了一种文化融合的现象,但其中最醒目的部分仍应是明确的佛教内核。 那么为何这本小说有一个明确的佛教主题(5 名朝圣者要前往印度取得真经),但学术界却基本上都在避免从一个彻底的佛教视角解读《西游记》的主题呢? 除了文学批评领域之外,梅维恒(Victor Mair)、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杜德桥(Glen Dudbridge)等学者在对中国古典小说起源史进行研究时,已经提出了佛经与通俗故事和早期中国小说的产生有着确切的联系。 但令人惊奇的是,近期关于《西游记》的文学阐释(特别是浦安迪的论著)仍然明显将其内涵解释为理学思想。 我在这里就是想试图打破这种一直以来的解释趋势。
在主张用佛教思想解读《西游记》时,我大部分的论述都参考了浦安迪的著作。 他的新书《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是对中国叙事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这本书注定要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 他所要表达的主旨是很明晰的,即在“明代理学的影响”[3]233、特别是16 世纪出现的“心学”的主导下[3]241,形成了一种三教杂糅的思想潜流。 这种披着理学外衣的三教观,不仅否认了《西游记》中鲜明的佛教寓言式表达,而且(至少在浦安迪看来)也质疑了《西游记》是否真的以佛教主题为核心。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浦安迪对《西游记》作为一个宗教朝圣故事所具有的信仰寄托加以轻视。 对这种观点的反驳,构成了我下文对于《西游记》中佛教寓意的论述框架。
本文从佛教视角解读《西游记》,不仅仅是希望为佛教传统正名。 我会主要论述佛教思想是如何融入小说本身的结构中的,尤其是怎样使用文学技巧达到这一目的的。 虽然《西游记》故事中体现的佛法是一个标准的大乘佛教概念,但其文本从一种全新的方式诠释了这些宗教信条:如我们所熟知的“业力”(karma)、“慈悲”(karuna)、“空”(sunya) 和“方便”(upaya) 的概念,都被以文学人物和情节结构的形式进行了诠释。 这种佛法和文学的成功融合, 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应该用佛教思想解读《西游记》, 而且还应加深对其中精湛文学技巧的认识。
总的来看,这种融合让我们对《西游记》的文本文类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难道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西游记》为佛教教义提供了一种文学形式,所以我们就可以将其本身看作一个宗教文本吗? 实际上,正如历史与小说,或者经典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区别那般模糊一样,在解释这一结论时,佛教理念本身也具有模糊性。 通过探讨《西游记》中的这些争议,希望提出这些关于文本传统和文本批评历史的问题。
二、中国式寓言与《西游记》中的佛教救赎论
想要对《西游记》中的佛教寓意进行正确的阐释,就必须谈到浦安迪对中国式寓言的整体描述。 他认为基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寓言模式根本不适用于明代小说,而中西方寓言模式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它们有着不同的宗教哲学传统。 基督教完全倾向于浦安迪所谓的“本体二元论”——邪恶与善良、不完美与真理、诅咒与救赎之间的纵向脱节(vertical disjunction)。 他指出,这种神学理论是“通过立意谋篇的‘寓言’,使一部叙事文大体的结构形制,指向一层未曾直接言明的复杂的理性模式”[1]166。 西方的寓言传统始于柏拉图式的对宇宙二元论的反思,然后被基督教圣经进行了二次诠释。 通过重申高等真理的不可言说性,这种解经传统反过来又强化了宇宙二元论,但是高等真理最终必须通过一般的叙事形式进行表达。
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似乎对激进的、本体论的二元论没有什么兴趣。 中国哲学中确实存在相互依存的“阴”和“阳”、“体”和“用”的二元结构。但这不是一个激进的分离系统和随之而来的从一个本体论状态转移到另一个本体论状态的问题,而是一个“互相交替,此消彼长,无中有而又有中无的二元图式”[1]169,在它们之间划定界限是愚蠢的。
这一发现直接影响了浦安迪对中国哲学世界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哲学形成了一种寓言意义上的回环往复:“宇宙无始无终,无所谓末日审判,也无所谓目的的终极,一切感觉与理智经验的对立物,无不蕴含其间,又两两互补共济、相依共存。”[1]168这种“整体存在论”确实体现了一种寓言意义的核心。 大量的叙事元素,都似乎在娱乐读者,只有“把这些因素置于一个较大的构局和循环的结构之中,其整体就能传达出作品的意旨”[1]168,它们才能被理智、正确地解读。 与其说是因为真理的不可言说性,不如说是因为“无量无边”的宇宙需要某种形式上的表达才能被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寓言的形式是必要的。 作者没有直接为超验性真理提供媒介,而是运用文本的内部元素构造成一个可以解读的世界观。
尽管西方和中国式寓言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浦安迪对两者的根本区别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假设:在寓言主题所要体现的思想层面,西方主张的“二元对立”与中国文化主张的“二元补衬”的区别。 浦安迪提出了这种结构层面的区别,其主要观点是中国的文化语境中缺乏本体二元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方的二元论透露着从一种条件(“罪”和“堕”)向另一种条件(启蒙和救赎)转变的问题。 因此,这种思想上的运动,或者说精神上的进步,是西方式寓言的重要转折点。 相对而言,包罗万象的中国宇宙观使得这种“定向”发展的概念不合逻辑。 鉴于中国文化缺乏这种本体论上的对立,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而说到这种寓言模式,大乘佛教传统中的大多数问题恰恰是注重将内化的救赎转化为外现的宗教传统和宗教实践。 《西游记》中的主角三藏法师就体现了这一点,他是一个慈悲好善的修行者,他对外在虔诚的执着追求,阻碍了他对内在真实的感知。 因此,他无法识别披着善意外衣出现在他面前的邪恶力量。 更重要的是, 他无法透过事物的外表看到内在的心魔——这正是他需要通过修行来参悟的。
《西游记》中反复出现的诸法皆空的主题,实际上是体现了三藏法师所代表的救赎(soteriologi⁃cal)困境。 在这一点上,佛教救赎论呈现出的心性修炼的多重形式和种种困境,与浦安迪的相互渗透的中国宇宙观正好吻合。 例如,与妖魔鬼怪的反复交锋实际上并非是他们旅途中的真正阻碍,因为这些妖魔其实是虚幻的。 而严格的佛教戒律本身反倒是成为了他们精神上的阻碍。 这一点在旅途的开始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了,比如在第14 回中,当时三藏法师因为孙悟空直接杀死了威胁他们的6 名强盗而羞怒难当。 三藏法师骂道:“这却是无故伤人的性命,如何做得和尚?”[4]2:308三藏法师严格遵守禁止杀生的戒律在这里实际上是犯下了两重错误。 首先,他对劫匪真实的威胁视而不见。 其次,这种威胁更是来源于他自己的目光短浅,也就是强盗角色的象征意义:他们很明显是六种器官的拟人化,是佛教语境中的取境生识的“六根”。 三藏法师信奉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美德,只会使他对所有形式的内在本质视而不见。
标准的宗教信条和朝圣试炼会导致一种妄想,即朝圣本身不过是徒劳——其实只要呆在家里就好了。 但是,当从明确的佛教角度对这种令人困惑的世界观进行分析时,我们会意识到这实际上表明了内在精神的得道是可以实现的。 这样的分析是对中国多元宇宙和基督教二元论宇宙之间差异的另一种演绎与诠释。 这种差异是如此的两极化,以至于它可以通过类型学上的连续性或不连续性的救赎世界观来表达。 基督教本体二元论实际上表现了一种世界的不连续性,这种观点认为“真正的现实”(really real)存在于一个截然不同的、独立于世俗的领域。 正如浦安迪告诉我们的那样,那是一种从低层世界向高层世界的转变。 相对而言,佛教救赎论则肯定了世界的连续性。 救赎存在于低层世界,即它只存在于现实世界。 因此,这种精神层面上的模糊不清是源于错误的认知,而不是源于本体论的分歧。 然而,佛教的精神超越并非完全没有存在主义上的变化。 因为不参悟真理是无法拯救众生的,正确的认知——甚至是对所属状态的认知,就是一种救赎意义上的转变。
浦安迪正确地认识到了《西游记》“寓言”中本体二元论的缺失,但认识二元论还是存在的。而这种特点对于佛教的救赎模式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不考虑这种精妙矛盾的存在,那么浦安迪所描述的“互为补充的中国宇宙”确实是非常无趣的。 那些朝圣者真的还不如呆在家里。 如何在不违背本体非二元论的现实情况下,弥补认识论上的差距,是大乘佛教理论和《西游记》所面临的主要难题。
佛教所追求的那种内在的看似咫尺却又天涯、不易被参透的玄妙思想,往往是藉由心性修炼的语言来表达的。 正如孙悟空在旅程终点曾提醒三藏法师的那样:“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孙悟空接着阐述道:“但要一片志诚,雷音只在眼下。 似你这般恐惧惊惶,神思不安,大道远矣,雷音亦远矣。”[4]4:159
这些句子使用了一种距离目标近在咫尺而又远在天涯的形象描述,揭示了佛教救赎论玄妙的双重内涵。 在一个寓言意义上的又实际发生的修行故事中运用这种描述实在是恰到好处,且反过来又强化了小说中心性修炼的首要地位。 虽然在佛教思想中,对修行者自己而言,心灵朝圣的目的并不是外在的,但能够明了通向真理的目标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西游记》作为一部小说,它的优点是可以具体地展现这种心性修炼的过程。 具体来说,佛教的“空”在小说中经常出现,正是为我们的解读提供了关键的钥匙。
三、《西游记》的“空”之悖论与佛教的业力法则
想要正确体会“空”之义,我们必须回到朝圣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来。 浦安迪对这段旅程的解读,认为是毫无意义的,理由是每个朝圣者最后都缺乏一种精神层面的成长以及最后结局令人沮丧:“‘无字真经’这最后一个反讽便是个明白无误的玩笑,除非我们要着重强调中国哲理话语里常言的那种‘空灵’经卷可取的意思;那样,‘真经’最后复归一事本身又进一步贬低了取经功完的意义。”[3]243浦安迪的结论是,挽救这种朝圣体叙事的唯一方法是将其内化为“内心求道”,或者,他还有一种表述,即人们可以把这种无意义的寻求真经的过程作为修炼本身,“‘以悟为命’的唯名论观点是修炼道路上最后一个障碍”[3]254。
浦安迪得出的主旨揭示了他自己在“空”之悖论中的纠结:如果所有的表象,包括顿悟本身,都是虚空的,那么人们如何进行心性修炼呢? 想要通过坚持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来得道的尝试,只会显示出修行者并未参透所有宗教形式的“空”之本质。 这些努力最终只会导致精神上的无所适从,浦安迪认为西天取经是无意义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也印证了这一点。
尽管浦安迪对佛教教义还是持着尊重的态度,但他含蓄地指出“空”之悖论本身就是空洞的。 正如《西游记》中用《心经》来阐明,与“空”相对立的是虚幻的诸相: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因为它们本质上就是“空”。 这种佛教教义在《西游记》的黑风山一回中被完整地体现了出来,观音菩萨将自己化为了妖道:“行者看道:‘妙啊! 妙啊! 是妖精菩萨,还是菩萨妖精?’菩萨笑道:‘悟空,菩萨 妖 精, 总 是 一 念。 若 论 本 来, 皆 属 无有。’”[4]1:363这里可以看作观音的“真”与“假”形式——也就是“菩萨”和“妖魔”——之间的相互转换,实际上表明了所有虚幻的外在现象在“空”的本体论下是平等的。 因此,菩萨和妖魔之间“真”与“假”的相互转换和“虚”与“实”之间的相互渗透,两者的关系其实是平行的。
现在,我们已经摆脱了“空”之悖论的束缚,各种解读的可能性都向我们呈现了出来。 例如,在西行途中遇到的妖魔鬼怪可能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 浦安迪认为,与这些难以消除的“魔”(mara)的周期性接触,只是为了表现出修行者们缺乏精神上和感知上的进步。 然而,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魔”的存在其实发挥了一种积极的叙事功能。 它们存在的意义不是反复印证修行者在精神层面的迟钝,而是宏伟的小说叙事结构的一部分。
要理解这种设定,最简单的方法是从佛教意义上最显而易见的层面入手:即业力定律在《西游记》的世界观中无处不在。 在中国古典小说之前流行的文学体裁中其实早已有先例。 梅维恒(Victor Mair)和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都指出了在宝卷(precious rolls)的文本中业力主题已经非常流行。 梅维恒[5]23将宝卷的文本描述为发生在唐朝的“戏剧艺术的根本革命”的产物(pien-wen 变文);普实克认为,多样化的宝卷文本是在作为说唱文学的变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两者由于都“歌颂业力”而联系在一起,前者最终形成了韵文的形式[6]378。 他补充说,“这样的主题对中国通俗小说的所有其他分 支 都 有 着 很 大 的 影 响”[6]386。 内 田 道 夫(Uchida Michio)[7]则始终坚持《西游记》深受佛教信仰和佛教故事的影响,他试图把这部小说解读为一个通过化身取得业力层面的超越的故事。
然而,中国通俗小说以业力因果为核心,往往形成了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文学作品。 普实克将业力等同于“单纯的道德概念”,认为它“消弭了所有本不应发生的悲剧和悲情”,并总结为“虚幻的道德规则”[6]386。 夏志清也同意这一观点,他提到了这种业力法则所导致的“幼稚不真”[2]21,“仅能做个情节剧的或假虔诚的小把戏而已”[2]29。
这种观点非常尖锐,值得我们去探讨。 在孙悟空首次被三藏法师(第27~31 回)驱逐后,在随之而来的系列剧情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贯穿始终的道德主题。 这种道德基调显然是来自儒家思想,它在师徒的“忠孝”关系和符合礼制的人际关系主题上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方面体现在悟空和三藏法师的矛盾,另一方面也体现在黄袍怪和宝象国公主的私通。
在前者的剧情中,儒家的“忠孝”主题被呈现得质朴而又深刻。 孙悟空被师父三藏法师驱逐的时期,被描述为其精神堕落回“妖”的时期。 当八戒终于成功地将孙悟空劝回朝圣的队伍时,悟空坚持要净身,并说:“你那里知道,我自从回来,这几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 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4]2:85如果“妖精气”被解读为孙悟空精神堕落的隐喻,那么很明显,最终能够和解是由于师徒之间不可分割的纽带。 正如在另一个场景中,黄袍怪挑衅地说:“既受了师父赶逐,却有甚么嘴脸又来见人!”悟空回答说:“你这个泼怪,岂 知 一 日 为 师, 终 身 为 父, 父 子 无 隔 宿之仇!”[4]2:91-92
考虑到黄袍怪与宝象国公主的私通是不符合世俗礼教的,那么孙悟空因其违背儒家礼教而惩罚黄袍怪就是恰当的。 公主在给父母的一封密函中表达了她深切的痛苦,她声称自己已经败坏人伦,有伤风化[4]2:55。 孙悟空用孝道训诫公主,欲劝她回家,于是发问:“却怎么将身陪伴妖精,更不思念父母?”[4]2:88这种不自然的混合主义主题贯穿了《西游记》始终,但在这一事件中解决道德困境的独特方案却是“业”与“命”。 后文中我们才知道,黄袍怪和公主前世都位列仙班,二人立下誓言要一起下凡,在人间结为连理。 他们现世对道德和人伦的败坏是可以从“业障”的角度来解读 和 消 除 的。 这 正 是, “一 饮 一 啄, 莫 非 前定”[4]2:95,这也预示了小说的结局,在文学技巧上和袈裟的神力异曲同工。
但是诚然,以上的解读还没有抓住真正的重点。 业力仅仅是进入更宏观的大乘佛教救赎论的切入点,而这种论述又依靠文学技巧得以升华,虽然有一些人对这些技巧不屑一顾。 “业力”为小说提供了文学意义上和救赎论的基本框架。 余国藩(Anthony C. Yu)[8]124早已认识到应该将《西游记》看作一场源于业力因果和以自我救赎为目的的朝圣之旅[9]219。 由于每个朝圣者曾经犯下的“业”和所种下的“因”,所有人都必须踏上自我救赎的旅程,以清空他们的功德业力簿。 余国藩是这样表达的:“佛子还来归本愿,金蝉长老裹旃檀。”[4]1:186其中提到了三藏法师还是他的前身“金蝉子”时在佛祖讲道时睡着了,而产生了“业”。 实际上所有朝圣者的前世今生中都有这样类似的业力因果。
从业力的角度进行思考,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些循环往复的考验与折磨。 例如,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那些虚构的妖魔鬼怪的存在意义。 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看,朝圣者与妖魔的斗争说明了他们必须承受这种赎罪之痛,去了结他们曾种下的业力之“因”。 这种一报还一报的法则是如此清晰明确且无法改变,以至于这种强制性的痛苦可以被精确计算为九九八十一难。 这些考验都是注定的,虽然三藏法师每次都上了这些虚幻妖魔的当,但是它们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表现三藏法师的迂腐蠢笨。 恰恰相反,正是这些源于业力因果的虚幻妖魔,才能使得朝圣者们到达终点,取得真经。 这种“魔”是取经路上必要的过程,而不是路途上的阻碍。 更宏观来看,这些虚幻的表象并非预示着“空”之悖论所导致的宗教困局(religious paralysis)。 甚至恰恰相反,它们直接证明了终极意义的“虚”与现实意义的“实”其实都是平等的——因为二者实际上都促进了心性修炼。 真正的悖论其实是,即使三藏法师有着坚持遵守宗教教条的强烈意志,也并不代表他会一直那样固执。
业力的法则在《西游记》中随处可见,这表明了其内涵十分深奥,绝不仅仅是一种因果相报的世界观,更宏观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其普遍性上:朝圣者的业报之旅与他人的业力命运相互交织,正如许多情节中所揭示的那样,朝圣者所积的“善果”同时也与其他角色的业报相互交织。 因此,朝圣者们在西行取经的旅途中实际上也成为了其他角色命运业报中的重要一环。
这种“力”在乌鸡国和朱紫国两回的剧情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这两回都讲述了相似的故事,即这两国的君主都因为冒犯了神佛而招致了业报。 这种业报的实施者是妖魔,他们的关键作用再次被描述为——他们是在为国王“消灾”。 通过让君主遭受各种劫难,妖魔会驱散代表灾祸的“业”,但是往往也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这些剧情设定使得朝圣者们能够在恰当的时间找到和制服妖魔,了结皇权命运的“业”,同时为自己创造价值。
这样的机会使得朝圣者们自己和旅途中所有的邂逅都能受益。 在经受磨难的同时,朝圣者们也把其他角色带入了佛教的统一体系中。 这个主题反复被没有悟道的妖魔提出来,他愤怒地质问孙悟空:“你原来是大闹天宫的那厮,你既脱身保唐僧西去,你走你的路去便罢了。 怎么罗织管事!”[4]3:349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朝圣者们和其他人的心性修炼之路相互交织。其实除了这种命运般的联系,还有一点是因为佛教普度众生的慈悲观。 考虑到这种慈悲之心,我们就可以跳出业力推动的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充分满足因果定律的叙述模式可能会导致一种道德决定论,但最终众生得到的解放与救赎,表明了在因果业报之下的最终目的仍是慈悲为怀,普度众生。
整部小说确实常常为了最终的目标而刻意制造阻碍。 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许多普实克所谓的“虚构的道德体系”的例子。 其实一开始,这种注定的考验就有着一种矫枉过正之感。 这一点在第99 回观音菩萨的考验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尽管师徒一行人已经取得了真经,但她还是马上又再制造一个考验。 太上老君告诉孙悟空,观音为了考验他们的决心和毅力,才将老君的道童化为妖魔,这样看来这种取经途中的考验几乎就是故意设置的。 这让孙悟空在九霄之上都愤愤难平。 孙悟空这样说道:
这菩萨也老大惫懒! 当时解脱老孙,教保唐僧西去取经,我说路途艰涩难行,他曾许我到急难处亲来相救;如今反使精邪掯害,语言不的,该他一世无夫![4]2:162
尽管孙悟空因为观音菩萨的所作所为而怒气冲冲是可以理解的,但观音的有意为难其实可以用佛教意义上的方便法门(skill-means)来解释。菩萨有着无上的智慧和慈悲,会用真的大智慧普度众生。 这种使命不仅包括,甚至就是确实需要“有意为之”来引导每个个体消除业障、修炼得道。 通过这种深层次的剖析,我们可以解读出取经之行背后超越业力的意义所在:与其说是一种为了消除业障的强制性考验,倒不如说它是为了实现小说显而易见的心性修炼的目标而故意设置的。
一旦我们从“方便法门”的角度来解读《西游记》文本的主要框架,就可以意识到全文实际上是在重演和强调这场朝圣之旅的序言。 在介绍孙悟空和三藏法师的人物背景之后和真正开始西天取经的旅途之前,发生了一系列看似与故事主题毫不相关的事件,即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 其造成的最终结果是观音菩萨因此选中了玄奘作为取经的朝圣者。 然而,这个故事最主要的部分都是在阐述唐太宗自身在阴曹地府行走一遭而有所悟带来的“果”,给天下生灵,甚至为地府的亡魂都带来了善报。 唐太宗此行让人联想到了佛教“目连救母因缘”的典故,虽然目连的故事主要是为了表达儒家对孝道美德的追求,但佛教慈悲为怀的教义使得目连最终从阴曹地府将母亲拯救了出来,获得了真正解脱。
第8 回中观音菩萨从印度西天远赴中土的旅程,则可以视为朝圣之旅的另一个缩影。 观音此行也为西行的救赎之旅拉开了序幕,因为她将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从他们苦痛的现状中拯救出来,让他们作为唐僧的弟子,保护他西天取经。 唐太宗、观音菩萨和师徒五人——他们这一系列的“朝圣之旅”,都是宏大的小说架构的一部分,这些精巧的情节设计最终达到了普度众生的目的。 这种“力”正是“方便法门”的本质与精髓。
浦安迪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那位腾云驾雾的猴子不可以一个筋斗越过喜马拉雅山去把那部渴望已久的真经取来,使他那位凡胎肉躯的师傅也可以免受更多的苦难?”[3]243这个问题也体现在八戒在流沙河的东岸对孙悟空抱怨说:“哥啊,既是这般容易,你把师父背着,只消点点头,躬躬腰,跳过去罢了,何必苦苦的与他厮战?”孙悟空的回答清楚地回应了这一问题:
但只是师父要穷历异邦,不能够超脱苦海,所以寸步难行也。 我和你只做得个拥护,保得他身在命在,替不得这些苦恼,也取不得经来。[4]1:436
结合前文的论述,孙行者的回答中所隐含的道理是很清楚的。 结合佛教救世机制中消除业障、祛除苦难、方便法门(skill-means)和慈悲之心的相互交织,我们最终可以得出一个无可争辩的结论——取经之旅本身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正是核心所在。 没有取经之旅,这种救赎机制也无法成功运行。 这种机制必须接连不断地出现,这是因为《西游记》世界观中的核心问题正是“道”与“法”的有无。 通过积极入世和进行宗教实践来得道,其本质上与我们前文提到的“空”之悖论是一脉相承的,在这种理解下,即使是“魔”本身也可以促进心性修炼。
既然这种宗教实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阐述,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取经之旅的结局呢? 浦安迪认为西天取经的结局不过是“最后一个反讽”,也就是获得了无字真经——我们该如何反驳这一观点呢? 实际上朝圣者们所取得的无字真经并没有一丝一毫的讽刺意味。 正如我们在关于佛教救赎论的讨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得道并不是外在的,因此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也不能是物质的。 然而,这也并不代表它是可以轻易得到的。 用看似咫尺却又天涯来形容得道的空间意象,形象地体现了修炼和得道的二者之间的相互偶然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没有必要对结局的解读采取如此严格的态度:它可以被看作对语言的“空”进行的最后的不可抗拒的点化。这种小小的嘲讽幽默相对于其严肃的思想内核而言无伤大雅。 其实这种嘲讽恰好与禅宗文献中对语言文字的贬低相呼应,对佛教教义本身并没有任何威胁。 禅宗本就倾向于打破与揭穿传统的佛教偶像,这实际上表明了戏说那些严肃的主题是可以被允许的。
四、《西游记》的文本性质与创作意图
如果不辨明小说对于宏观的中国佛教文本传统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对《西游记》中佛教寓意的解读就不可能是完整的。 我认为,我们将《西游记》看作一部虚构的小说的同时,也可以将其看作佛教宗教文学作品。 这一问题不在于作者吴承恩是否这样看,而应在于其文本本身表现出了怎样的内核。 这种思想内核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长久以来,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文本体裁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佛教教义和文学形态之间的诗意渗透。 在这一过程中,源于狭义理解上的自我修行从而形成的一种近似“戏说”的佛教救赎论,与佛教的顿悟说,都是在文学文本的形式上达成了“解脱”。
我们把《西游记》看作一部宗教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正视了小说中出现的佛教元素,事实上,这也意味着将一部通俗小说归纳为一部宗教典籍。 这两种作品形式的意外融合,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一种假设。 正如余国藩[9]对我们一直认为的常识——任何与宗教相关的都是庄严而虔诚的——提出的质疑,我们需要对那些看似与神圣的宗教典籍相悖的想象部分进行研究。
说到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棘手的概念,也就是“正统”问题,即小说是否符合传统权威的佛教经典的设定。 其实所有的宗教都宣称拥有大量的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传世经典,同时也有一些人提出,这些经典构成了一种权威的文学体式。尽管亚洲的佛教传统几乎没有对经典文献的文体进行过限制和干涉,但文本合法性与正统性的标准一直是各宗教流派争论的根源。 最早的巴利语文献(Pali literature)就是通过佛陀的真言(即佛语:Buddha-vacana)确立了经典的标准。 然而,佛语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解释:首先,史学家将其从字面上解释为释迦牟尼真实演讲的记录;其次,功能语言学家认为,佛语是指任何具有宗教效力的语言文字。 毫无疑问,前文关于《西游记》中运用“方便法门”来普度众生的论述,实际上是说明了在大乘佛教传统中第二种解释占据主导地位。 通过这种推理,将《西游记》纳入宗教文本体系就无可厚非了。
这种观点稍显轻率和教条主义,但它确实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需要去辨明在中国佛教语境中权威经典的标准。 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虚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西游记》中被认为的想象与虚构,这涉及宗教文献中能否存在通俗文学文本的问题。 虽然佛经作为最初的动力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现和发展,但这并不能代表小说可以成为权威的宗教文献的一部分。 虚构的文本可能涉及虔诚的宗教信仰,但它在本质上仍然被认为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低等级的存在;或者从某种更坏的角度而言,它代表了宗教的堕落(或者说人人皆可得之)。梅维恒对文本是否具有专业性或独特性提出了一个假设[5]9,提出变文是说书人所创造的,因此不同于宗教僧侣的讲唱(chiang-ching-wen 讲经文)。
然而,这种假设在中国佛教语境中并不一定成立,我们一旦考察到宗教文本相对于宗教思想和宗教实践而言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就会明白这一点。 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在他关于文类的理论著作中[10]为这种文本形式提供了一种意义深远的理论基础;白居迪(Judith Ber⁃ling)在最近的一篇讨论禅宗语录(recorded say⁃ing)体裁[11]56-88的文章中,更是给予了这种作品更公允的历史地位。 她对佛教文献演变的考察不仅展现了文本形式的发展历史(所有这些文本都宣称是权威典籍),而且还讨论了文学体裁本身的构成, 指出了“文类的形式或者内容实际上都是宗教团体观点的具象化”[11]58。
白居迪对这种宗教的演变兴趣颇深,她试图弄清楚宋代(960-1279)佛教语录中反传统和充满矛盾斗争的内容是如何被视为正统佛教语录的。 当反常的反传统的语录开始出现,其中某些例子甚至可以追溯到印度佛本生(jataka)故事传统,这实际上是为了让已经确立的文本传统传续下去。 禅宗语录指出了中国佛教传统文献中存在很多自相矛盾甚至是有点戏剧性的颠覆观点。 例如,语录中提到用经书中的文字记录来表达“大悟无言”的教义,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 尽管这样把“无言教诲”记录下来的讽刺之举,有可能破坏了佛学传教的完整性,但语录也难能可贵地为我们保留了历史上宗教实践的证据。 由于佛教教义在寺庙间的流传,把佛教大师的公案(pub⁃lic cases)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流通货币”,最终导致人们自发地将那些话语和行为故事编纂成了文本。 这些文本的出现反过来又促进了宗教实践,例如将公案用作说教的手段,甚至作为冥想的对象[11]76-83。 白居迪认为,这种宗教文本和宗教实践的相互渗透,是“在激进的大乘佛教观下形成的禅宗独特的佛教语言模式”[11]83——《西游记》也正是用恢弘的文学气势掩盖了其思想内核的“空”。
语录和《西游记》其实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它们都为“空”之悖论可能造成的宗教困局(reli⁃gious paralysis)提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显示出文本对于宗教而言和其本身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早在大乘佛教的开创性经典《妙法莲华经》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一点,该经将自身视为一种宗教文本,从而表现出了一种特殊的自我关照。 其中以第16 品最具代表性[12],经文中指出,要信解如来诚谛之语,这比执着于“一心欲见佛,不自惜身命”更为重要,佛语皆实不虚,佛语就是佛法。 这一主张的意义在于“是一种把源自佛陀(语言和行为)的佛法载入留给信徒的佛经中的,润物无声而又意义深远的传教”[11]67。这一主张也带来了随之宗教实践的转变和发展。 遵从《法华经》的告诫去抄写佛经,被认为是一种值得赞扬的行为。 在众生眼中,佛经常被视为护身符,朗诵佛经可以拥有抵御恶魔和邪恶的力量。
这种做法在《西游记》中,当三藏法师从浮屠山的乌巢禅师那里收到《心经》时,更是被直接指明了。 乌巢禅师教导三藏法师如何诵读《心经》:“若遇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4]1:393要明白这一情节的意义所在,就不能不提到在世俗认知中佛经所具有的神奇力量。 这种力量的来源就是《心经》的文本本身,因为它是无上智慧的总和,它是“无上咒”,是“大神咒”[13]。
宗教文本所具有的救赎功能(不仅仅具有解释的功能)是多样化的,它超越了物理保护或者单纯护身符的作用。 虽然禅宗语录中保留了那些佛教教义与具体宗教实践相矛盾的部分,但它还是为宗教实践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创新性的“解”(solution)。 如果不能理解宗教文本与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就无法理解这种“解”,这一点也反映在文本的内容和形式中。
终究,我没能找到证据证明《西游记》曾被视为是和《妙法莲华经》以及语录一样的宗教文本。将佛法巧妙地融入小说中,是对既往宗教文本传统的延伸与发展。 但是其未能被信众广泛地作为修行与实践的对象,这一现实妨碍了我们将《西游记》归类于权威的宗教典籍。 然而,关于经典标准的讨论,引起了我们对既往《西游记》整体解读传统的质疑,确切来说在我们眼中《西游记》已经转变为佛教文学的杰作。 因为《西游记》运用独具匠心的文学技巧解决了佛教教义和宗教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大乘佛教世界观下本体论上的连续性与认识论上的不连续性之间的混淆——所以我们可以将其文本视为宗教实践的对象。
如果这样的推论似乎还不能令人信服,那就让我谈谈最后一个问题:作者意图。 《西游记》的作者意图与寻常主要关注历史批评的作者意图迥然有别,《西游记》真正的创作意图一直在折磨着文本阐释学领域的学者们。 而我最感兴趣的是《西游记》的思想核心和文学整体。 我并不是要轻视吴承恩对自己作品的理解,但我确实要对浦安迪得出的结论——由于明代小说产生于统一的理学文人环境,所以我们必须将其解读为以理学为核心的作品——提出质疑。 无论我们如何挖掘与还原出了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人生历程的细节,文本本身才应该是我们论述与研究的主要证据。如果没有意识到《西游记》中那些情节和线索是被有意设置的,就很难梳理出《西游记》中杂乱交织的佛教脉络。
我不想说吴承恩是一个彻底的佛教徒,也不想说那些理学分析是不正确的。 毕竟,中国文化对待事物的多样性和矛盾性,往往是求同存异而不是全面否定。 作者创作的天分正是在于能够很好地传达出他思想遗产中所有的宝贵要素。 余国藩谈到“作者结合佛道的企图并非是自觉性的”[8]229,也正是暗示了这一点,这实际上表明了作者自身就是其自我思想文化的一个投射。 无论作者对这一切的终极内涵持什么观点和态度,他创作的文本都保留着一种整体性,让他人可以通过自己多样化的情感去进行解读。 一部真正的杰作所体现的内涵绝不仅仅是作者有限的想法能够决定的,它自身便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完整生命体。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难道不能把《西游记》看作一个在全新的层面上,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的文本吗? 这种形式反映了小说所处时代的文化资料,主要是当时佛教传奇故事的流行。正如我试图阐述的那样,《西游记》的理论内核如实地体现了大乘佛教思想,正是这种思想内核使得通过虚构的形式来现身说法都如此顺理成章。 这部小说的形式是服务于和脱胎于其主要的阅读功效的——那就是向读者们揭露救赎的本质。 《西游记》成功地以救赎论为核心形成了文本和吸引了读者,实际上就是证明了,这部文本本身就是无上佛法的具象化,是佛教意义上的“方便法门”。 在我看来,《西游记》是一个世俗的、调侃的故事,而不是一篇严肃而漫谈的佛法论,这种说法应该更让佛教徒们喜闻乐见吧!①除了引文所涉及的参考文献之外,本文还参考了以下文献:CAMPANY R. Demons, Gods, and Pilgrims: The Demonology of the Hsiyu Chi. 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7:95-115,1985;DUDBRIDGE G. The His-yu chi: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RUSEK J. Researches into the Beginnings of the Chinese Popular Novel .Archiv Orienální,1939:11:91-132;GROOT J.J.M.DE.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Ch'eng-Wen Publications,1969;LOPEZ D.S,JR. ed.Buddhist Hermeneutics.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8;ORZECH C. Cosmology in action:recursive cosmology,soteriology,and author⁃ity in Chen-Yen Buddhism.University of Chicago,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