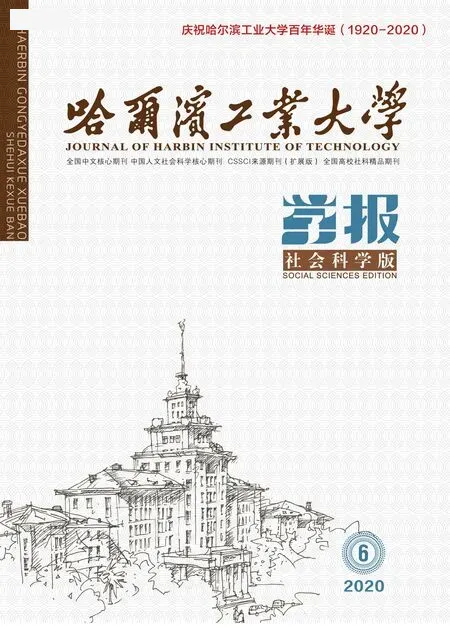马尔库塞革命理论的“自然—生态”维度
申扶民,李玉玲
(广西民族大学a.文学院; b.马克思主义学院,南宁530006)
法兰克福学派以其社会批判理论而闻名于世,其中,相对于学派其他成员,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 在马尔库塞的著作当中,他毫不隐讳其激进的革命锋芒,其社会革命思想广为人知、影响深远,在20 世纪60 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运动中颇受推崇。 马尔库塞的革命理论不只是着眼于人类自身,而是从一个更为宏阔的视野,即从人类置身于其中的自然以及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来探讨人类社会的变革。 长期以来,马尔库塞“自然—生态”维度的革命理论一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和关注,尤其是其对革命与“自然—生态”相互关系的探讨,更是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就此问题做一些初步的阐发。
一、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然与革命”思想的发掘
在1972 年出版的《阻拒革命与反抗》一书中,马尔库塞明确提出了自然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将自然当作解放的领域,是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题。 尽管人们一再重新阅读和阐释,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主题。 ……正是在这里,‘自然’找到了自己在革命理论中的位置”[1]63-64。 1932 年,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首次公开出版。 自此以后,这部《手稿》在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各种解读和阐释。 然而,在马尔库塞看来,“自然与革命”的主题却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实际上,马尔库塞是《手稿》的最早研究者之一,就在《手稿》出版的同一年,马尔库塞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的文章,对《手稿》进行了评论,这是最早的《手稿》研究成果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马尔库塞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这部马克思早期作品的重要意义,那就是自然与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革命理论的终极理想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实现。 共产主义革命“本身标志着——除了经济剧变——人类整个历史中的一场革命及其存在的定义:‘这个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冲突的真正解决’”[2]5。 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统一为标志的。
马尔库塞将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解释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统一的中介和纽带, “通过对象化,人与对象的特定关系,人的生产方式,更具体地确定为普遍性与自由。 对象化——将人定义为‘对象性的存在物’——不是简单的对人与自然统一的进一步定义,而是这种统一的更密切、更深层的基础”[2]17。 作为人与自然统一基础的对象化,表明“自然作为人类的手段,其意义不仅仅意味着人类的肉体生存仅仅依靠客观、有机和无机的自然作为生命的手段,或者在他的‘需要’的直接压力下,他‘生产’(占有、对待、准备等)客观世界作为食物、衣服、住宿等对象”[2]16-17。 人对自然的对象化活动并非是纯粹为了满足肉体生存的经济活动,“马克思在这里明确谈到‘精神的、无机的自然’‘精神滋养’以及‘人的肉体和精神生活’”[2]16-17。由于自然对于人的存在具有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价值,因此,在对象化的过程中,人类可以超越狭隘的经济利益,与自然建立多维度的关系。
人对自然的对象化是通过劳动来完成的。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非但未能给人带来解放和自由,反而成为禁锢和奴役人的工具。 这种异化劳动的本质在于,资本家将自然完全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通过受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劳动从中榨取最大的利润,其结果是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双重奴役,人的身心遭受极大的摧残,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 因此,人的解放必须以解放自然为前提,人只有摆脱了对自然的异化劳动,才能获取自由。 马尔库塞特别强调这一思想在马克思手稿中的重要性:“从一开始,被批判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基本概念,就不是简单地被当作经济概念并加以批判,而是被视为人类历史关键进程中的概念;因此,通过对人类现实的真正占有以实现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将变革整个人类历史。”[2]9这种革命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具有客观的基础,即人类无论在本然的层面、还是在实然的层面,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自然而存在,“人就是自然。 自然是他的‘表达’,‘他的工作和他的现实’。 无论何时我们在人类历史上遇到自然,它都是‘人的自然’,而人就其自身来说也总是‘人的自然’。 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在多大程度上‘人道主义’ 就是‘自然主义’”[2]17。 “人的自然”以及“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等同,意味着对自然的解放同时也是对人的解放。 而要解放自然,就必须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
为此,人首先要对自身及其在自然中的地位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对人的“感性”界定是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所在,“马克思说:‘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是被动的、受制约的、有限的生物’。并说:‘感性的就是被动的’”[2]20。 人的感性特征决定了人的有限性和被动性,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不可能脱离自然而受到自然的制约。 有限的、被动的感性并非人的缺陷,相反,它成为革命的一个突破口,“在马克思这里,正是感性这个概念导致了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革命理论的决定性转变”[2]21。德国古典哲学以其同感性相对的思辨理性而著称,马克思将这种停留于纯粹思辨理性的哲学称之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它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社会革命。 只有当哲学付诸感性的实践活动,才能引发历史的变革,因而马克思认为“感性具有破坏旧历史的潜能”[1]63。 感性的这种潜能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实现,“我们现在必须提出这样的劳动概念,它与将人定义为‘自然的’和‘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有内在关联,我们将发现正是在劳动中,不仅痛苦和需要,而且人的普遍性和自由是如何成为现实的”[2]22。 这样一种彻底摒弃了异化的劳动,不再将自然视为私有财产,从而在根本上修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只有现在,在作为人与自然统一的人的全部本质已经通过对象化的实践—社会—历史进程而变得具体之后,我们才能理解人作为‘普遍的’和‘自由的’类存在的定义。 人类的历史同时也是‘整个自然’的进程;他的历史是整个自然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在他与整个自然的‘普遍’关系中,自然最终不是限制或外在于他的东西”[2]24-25。 在这种新型关系中,自然由以前的“私有财产”变为“真正的财产”,它服务于人的本质的自由实现。
由此可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与人的异化劳动相对应的自然是私有财产,而与人的自由劳动相对应的自然则是真正的财产,“在私有财产的情况下,当一个对象可以使用时,它就是‘财产’;这种使用要么在于直接消费,要么在于能够被转化为资本。 …… 与此相反,‘真正的人类财产’现在被描述为对它的真正占有”[2]32-33。 对自然的真正占有,意味着自然对于人类超越了纯粹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它将不只是表现为原材料——有机的或无机的物质,而是作为有其自身权利的生命力量,作为主体—客体而表现出来。为生命而奋斗成为人与自然的共同主旨。 于是,人将成为一个活的客体;感觉就会‘为了物的目的而将自己与物联系在一起’”[1]126。 在自由劳动对自然的占有中,人与自然形成了互为主客体的关系,人对自然的尊重以及二者的共生,取代了异化劳动对自然的压榨以及由此导致的二者的对立。 在马尔库塞看来,自由劳动对异化劳动的取代、真正财产对私有财产的取代“不是结束,而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开始”[2]33。 由此拉开帷幕的革命前景,正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所展望的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 概言之,马尔库塞从《手稿》中所发掘出的新的革命思想,就是只有解放自然,才能解放人类自身,这是互利双赢的革命,而非你死我活或两败俱伤的革命。
二、自然审美的自由革命意涵
马尔库塞非常重视自然审美与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强调自然审美的自由革命意涵。 马尔库塞从“审美”一词的历史演化中,发掘出其自由内涵,“在哲学史上,审美这个词的目的在于这样一个领域,它在现实的自由中保存了感觉的真理”[4]173。 “审美”的字源义是“感性”,它的目的在于追求现实世界的自由王国。 自然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最为根本的感性世界,就是人类追求自由、实现自由的疆域。 就此而言,自然审美“恢复了虚耗于永不停歇的竞争活动中不复存在的感性的审美特性,正是这些审美特性揭示出自由的崭新性质”[1]60-61。 马尔库塞的这些思想观点源于自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家,包括康德、席勒和马克思。 通过对这些哲学家思想的解读,马尔库塞阐释了自然审美的自由革命意涵。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是第一位明确将自由与自然审美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马尔库塞认为这是康德思想当中最为革命性的地方,“第三批判当中最进步的概念所具有的真正革命意义尚未得到探究。 艺术中的审美形式以自然中的审美形式(自然美)作为相互关联之物,更确切地说是所渴求之物。 如果美的观念不仅与艺术、而且也与自然相关,这不只是类比,或将人的观念强加于自然——它是这样一种洞见,即作为自由象征的审美形式,既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或契机?),也是自然宇宙存在的客观属性”[1]66-67。 作为自由象征的自然美,排除了实用性的功利目的,在自身的无目的性中蕴涵着人类实现自由的合目的性。 对自然的非功利审美反映了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和“无规律的合规律性”,这两个范畴“界定了真正的非压抑性秩序的本质。 第一个范畴规定了美的结构,第二个范畴规定了自由的结构。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在被释放的自然与人的潜能的自由游戏中所产生的喜悦”[4]178。 其中,在“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自然审美活动中,自然“不是根据其有用性,依照其可能服务的任何目的来表现和判断的。 在审美想象中,对象自由地成为自身。 ……在一种新的意义上,主体与客体获得了自由”[4]179。 康德的第三批判通过审美将人的自由与自然联系起来的思想,不亚于第一批判的“哥白尼式”革命,“在第三批判中,人与自然在审美的维度结合起来,自然僵硬的‘他性’被消解,美表现为‘道德的象征’。在此,自由王国与自然王国的统一,既不被视为受自然的控制,也不被视为使自然屈从于人的目的,而是赋予自然一种理想的合目的性:‘属于它自身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1]73。 正是从康德的自然审美理论中,马尔库塞发现了人性从功利目的的禁锢中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潜能。 从生态的角度来看,由于对自然非功利的审美使之摆脱了人类的控制和掠夺,自然美成为了生态道德的象征,意味着以统治自然为目的的传统功利主义伦理可以在非功利的自然审美中被超越,从而产生马尔库塞所说的解放的巨变——人与自然和平共处。
作为康德思想的衣钵传人,席勒进一步深化了自然审美的革命内涵,“在《判断力批判》出版几年之后,席勒就从康德的思想中,引申出一种新的文明模式的想法”[4]178。 席勒的新文明模式想法,集中体现在他的《审美教育书简》一书中。 马尔库塞认为,这部著作“旨在借助审美功能的解放力量,实现重建文明的目的:审美功能被认为包含着一种新的现实原则的可能性”[4]181。 席勒眼中的新文明模式,就是旧文明模式所存在的各种对立冲突,通过审美的方式得以化解,归于和谐统一,由此重建文明。 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是建构新文明的一个重要前提,席勒敏锐地发现了工业社会中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尖锐对立,马尔库塞特别引用了席勒的一段文字,来描述工业文明所存在的这种对立给人带来的不幸遭遇,“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 永远被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单的碎片上,人把自己也变成只是一个碎片。 耳朵里所听到的永远只是由他操作的机器轮盘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声音,他从未使自己的存在得到和谐发展”[4]187。 人在工业文明中所从事的劳动,是一种致使人被奴役的异化劳动,它是人类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极端对立的表现形态。 由于现有的文明模式无法调解这两种冲突之间的对抗,席勒引入游戏冲动来进行调和,因为游戏冲动“以美作为它的对象,以自由作为它的目标”[4]188。 马尔库塞认为,就自然审美而言,游戏冲动并非同自然物嬉戏,它有非常严肃的目的,“追求的是‘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将人从非人的存在条件中解放出来”[4]188。 也就是说,人们是在游戏冲动的自然审美过程中,获得了自由。 一方面,自然作为审美对象,“就不是作为被人控制的东西(如同在现存的文明中那样),而是作为‘沉思的’对象。 ……当从残暴的控制和剥削中解放出来,而被游戏冲动所塑造,自然也会从其自身的粗野中解放出来,并且将自由地展示它无目的的形式的财富”[4]190-191;另一方面,人作为审美主体,“审美经验将消除那种将人变成劳动工具的残暴的和剥削的生产力。 ……摆脱了贫困和焦虑之后,人类活动就成为显示——各种潜能的自由显现”[4]191。 摒弃了功利目的的自然审美,在使自然摆脱掠夺的同时,也使人从异化劳动的禁锢中解脱出来。 由此可见,自然审美既是对自然的解放,也是对人的解放。
自然美具有革命的潜能,也是马克思对于自然的一个重要看法。 马克思“把自然理解为这样一个宇宙,它变成为了使人满意而意气相投的媒介,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自然自身令人愉悦的力量和性质也得以恢复和解放”[1]67。 人通过解放自然以满足自己,截然不同于资本主义通过掠夺自然以满足自己,“与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形成鲜明对比,对‘自然的人的占有’将会是非暴力的、非破坏性的:它指向自然内在的充满活力的、感性的、审美的特性”[1]67。 人对自然的这种占有,就是遵循自然自身的规律,发掘自然内在的潜能,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自然。 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把‘按照美的规律’塑造对象世界,说成是自由人实践活动的一个特征。 这绝非信口开河的说法。 审美的性质在本质上是非暴力的、非控制的”[1]74。 这种非暴力、非控制的自然审美“是一种从事物本身的角度去看待事物的能力,从而去体验包容于它们之中的欢乐和自然的爱欲能量——一种有待解放的能量;自然也等待着革命!”[1]74
马尔库塞从康德、席勒和马克思的审美自然观中洞悉到了社会变革的契机,“审美的维度是自由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审美维度摒弃了暴力、残忍、野蛮,由此可见,它将成为自由社会的本质属性”[1]68。 从生态的角度来说,在审美维度摒弃对自然的暴力、残酷和野蛮行为,不仅是对自然权利的尊重和承认,而且因为对自然的热爱和赞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从而证实了在“自然—生态”维度能够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实现自由社会的革命理想。
三、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与社会变革
1972 年,在法国召开的一次生态会议上,马尔库塞发表了一篇题为《生态与革命》的演讲。在演讲中,马尔库塞提出:“为什么要关注生态?因为对地球的侵犯是反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5]173同一年,马尔库塞出版了著作《阻拒革命与反抗》,其中的一章“自然与革命”也涉及到生态问题。 这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表明了生态问题已成为这一时期马尔库塞思想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为使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解而进行斗争,对于马尔库塞至关重要”[6]。 实际上,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生态破坏日益凸显,人们的生态意识也随之逐渐萌发。 各种生态思想通过科学、哲学和文学艺术的方式广为传播,生态观念和理念逐渐被大众知晓和接受。 尤其是进入20 世纪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生态破坏之深广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从根源上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对生态的戕害,成为科学界和思想界的一个共识。 在科学界,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农药对生态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警醒世人关注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成为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里程碑之作。 在思想界,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不少都汲取了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形成了颇有影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其中,马尔库塞作为最早发掘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然与革命思想的人,时隔40年之后,更为明确地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与革命联系起来。
马尔库塞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化的自然、被污染的自然、军事化的自然,不仅在生态的意义上,而且正是在存在的意义上,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 它阻碍了人在环境中的爱欲宣泄(以及转化),剥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使人置身于自然之外并与之对立”[1]60。 人所陷入的困境源于人对自然的伤害,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资本主义本身不仅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反而加速了这一危局,“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发动对自然的战争,包括人性自然和外部自然。 由于日益增强的剥削需求产生了与自然本身的冲突,因为自然是同侵略和毁灭的本能作斗争的生命本能的根源所在。 剥削的需求逐渐减少和耗竭了资源。 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越高,它的破坏就越大。 这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一个标志”[5]174。 对自然的控制和剥削,是资本主义对人进行控制和剥削的物质基础。 因此,只有使自然摆脱资本主义的盘剥,人自身才能从被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马尔库塞将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变革同自然的解放联系在一起,“自然应该作为反抗剥削社会斗争中的同盟军,因为在剥削社会中,对自然的侵害加剧了对人的侵害。 对自然的解放力量及其在构建自由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的发现,成为社会变革的新力量”[1]59。 人的解放应当建立在自然的解放基础之上,自然的解放包括两个层面:“(1)人的本性:作为人的理性和经验基础的人的原初冲动和感觉;(2)外部自然:人的生存环境。”[1]59在第一个层面,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被日益强化的工具技术理性所压制,人源于自然的原初脐带被剪断,并且在工具技术理性的操控之下反噬自然。 因此,解放自然意味着摆脱工具理性的禁锢,在与自然的统一中重新恢复人的自然本性。 在第二个层面,自然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回到前技术时代,而是充分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将人和自然从科学和技术服务于剥削的破坏性滥用中解放出来”[1]60。 马尔库塞辩证地看待科学技术对于自然的双刃剑作用,并未因为其对自然的破坏而因噎废食,而是强调其正面作用和积极影响。解铃还须系铃人,科学技术对自然所造成的破坏,必须通过科学技术自身来修复,而非简单地摒弃技术,重返前工业技术时代。 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思想的发展,应当建立在将自然作为生命整体的经验基础之上,这一生命整体有待保护和‘开化’,而技术应当将科学应用到生命环境的重建之上”[1]61。 这与那种耽于幻想、沉迷于阿卡迪亚式田园牧歌社会的浪漫主义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然的重建和解放,有赖于人类在思想观念上重新审视自然,从根本上转变对自然的态度,“自然是拥有其自身的权利主体—— 一个与之生存于共同人性宇宙的主体”[1]60。 如此,方可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隔阂。 将自然视为具有自身存在权利的主体,无疑是对将人与自然进行主客二分、并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西方传统思想的挑战。将自然解放为挣脱人类禁锢的主体,意味着彻底摒弃对自然的剥夺和侵犯,恢复自然应有的尊严和价值,“就是恢复自然中促进生命的力量”[1]60。而自然所蕴含的这种力量,却正是压榨自然、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极力掩盖的。 因此,唯有恢复自然促动生命的力量,才存在人类解放的前景。 对于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尔库塞从生态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之间的具体关联,已经清楚地体现在今天生态活动在激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上”[1]61。 一方面,生态危机及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空气和水的污染、噪音、工商业对空旷的自然空间的侵害,所有这些都具有奴役和禁锢的强大力量。 反对它们的斗争,就是一场政治斗争;对自然的破坏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之不可分割达到了什么程度,这是显而易见的”[1]61。 而另一方面,“生态学的政治功能容易被‘中立化’,被用于美化现存的制度”[1]61。尽管资本主义在技术和舆论层面上也会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但不会从根本上触及生态破坏的制度原因。 因此,为了避免生态学被资本主义所利用,必须“使生态学发展到在资本主义结构中再也不能容纳的地步,这意味着开始超越在资本主义结构内的发展”[1]61。 只有使生态学超越资本主义的结构,才能解放自然,从而引发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在开展的生态运动,马尔库塞既指出了其所面临的挑战,也肯定了其积极意义,“生态运动正在攻击资本主义的‘生存空间’,即利润领域和废物产生的扩张。 然而,反对污染的斗争容易被收编。 如今,几乎没有广告不劝告你‘保护环境’,终止污染和毒害。 创立了各种委员会以控制犯罪团伙。 确实,生态运动有助于美化环境,使它舒适宜人,不那么丑,更健康,因此,更可容忍。 显然,这是一种合作,但它也是一种进步的因素,因为在这种合作中,一定数量的需要和渴望开始在资本主义的核心表达出来,人们的行为、经验及其对待工作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5]175。 虽然通过榨取自然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是资本主义的终极目的,但资本家也清醒地意识到生态危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也会在不危及自身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倡导环保活动。 就此而言,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所开展的生态活动也具有逐渐改变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积极意义。 然而,这种改良性质的生态运动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因而也无法真正使人获得解放,因此,通过毫不妥协的生态斗争来追求社会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不是对现存社会的净化,而是对它的取代”[5]175。 在《生态与革命》演讲的结尾,马尔库塞发出号召:“任何资本主义生态都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局限。 真正的生态应当融入为社会主义政治而积极斗争的洪流中,这场斗争必须在生产过程和个人残缺意识的根基上攻击资本主义制度。”[5]176在人类社会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进程中,马尔库塞的这一号召具有更为鲜明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结 语
歌德曾经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任何一种理论,如果脱离实践,就如同没有血肉的枯槁之躯。 马尔库塞的思想之所以能够产生持续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源于人类社会所存在的重大问题,并试图为其提供解决的方案。 面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自然和生态问题,马尔库塞不仅发掘出蕴含于前人思想中的理论资源,并且将其发扬光大,使之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正在建设中的生态文明以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来说,汲取马尔库塞的思想理论,对这场里程碑式的社会革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