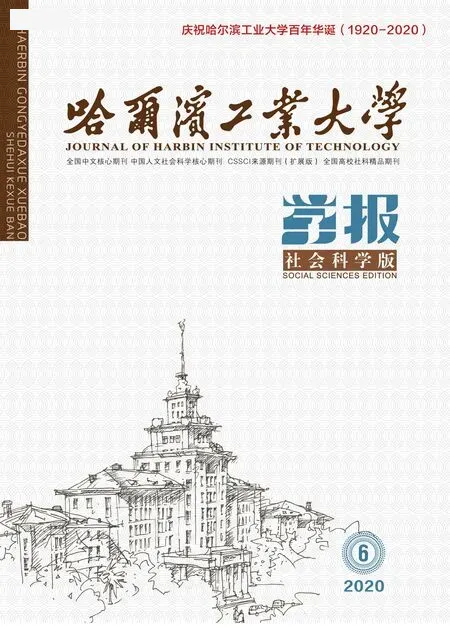韩愈、李翱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韩 强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300350)
一、韩愈、李翱的承先启后作用
韩愈(公元768—824 年)、李翱(公元772—841 年)这两位思想家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先秦、两汉经过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荀和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尽管对善恶的来源有不同的说法,但他们都是从本原上谈人性的善恶问题。 从西汉董仲舒开始提倡“性三品”论,一直延续到唐代韩愈。
这中间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家首先从“以无为本”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 玄学家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即是“自然”,“自然”无形无为,却可以“成济万物”,包括“名教”在内的万事万物皆是从自然而来,充分体现了“自然”的原则。 所以,王弼一方面认为“名教”的存在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又强调“名教”应该合乎“自然”的原则。 圣人与官长的作用就在于使“名教”合乎“自然”,“行无为之事”,只有体现“自然”的“名教”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 王弼之后,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为反对司马氏虚伪的“以孝治天下”,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尽管他们的“任自然”不是任情纵欲,他们的思想深处还是希望以合乎“自然”的“名教”社会作为理想,但是“任自然”的口号成为一些人“放荡形骸”的借口,尚虚谈的风气日盛,于是裴頠以《崇有论》来强调“名教”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又有郭象以“玄冥独化”论证“名教即自然”。 因此,儒道合流的魏晋玄学,虽然标榜“崇尚自然”,但对社会的看法,还是以儒家的礼教为本位,这就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人伦关系的重视。
外来的佛教文化思想也极力利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以求达到儒道佛合流。 如果说儒道合流产生了玄学的名教自然之辨,那么儒道佛合流则产生了佛法名教之辨。
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始,就面临着出世解脱与入世生活、修持佛法与信奉名教的矛盾。 当人们对佛教出家修行、见人无跪拜之礼提出异议和责难时,佛教徒就一方面以“苟有大德,不拘于小”来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又强调“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1]19, 佛教的出家修行,“亦得无为,福流后世”[1]10,“至于成佛,父母兄弟皆 得 度 世, 是 不 为 孝, 是 不 为 仁, 孰 为 仁 孝哉!”[1]25佛教为了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以求发展,便不断地与儒家礼教进行妥协。 其基本方法是把儒家与佛教的观念相互比附,例如以《周易》的“四德”(元、亨、利、贞)比附佛教的“四德”(常、乐、我、净);以“五常”(仁、义、理、智、信)比附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 甚至不惜改变佛教的内容,在佛教思想体系中加入儒家礼教的内容,例如把“孝”说成是儒佛共同尊奉的宗旨,进而论证佛儒一致,这都有利于帝王的教化。 东晋名僧慧远在《答恒太尉书》和《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把佛教的义理与维护名教的传统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宣扬“孝”是佛教的世俗要求。
所以,韩愈、李翱面临玄学佛教的本体论,首先是如何改造传统儒家的人性本原论,建立儒家的本体论。 除了具体问题,还有方法论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说明韩愈、李翱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二、韩愈、李翱对佛教的批判
佛教是从西域传入中国,南北朝时期大行其道,信众颇多。 韩愈认为,到了唐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后,佛教在理论上有这一时期的天命神权的观念,寺院经济也有很大的扩张,甚至出现了“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局面,僧侣们不劳而食,寺院道观不计其数,严重耗费了国家的人力和财力,严重威胁着人民生活和国家安全,形成了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封建国家和寺院集团之间的矛盾。 在教义上,佛教宣扬度化,厌世即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韩愈是唐代坚定的反佛者。 韩愈认为,中国的天子不应该信奉佛教,那些求佛信佛的人,不仅没有得到幸福,而且不顾父母兄弟和妻子儿女,不断向佛教供奉,导致家破人亡。 以前,佛教没有传进中国,人民安居乐业。 韩愈把这些写成《论佛骨表》,建议唐宪宗把佛骨投入水火,而且还给群臣们看,使皇帝震怒,韩愈差点丢了性命。
张籍希望韩愈能作一部像《孟子》《法言》那样的书彻底批判佛教,以正视听,韩愈回信说:
“昔者圣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辞矣,然犹不敢公传道之,口授弟子,至于后世,然后其书出焉。 其所以虑患之道微也。 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辅相,吾岂敢昌言排之哉? 择其可语者诲之,犹时与吾悖,其声哓哓。 若遂成其书,则见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为狂为惑。 其身之不能恤,书于吾何有? 夫子,圣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其馀辅而相者周天下,犹且绝粮于陈,畏于匡,毁于叔孙,奔走于齐、鲁、宋、卫之郊。 其道虽尊,其穷也亦甚矣!赖其徒相与守之,卒有立于天下。 向使独言之而独书之,其存也可冀乎? 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盖六百年有馀矣。 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2]
李翱也是坚决反对佛教的。 李翱说:
“佛法之染流于中国也,六百馀年矣。始于汉,浸淫于魏、晋、宋之间,而澜漫于梁萧氏,遵奉之以及于兹。 盖后汉氏无辨而排之者,遂使夷狄之术,行于中华,故吉凶之礼谬乱,其不尽为戎礼也无几矣。 且杨氏之述《丧仪》,岂不以礼法迁坏,衣冠士大夫与庶人委巷无别,为是而欲纠之以礼者耶? 是宜合于礼者存诸,愆于礼者辨而去之,安得专已心而言也? 苟惧时俗之怒已耶,则杨氏之仪,据于古而拂于俗者多矣。 置而勿言,则犹可也,既论之而书以为仪,舍圣人之道,则祸流于将来也无穷矣。 佛法之所言者,列御寇、庄周所言详矣,其馀则皆戎狄之道也。 使佛生于中国,则其为作也必异于是……虽享百年者亦尽矣,天行乎上,地载乎下,其所以生育于其间者,畜兽、禽鸟、鱼鳖、蛇龙之类而止尔,况必不可使举而行之者耶? 夫不可使天下举而行之者,则非圣人之道也。 故其徒也,不蚕而衣裳具,弗耨而饮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养已者,至于几千百万人。 推是而冻馁者几何人可知矣。 于是筑楼殿宫阁以事之,饰土木铜铁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虽璇室、象廊、倾宫、鹿台、章华、阿房弗加也,是岂不出乎百姓之财力欤?”[3]
李翱认为,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到唐代已经600 多年了,“这种夷狄之术,行于中华,故吉凶之礼谬乱”,特别是杨垂所集的《丧仪》,乱了儒家传统的礼义,“祸流于将来也无穷矣”,这决不是圣人之道。 因此,必须恢复中国传统的道德礼教。
韩愈、李翱大张旗鼓地反佛,实际上是要扭转社会风气,为儒家思想造舆论。 宋明的大思想家都是反佛的,“辟佛老正人心”成了他们响亮的口号。 例如,张载说:“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有无混一之常。 若谓万象谓太虚所见(现)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 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之以虚空为性,不知相天道为用,反以人见之小因缘天地。 明有不尽,则诬世界乾坤为幻化,幽明不能举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阴一阳,范围天地,通乎昼夜三极大中之矩,遂儒、佛、老庄混然一途。”[4]
二程从自然界和人的消长变化规律(理)出发,批判佛教空幻不实的思想。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此所以为常也。 为释氏者,以成坏为无常,是独不知乃所以为常也。 今夫人生百年者长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谓常也。 释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为妄,何其陋也。”[5]394一切生物都有生死,这是常道,不像佛教所说的空幻不实,如果该死不死,就违背了自然规律,那就不正常了。 “释氏言成住坏空,便是不知道。 只有成坏,无住空。 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尽便枯坏了。 他以谓如木之生,生长既足却自往,然后却渐渐毁坏。 天下之物,无有住者。 婴儿一生,长一日便是减一日,何尝得住。”[5]195二程否定佛教“空”的思想。 他们承认成、坏,否认住、空,成、坏是常理,否定了佛教万事皆空的思想。
三、性情三品对应论总结了先秦两汉儒家的人性论
韩愈的性情三品对应论是对两汉性三品思想的总结。 董仲舒以天道阴阳为起点,提出“阳仁阴贪”的人性生成论和性三品论,以及三纲五常的他律道德系统。 王充以气禀厚薄为起点,提出才性三品和正命、遭命的观点。 荀悦以气化形神为起点提出形神为性、命有三品的观点。 韩愈不像两汉儒家那样详细地说明宇宙气化生成人性的过程,而是直接从“生之谓性”出发,说明性情三品对应关系和五常之道的他律道德。 韩愈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五德,这是人先天固有的,但是每个人又有差异。 上品的人性“主于一而行于四”,以一德为主,通于其他四德;中品的人性对于某一德有所不足,对于其他四德或有不符合的情况;下品的人性“反于一而背于四”,对于一德违反,对于其他四德也不符合。 情的具体内容是喜、怒、哀、惧、爱、恶、欲。 与人性的三品相对应,情也有三品:上品的人情“动而处其中”,中品的人情发动有过而不及,下品的人情任情而行,不符合道德标准[6]64。 这里韩愈采取了生理、心理和伦理相结合的方法制定了一个性情三品对应论的他律道德系统。 在七情中,欲主要是生理欲望,喜怒哀惧爱恶是心理感情,仁义礼智信是伦理道德。 韩愈根据道德的先天差别说明情的先天差别,这与董仲舒、王充那种由情欲、才质的先天差别说明道德的先天差别的方法不同,而是利用了性发为情的观点,进一步强调道德对情欲的超越性和决定性。 同时,韩愈也详细分析了道德差别中五性相互配合的差别,以及感情发作是否合乎节度的问题,这显然比董仲舒“心性情”的抑恶于内、扬善于外的观点更细致。
韩愈引用了《大学》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君臣父子之道,提出了仁义之行和诗、书、易、春秋的礼乐教化为儒家道德教育。 要求人们学习先王之教,“早夜以思,支其不如舜者,犹如其舜者”。 上品人性本来就善,学而愈明。 中品人性可以导而上下,要加以引导,使他们不溺于佛道。 下品人性“不能深达事体”,但也要教化,使他们“畏威而寡罪”,不犯上作乱。
韩愈心性论的特点是只讲教化——学习礼乐诗书,不讲“格物致知”,他把《大学》的诚意正心引向《中庸》,因此说:“圣人抱诚明之性,根中庸之至德苟发诸中形于外者,不由思虑,莫匪规矩,不善之心无自入焉。 可择之行无自加焉”,只有圣人才能“从容中道”,“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7]。 韩愈的心性修养论实际上并没有超出两汉儒家那种圣人用礼义节制广大民众情欲的礼教方法。
朱熹评论说:“退之说性,只将仁义礼智来说,便是识见高处。 如论三品亦是。 但以某观人之性,岂独三品,须有百千万品。 退之所论,缺少了一‘气’字。 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8]
朱熹一方面肯定韩愈把人性定为仁义礼智,抓住了天命之性,另一方面又批评韩愈性三品的缺点,所谓“三品”是不对的,因为人的差别何止三品,可以说是千差万别。 从张载、二程开始,提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是为了说明所有的人都一样,关键在于每个人的具体行为的善恶是从道心(天理),还是从人心(人欲)上发出,人欲是气质之性的表现。 也就是说,理学家的性两元论,既可以说明所有的人先天平等(同时具有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又可以说明每个人的表现不同。 如果从先秦两汉的人性论来说,性两元论是对所有的人性论的总结:一方面,以孟子的人性善和董仲舒的仁义礼智为根本的人性,另一方面,把荀子的人性恶和杨雄的善恶混合包含在气质之性中,最后用孟子的“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来说明具体的表现不同。
四、韩愈的儒家道统说
韩愈为了恢复儒家的权威,表示自己学有本源,仿照佛教世袭传法的法统,建立了儒家圣人传道的道统。 韩愈认为,儒家之道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9]63。 韩愈以孔孟的继承人自居,表示要发扬光大儒家传统。
为了区别儒、道、佛三家,韩愈从概念上定性“仁”。 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仁义为定名,道德为虚位。”[9]60韩愈从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入手,指出“道”和“德”是两个最大的概念,各种学派都可以在“道”与“德”这两个概念中充实不同的内容。 老子的“道”和“德”是“无”和“无为”,而儒家的“道德”是“仁义”。 但是韩愈并没有进一步看到“仁”与“义”对于道德是定名,而作为儒墨两家共同使用的概念,又是虚位概念。儒家的“仁”是爱有等差,“义”与“利”对立,而墨家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就是仁义。 虽然韩愈也批评了墨家思想,但主张“博爱之谓仁”与儒家的爱有等差的“仁者爱人”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却带有墨家“兼爱”的色彩。
韩愈不仅从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上批判了佛道两家,并且从人性论上总结了儒家思想。 韩愈认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以及杨雄的善恶混都是在上、中、下三品人性中“得其一而失其二者”[6]64,至于佛老两家乃是异端杂言。
韩愈大讲“仁义为定名”和性三品是为了宣扬儒家道统,这种“定名”方法与董仲舒的“名性不以上,不以下,而以其中”的方法相同。 虽然魏晋玄学已经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述了心性关系,但是韩愈的心性思想并没有达到本体论的高度。 韩愈看不到玄学的自我超越是超越情欲和仁义道德,佛教的自我超越是超越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 他只是从佛道两家不讲仁义道德这一点上对其批判,这种批判没有达到本体论的理论思维高度,因此韩愈的心性论仍然停留在董仲舒性三品的思维模式中。
道统说,实际上为儒家创造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的“道统”,朱熹改变了这个“道统”。 朱熹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尧之一言,至矣尽矣。”[10]这样,道统就成为十六字心传。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在《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以及《政道与治道》中也大谈“道统”。
五、教化养心并用的内圣外王之道
韩愈的心性论在三个方面对宋明理学产生了影响。 第一,从儒家仁义道德观念对佛道进行批判,提出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孟的儒家道统。这种道统说正是现代新儒家所宣扬的从三代圣王到孔孟直至程朱陆王的中国文化一本性。 第二,性情三品对应论中性发为情和发而中节的观点,为宋明理学程朱的心性情体用动静关系奠定了基础。 第三,心性修养论中《大学》的诚意正心与《中庸》的至诚之道的结合,为宋明理学心性论融合孔孟、《中庸》《易传》《大学》的各种心性观点作了初步的准备。
韩愈虽然没有达到本体论,但他所开列的这些书,实际上为宋明理学做了方法论的工作。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指出:宋明儒家对《论》《孟》《中庸》《易传》的心体、性体、道体的理解和发挥,明显地说出了“天道性命通而合为一”“心性是一”。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大学》的理解:《大学》言“明明德”未表示“明德”即是吾人之心性,甚至根本不表示此意,乃只是“光明的德行”之意,但宋明儒家一起皆认为“明德”就是因地之心性说。 另外《大学》言“致知在格物”,只是列了一个正心诚意的实践纲领,“在内圣之学之义理方向上为不确定者,究竟往哪里走,其自身不能决定”,这就使伊川、朱子与阳明及刘蕺山“得以填彩而有三套讲法”[11]17-18。 根据上述宋明儒者对《论》《孟》《中庸》《 易传》及《大学》的不同解释,牟宗三又疏导了宋明理学的发展线索:首先,北宋有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三家是由中庸、易传之讲天道诚体,回归到论语孟子而讲心性。 他们所体悟的道体、性体以至仁体、心体,皆静态地为本体的“实有”,动态地表宇宙的生化之理,同时亦即道德创造之实体,它是理,同时亦是心,亦是神,所以是“即存有即活动”者[11]17-18。 在周、张、程(明道)之后,又分为三系:一是五峰、蕺山系,此承由濂溪、模渠、明道之园教模型(一本义)开出,此系客观地讲性体,以《中庸》《易传》为主,主观地讲心体,以《论》《孟》为主。 特别提出“以心著性”,义以明心性所以为一……于工夫则重“逆觉体证”。 二是象山阴明系,“是以《论》《孟》摄《易》《庸》,而以《论》《孟》为主。 此系只是一心之朗现,一心之申展,一心之遍润”于工夫,亦是以“逆觉体证”为主者。 三是伊川、朱子系,“是以《中庸》《易传》与《大学》合,而 以《大学》为主。 于《中庸》《易传》所讲之道体性体只收缩提练而为一本体的存在,即‘只存有不活动’之理,于孔子之仁亦只视为理,于孟子之本心则转为实然的灵气之心,因此于工夫特重后天之涵养以及格物致知的横摄,此大体是顺取之路”。 这三系中,又可以《论》《孟》《易》《庸》为标准,将一、二两系合为一大系,名曰纵贯系统,伊川、朱子系所成者,名曰横摄系统。 前者为大宗,后者为旁枝(歧出之新)[11]49。
六、李翱的心寂、性静、情动开创了本体论
李翱说:“昔者之注解《中庸》者……以事解也,我以心通也。”[12]555所谓“心通”就是“明诚”。李翱把“诚”的道德意志抽象为天与人的共同本性。 李翱说:“诚者,圣人之性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语默无不处也。”[13]551“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性者,天命也。‘率性之谓道’何谓也? 曰:率,循也。 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 道也者,至诚也。 ……诚者,定也,不动也。”[12]554-555李翱吸取了汉代“人生而静天之性”和《易传》的寂感神通解释《中庸》的“天命之谓性”,使“诚”不仅具有天人共同本性的意义,而且有了寂然不动和感而遂通的意义。 所谓“寂然不动”是说“诚”作为天人共同本性具有定和静的本性。 例如“由(冉求)也非好勇而无惧也,其心寂然不动”[13]552,就是说道德意志之“诚”坚持而不动摇。 所谓“感而遂通”,是说天下至诚为能化,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 这些解释虽然没有使用本体范畴,却已经透露出本体论的思想萌芽。
李翱还从感觉的视听和心的思维来说明心的动静关系。 《易传》的“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本来是说“易”生生变化的过程,讲的是天道。 李翱用这些话说明天人的共同本性——“诚”,使“诚”具有宇宙论的意义,同时又用来说明人的主观精神。李翱认为,心本来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但是由于感觉与外界接触产生了视听思虑,因此要保持心的寂然不动、“动静皆离”的状态,就必须“明辨焉,而不应于物”[12]554。 这实际是庄子和玄学家所说的心如明镜,照物而不应于物,佛教所说的“不著于物”。 一方面,这种“不应于物”的心理状态就是诚意、正心,因此心的寂然不动实际就是超越感觉和理智、以直觉与“天命之性”相通;另一方面,性的感而遂通又通过心表现出来,心有思有虑,“动静不息,是乃情也”[12]553,“情有善有不善”[12]556。 李翱所说的“心”一方面是寂然不动、与性相通,另一方面又感而遂通表现为情。 虽然李翱没有明确“性具于心”,也没有使用体用范畴,但其观点已经吸取玄学佛教带有心体用论的色彩。
李翱利用了《易传》的“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和《大学》的“格物致知”以及《中庸》的“诚者天之道”,提出了诚静之性与心寂情动的观点,已朝着本体论的方向迈进。 但真正达到本体论高度的是宋明理学家周敦颐。 周敦颐利用了道士陈抟的《无极图》,制定了《太极图》,并写了《太极图说》,从“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体论和“立人极”的天人之道上说明“人极”就是“太极”,二者是“天人合德”的“诚”性本体,使“诚”具有了宇宙本体论的意义。 《太极图说》可以看作是宋明理学的宇宙本体论和心性本体论的基本纲领,它影响着程颢的“天人一本”,张载、程颐、朱熹的“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性两元论。
七、性与情不相无和性善情昏
李翱扬弃了汉唐儒家性三品论的观点,提出了性善情昏的“性与情不相无”的观点。 李翱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性之所为也。 情既昏,性斯匿矣。 非性之过也,七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 …… 性与情不相无也。 虽然无性则情无所生矣。 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13]550-551这里,李翱看到了性与情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性而生情”,“无性则情无所生”;另一方面,“情为性之动”,“性不自性,由情以明”。 情是性的表现,作为表现性的情,可以与性一致,也可以与性不一致。
李翱认为,“凡人之性犹圣人之性”,“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 “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12]555-556。 也就是说,圣人与凡人在先天性善上是平等的,其区别在于后天嗜欲好恶不同,因此有圣人之情和凡人之性的区别。
圣人是先觉者。 “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13]551这是因为圣人能保持寂然不动的心理状态坚持道德意志的“诚”,使喜怒哀乐之情“动而中礼”[13]551。 因此,圣人虽有情而未常有情,这是性情一致的善。 凡人被七情昏蔽,就像“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13]550,因此掩盖了善性,情与性不一致,所以不善。
李翱还认为,情是性的表现,言行即是“人之文”,他根据能否“中节”把“人之文”划分为四等:“出言居乎中者,圣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圣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贤人之文也;背而走者,盖庸人之文也。”[14]这种划分也是对后天具体人的划分。 虽然不是先天等级差别,但还带有简单化的缺点,不能说明具体人的多样性,也就是说仍有汉唐性三品论的残余。
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达到本体论,他在《太极图说》的前一部分描绘了宇宙的生成过程:“太极—阴阳—五行—四时—万物(人得其透为灵者)”。 这与汉代董仲舒的“元气—阴阳—五行—四时—万物”的宇宙生成论相似。 《太极图说》后一部分讲了人的形神生理基础和气质善恶来源于阴阳五行,提出了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的立人极观点。 这实际是从宇宙发生论说明人性的来源,又把“立人极”的道德提升为宇宙本体。
周敦颐在《周子通书》里,进一步说明了“立人极”的详细内容,提出了诚体神用几微的道德本体。周敦颐认为,“诚”是“圣人之本”“万物资始”“性命之源”,它是纯粹至善的,贯穿在万物化生的元、亨、利、贞各个阶段中。 “诚”又是伦理道德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并且贯穿在人们的思维和道德修养中[15]。 因此,周敦颐又说:“诚无为,几善恶。 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 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执焉之谓贤。 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16]这样,周敦颐就以“诚”的道德意志为宇宙和人性的共同本体,一方面说明乾道变化的元亨利贞,另一方面说明道德的仁义礼智信和气质善恶来源,建立了一个由天道到人道的他律道德系统。
八、无思、心寂、至诚的复性说
李翱认为,圣人之性与情一致,表现为善,而凡人被七情昏蔽掩盖了善性,因此要恢复本来的善性。 李翱把“复性”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由“弗思弗虑情不生”进入“无虑无思”的“正思”境界,这是“斋戒其心”的虚静状态。 “正思”尚未摆脱“思”,“犹未离于静”[12]553,动静不息,仍然有情,还不能复性。 第二个阶段是“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是至诚也”[12]553-554。 到了这个阶段,就“性情两忘”,见闻而不动心,“明辨焉而不应于物”,“是知之至也”。 这才能去掉妄情,而恢复善良本性。 李翱的复性说,实际是运用了庄子“心斋”“坐忘”“反其性”与道同体的直觉方法。李翱讲的由“弗思弗虑”的“正思”阶段进入“动静皆离”“性情两忘”的“至诚”阶段,与佛教由渐悟到顿悟的修持方法差不多。
宋明理学家周敦颐也主张“主静无欲”。 周敦颐说:“无欲则静虚动直。 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 明通公溥,庶矣乎!”[17]这实际是老子“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和庄子“虚静恬淡,寂莫无为”的“体道”方法。 周敦颐把这种方法与孟子的养心寡欲相结合,认为“养心不止守寡而存目,盖寡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18],达到彻底的无欲,就不生“妄心”,没有“不善之动”,就可以做到“诚心”[19]。
周敦颐一方面主张用直觉的方法体验“诚”,另一方面又主张用礼义教化节制情欲。 周敦颐说:“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 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20]这实际是汉代礼义政教的观点。 周敦颐的心性论思想是从宇宙生化与人伦道德一体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心性本体论。 他的太极—阴阳—五行—四时—万物(人)的产生过程及人的刚柔善恶中的划分都带有两汉阴阳五行生成万物和人类性三品的痕迹。 但是,他以“无极而太极”“寂然不动”的“诚”体和“感而遂通”的“神”用改造了汉代的气化人性论,使宇宙本体和人性统一于“纯粹至善”的“诚”,并且进一步把人的心理素质划分为刚、柔、善、恶、中,这就为性两元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诚”即是张载所说的“天地之性”,而刚柔善恶中即是张载所说的“气质之性”。
现代新儒家唐君毅说:“李翱言灭息妄情,由情复性,以性其情,其用语类似庄子、淮南、何、王之言,不可讳也”,“至于习之言‘诚而不息则虚,虚而不息则明’,固不同于《中庸》之诚明并言之。谓诚不息则虚,盖谓唯诚不息而后不滞不执,此中固有虚义。 虚则能容能照,而有明义。 此固非不可说。 亦未尝不可于佛家所谓不滞不执之义,或空我执法执以去障之旨者”[21]。
由此可见,李翱的心寂、性静、情动和复性说带有儒、释、道融合的色彩。 虽然李翱没有明确使用“性本体”和“性具于心”“心有体用”的概念、命题,但是他对心的寂感神通的宇宙论的分析,已经透露出心性本体论的初步思想。 可以说,李翱是汉唐儒家向宋明理学过渡的一个中间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