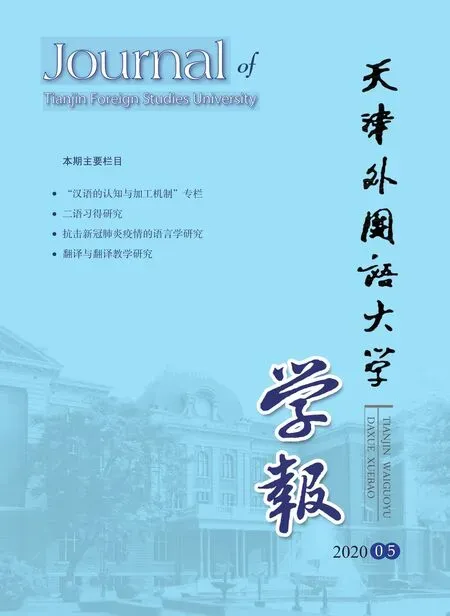从空符号的特点看文学的艺术性
王 军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空符号有两种基本类型,分别涉及能指和所指这两个符号的基本构成要素。第一种类型的空符号受到的关注最多,是指能指的符号载体为“能被感知到的‘无声无色无形’的空无,即能指在物质上处于缺失状态,但却能被感知”,并且通常具有确定的所指对象(曾庆香,2017:23)①,包括“空白、黑暗、寂静、无语、无嗅、无味、无表情、拒绝答复等等”(赵毅衡,2016:25)。第二种类型的空符号是以所指为空为基本特征,尽管这种空并非完全为空,只是语义较为空泛而已。空符号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一般称作零符号(zero sign)(如Jakobson,1984;Sebeok,1985;Ephratt,2008),也会以“欲言还止”(aposiopesis)(如“滚,不然……”)(赵毅衡,2016:26)为话题进行研究。国内研究中最早使用空符号这一说法的是王希杰(1989),但是研究最为深入、全面且广为认可的是韦世林(2012)的专著《空符号论》。也有一些学者(如王东、李兵,2013a,b;曾庆香,2017)沿用国外学者的说法,使用“零符号”这一术语。即便人们不使用空符号、零符号这类说法,所研究的对象也未必不是空符号现象,如国外对静默(silence),尤其是“雄辩的静默”(eloquent silence)的研究(如Ephratt,2008;Bilmes,1994),还有国内对停顿、留白等的研究(如苏少波,2000;李勇忠,2009)。由此可见,作为与显性符号对立的空符号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话题,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研究价值的话题。很多学者(如Sontag,1969;Poyatos,2002)都认为,静默或者空符号与言语都是同等重要的交际方式。哈佛大学知名语言学家Steven Pinker(1994)颇为深刻地指出,人们所听到的并非是声音,而是(抽象的)语言,换句话说,人们交际时所获取的信息并非是听到的那些话或读到的那些文字,而是这些语言符号背后的那些抽象语言单位,即意义,而意义的载体既可能是言语或文字,也可能是非言语成分,包括空符号。我们下面将首先对空符号有别于一般符号的主要特征进行阐述,重点分析其能指的开放性问题,然后从空符号的概念出发分析文学作品中三种主要的空符号类型,以揭示文学艺术性的产生根源。
二、空符号的开放性特征
无论是曾庆香(2017)还是赵毅衡(2016)都强调空符号具有被感知的属性,如果一个符号完全不能被感知,也就不成其为符号了,同时空符号也必须有所指,无所指的也不是空符号。王希杰(2012)认为,空符号就是符号的空档与缺位,这在语言中广泛存在。例如,汉语有“鸡”这个词,而英语却没有与之对应的表达这一概念的词,所以汉语的“鸡”在英语中对应的是一个空符号;汉语的亲属称谓词,如“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等在英语中对应的也都是空符号;汉语中有“一本书”、“一支铅笔”,而英语中只能说a book,a pencil,所以汉语的量词“本”和“支”在英语中属于空符号。我们不赞同上述对空符号的界定方法,也不认为这里所提到的空档或缺位就是空符号,原因有两点。首先,王希杰所举的例子都是从对比的视角来看问题,如果出现我有你无或你有我无的现象,无的一方就属于空符号。依照这样的判断标准,空符号很可能会无所不在,因为我们随便找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作为参照,都会很容易地找到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空符号。虽然真正的空符号也需要与一般的符号同时使用时才能显示出空符号的存在与价值(如话语过程中的停顿,作为空符号的停顿必须以一般语音符号为参照),但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空符号和一般符号同处于一个相同的认知域或观察范围中,而王希杰所说的空符号却是把空符号与一般符号置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域或观察范围(即两种不同的语言)里,这不属于本文考察的范围。其次,王希杰所说的空符号通常并不能被受话人所感知,如英语为母语者在使用a book时不可能感知到中间缺失了一个量词。因此,把能被感知作为符号(包括空符号)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曾庆香(2017:24)转引了赵毅衡(2012:26)提到的Eco(1976)举过的一个例子,即汽车不打灯表示直行,旗舰上不升司令旗表示司令不在舰上。她认为,这两个例子属于“能指空无的现象”,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因为如果能指空无,符号也将不复存在,而既然没有了符号,何以判断汽车将要直行和司令不在舰上呢?既然所指义是明确的(汽车直行或司令在舰上),能指就一定存在。这个能指可以是空符号(前提是当我们把打灯转向或升旗司令在视作参照时),也可以是一般的符号(前提是当我们把灯不亮或舰上不升旗直接视作符号时)。究竟是空符号还是一般符号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但无论怎样,所指义的产生不可能离开能指符号。
空符号必须有所指,而无所指看似空符号的现象其实并非属于符号。对于所谓无所指的空符号我们需要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属于真正的无所指,而既然无所指,就不属于空符号以及符号的范畴。例如,口语交流中的停顿如果属于生理或非逻辑原因造成的,就不是空符号,因为这种停顿不具有任何交际意义,这属于真正的无所指;如果因为停顿带来意义的变化或形成某种期待,这种停顿就是有所指的空符号,如下例所示(∅表示停顿)。
(1)To govern ∅ people ∅ use language.(Ephratt,2008:1927)
(2)这苹果∅不大∅好吃。
(3)老师:我下面提一个问题。∅为什么……
在例(1)中停顿承担着句法标记的作用,to govern ∅ people use language的意思是人民要想统治,就要使用语言,而to govern people ∅ use language的意思是要想统治人民,就要使用语言。停顿这种句法标记能够被受话人感知,因而是可被感知的能指,同时受话人能够理解其正确含义,因而是有所指的。例(2)的情况也一样。例(3)中的停顿不是句法标记,而是发话人(老师)的一种课堂组织手段,老师有意识地停顿,希望学生集中注意力听清问题,而学生也会在老师的停顿中做好听的准备,所以此处的停顿也是一种可被感知且有所指的空符号。
还有一种所谓的无所指情况比较复杂,但却仍然属于空符号。前面我们提到的曾庆香所认为的无所指情况就属于这种类型。这种无所指并非表示不指称任何事物,只是所指对象不那么明确,所指的范围比较宽泛(但绝不是不着边际)而已。Jakobson(1984:153)曾说,当一个语言符号的所指被赋予一个零值(zero value)时,该零值所代表的是一种无法区分的或不确定的意义(undifferentiated or non-specified meaning)(Cantor,2016:211)。但这句话有两个地方很容易产生误导:一是零值的提法很容易让人产生无所指的印象,二是零值与代表一种无法区分的或不确定的意义存在矛盾,因为既然是零值,就应该是意义的空无,即便是无法区分或不确定的意义,依然是意义,依然是有所指的。这直接影响到空符号与一般符号之间的区别以及我们对文学艺术性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非常赞同巴尔特的文学零符号学思想,他认为:“文学作为自性的符号体系,在于所指世界相联系的过程中总会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和‘空无’……能指形式与所指位置之间存有……巨大缝隙和空洞……表面上能指与某一所指相连,但实质上能指指向的只是所指所在的‘位置’,‘所指’实际上就是一个空无。这种‘空无’就是一种生发性的空间,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可能在这一位置上充当‘临时所指’。”(王东、李兵,2013b:139)因此,空符号既不是无所指,也往往不具有明确的所指对象。空符号的所指类似于认知语言学中的框架(frame)(Fillmore,1982),属于一个抽象的结构,内部包含许多待释成分(也称作槽位(slot))。以饭店为例,根据框架理论,一个典型的饭店框架包含一系列的构成成分,如饭店这一建筑本身、服务员、菜单、餐桌、盘子、菜肴等。如果认为各个构成成分是具体的,作为框架的饭店就是抽象的,它是一个汇集了很多构成成分的集合。饭店框架的内容包罗万象,但范围又比较有限,仅限与其直接相关的事物。当一个人用手指向一家饭店却不说任何话时,他指向的只是一个框架或是一个位置,所指的具体含义并不明确,或许他想表达的具体意思是那个建筑物很漂亮,或者那家饭店菜好吃,或者那个地方我去过。在用语言或其他方式明确所指是什么之前,其他人所能获得的信息是他想表达的内容一定与那家饭店有关。有时空符号的所指就是这样,它既指向某种事物,但又并不明确具体指向哪一个事物;它指向的事物虽然不明确,但也不会让受话人天马行空地去胡乱猜测。
总之,一个有价值的空符号既要能够让受话人感受到能指的存在,也要让受话人有一个寻找到具体所指的方向。空符号会留给受话人一个寻找真正所指的空间,他既不会随意得到一个具体的所指,也不会漫无目标地胡乱猜测具体的所指为何物。寻找这种空符号的具体所指就像是在一个抽奖箱里摸奖券,摸奖人清楚地知道奖券就在箱子里,也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寻找奖券,他会非常积极甚至充满激情地去寻找目标。空符号就是一个抽奖箱,范围有限,但没有现成的答案。空符号提出的是一个开放性的选题,答案自然也是开放性的。
三、空符号之于文学
文学之所以是艺术不仅仅是因为文学文本本身能够传递大量的信息,并展示其语言之美,还在于它能够在读者心中产生共鸣,激发读者产生更多的联想,让原本圄于文本的信息获得增值,让文本充满现实的活力。汪曾祺(1994:5)非常强调文学文本对读者的影响:“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所谓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或活力一定是作品能够激发观众或读者积极参与的热情。作品中什么性质的内容可以唤起读者的热情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非常复杂,我们这里尝试从空符号的角度来回答。
艺术水准高的文学作品都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艺术性不佳的作品很快就会被遗忘,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与蔡格尼克效应(Zeigarnick Effect,又称未完成效应)(https://www.psychologistworld.com/memory/zeigarnik-effect-interruptions-memory)有关。蔡格尼克效应是心理学中有关记忆加工的阻断效应。最初立陶宛的心理学家蔡格尼克(Bluma Zeigarnick)的导师Kurt Lewin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即咖啡馆里的服务员对于那些未支付的账单记得非常清楚,但对于那些已经支付过的账单的记忆却比较模糊。这似乎表明已经完成的任务容易被遗忘,而未完成的或被打断的任务会让人记忆犹新。蔡格尼克通过实验验证了这种现象,并于1927年发表了论文《论完成与未完成的任务》。所谓未完成或被阻断的任务往往意味着任务的不完美,留有一些空白,而正是这些空白之处更容易引起关注,激发人们实现“完型”(gestalt)的冲动。如果一项任务彻底完成了,人们就会把这项任务搁置在一旁,不再给予关注。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在学术界引起争鸣的论文更容易被学者们所关注,在娱乐界明星人品完美的记录一旦被打破,总能激发更强烈的关注,维纳斯缺失的断臂成为其艺术价值永恒的焦点,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之所以流传久远,就是因为be所表达语义的不确定性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巴尔特曾说:“文学写作就是挑战与质疑,而不是提供固态的艺术价值。”(Rick,1994:22)一旦艺术价值被作者固定了,或者说完全阐释透了,该作品也就失去了活力,不再会引人驻足观赏。
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认为,作品的教育与娱乐功能需要在读者的阅读中实现,该实现过程就是作品获得生命力和最后完成的过程。因此,读者在此过程中是主动的,作者的话语只是在引导读者获取想要得到的信息。对于接受美学的创始人之一的伊瑟尔(Iser)来说,文学文本的完成必须经过读者的阅读过程,文本的潜在意义需要通过读者来实现。“文本之所以能成为文学作品,是因为它具有结构上的‘空白’。文学文本只提供给读者一个‘图式化’的框架,这个框架无论在哪一个方向和层次上都需要有足够的‘空白’,有待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填补与充实。”(李勇忠,2009:72)文学作品中的空白是什么?它是否属于空符号,也就是说是否能够满足空符号概念的要求?
从我们预先设定的空符号的概念出发,文学作品中的空符号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具有显性替代标记的空符号,这类空符号最容易识别。一般来说,空符号不应该有任何显性标记,如话语中的沉默、停顿都可以成为空符号,但它们没有任何语音形式的体现,完全是靠与言语的对照才能体现它们的存在。这里所说的有显性标记的空符号的特殊性在于这些显性标记仅仅用来提示此处内容缺失,而本身并不表达任何含义。例如,贾平凹的作品《废都》中使用了大量的“□”符号,用来避免直接描写性行为。这些“□”本身并不是空符号,而是空符号的替代标记。实际上,文学作品中最常用的显性空符号标记是省略号“……”,有时也会使用长连线“ ”。这类省略号的作用有很多(祝敏青,2019),其中有的所指义比较明确,而有的则含义模糊。例如:
(4)“她的胸脯真美,像个受难的女英雄,高高地挺起。我真的想上去碰一碰她的……看看是不是塑像。我对自己有这种想法很害怕。”
(5)她对主编说杨必然是个出色的编辑,是个出色的人,那个早晨他不是调戏少女,他只是,他只是……他只是……他不过是……
于是主编也对杨必然的妻子说了声:“知道了。”
例(4)选自严歌苓的中篇小说《白蛇》,这是徐群山日记里记录的对舞蹈演员孙丽坤的仰慕,省略号的所指非常明确,不言自明。例(5)是铁凝《蝴蝶发笑》中的一段,杨必然因为动手掐了一个少女背后的蝴蝶,就被认定是调戏少女,遭到编辑部解雇,于是杨必然的妻子来到编辑部与主编有了上述对话。此处省略的内容或所指比较模糊,连发话人都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然而这种难以言表的空符号却被主编解读了(当事人的妻子底气不足,无法自圆其说),不需要她作更多的解释。
韦世林(2012:133-139)所提到的“篇章文面中的空符号”虽然也与文学作品有或多或少的关联,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空符号,不符合我们对空符号的定义。比如,她认为,页边距、字间距、行间距、空格等都是空符号,毫无疑问这些地方相对于文字而言都是空的,但这种空往往不能被读者所感知,也很难说表达怎样的所指义。她还认为,所谓的“楼梯诗”(即诗行像楼梯一样错开)和“英雄纪念碑诗”(诗词的排版方式构成了纪念碑的形状)本身是实符号(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一般符号),但这种实符号源于周围空符号的映衬作用。我们并不认为实符号周围的空就是空符号,因为读者所感知到的只是实符号,空符号不但不能被感知,也并不具有任何所指义。
第二类是结构内容缺失所形成的空符号,这类空符号没有像第一类空符号那样的显性标记,只是作为整体的某些部分内容缺失了,但这种缺失可以被感知。例如,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需要有始有终,当然也少不了过程,这种完整性一旦被打破(如故事没有交代最终的结果,或者没有提及故事的起因),就会留下空白,而且这种空白很容易会被读者感受到(即能指可被感知),但对于具体的所指是什么,就需要读者根据已有的内容进行合理的推断。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所指必然存在,同时也不会是一个任意的所指,真正的所指往往需要发挥读者的想象力和推理能力,来得出一个令自己信服的结论。这正是文学故事的魅力所在,因为根据萨特的美学思想,文学作品都是面向读者的呼吁(朱立元,2004),是用一种空符号的方式来激发读者积极参与意义的建构和完善。
部分缺失的整体关系中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因果关系,即有因无果,或无因有果。因果关系是一种自然的逻辑关系,具有不可分割的完整性,深深根植于人的完型心理中。每当读到某个人物自杀了(此为果),读者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此为因),因此时就成了一个能被感知的,又具有一定所指的空符号。例如,欧·亨利的著名短篇小说《最后的常春藤叶》讲的是一个得了重症肺炎的女子琼珊与病魔抗争的故事。她看着窗外的常春藤叶一片片掉落,感觉自己的生命也将随着最后一片叶子的掉落而凋亡。叶子枯萎掉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种因果关系。正是这种不可阻挡的因果关系,琼珊感觉自己生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就等最后一片叶子掉落,自己的生命也就到了终点。故事的精彩之处就在于有人(同样得了肺炎的贝尔曼先生)打破了这种因果关系,让果始终无法出现(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即最后一片藤叶也掉落了,但贝尔曼先生用画笔在墙上画上了一片藤叶来替代)。无论是读者还是文学评论家都把焦点放在最后的那片藤叶上,认为这个有形的符号代表了生命和最后的希望。我们也可以从空符号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个情节。主人公在病入膏肓的时候,虽然仅有的一片藤叶仍让她怀有一点点生的希望,但更多的恐怕是她对藤叶即将掉落这个空符号的极大恐惧,是这种恐惧让她抓住了唯一的一点寄托,坚持着不愿放弃。我们也都可以看到小说本身并没有多少内容渲染她与死神抗争的积极心态,反而是主要描写她随着藤叶的掉落情绪越来越低落,越来越绝望,在到处弥漫的悲伤气氛中才流露出那么一点对生命的渴望。藤叶掉落这个空符号之所以在文学评论中不那么引人注目,恐怕主要是那个显性的符号(最后一片藤叶)太过醒目,其象征意义太过强烈,而且还有着满满的拼搏向上的“正能量”。
第三类文学空符号比第二类更加隐蔽,需要更多积极的智力活动参与方能挖掘出其所指含义,这类似于接受美学所讲的文本结构上的空白(朱立元,2004)。但我们认为这主要是一种语义上的空白,形成原因既有语言本身的问题,也有作者语言表达含蓄抽象的问题。首先,语言中的能指总是有限的,而用其表达的所指却是无限的,作为能指的语言符号永远不可能全面、准确地表达无限丰富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巨大缝隙的根本原因(王东、李兵,2013b:139)。而这种缝隙就是一种空符号,需要读者敏锐地发现它,并再现其语言无法穷尽的丰富含义。例如:
(6)“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
“排出”一词虽然非常形象生动,而且契合孔乙己当时的身份形象,但如果读者没有在自己脑海中构建出一个丰富立体的形象,这个词也仅仅是表示一个特别的动作而已。任何一个词都是一个一般的语言符号(能指),对应某一常规语义(所指),这样一种固定甚至僵化的对应关系不可能让语言具有任何艺术性或感染力。我们应该把语言符号视作一个符号与空符号的结合体,其中符号负责指称常规语义,而空符号负责指称具体生动的语义。空符号是符号所留下的一个巨大的阐释空间,需要读者根据语言语境、个人的百科知识以及推理、想象能力等来填充这一空间,努力再现作者心目中的形象。由于作者和读者各方面的个体差异,读者再现的形象不可能与作者的一致,而且不同读者所再现的内容也会参差不齐,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恰恰是艺术魅力体现的一种方式。
其次,语言表达有抽象与具体之分,越是具体、明确、详尽的语言,留给读者个人发挥的余地越小,而相对抽象的语言更容易被读者借用来填充个性化的信息。换句话说,抽象的语言会预留更大的空间,体现为一种空符号,供读者来阐释,这种空符号的所指存在于读者的头脑中,而非一种规约化的固定含义,没有所谓的“固态的艺术价值”(Rick,1994:22)。前面提到的to be or not to b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看似具体的表达实际上是高度抽象的,而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机制就是隐喻。隐喻是由源域与目标域构成的一个整体,是一种基于相似性的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关系(Lakoff & Johnson,1980)。在显性话语中,如果只有源域,而没有目标域,这就意味着存在一个为目标域而预留的空白,我们可以视其为空符号。对该空符号所指的确定既有赖于隐喻的常规关系,也有赖于读者个人的解读,这就会导致出现很多不同的所指。而相对于这些较为具体的不同所指,源域的表达方式就显得比较抽象。请看Robert Frost的诗歌The Road Not Taken最后两行:
(7)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作者在诗中并未提及生活的选择之类的内容,但读者都读出了这层含义,而不认为作者只是在谈选择走哪一条道路(Sweetser,2017)。“生活即旅行”(LIFE IS JOURNEY)是一个常见的概念隐喻,当旅行被提及,而生活未被提及,生活就成了该隐喻的一个留白,读者就会努力寻找内容进行填充。事实上,生活本身也是抽象的,读者会用更加具体的实例来诠释这种生活,诗歌的艺术性和感染力也就由此弥漫开来。
由隐喻生成的留白也可以从前面所谈的第二类文学空符号角度去阐释,就是从整体性的视角出发来分析是源域还是目标域的缺失留下的空白。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将另文讨论。
四、结语
文学空符号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显性空符号的能指比较容易被感知,这不仅仅是因为这种空符号有明显的标记,还因为这些标记占有较为明确的句法或语篇位置。显性空符号的所指既有比较确定的,也有比较模糊、难以固定的,但是范围总是比较明确,被限定在一个较为具体的框架内。我们讨论了两种隐性的空符号:一种是基于整体性的部分缺失所形成的空符号,另一种是抽象表达所形成的空符号。隐性空符号的特点是不易被觉察,需要读者不断结合语境与自己的体验来发现这类空符号,并付出一定的智力才能解析出有价值的所指含义。相对于显性空符号,隐性空符号的边界、位置、地位往往是模糊的,漫不经心或粗心的读者可能感受不到这些空符号的存在,自然也就解读不出最终的所指义。但对于细心而专注的读者来说,不断发现这些空符号,努力寻找这些空符号的所指义,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就在不断增强与升华,文学艺术的魅力也就越凸显。因此,文学的艺术性与活力很大程度上在于读者能否对空符号作出有效的识别与契合自身背景的解读。文学空符号研究中读者的地位非常重要,正是因为读者参与到意义的构建中,文学意义才变得丰富多彩。而以往的符号学研究更加注重稳定的能指与所指关系,注重社会规约。这种差异类似于社会符号学与传统符号学之间的关系,因为“社会符号学认为意义是在交际双方的协商过程中生成的……社会活动参与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因素”(田海龙,2015:4)。这种思想也非常契合我们对文学空符号的研究。
注释:
① 曾庆香(2017:23)较为完整的空符号定义是:“能指为能被感知到的‘无声无色无形’的空无,即能指在物质上处于缺失状态,但却能被感知,并且具有确定的所指对象。”但是我们对该句的主语为能指和“具有确定的所指对象”持不同意见。首先,因为能指是一个心理层面的概念,是符号之所以成为符号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分,不可能表现为“空无”,真正表现为“空无”的是能指的物质载体,或称符号载体,因此我们把能指改为“能指的符号载体”;其次,我们认为,能指并不总是具有确定的所指对象,所以把“具有确定的所指对象”改为“通常具有确定的所指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