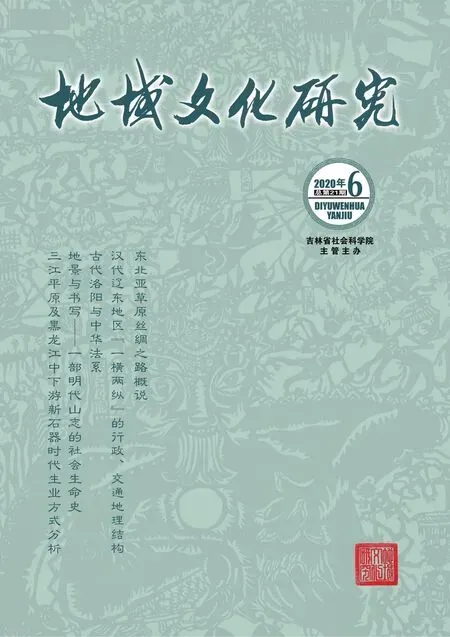从“中心”到“边缘”:广西上思舞鹿民俗功能的场域变迁
胡 媛
舞鹿是广西上思县独有的一项儿童舞蹈,以儿童穿上“鹿”形状的道具模拟鹿的动作来展示,2012年入选第四批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舞鹿从什么时候兴起,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但其口耳相传的历史轨迹表明:舞鹿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盛行一时,成为当地民俗文化的重要活动;20世纪90年代开始衰落;2000年后国家“非遗”活动的兴起,地方政府重新挖掘抢救,舞鹿又被重视,但已不复当年的辉煌。在笔者的调研过程中发现,舞鹿的结构形态一直变化不大,然而其生存的社会制度、秩序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即其生活的社会场域的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何为“场”?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①[法]皮埃尔·布迪厄著,许钧译:《关于电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5页。如果把舞鹿生存的社会空间想象成一个场,不仅场里有其他民艺活动与其争斗夺主权,场外亦有其他民艺活动的入侵争夺。如此,我们或许可以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观照:在变与不变之中,舞鹿在其生存的结构秩序里与其他民艺如何博弈。
一、不变的上思舞鹿结构形态
上思舞鹿作为一项民族儿童舞蹈,它的表演需要道具“鹿”来辅助完成,因此道具的制作既讲究工艺技巧又要契合儿童表演的天真烂漫。从工艺而言,舞鹿道具的制作有固定的程序与要求,道具“鹿”既要做得轻巧、颜色丰富艳丽,又具有鹿的形象特征;从舞蹈而言,舞鹿的表演生动活泼,旨在以儿童的嬉戏模拟鹿的日常动作。以此,无论是作为外在形式的舞鹿道具制作还是作为内在形式的舞鹿表演动作,都有章可循,变化不大。
(一)舞鹿的“鹿”制作
舞鹿的“鹿”制作主要包括两部分:鹿头、鹿衣(鹿身),其中鹿头的制作是最讲究、最重要的部分,鹿衣即和鹿头缝接一起被当作鹿身的布。鹿的制作用到的材料主要有:优质黄泥、白布、牛皮纸、砂纸、糨糊、粗竹、染料、树杈、木棉树、老樟树、干树皮、特制规则钉等。鹿头是用竹篾编成,贴上砂纸涂上红色或黄色如果贴的是布料就更耐用;接着在砂纸或布料上画上鹿的眼睛、嘴巴和耳朵,也可用硬纸做耳朵。鹿角是用长柄像鹿角的树杈做成,涂上红色或黄色,树杈的柄长到鹿头里面,舞鹿的人就是在鹿身里面拿着这两条长柄舞的。鹿头的嘴开得很大,这样在舞鹿过程中,有人扔红包到地上的话,可通过鹿嘴伸出手把红包捡起来。跟舞狮高难度的抢红包相比,舞鹿的捡红包简单得多,这可能是因为舞鹿的都是些8—13岁儿童,不具备做高难度的动作的条件。鹿衣(鹿身)主要是用1.5米左右的白布制成,另加一条尾巴,用黄色颜料画边,用红、绿颜色画梅花鹿的斑纹,再要添画四条腿。现在一个鹿的制作至少要250元,原来一直有专门的民间艺人制作鹿头,但是现在制作鹿的人依然是老艺人,几乎没有年轻人从事这项工作。
(二)舞鹿的表演
舞鹿的表演工具:鹿头、鹿衣(鹿身)、小锣、小鼓、小镲等;鹿衣是和鹿头缝在一起的整套工具,乐器用来给舞鹿伴奏。舞鹿表演者由8—13岁的儿童扮演,伴奏没有年龄的要求。舞鹿原来一直是只有2 个人舞,20世纪80年代后增加到4 个人舞,而以鼓、锣、镲三种乐器为伴奏一直没变。因此,一个舞队至少要6 个人组成:2 只“鹿”,1 人舞1 只,敲锣、打鼓、拍镲各1 人,还有1个带队的东家。带队的东家负责舞鹿道具的配备,出演时,东家把鹿队带到村头就可以了,剩下的就由儿童挨家挨户地去表演;但如果是主家邀请的话,东家就要带队去主家表演。表演过程:每套舞鹿的顺序是先恭喜,演奏的鼓乐声——咚咚咚咚咚咚嚓!此时如果带有鞭炮就放一封小鞭炮;接着开始舞鹿,几头小鹿或跳或蹦,或相互顶角,此时的奏乐声——咚咚嚓!咚咚嚓!咚咚嚓!咚咚嚓嚓!咚咚嚓!反复演奏;最后结束的演奏声和开头的演奏声一样。表演的动作:舞鹿由男童手执鹿头,身披鹿衣模仿鹿的动作、形态进行表演;表演主要由匍匐、并腿小跳、顶角、对拜、一字横排拜、碎步转身等动作组成,依节拍而起舞,按四拍、六拍、散拍等节奏转换舞姿,在节奏上有前紧后松的特点。一套鹿的表演时间一般10分钟左右(一段完整的舞鹿程序大概一两分钟就可完成,10分钟的舞鹿其实已经是在不断地重复动作了),但也有以主家给的红包为准,快给就快演完,慢给就慢演完,也有多给就演久点,少给就结束早点。整个表演过程主要是模拟鹿在森林中抢夺食物、嬉戏的场景,配以鹿的道具,以及儿童笨拙又灵巧、细碎又连贯、稚嫩又成套的动作,呈现出朴实、小巧又充满了童趣和天真的美。
总之,无论是作为道具“鹿”的制作还是作为舞蹈表演的“鹿”,都是一套可习得的人类活动体系,它是有组织、有秩序、有程序、配套完整的活动,多少体现了民俗活动作为文化要素构成部分所体现出的永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这些不变的要素规训了舞鹿活动的特质,以及人们对舞鹿文化功能的一个基本诉求:娱乐。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的关键问题是:舞鹿生存的社会环境及社会制度是不断变化的,且人们对“娱乐”形式的诉求也是变化的。民俗作为文化要素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倘若它的文化功能已能被其他东西所代替,即意味着在它生存的场域里,“战争”已然开启。正所谓“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这些争夺旨在继续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①[英]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在一个场域中,往往存在着各种积极活动的力量,它们之间的不断“博弈”。如此,处于“中心”时期即还掌握“主权”时的舞鹿,它是如何宣示它的“主权”话语的呢?
二、舞鹿“中心”时期文化功能的显现
关于舞鹿“话语权”的呈现在于群众对它的认可度,它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并且这些要求的满足暂时是没有东西能代替的,对它的认可成为一时的主流;而舞鹿在群众中的热闹程度则是反观群众认可度的最好佐证。那么,能满足群众需求无疑是舞鹿文化功能的无可替代性。
(一)民俗活动:舞鹿的娱乐功能
舞鹿作为上思本地的一项重要民俗活动,它有特定的活动时间、活动场所、活动内容等,即所谓的“一种依传统力量而使社区分子遵守的标准化的行为方式”②[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0页。。在舞鹿盛行的年代,舞鹿是上思老百姓在春节期间以及其他人生礼仪时刻的重要民俗活动,每年春节到正月十五时段都有表演;平时的例如贺寿、婚礼、小孩满月、进新房等喜庆日子,一般都是应主家的邀请来庆祝,这个时候则需要在鹿头挂红花,以示吉庆瑞祥。春节期间的舞鹿表演要进行启鹿、封仓仪式:初一早给土地庙烧香叩拜表演作为“启鹿”仪式,“启鹿”后便开始到周边村屯给各家各户拜贺祝福迎接新年;正月十五再到土地庙烧香叩拜表演以示舞鹿结束即“封仓”仪式。春节期间的舞鹿是自行前去各家庆贺,家家户户提前准备好红包给进门表演的舞鹿队;舞鹿队先在本村舞,再到其他村。每到一个村子,要先到村里的土地庙表演,祝福该村在新年里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然后再到各家各户去,在庭院或堂屋演。
可知,此时的舞鹿是一种规范化、标准化、自觉化的活动:首先它是春节期间固定的表演活动;其次舞鹿队自发地到各家各户表演;再者是每家每户自愿地准备好红包接待到来表演的舞鹿队;最后是以舞鹿作为人生礼仪欢庆的方式得到大家的认同。舞鹿在无形中规训了人们去遵守这样的传统;而人也因为遵从了这样的行为活动,认同且暂时性地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
(二)传说:舞鹿的信仰功能
舞鹿只流传于广西上思县思阳镇、在妙镇、七门乡、平福乡、华兰乡、叫安乡、公正乡、东屏乡、那琴乡等壮族聚居地,其中叫安乡那歪村、思阳镇达丁村等一带较为流行。从老艺人的采访中,我们大抵知道舞鹿萌发于清朝初年,而经过上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有一定的程序和稳定性的表演形式,并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后成为重要的民俗活动。①采访者:胡媛;被采访者:李琉彬;采访地点:广西上思县叫安乡那歪村舞鹿传承基地;采访时间:2017年9月28日。然而舞鹿起源于何时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只是在民间有口头流传。我们在《上思县志》中,找到寥寥数字关于舞鹿的介绍:“舞鹿,每年正月,儿童少年装鹿白天巡村到各家之门前而舞,恭贺新年。鹿,笼作头,布作身,画上梅花点。每队一对鹿,每鹿一人舞,配锣、鼓、钗打击乐。”②上思县志编纂委员会:《上思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6页。调研过程中,80 岁的舞鹿老艺人岳椿秀说,他幼年学舞鹿时听老人说起,早时候当地曾经有过水痘传染严重危及小孩生命的事情,危急中人们投医无门。据说当时有位老人做了个梦,梦到有位仙人告诉他说将鹿的粪便用火烘干入药,可消除病危。人们照做,真的有效,治好了水痘,当地人也从此知道如何应对水痘。为了纪念鹿的功劳,人民以小孩舞鹿来表达对鹿的感恩之情,这就是舞鹿的最初来源,也成了舞鹿起源的传说。
如此,有起源有传说有历史,无疑给舞鹿这项民俗活动营造了历史文化渊源,而舞鹿的“报恩”“还愿”之意,正是其娱乐功能背景下衍生的道德、教育功能,进一步强化舞鹿的文化功能,而民俗活动的地位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秩序结构中的文化功能所决定的,即舞鹿的文化功能越显现、越得到人们的认可,其在民众生活的地位越重。然而不同于其他宗教仪式具备强大的约束性、神秘性,舞鹿的发生更多的是一种“自愿”行为。恰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它又满足了人们娱乐、寓教、寄托愿望的要求。
(三)仪式:舞鹿的民族意识功能
在这样有娱乐、有传说、有信仰的背景下,舞鹿文化功能揭示的是上思北麓壮族民族意识文化,在无形中显示文化功能衍生的多样性。而舞鹿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南方某一偏倚的少数民族村落中,其民俗文化的特性,带有深刻的民族意识与族群记忆,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人民群众。
首先舞鹿作为一种原生态的舞蹈形态,反映了上思北麓壮族人们的原始生活状态。所谓的原生态舞蹈体现的是先民在“歌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时的状态,它表现的是一种自娱自乐而不是表演性质,是参与而不是观赏,是随性而不是刻意的舞蹈,它是普通民众在民俗仪式或民俗活动中传承的民间舞蹈。原始的舞蹈状态是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生活状态的最直接记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舞鹿确实简单且没有什么规范的动作可言的原因,毕竟老祖宗一直流传下来的舞鹿动作也就只有这几个动作,这么多年都未曾变过、改过、换过。如我们在调研时问舞鹿传承人李琉彬,现今小朋友表演的舞鹿动作是谁教的?他说是他自己,我们追问,他的又是谁教的?他说一直都是这样舞的,从小看到老,舞鹿就是这样的。③采访者:胡媛;被采访者:李琉彬;采访地点:广西上思县叫安乡那歪村舞鹿传承基地;采访时间:2017年9月28日。这又间接反映了舞鹿当年盛行的状况:耳濡目染,理所当然就学会了。动作简单如舞鹿的“蹲、跳、匍匐、左右摇头、顶角”类似小孩嬉戏时的常态表现,而也只有小孩才能把这些简单的动作舞出孩子特有的天性;一旦动作规范化或者复杂化,对于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孩童而言,具有相当的难度,而这与舞鹿起源的初衷又是格格不入。舞鹿与其说是舞蹈,不如说是一种仪式,或者说是仪式舞蹈。
其次舞鹿作为一种仪式活动,承载了先民的原始祷告和愿望。舞鹿的动作简单,即模拟鹿在森林中抢食的动作和神态。但是舞鹿本身蕴含了深刻的意义和内涵,舞鹿起源于对鹿的感恩,在其历史的发展中,感恩成了舞鹿故事的初源,并衍生出寄意升官、福禄、平安、吉祥、和睦的内涵。可以说,舞鹿的动作和意义是两个相互脱离的关系,即其动作本身跟意义不构成相互关系,各自独立而存在。这在仪式活动中很少见,因为任何仪式动作都具有相关的内涵与之相呼应,而在舞鹿中,动作是动作,内涵是内涵,这让人有舞鹿的动作与内涵两者间对不上号的感觉,即舞鹿这样表演跟舞鹿潜藏的内涵没关系。对舞鹿整体而言,它表现了上思壮族人民对美好事物的寄托,并把这种希望通过简单的动作化为具体的祝福,成为舞鹿文化功能的延伸。
最后舞鹿作为一种民族记忆的载体,内蕴了民族的历史文化。舞鹿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了一段历史的生活,存续了一段族群的记忆。上思十万大山作为森林文化的代表,它丰富的物种和野生动物,直接涵养了舞鹿的存在前提,而有史料佐证,梅花鹿曾是当地常有的动物之一。可以说,以舞鹿呈现的民族记忆与传说相互印证,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映。鹿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与“禄”谐音,是“福禄”之意,而“福禄寿”在中国文化中寄意着深刻的内涵和最美好的祝福和愿望。有福有禄有寿,贯穿了人的一生,也是幸福人生的直接写照,这是一种普世价值观。这也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舞蹈,却能保留到现在的原因。
可见,舞鹿不但能满足人体机能的需要,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功能,有它的价值。在机体上,对儿童而言,嬉戏是一种自我天性的释放,并且跟随节拍舞动动作也锻炼了儿童的协调能力;对大人而言,它把人从常轨故辙中解放出来,消除生活的压抑、紧张与拘束。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乡村,因为没有什么文娱活动,这样的民俗活动在调节生活与精神的协调显得尤其重要。而舞鹿的文化功能在于它是一种感恩先人、祈愿、祝福的形式,是上思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是对未知的一种期待;深层意念里是上思北麓壮族人民的一种民族意识与记忆,它有自己独特的民族传说和民族记忆。
三、舞鹿文化功能的“边缘”化
舞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慢慢地衰退直到现在,具体表现在:舞鹿队的解散、舞鹿活动的减少、舞鹿市场的萧条、观众的缺失等。而一种民俗活动是有相对的稳固性的,它存在因为有可满足人类需求的功能,舞鹿的衰落说明了自身文化功能在满足人类需求上已经不必备唯一性了。诚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形式上有些要素是不变的,它们是规定于它所有的活动的性质;有些要素是可以变异的,这变异或许是起于同一问题可有种种不同的办法,或是起于任何解决所附带的不十分要紧的细节。”①[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1页。在社会环境、社会秩序以及人类精神诉求不断变化的情境下,不变的是舞鹿的文化功能要素;而偏偏舞鹿的这些文化功能要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然可被其他东西代替。这些代替性的东西分属舞鹿生存的场域内与场域外的双重争夺。如此,舞鹿的衰落成了必然。
(一)舞鹿审美的简化与新媒体的冲击
在当地群众看来,舞鹿是缺乏“看头”的,即其本身审美的缺乏。舞鹿与舞狮应同属于一类的民间活动,然而舞狮所具有的技巧性、壮观性、灵活性、审美性、知名度等都是舞鹿所不能比的,但是在目前的状态下舞狮依然步履维艰,何况是舞鹿呢。舞鹿在动作上过于简单且表演程序单一,反复于“蹦跳”“匍匐”“顶角”“左右摇头”,连作为“外人”的我们第一次看到都觉得没什么新意,何况是司空见惯的当地人呢。而其动作在缺乏新意的同时亦缺乏内容的连贯性,我们在传承人李琉彬的解说下才稍微明白是模拟鹿于聚散中抢食。而在当今各种娱乐、文化的冲击下如果不是冲着舞鹿衍生的美好祝愿,无论对东家还是观众,都是毫无吸引力的。毕竟1个舞鹿队至少有5个人,请1次至少要500元钱,然而就只能看到2个小孩戴着鹿头、披着鹿衣像两头小鹿在森林窜来窜去,其他3个敲锣打鼓,一两分钟就能把全部动作表演一遍,而花500 元钱请人来舞一场狮,可能更为精彩、壮观和热闹。舞鹿兴盛的时候,舞鹿在上思几乎是村村有,而那些年代舞鹿的所得也不过几分几毛钱,却如此繁盛,很大原因在于舞鹿是一项民间的祝福活动,它舞的是热闹,是祝福,是狂欢,是当地人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是全民参与的活动。而这样的狂欢与热闹,现在已被各色各样的新媒体取代,舞鹿不仅没有市场,甚至在许多村里也慢慢地被遗忘,以至于我们现在只能到舞鹿的传承之地——叫安乡那歪村才能看到。
(二)舞鹿传承人的断代与缺席
舞鹿传承人李琉彬(今年74 岁)是叫安乡那歪村村民。在笔者采访中,李琉彬艺人告诉我们,舞鹿盛行的时候,几乎村村都有,但是现在几乎都没有了。①采访者:胡媛;被采访者:李琉彬;采访地点:广西上思县叫安乡那歪村舞鹿传承基地;采访时间:2017年9月28日。李琉彬的重要搭档李参彬,今年也70岁了,他们负责那歪村舞鹿的传承,那歪村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样热心的传承人以及一些热心的推动者、才保存了今天那歪村甚至是上思舞鹿的延续。他们在村中挑选8岁以上的儿童,教他们舞鹿的基本动作和步骤,一般跳几年到了14岁左右就重新挑选一批,从而使得舞鹿可以生生不息地流传下来。但是与早年的专业舞鹿队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舞鹿队主要是业余的。一是小孩要上学,舞鹿对他们而言是学习之外的“好玩”而已;二是现在对舞鹿的市场需求并没有早年来得强烈,这可能是因为舞鹿过于简单又或许是舞鹿的没落导致了人们对它的遗忘;三来与同样具备喜庆、祝贺功能的舞狮相比,人们更青睐舞狮场面的霸气、动作的惊魂、技巧的丰富。由此可见,舞鹿面临着传承人年纪越来越大,学习的人越来越少,现存的舞蹈元素难以适应现在市场的需求等尴尬局面。上思舞鹿这个壮族特有的儿童舞蹈几乎处于失传的状态。

表1 上思县叫安乡那歪村舞鹿传承谱系
由上表可知,现还在世的主要舞鹿传承人,年纪最大的是74岁的自治区舞鹿非遗传承人李琉彬,年纪最小的是20岁的黄世民,虽然从该表来看还后继有人。但结合我们对那歪村舞鹿的实地调研,发现情况并不乐观:调研时组织的舞鹿队是从学校匆匆赶回来的四个初中男生,分别是12—14 岁,他们8岁开始利用课余时间跟李琉彬学习舞鹿,平时表演机会不多,但过年会到各家舞鹿;年纪最小的传承人黄世民没有看到,听说外出打工去了。由此可见,对年轻一代人而言,学习舞鹿并不是件“有前途”的事情,或许打工还是另一条出路。这样看来,目前舞鹿的年轻传承人是有的,但是能否真正地承担起传承,还有待商榷。
(三)舞鹿传承保护意识的淡薄
对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大都是随着国家对“非遗”的重视而重新进入当地政府的视野,从而开始重视当地的“非遗”,舞鹿也不例外。就舞鹿而言,2000年之前都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而此时,对于已经萧条了几十年的舞鹿而言,实际上,它已经退出了民众的生活,就相当于根植于群众的土壤已经贫瘠甚至是没了土壤,要恢复,谈何容易。即便是2000年后,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视,地方政府深入民间去发现和挖掘民间的文化遗产,但也只是简单的记录,对舞鹿的宣传和保护很难一下子做到位。对当地群众而言,曾经的娱乐活动,寄意着祈福、还愿等美好祝福、意蕴的舞鹿因为逐渐淡出了生活的视线,变成可有可无,也就不觉得它对生活的意义有多大。以此,舞鹿原本对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就被淡化,成了表面形式上的儿童游戏罢了。然而舞鹿虽简单但又不是一般的儿童游戏,它具有一定的表演程序,需要学习才能获得,并且需要在固定的时间、场所进行表演才有意义。总之,舞鹿的表演需要人、时间、场所、财力、学习等支撑才能实现,这就导致了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耗时、耗力去学习已被认为没有“前途”的“游戏”。
总的来说,一项民俗活动由繁盛到没落,由中心到边缘,既有社会、历史、文化等客观因素,也有自身的主观因素。舞鹿场域从中心到边缘的流变,同样是时代与自身等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
结 语
我们回顾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民间生活的日常状况,是较为单调的,而封闭的地区更甚。所以为什么在今天各种文化倾向于同化,而较为封闭和偏远的山村能够很好地保存了自己的民俗传统文化在于:首先传统文化有自己的相对的稳定性,其次由于地缘环境原因受到外界的干扰较少,但这样的文化传统秩序,并不是所有的都可“坚如磐石”,一旦有更加热切、新鲜、有活力的外部势力进入时,它是可以被瓦解,被解散,被代替的。特别如舞鹿这样,它的基本功能是娱乐,而在“非遗”的视域里,舞鹿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传统民间儿童舞蹈,其文化内涵、审美特性、民族个性和符号意义等,对民族特性的挖掘和发现,对民间传统的认识和共鸣,对原生态舞蹈的起源和发展等,有着深刻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视角,重新审视、挖掘舞鹿在当下的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