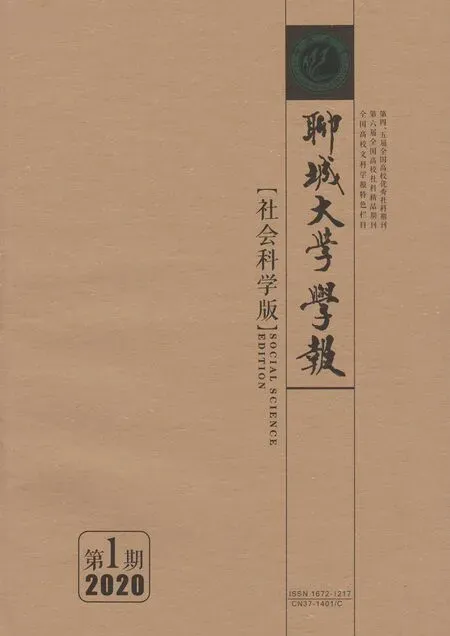中国古代文学的异域解读
——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谫论
卞东波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一、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产生的学术背景
中日两国有悠久的汉籍交流史,随着汉籍传入日本,日本对汉籍的研读也因之而产生。早期对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的研究主要是日本贵族、学者、僧侣研读、讲习中国文学的产物。在平安时代,《文选》与《白氏文集》是当时贵族学习汉文学的主要模板,也是大学寮中博士的主要教材。当时主讲《文选》最著名的博士家是菅原家和大江家,两家也形成了自己的“文选学”,他们的讲义被称为“菅家证本”“江家证本”。江户时代著名儒学家林鹅峰(1618-1680)《题侄宪所藏〈文选〉后》尝云:“故本朝菅、江诸家博士,成业扬名,藉此书(《文选》)之力者不为不多。”①《鹅峰林学士文集》卷一百,日野龙夫编:《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12卷,东京:ペりかん社,1997年,第407页。菅、江二家对《文选》的注释目前大部已经散佚,但在日本古写本九条本《文选》识语中还保存着一些“菅家证本”的逸文②参见陈翀:《〈文选集注〉李善表卷之复原及作者问题再考》,王立群主编,郭宝军、张亚军副主编:《第十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61页。。室町时代学者菅原和长(1460-1529)的《御注文选表解》是东亚最早对李善《上文选注表》的注释之作,本书融聚了传为菅原道真的“御注”以及菅原和长的“愚解”,不但是菅原家“文选学”的直接遗存,也是研究日本中世“文选学”的宝贵资料③参见卞东波:《〈文选〉东传学之一斑——菅原和长〈文选御注表解〉探析》,《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2年第4期。亦参见山崎诚:《式家文選学一斑——文選集註の利用》,载氏著:《中世学問史の基底と展開》,东京:和泉书院,1993年。。
到了日本中世之后,汉籍与汉文学的接受主体转到五山寺院中的禅僧,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模板也从《文选》《白氏文集》变为《古文真宝》《三体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等被中国视为初学者读物的文学总集,汉诗的典范诗人也变为唐代的杜甫、韩愈,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等人,故在室町时代产生了很多《古文真宝》《三体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杜诗、韩文、东坡诗、山谷诗的“抄物”。“抄物”是当时五山禅僧对汉籍进行解说与注释之书物的统称。这些抄物使用的语言或为汉语,或为假名,或为汉文与假名的混合体。当时的杜诗抄物有心华元棣(1339-?)的《心华臆断》、江西龙派(1375-1446)的《杜诗续翠抄》、雪岭永瑾(1447-1537)的《杜诗抄》以及仁甫圣寿的《续臆断》,其中《杜诗续翠抄》和《杜诗抄》流传至今。崇杜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江户初期儒学家伊藤东涯(1670-1736)为清代陈廷敬《杜律诗话》和刻本作序时说:“今也承平百年,文运丕阐,杜诗始盛于世矣。”虽然从学术史来看,江户的杜诗热可以追溯到室町时代,但江户时代杜诗的出版热潮则是室町时代无法比拟的。当时众多中国的杜诗注本在日本被陆续翻刻,如元赵汸选注的《翰林考正杜律五言赵注句解》,明薛益注的《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明邵宝集注的《刻杜少陵先生诗分类集注》《刻杜少陵先生诗集注绝句》,明邵傅集解的《杜律五言集解大全》等。而且江户学者自己也创作了很多杜诗的注本,如宇都宫遯庵(1633-1709)的《鳌头增广杜律集解》、佚名的《杜律要约》、大典显常(1719-1801)的《杜律发挥》以及津阪东阳(1757-1825)的《杜律详解》。江户时代刊刻的杜诗注本基本以杜律为中心,可见彼时日本文人对杜诗的关注点,而这些杜律注本至今仍有学术价值,中国学者所撰的《杜甫全集校注》①萧涤非主编,张忠纲终审统稿,廖仲安、张忠纲、郑庆笃、焦裕银、李华副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也引用过日本的杜律注本。
五山时期关于东坡诗、山谷诗的抄物最多,禅林中流行着所谓“东坡山谷,味噌酱油”之说。五山禅僧以旧题宋代王十朋所作的《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东坡先生诗》为底本,援引流传到日本的坡诗施顾注、赵次公注对王注予以增补辨证,并从自己的角度再加以阐发,从而形成了很多新的注本,如大岳周崇(1345-1423)的《翰苑遗芳》、瑞溪周凤(1392-1473)的《坡诗脞说》、一韩智翊(生卒年不详)的《蕉雨余滴》、江西龙派的《天马玉津沫》、万里集九(1428-?)的《天下白》等等,笑云清三(1492-1520)则将上述诸书加以汇集,加以己见,形成一部规模更大的日本苏诗集注本《四河入海》。山谷诗的抄物在日本则有万里集九所作的《帐中香》,以及月舟寿桂(1460-1533)所作的《山谷幻云抄》②参见根ヶ山彻:《月舟壽桂講〈山谷幻雲抄〉考》,载《東方学》第115号,2008年,第88-105页。等等。
江户幕府建立之后,立儒学为官学,任用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等大儒。当时的汉学者主要致力于朱子学在日本的发展,而于文学创作不甚重视,友野霞舟(1791-1849)《锦天山房诗话》(上册)云:“国初诸老皆专攻经学,不复留意于辞章,虽间有所作,多以语录为诗,或以国雅为诗。”③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第8卷《锦天山房诗话》,东京:文会堂书店,1921年,第328页。洎江户中期,以荻生徂徕(1666-1728)为代表的“古文辞学派”(又称“蘐园学派”)崛起,他们在学术思想上以反朱子学为主要特征,在文学上主张学习唐诗及明诗。荻生徂徕《与薮震庵》(《徂徕集》卷二十三)云:
不佞始习程朱之学,而修欧苏之辞。方其时,意亦谓先王孔子之道在是矣。是无它,习乎宋文故也。后有感于明人之言,而后知辞有古今焉。知辞有古今,而后取程朱书读之,稍稍知其与先王孔子不合矣。夫然后取秦汉以上书,而求所谓古言者,以推诸六经焉,则六经之旨,了然如指诸掌矣。是亦无它,习乎古文故也。
徂徕认为,要领会“先王孔子之道”,不能依据宋儒的“近言”,而要通过秦汉以上的“古言”。明代李梦阳等前七子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李梦阳传》)的复古主张,徂徕则认为可以通过学习李、王等的文章达到秦汉的“古言”,最后达到“先王孔子之道”。当时的蘐园派学者几乎都持这种看法。如山县孝孺《刻弇州尺牍叙》云:
我徂徕先生征《论语》、著二《辨》(引者按:即《辨道》《辨名》),拯斯文于既坠,而先王、孔子之道炳如。其始来也,假道于李、王古文辞。故不修古文辞,不能续先生书而达其旨,况于六经、《论语》乎?文章之不可已也,其如是耶!李、王文士,其道无足述,在唯其文辞可以进于古文,则李、王何不可述?
尽管李、王之道“无足述”,但“其文辞可以进于古文”,故“假道于李、王古文辞”是达到“先王、孔子之道”的最佳路径。又源大简《弇州诗集序》云:
济南、娄东之才也,物子而后知其出群拔萃,不翅渊综广博,清通简要,如显处视月,牗中窥日矣。物子一唱,而后我大东之人靡然称王、李……夫物子之有功于天下后世,虽比之孔子,何让哉!噫!微物子,后死者不得与斯文焉!而物子得之者,以其阶梯王、李,知古文辞通于古经之故也。
所谓“阶梯王、李,知古文辞通于古经”与上文表达的意思并无二致,“阶梯”之说亦见于宫廷高《弇州尺牍解序》中:“文要必得法,得法而诣古,王、李之文盖其阶梯也。”职是之故,李、王等明七子的文集在江户中期风靡一时,俞樾《东瀛诗选序》:“其始犹沿袭宋季之派,其后物徂徕出,提倡古学,慨然以复古为教,遂使家有沧溟之集,人抱弇州之书。”这种盛况正反映了当时江户诗坛学习明七子的热潮,这股热潮与荻生徂徕等蘐园派的推动直接相关①不过,荻生徂徕并非是最早在江户诗坛提倡唐诗和明诗的,在他之前已有一些学者开始重视明七子诗,如新井白石以及木下顺庵弟子柳川震泽。梁田蜕岩:《蜕岩先生答问书》卷上《答左海竹田生》云:“元禄中,白云先生(新井白石)出于江户,专祖述唐诗,其入门学万历七子,自是世上诗风渐趋之,继而徂徕先生大变诗风,亦主之。”(池田四郎次郎等编:《日本艺林丛书》第2卷,东京:六合馆,1928年,第32页)又东条耕:《先哲丛谈续编》卷二载:“宝永、正德之间,物徂徕以夸博之议、杰出之才,左袒嘉、隆李、王之绪论,专唱其教,于是李、王诗风大行于世。其实创起于震泽之早年好读其集……宽文初,震泽校定陈继儒《嘉隆七子诗集注解》,使书铺刊之,又延宝中校刻李卓吾《正续明诗选》,我土刻明诗者,以此二书为始焉。”这里参考了刘芳亮先生的观点,见氏著:《日本江户汉诗对明代诗歌的接受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古文辞学说的风靡,带动了以李、王为代表的七子诗在日本的流行②参见刘芳亮:《江户前期明七子派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许昌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而传为李攀龙所编的《唐诗选》也在江户时代被多次翻刻,极其流行,据蒋寅先生考察,日本刊行的《唐诗选》版本多达93种③蒋寅:《旧题李攀龙〈唐诗选〉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日本接受中国文学的一个侧面》,载《国学研究》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63-386页。。熊坂台州(1739-1803)《白云馆近体诗式》云:
自物子唱李、王之业,服子迁左袒于沧溟选以来,海内学者率视《唐诗选》犹国风雅颂,不但学诗者朝习夕诵,号称善书家者,亦唯其诗句是书。无论辇毂之下,都会之地,篆隶法帖,行草石刻,至于僻邑穷乡,水村草市,酒家屏障,茶店题壁,亦莫不书李《选》所收者。噫!亦盛矣!
《唐诗选》流行的重要原因在于其编者传为李攀龙,而李氏是当时受追捧的明七子之一,同时《唐诗选》是由蘐园派主将服部南郭(1683-1759)校订的。江户时代出现的《唐诗选》注本,如千叶玄之(1727-1792)的《唐诗选掌故》、宇野明霞(1698-1745)的《唐诗集注》、大典显常的《唐诗解颐》、户崎淡园(1724-1806)的《笺注唐诗选》《唐诗选余言》、皆川淇园(1734-1807)的《唐诗通解》等,都或多或少与蘐园学派有关。
与此同时,明诗也在江户诗坛大为流行。林义卿(1708-1780)《诸体诗则》卷上:“本邦三十年来,徂徕先生之学化被海内,是以一时后进,皆能知开元、天宝之后,又有明诗。因明学唐则自然至于盛唐。”④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第8卷,第180页。这里将明诗与开元、天宝相并列,可见彼时明诗地位的隆升。因为当时日本的诗人将唐诗视为最高诗学典范,通过学习明诗最终可以“至于盛唐”(见上)或“优入唐域”(香川修德《明诗大观序》)。此种诗学风潮极大地改变了江户诗坛的面貌,友野霞舟《锦天山房诗话》上册云:“蘐老颖迈之资,桀骜之才,刻励揣摩,别出手眼,首唱古文辞,大声疾呼,以夸后进,海内风靡,文体为之一变,其功伟矣。”⑤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第9卷,第521页。所谓“文体为之一变”即当时的诗坛风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也影响到了出版状况,明诗选集于彼时在日本被大量翻刻,如李贽(1527-1602)编的《皇明诗选》《续皇明诗选》,陈继儒(1558-1839)句解、明李士安补注的《明七子诗集注解》,李雯(1608-1647)、陈子龙(1618-1667)、宋征舆(1618-1667)同编的《明诗选》,汪万顷辑注的《新镌出像皇明千家诗》,穆光胤删订、明陈素蕴校刊的《明诗正声》,陈荚、李昂枝评选的《明九大家诗选》;此外还有日本学者编纂的明诗总集,如伊藤长坚编的《明诗大观》,荻生徂徕编的《唐后诗》等书。在此基础上,日本也刊刻了不少明诗注本,如荻生徂徕的《绝句解》《绝句解拾遗》、宇佐美灊水(1710-1776)的《绝句解拾遗考证》、中川景德(生卒年不详)的《绝句解辨书》、祗园南海(1676-1751)的《明诗俚评》、宫濑龙门(1719-1771)的《明李王七言律解》、井上兰台(1705-1761)的《明七子诗解》、宇野明霞(1698-1745)的《嘉靖七子近体集》、中条允(生卒年不详)的《明七子诗掌故》等。这些明诗注本出现的原因,如祗园南海《明诗俚评序》所言:“然学诗者初读汉唐之诗,犹梦中听钧天乐,非不知其音之灵妙,但其茫然不能识灵妙之所在,不如先读明诗之易成功耳。”“汉唐之诗”固然是最高的诗学典范,但如果诗学修养不够深,则“茫然不能识灵妙之所在”,所以不如“先读明诗”来帮助理解唐诗。这明显受到蘐园派诗学主张的影响。明代诗人很多,最能代表明诗风范的就是明七子之诗。《七子诗集注解》末有宇都宫遯庵跋云:“七子诗之于他明诗,犹四灵之于羽毛鳞介,其格律鉴裁自非具眼者不易知之。”这也是当时明诗注本以七子为主的原因所在。
所谓物极必反,蘐园派追崇李、王等人古文辞学的结果导致不少人陷入模拟、蹈袭的恶习之中。中井竹山(1730-1804)《奠阴集》卷二《呈蜕岩先生书》:“今人稍嫓文词者,乃啜王、李遗粕,拾物、服余唾,开口辄唱唐明,謷然侈大,奴仆视宋人。及观其所作,连篇不出白云、明月之字,堆案唯是寸攘尺取之语。加之往往才短识陋,勉强搜索,始克作篇。”①水田纪久编:《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8卷,东京:ペりかん社,1987年,第29页。所谓“啜王(世贞)、李(攀龙)遗粕,拾物(徂徕)、服(南郭)余唾”,即是对时人模拟之习的痕诋;而“连篇不出白云、明月之字”则指斥当时诗歌创作的模式化弊端。类似的说法亦见于芥焕彦章(1710-1785)《丹丘诗话》卷下:“近物子首唱明诗,海内向风,夫人诵法于鳞而争事剽窃,神韵乃乖。‘青山万里’动辄盈篇,纷纷刻鹜,至使人厌。岂谓之善学邪?”②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第2卷,东京:文会堂书店,1920年,第623页。“争事剽窃”的结果必然导致“神韵乃乖”,故至宽政、文化年间,以市河宽斋(1749-1820)、大窪诗佛(1767-1837)、菊池五山(1767-1849)、柏木如亭(1767-1819)为代表的“江湖诗社”诗人开始提倡学习“清新”之宋诗,以此来反对伪唐诗和明诗,故在江户后期又产生了一些关于南宋三大家诗集的选本与注本③参见卞东波:《宋诗东传与异域阐释——四种宋人诗集日本古注本考论》,《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从上可见,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的刊刻与流行与日本诗坛的风气以及江户思想的变迁是息息相关的。
二、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的阐释方法
在东亚诗歌注释史上,注释之学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以《文选》李善注为代表,注重对文本中典故出处的考掘,以旁征博引为主要特征,而逊于对诗意的阐发,宋代的唐诗注释、宋人注宋诗都讲究“无一字无来处”,基本都是受到《文选》李善注的影响;另一派则不事文字之训诂、典故之疏解,而重视对文本大意的阐释发挥。宇佐美灊水《绝句解拾遗考证序》引荻生徂徕手泽例言云:“古来笺诗,其据引则学步李善,解释则借吻考亭。”所谓“借吻考亭”就是指借理学来解诗。在中国宋代之前的诗歌解释中,学者或以美刺说诗,或以礼制说诗,或以“物象类型”说诗。总而言之,都认为诗歌言与意之间存在某种张力,或者“言此意彼”的现象,可以称之为“讽寓”(allegory),用“讽寓”之法来解读诗歌,则为“讽寓性阐释”(allegoresis)①关于“讽寓”、“讽寓阐释”参见张隆溪:《讽寓》,《外国文学》2003年第6期。又参见苏源熙著、卞东波译:《中国美学问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日本的汉诗阐释也可以分为这两派,一派“学步李善”,另一派追求“讽寓性阐释”。《禅月大师山居诗略注》(下简称《略注》)前有注者海门元旷之序云:
二三子遂誊写将去,少焉,复袖稿本来,曰:“异哉!师注诗也,特勤质乎事实,而于诗义略之,非阙然邪?”呜乎!杂华妙谈,非如聋之徒所闻;《春秋》微言,虽曰游、夏不得措一辞乎其间。何矧如余者,堪容喙于大师雅言乎?余所注者,只在质于事实耳,其如演义,余岂与也哉!余岂与也哉!
《略注》的解诗特色就是注重对诗中语典、事典的解释,而不对诗意进行过度的发挥。序中引用元旷弟子的疑问:“师注诗也,特勤质乎事实,而于诗义略之。”元旷的回答进一步说明了其注释思想:“余所注者,只在质于事实耳,其如演义,余岂与也哉!余岂与也哉!”他强调他关注的是“事实”(语典、事典),而非“演义”,即对诗歌大意的发挥推衍。他认为,如果连诗中的“事实”都不能解释明白,岂不如“聋之徒”一般;至于发挥诗歌中的微言大义,就像“《春秋》微言”,精通“文学”的子游、子夏亦难解释清楚。海门元旷的这种学风也与江户曹洞宗追求“多闻博物,藏收竺坟鲁典”(卍山道白《归藏采逸集序》),融通内外二典以及临济、曹洞二宗的风气相关。
禅宗僧人如此,文人学者亦有持此种方法者,津阪东阳《杜律详解》下卷卷首有津阪拙修(孝绰之子)识语云:“从前诸家笺释,各有得失,盖训诂家与风人肝肠意见不同,偶尔遣兴,目前咏景,亦必求所寄托,牵强傅会,横生枝叶,遂使诗为谜,岂作者之意哉?”可见,津阪东阳注释杜诗,亦反对在诗中搜求所谓的比兴寄托,这样无疑只会造成诗意解释的牵强附会,而使“偶尔遣兴,目前咏景”的诗歌成为“诗谜”。
江户时代的大部分中国文集的注本属于这种看重“事实”的一派,如当时的杜诗注本、唐诗注本、《冠注祖英集》、明七子诗集注本,以及宇都宫遯庵所作的注本都属于这种类型。这些注本“学步李善”可能也与江户学术史上折衷学派的兴起有很大关系。江户折衷学派肇始于井上金峨(1732-1784)等人,东条耕《先哲丛谈后编》卷七载:
金峨之学不偏主一家,取舍训诂于汉唐之注疏,折衷群言,磅礴义理于宋明之诸家,撰择稳当,以阐发先圣之遗旨,匡前修之不逮焉。与近世经生胶滞文字、恣意悍言、求异先儒、联比众说、务事博杂,夸诬后学者不同日而语也。宝历以降,人知物赤城、太宰紫芝以韩商之学,误解六经、绕缠圣言之害者,其辨斥攻击,自金峨始焉。关东之学,为之一变。近世所谓折衷家者,若丰岛丰洲、古昔阳、山本北山、大田锦城等诸家,皆以经义著称,其实皆兴起于金峨之风焉云。
折衷学派“不偏主一家”,故能够“折衷”汉唐的训诂之学与宋明的义理之学。折衷学派之兴起与时人不满蘐园派“以韩商之学,误解六经,绕缠圣言”,及当时经生“胶滞文字、恣意悍言、求异先儒、联比众说、务事博杂、夸诬后学”的风气相关。江户后期宗宋诗风的开创者山本北山就是井上金峨的学生,折衷学派的兴起对当时的中国古代文学注本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使得这些注本在注释上追求一种质朴实的实证之风。
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除了有强调“事实”的一派,也有重视“演义”的一脉,而且这一派也渊远流长。这种注重诗歌“演义”,阐释诗中微言大意的解诗方式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从《诗小序》以美刺说诗,王逸《楚辞章句》以“香草美人”解《楚辞》,到《文选》五臣注以君臣关系、君子—小人关系说诗,再到南宋曾原一的《选诗演义》、谢枋得的《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都是用“讽寓”的方式解诗,将诗歌解释为政治寓言,诗歌中的物象都是一种文学隐喻。如惠洪《天厨禁脔》卷中评杜甫《江村》中“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一联云:“妻比臣,夫比君,棋局,直道也。针合直而敲曲之,言老臣以直道成帝业,而幼君坏其法。稚子,比幼君也。”这种解读诗歌的方式就是将诗歌中的物象与君臣、君子—小人对应起来,认为每首诗歌背后都有政治隐含意,从而造成诗歌字面意与隐含意之间的阐释张力,即形成言此意彼的“讽寓性解读”。
这种讽寓解释方式对日本的汉诗注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室町时代的《中兴禅林风月集注》就是典型的代表。室町和江户时代的黄庭坚《演雅》注本也喜用这种方式说诗。黄庭坚《演雅》四十句,每句都写到一种动物,描写了其习性,这本是一首典型的“以赋为诗”的咏物之作,宋代的任渊注仅解释诗中的字词语汇,但日本的注本几乎都执着于诗中物象背后讽寓意的揭示。如万里集九《帐中香》说:“凡举四十六种鸟虫,其内骥与鱼虾,盖无毁誉,但因类话举之。又以白鸥而比公之闲,其所讽之者,只四十二类而已。颇比群小人,其所嗜之性各异。”万里集九认为,山谷此诗对诗中42种鸟虫的描绘都有“讽”意,这里的“讽”就可以理解为“讽寓”,即用这些鸟虫“比群小人”。卧云子《山谷演雅诗图解跋》云:“黄山谷之所著《演雅》之诗,依托昆虫比况谗佞。”所谓“依托”“比况”即讽寓之意,亦是将诗中的物象比附为政治性的“谗佞”,完全是对诗意的推衍发挥。①关于《演雅》日本注本的“讽寓性解读”,笔者有详论,参见卞东波:《宋代文本的异域阐释——黄庭坚<演雅>日本古注考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1期。
江户时代原公逸的《古诗十九首解》(下简称《十九首解》)、石作贞的《古诗十九首掇解》亦用“讽寓”之法解诗。兹以《十九首解》为例略加说明,如解“明月何皎皎”一诗云:
比也。人主任贤不专,故群小争权,政多门。典法之缺废,社稷之倾覆,莫不阶于斯也。盖荡子二三其行,然而不失贞静之心、妾妇之道尔。士立于人本朝,无补于国家,岂其志乎?曹子建诗:“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诚然哉!
原诗以女性的口吻写出其夫远游不归而己思念不已、愁思难排之情,张庚《古诗十九首解》云:“此写离居之情。以客情之乐对照独居之愁,极有精思。”②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98页。但《十九首解》却从诗中的“愁思当告谁”等句读出了“人主”昏愦、“群小”恣肆争权的讽寓之意。③参见卞东波:《讽寓阐释的异域回响——江户时代<古诗十九首>日本注本考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笔者曾将这种解诗方式归因为中国语言哲学中“言不尽意”的传统思维,以及中国古代用诗时的“断章取义”传统。④参见卞东波:《曾原一<选诗演义>与宋代的“文选学”》,《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另外,中国古典诗歌诗意的隐晦、模糊、含蓄也为讽寓阐释提供空间。如田晓菲教授指出的,《古诗十九首》“文字表面上直白透彻”,实则有很多“隐含的信息”,盖缘于其“自身的隐性诗学属性”⑤参见田晓菲撰,卞东波译:《高楼女子:〈古诗十九首〉与隐/显诗学》,《文学研究》第2卷第2期,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而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诗无达诂”说也是诗意阐释多样性的思想基础。
以上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文本日本阐释的两种方法,另外中国文集日本注本也开创了一些注释新方法。宇佐美灊水《绝句解拾遗考证序》引荻生徂徕手泽例言云:
一诗所诠,延蔓数纸。武库森矗,反碍电目;理窟勃窣,乃翳金心。虽夸富赡,安资讽咏?今湔旧套,特创新规。事唯标用某事,而使之自考;意不必说何意,而导其独思。时添一字,跃如言下,此是程明道说诗方;忽发数语,泠然意外,亦为刘辰翁评诗法。
灊水提到荻生徂徕《绝句解》《绝句解拾遗》在诗歌注释上的“新规”,即“事唯标用某事”及在注释时“时添一字”,并说这是“程明道说诗方”和“刘辰翁评诗法”,不过将这种方式贯彻到整个诗歌注释中的还是中国文集的一些日本注本。如《绝句解》注王世贞《题杂画》仅云:“后二句用王弘之事。”并不具体引出王弘之事的内容。这种简省的方式也呼应了源伊信《绝句解序》中之语:“夫解,成于易简。简,约也;易,俚也。不俚则喻之不迩,不约则厌于读。厌与不迩,非所以益于学者也,可谓简易,解之良方也。”井上兰台的《明七子诗解》在解诗上也用了这种方法。兰台虽然在学术上属于折衷一派,但《诗解》一书从书名到注释方式皆可看到荻生徂徕《绝句解》的影响。《诗解》也很少引用大段文字注释诗中的典故、语汇,碰到需要注释的典故,只是简单地说“某某事”。如卷一《寄吴明卿兼简徐子与》“舍人殊有凤凰毛”,注“凤凰毛”仅云:“谢超宗事。”此指《南齐书•谢超宗传》中,宋孝武帝称“超宗殊有凤毛”之语①按洪迈:《容斋随笔》卷四载:“宋孝武嗟赏谢凤之子超宗曰:‘殊有凤毛。’今人以子为凤毛,多谓出此。按《世说》,王劭风姿似其父导,桓温曰:‘大奴固自有凤毛。’其事在前,与此不同。”桓温语见《世说新语•容止篇》。。“时添一字,跃如言下”也是《绝句解》的特色,《诗解》注诗时也在句中或两句之间添字,以便阅读。如卷一《集徐子舆席上因怀梁公实》“岭南梅树春【应】堪折,【连下读】赠我宁无驿使还【乎】。”方括号中的字都是所添之字,主要是虚词和语气词,用于连接诗语,使意脉更加通畅,应与日本的汉文训读有关。
除此之外,在诗歌注释方法上,日本的明七子诗集注本还提出了“意解”或“意悟”之说。宫濑龙门《明李王七言律解》在疏通诗歌中的所有典故及阅读障碍的同时,提出很多好诗只可意会,而不能用语言解说。如卷上评《吴明卿自建宁移邵武有寄》“五马忽惊龙渚气,双轓犹画幔亭云”云:“妙语可意悟,不可解说。”这里的“意悟”,即意会之意。与之类似的是,宇野明霞《嘉靖七子近体集》也提出诗歌的“意解”与“辞解”(或“言解”)问题,卷二《答元美吴门邂逅于鳞有赠》“飞龙忽报干将合,老骥还惊匹练开。共向风云论二子,谁知天地此徘徊”,注云:“可以意解,不可以辞解。”“‘中原二子’亦公之常言,谓己与元美。‘天地’字妙,然亦不可言解也。”所谓“意解”,即通过意脉来理解,与“意会”意同;“辞解”,即从字面去解释。“意解”与宫濑龙门《明李王七言律解》所谓的“意悟”之说有相似之处。
在解说诗意时,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还喜欢分段解诗,这是室町时代以来的传统,也是中国明清时代解诗常用的方法。日本中世注本对中国诗歌分段解释以瑞溪周凤的苏诗注本《坡诗脞说》最为典型,此书的特色就是对苏诗每首诗都分段解之,略举一例。《坡诗脞说》卷四注《芙蓉城并序》云:“此篇七段。起句以下二句一段,‘珠帘’以下六句一段,‘天门’以下四句一段,‘因过’以下六句一段,‘仙宫’以下七句一段。‘蘧蘧’以下六句一段,‘此生’以下六句一段。”因诗句较长,乃根据诗歌意脉将诗歌分为若干段落,逐段疏解,这样较能看出诗意的演进。此种分段解诗的方式与这些文献乃“抄物”的性质相关,“抄物”很大一部分是当时学者、僧人讲读文献的记录,为了讲授的方便或需要,在讲解中进行分段也是必要的手段。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彼时的一些中国文集注本也采用了这种解诗方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津阪东阳编注的《古诗大观》,此书对《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两首长诗进行了注解,东阳在《孔雀东南飞》篇末云:“凡读长诗,须知解数,语曰:‘能理乱丝,始可读诗。’谓明解数也。盖大篇段落必多妙绪,全每段自作提结,又段段相联络,读者细心玩之,乃知其妙矣。若囫囵读去,不分解数,则条理相紊,何以得要领耶?”《孔雀东南飞》比较长,东阳称之为“古今第一首长诗”(《古诗大观题识》),故东阳将《孔雀东南飞》分成若干段落,然后概括每段之诗意,并发表意见。如“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出门登车去,泪落百余行”,东阳注云:“已上二十句,上半叙拜母告别,婉而成章,妙不容口。下半叙与小姑惜别,悲怆之中,复极温厚,风人之旨,尤微婉矣。末梢二句,并总收之,余哀悠悠,可会作法。”此段文字总结了这二十句的意脉,评述了此诗的叙事艺术,并两次指出其“婉”的特色,认为其有所谓“风人之旨”,并有《诗经》“温柔敦厚”的特质,这也是对《孔雀东南飞》的肯定,“可会作法”则指出其在诗歌写作上的方法意义。
总体而言,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的注释比较朴实,以字句训诂,典故考释为主,体现出实证的倾向,但亦有部分注本呈现“讽寓性阐释”,注重诗意的发挥、推衍。同时,这些注本也使用“事唯标用某事”及“时添一字”的方法,追求简洁,注重“意解”或“意悟”之说。
三、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的学术价值
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一些在中国失传的中国诗集古注就保存在这些汉籍之中。如南宋初年赵次公所作的东坡诗注,日本苏诗古注本《四河入海》中保存了旧题王十朋所编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未见的大量赵次公注。通过《四河入海》,可以窥见赵次公注的原貌,即赵注不但有注文,而且还有赵次公唱和苏轼的诗,这些“和苏诗”更有赵次公之子的注释①参见王连旺:《赵次公“和苏诗”辑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7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苏诗赵次公注的辑佚与整理新考》,《古典文献研究》第22辑上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再如,宋人施元之、顾禧、施宿所著的《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一向被视为苏诗宋注中的精品,但目前仅存三十六卷,仍有六卷散佚不存,但幸运的是,在日本还保存着卷首施宿所撰的《东坡先生年谱》古钞本,日本坡诗古注本《翰苑遗芳》中还保存着施顾注失传六卷的佚文②参见卞东波:《域外汉籍与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之研究》,《文学遗产》2017年第6期。。故要研究苏轼诗的赵次公注、施顾注,必须要利用日本的古注本。
此外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还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文献。宋末何新之所编的《诗林万选》是一部大型的唐宋诗总集,此书清初时仍存,厉鹗(1692-1752)所编的《宋诗纪事》引录了《诗林万选》中80首宋人之诗,但该书所选的唐诗部分不详。不过,《三体诗》的日本古注本松永昌易(1619-1680)《首书三体诗》引录了两条关于《诗林万选》的材料:
或云,已下至《秋思》皆杜牧诗也。然《遗响》载此诗于雍陶诗部,“桥西”作“桥边”,余同。“澧”作“漕”。又云,以此诗为杜牧诗无实据,不足取之。《诗林万选》亦作雍陶诗也,评云:“平淡体,淡中有味。”“澧”作“漕”。(卷之一上雍陶《城西访友人别墅》首书)
或说云,本集题作《旅舍遇雨》,《诗林万选》:“推敲体,追琢字眼。”题作《旅馆遇春》,“色”作“气”,“愁”作“秋”。(卷之一上杜荀鹤《旅怀》首书)
松永昌易生活的时代略早于厉鹗,可能在明清之际此书犹存于世,并且东传到了日本,并为松永昌易所见。《首书三体诗》末有昌易跋云:“余窃历观文囿,泛览辞林。”又时人称昌易为“近代经学博赡之儒宗”(《尺五堂恭俭先生行状》,载《尺五先生全集》卷首)。可见,昌易学问以“博赡”为特色,他很有可能见过传到日本的《诗林万选》。从《首书三体诗》保存的《诗林万选》唐诗部分佚文来看,此书和宋元之际的其他诗歌选本一样是带有评点的,并将诗歌分为“平淡体”“推敲体”等类,而且所录的文本与传世文献多有差异。
学者曾对南宋中后期成书的古文总集《古文标准》做过研究,从《古文集成》中辑得30余条佚文③参见侯体健:《南宋评点选本〈古文标准〉考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关于《诗林万选》《古文标准》的佚文,参考了卞东波、石立善主编:《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丛刊》中李心畅所撰的《首书三体诗》《新增评注古文真宝后集》解题。,但在江户时代《古文真宝后集》的评注本中还保存着一些《古文标准》的佚文。如山崎保春(生卒年不详)注、生驹登(生卒年不详)增注的《新增评注古文真宝后集》卷二注《进学解》云:“《古文标准》题注据本传云:‘公再为国子博士,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奇其才,改吏部郎中、史官撰修,时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④毛利琥珀(生卒年不详)编著的《古文真宝后集合解评林》卷上注《爱莲说》云:“《古文标准》注云:‘濂溪先生道学宗师,其爱莲华取其有君子之德,异乎众人之爱也。学者玩味斯文,当悟其旨。’”(此注亦见《新增评注古文真宝后集》)本条亦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刊孤本《新编诸儒批点古今文章正印》后集卷一,可以和中国文献相印证,可见日本注本所引的《古文标准》应有一定的文献依据。本条《古文标准》未见中国传世文献,可资补遗。
佚名所作的《鳌头白云诗集》是元代诗僧释英《白云集》的日本注本,其所引文献皆为清代以前的文献,则其成书很可能在室町末或江户初,其中也引用了一些在中国本土失传的文献。如卷一《秋夜曲》“鸳鸯屏冷初日红”注引颜潜庵《鸳鸯诗》:“采采珍禽世罕俦,天生匹耦得风流。用心不改同相守,翠翼相辉每共游。霜瓦对眠金殿晓,种沙双点玉田秋。此生莫遣分离别,交颈成欢到白头。”卷二《赠郑炳文》“两鬓星星小幅巾”注引颜服膺诗“一幅乌纱折角偏”。按:颜服膺,号潜庵,明代道士,号安仁冲虚山道士,着有《咏物诗》六卷。事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三《羽士张宇初小传》。朱彝尊又云,其集“访之未得”。《吴诗集览》卷二七下、《鸽经》、《绘事琐言》卷六、《渊鉴类函》卷三六五、《斩鬼传》卷三尝引其诗,皆为咏物诗。《鳌头白云诗集》所引皆为咏物之作,当是《咏物诗》之逸诗。又《鳌头白云诗集》卷一《过瓜洲》“春色自蔷薇”注引丘濬诗“红刺青茎巧样妆,连春接夏正芬芳。新含丽色县高架,密布清阴覆小堂。浓似凭露染,轻如燕燕逐飞翔。几回白昼看明媚,疑是买臣归故乡”。按此诗前四句见清恽格(1633-1690)《瓯香馆集》卷三《谁撮》,但丘濬(1421-1495)乃明人,不可能袭用恽格之诗,恽格为清代书法家,可能见过丘濬此诗并写成书法,后人误以为恽诗。则《鳌头白云诗集》所引文献也还有助于辨伪考证。
除了有助于辑佚之外,在诗歌注释上,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亦有较大的价值。很多中国没有注本的唐宋诗集,在日本却有详细的古注本,如唐代的寒山诗,中国古代没有注本传世,但在日本却有四部汉文古注本。宋代诗僧雪窦重显的《祖英集》在中国亦无注本,但在日本却有《冠注祖英集》;释惠洪的《石门文字禅》在中国无注,但有日本廓门贯彻的《注石门文字禅》;元代诗僧释英的《白云集》在中国无注,但日本有佚名所作的《鳌头白云诗集》。再如,南宋末年的江湖诗人群体在中国研究不够充分,收录江湖诗人作品的《江湖集》也散佚不全,不过笔者在日本汉籍中发现数量颇多的江湖诗人佚诗,而且日本汉籍《中兴禅林风月集注》《锦绣段详注》《续锦绣段抄》中还有对江湖诗人诗歌的注释,这是东亚最早对江湖诗人的研究①参见卞东波:《域外汉籍所见南宋江湖诗人新资料及其价值》,《古典文献研究》第16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
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集无中国古代注本传世,今有佟培基先生之《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等注本,然江户时代的唐诗注本,如东褧《唐诗正声笺注》中的孟诗之注颇有可资考证之处,如卷四孟浩然《听郑五愔弹琴》“半酣下衫袖”句下注:“庾信诗:‘衫袖偏宜短。’”可知“衫袖”之用法出自庾信。高适之诗,中国古代亦无注本,今有孙钦善先生的《高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等注本,东褧《唐诗正声笺注》亦有可补孙先生校注者。如卷五高适《蓟门•黯黯长城外》“胡骑虽凭陵”注云:“《左传》:‘凭陵我城郭。’”本处“凭陵”之出处可补孙先生的校注。又同卷《东平路作•清旷凉夜月》“清旷凉夜月”,东褧注云:“谢灵运诗:‘清旷招远风。’《月赋》:‘凉夜自凄。’”则知“清旷”“凉月”皆出自陈郡谢氏之手,亦可补孙注。又李颀之诗古代无注本,今有王锡九先生所著的《李颀诗歌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东褧《唐诗正声笺注》卷四李颀《题綦毋校书田居》“生事本渔钓”注云:“潘岳《闲居赋》:‘池沼足以渔钓。’”“渔钓”等语出处可补王先生之校注。
即使中国古代有注的古代诗集,日本古注本亦有补遗之功。杜甫的诗集在中国有所谓“千家注杜”之说,近年来又出版了新注本,如萧涤非先生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下称萧注)、谢思炜先生的《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萧注备举诸家之说,可谓博观约取的集成之作。其对江户时代杜律注本亦间有援引,但仍有可补充之处,略举一例:萧注引津阪东阳《杜律详解》注《奉寄别马巴州》中“春湖”为洞庭,大典显常《杜律发挥》卷上则云:“旧注以‘春湖’为洞庭,洞庭去荆南又远,非刺史越境能至之地。若以为罢官事,则骊驹、玉珂又不妥当,故不可从。但不知梓阆间有湖,姑待后考。”这里从地理上指出“旧注”之谬,可备一说。
陆游之诗在中国古代没有注本传世,今有钱仲联先生的《剑南诗稿校注》(下简称钱注),但在二百多年前,日本即有市河宽斋的《陆诗考实》《陆诗意注》(下简称《意注》)二注。虽然其成书约在二百年前,但宽斋之注仍有可以补充钱注之处。今略举数例:《意注》卷三《阻风》“吾道无淹速,风伯非所尤”注云:“韩愈《讼风伯》文:‘我知其端兮,风伯是尤。’”钱注引《风俗通义•风伯》《独断》注“风伯”,但未注“风伯尤”之出典,当出自韩愈文。《意注》卷四《月下小酌》“传杯瓮面清”,钱注未释“瓮面”之意,《意注》云:“《鸿书要录》:‘江东云“缸面”,犹河北称“瓮头”,谓初熟酒也。’”《鸿书要录》已不传,此处当转引自清人陈元龙所著《格致镜原》卷二十二。不过,上引同样的话已经见于宋代的文献,如朱长文《墨池编》卷四已有此语。《意注》卷五《夜闻姑恶》题下注云:“范成大《姑恶》诗序:‘姑恶,水禽,以其声得名。世传姑虐其妇,妇死所化。’”钱注未注“姑恶”之意,可补①参见李晓田:《市河宽斋〈陆诗意注〉考论》(《新宋学》第6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以及笔者指导的硕士论文《日本江户时代的陆诗选本注本研究》下辑第三章(南京大学文学院,2018年)。笔者在此基础又有所考证。。
除此之外,这些日本古注本还有诗歌接受史的价值。《孔雀东南飞》是中国第一首长篇民间叙事诗,历来评价甚高,然中国古代无注,在日本则有津阪东阳《古诗大观》中之注,津阪东阳在该书题识中称《孔雀东南飞》云:
古今第一首长诗,其妙殆神工矣。盖格局端严,风调圆转,虚实互用,整散错出,节节相生,多多益办,顿错起伏,变化不测,波澜开阖,神脉掣动。使读者亶亶而不厌,学者作叙事词万所当钻仰也。
这里津阪东阳指出《孔雀东南飞》“格局端严”,即在结构布局上严整平衡;在叙事技巧上“虚实互用,整散错出,节节相生”,能够巧妙地处理好写作中虚与实、整与散的关系,从而能够层层推进,最终形成“变化不测,波澜开阖,神脉掣动”的艺术效果。这段评论颇有见地,既指出了《孔雀东南飞》的艺术成就,又指出其叙事之法是应当努力“钻仰”者,即道出了其方法论上的意义。
江户时代中期受到蘐园派的影响,彼时涌现大量的唐诗注本,这些注本除了注解诗句之外,亦间有评论,这些评论可视为江户时代唐诗接受的绝佳资料。略举一例,杜甫《饮中八仙歌》是千古名作,中国的历代评论主要关注其艺术手法的“创格”②如《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一云:“古无此体。”王嗣奭:《杜臆》卷一:“此创格。”夏力恕:《杜诗增注》卷一:“此篇为少陵创格。”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卷六:“格法古未曾有。”,而对该诗的思想内涵论之较少,日本杜诗注本入江南溟《唐诗句解•七言古》解此诗云:
此篇体裁新奇,前无古人,甚有深义,然《训解》云:“此赋八人之豪饮也。”肤浅不可从。杜甫窃以为八仙各大器而不擢用焉,是以豪放泆荡,逃俗耽酒,葆光自晦,其志嘐嘐,不遇尧舜之世为憾而已。杜甫窃感伤焉,为天下哀之,因题“饮中八仙”以寓意于其中。
“训解”指明人所作的《唐诗训解》,所言颇为皮相。南溟先指出此诗“体裁新奇”,继而直指此诗“甚有深义”。其深义何在?南溟有剀切的解释。杜甫诗中所写的八人,皆怀有“大器”,但不能为国家所用,只能以“豪放泆荡,逃俗耽酒”作为掩饰,其实是一种“葆光自晦”之举。杜甫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够从这些人的放荡之举中看他们有志不获骋的苦闷,为他们“不遇尧舜之世”而感到遗憾。这也是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对当时病态社会的深切观察,南溟的评论与当代学者所论颇相合③参见程千帆:《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读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载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四、结语
陈琏《注唐诗三体序》云:“选诗固难,注诗尤难,非学识大过于人,焉能及此哉!”(《琴轩集》卷六)杭世骏《李太白集辑注序》也说到同样的意思:
作者不易,笺疏家尤难,何也?作者以才为主,而辅之以学,兴到笔随,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纵横曼衍以极其所至,不必沾沾獭祭也。为之笺与疏者,必语语核其指归而意象乃明,必字字还其根据而证佐乃确,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于作者之卷轴,而后可以从事焉,空陋者固不足以与乎,此粗疏者尤未可以轻试也。(《道古堂文集》卷八)
笺注之学需要“学识大过于人”,有充足的学问储备,方能做到“语语必核其指归”,“字字还其根据”。诗歌注释又是笺注之学的难中之难,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著录施元之、顾禧、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云:
陆放翁为作序,颇言注之难,盖其一时事实,既非亲见,又无故老传闻,有不能尽知者。噫,岂独坡诗也哉!注杜诗者非不多,往往穿凿傅会,皆臆决之过也。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91-592页。
可见诗歌注释不但要通四部之学,而且要知“一时事实”,即作者写作时的当代时事或历史语境,否则只能是“释事而忘意”;既要通“古典”,亦要通“今典”。陈振孙也提到失败的诗注往往“穿凿傅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臆决之过”。宋人许尹称赞任渊为黄庭坚、陈师道诗集所作之注云:“三江任君子渊,博极群书,尚友古人。暇日遂以二家诗为之注解,且为原本立意始末,以晓学者。非若世之笺训,但能标题出处而已也。”②黄庭坚撰,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庭坚诗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卷首第2页。坡诗难注,黄、陈诗亦难注,任渊不但勇于给两家作注,而且至今都予以好评,其原因就在于任氏能够“博极群书”,有充足的学问储备;亦能“尚友古人”,对古人妙意可以细心体会,从而在“标题出处”之外,注出诗歌的深意。
反观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水平或有差参,但大部分都做到了事必有证,援据有理。这些古注本虽作于数百年前,但其价值并没有随岁月而流逝。我们常常感慨近代日本汉学之发达,日本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之深入,其实近代以降的日本汉学是建立在传统汉学基础之上的。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反映了早期日本汉学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历来没有注本的中国文集,这些日本古注本无疑有益于我们理解这些文本;而有注的中国文集,日本之注亦多有可资考证及补充之处。同时,这批文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域外传播与接受的宝贵史料。